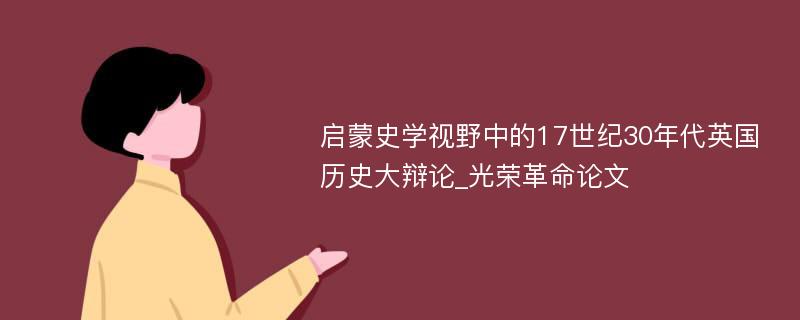
启蒙史学视野下的1730年代英国历史大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史学论文,视野论文,年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730年9月5日至1731年5月22日,托利党的领军人物之一博林布鲁克① 在周刊杂志《匠人》(The Craftsman)上以书信的形式连续发表了24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英国历史的基本演变过程及其性质的认识和理解、并对英国历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解释。这些文章后来被汇集成书,以《英国史论》② 为书名单独出版,成为博林布鲁克的主要历史著作③。博林布鲁克的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他涉足历史研究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引发了一场历时5年之久的关于英国历史的大论战。这场历史大论战不仅直接影响着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辉格党与托利党这两大政党的势力消长和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且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方法上都对此后英国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英国的国史研究产生了具体而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史家在研究博林布鲁克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会提到这次大论战,有些学者也曾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或者论述过这次历史大论战与18世纪20—30年代英国党派政治发展的关系、或者着重探讨它对大卫·休谟的英国史著述的影响。④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史学界尚未有人就这场历史大论战对后来英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展开过专门的系统研究,甚至在现有的英国史学史研究中仍未对它的真正意义予以应有的重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有意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已有积累⑤ 的基础上,具体地探讨一下这次历史大论战的“史学意义”,并希望能以此抛砖引玉,使这次大论战在英国史学史上享有其应有的地位。
一
这场历史大论战是由当时在野的反对派政治家们挑起、并在双方政治家们之间展开的,各自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鲜明的党派烙印。它完全是一种党派斗争的直接产物,是政治家和党派集团利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
1726年12月5日,此前不久才结束多年的法国流亡生活回到国内的博林布鲁克,伙同好友A.波普、J.斯威夫特等人创办了《匠人》杂志,纷纷撰文对当时沃尔波政府的内外政策展开了全面批判。沃尔波政府则通过收买或者提供赞助等手段,控制了《伦敦杂志》(The London Journal)、《每日报》(Daily Courant)和《自由不列颠人》(Free Briton)等报纸杂志⑥,并在D.迪福等人的带领下奋起反击。两大阵营之间由此而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经济大论战”。⑦ 当1730年博林布鲁克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对沃尔波政府展开批判的时候,沃尔波阵营同样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于是就形成了这场“历史大论战”。所以说,所谓的“历史大论战”实际上也就是此前“政治经济大论战”的继续。
在这场历史大论战中,出现了一种表面上看来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反对派托利党的斗士博林布鲁克将自己伪装在高尚的辉格主义大旗之下,而将不光彩的托利主义旗帜覆盖在辉格党的沃尔波身上。”⑧ 毫无疑问,这种场面的形成是由于大论战的挑起者博林布鲁克的杰作,因为是他首先运用17世纪英国议会派人士提出的所谓“祖传宪政”(ancient constitution)的理论向沃尔波政府发起攻击的。
所谓的“祖传宪政”理论,原是17世纪的议会派为了与日趋专制的王权相抗衡而提出来的一种夸大英国议会式宪政的历史传统的假说,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爱德华·科克爵士、威廉·普林以及阿尔杰农·悉尼等人。⑨ 博林布鲁克在其《英国史论》中全面继承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在用以解释英国历史的具体演变过程时对此有所发展。博林布鲁克的论点可以归纳如下:英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自由传统的国家,“自由的精神”自古以来就深深地扎根于英国人民的心中,始终是英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最高权力的集中代表;作为这种自由精神和自由传统的具体体现,英国人民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开始就已经建立了一种旨在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以议会为核心的、以权力的相互制衡为原则的“自由宪政”(free constitution),并逐步发展成为“祖传宪政”,英国人民就是在这个宪政制度的保护下享受着高度的民主和自由;与此同时,“祖传宪政”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虽然也曾多次遭受过来自外族入侵和“内讧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faction)的侵扰和破坏,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中断英国的这种自由传统;在英国历史上,凡是维护“祖传宪政”的国王和大臣都是“自由的精神”的代表,凡是损害“祖传宪政”的国王和大臣都是“内讧的精神”的代表,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贯串于英国历史的全过程,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祖传宪政”在这种对立和斗争中不断完善起来,而代表“内讧的精神”的坏国王和佞臣们则最终都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因而英国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就是“自由的精神”与“内讧的精神”持续不断地相互斗争的过程,这一本质始终没有改变。⑩
面对博林布鲁克的攻击,沃尔波阵营直接借助于由亨利·斯佩尔曼爵士和罗伯特·布雷迪所强调的“封建社会”理论(11) 进行了反驳。他们的论点如下:英国人民真正享受自由权利始于光荣革命,在此之前民众只有饱受国王和教俗两界贵族们压迫的“自由”;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民众只是一群粗野的未开化人,他们受到国王以及大小贵族们的统治,根本不可能享有制度所赋予的任何自由和权利;诺曼征服带来了欧洲大陆早已实行的封建制度,国王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国王、贵族和教会僧侣占有着全国的所有土地,民众只不过是他们的主人们可以随意处置的工具而已;无论是诺曼征服之前还是之后,国王都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议会本身就是国王的封臣们向国王应尽的封建义务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出席议会的成员都是国王指定的大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民众的代表得以参加议会始于亨利三世时期,但并不是受到国王的指派,而是个别野心勃勃的贵族(即西门·德·孟福尔伯爵)耍弄阴谋的结果,因为他企图借民众的力量来增加自己与国王进行对抗的实力;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民众的代表在议会里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与贵族及教会的代表相比始终都是微不足道的;英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封建时代,它既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也不同于现代;与英国人民享受着高度自由的现代相比,无论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英国人民都像奴隶一样处于国王和教俗贵族的专制统治之下。(12)
对于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谈论现实还是谈论历史,如何评价光荣革命的性质及其影响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场历史大论战的双方阵营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同样也反映出了各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实利益和立场。博林布鲁克的《英国史论》只写到1640年英国革命的前夜为止,并没有涉及对光荣革命的评价问题,这决不是他最终想得到的结果,因而他没有就此善罢甘休。从1733年10月27日至1734年2月2日、1734年9月9日至12月28日,博林布鲁克又分别在《匠人》杂志上以书信连载的方式发表了19篇系列文章,以英国“党派”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斗争为基本线索,概述了自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来直至18世纪30年代的英国历史过程,并着重对王朝复辟、王位继承排斥危机、光荣革命以及汉诺威王朝的建立和沃尔波内阁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开了讨论。后来这些文章以《论党派》(13) 为题单独整理成书,成为博林布鲁克生平最重要的政论和史论著作之一。就其中包含的丰富历史内容而言,此书实际上就是《英国史论》的续篇。在他看来,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光荣革命为止,是英国历史上党派政治最为盛行的时期,是“内讧的精神”绝对压制“自由的精神”、因而也是继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父子统治之后“祖传宪政”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英国又一次陷入了分裂和内战的危机之中;在这重要历史关头,光荣革命的成功重新唤起了英国人民心中的“自由的精神”、恢复了“祖传宪政”的基本原则,从而使得英国人民有幸避免了一次民族大灾难;然而,由于光荣革命之后掌握政权的各派政治势力并没有将原先达成的基本原则付诸实践,而是纷纷成为“内讧的精神”的实践者,使得英国再一次陷入了对立与分裂的状态;尤其是汉诺威王朝建立之后,以沃尔波为代表的辉格党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成了不断加剧这种分裂趋势的根源,并且已经使英国重新回到了没有自由的奴隶时代,因而英国人民必须聚集在“自由的精神”大旗之下奋起斗争,才能摆脱被奴役的命运。(14)
沃尔波阵营的反击也毫不示弱,他们反复强调的一种观点就是:光荣革命确立了以“混合政体”和权力制衡为核心内容的真正的自由宪政原则,英国人民享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才从此有了保障,而在光荣革命以前的任何时代里,英国人民都处在专制暴君的统治之下;光荣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英国宪政制度是以往任何制度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沃尔波政府是光荣革命达成的基本原则最忠实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因而现在是英国历史上最自由、最幸福的时期。(15)
二
由上可见,论战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党派利益,在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的相关解释上确实称得上针锋相对。然而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似乎却都接受并利用了对方党派曾在17世纪鼓吹过的历史理论框架,从而形成了各自的党派立场与各自的传统历史观的不一致性。(1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的这种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无论从动机上还是从手段上,双方都是在利用历史为各自的现实政治利益和理念服务,因而就使得这场“历史大论战”不仅成了一个党派斗争的现实舞台,而且也成了一个彻底地将历史研究政治化的典型,从而对18世纪英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尤其是对英国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史学发展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相对于此前基督教神学对欧洲史学的绝对干预而言,它代表着欧洲史学逐渐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趋势,是与欧洲史学的世俗化过程相适应的。这场历史大论战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性格不仅符合欧洲史学的这一总体发展趋势,而且也反映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历经动荡的英国国内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
英国社会在17世纪中后期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体制革命以后,又在所谓“光荣革命体制”下经过30多年的磨合与调整,到了18世纪20—30年代,以君主立宪为特征的英国近代社会政治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起来。如果说J.洛克在革命之后不久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对那场社会革命的原理及其合理性进行的辩护还仅仅是原则性的和逻辑性的,那么在经历了30多年的具体实践之后,如何从英国历史演变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该革命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就成了推动和实现那场革命的社会集团所必须面临的历史使命。
作为该社会集团的代言人,无论是博林布鲁克阵营还是沃尔波阵营,都在尝试着从不同的历史角度为那场革命、从而也是为本集团的所作所为进行历史的阐释。论战双方在赞扬光荣革命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反映出双方在肯定和维护那场社会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所取得的基本成果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共同利益;而双方在关于光荣革命前后英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性质的解释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则说明该社会集团内部两大党派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权益。由此可见,作为一次涉及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行为,这场历史大论战本身无疑是在实践着历史学所担负的社会功能。可以说,它是一种在党派对立尖锐突出的情况下、以较为特殊的方式回应社会需求的历史研究,并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内容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奠定了英国启蒙史学的基础,堪称为18世纪英国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历史研究一旦与现实的政治实用性相结合,势必会影响到研究活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而且这种客观性和公正性还会随着政治实用性的强弱而波动。作为激烈的党派斗争的舞台之一,那场历史大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实用性和党派情绪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使得当时以及后来英国的国史研究成了英国历史学中最敏感、最无法达成共识、以至于也是最难以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的领域。应该说历史大论战是在试图回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只是它并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个课题,甚至还因其过于强烈的党派色彩而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然而,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遗憾,才促使后来像大卫·休谟那样企图超越党派立场的国史研究的出现。(17)
三
尽管这次历史大论战参与双方的立场和观点针锋相对,然而他们在论述各自的英国历史构图时却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力图从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英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与性质,而且是以论述政治制度与人民的自由权利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的。博林布鲁克阵营通过考察所谓“祖传宪政”的起源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状况,不仅对历史上重要的人和事进行了或褒或贬的评价,也对英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性质提出了定性思考。沃尔波阵营运用前人关于“封建社会”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英国封建制度的起源以及与英国宪政的关系等历史影响的考察,对英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分期性”思考。论战双方的论述中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并不是等量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双方以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为视角考察历史的做法却为此后英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示范,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18)
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比昂多以其《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的历史,472—1440年》一书首倡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不仅开创了欧洲近代史学中“三阶段分期法”的基本模式,而且也对欧洲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思考。(19) 在这场英国历史大论战中,双方阵营都继承和发展了比昂多的这一学术遗产和研究思路,将它具体运用于英国历史研究,对国别史研究中的“通史式”把握和“分期式”考察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不仅为英国史研究、甚至也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国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途径。
关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定位,是欧洲近代史学中“三阶段分期法”得以立足的理论前提。同样,对英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的认可,也就是对英国历史进行“三阶段分期”的学术基础。尽管欧洲史学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展开真正的系统研究是在19世纪(20),尽管亨利·斯佩尔曼和罗伯特·布雷迪关于英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现和探讨尚不完善,然而这场历史大论战的参与双方却能够在利用他们二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共同揭示了英国历史的“三阶段分期”模式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的基本内容如下:11世纪的诺曼征服和15世纪都铎王朝的建立,使得英国社会的财产占有状况和英国政治权力的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从而也使得英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而英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可以分别以它们为界线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都铎王朝建立之后。
从诺曼征服到都铎王朝的建立,正是英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对它的历史定位认可与否正是英国历史分期中的关键所在。在沃尔波阵营看来,诺曼征服为英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使英国历史的进程从未开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发展到了有明确而完备的政治制度的时代;都铎王朝建立之后,国王和议会在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英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英国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1)
相对于沃尔波阵营的正面阐述而言,博林布鲁克阵营的论述则显得隐晦难懂。他们尽管不承认英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本质性”变化,却对诺曼征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都铎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出现的新局面表示了认同,只是采取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表述方式而已。在他们看来,前者是对“自由的精神”和“祖传宪政”的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开启了英国历史上“内讧的精神”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而后者却是对“自由的精神”和“祖传宪政”的空前规模的大恢复,使英国历史重新迎来了以“自由的精神”为主导的新时代。(22) 由此可见,博林布鲁克阵营不仅完全承认诺曼征服和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而且与沃尔波阵营一起构建了英国历史“三阶段分期”模式的基本框架。
另外,关于英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理论学说原先只是英国学术界个别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被赋予了强烈的“托利主义”党派意识的色彩。经过这次历史大论战之后,由于辉格派的沃尔波阵营给这一理论披上了官方化的外衣,从而极大地淡化了它原来的党派色彩,并促进了它作为一种历史知识的普及。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直接为开辟英国国史研究的新思路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
作为欧洲近代史学的杰出成果之一,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观念也始于比昂多。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观念并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直到18世纪下半叶,它才在爱德华·吉本的著作中得到了响应,并在浪漫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确立起来。(23) 实际上,在这场英国历史大论战中,双方阵营在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各自的理论解释的时候,不仅在“阶段性”考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分期,而且都对贯穿其中的“连续性”给予了充分的描述,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历史进步主义的倾向。
沃尔波阵营对英国历史的解释主要围绕着两条主要线索展开:一是英国的政治制度从不完善到完善、并逐渐达到完美的历史演变过程,二是英国人民的自由权利从无到有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他们看来,英国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野蛮蒙昧的古代社会逐渐走向文明开化的近代社会的前后相继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由低而高的进步趋势,而政治制度建设的状况就是衡量这种进步性的主要标准。他们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视为英国政治制度的初始阶段,虽然没有规范化的明确条文,但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已经存在,即作为统治者的国王和贵族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欺压人民,而人民则没有任何自由权利。诺曼征服之后,国王以欧洲大陆早已实行的封建制度为蓝本,在英国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在封建社会里,国王和贵族们的统治地位依旧,尤其是国王掌握的专制权力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英国社会毕竟开始有了规范化的政治秩序,从而脱离了野蛮蒙昧状态,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根本性转变。都铎王朝的建立,尽管并未改变原来的基本统治秩序,但是由于人民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国王不得不对政治机构进行某些调整、并增添某些新因素,从而使得英国的政治制度更加趋于完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人民开始拥有了某些权利,国王独揽大权而人民毫无权利的时代宣告结束,这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各种政治原则及其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使得英国的政治体制趋于完美,从而成为人民享有自由权利的根本保障,英国人民从此才真正开始充分地享受自由权利。在这里,“光荣革命”似乎可以被视为又一个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点。然而,沃尔波阵营的理论家们并没有顺着这种思路继续推论下去,而是将它看作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尤其是都铎王朝以来的英国政治制度不断演变的一个最完善的终点和英国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并根据自身党派利益的需要,在它与自己的统治之间建立起内在逻辑关系。由此看来,根据沃尔波阵营的历史解释,英国社会的历史运动是一个拥有明确的起始点和顶点的、呈直线型渐次向上发展的连续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孔多塞历史哲学体系的萌芽。(24)
相对于沃尔波阵营的直线型发展观,博林布鲁克阵营对英国历史的解释理论具有明显的环周形封闭性特征。他们为英国的历史发展设定了一个至善至美的起点,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深深地植根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人民心中的“自由的精神”和能够保障人民充分享受自由权利的“祖传宪政”。与此同时,他们又为“自由的精神”设定了一个对立的存在——“内讧的精神”,它时刻都在企图干扰人民对“自由的精神”的向往、破坏“祖传宪政”的正常运行,致使英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再出现倒退。“自由的精神”与“内讧的精神”的这种二元对立导致了它们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就是恢复还是破坏“祖传宪政”?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构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要内容,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幸福”时期(即人民能够享受自由权利)和“不幸”时期(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实际上都是它们二者相互斗争及其势力消长状况的具体体现。“光荣革命体制”的建立是“祖传宪政”的重建,是“自由的精神”战胜“内讧的精神”的结果,标志着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个“二元对立”的周期运动的终结。由此可见,在博林布鲁克阵营的历史解释中,英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一个有起点和终点的完整过程,只不过他们的这种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或者说二者尽管表现形式不同,而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后者只不过是对前者的回归。与此同时,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明显的进步趋势,只是这种进步性仅仅存在于两个“端点”之间。博林布鲁克阵营的这种历史观既有以前基督教神学史观的影子,(25) 也有同时代理性主义史观的要素。(26) 然而,它与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没有神的参与以及从世俗的眼光和党派政治的现实需要出发对英国历史现象所作的具体描述和考察;而它对理性主义史观的最大超越,则在于其丰富的历史发展连续性思想和明确的分期观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博林布鲁克阵营对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社会现状的评价和定位来看, “光荣革命体制”的建立似乎也可以被视为英国历史发展又一次周期运动的新起点,这也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党派利益。不过,博林布鲁克阵营的理论家们并未跨出这一步。他们将历史服务于现实政治,在具体的历史叙述中掺入了不少对现实的影射,却严格区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线,不把二者简单地混为一谈,表现了一定的学术品位。
综上所述,这场历史大论战的双方根据各自党派的现实利益、以“三阶段分期”的模式和历史连续性观念考察本国的历史,这种作法不仅使它在党派斗争的形式下实践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而且为18世纪英国的国史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使得这场论战具备了近代史学的基本特质,从而确立了它作为英国启蒙史学的先驱者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论战双方的历史解释中所包含的这些超越同时代欧洲启蒙史学的因素,既从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决定了此后英国启蒙史学的独特性,也切实地丰富了欧洲启蒙史学,为进一步深刻认识欧洲启蒙史学的多样性提供了启示。
注释:
① Henry St.John,1st Viscount Bolingbroke,1678-1751年。
② Henry St.John Bolingbroke,“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ngland”,1730-1731,in The Works of the Late Right Honorable Henry St.John,Lord Viscount Bolingbroke,7 Vols.Vol.I .
③ Issac Kramnick,“Augustan Politics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Past,1730-1735.”History And Theory,Vol,Ⅵ,1967,pp.33-56 ; 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177-187.
④ 大野精三郎「1730年代の歷史論争とヒユ一ム『ィギリス史』」(『一橋論叢』第70卷第4号);大野精三郎『歷史家ヒユ一ムとその社会哲学』(岩波書店,1977年),第147—162页;舟橋喜惠『ヒユ一ムと人間の哲学』(勁草書房,1985年),第196—254页。
⑤ 笔者在拙文「D·ヒユ一ムの『ィギリス史』につぃて」(『史学研究』第178号,1988年,第43—63页)中也曾简要地论及这次历史大论战对休谟历史研究的影响。
⑥ 它们于1735年合并为《每日公报》(The Daily Gazetteer)。
⑦ 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PP.17-24;大野精三朗『歷史家ヒユ一ムとその社会哲学』第32—38页。另外,关于《匠人》杂志的发行情况还可以参见王晴佳、陈兼主编:《中西历史论辩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脚注。
⑧ Issac Kramnick,“Augustan Politics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Past,1730-35.”History And Theory,Vol.Ⅵ,1967,p.33.
⑨ 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1987,Ch.2,3,7.John Kenyon,The History Me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3,pp.20-25.
⑩ 大野精三郎『歷史家ヒユ一ムとその社会哲学』,第148—150页;Issac Kramnick,“Augustan Politics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Past,1730-35.” History And Theory,Vol.Ⅵ,1967,pp.38-40; 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pp.24-26; 王晴佳《博林布鲁克的历史研究》(前引《中西历史论辩集》,第242—243页);拙文「ボ一リングブルックの歷史觀に関する一考察」(『西洋史学報』第12期,1986年,第23—29页)。
(11) 详见J.G.A.Pocock,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Ch.4,5,8.
(12) 大野精三郎『歷史家ヒユ一ムとその社会哲学』,第151—153页;Issac Kramnick,“Augustan Politics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Past,1730-35.”History And Theory,Vol.Ⅵ,1967,pp.40-46; 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pp.127-136.
(13) Henry St.John Bolingbroke,“A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1733-34,in The Works of the late Right Honorable Henry St.John,Lord Viscount Bolingbroke,7 Vols.,Vol.Ⅱ.
(14) 大野精三郎『歷史家ヒユ一ムとその社会哲学』,第36—37页和第153—154页;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pp.26-30;拙文「ボ一リングブルックの歷史觀に関する一考察」(前引『西洋史学報』,第30—31页)。
(15) 大野精三郎『歷史家ヒユ一ムとその社会哲学』,第37—38页和第152—154页;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pp.130-131; Issac Kramnick,“Augustan Politics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Past,1730-35.”History And Theory,Vol.Ⅵ,1967,p.41.
(16) 实际上博林布鲁克在论战中鼓吹的“祖传宪政”史观与17世纪议会派理论家倡导的“祖传宪政”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关论述请参阅前引拙文「ボ一リングブルックの歷史觀に関する一考察」(『西洋史学報』,第31—32页)。另外,沃尔波阵营虽然利用了托利派历史学家R·布雷迪关于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成果,但是双方的基本立场和所要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不同的,可参阅Issac Kramnick,“Augustan Politics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Past,1730-35.”History and Theory,Vol.Ⅵ,1967,pp.37-38.
(17) 拙文「D·ヒユ一ムの『ィギリス史』につぃて」(『史学研究』第178号,1988年,第43—63页)。
(18) 此后的大卫·休谟、威廉·罗伯森、约翰·米勒、爱德华·吉本乃至于19世纪的亨利·哈兰等人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19) 关于比昂多《罗马帝国衰落以后的历史,472—144年》的详情,可参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上卷,第705—708页;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0—91页;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107页。
(20) 参见前引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51—53章。
(21) 大野精三郎『歷史家ヒユ一ムとその社会哲学』,第37—38页和第152—154页;Issac Kramnick,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pp.130-131; Issac Kramnick,“Augustan Politics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Past,1730-35.”History and Theory,Vol.Ⅵ,1967,p.41.
(22) 拙文「ボ一リングブルックの歷史觀に関する一考察」(『西洋史学報』,第30—31页)。
(23) 参见前引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705—708页;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106—107页。
(24) 参见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尤其是其《绪论》部分。
(25) 关于基督教神学史观可参见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2—64页;前引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68—75页和第88—92页;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5—60页。
(26) 关于理性主义史学(以及启蒙史学)可参见前引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133—165页;前引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第9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