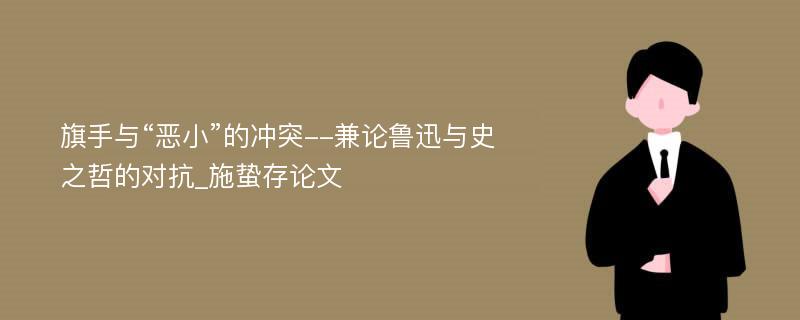
旗手与“恶少”的冲突——也谈鲁迅与施蛰存的交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恶少论文,旗手论文,也谈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733(2004)01-0027-05
鲁迅与施蛰存不是同辈人,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施蛰存还在塾师那儿发蒙。在三十年代风雨如磐的搏击中,鲁迅深知环境的阴险与丑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实际上,他一直没有把“锋”对准施蛰存。鲁迅认为,施蛰存“还不配”成为自己的刀锋所瞄准的对象,因此,开始时,鲁迅只是在几次论述中“顺手一枪”捎带批评了稚嫩的施蛰存。在鲁迅看来,三十年代,复古逆流已然成不了气候,只是痛惜缺少辫子和穿洋服的青年人不应有“骸骨的迷恋”。而施蛰存意气用事,先借鲁迅和鲁迅的笔名“丰之余”打哑语,后又改用所谓推荐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篇和《伪自由书》等来刺伤鲁迅,鲁迅才接二连三地反击,直到揭出“洋场恶少”的真相。总的看来,在鲁迅的论敌中,施蛰存并不是鲁迅论争和交锋的主要对象。然而,近些年来,随着“重评鲁迅”、“扫荡名人”的风气四起,这段公案也一再被翻掘出来,成为许多人作文的材料。有些文章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鲁迅太“刻毒”、对施蛰存“误会太深”,要么认为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或者认为施蛰存多么无辜,连五十年代“反右”和“文革”中受到的伤害,都要算到鲁迅的头上。这种借施蛰存贬低鲁迅的做法,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来讨论一下这场论争的基本情况。
近几年讨论鲁迅与施蛰存的冲突的文章主要有:刘凌《施蛰存与鲁迅的一段交往》[1],朱严夫《施蛰存与鲁迅的两次论争》[2],杨迎平《施蛰存同鲁迅的交往与交锋》[3],另外,房向东在其著作《鲁迅和他“骂”过的人》中,也有一篇《读古书·“新生党”及“洋场恶少”——鲁迅与施蛰存》有所论及。本文主要以杨迎平(以下简称“杨文”)和房向东的文章(简称“房文”)提出看法,以便澄清鲁迅与施蛰存冲突的真相。
“知人论世”是鲁迅一贯主张的方法,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应该把问题放回那个时代。我们要辨清冲突的缘起、经过,要对冲突的性质给予界定,要弄清楚鲁迅为什么就《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抓住施蛰存不放,施蛰存到底受了什么委屈。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鲁迅或施蛰存,当然也完全可以在辨明事实真相后,“跳出五行外”,给予历史人物以公正的评价。
这里,我要对本文的题目有所说明。“洋场恶少”是鲁迅当年给施蛰存的称呼,今天来看,鲁迅先生确实言重了,但顾念到当时鲁迅在险恶处境中的客观斗争形势,加上又是出现在杂文中的名词,也就可以理解了。我在这里借用这个称呼,决没有对施蛰存先生任何不恭的意思。
一
这次论争的起因并不复杂,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论争过程。
1933年9月,《大晚报》编辑给施蛰存寄了一张表格,要求填注:(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介绍给青年的书。在要介绍给青年的书中,施蛰存填了《庄子》、《文选》并附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认为:“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推荐这两部书,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扩大一点字汇”。
鲁迅于1933年10月1日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10月6日发表在《申报·自由谈》。(收入《准风月谈》时题目为《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在这篇文章里,施蛰存推荐《庄子》与《文选》仅仅是鲁迅写这篇杂文的一点因由,鲁迅的用意在于“感旧”,在于防止年轻人“骸骨的迷恋”,在于探讨民族的“立足”、“生存竞争”,在于告诫人们:复古不光是遗老遗少,还有“新党”,关注我们的生存,实在比读《庄子》和《文选》重要。
于是,施蛰存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发表于10月8日《申报·自由谈》上,为自己推荐《庄子》与《文选》作解释。他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但要自己“酿造”。接着,他以鲁迅举例,“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并对鲁迅先生讽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版的信封等表示不满。
10月12日,鲁迅又以“丰之余”的笔名写了《“感旧”以后》,以(上)、(下)两篇分别于10月15日和16日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鲁迅先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接着,鲁迅表示不同意用瓶和酒来比喻“文学修养”,告诫施蛰存既然考官不能以词取士,当教员和编辑当然也不能以《庄子》和《文选》劝青年。对施蛰存举出“鲁迅先生”的文章与《庄子》的关系做例,“丰之余”认为“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糊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最后,鲁迅说:“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至此,论争还在围绕推荐《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进行。论争恶化是由施蛰存10月19日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引起的。他说:“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篇及《伪自由书》”。文章结尾,施蛰存不希望报纸讨论这个问题。“丰之余”终于被惹怒了,他于10月20日写了《扑空》。先揭露“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接着指出施蛰存的攻击“有些语无伦次了,好象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这是一计重拳。施蛰存就此已无力还击,“洋场恶少”的帽子戴了一生。这之后他虽又写了《突围》等篇,并在多种场合也“捎带一枪”地进行反击,但怎么都掩不住他的失败。鲁迅后来还在《反刍》、《中国文与中国人》、《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篇以及《准风月谈·后记》中,顺便对此进行讥讽。
二
施蛰存与鲁迅的这次论争,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论争?这是首先应该分辨清楚的。关于这个问题,刘凌和朱严夫的文章只介绍了论争的经过和施蛰存与鲁迅的交往,对论争的性质等则存而不论。房向东和杨迎平都对这次论争进行了分析。
房向东开始认为:两人都没有错。他说:“施蛰存曾被鲁迅‘骂’为‘洋场恶少’,今天看来似乎言重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容。无非是关于读古书问题的看法有异。”他在回顾“丰之余”的文章后又说:“鲁迅所举的例子,似乎给人小题大做之嫌。”“我以为,读一点《庄子》作一点古诗词和古文,与复古并不是一回事。况且,古的形式,也可以装进新的内涵,鲁迅早期鼓吹新观念的文章,如《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用的也是文言;鲁迅也作了许多律诗,都是证明。到了后来,钱钟书用文言文作《管锥篇》等,大家只觉得这是新文化中的一个景观,并不觉得‘复古’了。”这些论证,似乎持论公正。最后,“房文”认为,施蛰存是针对文学青年讲的,鲁迅是针对不作文的广大青年说的,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言下之意是鲁迅曲解了施蛰存的原意,制造事端,挑起争论。
杨迎平的《施蛰存同鲁迅的交往与交锋》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鲁迅研究”专栏。该文首先列举了“施蛰存作为晚辈,对鲁迅的尊敬是由来已久的。”接着介绍论争经过,认为“鲁迅对此事有点小题大做,上纲上线”。认为施蛰存年轻气盛,意气用事,“以牙还牙”“讽刺挖苦鲁迅”,“再次刺伤鲁迅”。进而分析“在这件事上,双方都有责任”,“鲁迅不一定全对,施蛰存不一定全错”。最后作者得出结论:“通过施蛰存与鲁迅的交锋,特别是看到施蛰存斗胆与鲁迅交锋和论争,使我们看到了30年代文坛活跃、自由的气氛,正因为如此,30年代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时期。”
在这里,我们要先回答这几位作者对鲁迅和施蛰存“各打五十大板”的问题。在这次论争中,施蛰存始终以低调出场,用委屈的口吻参与争论,似乎他是无辜的,就因为推荐了两本书,惹了这么一场争论,最后还落得“以此取悦当道”,向当局献策,成了“洋场恶少”!这么一个尊敬鲁迅的谦谦君子,被鲁迅一而再,再而三地痛击,“洋场恶少”的帽子甚至在“反右”和“文革”中再次让施先生遭难,这似乎就更值得让人们同情。然而,事实决非如此。施蛰存在致《大晚报》主编崔万秋的信《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争》中,将该报要发动读者讨论这件事情喻为弧光灯下的拳击,表示自己不愿出场向鲁迅挑战,一脸无辜。然而,鲁迅立即指出,在弧光灯下,甚至在弧光灯启动前的黑暗里,施蛰存早已挥了几记老拳,然后“飘然远引”“遁入无形”,让鲁迅在弧光灯下独施拳脚。
在这次论争中,我们看不出施蛰存对鲁迅“由来已久”的敬意,看到的倒是阴损刻毒的攻击。施蛰存一开始就知道“丰之余”是鲁迅,在他第一篇回答鲁迅的批评文章《<庄子>与<文选>》中,他就装聋作哑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在致崔万秋的信中,他更是别有用心地要改推荐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篇和《伪自由书》,他要让读者明白:施蛰存是没有推荐鲁迅的书才得罪鲁迅,鲁迅这才与他过不去。这真是很阴很损的一招。在遭批评之后,施蛰存还在一些文章中,说鲁迅自己看古书,还做过古文,捐资重刻《百喻经》,以示鲁迅于人于己的不同标准。在《服尔泰》一文中,攻击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在《杂文的文艺价值》中,他讽刺鲁迅“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这哪儿能看出“尊敬已久”?据此鲁迅必须揭出真相。他在1934年7月17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他(施蛰存)握有编辑两种杂志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在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的信中,更进一步指出:“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
在这些你来我往的拳脚中,施蛰存处处施的是暗拳、阴招,他在不遗余力地进攻。鲁迅的还击当然异常有力,他是胜利者。除了认为施蛰存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取悦当道(这毕竟是私人通信中的话)有些言重外,鲁迅的论战,义正词严,不容黑白混淆!
三
鲁迅为什么要“小题大做”,揪住施蛰存不放?
在论争的开始阶段,鲁迅是借施蛰存推荐《庄子》与《文选》这件事,批评一种现象。他在《“感旧”以后(上)》中说:“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他要驳斥的是“遗少群”,是穿西服的复古者。这清楚地表明,鲁迅决没有和施蛰存个人过不去的意思。
施蛰存推荐《庄子》与《文选》,引起鲁迅的注意,并提出批评,正表明了鲁迅的敏锐的见识,清醒的头脑。作为革命文学的旗手,鲁迅在这件事情中间,发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的提出论争,没有任何个人的私见、成见在里面。
“四·一二”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动摇着黑暗的统治。呼应这一革命浪潮,在文化战线上,就是革命文学取代文学革命,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开展。这时,当局对革命文学采取了残酷的围剿政策,一方面逮捕和残杀革命作家,封闭进步刊物。另一方面,组织流氓和御用文人,宣扬法西斯文化,借孔孟思想,抵御马克思主义,用所谓“新生活”消解人们对革命思想的追求。在文坛上,新旧文学的斗争也发生了变化。经过新文学阵营的奋斗,新文学的各种体裁,均取得很大的成绩,传统文学已经渐渐退出,新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的复古,已经不再是穿长衫遗老的鼓噪,而变为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倡导和示范。“五·四”之后,重新鼓吹孔孟之道,已成为当局对抗日益兴旺的革命文学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的鲁迅,对于并非遗老的施蛰存的推荐《庄子》与《文选》,保持着固有的警惕,对这一现象提出批评,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鲁迅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批评施蛰存,恰恰说明鲁迅没有任何私见,不是与施蛰存个人过不去。鲁迅是从左翼文学运动的健康开展的大局出发,对一种妨碍这一文学运动的现象保持着敏锐的警觉的表现。
鲁迅以为,中国的青年,不能靠“‘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他甚至认为,“‘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而如今提倡读孔孟,读《庄子》与《文选》,则更混帐。进步的青年如果不考虑“立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则读了多少古书,获得多少活字汇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说鲁迅对读古书这一社会现象保持警觉是鲁迅作为革命家的人所不及之处的话,那么,围绕《庄子》与《文选》的争论,正表现了鲁迅和施蛰存境界的高低了。施蛰存在论争中始终抓住鲁迅自己读古书、作古文等不放,试图证明:你自己做得,现在的青年如何做不得?鲁迅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认为不读《庄子》与《文选》的青年,仅仅“文字拙直,缺少活字汇”——不会作文而已,而不思考“立足”的青年——又将如何?
我们把讨论的问题进一步缩小。就算是作为“青年文学的修养之助”,在鲁迅看来,施蛰存的做法也是可笑的。在古书中去找活字汇,去提高青年文学的修养,这条路同样走不通。鲁迅在《“感旧”以后(上)》说:“他(施蛰存)的文章中,诚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糊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鲁迅自己对与施蛰存的这场争论,他的看法是“无聊”。他在致姚克的信中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了的,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至此,论争随着鲁迅的觉得“无聊”而渐告平息。而这之后,施蛰存仍耿耿于怀。他在自己编选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被人指斥“计划之草率,选学之不当,标点之谬误”后,于1935年11月25日发表《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告白》进行辩解:“但是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对此,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文人比较学》中予以回击:“中国的文人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但一面也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三十年代的那场论争,基本事实已经清楚:施蛰存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在与鲁迅搏斗;鲁迅认为1934年7月《申报·谈言》上署名“寒白”的文章是施蛰存所为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以上材料均见“杨文”)。这次论争的双方并不是一个等量级,鲁迅从左翼文学运动的大局出发,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对遗老、遗少的复古逆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但告诫在古书中寻找活字汇不可取,而且从根本上就不应该引导青年寻找活字汇。施蛰存则意气用事,使出一些很不光彩的拳术。时至今日,鲁迅先生早已作古,他的堂堂正正的批评,却被学者们拿来与施蛰存各打五十大板,甚至作为同情施蛰存先生的陪衬。连施蛰存敢于同鲁迅叫板也成了他的功绩受到赞扬,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甚至黑白颠倒的“重评鲁迅”,将会评出个什么样子来?
施蛰存先生至今仍在为繁荣祖国文化工作,这种精神我们是钦佩的。不错,他的“洋场恶少”的帽子是鲁迅给的,在“反右”和“文革”中他为此遭受苦难,这是鲁迅先生始料不及的。在那些不正常的年代里,鲁迅先生如果健在,同样要遭受苦难。他怎么能对他去世后几十年的事情负责?
“重评鲁迅”,我们仍要将鲁迅放回他所处的时代,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我们不能把鲁迅继续放在神坛上供奉,也决不能通过“重评”羞辱和毁谤鲁迅!
在校对本文时,惊闻施蛰存先生辞世的噩耗,仅以此文表示对施先生的沉痛悼念。
收稿日期:2003-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