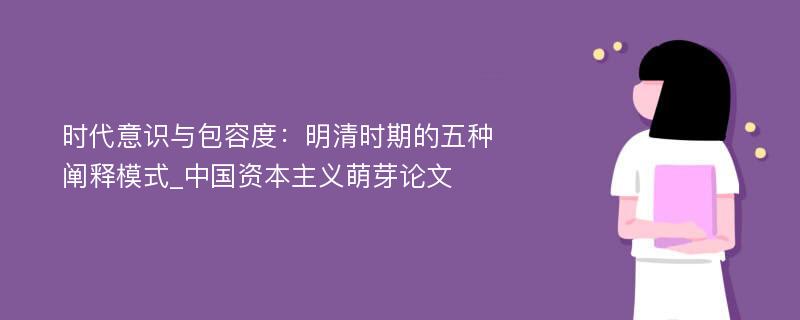
时代感与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种解释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感论文,明清论文,五种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644年,崇祯自杀、“李闯”称孤、“清军”入关——这三个交织在一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年依次上演。时人称之为“天崩地裂”、“天下陆沉”,由此可以想见他们心中的悲愤。对于汉族士人这群“治统”与“道统”的守护者来说,究竟何去何从,是自杀殉国,还是改事二姓;是救民于水火,还是做异族之奴才,成为他们必须做出的抉择,而“生为明臣,死为明鬼”的伦理纲常,与顺应“有德者得天下”的王朝更替法则即成为他们各自抉择背后不同的合理性解释,但关外满族的兴起却使“华夷之防”的文化冲突凸显。就此,明清易代成为“有德者得天下”的王朝更替法则与“华夷之防”的文化界限这两套同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对抗性话语相互竞争的场地。
迨至近代,当西方文明凭借其强大军事力量蛮横地闯入中华大地的时候,明清易代之际那份道德的紧张感再次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升腾起来,随即化为熊熊燃烧的民族革命的烈火,而有着强烈民族色彩的清朝政府则成为他们首先革命的对象。然而此时闯入的西方列强也已不再是所谓的野蛮“夷狄”部落,而是有着高度文明的异族国家。中国的失败不仅仅是武力上的无能,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落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正视的问题。当他们反思中国何以挨打,从何处开始落后的时候,明清之际这一历史时代也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他们论说的对象,也成为近代以来风起云涌的各类话语体系争夺的焦点,其间有太多的头绪与纠葛亟待清理与展开,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
在“康乾盛世”的歌舞升平中,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人那份文化的痛楚渐趋消退。但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中华文明遭受到严重的挑战,这种相似的时代境遇,又让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心中再次敲响“夷夏之别”的警世长钟。明清之际这一“天下陆沉”的时代恰好成为他们革命精神的誓师地、祭奠地。孙中山、章炳麟、陈天华、邹容等革命家无一不以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忆作为反抗清朝腐朽统治、宣传革命正义性的历史资源。1894年,孙中山等人成立兴中会,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革命宗旨。1903年农历3月19日,章炳麟等人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公开在崇祯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并且将南明永历朝廷的最终败亡视为中国的亡国之日。①之后,孙中山在解释同盟会纲领之一“民族主义”的时候,也直接指出:“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府,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②
而明清之际满人的屠杀政策则成为当时的革命派论证满汉关系“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的最好证据,③成为他们革命最为正当的理由。同时,他们还大量地印发有关清初统治者屠戮汉人的史籍,比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又编订出版《陆沉记》、《荡虏丛书》、《明季实录》等资料丛书,以揭露清军入关后的暴行与统治的黑暗,希望以此激起汉人心中那份尘封已久的亡国之恨。通过反复叙说明清之际汉人那段悲惨的历史记忆,来强调满汉民族仇恨之深,推翻清朝统治的必要,是此时革命派最有力的宣传手段之一。
在这种解释模式中,“华夷之别”的文化意识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之中被重现阐述,明清之际汉族士人那份文化的痛楚与焦虑复活。但在这种激昂与悲壮的感情之中,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反而显得不太那么重要,革命动员成了他们唯一的目标。清王朝在反民族压迫的革命洪流中灭亡,但中国却并没有因此而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反而国家愈发分裂,民族命运危在旦夕。虽然有人开始反思这套民族革命话语的正确性,但依然不改它在明清易代史解释上的强势地位。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便是民族革命时代的产物,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④在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纲》引论中,他对自己的民族史观做了更为全面的表述,明确说:“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但“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是分作三个时期,换了三个对象的,我们的民族革命运动,则始终一贯,不过领导的人物和标帜的口号有些不同罢了”。“满清”正是他心目中民族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和第一个对象。⑤因此,有学者称“这不仅使萧一山画地为牢,无法就丰富多彩的清代历史展开多方面的研究,而且还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中”,而且他的民族革命史观“只是感情的产物,不是深刻的哲学思考,没有坚实的科学依据”。⑥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也认为“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⑦
虽然这种声音在后来阶级革命的浪潮中有所消沉,但至20世纪90年代又再次响起。顾诚的《南明史》即是典型的代表。无可否认,该书对明清之际一系列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代表着南明史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⑧但它背后的解释话语却显得复杂多变,其中大汉族情绪尤为强烈。首先它认为清朝在多方势力的较量中最终取胜,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剽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人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的结果。它虽然承认清朝国势一度强盛,但随之话锋一转,即严厉地指责“满族入关打断了明朝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中国同西方的距离越来越大”。⑨总而观之,它对明清易代的评价事实上是以近代化话语为包裹,以阶级革命话语为内衬,以民族革命话语为核心的解释体系。诚如李治亭所说的《南明史》“是为明朝覆亡唱出的一首挽歌,是对‘汉族各派’联合‘抗清’斗争写的唱片赞美诗,是对清朝统一中国发出的一道声讨的檄文。《南明史》除了肯定农民战争外,基本上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期‘反清排满’思潮的集中反映”。⑩
陈梧桐却赞同顾诚对明清易代的解释,并且明确提出不能“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认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但他之所以要求用民族革命的话语来解释明清易代,也已经不再是基于传统的“华夷之防”的文化焦虑,而是认为那样“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1)张玉兴在讨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时,也指出目前学术界存在“漠视事实、曲解历史、甚至混淆是非、肯定投降、回护变节”的情况,认为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正反面人物不容混淆,反民族压迫精神是一种伟大操守,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对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12)
这些解释与顾诚用阶级革命和现代化话语来包裹民族革命情绪的做法是一致的。与其说他们抛弃了汉民族情绪,还不如说是传统的“华夷之防”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顾诚等人表达民族情绪时的闪烁其词,事实上也显现出民族革命话语体系所遭遇到的压力及其发生的演变。
迄今为止,民族革命话语这套解释模式依然是对明清之际这一时代较为强势的解释方式之一,影响深远。正如秦宝琦所言: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对清王朝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即认为其建立者——满族是“外族”、“异族”,其入关是“外族”、“异族”对中国的“入侵”,视明清更替为历史的倒退,视清王朝为“异端”。(13)
在这套解释模式中,研究者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并以此评判处于这一变革时代之中的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行。在论述与评价中,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是衡量古人、评判往事的尺度,当时的历史环境却很大程度上被置之不顾。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套解释模式所强调的是明清易代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断裂,特别是明清两朝政权性质、民族色彩的不同,而对明清两代这些方面的内在连续性显然关注不够。
二、王朝更替的解释模式
不论革命派思想多么狂热,民族情绪多么激昂,民族革命话语始终未能独霸对明清易代史的解释。事实上,它是一种被长期压抑的声音,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才爆发出来的。在清代兴盛的时候,王朝更替说才是解释明清之际这一时代的主流话语。因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清朝无疑已被视为当之无愧的正统,汉族士人的利益早已与“满清”政权牢牢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之故,当洪秀全高举义旗的时候,迎来的不是汉族士人的拥护,而是坚决的抵抗。
迨至清末,这套解释模式虽遭到革命话语的诋毁,但却为当时的改良派所继承。他们否认在满清政府统治之下存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并且屡屡称颂清朝帝王的“功德”,(14)认为在清朝的统治之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15)而且明确指出满洲是中国国土,不是异国;“满清”入关取代明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更迭,不是中国的灭亡,并以此批判革命派的反清排满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求“必多从政治上立论,而少从种族上立论”。(16)虽然这种声音为此后汹涌的革命潮流淹没,但坚守者依旧顽强。其中虽然以清朝遗老、遗少为主,(17)但也不乏饱学之士。
孟森就是以王朝更替说解释明清易代的。他批评辛亥革命后许多“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18)其《明清史讲义》即是应这一现象而作,全书是以明清两代统治者削平群雄、定鼎开国、宫廷之争、守成败亡为其论述的主要线索,制度的变革、君主的智愚和朝臣的忠奸是其论述的主要对象,总结各朝统治者治国为政各项政策的利弊得失及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是其论述的主要目的。(19)无怪乎有人评论道:“在孟森的清史体系中,帝王将相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扮演历史进程的主角。”(20)
事实上,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无论革命浪潮如何冲击,其继明代之后的正统地位不可动摇,故此明清易代为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如何加以合理论证的问题。“有德者得天下”是传统王朝更替论的理论依据,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解释模式早已陈旧,它不得不也与“华夷之防”的解释模式一同演变。李鸿彬在重申明清易代是中国古代王朝正常更替的同时,认为满族的崛起与明朝的衰亡,无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属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谱系之中,但他这一观点却是以满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这一现代民族观念为出发点。(21)
20世纪90年代,随着明清史研究中汉民族情绪的又一次高涨(前文已有所论述),再次非难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比如顾诚严正地批评视清朝为明代理所当然继承者的观点只是将“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的习惯性做法,与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22)为此,李治亭明确地指出明清易代与同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只不过是王朝的更替,由朱家姓换上了爱新觉罗,并全面地批驳了学界视满族入关延缓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重建封建制王朝把中国拉向“倒退”的说法,但他对明清易代属于中国传统王朝鼎革说的认同,也不再以“有德者得天下”这一传统的王朝更替论为依据,而是基于对明清两代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比分析之上的。(23)
部分西方学者也用王朝更替模式来解释明清易代,其中司徒琳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但其研究目的似乎较之中国学者更为单纯,无意于争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是直接将明亡清兴作为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具体的探讨明朝何以亡国这一问题。她认为明朝以及后来的南明之所以灭亡,关键在于没有解决好两类矛盾,其一是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其二是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24)言下之意,清朝最终取胜的关键,即在于它成功地解决了这两类矛盾。
王朝更替说对明清易代的分析主要是从制度层面论述的,它始终强调的是明清两代之间的传承关系,对明清两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内在连续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它与民族革命解释模式之间最大的分歧,但是它们两者有一个共通之处,即都是眼光向上,专注于明清两代上层制度的变迁与权力关系的演变等方面的问题,对下层民众在历史演变中的作用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重视不够。
三、阶级革命的解释模式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阶级分析方法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成为1949年后中国史研究的主流话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论述道:“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他认为这是中国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最终灭亡的根源之所在。(25)这是用阶级革命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灭亡缘由的经典论述。
明朝何以亡国?在阶级话语的分析框架中,简而言之即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正如戴逸在《简明清史》中所论述的:“十七世纪前期,明王朝已经过了二百数十年的统治,各种矛盾长期地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统治机构腐败,社会危机加深,人民生活痛苦,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走过了兴旺的阶段,到达了日薄西山的黄昏。”就明末农民大起义失败的原因来说,他认为:“大顺政权虽然做了一系列工作,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彻底解决推翻明朝统治以后提到日程上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再加之农民军自身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以至于进入北京后迅速贪污等等原因共同导致了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失败。”(26)
但是清军入关,定鼎中原,这却给阶级分析方法带来了两难。一方面满族的兴起不能排除其反抗明朝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原因。毛泽东曾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27)李燕光更旗帜鲜明地认为:“清初的民族矛盾从内容和形式来说,都是与明末汉族内部阶级矛盾有区别的,但是,它的实质仍是属于阶级矛盾性质的。”(28)另一方面,清朝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也是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孰是孰非一直都是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史学家纠缠不清的问题。但这类文章主要是对明清(后金)之间的矛盾属于何种性质的争论,清朝兴起的原因却不是它们探讨的主要问题。在清朝为何能最终取胜的问题上,戴逸的论述堪称范本。他认为“清朝是新崛起的力量,组织严密、战斗力强,领导集团比较稳定而有进取心。并且在政治上作出重大的努力,逐步减少屠杀掠夺的行径,改变某些高压政策,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分化和削弱了抗清势力,逐渐显示出自己的优势,以至最终赢得了全国的统治权”。(29)简言之,即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作为统治者,却能对被统治者的激烈反抗做出让步,因此才赢得民心,取得胜利。
到了20世纪90年代,王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明代卷》与汤纲、南炳文合著的《明史》则是这类研究在新时期的典型代表。它们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各方面制度的演变及相关的重大事件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打上了阶级分析方法的鲜明烙印,但同时也揉进了一些近代化话语,将其作为自己的论据。(30)
阶级革命话语支配下的历史学对明清之际这一时代的研究无疑做出过巨大贡献。它对下层民众在历史演进中所起作用的重视,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详细论述等等方面,都是民族革命解释模式和王朝更替解释模式所忽视的问题,这一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也是与前二者之间对明清易代史解释的最大分歧之一。同时,在阶级分析方法的指导下大量以前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的社会经济史料被发掘出来,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做了很好的铺垫。
但是阶级革命解释模式真正的关注点,是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往往忽视构成规律的多元性因素。正如陈生玺所说,“所谓历史的发展规律,好像是一种超然的意志力量,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不过是完成这种超然意志的工具”。(31)并且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这套方法分析下的明清易代史研究在建国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常流于无实际意义的性质之争,而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变动的原因、方向、大小等具体问题反而未得到深入的研究。这使阶级分析方法流于表面,也将明清易代史研究引入了歧途。
四、近代化的解释模式
万明在《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一文中,将近70年来晚明史研究归纳为四个方面:以追寻资本主义萌芽为核心的社会经济视角、近代化/现代化的视角、导向多元结构认识的社会的视角、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化视角。(32)事实上,这四个视角同属于近代化话语的范畴,都是基于中国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之上的,所探讨的都是中国在晚明时期能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以此论证中国与西方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但也由此可见近代化解释模式内部较之其他解释模式更为复杂,存在多种观察的视角。
明清之际的近代化解释模式,最先出现的无疑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驳斥西方流行的“中国停滞论”及当时中国学者的附和,吕振羽、侯外庐、胡绳等学者都提出了明末清初中国社会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33)就此,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1949年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热闹非凡。可以说,许多优秀的学者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其贡献自不待言,正如尚钺所说这一研究“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外貌,把中国历史从漆黑一团的没有规律、没有发展的‘特殊论’、‘长期性’和‘停滞论’的模糊现象中挽救出来了”,(34)但需检讨之处也不少。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发生、发展是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西方话语的挑战中激发出来的。新中国建国初期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则显然是为了论证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5)这一论断,要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之中,寻找到“必然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般性”,要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解决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36)而寻找中西社会内在结构的构成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似性则是其主要的论证方法。在论证的过程中,西方俨然是一个有各类参数的坐标系,中国只是被嵌在这一坐标上并受其规范的一个点或者一条线。但也不能因此说中国学者要“以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方法做一些无意义的机械式的研究。
事实上,与其说他们是论证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在中国也适用,还不如说马克思的这一学说恰好为中国学者所用,成为他们论证“西方有,中国也有”的理论工具,(37)以及指责西方的入侵才是中国近代落后根源的理论依据。正如尚钺在论述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意义时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阐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所必需的,而且在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对于批判帝国主义侵略的荒诞思想和谬论,与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38)可见,建国初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仍是一种民族情绪的宣泄,在感情上,与前文所述的民族革命话语解释模式是相通的,只是在论证上显得更为严密,更有理论色彩。
但是这一研究却是在阶级分析方法指导下进行的。首先提出这一命题的便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吕振羽等人,毛泽东也持此观点。(39)而且阶级分析方法所采用的眼光向下的观察视角以及对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视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界的旧传统,从专注于上层历代帝王将相的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层面的演变,转向对下层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的具体探讨。这一点又与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新史学”是一致的。同时,大量相关的以往不为人知的地方文献被发掘出来,也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以近代化为依归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两类话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这也显示出在历史解释中,各类话语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叠加的关系,只是各自所处的时代、各自面对的问题有所不同而已。
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明清之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历史时期。许多学者认为它即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前文提到的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就持此种观点。尚钺等人在《中国历史纲要》中更是明确指出明代末年的中国社会已“具备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随之他在《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一书中详细地论证了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因素有“惊人”增长速度的观点,并且认为降至明末清初中国社会性质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40)邓拓也认为“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41)此外,王仲荦、李文治、梁方仲、傅衣凌、吴承明等学者都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末清初说(具体的时间段限有所不同),且都有非常深入的阐述。
在上述学者的眼中,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有着显著变化的时期,但它也是一个政权更替的大时代。这是他们在阐述资本主义萌芽时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满族的入关恰好成为他们论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何比西方迟缓二百余年的重要理由。陈振汉认为“从明末天启以至顺治末(1620-1661)四十年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革命农民的镇压,特别是清兵入关以后统率汉奸军队对中国人民进行残杀焚掠,全国劳动力有大量的绝对减少”。(42)在他的论述中,清兵入关对当时的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毫无疑问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正常发展的阻碍因素。吴海若也明确地指出:“直到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中国历史的发展本来可以走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但是却遇到了满族入侵,改变了这一历史的转折,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延缓了”;“满族侵入并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对于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历史来说,不能不是最大的不幸……但是,外来的落后势力和本国的反动势力,终究是不能长期使历史倒退的。在清朝统治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也还有一些发展。然而,中国的历史遇到了这一挫折,不能不延缓二百年”。(43)
他们的这些论述显然带有偏见和民族情绪。这一点在尚钺的论述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他首先高度地赞扬明末城市市民阶层和农民阶级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认为他们“打垮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京城陷落,皇帝自杀,明王朝封建统治陷于崩溃境地”,(44)随即严厉地指责那些“已被中国人民打倒的中国社会中最腐朽的封建势力”与满族勾结,向“中国农民革命军和广大城市市民群众进行极其残酷野蛮的报复性的大屠杀”,造成了中国新生产力(包括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毁灭性的大破坏,并将清军入关与13世纪蒙古族的统治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国的入侵连贯一气,认为它们是造成中国社会发展延缓的重要原因,甚至认为“雍乾之际,中国社会的表面安定,实际上却是为继续明末之后的另一次大革命准备力量”。(45)尚钺的这些论述可谓与萧一山的中国近代民族革命三阶段论如出一辙,其间的汉民族情绪溢于言表。无怪乎他不赞同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而要将其上推到明末清初。(46)
事实上,明末清初社会经济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特征早在唐宋,甚至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47)但清朝这一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及其统一战争中不乏杀戮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恰好为论证中国资本主义的幼芽不能长成参天大树以至于近代落后挨打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可以让人更坚定地相信中国社会发展较之西方延缓二百多年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干扰所致,而非中国汉族社会内部的原因。这其间更多的依旧是汉民族情绪的宣泄。近年来,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转向市场经济研究的吴承明在论述明清易代时这种汉民族情绪少却了许多,他主要是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来解释资本主义萌芽迟缓的原因,但依然将满族入关视之为阻碍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逆流”。(48)
20世纪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极度繁盛中迅速变成“明日黄花”,甚至被视为“虚假命题”,认为是一种“以假设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情结”。(49)这种评价实不为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确实包含了太多的感情色彩和现实观照。这一点与那套民族革命解释模式是相连贯的,不同之处即是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较为精细的阐述。
明清之际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对政治、文化、思想近代化的研究。在唯物史观中,它们作为上层建筑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它们自然也应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题中之义。首先开始这方面研究的是侯外庐,他在《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一书中曾提出明清之际出现了城市平民反对派及异端思想。(50)其后左云鹏、刘重日在《明代东林党争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市民运动的关系》一文中甚至认为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与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地主阶级反对派和城市中等阶级与平民阶级反对派,并且指出东林党是在反对极端皇权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是在东南沿海,特别是江浙地区的非身份性地主与商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政治活动与历代党争是有本质不同的。(51)尚钺在《明清之际中国市民运动的特征及其发展》一文中认为在明末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反封建专制的“市民阶级”。(52)
谢国桢对明季党社史研究用力独深,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详细地考证了明末党社的源流及其社会背景,可谓典范之作。(53)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一书论述了明末党社运动的发展过程,并着重探讨它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54)近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不少,其中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详述了明末东林党、复社的发生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17世纪英国的政党政治相比较,认为东林党、复社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专制皇权体系中生发出的异质体,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必将使中国走上近代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是由于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满族入主中原,重建了明朝的君主专制体制,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的民主运动进程中断,使与东林党、复社在思想上有直接继承关系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难以产生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55)
显然,在这些有关明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论述中,清军的入关成为延缓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与其说清军的入关确实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还不如说是现今的中国学者以此作为中国为何没有走上西方道路、为何在近代落后挨打的最好借口。因为所有的这些论述都未对清军入关后重建专制皇权的原因给予充分的探讨,都未对清军入关后的经济制度与措施进行深入的阐述。吴承明在检讨明清经济史研究时,就曾指出“我国研究这时期经济发展的论著,大都是明清并述或通论;像讲赋役,大都是从一条鞭直落到摊丁入地;讲商品、货币和市场,也是从嘉靖到乾隆;好像直线发展似的,不见曲折兴衰”,并认为自己原来回避17世纪的做法是可耻的。(56)岂止明清经济史研究如此,明清史其他方面的论述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不足。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外部干扰因素的强调与西方学者观察中国明清史时采用的全球化视角不谋而合。前者强调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武力,后者论述西方隐性的经济影响。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在1500-1800年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而白银即是连接中西方的桥梁。(57)可以讲,在全球化视野中,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明清之际这一时代的研究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17世纪危机’是‘世界17世纪危机’的一环”。(58)集众家之力而成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即是将中国明代史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进行考察的典范。它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论述都是以西方社会为参照展开的,并且明确认为中国在明代已经与西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并逐步融入了“浮现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同时指出明朝的衰落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巨大影响,主要是白银流入的剧减,恶化了明末的经济状况,而清初统治的不断稳定却又得益于外贸的恢复与大量白银的重新流入。(59)魏斐德在《洪业》一书中则在承认明清易代是中国传统时代王朝更迭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当时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之中加以论述,认为在白银的牵制下中国也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而清朝则以其独特的统治方式成功地将中国从这场世界性的危机中解脱出来。(60)其隐约可见的意图,即是要为西方社会寻找应对这样一场世界性危机的“中国经验”。
对中国明清易代史的研究,日本学者采用的观察视角与西方学者的全球化视角有所不同,他们往往将中国置于东亚这一国际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在他们的研究中,东亚才是与西方相对的地域概念。这虽然有别于西方学者的全球化视野,但都是试图将中国明清之际所遭遇的问题纳入到较大范围的国际视野之中进行解释。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一文即是从政治统治、民族关系以及国际贸易三个方面归纳和总结了日本史学界以东亚视角研究中国明清易代史所取得的成果,认为清朝的建立较为成功地将中国从17世纪整个东亚乃至世界性的危机之中挽救出来。(61)近年来这种国际化视角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与樊树志的《晚明史:1573-1644》即是这方面的力作。(62)
但在明清易代政治史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早已采用了这一视野。王思治等学者就曾系统地阐述了应将清史置于世界范围内考察,突出清朝统治对抵御西方殖民侵略的重要意义的问题,认为业已腐败的明朝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应予肯定。而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上所做的历史贡献也是以往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63)袁良义持相同观点,认为清军入关,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的统一,制止了外来侵略者的进犯。(64)庄吉发则很明确地指出,清朝积极整理边疆,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经过二百多年的统治,满汉蒙回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终于奠定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代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应该加以肯定。(65)
可见,全球化的观察视角与王朝更替解释模式密切相关,都以明亡清兴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或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角度讨论明清易代发生的缘由,或从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肯定清朝的历史功绩,将明清之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作为论证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总之,近百年来,明清易代史上述四类解释模式各自都有着复杂的演变过程,且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近代民族革命解释模式与传统的“华夷之别”是一脉相承的,而与之相对的王朝更迭解释模式则渊源于传统的“有德者得天下”的政治思想,但二者所关注的都是上层政治人物的活动以及重大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的演变,对下层民众的历史作用及下层社会经济生活的具体状况则漠然处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明清史学界逐渐接受阶级分析方法,并形成了明清易代史的阶级革命解释模式,将眼光转向下层民众及其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一改以往两种解释模式的观察视角,但这一眼光向下的视角在开启以现代化为依归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同时,也成为以往两种解释模式的新理论资源。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民族感情上又秉承了民族革命解释模式的传统,往往将清军入关视之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阻碍因素,但与之同属于近代化解释模式的全球化视野则更多的是承袭王朝更迭的解释方式,或从全球化角度分析明亡清兴的缘由,或从这一角度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学界近百年来各类明清易代史解释模式(如果说它们可以称之为“范式”的话)并未发生过杨念群所解读的那种非此即彼式的“范式转变”,也与库恩“范式转变”的原意相悖,它们恰恰表现出“一个累积的过程”,“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66)在上述解释模式中,其中两条脉络非常清晰,即由“华夷之别”思想而来的民族革命解释模式和由“有德者得天下”思想而来的王朝更替解释模式,它们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歇,而后起的阶级革命解释模式和近代化解释模式非但不能颠覆它们,反而成为它们各自完善的新证据和新方法。由此可见,近百年的明清易代史解释既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感,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度。
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纠结,关键即在于它们所关注的问题本质上是相通的,同属一个范畴,即都是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考察。其中民族革命和王朝更替两类解释模式所关注的是上层社会关系,即政权的性质、统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而阶级革命和近代化两类解释模式所关注的则是下层社会关系,即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分析来考察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然而,所有的社会关系,不论是君臣还是朋友,不论是阶级还是民族,事实上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具体的人和事来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决定了这四类解释模式只能是在同一个地方绕圈子,而无法实现根本性的“范式”转变。
五、一种新的解释模式:生态—灾害史研究
从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我们知道人既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有阶级、民族等社会身份以及与这些社会身份相应的社会思想,同时也有吃、穿等生理需求,因此,要全面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历史的真相,离不开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讨。且随着近年来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越发严重以及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人们也迫切地需要到历史中寻找“人与自然”共处的经验与教训。这些构成了生态史、环境史、灾荒史研究逐步兴盛的理论基础与时代背景。在这一总体趋势之下,明清易代史研究中一种新的解释模式也逐渐浮出水面。夏明方在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梳理中就已发现这种新的解释模式,即“生态经济模式”。(67)事实上,又岂止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有这种新解释模式的萌芽,可以说,这种新模式已经遍布了整个明清史研究,并且也不仅限于经济史,已经扩展到对明清时期其他方面的探讨,而对生态环境剧烈表现的自然灾害的研究则是生态史、环境史研究中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妨将这一概念稍作放大,称之为“生态—灾害史解释模式”。就明清易代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
如曹树基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一文中描述了明末华北在战争和鼠疫共同侵袭下的社会状况,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之后又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一书中更是直接明了地说“小老鼠灭了大明朝”,认为鼠疫使明朝政府最终丧失抵御李自成农民军进攻的能力。(68)这种锋芒毕露的观点自然少不了其他学者的质疑。(69)邱仲麟在《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系统的应变》一文中的观点与曹树基的论断有共通之处,但却较为谨慎。(70)这些成果主要是以明末瘟疫为研究对象探讨影响明清易代的生态因素的。而杜大恒等的《论明朝安全政策的环境影响》与赵玉田的《明代北方灾荒的社会控制》、《灾荒、生态环境与明代北方社会经济开发》、《明代北方的灾荒与农业开发》等论著则是从生态承受能力的角度对明朝灭亡做出了新解释。(71)而一些论述则从气候变迁的角度重新对明清之际政治危机、社会动乱的原因进行了探讨。(72)
从生态史、灾害史的角度重新阐述明清易代过程及其原因是近年来明清易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将研究对象从“人与人”的关系拓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关注点从以如何合理分配自然资源为核心问题的权力关系、阶级地位、民族矛盾等方面,转向以如何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核心问题的气候变迁、生态危机、自然灾害等方面,即由社会分配的问题转向了社会生产的问题。无疑,这是明清易代史研究最具革命性的发展方向,但它仍然不可能完全取消以往解释模式存在的意义,它所面对的问题与以往解释模式所应对的并非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关系。这决定了它终将与其他模式融汇于对明清易代的解释过程之中,犹如一条新的支流汇入江河之中,会让江河更加宽广,但不会彻底更换水源。而且,这一转变的实现是在前述四类解释模式对明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阐述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如果没有对社会分配问题的充分探讨以及对这些讨论的深刻反思,也就不可能对社会生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不可忽视的是,当前明清易代生态—灾害史解释模式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其一,目前相当一部分这类研究过分地强调自然生态对当时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影响,抛弃了许多已有的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有矫枉过正之嫌,没能真正地凸显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以及一些值得进一步发挥的观点往往一带而过或点到为止。其二,这类成果的研究对象显得过于零碎,其内在联系缺乏必要的系统性的归纳和探讨,导致当前明清易代生态—灾害史研究呈现出研究对象细碎化以及问题意识空泛化的整体状况,这种细化研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并非真正的实证研究。具体表现即是以某一地某一次大灾大疫为论据就得出明朝亡于生态危机的宏大结论,而对当时的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具体的复杂关系则所论甚少。其三,跨学科研究的力度不够。明末清初在自然科学界被称为“明清宇宙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历史时期,自然科学界特别是气候学、气象学、地理学等学科对这一时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与有效的研究方法,其中对各类灾害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方法及成果尤其值得历史学者大力借鉴、吸纳,正如夏明方所说自然灾害史的研究需要“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把灾荒问题和自然、生态、技术和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考察,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机械、片面、静止地看问题所易滋生的弊端”。(73)若能从这三方面加以完善,明清易代生态—灾害史解释模式将更具活力、更有说服力。
六、结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近百年来,明清易代史研究依次出现的五种解释模式恰好生动地验证了克罗齐那句哲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们的出现正是人们对近代以来中国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思考,并试图到明清之际这一包含着多重色彩的时代中寻找答案的漫漫历程。然而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又决定了明清易代的主题解释不可能淹没其他的声音。总而观之,在这复杂而漫长的明清易代史研究过程中,解释方式的演变既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感,更显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度。至此,使人们无法不感喟,在这不同的记忆视野里,让人真切感受到的惟有:“岂止新旧嬗递,予夺异数,更是无尽的宇宙叩问,永久的人生猜测,以及对未来不踏实的冀求与追逐。”(74)
注释:
①参见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85年,第187—188页。
②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6—297页。
③参见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号,日本东京,1905年。
④参见戎笙:《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见《清史论丛》第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⑤萧一山:《清史大纲·引论》,重庆:经世学社,1944年。
⑥戎笙:《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见《清史论丛》第八辑。
⑦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页。
⑧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⑨顾诚:《南明史·序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⑩李治亭:《南明史辨——评〈南明史〉》,《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
(11)陈梧桐:《明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6月20日。
(12)参见张玉兴:《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3)参见李鸿彬:《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秦宝琦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4)参见明夷:《法国革命论》,《民报》第3号号外,日本:东京,1906年。
(15)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号,日本横滨,1906年。
(16)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4号,日本横滨,1906年。
(17)参见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8)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4页。
(19)参见罗仲辉:《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的编撰特点》,《清史论丛》第八辑。
(20)戎笙:《萧一山和他的清史研究——纪念他逝世十周年》,《清史论丛》第八辑,。
(21)参见李鸿彬:《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秦宝琦序》,第1—2页。
(22)参见顾诚:《南明史·序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23)参见李治亭主编:《清朝通史·顺治朝分卷·导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24)参见司徒琳:《南明史·引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25)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4页。
(26)戴逸:《简明清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101页。
(2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4页。
(28)李燕光:《清代的满汉民族关系与满族的阶级关系》,《民族团结》1962年第7期。
(29)戴逸:《简明清史》,第119页。
(30)参见王毓铨主编:《中国通史·明代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31)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2)参见万明:《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33)参见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1页。
(34)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394页。
(3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
(36)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295、835页。
(37)吴承明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为论证“中国也有”,但他这一说法只能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目的上的转变和方法上的改进。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33页。
(38)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380页。
(39)参见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437—438页。
(40)参见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386—390页。
(41)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133页。
(4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第284页。
(4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第894页。
(44)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第216页。
(45)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73、77、131页。
(46)参见黎澍:《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47)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第804—841页;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第30—75页。
(48)参见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674页。
(49)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41页。
(50)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第1092页。
(51)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第258页。
(52)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第280页。
(53)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54)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55)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62—567页。
(56)参见吴承明:《吴承明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1—142页。
(57)参见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58)吴承明:《吴承明集》,第176页。
(59)参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节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82—400页。
(60)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导言》,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61)参见岸木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62)参见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63)参见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64)参见袁良义:《清军入关的历史功绩——为纪念清军入关350周年而作》,《史学集刊》1994年第4期。
(65)参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66)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7)夏明方:《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8)参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69)参见浅川:《万历年间华北地区鼠疫流行存疑》,《学海》2003年第4期。
(70)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第2分,2004年。
(71)参见杜大恒等:《论明朝安全政策的环境影响》,《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赵玉田:《明代北方灾荒的社会控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赵玉田:《灾荒、生态环境与明代北方社会经济开发》,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博士论文;赵玉田:《明代北方的灾荒与农业开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72)参见陈玉琼:《近500年华北地区最严重73的干旱及其影响》,《气象》1991年第3期;王铮、张丕远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李伯重:《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起大落》,《人口研究》1999年第1期;方修琦等:《极端气候事件—移民开垦—政策管理的互动——1661-1680年东北移民开垦对华北水旱灾的异地响应》,《中国科学(D辑)》2006年第36卷第7期;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第22卷第3号,转引自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73)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绪论》,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4)萧一山:《清代通史·王家范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标签: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文; 满族文化论文; 明清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满族论文; 南明史论文; 明朝论文; 专门史论文; 南宋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文艺复兴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