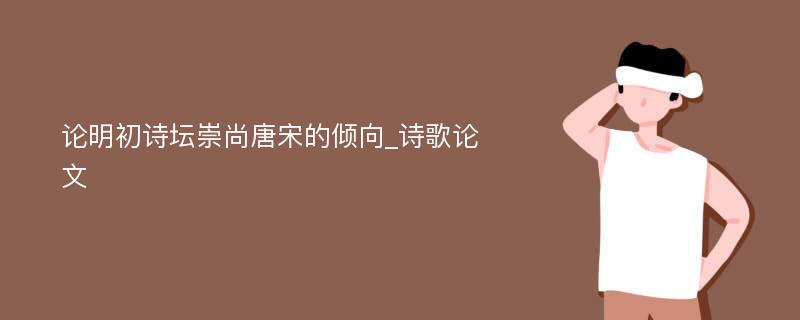
试论明初诗坛的崇唐抑宋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试论论文,倾向论文,崇唐抑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初诗坛,在东南地区形成了以地域为分野的吴中、浙江、闽中、江右和岭南五大文人集团。他们在各自地域先后崛起,共同推衍着明初诗坛复古思潮的发展。
明初五大文人集团由于各自的地域文化积淀而展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在创作上各具风格,不一而足。他们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力图在以前各朝代的诗歌中寻找一种体制完备的格式作为取法的典范,或宗唐,或由唐上溯汉魏及至《诗经》,或兼及唐宋。就诗歌文体而论,他们取法的朝代不尽相同;单就宗唐而论,其取法对象则比较宽泛,因而整个诗歌复古思潮显示出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各种复古诗歌理论以其朦胧、游移、各有侧重的形态而导致了一种杂乱无序的表征。然而,倘若我们对它们作一总体性的考察和横向的比较,则不难看出,这风格纷呈的众多诗歌理论与创作又具有一种共同的“崇唐抑宋”的倾向,这种倾向对明中叶前后七子的诗歌复古理论又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五大文人集团中,又以吴中、浙江、闽中三大文人集团建树较多,影响最大(注: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我朝诗道之昌,追复古昔,而闽、浙、吴中尤为极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5页。)。 本文旨在通过对其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分析与考察,勾勒出明初诗坛复古思潮中“崇唐抑宋”倾向的总体特征及其在明代诗歌流变史上的客观地位,以求对明中叶“诗必盛唐”理论的形成作出进一步的反思。
一
吴中文人集团,主要包括在吴中腹地结社唱酬的“吴中四杰”、“北郭十友”以及边缘区域的王彝、袁凯等在明初较有名气的诗人,是明初专力于诗歌创作的一个规模较大的文人群体。元末明初,吴中文人经常定期举行诗社活动来倡导诗歌风雅。在这种结社活动中,杨维桢是以大家的身份出现的。当时,杨维桢以其“铁崖体”享誉东南一带,被众文人争相仿效,以致成一时风气。然而,许多诗人又没有完全拘泥于他的囿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杨维桢提倡诗歌复古的思想正适合当时文人的心态;而与此同时,他的诗作抒写个人情性,风格险怪靡丽,也引起了致力于探索诗歌艺术的诗人们的不满。杨维桢诗歌险怪仿李贺,瑰奇妖丽仿温庭筠、李商隐,自成一家固然可以,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一些吴中文人虽师从杨维桢,却逐渐地脱离了铁崖体的诗风,拓展取法范围,改从摹拟古诗,特别是广泛地取法唐诗入手,使诗风表现出多样化的倾向。
名列“吴中四杰”、“北郭十友”之首的高启,是吴中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明初诗歌崇儒复雅的道路上,高启的着眼点在于探索诗体气格,雅化创作风格。高启以“格、意、趣”为作诗的三大要素。首先是辨别古诗体制高下,其次要融入自己的情感,再次要求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而达到高雅完美的意境。“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他以为领会了以上三点,然后诗风可以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最后要作到“声不违节,言必止义”,便可谓诗道具备了(注:《独庵集序》,高启《凫藻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0册,第279页。)。另外,高启深感到在创作中存在一个转益多师、 融汇贯通,进而自成一体的问题。他在《独庵集序》中便论及汉魏以降的古代诗人除杜甫之外“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的弊病,认为“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詠丘园之致”,都有“偏执之弊”,所以他提出“兼师众长,随事摹拟”以至“时至心融,浑然自成”的师古方法,从兼师百家入手,进而融汇贯通。故高启的诗歌不仅体制淳雅,而且音韵和谐完美,得以“嗣响盛唐”。如他的《送谢恭》一诗:“凉风起江海,万树尽秋声。摇落岂堪别?踌躇空复情。帆过京口渡,砧响石头城。为客归宜早,高堂白发生。”此诗化用唐人诗意,却自成格调,情景相融,很有盛唐笔势。高启的律诗,音节响亮明丽,一扫“铁崖体”多用仄韵、仄声字形成的幽咽晦暗的诗风。如《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涵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韵律疾徐错落有致,高亢而不失沉稳。沈德潜评为:“音节气味,格律词华,无不入妙。《青邱集》中为金和玉节。”(注: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一,第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高启格兼众体,包容万象的创作风格,对于元季纤秾之风,实有矫正之功力。他以拟古作为学诗门径,却不拘泥于复古,能够将个人才情、文化底蕴与诗歌格律高度融合,从而写出《青邱子》等洒脱不羁、抒发性灵的作品,在这一点上,确实得到了盛唐诗风的真谛。但高启毕竟殒年过早,他的创作尚未达到自成一体的境界。所以《四库提要》在评价他的成就时,一方面说他:“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同时又惋叹他摹拟太甚,以致“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这实在是一语中的评论。
“吴中四杰”中,杨基最受杨维桢称赏,在当时有“大杨”“小杨”之称。江朝宗《眉庵集》原序评杨基之诗“秾丽纤蔚,蔼然正大和平之音,殆有唐人风味”。正因为杨基并不拘束于杨维桢及其铁崖体,在诗歌艺术上直窥唐音,故其诗体现出正大和平的整体风貌。杨基诗以五言七言古体和七律擅长,杂言歌行则过于纤弱而似词。五言古诗最有名的一首《岳阳楼》:“春色醉巴陵,阑干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阔鱼龙气,婵娟帝子灵。何人夜吹笛,风急雨冥冥。”沈德潜以为此诗“应推五言射雕手,起结尤入神境”(注: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一,第24页。)。诗以春至洞庭入笔,描写岳阳楼与洞庭湖交相辉映的景况,“水吞三楚白”与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气势相亚,水楼相映,虚实相参。结尾以春夜闻笛宕开幻境,耐人寻味。杨基的七律属对工整,音韵雅致,格调隽永,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杨基的诗歌虽仍未脱元诗纤巧之习,然而大体上也脱离了铁崖体的风格。他的诗不像高启那样有明显的拟古痕迹,但从整体上看,确实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尤其在措辞用韵等方面深得唐人体格。恰如后人评论的:“(其诗)才长逸荡,兴多隽永”,且“格高韵胜,浑然无迹”(注:顾起伦《国雅品》, 转引自《明诗综》卷十,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9册,第342页。),在明初也算得上诗坛高手。
在“吴中四杰”中,张羽、徐贲的诗歌成就不及高杨二人。王世贞评价张徐二人“如乡士女,有质有情,而乏体度”(注:转引自《明诗综》卷十。)。张羽长于五言、七言古体。他的七言歌行笔力雄放,音节流畅,受到后人的称赞。他的五言古诗则“学杜学韦各有神理”(注:程孟阳语,转引自《明诗综》卷十。)。徐贲也是以古体诗见长,其诗体裁精密,字句熨帖。因“天性端谨,不逾规矩”(注:《四库提要·北郭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0册第547页。),故而才情稍逊。“四杰”之外,被何景明推为“明初诗人之冠”(注:转引自《明诗纪事》甲签卷十三,第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的袁凯也是“古诗学魏晋,近体学杜”。对于袁凯学杜,程孟阳有一个总的评价:“七言律诗,自宋、元来学杜,未有如叟之自然者,野逸玄澹,疏荡傲兀,往往得老杜兴会。……七言绝句,似乎率易似古乐府,亦是老杜法脉。”(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袁御史凯》引,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吴中文人多是由元入明的诗人,他们沿袭了元人在诗歌复古中的宗唐倾向。然而,与当时风云际遇、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征相呼应,他们多以元人的广泛宗唐得古来矫正元末纤秾缛丽诗风的流弊。吴中诗人的诗歌复古取向大致是“言选则入于汉魏,言律则入于唐”(注:周传《兰庭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420页。), 这又与他们的遭际有很大关系。吴中地区虽然一度安宁富庶,但吴中文人中不少人都历经过战乱沧桑,满目都是黎民百姓的苦难。“空村无人不敢入,野狗龈龈累百十。沟中死人血未干,终夜冤魂自相泣。”(袁凯《夜经胥浦乡时新被冠》)“桑柘阴阴绕岸栽,石阑销折卧苍苔。欲求姓氏无人识,时有逃军剥枣来。”(杨基《叹道傍废宅》)他们也有“鸟过凤生翼,龙归鱼在鳞。相期俱努力,天地正烽尘”(高启《与刘将军杜文学晚登西城》)的济世之心;有“中外诸侯原有约,东南豪杰岂无人”(杨基《闻官军南征解围有日喜而遂咏》)的踌躇满志;但更多的则是“英雄在承平,白首为渔樵。非无搏击能,不于狐兔遭”(杨基《感怀》)的不遇之悲。不论在元末还是明初,吴中文人都是游离在政治的边缘,由于诗人个性自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流露出封建末世知识分子特有的郁闷和愁苦。“我愁从何来,秋至忽见之。欲言竟难名,泯然聊自知。”(高启《我愁从何来》)这种忧愁不仅是对生命脆弱短促的感叹,也包含了诗人自我不能实现的痛苦。朝代更替,给吴中文人带来尤为深切的沧桑兴废感。他们对朱明王朝也有“四塞山河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高启《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的肯定和赞誉,然而更多的则是对仕途险恶的洞察,和对故土亲情的思念。这和朱元璋对吴中文人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吴中是张士诚盘踞的地区,对这一地域的文人朱元璋特别警惕和嫉恨,也使吴中文人与朱明王朝之间形成一层政治隔膜。所以,“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高启《悲歌》)的思想在吴中文人中甚为普遍。面对动荡的社会和险恶的世情,那志深笔长、慷慨悲凉的汉魏古风和曾在忧患离乱中慷慨悲歌的杜甫,便成了他们取法的典范。而这样一种诗风,自然就会与杨维桢的“铁崖体”大相径庭了。
吴中文人在元末明初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以展示个性、消遣自娱、寄托忧思为主要目的,将拟古创作推向高潮。他们选择了汉魏诗歌与唐诗作为最高标准,并摹仿唐诗的诗律气格进行创作。但吴中文人还没有有意识地梳理诗歌源流以及总结拟古经验,这种崇唐拟古倾向大多是从他们的创作中流露出来,并没有人进行过系统全面的理论阐述。高启的“格、意、趣”说和“兼师众长”的理论很显然也是创作经验的火花和灵感所致。发展到后期,董纪才明确提出了“尊唐卑宋”之说:“夫诗自三百篇后,变而为五七言,盛于唐,坏于宋,不易之论也。”(注:《题瞻山赖实父诗集后》,董纪《西郊笑端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779页。)但又并未详细地阐叙,加上董纪、 管时敏等诗人学唐诗的成就远不及前期诗人,因而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看出这一地域文人集团诗歌创作的基本倾向。
二
浙江文人是朱元璋所倚重的开国文臣,在理学渊源上则多为金华学派的余绪。作为极力复归汉文化正统的儒者,他们为明王朝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推动了明初诗风的转变。然而,浙江文人更多的是以颇受重用的政治家的面目出现在明初文坛上,其作为文人集团的特点相对要淡得多。就诗歌创作成就来看,浙江文人也不像吴中文人之纯粹于诗,而是首重于文,次重于诗。所以浙江文人的诗歌理论是与他们的文论密切联系的,与他们文论的复古方向大致一致。基本上以“宗经征圣”为准则,以唐诗为楷模,以理明辞达为指归。
浙江文人钱宰说过,诗之抒情言志,发自人的心声,一旦遭逢盛时,便是以“黄钟大吕”之音来“鸣帝世之盛(注:《长啸轩记》,钱宰《临安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555页。)。 和历代文人一样,浙江文人也推崇《诗经》,在三百篇之下,以世运论,则认为唐为最盛。王祎说:“三百篇尚矣,秦汉以下,诗莫盛于唐”。他认为以时代高下论,唐诗有三变:“其始也,承陈、隋之余风,尚浮靡而寡理至。开元以后,久于治平,其言始一于雅正,唐之诗于斯为盛。及其末也,世治既衰,日趋于卑弱,以至西昆之体作而变极矣。”(注:《张仲简诗序》,王祎《王忠文集》卷五,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110页。)而唐诗之盛,正与国运的鼎盛相关。 浙江文人于唐朝诗人中,又最推崇李、杜、韩三人。贝琼论诗说道:“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认为李杜二人的诗,雄伟壮丽,气势豪峻,刚柔相济。推其因,大凡“约乎情而反之正,表里国风而薄乎雅颂”(注:《乾坤清气序》,贝琼《清江文集》卷一,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297—298页。),远绍诗经风雅,得古诗遗意。朱右说:“唐兴,以诗文鸣者千余家,其间足以名后世而表见者,惟李白、杜甫、韩愈而已。诗其可易言哉?何则?李近于风,杜近于雅。韩虽以文显,而其诗正大从容,亦仿佛古颂之遗意。以故传通后世,人宗师之。”(注:《羽庭稿序》,朱右《白云稿》卷四,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46—47页。)宋濂则论杜甫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类《雅》、《颂》者,虽长篇短韵,变化不齐,体段之分明,脉络之联属,诚有不可紊者”(注:《杜诗举隅序》,宋濂《文宪集》卷五,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381—382页。)。诗固系一代之政而鸣国家之盛,近世诗风委靡不振,学诗者当复之于古。那么,于古何所取法呢?王祎引用元人杨载的话,认为“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以唐为宗”(注:《练伯上诗集序》,王祎《王忠文集》卷五,四库全书第1226册,第106—107页。)。乌斯道以为要选择古今诗以取信当世,则诗必得《三百篇》之旨,得《十九首》之遗风,得盛唐之体(注:《乾坤清气诗序》,乌斯道《春草斋文集》卷三,四库全书第1232册,第227页。)。 浙江文人力图为鸿业初开的明王朝描画一派盛世景象,他们开始在历史上寻找具有这种盛世气象的文学,不自觉地对诗歌源流做出反思,而将目光大致定位于唐朝,追叙唐诗之风雅传统,将唐诗作为最能体现《诗经》、汉魏古诗传统的典范。这种对唐诗的肯定与其说是诗歌理论上的尊奉,更不如说是对盛唐气象的尊奉和向往。
浙江文人能诗者不太多,成就较高的是刘基、贝琼,此外还有胡翰、宋濂、乌斯道等。胡应麟曾以刘基作为浙江文人的代表,究其实,刘基确实是浙江文人中诗歌成就较高的诗人。但就这一文人集团而言,诗歌创作则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特点,且成就高下不一,很难以一人概之。
刘基论诗主讽喻说,他在《送张山长序》中说道:“余观诗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讽喻。盖欲使闻者有所感动而以兴其懿德,非徒为诵美也。”他的创作继承了美刺讽戒的传统,多忧时感愤、格高气奇之作。如《述怀》、《二鬼》、《感时述事》八首等,表现出作者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个人遭际的不平与家国的不幸都从刘基诗歌中喷薄而出,故气势雄浑,慷慨深沉,在骨力纤弱的元末诗坛呈现出一种卓荦不凡的气象。沈德潜评论道:“元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注: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一,第1页。)同时刘基也是师法汉唐诗歌并效摹其辞藻的,其《旅兴》五十首等作品便有魏晋诗风,近体诗也多化用唐诗意境。如《古戍》:“古戍连山火,新城殷地笳。九州犹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迥云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烧不尽,时见两三花。”(注: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六,《覆瓿集》六,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153页。 )尾联便是由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衍化而来,又如《丙戌岁将赴京师,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笔法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相似:“疲马怀空枥,征衣怯路尘。那堪远游子,复送欲归人。月满西津夜,花明北固春。论文应有日,话别莫悲辛(注: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四,《覆瓿集》四,四库全书第1225册,第110页。)。 ”刘基一些描写宫闱怨情的小诗也很动人。如《长门怨》、《玉阶怨》等,唐诗中也有类似的佳构。朱庭表《筱园诗话》卷二以为:“夫刘青田之诗,多皮傅盛唐,已兆七子先声。”
浙江文人中另一位较有影响的诗人是贝琼。在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贝琼无意出仕,唯隐居以自保。“病疑耽酒过,穷觉向诗工”(注:《寒食三首》之一,贝琼《清江诗集》卷六,四库全书第1228 册, 第245页。),他刻意工诗,是一位儒者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 入明后,贝琼任国子助教,其温丽雅正的诗风主要体现在写景抒情和酬唱赠别的七言律诗当中。贝琼曾学诗于杨维桢,大概“学其所长,不学其所短,宗旨颇不相袭。”(注:《四库提要·清江诗集》,四库全书1228册,第179—180页。)他论诗以盛唐为宗,品评各代作家作品也以盛唐为准,以李、杜为则。贝琼敏锐地感觉到元诗“务铲宋之陈腐,以复于唐”(注:《陇上白云诗稿序》,贝琼《清江文集》卷二十九,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485页。)的创作导向。 他的《琼台集序》论李廷铉诗说:“其五言、七言近体,必拟杜甫;其歌谣、乐府,必拟李白。呜呼!志亦勤矣。”(注:贝琼《清江文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第1228册,第 481—482页。)贝琼本人的诗歌创作温丽平腴而不失自然高秀, 只是对诗歌的格调未刻意探寻,有的诗过于平易而失之滑俗,行笔用韵略显得板滞。大体上,贝琼也以与元末风气相异的诗歌面貌出现,是明初诗坛主流的代表。
浙江文人集团的其他诗人都未曾刻意工诗,诗歌创作的数量远远少于文。其中,宋濂、王祎、苏伯衡以及后期的方孝孺都官至显位,所以他们的诗多为朝廷应制之作,较多地表现自己入世报国和官场进退之心,但也追摹唐人。如宋濂的诗,长篇规摹杜甫、韩愈,只是时或失之冗沓。他的应制诗歌主要是叙述国典之隆,展现明开国博大昌明的气象,已初显台阁之风。五言古诗如《送许时用还剡》,风格颇淳雅,却过于轻巧柔丽,未脱元习。王祎、苏伯衡的诗风与宋濂相似。另外,浙江诗人大都以五言古诗见长,如乌斯道《春草杂言》五首、钱宰《拟西北有高楼》、朱右《过杨井山》等,刻意复古,平易典丽,不为艳仄之声,有拟古的创作倾向。
综观浙江文人的诗论与创作,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浙江文人多为儒者之诗,托诗以言志,提倡实用主义的文学观。他们重视诗歌的现实作用,诗歌多吟咏性情之正,描写国朝之盛,故气格骨力超过吴中文人。只是在反拨元末轻艳靡丽之习时,不太讲究创作技巧,在艺术成就上不如吴中作家。其二,他们的诗歌倡言复古,但未有明显的拟古倾向;同时,理论与创作存在差距。他们理论上崇尚唐诗,但在创作上取法却并不那么一致,而是兼师汉魏六朝与唐诗,有时甚至兼受唐、宋诗风的影响。如后期诗人方孝孺于诗歌中多说理议论,他的诗如《闲居感怀》十七首之八:“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注: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1235册,第667页。 )表现了一位参政者的严肃思考,受宋人影响更大。也正因为如此,浙江文人的宗唐就较其它文人集团要复杂一些。
三
明初的闽中文人集团以其不同于吴、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展现出不同的风貌。闽中文人大多数并没有卷入明初的政治纷争,他们远绍南宋末闽地文学理论家严羽提倡盛唐诗歌的论诗言论,在自己的地域范围内继续着中原文化的积淀和吸纳,最后形成明初诗歌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唐诗品汇》。与其余各文人集团不同的是,闽中文人崇唐诗论主张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而开启明代闽地诗论与诗风的主要人物则是张以宁。
张以宁论诗以为“后乎三百篇,莫高于陶,莫盛于李杜。”(注:《黄子肃诗集序》,张以宁《翠屏集》卷三,四库全书1226册,第 590页。)后世学者多学杜,少学李。故张以宁比较李杜二人道:“尝窃论杜由学而至,精义入神,故赋多于比兴,以追二《雅》;李由才而入,妙悟天出,故比兴多于赋,以继《国风》。”(注:《钓鱼轩诗集序》,张以宁《翠屏集》卷三,四库全书1226册,第591页。 )他对宋人学杜提出批评,以为“善学杜者,必本之于二南风雅,干之于汉魏乐府古诗,而枝叶之以晋宋齐梁众作,而后杜可几也。盖必极诸家之变态,乃能成一家之自得。”(注:《马易之金台集序》,张以宁《翠屏集》卷三,第518页。)张以宁的诗歌, 后人评论说是“沉郁雄健者可追汉魏,清宛俊逸者足配盛唐”(注:陈廷器语,转引自《明三十家诗选》。),以为“其长篇浩汗雄豪似李,其五七言律浑厚老成似杜,其五言选优柔和缓似韦,兼众体而具之,信乎名下无虚士也。”(注:陈南宾《翠屏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35册,第667页。 )明初闽地以诗称者还有“崇安二蓝”,即蓝仁、蓝智。他们没有留下诗论,他们的宗唐倾向主要体现在具体创作中。其诗歌有的反映元末混乱的社会局面以及黎民百姓的痛苦,更多的诗篇则是抒发朝代变易之悲慨和仕途的险恶,以及隐逸自适的心态。在描写社会,体察民情,委婉而讽,诗律平和等方面,与杜甫有相通之处。而在写景抒情方面,又有王、孟的隐逸风格。二蓝诗力追盛唐,注重格律,尚无模拟痕迹。朱彝尊评价道:“(二蓝)体格专法唐人,间入中晚。盖十子之先,闽中诗派,实其昆友倡之。”(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对闽中诗论形成发生过影响的还有林弼。林弼于诗以三百篇为尚,另择汉魏、李杜诗歌为高格。他认为“三百篇者,昆仑也,渤澥也;汉魏李杜,乔岳也,大川也。”古人之诗高似昆仑,深于渤澥,后人纵使不能全部领会,则“一篇之佳,亦古人之一块;一句之善,亦古人之一沤也。”(注:《块沤集序》,林弼《林登州集》卷十三,四库全书1227册,第110—111页。)
考察一下以上几位诗人的籍贯,我们便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四人中,张以宁是闽东人,二蓝是闽北人,林弼是闽南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崇尚唐诗,这无疑标志着元代纤秾诗风在闽地的终结,而同时又为闽中十子宗唐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初闽地的诗歌创作和复古理论的高潮,是以林鸿为核心人物的闽中诗派形成和活动时期。林鸿于元明之际已有诗名,不过当时林鸿还未达到“开元之盛风”的境界。而十年之后,他完成了这个转化。其间,林鸿由将乐县训导擢升礼部精膳司外郎后,因殿前应制作《龙池春晓》、《孤雁》二诗而名扬京师。洪武十三年(1380)林鸿将诗集正式命名为《鸣盛集》,刘崧为其作序便说他“窥陈拾遗之阃奥而骎骎乎开元之盛风,若殷璠所论‘神来气来情来’者,莫不兼备,虽其天资卓绝,心会神融,然亦国家气运之盛驯致然也”。当时在明朝开国的台阁大臣中,以诗文名者都在倡导盛唐诗风。林鸿以“鸣盛”题其集,一是仿效唐朝“开元之盛风”,二是鸣“国家气运之盛”。据《明史·文苑传》记载,林鸿“年未四十自免归”。显然,林鸿是在完成了地域文化传统与国朝倡鸣盛世的复古思潮的融合之后,辞官归闽的。这时,其由宗唐到独尊盛唐的取向已日渐成熟了。当时,一批在闽地隐居不仕的诗人便聚集在林鸿周围,将其诗歌言论奉为圭臬,后人择其中诗名较大者冠以“闽中十子”之名,一时风气所染,彬彬称盛。不仅创作繁荣,而且以高棅的《唐诗品汇》的编选完成了规仿盛唐诗歌理论的全面总结(注:关于闽地诗歌的发展和“闽中十子”的形成,参阅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第五章第一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高棅《唐诗品汇》凡例中记载其理论依据道:“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予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辩,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由此可见,林鸿提出的以开元、天宝之诗为楷式的复古主张,为高棅《唐诗品汇》的编选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高棅推崇殷璠宗盛唐诗且审辨诸体的编选原则。与此同时,高棅也服膺严羽“以汉魏、晋、盛唐为诗,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诗论。这些正是高棅用以制订编选标准的理论借鉴。
《唐诗品汇》的编选目的甚为明确,即“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注:《唐诗品汇总序》,《唐诗品汇》第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版。)。高棅于《总序》开头便提出:“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他在每一种诗体的正始目都追溯诗体的源流以辨明各类体裁的客观发展过程。高棅以为文变系乎世运,因时代气运的变化,唐诗经历了四变:“隋氏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注:高棅《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正变》,《唐诗品汇》第51页。)从数量上看,《唐诗品汇》选诗以盛唐为主,盛唐又以李杜为主(李白选诗408首,杜甫选诗301首)。从品目上看,“正宗”是指远绍风雅,开创并展示盛世正派之音;“大家”是兼善众体的集大成者;“名家”是指鸣其所长,偏于一格的诗人;“羽翼”则是指辅弼、光大之意。这四目收入盛唐诗,可见高棅认为盛唐之诗代表了唐诗成就最突出的阶段。高棅在《总序》中列出“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四点来品评诗歌体格,兼顾了格调和神韵等方面,但只是单纯从形式上去分析唐诗,尚未达到较高的理论水平。在《总序》结尾,高棅指出:“诚使吟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由此可见,高棅的目的主要在于倡导盛唐之诗以供后人学诗有所楷模。高棅倾其学识才力研揣编选唐诗,在艺术上不无探索之功,同时这种对盛世之音的倡导,与上升时期的明王朝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吉玉融、马得华序《唐诗品汇》曰:“全闽学古者,振发歆动,能相与鸣国家之盛,必廷礼为之倡。”所以《唐诗品汇》一书之所以“终明之世,馆阁宗之”(注:《明史》文苑传二,第7336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也就是必然的了。
“闽中十子”的诗歌作品大多是在规摹盛唐这一理论指导下努力实践的结果。林鸿的古体采自汉魏以下,以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晋唐诗人的作品为师法对象。而林鸿之专学盛唐,主要指其五七言律体。五言律诗中,如《出塞》九首、《送高郎中使北》、《拟唐太和公主和蕃》等,声律气骨有开元之风。然而此类反映社会生活、咏史抒怀的作品也不多,大多数则是题赠送别、咏物观景之作,故诗风平易而无豪逸之气。七言律诗如《春日游东苑应制》、《春日陪车驾幸蒋山应制》四首、《早朝》、《金门待漏送别》等为应制诗作,格调端正,雍容雅致,有台阁诗风。“闽中十子”其他诗人也未脱离这种规摹、形似的创作风格。其中,王恭、王偁二人诗歌成就较突出。王恭论诗“五七言长歌、律、绝句,则一欲追唐开元、天宝、大历诸君子,而五言五选则时或祖汉魏六朝诸作者而为之,宋元而下不论也”(注:林环《白云樵唱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84—85页。)。他的诗歌取法范围较林鸿、高棅更广,但诗作流于中唐之韵,有大历十子遗音。王偁一生游历甚广,其际遇与李白相似,诗歌也多规摹陈子昂和李白。如《感寓》四十八首,便有陈子昂遗风。再如《塞下曲》、《将进酒》等歌行,深得太白风骨。近体诗则拘于格律,有摹仿之迹。高棅理论建树胜于创作成就,他以不同体裁效仿不同唐人:歌行仿李白,五言古诗有的效常建体,七言律则拟岑参、高适,都是盛唐之音,但只得字句,不见精神。其他诗人如郑定《渭上观猎》、王褒《元夕观灯应制》、唐泰《江上书怀寄周大林大》等也都是摹唐之作。
“闽中十子”以字句圆润秀美的诗歌不同于元末委靡纤弱之诗风,的确起了扭转风气的作用。然而单纯从形式上规仿盛唐“摹其色象,按其音节”,离盛唐格调还相差很远,加上诗歌内容多以游赏观景、应制酬赠为题材,反映生活面不广,所以尽管格律圆熟,却不免流于体格复沓、千篇一律了。闽中诗人试图从形式上叩开盛唐诗歌艺术殿堂的大门并收获到了《唐诗品汇》这样一个理论硕果,然而这种摹拟形似的复古理论用来指导创作,未免有较大的误区。尽管闽中文人对盛唐之音的推崇正好符合上升时期明王朝文化政策的要求,但他们的诗歌创作日渐流于肤廓空疏则是不容忽视的倾向。其结果,不仅盛唐气象未曾再现,反而使诗坛整体风格都向“台阁”诗风转化了。
四
“崇唐抑宋”倾向是明初诗坛复古思潮的一个较明显的特征,它与明初统治者“诏复衣冠如唐制”(注:《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三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525页。 )等政治复古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从诗歌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倾向既是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延续,又是明中叶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理论的先声。
唐、宋诗歌虽以朝代为分野,其门户之争却是由于风格的差异而造成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已经成为一种体制完备、非常成熟的体裁,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宋诗能有别于唐诗而独具一格,也自然是后代诗歌所难以企及的。正因为如此,后人才在唐诗和宋诗之间展开了一场与中国后半部古代文学史相始终的风格之争。
早在南宋初期,以张戒为首的宋代诗论家便对宋诗的发展道路作出过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张戒将诗歌分为五等,明确地划分了唐、宋诗的界限,谓“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并且对于苏、黄及其后学的作诗之法提出批评:“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他甚至认为“苏、黄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注:张戒《岁寒堂诗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33页、第37页。)。在对江西诗派的理论声讨中,曾几、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人在创作上各辟蹊径,终于走出了江西诗派的墙垣,使宋代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至此,南宋诗坛形成了公开批评宋诗流弊、转趋唐人的倾向。朱熹等理学家也参与其中,门户各不相同。而南宋中后期的唐、宋诗之争主要表现为对江西诗风与永嘉诗风之间的争论。南宋末批评家严羽立足于救弊补偏,将目光集中于盛唐诗歌,得出“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四库全书第1480册,第812页。 )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于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作了全面的艺术上的探寻,为南宋时期唐、宋诗之争划上了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句号。
和南宋相呼应,北方的金也展开了对宋诗的批评。金人论诗主张复古,以为“当师《三百篇》、《离骚》、《文选》、《古诗十九首》,下及李、杜”(注:《答李天英书》,赵秉文《滏水集》卷十九,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256页。)。由唐而及魏晋、秦汉, 师古对象并非单一。对于唐诗,各自的师法对象也不同。如赵秉文作诗师法杜甫、柳宗元、韦应物;王若虚则学白居易,元好问在推崇韦应物和柳宗元时,还上溯至陶渊明和谢灵运。当时的唐诗选本《唐诗鼓吹》则多选中晚唐律诗。“大抵遒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注:《四库提要·唐诗鼓吹》,四库全书第1365册,第382页。 )元人继承南宋与金代诗坛的诗学风气:一为宗唐,二为复古。但也不是那么统一的。元人选取了较宽泛的取法唐诗的道路。方回之后,戴表元提出“宗唐得古”之说。戴表元的学生袁桷承其师说,也将眼光转向了唐:“诗盛于唐,终唐盛衰,其律体尤为最精”(注:《书番阳生诗》,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643页。); “松雪翁诗法,高踵魏晋,为律诗则专守唐法。”(注:《跋子昂赠李公茂诗》,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九,第649页。)此后, 随着元代南北复古诗风的汇合以及对前朝诗风的批评,崇唐抑宋的诗学风气愈演愈浓。表现在创作上“近时学者,于诗无作则已,作则五言必归黄初,歌行、乐府、七言蕲至盛唐”(注:欧阳玄《萧同可诗序》,《圭斋文集》卷八,四库全书第1210册,第63页。)。元代中后期诗人在诗歌复古上,主张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而宗唐诗则不甚分初盛中晚(注: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六,《笔记小说大观》本十六册,第32页。)。元人这种宽泛地学唐,使元末诗歌出现了纤弱的倾向。然而,当元诗中这种纤秾诗风出现的时候,诗坛上对盛唐诗风的提倡也同样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元中后期出现的唐诗选本——杨士弘的《唐音》。他不满前代诸选本之略于初盛而详于中晚,将唐诗分为“始音”、“正音”、“遗响”。其中“正音”再以体制分类,收诗数量甚多,体现其以盛唐为宗的选诗倾向。这样,从南宋严羽到杨士弘的《唐音》,以盛唐诗歌为典范的倾向在唐宋诗之争中越来越凸现出来了。
经过元代诗人对宋诗救弊补偏的反思以及倡导宗唐得古的艺术追求,明初诗坛对宋诗的关注甚微,仅体现在寥寥几位对宋诗有所袒护的诗家评论中。明初文人黄容在《江雨轩诗序》中记载了江右诗人刘崧的“宋无诗”说。他指出:“近世有刘崧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他姑置之,诗至《三百篇》至矣,何子夏、毛苌之论,尚遗所昧,寥寥千五百余年,至朱子而始明,宁无一见以及崧者。”(注:黄容《江雨轩诗序》,见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第257页。 )黄容于宋诗中举出朱熹来反驳刘崧的“宋无诗”说,显然流于理学派一脉,所以尽管他在下文斥责之词激烈,却不为诗家所认同。另有瞿佑在《归田诗话》上卷也批评了当时诗坛的崇唐抑宋倾向:“(又谓)世人但知尊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辞,乃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瞿佑则以为“举世宗唐恐未公”。于是他编选宋、金、元律诗为《鼓吹续音》,作为元好问《唐诗鼓吹》的继续。瞿佑的言行只不过对诗坛的整体倾向提出反拨,未触及唐宋诗之争的关键问题,故影响也不大。此外,由于朱元璋以理学开国,而宋代理学盛行,势必引起致力于政治复古的文人的重视,其中主要是对宋文的肯定。宋濂在《苏平仲文集序》中论文“自秦以下,莫盛于宋”;方孝孺则发挥宋濂之说而论诗:“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注:《谈诗五首》之二,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四,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722页。)这种文学观点是与明初复归正统的思想相契合的, 但在指导诗歌创作方面作用不大。在明初诗坛上,既与政治复古的时代背景相呼应,又符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的思想倾向仍是“宗唐”。
如果以时间顺序串联明初五大文人集团的诗歌创作与理论,便不难发现:在诗歌复古道路上,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宗唐取向对元末诗风进行反拨,对于开明诗雅正之风有着轻重不同的推进作用。在对复古诗歌孜孜以求的探索中,盛唐诗歌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高峰而得到明初诗人们的肯定和认同,他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专宗盛唐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初诗人推崇盛唐,是对元人广泛宗唐所导致的纤秾诗风的流弊有所体察和反思的结果,同时又与明代开国时润色鸿业的文化要求相统一,从而成为明初崇儒复雅的文学潮流中的重要部分。在明初崇儒复雅的文学潮流中,有的侧重于崇儒,有的侧重于复雅。所以规摹盛唐诗歌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吴中、闽中和岭南文人侧重于艺术形式上的规摹。江右和浙江文人则主要是从诗歌的时代内涵方面规摹盛唐诗歌。他们倾慕于盛唐诗歌雍容大方的气象,地负海涵的内容以及繁荣昌盛的时代气氛。在对盛世之音的倡导中,盛唐诗歌作为诗歌复古的典范,成了明代庙堂文化的重要内涵。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明初诗人在理论上规摹盛唐,在创作中却并没有达到盛唐诗歌的艺术水平,甚至反而因门户之见而水平愈下了。在入明之初,吴中文人高启以兼师众长、随事摹拟为拟古原则,在创作中既摹拟古人又驰骋才情,诗歌风骨遒健,才气横逸。浙江文人刘基则是以儒家风雅传统,于拟古之中更多地注入忧时愤世、关注社会的现实内容,使诗歌沉郁顿挫,独具风格。他们的宗唐理论与拟古创作还能够达到一致。到“闽中十子”就不同了,尽管他们标榜盛唐之音,个人创作却又往往流于中、晚唐风格。江右、岭南文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岭南诗人孙蕡的诗歌,如《南京行》、《云南乐》、《湖州乐》、《广州歌》等写都市繁华的景象,以及经济的活跃,反映出明开国之初诗人的喜悦心情。《国雅》评论岭南诗人道:“广中四杰,并有盛才,特闲于七言。如孙(蕡)之《蒋陵儿》、《次武昌》,黄(哲)之《站城南》,李(德)之《秋情》等篇,能自迥出常境,绮崭处亦类初唐语”(注:转引自《明诗纪事》甲签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将南园前五子的诗歌风格归于初唐一类是较为客观公允的。江右诗人刘崧论诗推崇盛唐,诗风与盛唐也相距甚远。后来江西诗人作为“台阁体”的主力,他们倡导盛唐诗歌“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注:《玉雪斋诗集序》,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3页。),将诗歌的内容局限在歌咏升平、褒扬正统的思想范围内,最终流于肤廓平庸,典雅而平淡无味,诗风日益卑冗不振。
明初诗人规摹盛唐,但由于时代氛围的影响和个人才气的局限,他们诗歌中得“盛唐之音”的方面是有限的。这同时也向人们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复古诗歌的创作与其它创作活动一样,是各种创作因素的整合,单纯从古人的经典诗作中套用其格式,或者一味想重复古人的创作实践以达到古人的创作成就,都是不可取或者不可能的。到后来,李东阳力矫“台阁体”之弊,首倡“格调说”。前七子为文学复古确定了明确的模式:楚骚,汉赋,唐诗。他们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试图找出各种文体的典范以创造出典范的封建文学,并以此作为复古文学的最高追求。他们这种对复古文学范本的选择对于复古理论——格调说的最终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诗歌复古理论的自成体系,它对复古诗歌创作的指导作用却越来越弱了。这样,在明代诗歌复古理论的演进中,创作对理论的偏离也愈来愈远。综观南宋以后整个诗歌复古的发展历程,唐、宋风格之争作为一条线索一直贯穿始终,而明初诗坛这种尊唐抑宋倾向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体现出文学自身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面貌。
标签:诗歌论文; 明诗别裁集论文; 唐诗论文; 读书论文; 唐诗品汇论文; 杨维桢论文; 张以宁论文; 吴中论文; 明诗综论文; 古诗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