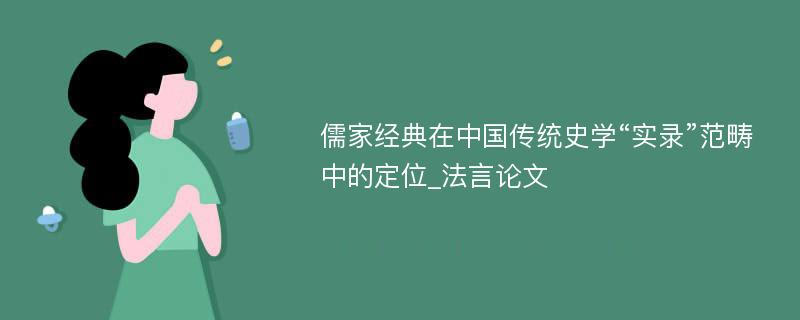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史学论文,取向论文,中国传统论文,范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实录”既是一种历史著作的书名或体裁文类,也是一种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从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方面说,实录观念肇始于先秦的“书法不隐”,汉代史家围绕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论,提出了实录概念,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的阐发申论,唐初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实录论,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观念和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核心观念和范畴,历代史家论述很简略,对实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清晰界定,人们对实录的理解也一直比较笼统和感性。一般认为,实录就是史家在历史撰述过程中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并将实录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予以赞誉。在这层意义上,实录与求真、信史、直书等概念密切关联,人们甚至把这几种概念混而用之,如在史学批评中常说“直书实录”等。我们认为,要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实录观念有切实认识和把握,必须弄清实录观念中三个核心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载录史事,二是用什么样的文字和叙事方法载录史事,三是载录什么样的史事。综合历代史家关于实录的相关表述可以看出,在《春秋》经学的统摄和导引下,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以彰善瘅恶、劝诫褒贬为终极目的,以史载道,撰史明道,用寓含褒贬的语言文字和蕴藏史家撰史旨趣的体裁体例载录史事,劝诫资治,弘扬道义,为当世朝野提供道德示范和王道借鉴。与近现代史学揭示历史真相、客观认知历史的史学目的和理性要求不同,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将道德评断导入历史事实,呈现出客观性和道德性二重属性。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亦经亦史,半经半史,以经为体,以史为用,充溢着较浓厚的经学趣味,体现了经学对于史学的统摄力。本文拟通过对班固、刘勰、柳虬、刘知幾等人的实录观念的简要分析,阐释中国传统史学中实录观念的经学取向。
一、《春秋》经学与扬雄、班固对《史记》的实录评价
五经之一的《春秋》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根基。大体而言,《春秋》给予中国传统史学四大导向:其一,“书法不隐”的书法原则;其二,通过一定的记事原则对历史事件毁誉褒贬,从而体现褒善贬恶道义的“春秋笔法”;其三,为尊者、贤者、亲者讳饰的道德理念;其四,求善劝诫的治史目标。
从南史书“崔杼弑其君”和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两件史事来看,孔子赞誉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孔子所言“不隐”应该是指不隐善恶,不隐道义。由于儒家经典的记述和圣人孔子的赞许,“书法不隐”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学术范式和作史原则。
面对春秋时期世衰道微、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编订《春秋》,以图维系世道人心,达义救世。孔子编订《春秋》的理念和作史方法,后人概括为“春秋笔法”。虽然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春秋笔法”可能有不同理解,但《左传》概括出《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①就是“春秋笔法”的主要内涵。《春秋》五例是《春秋》经学经法、史法和文法的统一。简言之,经法旨在惩恶劝善,以求善为目标;史法旨在通古今之变,以秉笔直书的态度和撰史方法求真求实;文法立足于属辞比事,以显褒贬劝诫之意。
在继承先秦史学秉笔直书和书法无隐撰史传统的基础上,围绕对《史记》的评论,汉代史家提出了实录概念。从现有材料看,“实录”一词最早出现于扬雄《法言·重黎篇》:“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扬雄用“实录”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有些突兀,让人很难理解他所言实录的内涵,以及他选用“实录”二字的意蕴所在,故宋代宋咸、司马光等人在注《法言》时对扬雄所言实录的含义就有不同理解②。
扬雄在《法言·重黎篇》中用“实录”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虽然没有对实录的含义做具体说明,但他在《君子篇》对《史记》有一个较明确的评论,有助于我们对扬雄所言实录的理解。扬雄《法言·君子篇》把刘安《淮南子》与司马迁《史记》进行对比,认为“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显然,《史记》对于圣人之用是扬雄最为称许的。《淮南子》浮辩虚妄,杂而不典,不可取信,而且其思想主旨是黄老道家,宣扬的是由文返质,无为而治,与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有较大差异,对于维系世道人心用处不大,故圣人君子弃而不用。《史记》则实录不隐,如鲁史旧文,故圣人将有采择以正褒贬。综合《法言·君子篇》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扬雄所言《史记》对于圣人君子之用主要在于其蕴含的天人相关之理,古今变化之势,兴衰治乱之迹,维系世道人心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扬雄撰写《法言》的动机和旨趣亦是我们理解其实录观念内在意蕴的窗口。《汉书·扬雄传》载: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据此可知,扬雄是站在儒家经学立场上评价司马迁的,并概括出《史记》的“实录”性质。扬雄用“实录”评价《史记》,其意在批评司马迁不为尊者隐讳,历史观点不同于圣人,是非评价谬于《春秋》经学。在扬雄眼里,那些有损汉初诸帝形象的史事,本来都是要隐讳的,但司马迁却都如实记载。这种不顾场合,不分对象,不知讳饰的大实话,扬雄称之“实录”,这或许是“实录”最初始的意义。
与扬雄不同,班固从史学批评的角度肯定司马迁所撰著的《史记》是实录,但班固所言的实录,其意义较扬雄有所引申和扩展。他说:
然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③班固不同于司马迁,是一个虔诚的儒家卫道士,宗经矩圣。他“旁贯五经,上下洽通”④,撰写《汉书》,其宗旨在于宣汉。西晋傅玄批评班固说:“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⑤在撰史方面,班固虽然与司马迁异趣,但他也用“实录”二字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并从义、文、事三个方面阐明其理由,大体上还是用“春秋笔法”的标准对《史记》进行评价。
“善序事理”是说《史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阐明了历史中蕴含的“道”。关于“事理”,章学诚解释说:“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⑥道存于史事中,事中蕴含道义,若要事中见道,以事明理,文字表述和历史叙事的方法就很重要。讲求词序是《春秋》属辞的特点之一⑦,讲求时序是《春秋》比事的主要方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⑧。只有词序、时序顺畅合理,事理才能昌明,大道才能彰显。班固认为,司马迁得《春秋》属辞比事之旨,叙事井井有条,事理晓彻。对此,刘勰看得很清楚,他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指出,《史记》“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⑨。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是说《史记》在文字表述上严谨、准确,文如其人其事,文质相称。“春秋笔法”既是经法、史法,也是文法。在文法方面,《春秋》尚简用晦,用词极其严格,通过特定的词和词序,达道义,彰善恶,寓褒贬。班固认为,《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的文辞特点与春秋笔法中的文法是一致的,即用词准确,质朴切直,不浮夸粉饰,不粗俗鄙陋,叙事恰如其分。
班固认为《史记》“事核”,即所叙历史事实真实、准确、可信,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隐善恶,不隐道义的“书法不隐”是孔子称赞的作史原则,春秋五例中第四例“尽而不污”,说的就是叙事要尽其事实而不纡曲。杜预《春秋序》说:“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⑩显然,《春秋》对于违礼背道的人和事,直书其事,不加隐晦。班固认为,“事核”是实录的应有之义,要求史家撰史要做到事实清楚,翔实正确,其思想应该是来源于《春秋》经学“尽而不污”,“直书其事”之例。班固所言“事核”之“事”,并非全部历史真相,而是历史上的善、恶之事。
彰善瘅恶是《春秋》的宗旨,也是孔子编订《春秋》的终极目的,反映了《春秋》经学对历史撰述的基本要求。《春秋》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惩恶而劝善。班固说《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即认为《史记》在文直、事核的基础上,对善人善事善行如实记述,对恶人恶行不隐讳,做到美恶如实,揭示于世。明代何乔新曾指出,《史记》所写“伯夷古之贤人,则冠之于卷首;晏婴善与人交,则愿为之执鞭,其‘不虚美’可知。陈平之谋略,而不讳其盗嫂、受金之奸;张汤之荐贤,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隐恶’可见”(11)。钱大昕批评王允所谓《史记》“谤书”之说,认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何名为谤?且使迁诚谤,则光武贤主,贾、郑名儒,何不闻议废其书?故知王允偏心,固非通论”(12)。
若以近代客观史学来比照,扬雄、班固所言的实录,虽然是记录历史事实,但这个事实并非历史本相,而是对依照儒家标准而呈现的善事恶行。对这些善、恶之事如实记录,便是实录,与近现代史学揭示历史真相、科学认知历史的治史目的和客观理性要求并非同义。
二、依经附圣是直书实录的前提和原则
汉代围绕《史记》评论提出实录概念,并逐渐得到后世史家的认同和接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录”成为史家史学批评常用术语之一。南朝沈约批评一些有关南朝刘宋的史著“多非实录”(13),遂决心重新撰修。北魏高允认为,“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14),用“实录”来评定历史撰述的政治性质和鉴戒功用。崔鸿自言其所著《十六国春秋》删正旧史差谬,“定为实录”,用“实录”标示其历史著作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刘勰一直以直笔撰史的倡导者而为史家所称道。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对魏晋以前史学发展边叙边议,通过对史家史著的品评,阐发他的史学观念。在刘勰诸多史学观念中,直笔、实录观念是其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概言之,针对魏晋时期种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刘勰提出严厉批评,既谴责班固遗亲攘美,征贿鬻笔,批评袁山松《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偏颇杂驳”;又呵斥薛莹的《后汉记》、谢承的《后汉书》“疏谬少信”。通过对曲笔作史的批评,表明他对于直笔的向往和尊崇。对于《史记》,刘勰承袭扬雄、班固的观点,给出“实录无隐”的评价,称赞《史记》叙事有法,实录无隐,文辞博雅弘辩。在对魏晋以前史家史著品评褒贬以后,刘勰提出撰史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极力倡导史家在撰史过程中要做到“文疑则阙”,“析理居正”,尽可能撰写信史,并将“良史之直笔”定为“万代一准”。在《史传》篇最后,他宣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综观《文心雕龙》中《宗经》、《征圣》、《史传》诸篇,我们不难看出,刘勰的直笔、实录观念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经上位,史下位,史学原则从属于经学原则。《文心雕龙》开篇就是《原道》、《征圣》和《宗经》。他在《宗经》篇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即经是最高的道,是一切撰述的总纲。从史学方面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纪传盟檄,《春秋》为根”,《春秋》既是儒家经典,也是史学之根,《春秋》五例是一切历史撰述的准绳。只有宗经,历史撰述才能做到事信义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在刘勰看来,直书、实录的前提是宗经,依经撰史,自然就能做到“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
第二,撰史要依经附圣。虽然刘勰一再强调直笔作史,但他又在《史传》篇中说:“是立义远言,宜依经以树则;劝诫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意思是说,任何历史撰述必须符合经义经法,是非评判,善恶权衡必须以圣人之言为准的。他在《征圣》篇亦主张:“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也就是说,对历史著述的评价必须征诸圣人之言,检之以圣人的是非褒贬,从而构建起由经窥圣、由圣统文的逻辑顺序。
第三,撰史的目的不在于保存历史事实,也不在于客观认知历史,而在于求治和求善。通过历史撰述,“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直笔撰史也是为了“彰善瘅恶,以树风声”(15)。
第四,通过属辞比事,寓褒贬于历史叙事之中。刘勰指出:“《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刘勰十分推崇《春秋》微言大义,著史也要依《春秋》之例,通过对善恶得失的记述和褒贬,让天下百姓知晓道义所在,礼义所向。
刘勰的直笔、实录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以经统史、史归于经的思想主张,使刘勰的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经学取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虽然从学科分类上离经自立,但史学的内在精神仍然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
北周史官柳虬有一篇上疏,对史官密书善未足惩劝提出批评,要求史官当朝显言其状。柳虬说: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
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
伏惟陛下则天稽古,劳心庶政。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16)柳虬首先肯定了直书的史学传统,同时指出史官密为记注的制度影响了直书作用的发挥,成为曲笔产生的一个制度性根源。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坚持直书,避免曲笔,更好地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呢?柳虬提出:“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
人们一般都很关注柳虬所宣扬的直笔主张,但柳虬上疏中还有两句话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第一句是“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在柳虬看来,直笔撰史,并不是保存历史事实,也不是客观记述历史发展过程,更不是科学客观地认识历史,而是要以道义为准绳,以辨善恶、正是非的旨趣载录史事,记功过,表兴衰,以为当世鉴戒,弘扬道义,为社会树立道德典范和伦理标杆,这种撰史目的与传统经学要求完全一致,经学旨趣浓厚。柳虬虽然说的是直笔撰史,但这种直笔与近现代史学要求客观记述、揭示历史真相,科学理性认知历史的撰史理念大相异趣。第二句是“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柳虬认为,密书记注制度虽然客观上可以为后世留下一些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无益于当世。在柳虬看来,史官撰述有益于当世才是最重要的,董狐、南史勤于记注,敢于记注,直笔记述,但所记注君主言行并不是为了让记注文字流传和保存,而是通过记注为当代人呈现善恶的标准,为社会提供道德示范,为当下政治提供可资鉴戒的政治实例。在为后世保存历史真相与为当世提供政治鉴戒和道德示范两种选择中,为当世彰显善恶,树立风声才是“实录”的首要义旨,史官应该通过历史撰述直接参与当代的政教风化。在这一意义上,史学已成为经学的工具。
三、在《春秋》大义下直书与曲笔折衷调和
刘知幾《史通》的问世,表明唐朝初年,予夺褒贬、彰善瘅恶的实录史学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实录”也从较为模糊的一般观念升华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核心概念和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从实录观念升华到较为系统的实录论,刘知幾做出了重要贡献。关于刘知幾的实录论及其史学理论贡献,许冠三先生《刘知幾实录史学》已有深入的研究,傅振伦、施丁等先生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知幾在《史通》中一方面称赞直书,倡导实录,坚决反对曲笔,一方面又为曲笔留下一扇方便之门,并极力为曲笔现象提供合理解释和辩护,陷于自我矛盾之中。刘知幾这种无法挣脱的自我矛盾,恰恰是《春秋》经学道德取向与史学客观取向之间矛盾的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刘知幾的实录论,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而且是经为体,史为用。
坚持直书实录,反对曲笔作史是刘知幾的基本史学主张,也处于其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傅振伦先生曾经说:“盖知幾主张撰述史书,贵为实录。”又说:“知幾既以史之所贵,在于写真,求为实录。”(17)许冠三也说:“知幾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盖《史通》四十九篇,实无一篇不以‘明镜照物’之直书为依归,亦无一篇不以‘据事直书’之实录为准。全书八万九千字,亦无一字不在讲究‘善恶毕彰,真伪尽露’。”(18)
刘知幾的实录观念源于《春秋》经学,承继于扬雄、班固,发扬于刘勰《史传》。他在《鉴识》篇中说:“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孔融)之含异,等公干(刘桢)之有逸,如子云(扬雄)之含章,类长卿(司马相如)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刘知幾所言的实录,除重申班固实录观念外,对史文是否质朴切直,表述是否虚华更为关注。在《惑经》篇中,刘知幾又说:“史官执简”,宜类“明镜之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之传响,清浊必闻”,要做到“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样才能称为“实录”,这与班固“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观念近乎一致。关于直书撰史的目的,刘知幾也仍然停留在《春秋》惩恶劝善、达义明道的基本旨趣上。《载文》篇云:“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真)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刘知幾所言的“直书”是一种相对意义的直书,而非绝对意义的直书,他同时为曲笔留下了一扇方便之门。直书是刘知幾实录观的核心,《史通·直书》篇虽然慨叹直书实录之难,但还是极力推重“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直书精神和崇高气节,强调“史之为务,申以戏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移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如果仅从《直书》篇看,刘知幾的直书包括史官写史独立性和作史客观性双层含义,与近现代史学客观理性相近。但刘知幾在《曲笔》篇中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后兹以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面对直书善恶与恪守纲常名教的冲突,刘知幾做了让步。本来隐讳是《春秋》之义,与客观理性意义上的直书实录是矛盾的。但刘知幾承认“子为父隐”的隐讳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是另一种形态的直书,刘知幾的直书在名教面前转了个弯。即使是直道不足,只要能够弘扬名教,恪守名教,曲笔是可以理解并被接受的,这就为曲笔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也使其直书呈现出相对性。换言之,刘知幾所言直书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直书,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直书,内含史事客观性和道德崇高性二重属性。
刘知幾在主张直书同时,又为曲笔辩护。刘知幾把曲笔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真正的曲笔,一种是合情合理的曲笔。他所反对的是真正的曲笔,对合情合理的曲笔不仅包容甚至怂恿。《史通·曲笔》载:“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书》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异豺虎可也。”这些都是刘知幾所言的真正的曲笔,他对此斥之深,恨之切。从刘知幾列举的这些真正的曲笔事例来看,都集中于史家因动机不纯,史德不高造成的曲笔。而对于那些事涉君、亲,言多隐讳的曲笔,在刘知幾看来,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是撰史时所必须做到的。因为这种曲笔也是另一种形态的直道,即使有违直道,但符合《春秋》大义,符合纲常名教的道德要求。他说:“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19)只要史家撰史动机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符合《春秋》大义,宣扬纲常名教,即使是曲笔,也是合情合理的,不仅不要谴责,反而要给予包容和鼓励。在刘知幾的观念中,直书与曲笔两种尖锐对立的撰史态度和作史方法,在《春秋》大义和名教原则下,居然得到折衷调和。这种折衷调和实质上是以史学牺牲自身独立性和客观性为代价,向经学屈服的结果。以坚持直书,反对曲笔而著称的刘知幾在《春秋》经学的道德性和史学的客观性选择中,偏向经学一方,成为经学的守望者。
注释:
①《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
②宋咸注云:“迁采《春秋》、《尚书》、《国语》、《战国策》而作《史记》,其议事甚多疏略,未尽品藻之善,故扬雄称实录而已。盖言但能实录,传记之事也。”司马光注云:“记事而已。”
③《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曰”。
④《汉书》卷一百《叙传下》。
⑤转引自刘知幾《史通》内篇《书事》,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0页。
⑥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9页。
⑦如《春秋》僖公十六年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六年载:“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之嗔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董仲舒亦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陨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鹢之辞是也。”可见,“石五”、“六鹢”的词序正反映出记录者观察之先后次序,若写成“五石”、“六鹢”则谬而不真。
⑧《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⑨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史传》,祖保泉解说本,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⑩《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
(11)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二《诸史》,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
(1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史记志疑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3)《宋书》卷一百《自序》。
(14)《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
(15)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史传》,第295页。
(16)《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
(17)傅振伦:《刘知幾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4页。
(18)许冠三:《刘知幾实录史学》绪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
(19)刘知幾:《史通》内篇《书事》,第405页。
标签:法言论文; 汉朝论文; 司马迁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读书论文; 史通论文; 史记论文; 国学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