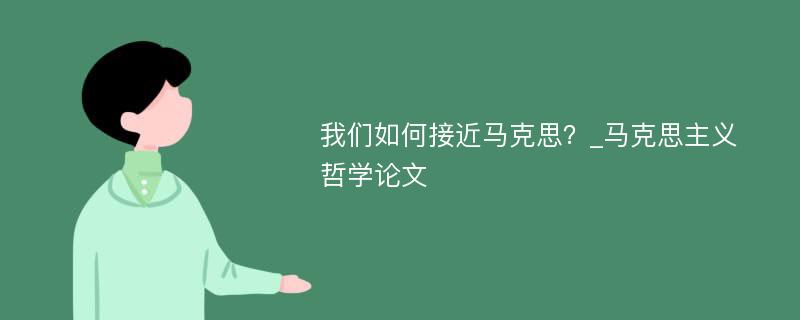
我们如何走近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504 (2000)03—0005—05
一、一个世纪性的“悖论”
在物理时间的意义上,我们的确告别了旧的世纪。然而,人的历史并不是由纯粹的物理时间所构成,历史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活动的结果。因此,物理意义时间的流逝,决不表明我们的精神状态、思想状态和生存状态已真正走出了旧的世纪,我们仍然需要清醒头脑,把20世纪没有完成的事情继续认真地做下去。
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说,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正是在上个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入中国,由此便开始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史,并且与这部理解史相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国家的思想理论话语中,逐渐奠定了其十分独特的地位,它不仅直接制约着哲学中其它领域的理论发展状态,而且还由于它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因而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合法性根据的重大职责。由于这种十分独特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命运与整个国家和全体中国人的生存命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极为重大的内在关联。深入地去反省这段历史,我们一定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过去的世纪决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告别的世纪,这其间诸多的经验教训,是决不应该随“旧世纪”日历的翻过而随风而去的。
回顾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贯穿于其中的主题无疑就是究竟应如何“走近”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究竟如何以一种符合其理论本性的方式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人们就始终在努力“走近”马克思,企求按照“马克思本身”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在此过程中,再三重复而挥之不去的却是这样一个悖论性的现象:当我们似乎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近”,即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词句最为熟稔,甚至倒背如流的时候,历史却表明:马克思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愚蠢、偏见和狂妄,此时,马克思实际上离我们无比遥远;可是,当我们似乎离马克思“最远”,即我们把眼光放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上,从实践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之时,历史却恰恰证明:马克思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离马克思最近。
这似乎是悖论,然而却是事实。可以说,近一个世纪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一直在循环着这一“悖论”,而且越是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这一“悖论”就表现得越突出,对中国人生存命运的影响就越大。对于这一“悖论”性的事实,人们通常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词句并没有错,只是由于人们把它们教条化了,才导致或“左”或“右”的恶果,只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就可以在现实中避免错误,无往不胜。这一解释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拒绝简单的答案而把问题推向更深入的层面,人们就需要进一步追问:教条之害,可谓人人皆知,可为什么在“人人喊打”之时仍然会再三重犯而难以根除呢?实事求是之益,也是人人知晓,可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会一再地边高喊着“实事求是”的口号,边陷入虚幻生活的泥淖呢?在新的世纪里,人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是否能获得一种成熟的智慧,从而避免重蹈以往的失误并彻底超越那一历史性悖论的方法呢?
我们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件事情是不可回避的:一是必须深入检讨导致上述这一“悖论性”事实的深层症结,二是必须“回到事情本身”,重新反省我们究竟应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走近”马克思。只有在这两方面实现一种深刻的“意识转变”,我们才能真正自信地告别“旧世纪”,走上“新世纪”的征途。
二、“实践优先”与“开放创造”:马克思所独具的理论境界
正如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同的“品位”和“档次”一样,哲学理论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品位”和“档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而思想品格和理论境界是一种理论最重要的东西。在深入检讨导致前面那一悖论性事实的深层症结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跃进思想深处,切实领会马克思哲学所独具的思想品格和理论境界。我们认为,马克思高出哲学史上其它思想家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它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完整地确立了实践观点,并从此出发,彻底颠倒了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生活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对理论“存在本性”和“存在方式”的理解,从而真正使“开放创造”成为了理论的生命之源和自觉追求。
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迷恋是马克思之前一切传统哲学的根本特点,它们为自己设定的使命在于以一种超验的实体主义方式去一劳永逸地捕获世界的“最终奥秘”,因而,它认为其理论必然具有如下性质:(1)绝对性,哲学理论代表着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都适用的“绝对真理”,具有超越时空、“永恒在场”的性质。(2)神圣性, 哲学是少数具备超人慧眼的人从事的事业,这些人超越世俗芸芸众生而与真理同在,因而具有超凡脱俗甚至神秘的性质。(3)封闭性。 哲学既是世界和人的生活实践的规定者,又是理论自我存在的规定者,因此它自足完备、毋需外求。把理论予以“绝对化”和“神圣化”并由此而导致理论的“封闭化”,这种对“逻各斯”的虚幻崇拜构成了整个传统哲学的旗帜和徽章。
与此不同,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凸显了“实践优先”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彻底颠覆了哲学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把理论神圣化、绝对化和封闭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从而完成了一种根本的范式转换。他第一次获得了这一洞见:在理论与实践二者关系中,实践具有首要的、优先的地位,理论惟有忠实并创造性地回应实践,才能证实其自身价值,否则它就会成为生活实践的绊脚石,与生活实践相比,一切理论体系都不是自足的而是有“缺口”的,不是充足的而是“不完备”的,不是已“定性”的而总是“不定性”的。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一切理论都具有如下特点:(1)相对性。 任何理论都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生存境遇,才能确证其存在价值,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适用的理论等于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不适用,因而是毫无意义的。(2)世俗性。理论不是高居于生活之上的神圣之物,相反, “在黑格尔之后,哲学已经变为一种世俗的东西了”,这即是说,哲学不是透明纯净的水晶宫里的向壁思辨,其生命之根深植于不断变动、充满矛盾的尘世生活之中。(3)开放创造性。相对永恒变动、 无比复杂的生活实践,任何理论都不能把现实生活的所有真理一网打尽,因而都是不完备、不充分的,因此,一切把世界和人的现实生活限制在一个原则上的企图,都不过是理性的幻觉和僭妄,只有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开放自身,创造性地更新其内容和形式,理论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可见,马克思立足于自觉的生活实践观点,自觉地把“开放创造”作为理论的生命之源,彻底放弃了从原则和教条出发来强制性地规范生活实践的企图,把理论从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之中解放了出来,从而第一次实现了“理论的解放”并因而实现了“实践的解放”。可以说,正是“实践优先”与“开放创造”,构成了马克思所独具的、区别于一切传统哲学的理论境界,正因为此,我们才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哲学史第一个“自觉的理论”,或者说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理论的自觉”。
“实践优先”与“开放创造”成为马克思所独具的理论境界,这与马克思追求人类幸福、自由和解放的思想信念与价值指向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真诚地相信,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的实践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性,理论惟有服从这种实践,创造性地向这种实践开放,为它提供积极的思想支持,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在此意义上,“实践优先”与“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在最深层所表现的是马克思献身人类福祉、追求人类解放的无私情怀。
三、“境界”的失落:难以“走近”马克思的深层症结
在明确了马克思所独具的理论境界之后,回头反思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上,当我们因犯各种或“左”或“右”错误、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失落了马克思“实践优先”与“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之时。“实践优先”与“开放创造”境界的失落,是人们难以走近马克思的深层症结。这种理论境界的失落,最集中地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把马克思哲学当成一种十分狭隘的宗派性理论,并从此出发,既拒斥吸收人类文化的其它精神营养,又拒斥回应现实生活实践的新鲜刺激,最后使马克思哲学完全自我封闭起来,成为一种可在任何时候适用于任何问题的抽象原则。
在历史上,我们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万能钥匙”,宣称只要掌握了这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所有“锁头”;我们也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化成某种可筛选“精华”和“糟粕”,实现择优汰劣的现成原则,这种原则往往通过一种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来体现,如物性与人性、群性与个性、理性与非理性、一元论与多元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可知论与怀疑论……,等等,在这些二分法中,前者总是优越于后者,只要坚持前者,就可放心地在后者身上贴上荒谬的标签,并毫不犹豫地宣告其终结,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就是掌握这些原则;我们也曾把马克思哲学视为简单的现成公式,把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理论、一切历史事件通通“判决”了一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裁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摩尔根的遗传理论被定性为“唯心主义”的梦呓;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被判定为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假学术”等等,即是这种“判决”中少数的几个“经典”事例。所有这些充分说明,马克思所固有的“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已彻底被窒息。
二是把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定性化”,使一种本来旨在激励人进行创造的开放性理论变成了一种束缚人思想和手脚的“定性化”教条。人们曾相信,在某个时空中肯定存在着一种“标准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存哲学的缺陷仅在于它偏离了此标准模式,人们的任务就是克服“主观偏见”,直至最后直面这种哲学并“还原”和“复写”出这种哲学;人们曾相信,一定存在着某种“标准”的哲学语言和“标准”的哲学表现形式,人们的任务仅在于临摹和照搬这套语言和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的任何“试验”都属不务正业的非份之举;人们也曾相信,马克思在一定具体条件下所说过的话都具有在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适用的无条件的意义,在具体生活实践中,人们只要重复原则,即可万事大吉。
这二者都失落了马克思所独具的“实践优先”和“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马克思哲学变成了某种与传统哲学没有根本区别的狭隘性理论。
四、我们如何走近马克思
以上的讨论,其目的是为了回答“如何走近马克思”这一根本性问题。以此为背景,我们将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并得出一些十分重要的结论。首先,“走近”马克思,究竟应走近马克思的什么东西?或者说走近的“目标”和“对象”究竟应是什么?
很显然,要“走近”马克思,我们首先要认真钻研马克思的理论本文,了解马克思说了一些什么,是如何说的。但是,仅停留于此还不够,要切实理解马克思,我们还必须透过本文,去把握那种体现在字里行间的理论境界,即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实践优先”和“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如果套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实践优先”和“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是马克思哲学的“体”,而马克思的具体论述和文字则是由这种“体”所体现的“用”,与“用”相比,“体”是灵魂性、核心性的东西,因而更具有根本性。因此,只有在充分掌握马克思理论本文的基础上,再去体会、把握和发挥其蕴含的理论境界,我们才能切实地走近马克思。
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存在着两种理论形态,一种是付诸文字、写在字里行间的“显性理论”,另一种是未写出的、体现在字里行间的无形的“隐性理论”,前者是马克思针对他的时代的生活实践所发表的具体看法,而后者则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结构的“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意境,产生于一定时空中的具体话语总是暂时和相对的,隐含在具体话语之后并支配着具体话语的深层结构才是永恒常在的,因此,走近马克思,一方面是走近其“文本”,另一方面,更关键在于走近其“境界”,只有把二者合理地统一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走近马克思。
与上述密切相关,当我们说“走近马克思”时,这里面已蕴含着我们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表现出何种“姿态”,来进行这种“互动”呢?
我们认为,真正良性的互动应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这意味着,在走向马克思时,我们一方面必须认真聆听马克思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们又决不能把这种“走近”理解为趋向某种一经产生就现成存在的“实体”(若如此,只能表明我们已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思辨的实体主义哲学等量齐观),而应该把这种“走近”理解成能动的“对话”,理解成积极地“生成”和“创造”。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最为重大的贡献就在于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彰显了“实践优先”和“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因此,在走近马克思时,最好的方式是既尊重马克思的具体论述,同时又不把马克思完全束缚在现成词句中,而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从产生于一时一地的词句中解放出来,让马克思与不断变动的的人类文化和生活实践进行新的“视界融合”,以使其不断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态。这样做,也许在一些具体词句上会与马克思不完全一致,但它最深层地体现了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理论境界,因而离马克思最近。
这一点,在如何处理同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上,可以得到十分鲜明地体现。在我们国家的哲学领域中,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还存在着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三种类型的理论在我们的思想土壤中都已经扎下了根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同其它二者的关系呢?自觉地贯彻马克思“实践优先”与“开放创造”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境界,我们认为,不同的哲学类型和派别虽然有排它的成分,但也存在着人类性、世界性的内容,不同的哲学在理论上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吸纳,乃至融通,因此,我们决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愚蠢地把中国传统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封建意识”,也不能再无知地把西方哲学贬斥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呓语,而应该坦率地承认:二者都包含着属于人类思想精华的内容,西方哲学长于逻辑化的思维,中国传统哲学则发挥了具象化的理念性思维,前者较看重知识、致力于智力外化、着意于求真,后者比较看重义理、致力于智力内化、着意于得道;前者注重解决生命的外在矛盾、比较看重“安身立命”,后者注重解决生命的内在矛盾、比较看重“安心立命”;前者注重深究物理、特别发挥了横通的分析精神,后者注重参透玄理、特别发挥了纵贯的整合精神;等等,所有这些,对于今日中国和人类的发展,都分别发挥不可代替的互补作用。面向生活实践,以一种“开放创造”的姿态,向它们真诚开放,马克思将在与它们的交融和汇合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近马克思?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思想解释力与时代感召力,与其它理论相比,它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更强的说服力(对象方面的原因),此外,还有主体上的原因。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必须走近马克思,是因为这种理论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以不断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地促进人的自由发展。走近马克思,为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福祉。对此具有高度的自觉,将使我们抛弃一切与人的现实生活相敌对的教条,并使马克思的哲学真正成为内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生活发展的强大思想力量。
以上三个问题,是我们在“走近马克思”时所遇到的最为重大的问题。我们相信,只要追随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和真境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走近马克思的同时,也走近我们幸福的生活,从而使我们在新世纪的步伐更加稳健、更加踏实。
收稿日期:2000—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