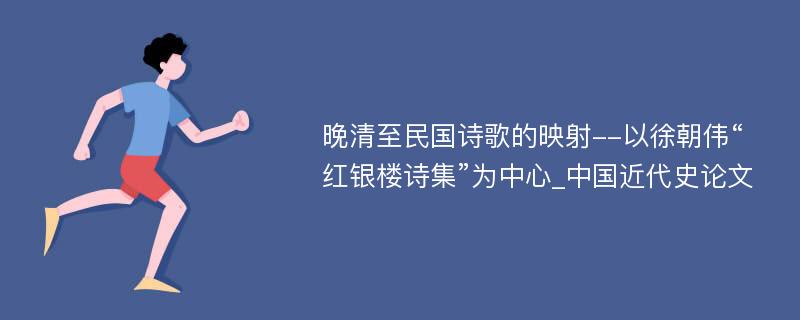
从晚清走向民国的诗心映射——以徐兆玮《虹隐楼诗集》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诗集论文,的诗论文,民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3-0134-09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绝大变局,身处变局中的士人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大体上都要在保守于旧制度与推翻旧制度两种政治力量之间选择,而最终一部分成为前清遗老,在无可奈何的境遇中延续生命,一部分则参与到民国肇建的历史进程中去。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民国肇建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社会政治变怪百端,兵戎频仍;文化领域新旧冲突,论争蜂起。在时代的歧路口,相当一批士人回归了故土乡园,或投身于地方社会的近代性重构,或以隐居的方式观察思考着历史的走向。晚清民初的变局与任何一次易代鼎革相比,都有其特殊性,各种环节、各个层面都具有研究价值。如果我们将自晚清进入民国的士人的思想与生活设为特定视角的话,那么一方面需要着眼于大量的历史文献,从史料中勘探实况;一方面应注意文学文献,从作品与诗心中了解变局之史实以及身处历史大潮中人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徐兆玮《虹隐楼诗集》的重要价值是不应忽略的。① 一、甲午与辛亥:晚清社会变局的浓墨呈现 徐兆玮(1867-1940),字少逵,号倚虹、棣秋生,晚年自号虹隐,别署剑心。常熟何市人。早年师从太仓胡益谦、王影石学经文与诗赋,攻书记诵能过目不忘。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十五年(1889)进士及第,十六年(1890)恩科补行殿试,选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散馆,授编修,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考试翰詹,钦定二等,奉旨照旧供职。[1]188 从徐兆玮初仕于朝廷的经历可知,他有着与明清时代许多由科举之途入仕者相似的最初经历:从庶吉士到翰林编修,这预示着一条仕宦的坦途。正因为如此,光绪十八年五月他写下《五月初三日散馆,引见授职编修恭纪》云:“北斗丹梯引侍臣,沉沉琼宇肃清晨。蓬莱许注长生籍,槐柳同依上苑春。石室编摩容炳烛,玉堂制作愧扶轮。词章自古须根柢,阳叶阴条勉日新。”这是一首极为习见的纪恩诗,以古典的形式与词汇表达出历代翰林共有的“扶轮”之情。相信如果没有晚清的内忧外患和历史巨变,徐兆玮的人生将沿着传统文人的惯常道路递进,而《虹隐楼诗集》也将是另外一种风度与境界。 然而甲午战争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所谓的“同治中兴”由此终结了,中日战争的失败给清王朝极大的耻辱,也给予了最大的危机警示。从战火燃起到渐灭,士林阶层普遍处于忧患、哀痛、愤苦、激动之中,身居朝廷文职的徐兆玮对甲午战事显然有更多的了解,也有更深的哀愤和思考。相关的诗歌作品是《虹隐楼诗集》中最具有诗史价值的一部分,一个心忧国事,“请缨拼上桃花马,不为深宫望幸稀”[2]29的爱国士人的形象亦由此凸显。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由清军和日军在朝鲜半岛的牙山之战拉开序幕的。1894年5月初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 000多人进入朝鲜,驻扎忠清道牙山县。日本也向朝鲜大举增兵,抢占仁川、汉城等军事重镇,决意与中国一战。不久双方开战,叶、聂部失守于成欢、牙山一线,退到平壤与左宝贵所部奉军会合,再败于平壤。陆战失败后,日军完全占领朝鲜。而平壤陷落三天后的9月15日,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上发动海战,企图控制黄海制海权,邓世昌等爱国将士率舰奋战壮烈牺牲。北洋舰队为保存实力,退至威海港内。不久清军在辽东半岛、威海卫进行的海战中又接连失败,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日军占领丹东等地。1895年1月底,海军提督丁汝昌统领的北洋水师在日军进攻下全军覆灭,清廷在甲午战争宣告彻底失败。[3]对这一使民族蒙羞的重大历史事件,《虹隐楼诗集》中《银河篇》《宫怨》《中秋夜大雨,用杜工部八月十五夜月二首韵》《既望始见月,复用工部十六夜玩月、十七夜对月二首韵》《送映南归里》《重九用工部九日曲江韵》《寄映南即次其出都韵二首》《高丽遗民麇集城根,驱车过之,抚然有作》《悯忠寺石坛传为唐太宗征高丽回瘗战骨处》《里门杂事》《台民怨》等诗歌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而《牙山哀》《平壤哀》《楼船篇》三首则是分别对陆战、海战的专题性感发志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兹录其中二首,为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增添一段心史。 《牙山哀》: 妖蟆吐雹扶桑东,坏云低压涛山红。荒磷三万抱沉船,中宵雨泣愁鲛宫。厖臣握策日鹗顾,坐使孤戍成沙虫。援军不发士坚卧,骄虏横海扇腥风。神坛王气已消歇,甘泉夜半传云烽。严旨敦促不厝意,高牙静拥千艨艟。关东鼠子敢跳荡,老谋深远竹在胸。韬弓卧甲忽偷渡,可怜一炬熸虬龙。君不见,材官铁骑坐嚄唶,登舟誓死吞疆敌。狂鲸怒噬不择肥,手张空弮痛何益。风轮转紫海水枯,炮车纵横摧霹雳。韩江饮马梦犹温,荒溟怨血千年碧。神山东望阵云昏,毅魄恣雎长喟息。呜呼,北门锁钥谁护持,百万金钱掷漏卮。借道远烦回纥马,愆期先漏多鱼师。小夷狡诡安足怪,筹边廿载纷遨嬉。望祭江隈有余恸,肠断焚舟掬指时。 《楼船篇》: 为邓壮节公赋也。公名世昌,粤东人,以欧洲学生管驾致远兵轮。大东沟之战,倭舰倍我,我师畏敌,有退志,阵遂乱。公知事不济,鼓轮前,首冲倭提督坐舰,毁之,又毁其兵轮一艘,而致远沉矣。公投于水,仆刘相忠随之,携木梃授公,欲援之起,力拒弗纳而死。中国创设海军以来,管驾之以死勤事者,壮节一人而已。所豢犬尾壮节入水,随毙,亦忠义之气所感被也。彼身为元戎,全师降敌,而仰药以塞天下之口,如丁汝昌者。盖犬彘羞为侪伍矣,何足与壮节絜短长哉! 峨峨楼船,觵觵亮节。沧海或可填,心光誓不灭。嗟哉海东虮虱臣,与船生死忘其身。孤忠迈往无等伦,上为剑气凌星辰。大官遇敌乃畏死,敌人视之亦如羊与豕。愿天再生十百邓将军,剪浪屠鲸反手耳。 《牙山哀》以沉哀茹痛之情对牙山之战作全景式的叙写,有对日寇骄虏的声讨,亦有对将士壮烈应战的礼颂。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涉及对战略和战术失误的检讨用笔比较含蓄,但指出“小夷狡诡安足怪,筹边廿载纷遨嬉”却是直截了当的,批判的笔锋已经指向朝廷统治集团最高阶层了。战事失败,是兵弱、器弱,还是人心不振、人谋不足,当时讨论者颇多,作者显然有所思考。《楼船篇》对邓世昌大东沟之战忠勇壮烈形象给予了激情歌颂,表现出置生死于度外的孤忠壮举和以身填海、精光不灭的气节。“愿天再生十百邓将军,剪浪屠鲸反手耳”,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期待,却代表了一代士人对民族自强的渴望。无疑“大官遇敌乃畏死,敌人视之亦如羊与豕”是针对丁汝昌先降后死而言的,徐兆玮对此极为鄙视。尽管关于丁汝昌海战过程中的表现与事实或未必尽符,但其对“身为元戎,全师降敌”绝不宽恕,乃至视其为犬彘不如者的态度,在那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激荡人心的。 从《既望始见月,复用工部十六夜玩月、十七夜对月二首韵》中“夜郎徒自大,天意厌维新”之表述可知,在清末改革维新的思潮中,徐兆玮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宣统三年(1911)前后他回乡参与地方事务,是常熟一地与“旧党”人物抗衡的“新派”中坚力量。《棣秋馆日记》中详实记录了他于辛亥革命之际的行迹,可见对共和立宪的心理状态。如(十月初八)“唐海平来,言拟译《平民政治:卜书,易名《共和政治》。邓秋枚以《国粹学报》滞销,改出《共和杂志》,大畅销。今日惟《共和》二字稍可卖几钱耳”(十一月十二日)。“与孙师郑函云:‘和议已有眉目,释干戈而取决于国会。共和政体南省狂热已久,北方应有同情。’”(十一月望日)“孙中山举为大总统,于十三日履任,即改用阳历,以是日为元旦。《民立报》著议论之,以为改历大事,不应如是轻率。然不以是改新日月,又何以振兴民气乎?见仁见智,各具一解,一二人之私臆,未可遽定是非也。”(二十七日)“今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十五日,各处行补祝元旦之礼。吾乡亦令店铺挂灯,以寓庆祝之意。”(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十九号,辛亥十二月初一日)“今日改用新历纪年。闻宣统帝将行禅让,南北战争可以罢休,金融机关亦稍周转矣。”[4] 宣统三年是改朝易代之际,争论了多年的“变更政体,实行立宪”变成了政治现实,其意义绝不啻清王朝的终结。该年徐兆玮往来于家乡与京城之间,《虹隐楼诗集》收录的“辛亥”作品共34题,“阳鸟谁安宅,桑田倏变迁”[5]69是该年全部诗歌创作的主题,其中《万寿山》值得一读: 绵绵万寿山,下有延寿寺。纯皇隆孝养,郊埛贡灵瑞。特辟清漪园,溪山无尽意。宏规岂虚构,继述在后嗣。慈圣春秋高,垂帘倦临莅。土木竣西苑,颐和始缮治。内库出羡余,事不劳计吏。因鉴孺慕忱,谆谆戒奢恣。维时畿辅灾,洚水淹平地。农田卒污莱,老羸痛播弃。乌台有直吏,伏阙陈谠议。行作非其时,惧为圣德累。请发水衡钱,遣使振穷匮。愚忠冒斧锧,行间皆血泪。严谴降一官,足令举朝愧。十载营桂宫,花石益妍媚。云岚入绮筵,天风下鸾吹。顾独念时艰,宵旰不遑寐。迎銮瀛秀门,懿训俯宣示。变法图自强,纷更戎再四。宗祏询安危,便殿勤政事。谁知乏老成,谋国误险诐。昌言歼远夷,用兵如儿戏。鸱张市井徒,妄欲窥神器。城阙生烟尘。风人伤内奰。……宫花侵辇路,山鸟忘警跸。廿年换沧桑,往事足歔嚱。盛衰会有时,胜游岂再值。待翻《野获篇》,更续《长安志》。 此诗为长篇巨制,这里节录其中一部分,已可略见自光绪十四年(1888)颐和园重建以来20多年清王朝政治、外交、军事、民生之概况,浓缩了晚清激烈动荡、濒临崩解的诸多历史因素。对“慈圣”,诗人在婉讽中包含着犀利的锋芒,而对顾命大臣之谋国偏误,用兵无知则不假辞色。“内奰”一词出于《诗·大雅·荡》:“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毛传》:“奰,怒也。”指商纣的恶行激起国内百姓的怨怒,亦泛称内乱。“城阙生烟尘,风人伤内奰”概述晚清社会之动荡和民心之哀恸,实际上已预兆了“龙蛇起陆齐州动”[6]71以致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必然。结尾云“待翻《野获篇》,更续《长安志》”,颇有为一个过去的时代存史的意味,令人警醒。 再看《天津杂感》(其二): 大厦将倾一木支,颠危强与共扶持。传闻南粤贻书屡,叹息兴元下诏迟。来日变迁谁预料,人心离析邈难追。凄凉夜色侵寒袂,正是津门月上时。 根据《棣秋馆日记》,此诗写于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其时武昌起义的消息早已坐实,各地纷纷宣布脱离清廷,京师一片混乱,传闻四起。南粤虽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宣布独立问题上两广总督张鸣岐一面与清廷暗通,加强防务,一面以所谓怀柔策略应对革命党人。对此徐兆玮认为清廷的颓势绝无可挽救,大厦将倾,一木能支几时?最重要的是士气、民心向往共和,宣统迟迟不肯下诏逊位,实在可悲可叹。他在此时断言“四夷久欲窥周鼎,三户谁知应楚谣”[7]72,对外国势力伺机侵华的危险保持着清醒的认知,这在其后的历史中得到了印证。 徐兆玮诗稿原本逐年编次,比较完整,但1937年故乡沦陷时兆玮带领全家出逃避难。及至返回,家中已屡遭劫掠,诗集也有一部分被毁,其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三十四年(1908)共12年的诗稿全部失去。对此兆玮非常痛惜,视为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生前一直无意把诗集刊印出来,并说刊印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8]2。相信在那些散佚的诗作中有更多对晚清社会变动的真实记录,但即使如此,今存于《虹隐楼诗集》中的不少光宣之际的作品仍然披露了许多重要史实,尤其甲午与辛亥年的作品,对晚清变局加以浓墨呈现已足称诗史,也是诗人怀着清醒的痛苦告别晚清,走向民国的心史。 二、归来虞山:民国士人生活的真实影像 作为一位晚清文臣,徐兆玮带着一代人的历史记忆进入了民国,他将癸丑年(1913)的诗歌作品总名为《归来集》是颇具寓意的。然而他的“归来”却经历了一个过程。1912年至1923年,对民国来说本应是最有希望的年代,最后却成为一个最奸穷怪变的时代。对共和立宪的企盼与对共和立宪的陌生,让一些政治集团和个人攫取利益的野心有了恶性膨胀的空间,遂使政体国事陷入混乱。在这一期间徐兆玮是“局中人”,既当选为常熟县副民政长,从事地方公共事业建设,又当选为国会议员,参与议政。1923年,当直系北洋军阀曹锟用贿选手段企图当选总统时,他站到了拒贿辞任者的队伍中,表现出清正风裁。自此之后方息影乡居,在虹隐楼阅读古今,从事著述,真正进入了“归来待续杜陵篇”“持杯更与说逃禅”[9]73的人生历程。 《虹隐楼诗集》中民国以来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与时事世道相关,一类表现日常生活。这两类作品合而观之便可窥见“跨时代”者的真实行履和心态,而在古典的形式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位经历了晚清与民国的“士”之变与不变。 在《虹隐楼诗集》的“民国篇”中感时而发的作品有很大的思想容量,需要通过细读,将“跨时代”者的一般书写与具体书写区别开来,才能真正理解。何谓一般书写?如《二月十三日为旧历甲寅除夕》云:“俯仰人世间,今宵益惘然。入春才九日,改历已三年。爆竹惊山鬼,明灯照市廛。江村仍旧俗,谁识海为田。”这样的感慨在清末民初之士中是普遍的,其中带有对前朝的集体记忆,同时包含了对新时代不确定性的惘然、疑虑与期待。若欲探究其思想倾向,孤立地看则难明所以,须与写于1913年的《得师郑书却寄》“覆瓿玄文羞颂莽,登楼词客倦依刘。蓬莱浅水终难近,玉树歌翻未到忧”合读,方知其内心对某些政治力量保持着警惕和距离。 “桑海五年新政体,蓬山卅年老词林。”[10]91在那个旷世政体大变局中这位“老词林”保持了清醒的取向和立场,试看1916年徐兆玮自家乡北上后所作的两首诗: 《十一月四日为二年非法解散国会之日,两院同人于农事试验场畅观楼开会纪念感赋》: 从来防口甚防川,家国兴亡岂偶然。未许河山归一姓,不辞风雨会长筵。云萍聚散前尘渺,霜菊横斜晚节坚。噩梦那堪回首忆,相期同著祖生鞭。 《元日赴众议院茶会有感》: 林塘耽静岁三更,松菊犹存忍背盟。何意行藏乖始愿,转从忧患惜余生。簪裾雅集天星聚,杯杓清谈快雪晴。来日茫茫悲世事,春秋据乱冀升平。 写作上述诗歌的两年前是民国初建的昏暗岁月,先是袁世凯下令将国会解散,遣返议员,继而下令解散各省议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此法实可称为“袁氏约法”,把总统权扩大到专制皇帝的程度,公然确立了独裁政体,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完全被摧毁,“中华民国”徒剩空名。徐兆玮指出,袁氏之所以非法解散国会,是“防口甚防川”,而此事关乎“家国兴亡”,是对革命大业的“背盟”,有良知的士人应予以坚决抵制。“未许河山归一姓”“相期同著祖生鞭”是走出晚清对建立共和充满期待的士人讨伐袁氏独裁的宣示。诗人表示在正邪较量中拒绝察脉望色、犹豫彷徨,当存松菊高洁之性,“霜菊横斜晚节坚”一语凸显出其人格形象。 “五年经再厄,万里此扁舟。归梦心先喜,危时志未休。”[11]97从1917年的这首诗可以看出徐兆玮在出处之间徘徊,欲归虞山而其志未休。实际上即使他回到虞东家乡,心仍紧系于家国存亡。他是甲午战争时代的亲历者,对日本侵华有着刻骨铭心之恸,而身在虞东对上海抗战的情况非常熟悉,《虹隐楼诗集》中存有关于两次上海事变(淞沪抗战和“八一三事变”)的作品。先看《和燕谷老人闻上海十九路军战胜日军志喜之作》: 东师不战弃全辽,井底群蛙气益骄。愤起挥戈能退日,伫看挽弓竟退潮。余皇舟烬江波沸,霹雳车摧地轴摇。仗有一韩寒贼胆,清人河上尽逍遥。 搴旗闸北蹴江湾,杀敌奇功媲谅山。海外邮船争动色,巷中童话尽开颜。忧危顿觉心神王,衰朽浑望旅力孱。士饱马腾民意慰,箪壶远犒到行间。 前锋一卒敌千人,始识将军细柳真。狭巷短兵如刈草,长沟复堑足藏身。岂容上国来蛇豕,谁谓中原少凤麟。不是廿年疲内战,早应虎视慑东邻。 吴淞江上阵如云,电掣雷轰百里闻。壮气先褫关白魂,威名群说岳家军。忧谗毕竟金难铄。好战终看火自焚。顷刻捷书腾万口,几人摛藻为铭勋。 这是对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日军的淞沪之战的历史记录,“东师不战弃全辽,井底群蛙气益骄”是对“九一八事变”后时局的描述,不战而弃助长了日军的气焰,但中国毕竟有“将军细柳真”与“一卒敌千人”的热血将士,他们在吴淞江和闸北战场浴血奋战,重创日军。这是四首七律连缀的组诗,从落墨至结尾一气呵成,久郁心中之恨磅礴喷发,战场与将士、江上与狭巷、前锋与后援,诗人以激情贯穿,熔铸一体,绘出一幅壮烈而豪迈的淞沪战事图,表达出深厚的民族情感与正义之气。淞沪抗战因南京政府采取消极战略,最终以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的《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结束。闻此消息徐兆玮深感忧愤,写《书愤和师郑》诗云:“岂是晋侯甘退舍,但闻魏绛利和戎”,“诸夏已无清净土,只余东海可埋忧”,读来深知诗人忧来无端,长歌当哭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军民自8月13日起历时3个月进行了抵抗日军的战役,史称“淞沪会战”,其战况极为惨烈悲壮。次年徐兆玮作《八一三》诗纪念:(其一)“血战经年后,重逢八一三。金城雄汉上,铁泪洒江南。入坎生何乐,同仇死亦甘。孤舟飘海澨,风雪更难堪。”(其二)“万众同心誓,无忘八一三。衔碑伤石阙,茹素效瞿昙。转徙仍无定,艰危各饱谙。高楼罢歌舞,莫再蹈荒耽。”在家国危亡之际,诗人守持着内心深沉的民族情感,其“入坎生何乐,同仇死亦甘”的呼声真如杜宇血啼。为纪念八一三国难,江南各界于当日商肆休业,停止娱乐活动,茹素一周节省金钱以救济难民,诗人倡导之、力行之,直吁“高楼罢歌舞,莫再蹈荒耽”。这类作品风骨高峻,正气凛然,是体察理解抗战时期江南士人感情意志的生动文本。 随着时代的浪潮从晚清卷入民国后,徐兆玮的生命轨迹中镌刻着极深的历劫红羊的印记。但在注意《虹隐楼诗集》中这类作品的同时,还应注意他大量的日常生活类题材写作,缺少了日常生活维度的考察,便难以了解徐兆玮归来虞山的全部生活情状与心态。 何谓日常生活?文人的日常生活可以从与“人”相关和与“文”相关两个角度去考察。前者包括人之于环境、之于生存所面对的一切衣食住行、起居日用、四时节序等;后者包括文人之“文”化入生活的内容,如人际交往、文字往还、琴棋书画、社群文会、藏书钞传、隐读养性、怡老消遣。凡此种种,都是地道的日常经验。文人的日常生活是平常与非常、静态与动态的统一。所谓诗人——尤其是以古典形式创作的诗人——是习惯于日常生活中沉浸诗思,在诗歌创作中反映日常生活内容的。日常生活决定了诗人的规约性认知和个体认知,既表现出其生存状态,也形成其品味境界。我们极为鲜见不涉笔日常生活的诗人,而徐兆玮的诗歌创作是日记性、编年体式的,故日常生活入诗更多。这里试看《村居杂兴》: 菜畦麦陇自莓莓,踏遍林隈又水隈。难得岁朝风日丽,好怀能有几回开。(其一) 水竹萧闲静者居,白沙浅处聚游鱼。四围倒影都无著,只觉方塘一鑑虚。(其四) 蓬门竟绝一人来,石径萦纡长绿苔。漠漠东溪终日雨,朱阑何处染尘埃。(其五) 南荣袖手坐朝曦,吟卷随身亦懒披。人日自来多感触,裁笺先寄草堂诗。(其七) 晓来微霰下庭阶,松竹疏森不改青。莫诩凌风知劲节,镜中鬓发已星星。(其八) 琐窗钩起一重帘,插架丛刊自署签。任是拥裘还被酒,春寒犹觉十分严。(其九) 一角茅亭夜有霜,树头明净见初旸。农言试验今宵雨,春涨盈盈半亩塘。(其十二) 这是一组诗作,作者于篇末自注云:“新正谢客,日赋一诗,记阴晴,验风雨,得二十九首而正月尽矣。因之辍笔。”[12]146以上只是节录了他初一至十二日间的部分作品,已可见内容是何等的“日常”!这里有林隈散步、水塘观鱼,有虚室待友、裁笺作诗,有对镜览鬓、插架署签,有拥裘饮酒、农谚验雨。如再循卷细读,则一瓢一笠、麦苗豆荚、路润泥融、倦酒登楼、近市行药、溪头鹤走、久旱逢雨、行歌互答,皆作为意象或细节化成诗句。值得一提的是,《虹隐楼诗集》中这类“记阴晴”的气候诗特别多,不无寓意。如《四日暖可御葛,五日重裘不温,口占志气候之异》云:“寒燠两无节,天公亦反常。何能行赤道,至竟筮归藏。气运有时迕,浮生只是忙。睡余山骨瘦,一任变炎凉。”显然这里对日常生活的记录与感兴已不止于气候本身了,“气候之异”是一个喻体,诗人藉此隐含着对时局变幻的敏感观察和人生喟叹。 节俗诗是《虹隐楼诗集》中的又一大宗,一年四季中的重要节日皆见于歌咏,而以冬春两季的节俗书写较多。除夕、元日、人日、上元、上巳、寒食、清明这些具有聚合离散意义的节令每每触及诗人内心,旧山黯淡、人鬼俱惊的心境在节日时空中弥漫,映射出特定的历史情境。当然亦有一些人文色彩浓郁的节俗风情化作了诗料,在其苦闷窒息的铁屋中打开一扇天窗,透入丝丝阳光。徐兆玮写于1920年初的《探梅》《煮雪》《围炉》《酿酒》《藏花》《曝日》《火砚》《祀灶》《糊窗》《扫尘》《送穷》《祭诗》12首“消寒诗”非常典型,江南严冬或雅或俗的每项消寒活动乃至细节性的民间文化在诗人笔下排比铺陈,极富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晕玉一涡先得气,生花双管为嘘枯”;“香熏睡鸭留能久,纸触寒蝇脆有声”[13]102,细腻活泼的笔致中呈现出诗人形象的另一个侧面。 文字往还是传统文人惯常的交游方式,实际上已演化为日常生活内容。这类作品有一部分关乎政治与时局,一部分则纯属文人的酬唱互答,具有“日用之道”的特征。读其《行年五十矣,丙辰七月二十一日生朝师郑赋诗为寿,次韵奉酬》“消受故人一樽酒,清谈剪烛到深更”,“降寅一岁比公迟,缄札分驰系梦思”,可见诗人交友一往情深。《钱新甫同年骏祥以八十自述及重谐花烛词征和,赋此为献》乃戏谑之作,“琼林迟宴尊前辈,采服承欢羡后贤”;“愧我岁刚周甲子,朝来揽镜笑华颠”;“婚仪应比金刚石,绮梦重温玉镜台”云云,足见诗人性情蕴含着多少幽默谐趣。归来虞山后经历了太多的颠沛苦难,他似乎等待着每一个偶然的机会以一抒胸臆,所以具有民间生活意味的饮肆、寿庆、婚仪、题影、伴游等就往往成为诗人骋怀的题材了。在《虹隐楼诗集》中,此类作品占有一定的比例,构成了民国文人生活的日常图像。与其时政题材的作品合读可知,从晚清走来的一代士人并非是一种沉默的存在,他们“老去诗心未寂寞”[14]171,习惯于“乐群”生活,在“游于艺”中延续传统,扩展其精神领域。 三、肩随西昆:聊借古辞,用伸今愫 在徐兆玮所处的那个新与旧交替、希望与绝望并生的时代,选择何种文学表现手段不仅是艺术兴趣的问题,也与情感蕴聚及其思想取向有关。“聊借古辞,用伸今愫”[15]186是那一代人较为普遍的策略,进一步的问题是“向谁取借”?很明显,徐兆玮选择了李商隐,具体地说是采用西昆体。其《漫社二集题词》云“肩随西昆杨大年”,意在说明其诗学路径是从西昆体走向玉谿生,以隐约深曲、包孕密致的手法书写那个晦暗复杂的时代,抒发内心世界的深沉情感。 徐兆玮步武西昆是受到虞山地域文化影响的群体性选择。自明末清初虞山诗人就形成了以李商隐为好尚的风气,石林“常笺解李义山诗及《类纂》”[16]1289,钱龙惕诗歌创作“原本温、李,旁及于子瞻、裕之,憔悴婉笃,大约愁苦之词居多”[17]71。钱谦益“苦爱义山诗”,其“近体芬芳悱恻,神矣圣矣,义山复生,无以加之”[18]36。义山诗是钱谦益的诗学渊源之一,由义山而窥少陵堂奥正是牧斋的诗学路径,在虞山地区具有重要影响。接着冯班更大张西昆旗帜,在《同人拟西昆体诗序》中曾自述:“余自束发受书,逮及壮岁,经业之暇,留心联绝。于时好事多绮纨子弟,会集之间,必有丝竹管弦,红妆夹坐,刻烛擘笺,尚于绮丽,以温、李为范式。”[19]冯氏的西昆取则由吴乔进一步发扬,其云:“于李、杜、韩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义山一人。既欲自立,势不得不行其心之所喜深奥之路。”[20]651 王应奎曾分析清代虞山派有“钱蒙叟倡于前,冯钝吟振于后”的变化,[21]又云“吾邑诗人自某宗伯下……学诗者宗定远为多”[22]88。其实宗钱与宗冯,总体来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艺术表现上都具有婉娈托讽、沉博雄丽的风格,曲尽万态之变而精索难言之要,只是钱谦益唯倡少陵与义山而不及西昆,冯班则合晚唐温李于一手,明确标举西昆体,扇扬西昆风。虞山后辈诗人大致都“源导东涧,宗趣以杜陵、玉溪为归宗”[23],在表现手法上则多瓣香西昆。徐兆玮是一个典型。先师钱仲联《张璚隐传》记载:“始公(按,指张鸿)之居京师,与吴县曹君直、汪衮甫、同邑徐少逵诸君为近体诗,涵揉比兴,由西昆以溯玉溪,才艳惊绝,与所谓同光体者殊厥帜。一时海内谈艺之士,无不知有《西砖酬唱集》者。西砖者,公所居胡同名也。”[24]在近代西昆体诗派中,吴下汪荣宝、曹元忠、张鸿、徐兆玮皆为中坚人物,徐氏在《蛮巢诗词稿序》中述及《西砖酬唱集》编纂之旨乃在以西昆之体药西江之习,并称“知君深者莫予若也”[25]。由此可见,徐兆玮“肩随西昆”既有地域诗学传统的影响,也与当时吴下诗人群体的取向有关。 徐兆玮《虹隐楼诗集》中宗法李商隐的印记是相当明显的,对义山诗他几乎烂熟于心,随手集句即成华章,其思想情感融于成句之中,不唯技法圆熟,亦深涵意蕴。试读《秋日感事书怀集义山》: 黄竹歌声动地哀,西师万众几时回。空闻虎旅鸣宵柝,便是胡僧话劫灰。沛国东风吹大泽,秋庭暮雨类轻埃。玉盘进泪伤心数,密锁重关掩绿苔。 耽酒成仙几十春,浮云一片是吾身。沧海白石樵渔路,苦海迷途去未因。半曲新词写绵纸,全家罗袜起秋尘。旧山万仞青霞外,沦谪千年别帝宸。 昨夜星辰昨夜风,西来双燕信休通。一条雪浪吼巫峡,独立寒流吊楚宫。白道青松了然在,后门前槛思无穷。天池辽阔谁相待,万里高飞雁与鸿。 未解当年重物华,成由勤俭破由奢。如何四纪为天子,犹得三朝托后车。卜肆至今多寂寞,东人望幸久咨嗟。金銮不问残灯事,万古春魂倚暮霞。 此诗作于1914年。徐兆玮于此题连集20首,用颇为可观的规模形成了一个抒情格局。所谓感秋乃感时也,此借义山华文谲喻之词,寄托易代世衰之忧患。在“旧山万仞青霞外”的弘深凄美的背景中诗人作“沦谪千年别帝宸”的告别,这是对前朝及其所代表的制度的告别,自然不能不产生“独立寒流吊楚宫”的无穷感哀以及“后门前槛思无穷”的深刻反思。徐兆玮与李商隐相隔千年,都有着至深的世纪末情结,因此蟠胸细润的义山诗便很容易成为其表现灵府的利器了。除上述作品外,《游仙诗集义山》《咏史集义山》《追悼龙尾集义山》等集句之作,都寄托了晚清民初之国事,美人香草之词隐含着江山摇落之感,诗人“借口而言”一浇心中块垒,在《虹隐楼诗集》中具有标志意义。 其实徐兆玮的“聊借古辞,用伸今愫”不止于直接的“集义山”“集飞卿”,对此我们应作广义的理解,即萃取晚唐诗的精华,采用义山主文谲谏手法来表达蟠郁的情愫。他的一首诗往往就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如作于1932年的《悼鹤》: 豢汝已十年,一夕丧兽口。岂无捍御力,失败事亦偶。朅来遭兵祸,人命如鸡狗。速死庸非福,深羡得天厚。所惜水边梅,天寒谁与守。篆铭大江中,华表千岁后。年代已微冥,人民复何有。蜕骨遗尘寰,酹以一杯酒。蹁跹学舞姿,宵深入梦否。 鹤之死或有其事,但诗人的诠释显然是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全诗以悲鹤为标,假物以寄思兴怀,悲慨国事之蜩螗沸羹,表达对谁守疆土、谁御外辱的深深忧虑。这种宛转曲致的艺术表现在诗人创作中成为显著的审美特征,其超卓之处往往在于:许多作品的符号意义未必十分明确,而随着诗人的描写,读者在深远幽折中感受到微文讥刺的用心,体味到哀感顽艳的悲情。 这里不妨稍举数例。《闻布谷声有感》:“积云漠漠罨重城,五月初闻布谷声”;“槐南万蚁争新筑,舍北群鸥负旧盟。”《银河篇》:“红霓剑采横南天,凌穹蹋月斫桂烟”;“闻道驰云奉使槎,苍鲸剪浪排霞归”;“清泪涵空落彗芒,芙蓉径外洗兵雨。”《楗关》:“山风飒作不平鸣,蝉翼千钧较重轻。”《蛙声》:“水溢秧塍小径长,萧疏垂柳有斜阳。东西万喙争腾沸,不辨官私噪一场。”《效义山辛未七夕》:“岁岁秋期总玉京,仙家真有别离情。已闻绣户停机杼,又见银河洗甲兵。”《雨中牡丹用义山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韵》:“梦里瑶华醒莫追,绛宫疑雨误仙期。余春散绮蜂犹恋,下苑销香蝶未知。粉态依然绫作障,朱颜回忆锦成帷。玉房金蕊皆零落,占领东风剩一枝。”《河水未泮欲归无舟孤馆明灯百端交集》:“银汉红墙违咫尺,蓬莱弱水阻三千。寒消炙砚围炉候,梦在枫江苇渚边。”《岁暮书怀》:“待看东海变桑田,飘渺蓬莱不得仙。蜃气幻成神鬼窟,鼃声还是莽新年。” 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云:“诗歌之道,主乎微讽,比兴之旨,不辞隐约。若其情随词暴,味共篇终,斯管、孟之立言,非三百之为教也。”[26]19-20无疑,徐兆玮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昆派的这种艺术标准内化为审美追求。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抑郁苦闷者用比兴微讽的手法方能寄托心绪,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辞隐约”酝酿出的是一种具有崇高感的悲剧美。作者用丽辞藻绘包裹着微文谲谏,在触动人们哀感时也蕴聚着思考的力量;在有意形塑一个历经盛衰而归于平淡的形象时,却不经意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瞻望企远的诗人背影。 在近代诗歌史上,徐兆玮等跨越时代的诗人以群体的名义被学者打量过,但作为个体,他们的生平经历和创作仍处于榛莽未启的状态。从形式上看,他们习惯采用的是古典诗体,并在这种古典形态的写作中回溯、融汇经典的体派与风格,达到了纯熟的艺术境界;而在心理上,他们既承载了对旧时代的集体记忆,又兼容了社会巨变后的深刻感受,其诗歌之舟抵达了前人不可及,而又极易被后来的新文学风景遮蔽的苍茫堤岸。显然我们不应让这一诗歌之舟在那里长久搁浅,本文以《虹隐楼诗集》为样本做一番探析,聊为引玉之砖。 收稿日期:2015-03-01 注释: ①“虹隐楼”为徐兆玮的藏书楼名,《虹隐楼诗集》原为稿本,为其孙徐昂千收藏,后经整理并请钱仲联先生作序自刊,未公开出版发行,故将其称为“徐昂千家刻本”。本文中的徐兆玮诗歌作品,皆录自该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