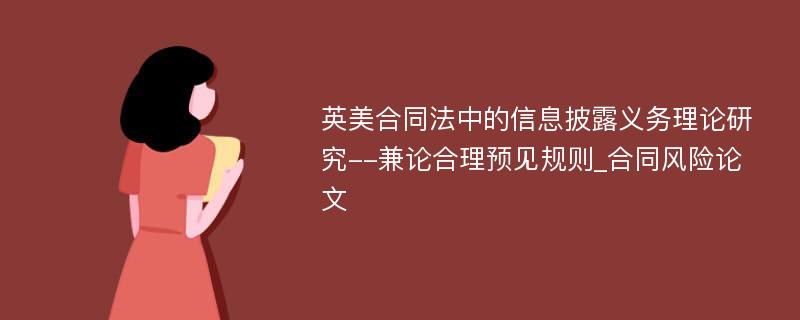
英美合同法中的信息揭示义务理论研究——兼谈合理预见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英美论文,合同法论文,义务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合同法上的著名判例Hadley V.Baxendale案确立了合理预见规则,而我国《合同法》第113条关于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正是对这一规则的借鉴。我国民商法学界近几年来对合理预见规则已有所研究,但是,大多数人是从传统民法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如研究该规则与过错及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该规则的理论构成等问题。笔者注意到,以经济分析法学理论对合理预见规则加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认为,法院审理合同案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解释合同的问题,当事人出于节省交易费用的原因会留下一些合同漏洞,而谋略心理使当事人隐匿信息,更可能形成合同空白,不利于提高合同交易的经济效率与增加社会福利。由于谋略行为是合同漏洞的主要成因,因此“多数人所期望”这种传统的合同解释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效率原则的要求。这样,为了减少谋略行为和合同漏洞,英美合同法学者主张缔约阶段合同当事人负有信息揭示义务,同时合同法中的合理预见规则作为一种附条件的“有限责任制度”,正是出于对违反该义务的当事人的制裁。围绕这个问题,本文不揣浅陋,试图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可能会留下合同漏洞,合同解释的必要性由此而生。事实表明,“多数人所期望”这一传统的合同解释方法未见得十分理想。
我们先来考察合同漏洞的成因。总体看来,形成合同漏洞的原因主要有二:交易费用和谋略行为(注:Ian Ayres & Robert Gertner,Filling Gaps in Contract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fault Rules,The Yale Law Journal Volume 99,Number 1,October pp 92-94(1989)。实际上,“当事人无法预知”也导致了合同漏洞,但由于在无法预见的情形下,当事人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使得我们很难采取激励机制,所以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交易费用和谋略行为这两种原因。)。所谓交易费用形成的合同漏洞是指,缔约阶段双方当事人就某些偶然事件磋商并加以约定,而该协商是需要交易成本的,包括律师费、通讯费用、起草与打印成本等,理性的当事人会衡量这些成本和利益,一旦发现该偶然事件的意义或发生的可能性都很小,可能就不加以约定了,这就形成了合同漏洞。而“当事人的谋略行为”产生的合同漏洞则具有另一番含义。现有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自愿交易才会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保证。而在非竞争的相互关系中,人们在谋略上的相互争斗会成为资源潜在浪费的一种根源,因为交易的各方出于战略原因会掩饰自己的偏好。如果没有一种从外面施加的规则遏制这种谋略斗争,则合同交易就不能保证经济朝着帕累托有效边界变化。合同一方当事人为了扩大自己从合同收益中所得的份额(即蛋糕的份额),可能谋略性地隐瞒某些可能增加合同总收益(即蛋糕的规模)的信息,这就产生了合同漏洞。
一般认为,“多数人所期望”规则是补充合同漏洞的一种方法。该方法的大意是,法院按照大多数情况下多数当事人所希望的条件来解释补充合同。按照这一逻辑,合同法规范提供的示范性合同条款,应该属于当事人本来可能明确协议选择的条款,这样会节约交易费用。Baird与Thomas Jackson两位学者也主张,调整合同关系的任意性法律规范向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条款)应该是他们所乐于选择的(注:Baird & Thomas Jackson,Fraudulent Conveyance Law and Its Proper Domain,38 Vand.L.Rev.p829(1985).)。这种理论对于解释交易费用产生的合同漏洞有一定价值,但也明显具有如下不足:第一,这种“多数人期望”仅仅是一种推断,忽视了个体差异,这种方法不能解释为什么还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订约成本以及人们为何还就不同的任意性规范进行磋商;第二,现有理论没有告诉我们“多数人所期望”规则如何具体化、类型化,这会给该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第三,更重要的是,事前磋商的成本可能是昂贵的,会使当事人做出无效率的选择,将事前磋商转变为法院事后抉择,而法院抉择也是代价高昂的,况且这种方法使法院成为事后包揽一切的“管家”,不具有激励性,不利于当事人形成谨慎订约的良好习惯(注:Ian Ayres & Robert Gertner,Filling Gaps in Contract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fault Rules,The Yale Law Journal Volume 99,Number 1,October p93(1989).)。所有这些表明,“多数人期望”方法忽视了当事人的投机心理,不当减轻了当事人事前协商的负担,加重了法院的事后解释工作,增加了合同交易的社会成本,难说合乎效率原则。
二
事实表明,“多数人所期望”方法的效果不佳,主要是因为它很难解释谋略行为产生的合同漏洞。笔者认为,为了贯彻效率思想,我们应该不再局限于“合同法的任意性规范仅仅应该是多数合同当事人本来所希望的”这种既有观点。立法者制定一种惩罚性任意性规范来诱导知情的当事人在磋商时主动揭示信息是有助于促进信息交流减少谋略行为的。这种规范是一种多数债权人实际上不喜欢的任意性规范,我们姑且称之为信息揭示义务规则,相关的学说见解可称之为信息揭示义务思想。许多英美法学者认为信息揭示义务规则不但是一种合同解释规则而且还对违约救济制度有所影响。Hadley V.Baxendale案确立的合理预见规则正反映了该信息揭示义务思想。
Hadley V.Baxendale案中磨坊主与运输商达成协议,由后者将一断裂的机轴运给一家维修商,送达迟延了几天,磨坊主要求运输商赔偿这几天停工期间的利润损失。磨坊主本来应该将可能发生间接损害即利润损失的情况告诉运输商并与其就全额赔偿达成协议,但是他基于谋略的原因向对方隐瞒了这些情况。此时,(多数的)磨坊主既不愿意告知风险信息(唯恐被运输商要挟),又希望能获得全额赔偿。如果法官判决运输商赔偿所有的间接损害,无异于鼓励那些可能发生巨额损害的磨坊主故意不告知相关信息,这明显有碍于合同效率的提高。为了遏制这种谋略行为,法院判决运输商只须赔偿他可以预见到的那些损害,而没有遵从“多数人所期望”这一规则。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磨坊主是否进行事先风险告知,其次才是运输商有无预见,而磨坊主的事先告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运输商的预见机会,并进而采取有效率的预防措施。尽管这种告知可能会引起运输价格的上涨,使磨坊主丧失谈判的优势,但是只要价格还没有涨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磨坊主就得告知对方,何况他最终还是会从该告知中受益,因为合同可以约定由运输商承担间接损害赔偿责任。为了使预先告知得以发生,法院以磨坊主是否向对方告知有关风险来影响其未来求偿的范围,这就是本案所确立的合理预见规则的基本逻辑。贯彻这一思想的合理预见规则可用以诱导知情的合同当事人向对方告知,英美合同法学者对其推崇有加。合理预见规则的“精髓”在于它是一种“惩罚”性的任意性规范,说它是任意性的,是因为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该规范对双方的约束力,转而适用其他规范或者按照双方的约定处理合同关系;说它是惩罚性的,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附条件的”有限责任思想。合理预见规则的理论前提认为,如果合同的履行对于某债权人来讲价值巨大,一旦债务人违约,该债权人遭受的损失可能也是巨大的。对该债权人而言,债务人仅仅承担有限责任是不够的,而为了让债务人负无限责任,债权人就不得不将可能发生间接损害的有关信息告知对方(当然,除此之外,债务人负无限责任还需要其他条件)。如果债权人未加以告知,可能就得不到全额赔偿了。正如波斯纳所言,该规则意味着“如果损失的风险仅为一方当事人所知,那另一方有理由不为此承担责任”,这就使知晓风险的一方或者采取预防措施或者将该风险告诉给对方并为此支付报酬让其承担该风险(注: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61~162.)。
合理预见规则反映的信息揭示义务理论的意义在于促使当事人揭示信息、明确合同条款、减少谋略行为,知情方“被迫”揭示的信息可使对方有机会采取最佳的充分的预防措施,这完全符合效率原则的要求。此外,该理论的效率精神还体现在其有助于一种“风险—价格—预防”机制的形成。合同当事人一般情况下是承担中等程度风险的,合同价格及违约赔偿额大体也据此确定。如果法官要求一方为对方承担较大风险,该方就有理由要求对方事先告知该风险并支付更高的价格,这样他才有激励采取积极预防措施应付更大的风险。相反,那些风险较小的当事人为了能在较低成本上成交合同,往往也愿意将自己“低价值、低风险”的情况告知对方,对方也将会因此而降低预防风险成本。这种“风险—价格—预防”机制有利于及时揭示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人们进行合同交易无非为了尽可能增加利益,而理性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仅要考虑是否有利可图,而且应当将其违约时必须承担的损害赔偿的风险考虑进去。当事人的风险预见能力固然取决于自己的实践经验与理性计算,但对方当事人的信息揭示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种“风险—价格—预防”机制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且,从法律角度看,这种机制既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合乎公平原则(注:关于合理预见规则的公平原则思考,请参见蓝承烈、闫仁河《论违约损害赔偿的合理预见规则》,载于《民商法论丛》第24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
三
十余年来,学者们对信息揭示义务理论展开了热烈讨论。鼓吹者有之,批判者亦有之。批判者主要从订约人谋略心理、保密权益等角度为谋略行为存在的合理性“辩护”,认为信息揭示义务理论及相关规则具有先天不足。在众多的批判观点中,下面两种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揭示义务理论轻视了谋略心理对当事人订约行为的决定性影响。由上可知,信息揭示义务规则的倡导者认为,我们可以借助该规则“遏制”谋略行为,但是后者可能成为前者无法逾越的障碍。虽然在理论上讲,一方当事人可能因违约遭受巨大损失,他应该告诉对方该合同的履行是很重要的很有价值的,如果对方“乘机勒索”,他同意适当“涨价”来换取对方为这些特殊损失承担责任。而实际上,合同的讨价还价是一个谋略性的信息传递过程,而非完全诚信的过程。一方尽力使对方相信自己没有理由支付较高价款,而对方却努力使其相信他应该支付较高价款。债权人通常要给对方留的印象是,合同履行对自己价值不大,即合同履行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利润。相反,债务人也想使对方相信,合同肯定能履行,合同对债权人是有价值的,自己的履行成本也是很高的,所以债权人应该支付较高价款,否则债务人就拒绝交易。可见,双方当事人都要尽量说些“假话”以使自己能在较低成本上达成交易。而且,有学者对近120年来数百个有关间接损害赔偿的案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没有哪个案件当中的债权人宣称他实施了信息揭示义务规则要求的信息揭示行为,没有人说他们曾经告诉过对方当事人自己会遭受非常巨大的间接损害(注:Jason Scott Johnston,Strategic Bargaining and the Eco nomic Theory of Contract Default Rules,The Yale Law Journal.Vol.100,pp 616-19(1990).)。既然信息揭示义务规则根本无法解决讨价还价过程中的谋略动机,那么该规则的应有作用必然难以发挥出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信息揭示义务规则与当事人保密利益相冲突,使债权人面临两难选择,致使该规则的适用效果大打折扣。违约救济制度中,合理预见规则可谓信息揭示义务思想的典型代表,此外,预期赔偿规则也颇具该思想的色彩。通过比较各种违约损害赔偿规则,我们可以发现,预期赔偿成为违约赔偿的主要规则,它使违约受害方处于合同履行时状态,与其他救济方法如恢复原状、信赖赔偿相比,很有优势,因为预期赔偿通常包括利润损失,这是其他规则所不具备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利润损失的计算通常需要债权人揭示有关商业经营信息,比如原材料、劳动力成本、库存规模、供货商、顾客的身份,甚至还要涉及其商业计划。预期赔偿规则假设违约受害方揭示用来证明赔偿的上述信息是毫无代价的。实则不然。所有这些信息可能是债权人想保密的,公布这些信息会损害其利益,损害其在未来合同交易中的谈判地位,从而使他为此要支付较高的代价。因此,如果当事人认为某秘密信息很重要,那么即使该信息的揭示有利于未来求偿,经过利益衡量后,该当事人可能宁可不要求预期损害赔偿也不愿意公布该信息(注:Omri Ben-Shahar & Lisa Bernstein,The Secrecy Interest in Contract Law,The Yale Law Journal Volume 109,2000,pp 1885~88,p1892-93.)。由此看来,预期赔偿强调了受害方的“索赔利益”,却忽视了其另外一种值得保护的“保密利益”。信赖赔偿救济也要求受害方揭示某些信息,所以存在同样问题。诚然,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够共享信息,交易可能会更有效率,这是一种最佳交易条件,然而如果违约赔偿救济措施不能保护信息权利所有人,他就没有动力“放心大胆”地收集信息,不敢从事某些需要保密才能致富的行为。既然如此,我们应该从理想回归现实,退而求其次,选择无需要求揭示信息的恢复原状作为主要救济措施(注:Omri Ben-Shahar & Lisa Bernstein,The Secrecy Interest in Contract Law,The Yale Law Journal Volume 109,2000,pp 1885~88,p1892-93.)。这一观点主张“保密利益”优于“索赔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信息揭示义务理论的价值。
我们认为,在合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谋略动机始终控制当事人的心理。信息揭示义务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专门为解决谋略行为而立,带有一定反对商业投机的色彩,而合同交易尤其是商事交易必然带有某种投机成分,这样,该规则势必会引发商人在谋略投机与坦诚相告之间的博弈行为。而商业秘密更可以为权利人带来利润,法律要求当事人今天揭晓秘密以换取将来的损害求偿权益,当事人的犹豫心理是极为正常的人性表现。我们不应忘记,法律从来就是一种集体游戏规则,极可能损害个别人的利益,信息揭示义务规则概莫能外。
四
虽然我们对信息揭示义务规则的个别不足进行了辩解,但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该规则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下列见解对于理解这个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
第一,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合同漏洞的成因”。信息揭示义务规则最适于解释当事人谋略算计产生的合同漏洞,而不适于补充纯粹由交易费用、无法预知等形成的合同漏洞。但是,有时即使合同漏洞是谋略行为所致,法官也不能不加区别地一概运用信息揭示义务规则,而要适当考虑具体案件当事人揭示信息的利益与成本。当事人往往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法官尽量不要充当“事后诸葛亮”的角色。
第二,注意区分信息的种类。有人主张凡是属于私人信息就得告知对方,而公共信息则不必如此;有人主张免费取得的信息就得揭示出来,等等。但是不论如何,在市场经济就是信息经济的时代,法律不能要求一切信息都要公开,那样就可能违反了公平竞争,打击了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所以,法官必须要考虑商业秘密权益的存在并加以保护。尤其在当事人是有偿获得特定的私人信息时,法官必须要考虑保护当事人获取信息的积极性(注:Laidlaw V.Organ一案就反映出这一问题。案情大致是,Organ向Laidlaw购买了111大桶烟草。在签订合同时,Organ得到秘密消息说,1812年战争刚刚因为签署了停战协议而结束,该消息最终导致烟草价格飙升到合同价款之上。当Laidlaw的代理人问“是否存在可能使该标的物价格上升的消息”时,Organ保持了沉默。后来,Laidlaw想不履约,Organ起诉要求赔偿。关于Organ没有告知“停战”这一信息是否影响他求偿数额的问题,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认定Organ不负有揭示“他所专有的”信息的义务,因为对双方而言获取信息的手段是平等的( Barnett,Contracts Cases and Doctrine,Little,Brown and Company,pp 1225~1229(1995)) 。理查德·波斯纳认为,如果我们不允许人们拥有自己的信息从而受益,那么他们首先获取信息的积极性就会很小或没有,最终受损失的往往是社会。如果他不可能从隐蔽某些他拥有的信息而得益,那么他不可能有任何激励去开始其交易(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第139~140页)。)。
第三,注意区分特定的交易环境对当事人的影响。交易费用和谋略行为这两种因素都和竞争的充分程度有关。竞争越充分,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买卖双方都节约了大量的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所以,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减少谋略行为,使真实可靠的信息揭示得以发生,此时,法官更有理由认定合同当事人负有信息揭示的义务。
第四,注意区分当事人类型。商人之间的交易本带有一定投机性质,不可能要求商人之间相互告知一切信息。相反,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为了保护弱者应尽可能认定商人负有信息揭示义务。
第五,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合理预见规则属于任意性规范,可以由合同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英美合同法学者认定其属于任意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作为移植过来的一种规则,我们理当承认它是一个任意性规则。如果当事人没有排除适用的明确约定,法官应该根据其解释合同及分配违约损害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