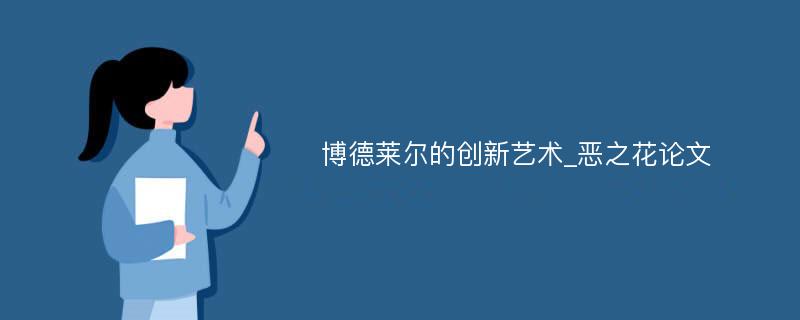
波德莱尔的创新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尔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德莱尔(1821-1867年)在法国诗歌乃至欧美诗坛上的地位是划时代的。正如法国一位评论家所说:“波德莱尔在生前受到种种攻讦,但在1867年之后,继之而来的是赞颂的合唱。”①他是颓废派的偶象,象征派的大师,被兰波称为“真正的上帝”,被安德烈·布勒东视作“道德观上的第一位超现实主义者”,保尔·瓦莱里把他看成法国“最重要的”诗人,诗人皮埃尔·让·茹弗将他称作“圣人”,英国诗人T.S.艾略特把他说成“现代和一切国家最伟大的诗人”②。1945年,法国作家让·柯克多写道:“他的目光逐渐地落到我们身上,就像星光照射到我们一样。”③当代评论家雨果·弗里德里希指出:“随着波德莱尔的出现,法国诗歌具有欧洲的规模。从它此后对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影响来看,可以证实这一点。再者,波德莱尔的作品在法国促使不同于浪漫派的诗歌流派产生,这些流派具有更大得多的创新性,渗透在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的作品中。”④确实,波德莱尔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是因为波德莱尔对诗歌的内容和艺术手法有过大胆的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对诗歌,而且对文艺理论和整个文学创作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波德莱尔的创新首先表现在诗歌描写对象上,以此所折射出来的美学观点具有崭新的意义。
十九世纪文学继承了以往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主要是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巴尔扎克和雨果的笔下,巴黎的黑暗腐朽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
不过,这些作家所描绘的仅仅是邪恶的人物,或者是这些人物活动的场所和背景,并没有专门以丑恶事物为唯一的描写对象。
波德莱尔则不同,巴黎这个大城市在他眼中只呈现出丑恶的东西。他笔下的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熙熙攘攘的都市,充满梦影的都市,/幽灵在大白天里拉行人的衣袖!/到处都有宛如树液一样的神秘,/在强有力巨人的细小脉管里涌流。”(《七个老头子》)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物,有的眼中出现恶相;有的目光宛如凛冽的寒霜;有的像跛行的走兽,脊梁和腿完全成直角,他仇恨世界,仿佛在用他的破鞋践踏无数死者;有的像来自地狱,幽灵一般向茫茫的目标走去;这些面目可憎的怪人,使诗人“逃回家中,关紧大门,中心惶惶,/像生病,像冻僵,精神发烧而混乱。”至于街上的老太婆,她们也是“弯腰曲背的怪物”,“低头前行,忍受无情的北风的鞭打,”(《小老太婆》)她们显然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波德莱尔尤其注意的是受到命运捉弄的盲人:“他们的眼睛失去神圣的光辉,/老是仰面朝天,如向远方凝望,/从没见到他们像在梦想一样,/把他们沉重的头向路面低垂。”(《盲人们》)他对盲人的观察是十分细致而独到的。诗人还注意到坐在绿呢赌台四周的老妓女,她们“尽是无唇的面庞,无血色的嘴唇,无齿的齿龈。”(《赌博》)在《恶之花》中,最不堪入目的丑大概是横陈街头的女尸了:“苍蝇嗡嗡地聚在腐烂的肚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粘稠的脓一样流动。”(《腐尸》)诗人的想象含有象征意义,这意义远远大于具体的形象本身。我们可以将腐尸看作社会的机体,它在诗人眼中幻化成一具实在的东西,它已经腐烂,发出恶臭,蛆虫乱爬。诗人对现实的厌弃,通过这一形象跃然纸上。
波德莱尔描写丑和丑恶的事物,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以往的诗人和作家,一般都是把美或美好的事物作为赞颂的对象,而贬斥丑恶的事物。波德莱尔则相反,他不认为丑恶的事物就是绝对的丑,而是认为丑中有美。在波德莱尔看来,自然即不美,也不迷人。他认为“自然是丑恶的”,⑤“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平庸的”;孤独的漫步者面对大森林的美不会感动,也不会击节叹赏。他感到自然的景色是丑的,“邪恶”的,这里是发出恶臭的腐尸,那里是行迹可疑的街道,这里是破旧垂死的东西,那里是肮脏不堪的令人不快的事物。诗人以粗俗的有毒的自然,以犯罪和罪恶的渊薮和沉沦的场所来代替美好的、优雅的自然。他认为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相反,美德是人为的,超自然的,”“恶不用费力,自然而然,命定地就形成了;善总是人为的产物。”⑥波德莱尔进一步认为,人类无法逃避沉沦,人生活在丑恶的现实中,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恶存在于人的心中,就像丑存在于世界的中心一样。愿望、激情、情感,一切都被一种天生的麻疯病毒害了。波德莱尔对世界和人类的看法是悲观的,这是他的美学观的出发点。然而他并不否认美的存在:“美一是由永恒的、不变的因素组成的,这种因素的数量极难确定;美二是由相对的、因时因地而定的因素组成的,这种因素轮流是,或者全部是时代、时尚、伦理、激情。第二种因素就像有趣的、令人心痒的、令人开胃的神圣点心的外表一样。如果没有它,第一种因素就会不易理解,微不足道,不适用于人性。我怀疑凡是美的样品会不包括这两种因素。”⑦波德莱尔关于美的观念包容极广,既有社会因素,也有时代因素,既有人的因素,也有情感因素,既是现时的,又是永恒的。可是,在诗歌中怎样表现美呢他认为应该写丑,从中“发掘恶中之美”,“在我看来,这是令人愉快的,尤其是这个任务越难完成,就越令人高兴。”⑧他还要表现“恶中的精神骚动”。对此他有过解释,他说:“雄壮的美最完美的典型是撒旦,——按照弥尔顿的方式来写。”⑨撒旦在弥尔顿的笔下是反抗上帝的英雄,但它是恶的精灵,弥尔顿从恶中发掘出了美。波德莱尔分析道:“这种古怪的事物确实值得注意:就是将美这种难以捕捉的因素引入在于表现人的灵与肉固有的丑的作品之中。”⑩这就是说,除了社会中、自然中存在的丑以外,还要描写人内心的精神的丑。
总的说来,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这在美学上具有创新意义。他明确意识到从丑中可以提炼出美,丑就是美,这种美学观点是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
二
波德莱尔在诗歌中展示了个人的苦闷心理,写出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悲惨命运。在诗歌中表现青年的这种心态,对文学来说是别开生面的。浪漫派在小说中塑造了世纪病的典型,而浪漫派诗歌只表现了爱情的失意,精神的孤独,政治上的失落感,在挖掘人的深层意识方面还仅仅是开始。波德莱尔则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自己对忧郁的描绘,他说:“忧愁可以说是美有名的伴侣,以致我不能设想(我的头脑会是一面受魔法盅惑的镜子吗?),美的典型中会没有不幸。”(11)因此,波德莱尔的描绘具有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
从诗集的内容来看,波德莱尔是在力图表现人的苦闷的精神状态。在《恶之花》中,诗人除了使用忧郁这个词外,还用了不少同义词和近义词,如无聊、烦恼、痛苦、晦气、悔恨等等。诗人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忧郁,形容为破钟那样,嘶哑的声音活像要咽气的伤兵(《破钟》)。他还把这种心境比作阴雨连绵的冬季,笼罩着阴暗的寒冷、亡魂、墓地、死气、雾(《忧郁之一》)。诗人说自己像活了一千年那样疲倦和厌倦,脑子像大坟场、万人冢(《忧郁之二》)。诗人百无聊赖,对万物厌弃,像个活尸一样,血管里流着忘川的绿水,而不是血液。最重要的一首诗《忧郁之四》描绘精神痛苦的各种感觉:疯狂、暴跳、发出吼叫、像鬼怪激荡、呻吟哀号。这个社会就像低垂沉重的天幕,人的脑壳深处像被蛛网封住一样,在这个牢笼里,希望乱碰乱撞,找不到出路。最后精神爆发危机,如同送葬一般,十分悲哀。烦恼得胜,在诗人的脑壳插上了黑旗。总之,忧郁像魔鬼一样纠缠着他。忧郁苦闷的精神状态是对现实生活,对“人类状况”不满而产生的病态情感,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是诗歌中出现的一种世纪病。还需要指出,在波德莱尔笔下,忧郁与理想构成一对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理想事物和希望只是短暂存在的。而忧郁却是长期的,与时间同在的。他认为时间是人的大敌,它吞噬生命,延长忧郁,拒绝接受幸福的幻觉。因此,人呆在极其尖锐的忧郁与理想的共处一体中:“我是伤口又是刀!/我是耳光又是面颊!我是四肢,又是车轮(按:指古代的一种酷刑,即把受刑者的四肢打断,再放在车轮上),/我是牺牲者,又是刽子手!”(《自惩者》)波德莱尔认为有才华的人就像落在甲板上的信天翁一样,这云天之王“出没于风暴中,嘲笑弓箭手”,而一旦流落在甲板上,“它巨人的翅膀却妨碍它行走。”(《信天翁》)有才能的诗人处于这浊世上的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日常生活的卑污平庸窒息了诗人的才具,他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干。诗人并不是没有理想追求,他也想“远远地飞离这种致病的瘴气”,认为抛弃这迷雾般压抑人和使人产生的巨大的生活忧郁“真是幸福无穷”(《高翔》)。诗人幻想在异国的宁静中生活,但这种对旅居热带小岛的回忆宛如前生(《前生》);他在黄昏的和谐中感受到优美的舞曲旋律,可是这种音乐最后却变成了怨诉(《黄昏的和声》)。总之,波德莱尔的精神苦闷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自身命运不济,寻找不到出路,而陷于悲观绝望的心境。1850年,《恶之花》在《家庭杂志》预先出版时,曾做广告说明该书“在于表现现代青年的激动和忧愁”。1851年,《议会信使报》也认为该书“在于勾画现代青年的精神骚动史”。(13)这两则说明正确表达了《恶之花》反映的内容的精神实质。
这种精神状态是诗人身世经历的产物。他的一生是一系列悲剧的组合(幼年丧父,与继父不和。遗产挥霍光之后以文为生,生活拮据)。忧虑、债务,从青年时代起就染上的疾病的复发,摧残着他的肉体和精神。《恶之花》就打上了这浪荡的、悲苦的、艰难的生活悲剧的烙印。波德莱尔从不隐瞒,这部诗集写的就是他的生活、他的梦想、他的反感、他的欢乐和他的痛苦。他在1866年给昂赛尔的信中说:“在这部残酷的作品里,我放进了我整个的心,我所有的温情,我的全部宗教(经过乔装打扮),我的所有仇恨。”(13)需要指出的是,波德莱尔在1848年间曾经一度热衷于政治。他在日记体的《我的坦露的心》中写道:“1848年我的迷醉。这种迷醉属于什么性质呢?这是复仇的兴趣。这是要毁坏的自然而然的乐趣。”他又说:“六月的恐怖行动。人民的狂热和资产阶级的疯狂。对犯罪的天然热爱。我对政变的愤慨。我多么想开枪啊!又是一个波拿巴家族的人!多么令人羞耻啊!拿破仑第三皇帝就是这样。”(14)他曾同《公安报》合作过两期。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使他精神深受震动。此后,他对共和派的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冷嘲热讽。米歇尔·布托尔指出,他认为当时的民众起着“说情者”的作用,他在这面镜子中企图认出自己。(15)就在同一时期,即1846年,他曾经把《恶之花》起名为《累斯博斯女人》;1848年11月,又改为《地狱的边缘》。这个书名具有社会主义派别使用的含义:傅利叶把“社会开端和工业处于不幸的年代”称之为“地狱边缘的时期”。当时有个记者写道:“今日,我们看到一部诗集《地狱的边缘》宣布要出版。无疑这是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诗歌。”(16)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理解为对社会的不满,具有反抗情绪。这种不满和反抗情绪是当时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心态流露。《恶之花》表现的正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的这种苦闷情绪。
三
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中提出了通感理论,把文学和其他艺术沟通起来,大大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为现代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这是他的一大功绩。
追根溯源,通感理论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图。近代哲学史上最先论述通感的是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他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互有联系的体系。波德莱尔从前人的鳞半爪的叙述中,总结出通感理论,他认为这是“各种官能中最科学的,因为唯有它包含了普遍的相似,或者说,这就是一种神秘的宗教称之为‘通感’的东西。”(17)
通感这个词主要出自波德莱尔的同名十四行诗。这首诗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因为它包含了波德莱尔诗艺的要点。在《通感》中,波德莱尔把诗人看作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媒介者。诗人能理解自然,因为自然同人相似(树木是活的柱子,发出含含糊糊的语言)。诗人在自己的各种感觉中看到宇宙的统一,这些感觉只是宇宙的可感反映。波德莱尔区分了两种现实:自然的,即物质的现实,这只是表面;精神的,即内在的现实,他认为这是宇宙起源的基因。通过象征——由自然提供的物质的、具体的符号,也是具有抽象意义的负载者——诗人能够理解更高的、精神的现实。他认为诗人本质上是明智的,命定能破译这些象征符号:人要不断穿越象征的森林,力图理解其中的含义。
波德莱尔由此指出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他在一篇艺术评论中写道:“一切、形态、运动、数量、色彩、香气,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精神界,都是富有含义的,相互作用的,相互转换的,相通的,”一切都建立在“普遍相通的、永不竭尽的资源”之上。这段话可以作为上述这句有名的诗的补充。这句诗扼要地,但完整而形象地提出了一切感觉相通的观点。《通感》主要从香味出发来阐发这一理论:某些香气同触感相似(“嫩如孩子肌肤”);这些香味随之又可以从声音得到理解(“柔和像双簧管”);最后溶入视觉之中(“翠绿好似草原”)。不同感觉互相交应,因为它们全都趋向同一道德概念:纯粹。无论孩子肌肤、双簧管,还是草原,都突出了纯洁,它们使人想起爱情的殿堂。接着诗人以腐蚀的丰富的和得意洋洋的香气与前面几种香气相对照,这些香气令人想到龙涎香、麝香、安息香、乳香,即包括整个异国情调的世界。这些香的质地能无限扩张(“具有无限事物那种扩张力量”),它们不断升腾,引导诗人幻想更高的现实。扩张于是变成入迷状态,感官的沉醉导致精神的入迷,因为这些香味“在歌唱着头脑和感官的热狂”。至此,通感达到了最高潮,这是狂热的头脑和感官作用的结果。
波德莱尔还认为诗歌应该同别的艺术相通。他从版画(卡洛、戈雅、韦尔奈)到雕塑(《面具》、《骷髅舞》),再到音乐和绘画,写出这些艺术形式之间相通的关系。在《灯塔》一诗中,他写到鲁本斯、达芬奇、伦勃朗、米开朗琪罗、皮热、华托、戈雅和德拉克罗瓦的画在诗人眼里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意象。波德莱尔认为绘画和诗歌是相通的。他说:“如果各种艺术不致力于力求互相代替,至少要力求互相借用新的力量。”他又说:“画家把音阶引进了绘画中”(18),艺术家从此可以用声音和色彩等手段去表达感情。
总之,波德莱尔认为可感知的形式乃是理想现实的表现和象征。《恶诺》就提供了大量通感的实例。他在一篇序言草稿中写过这样三句话:
“但愿法国诗歌拥有一种神秘的、不为人熟知的韵律学,就像拉丁语和英语那样;”
“但愿诗歌的句子能模仿(由此它接触到音乐艺术和数学)水平线、直升线、直降线;但愿它能笔直升上天空,毫不气喘,或者以地心吸力的速度下降到地狱;但愿它能沿着螺旋形前进,画出抛物线,或者画出构成一系列重迭角的曲线;”
“但愿诗歌同绘画艺术、烹调术和美容术结合起来,因为有可能表达一切甜蜜或愁苦,惊呆或恐惧的感觉,只要将某一名词与某一相同或相反的形容词组合起来。”(19)
在这三句话中,波德莱尔阐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词与词之间的某种组合,会产生奇异的现象;他在寻求达到通感的途径。在他看来,诗歌存在一种新的韵律学,根据这种规则写出来的诗句,能像线条一样变化无穷,但这种诗句必须同别的艺术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效果。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以不同方式组合的词取得的效果”更惊人、更神秘的了。于是他得出这个著名的说法:“只要人愿意,灵感总会来的,但它不一定在人愿意有灵感的时候就一定来到。——从语言和写作中,就像玩魔术一样,会获得引起联想的魔法。”(20)这种“联想的魔法”就是通感手法。波德莱尔属于这样的艺术家,他孜孜以求的是“发现艺术家赖以创作的隐蔽的法则,并从这种研究中得出一系列原则,这原则的神圣目的就是诗歌创作的必然性。”通感就是波德莱尔找到的诗歌创作的隐蔽法则,它像打开了一扇门,使艺术家能够深入到艺术的更高级的殿堂。因此,雨果说他“创造了新的颤栗”(《1859年10月6日给波德莱尔的信》),邦维尔称他为“最完全、最绝对意义上的新诗人”(《当代画廊》,1867),于依思芒斯认为他“做到了表达无法表达的东西……表达衰竭的精神和忧郁的心灵最易逃逸的、最紊乱的病态”(《反乎常理》,1884)。这些评价高度赞扬了波德莱尔运用通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四
与通感相关的是象征手法;波德莱尔以象征手法来描绘抽象的精神现象,大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描绘,使文学朝内倾性方向的发展极大地深入了一步。波德莱尔主张运用“艺术包含的一切手段”(21),这句话强调的并非指已有的,或不为人们所熟悉的技巧。
象征手法就是波德莱尔所力求创造的,丰富艺术表现力的主要手段之一。以《忧郁之四》这首诗为例,诗人是怎样表达和描绘忧郁这种精神心理状态的呢?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十分抽象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心态。波德莱尔别出心裁地用各种意象来表现这些心态。他在诗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第一个意象:他把天空写成锅盖扣在地平线上,这就立即造成一种压抑感;既然是锅盖,那就不会发出白光,而只能是黑光。这里写的是自然,又写的是脑壳(圆锅形)和精神;黑光同忧郁的精神感受密切相连,因为黑同阴郁的、悲伤的、沉闷的概念是相通的。第二和第三个意象:诗人把大地形容为一个牢狱,而把人的希望写成一只蝙蝠,关在这牢狱中,无法飞出去,只能困顿在里面。第四个意象:写雨水如同铁窗护条,与前面的牢狱意象相呼应。第五个意象:一群无声的卑污的蜘蛛在脑壳深处结网,网能产生封闭的感觉,加强忧郁之感。第六个意象:大钟吼叫起来,像游荡的鬼怪在呻吟哀号。大钟可看作形容精神紧张。第七个意象:一长列柩车没有鼓乐作为前导,从诗人心灵上缓慢经过,丧仪车队是哀伤的象征,且是没有鼓乐相伴的柩车,更显悲哀,写出了诗人心灵的悲戚感,沉重而深切。第八和第九个意象:希望因战败而哭泣,而烦恼得意地插上了胜利的黑旗,不是插在地上,是插在诗人低垂的脑壳上,多么残忍专制!这幅图画又多么凄惨!这一连串意象从各个角度来描绘忧郁,使难以捉摸的情感获得了具象的形态,以实写虚,以有形写无形,但又不是实实在在的有形,这能使读者再发挥想象,加以思索,去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这些意象所起的作用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比喻或图解,它们的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这就是象征手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象往往采用了拟人化或寓意化的手法。希望本是抽象概念,但在诗中时而化为蝙蝠,时而干脆就是“人”,因战败而哭泣。烦恼也是抽象概念,在诗中则化为“人”,残忍而专制。心境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抽象情绪,在诗中变为蜂蛛。波德莱尔认为拟人化或寓意化“这种非常有趣的样式,笨拙的画家给我们堆积得令人蔑视,其实却真正是诗歌最原始的和最自然的形式之一。”(22)在波德莱尔笔下,时间、爱情、美、死亡、偶然、羞耻、愤怒、仇恨、错误、罪恶、呜咽、复仇、寒热、光明、黑夜、骄傲、永恒、友爱、不朽、不洁、能力、人道、乐趣、德行、悔恨、工作、忠诚、愚笨、放浪、痛苦、岁月、怀念、虚无……都拟人化了,“对我来说,一切都拟人化。”(《天鹅》)有时这些抽象名词罗列在一起,有时整首诗都由拟人化的意象组成。《恶之花》中,抽象名词随处可见,由于拟人化或寓意化而改变了抽象名词本身的功能,使之变得具体、丰富、具有新的含义,这种手法使《恶之花》具有独特的光彩,显得深邃、隽永,别具一格,奇特而不荒唐,新颖而能令人接受。诗人说过:“美总是古怪的。我不想说,它是故意而冷冰冰地显得古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是一个摆脱了生活轨迹的妖怪。我是说它总是包含着一点古怪的意味,这种古怪是自然的,不是故意的,是下意识的,正是这种古怪使这成为特别的美,这是它的标志,它的特点。”《恶之花》就具有这种奇特的美。
大部分诗人都是从大自然中去寻找意象的,波德莱尔则相反,他很少从大自然中去寻求意象,而是常常颠倒这种比喻次序。例如,“低垂沉重的天幕像锅盖,”不是锅盖像天空,而是天空像锅盖;“大地变成了一座潮湿的牢狱,”雨水“宛如一座监狱的护条那样”,都是意象颠倒运用的例证。这种手法的美学效果令人惊奇,显得别致,以奇取胜。它能产生一种压抑感,因为在这种比喻中,由大变小,而且这是锅盖倒扣;牢狱则代表着不自由,读者很容易获得一种局促、憋闷、不舒服的感觉。波德莱尔寻找的意象往往都是邪恶的、有害的、难看的事物,具有一种“冷光”,给人阴冷、幽冥的感觉。
波德莱尔在散文诗的运用和推广方面的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散文诗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文学样式。先是阿洛瓦修斯·贝特朗发表《黑夜的加斯帕》,尤其是莫里斯·德·盖兰的《半人半马怪物》和《酒神女祭司》,对散文诗的体裁有所建树。他们的散文诗富有音乐节奏和诗意。贝特朗对波德莱尔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波德莱尔说过;“我们当中,哪一位在他雄心勃勃的时期,没有梦想过创作这样一种散文的奇迹呢?这种散文是诗意的,有音乐性的,没有诗韵和节奏,相当灵活,对比相当强烈,以致能适应心灵的抒情冲动,适应梦想的起伏和意识的跳跃。”(24)从1857年起,他准备发表一部散文诗集,此后在一些杂志上能见到他的散文诗。由于生活拮据,他生前未能如愿出版这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在他去世后才问世(1869),共有五十篇。他力求在这部散文诗集中“致力描绘现代生活,或者不如说描绘一种更抽象的现代生活,用的是《贝特朗)擅长的以描绘极其古怪别致的古代生活的方法。”(25)
波德莱尔可以说是散文诗创作的先驱,当时散文诗还是一个处女地。波德莱尔的用文诗发表后,诗人们纷纷仿效,于是散文诗终于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
波德莱尔给散文诗规定了大致的格式,认为散文诗是一种具有诗意和音乐性的散文。他感到真实适用于短篇小说,而节奏适用于诗歌,怎样把两者调和起来呢?于是他找到了散文诗,将真实和美、诗歌和写实、永恒和日常、可怕和滑稽、温柔和仇恨统一起来。波德莱尔进而指出,散文诗的内容写的是心灵的抒情冲动,梦想的起伏变化和意识的跳跃,也就是说要发掘内心世界。总之,波德莱尔认为散文诗是介于诗与小说的一种文学体裁,能将诗的节奏美、音乐美与小说的反映真实的自由结合起来,兼有两者之长。
波德莱尔的散文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巴黎的忧郁》虽然是《恶之花》的改写,但并没有受到诗歌的约束,这种改写是相当自由的,决不是《恶之花》的重更。试以同名的《邀游》为例,《恶之花》中的《邀游》其实是一首情诗,表达了诗人寻找甜美生活的理想;诗中描绘的国度多半指水乡泽国的荷兰。而散文诗《邀游》却改变了内容,这不是一篇抒写爱情理想的文字,而是写一个理想的地方,一个虚无缥缈之境。这些散文诗充满了柔和的诗意,写得十分随便,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但又十分精粹,短的只有一二百字,长的也不过两千来字,浓缩精炼,意味深长。至于内容,既有抒发自己的感慨,也有的某个社会场景描绘;既有城市风貌的写照,又有对月亮的吟哦;既有人物刻画,又有动物描写,不一而足。大多是平铺直叙的散文,也有的写成一篇短短的对话。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多种多样为日后的散文诗提供了典范。
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他一开始就明确意识到要理解艺术的“现代性”。他在评论画家康斯坦丁·吉斯(1802~1892)的作品时,特别提出了这一点。他说,吉斯“在寻找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性’;因为要表达题中之议,没有更好的字眼了。对他来说,就是要从时尚中抽取出历史性所包含的诗意内容,从暂时性抽取出永恒来。”(26)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从现实生活中具有历史性内容的事物,抽取出反映现代本质的诗意的东西,也就是从现时事物中抽取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这种现代性,必然不同于传统性,它包含了现时的本质,同时能传至将来。现代性是一种美学观点,波德莱尔用它来指导艺术和诗歌创作就具有高屋建瓴之势,站在了革新传统的的高度上。
波德莱尔深知,美存在于字句和诗歌语言的意象之中,“波德莱尔第一次在我们诗歌史上实践了真正的语言‘炼金术’,由此打开了诗歌现代性的纪元。”(27)波德莱尔为《恶之花》起草的《结束语》中这样写道:“噢,你啊,请证明我履行了手续,/就像一个完美的化学家和圣人。/因为我抽出了每种事物的本质,/你给了我泥土,我炼出了黄金。”这是波德莱尔对自己锤字炼句的形象说法。波德莱尔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是惊人的,正如他所说:“我整个一生都用来学习构造句子。”(28)这句话足以证明他对语言的重视。
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上的现代意识,是导致他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找到诗歌语言的奥秘,取得杰出成就的主要原因。福楼拜在给他的信中说得很正确:“你找到了使浪漫派年轻的方法。你迥异于任何人(这是所有优点中的第一位)。风格的独创取决于创作。你的句子塞满了思想,以致都要爆裂开来。”(29)兰波更进一步指出:“波德莱尔是第一个通灵人,诗王。”“通灵人”是兰波从前人那里发掘出来的一个字眼,指的是敢于突破传统,找到现代诗歌表现手法的诗人。波德莱尔确实是找到了现代诗歌的奥秘和开启现代文艺大门的钥匙。因此,他被尊称为现代派的鼻祖实在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①② 布吕奈尔等:《法国文学史》,第478、483页,博尔达斯出版社,巴黎,1981年。
③④ 雨果·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第40、39页,德诺埃尔—贡蒂埃出版社,1976年。
⑤⑧ 《1859年画展》,《波德莱尔全集》,第2卷,第181、183页,加里马出版社,1988年。
⑥⑦(26) 《现代生活的绘画》,《全集》,第2卷,第715、685、694页。
⑧(19) 《〈恶之花〉序初稿》,《全集》,第1卷,第181、183页,加里马出版社,1975年。
⑨(11)(20) 《迸发篇》,《全集》,第1卷,第658页。
⑩ 《笑的本质》,《全集》,第2卷,第526页。
(12)(29) 《〈恶之花〉说明》,《全集》,第1卷,第793、845页。
(13)(21)(22) 转自吕夫:《波德莱尔》,第102、124、128页,阿蒂埃出版社,1966年。
(14) 《全集》第1卷第679页。
(15)(16) 《法国文学史》,第5卷,第153、155页,社会出版社,1977年。
(17) 转自兰塞:《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第41、7-8页,纳唐出版社,1988年。
(23) 《1855年的世界博鉴会》,《全集》,第2卷,第578页。
(24)(25) 《全集》,第1卷,第275页。
(27) 兰塞:《十九世纪法国诗歌史》,第85页,法国大学出版社,1977年。
(28) 《通信集》,第2卷,第615、307页、第1卷,第676页,加里马出版社,197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