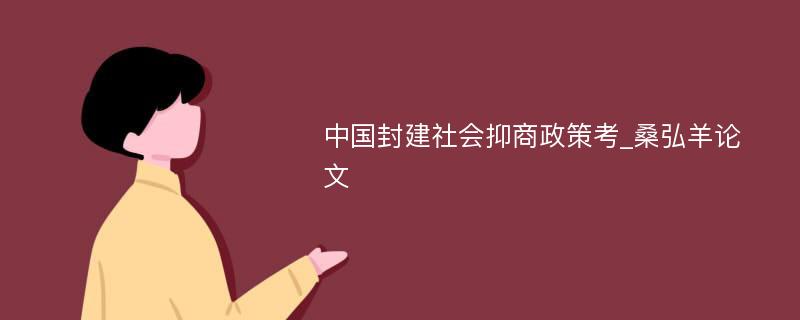
中国封建社会抑商政策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社会论文,中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的商业政策时,大多数论者总以“重农抑商”或“崇本抑末”概而论之,并认为这是封建统治者们奉行不逾的“固定国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推行的商业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得出的结论就会与此大不相同。
1
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无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它既是封建小农经济的基础,也是农业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如甲骨卜辞中关于殷商统治者为祈求农业丰收而进行的种种活动;西周统治者每年举行的隆重“藉礼”,以及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关于“农者,天下之本”[①]的告诫等等,无不充分说明了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但是,抑商则未必,抑与不抑,或抑的程度如何,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以及统治阶级和商人阶层力量的对比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政策思想,首倡于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②]。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变法。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一方面农业人口十分缺乏,已到了免征十年赋税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③]的地步;另一方面,城市商业活动却很兴盛。针对这种情况,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具体措施包括:(一)“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④],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杜绝商人利用年岁丰歉进行粮食投机,牟取暴利;(二)“重关市之赋”[⑤],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三)令商人及其奴仆均负担徭役,使“农逸而商劳”[⑥];(四)“食贵,籴食不利”[⑦],使商人以高价向农民购买食粮而受损;(五)“壹山泽”[⑧],由国家对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在上述诸措施中,又以重税和盐铁专卖为其主要内容。这些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巩固了秦国地主阶级政权,收到了“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⑨]的效果。但是,我们从商鞅的抑商政策来看,虽然在经济上对商业资本的发展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可是在政治上却并未对商人提出什么限制或约束。而且,商鞅抑商政策的实质,一方面,在于通过国家对山泽之利的垄断和对私营商业的干预,达到发展官营商业的目的;另一方面则在于禁止影响正常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奢侈品生产,以调整农商人口比例失调的矛盾。他说:“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⑩]这里的“末事”,当指那些奢侈品生产。因为商鞅明确指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11)既然把禁末列为富国强兵的条件之一,那么,他所指的“末事”,就不可能是正常的商业和一般的手工业,而只能是奢侈品生产。对于商业的职能,商鞅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他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食字衍,官犹职)。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12)他显然看到了商业在流通方面的作用,认为它与农业、官吏一样,是国家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
真正从政治上提出抑商,并在理论上作了发挥的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在《五蠹》篇中,称“工商之民”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明确提出要“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趋)本务而外末作”(13)。这里,减少商工游食人数,是对商鞅抑商政策的继承,而使其“名卑”,亦即降低其社会政治地位,则是韩非的首创。韩非的理论提出后,确实曾得到秦王嬴政的赞许,并将其付诸实施。秦王明令将“贾人”与“治狱吏不直者,诸尝捕亡人、赘婿”(14)等身份低贱者列为同类,后又将他们充征或戍边,故迁魏之孔氏于南阳,徙赵之卓氏于临邛等等。但仔细考察,秦王的抑商政策则既不严格,也缺少实际行动,而且主要矛头是针对六国旧工商业贵族集团。对这些人实行强制迁徙,旨在摧毁他们在经济、政治上的基础;而同为巨商大贾的乌氏倮(姓乌氏,名倮,氏读支)和寡妇清,就因为他们不是在六国境内成长起来的工商贵族,故非但不受限制,反而恩宠备至。由此可见,秦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说它既不严格,又缺乏持续的行动,是因为被迁徙的工商业者并没有受到具体的限制,他们到达迁徙地后很快又发达起来,如迁到南阳的孔氏照旧“大鼓铸”,“家富数千金”;迁到临邛的赵之卓氏也依然冶铁煮盐发家(15)。
与秦王朝相比,西汉时期倒是在“抑商”方面有了更实质性的内容,持续时间也较长。汉高祖刘邦即位伊始,即下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16),而且还颁布了“轻田税”令,使“重农抑商”在实践层面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中经惠、文、景诸朝,直到武帝时,还任用桑弘羊等人理财,在商业政策上推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打击富商大贾对经济的垄断和市场的操纵。这与西汉初年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在政治上,由于秦王朝对六国旧工商业贵族打击不力,使他们在西汉初年仍“连车骑,交守相”(17),对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构成威胁。在经济上,西汉建立之初,万象凋敝,农业劳动力十分缺乏,农业“户口不得而数者十二三”(18),经济衰败到“民无藏盖”,“天子不能具钧驷”(19)的地步。可是,一些富商大贾和豪强地主却仍在疯狂地兼并土地,掠夺人口,“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20)的现象普遍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才采取了上述抑商措施。
随着西汉社会经济日渐恢复,抑商政策也逐步松弛。到惠帝、高后时,商人“乘坚策马,履丝曳缟”(21)已成合法。到武帝时期,抑商内容就只剩下打击富商大贾兼并土地和垄断经济了,这从桑弘羊理财所采取的措施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无一不是针对富商大贾的,而对中小商人则不仅不抑,还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政策和主张。如桑弘羊一上台就提出“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的口号,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使农商工师各得所欲”(22),实际是农商并重。桑弘羊等人以商人之后裔上台执政,本身已使汉初的贱商令化为乌有。所以,元代史学家马端临评论说:桑弘羊等人上台,使“市井子孙不能为吏之法尽废矣”(23)。西汉末年,有人曾奏请哀帝重申“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之令,也只落得个被搁置不问的结果(24)。
东汉政权,本身就是在豪强富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地主兼商人出身。因此,通观东汉时期的历史,除了桓谭曾提出“禁民二业”的主张之外,几乎再找不出一点抑商的影子。即使这一点,到汉明帝时,因地方官禁民二业而影响农民因地制宜,在屯骑校尉刘般的建议下也被明令取消了。这样,原本就徒有其表的“抑商”政策最后连“表”也没有了。所以,东汉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这可以从东汉末年仲长统的一段描述中窥其端倪:“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从其心之所虑”,“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有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25)仲长统的记载只是一个事例,类似的例子还很多,限于篇幅不多赘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比较特殊。在此三百六十余年间,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割据分裂状况。大体上在三国两晋时盐铁实行专卖。南北朝时,专卖时兴时废。西晋时颁布过一些贱商令,如规定商人的衣着服饰等(26)。其他时期则基本上没有什么贱商或抑商法令颁布。相反,在三国时期,大商人与武装力量结合,在政治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如西蜀时期的大商人张世耳、苏双以及货殖世家糜竺,前者以巨资资助刘备起兵,后者则以妹嫁与刘备,以致出现“货殖之家,俟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27)的局面。对于这一时期的专卖,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因为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各武装力量和军事政权若不对一些重要商品进行专营,就无法保证重要的生产、生活和军事必需品的供应。所以,此时实行专卖,并不具有抑商的意图。
隋和唐初,统治者又曾重提汉初贱商之令,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如唐太宗初定官品时曾说:“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28)高宗时还仿刘邦之法,对工商业者的车骑、服饰等作了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只准穿白衣,不准著黄(29)等等。但是,由于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国势强盛,百姓安居乐业,中国封建王朝处于最强盛的时期。因此,此时对商业和商人的限制并不严厉。唐初的贱商令,从根本上讲仍是徒有其名,并无其实。它不仅对富商大贾不起丝毫作用,而且本身又与唐初实行的经济开放政策相矛盾。唐政府实行减轻商税政策,使那些名不列市籍,身不在市肆的富商大贾们,不仅不受贱商令的限制,而且利用唐初有利的经济形势,大展宏图。因此,唐建立不久,私营商业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商业资本迅速膨胀,以致出现了许多像邹凤炽那样“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30)的富商大贾。到中宗时期,贱商令已开始被卖官令所代替,其时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为中书”(31),“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32)。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又诏许藩镇保荐人物替升属下武将缺额,于是,“富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33)这样,工商杂流不能入仕的限制便被彻底冲破了。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他提出“因民之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34)的主张,通过控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发展官营商业的手段,推动整个商业的发展,形成了唐代以官营商业为主、私营商业为辅的发展格局。刘晏的这一政策主张,把自西汉桑弘羊以来重视商业的思想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如果说,唐代以前的统治者在开国之初还要象征性地颁布一些抑商法令的话,那么,到宋元时期的统治者则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相反,在宋代,一向被思想家们所提倡的“抑兼并”思想也被“不抑兼并”的国策所代替,还颁布了一系列“恤商”法令,对商人加以鼓励。如宋太祖受禅之初,即明确宣布:“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筐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35)太宗继位后,又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36)除了对商税作了规定外,宋初还严禁各级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并规定了处罚条例,如:“滞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37)王安石变法时期,虽然对豪商大贾采取了一些打击措施,但对正规商业却体恤有加,他下令“减免汴京国门商税数十种,税钱不满三十文的免征,运货至边易转勿税,石炭至京不征”(38),强调“榷法不宜过多”(39),让商人拥有更广泛的商品经营权。宋代还在政治上提高商人的地位,在选拔官吏时,“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40)这是封建统治者以法令的形式正式宣布抛弃自汉代以来奉行的商人及子孙不能入仕的禁律,较唐代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宋王朝的这些做法,不仅对富商大贾有利,而且也有利于中小商人的发展。所以,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不是没有政策依据的。
元代是一个比较重视商业的朝代,这几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元朝建立之初,就任用了一批回纥、汉族商人如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等为理财大臣,并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忽必烈在灭宋前一年就命福建行省向外商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41)又以巨资付给江南行省“与民互市”(42)。不仅当时的大都成为商业中心,杭州也是除“不计其数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43)。在元朝,连一些儒生也打破耻于言利的教条,公开宣扬儒士们经商是“亦有可为”的举动(44)。
明清两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一度凋敝,统治者也曾宣布过一些抑商或贱商法令。但从总体上看,这两朝重农有加,抑商却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基本上可以说是抑商为表,恤商为实。如明初朱元璋在颁布贱商令的同时,又说:“商贾之士皆人民也。”并有鉴于商贾多不读书之弊,特命儒士编书教之,开中国历史上商业教科书之端。此外,朱元璋还认为元末商税太重,改二十取一为三十税一,并扩大免税范围,“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45)明成祖又进一步扩大免税范围,“凡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46)在明代,商人及其子孙可以堂而皇之地应试科第,可以入仕为吏。据粗略统计,明代仅盐商子弟考取进士者就有180余人,成为举人者有340余人(47)。商人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使明初的贱商令反而变成了对农民的嘲弄。不仅如此,明中叶以后,又推行两项政策,对商人十分有利。一是嘉靖八年(1530)轮班匠制度的取消;一是万历九年(1581)“一条鞭法”的推行。前者使相沿二千多年的工匠徭役制度得以废除,工商业者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减轻。后者则使那些“操资无算”的富商大贾“亦以无田而免差”(48)。所以,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各地出现,无疑与这些恤商政策有着密切地关系。
清初,因反清势力很大,曾宣布过限织、禁矿、迁海的政策,但对商业仍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措施。顺治初定各省关税,京师免征一年,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和加增税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49)。康熙进一步提出:“利商便民”口号,严禁滥收商税(50)。雍正时在全国大规模推广“摊丁入亩”法(51),将全部劳役负担归入土地之中,使无地和少地的工商业者负担更进一步减轻。乾隆加大“恤商”力度,不仅取消了原来的禁矿、限织、迁海的禁令,还下令整顿关税,减免商税,给一些富商以召对、赐宴、赏赐的恩宠和“加价”、“加耗”、“减收盐税”等特权(52)。尤其是粮食免税和海禁开放以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53)。清代学者沈垚曾不无感慨地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概也。”(54)沈垚的感慨虽不无士人失落之悲凉,但却也较为准确地描述了当时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事实。
在对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商业政策及其实行情况作出较为系统的考察之后,还必须对两项与商业密切相关的经济政策做一番考辩,因为它们常常被一些论者作为历史上统治者推行抑商政策的重要例证。
2
第一,禁榷制度(亦称专卖制度)。它被一些论者称之为封建社会抑商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55)。所谓禁榷制度,即由封建政府凭借政权的力量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酒、铁、茶等进行垄断性经营。它首创于商鞅变法时期,其间除个别时期未曾实行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实行此项政策,有些朝代还辅之以均输、平准之法,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工商业政策。禁榷制度的实质是发展官营商业。因此,这里需要辨明的是官营商业是不是商业,发展官营商业是否一定就是抑商的问题。对于前者,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对于后者,回答则是否定的。因为:(一)从商业的职能来看,官营商业虽然在商品经营形式、资金来源和赢利目的等方面都与私商不同,但就其职能而言,则都是从事商品交换和组织流通领域的生产。而且,由于中国领域辽阔和个体小生产者的普遍存在,依靠政权的力量组织商品流通,还能起到私商所无法起到的作用。诸如唐代刘晏主持盐政时,长安“盐暴贵,诏取三万斛以赡关中,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56)。因此,不能说私商才是商,官商就不是商。(二)从历史上实行的禁榷制度来看,在唐以前多采用直接专卖制,如桑弘羊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商的经营范围,分割了一部分私商利润,有抑商的意味。但自唐中期以后,统治者相继采用间接专卖制(亦称就场专卖制,唐刘晏实行)、官商并卖制(宋王安石实行)、私商专卖制(明代张居正实行),使专卖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在直接专卖制时尚有一些抑商意味的话,到唐中期以后实行的几种专卖制,则完全变成了官商分利,互相利用了,靠专卖抑商的意义已荡然无存。无怪乎马端临曾指出:“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之人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57)马氏的评论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三)再从官商政策制定者的指导思想来看,也并非完全出自抑商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从重视商业及其社会功能的角度考虑的。如桑弘羊就认为:“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因此他明确主张:“农商皆重”(58)。桑弘羊的理论不仅论证了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也明确强调了封建国家对商业的依赖。另外,前述商鞅、韩非对商业社会经济职能的肯定,刘晏对桑弘羊思想的发展等,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既然制定官营商业政策者的目的主要在于重视商业的社会功能,那么,将其与抑商政策相提并论显然是讲不通的。而且,象刘晏等在推行官营政策时,非但不排斥私营商业,相反倒是很注意借重正当的私商之力,作为官营商业的补充。如他曾请代宗下令禁止地方对盐商征收过境税,以解除他们在食盐运销中的额外负担(59)。由此可见,官商政策不仅不是统治者推行抑商政策的手段,相反,却正是对商业的重视和依赖。
第二,除了禁榷制度外,历史上曾出现的重税政策,也被一些论者作为封建统治者推行抑商政策的典型事例。但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一方面,商税作为封建政府正常的税收之一,并不能笼统地用抑商政策待之。评判其是否有抑商倾向,要看商税征收的轻重是否合理。另一方面,还要看这种重税政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行的。一般而言,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出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目的,往往采取一些“恤商”的政策,商税征收相对较轻,而且就各王朝初年征收的商税趋势来看,基本上呈愈来愈轻之势。如汉初改秦之什一税为十五税一,景帝时又降为三十税一。隋初文帝废除关市之税。唐太宗也明令废除诸关,商人自由贩运。宋元时期,商税征收从总体上看较前更轻。宋朝商税主要有两种:一是过税或名关税,每千钱征税二十;一是住税或交易税,每千钱征税三十。元初商税无定制,太宗八年(1236)定天下赋税,商税也只是三十分取一。至元七年(1270),中原税制始定,三十分取一,以45000锭银为定额,有增余者作羡余。同时规定:“以上都商旅往来艰辛,特免其课。”至元二十年(1283),始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旧城市肆院务迁入都城市者,四十分取一。明代虽然仍实行三十税一的商税,但与元代相比,缩小了征税货物的范围,免税物品极广,这从前面讲到有关明代商业政策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清代在顺治时,“关征木植税,十分取二”,十八年(1661)又“定各口木植什一而税”。但到雍、乾年间,开始实行常关税率多以价百分之五征税,而且自康雍朝开始,随着“摊丁入亩”法的推行,使商人负担更加减轻(60)。
重税政策大多在王朝末年或特殊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导致中央政府财政发生困难,才对商业采取掠夺政策。如汉武帝北击匈奴,就强行向商人征收百分之六的财产税。唐肃宗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对江淮蜀汉富商实行“率贷”,“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所收巨万计”(61)。此外,如唐德宗年间、北宋徽宗年间、南宋时期、明万历年间和清嘉道年间等,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统治者也曾对商人实行苛重的税收盘剥,使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滞和破坏。但是,这种强取豪夺的作法,毕竟不是统治者的既定国策,加之时间延续也较短,不能作为抑商政策看待。另外,在这种时期,往往包括被称之为“操持本业”的农民也一样受到沉重的剥削,他们和商人都成为统治者刀砧上的鱼肉。这种特定时期由统治者采取的“权宜”之计,自然不能与抑商政策混为一谈。
3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并不像有些学者概括的那样,是“重农抑商”或“崇本抑末”。实际上,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统治者除了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外,另外也在推行重农而不抑商,甚或重农而又恤商的政策。而且,如果从时间跨度和政策执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后者还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即使有些王朝的统治者颁布了抑商政策或抑商令,也往往或执行时间很短,或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从而形成了既重农、又恤商的政策内涵。除了一些特殊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就是这样不断地调整经济政策,以使其适应封建经济的基础,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超常存在的经济原因。那么,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商业政策呢?具体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统治者认识到了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既对立又同一的关系。一般而言,商品经济总是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面而存在。这种对立性就表现在商品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必然促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卷入交换而成为商品,促使自然经济中交换价值生产不断扩大,促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不断提高,从而逐渐侵蚀和瓦解自然经济。但同时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又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就在于它可以做为自然经济的补充物而发挥作用。中国的封建经济是由个体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两个部分组成的。个体经济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为其特征,在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都较低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生产、生活必需品,而只有通过市场的商品交换才能得来。正如《汉书·食货志》载:盐、酒、铁、铜等物,“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62)。即使统治者在计算农户收支时,除食粟外,也不得不用钱币计算开支(63)这就说明,即使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与小农经济发生天然的联系,并形成一种互补性。地主阶级无论采取人身依附关系较强的部曲奴客制,还是采取人身依附关系较弱的细农租佃制来经营生产,都必须要和商品经济发生联系。地主阶级不得不收取实物地租,以维持生活,还要将一部分地租投入市场,使之货币商品化,从而获取自己其他方面的生活需求。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64)
第二,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经济关系,强化了封建统治者对商业资本的支持。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几乎从一开始就与商业资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众所周知,诞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正是得益于富商大贾的支持才巩固了政权。在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中,不仅豪商巨贾与官吏勾结,互相利用者有之,亦官亦商,或官吏经商者也不乏其人,甚至连皇亲国戚也尽入商贾之流。据史载,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就曾大做生意,她被籍没家产时,“私货山积,珍奇宝物侔于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65)
如果说,官商勾结和官吏经商虽为官商结合提供了条件,但尚非一条合法途径的话,而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和土地自由买卖制度则不仅为官商结合开辟了一条合法的途径,而且也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关系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因为富商大贾手中握有巨额的资财,他们投资于手工业和其它行业尚需承担一定风险,但投资于政府却可以得到官爵,转入土地又可以得到最稳妥的生息资产。这种一本万利的事情,商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中国历史上“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便成了商贾们基本的信条。商业资本大量转向土地,出现了土地兼并剧烈、小农大量破产的局面。通过卖官鬻爵和土地买卖,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彼此的联系得到了更进一步加强。这种经济关系的建立,又使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同一性更加牢固,从而为封建政权的稳固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基于此,封建统治者才不遗余力地维护这种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局面。
第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又不能不依赖商业资本为之提供财政收入。如汉代的口赋、算赋、更赋;唐代的户税和两税法中的“居人之税”,都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为政府提供财政收入。明代推行“一条鞭法”以后,赋税中货币比重进一步增加,即使来源于农业部分的税项也多以货币充之。另外,从商业为封建国家提供的税收数额来看,也十分可观。宋朝“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67),仅开封府就有税务机构41个,商税在宋初为11万贯,到熙宁十年(1077)增加到40万贯,以后还曾增加到55万缗有奇(68)。元代文宗天历年间(1328—1329),商税收入即达93万余锭,还不包括对回回商人的减免税等。这些仅指私商的税额,此外,封建国家经营的官营商业也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唐代刘晏理财时,盐利收入增至600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69)商业资本在封建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第四,历代思想家的反抑商思想(70),也对统治者的经济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反抑商思想,几乎是与抑商思想同时并存的。早在西汉初实行贱商政策之时,司马迁就曾将农工商虞并称:“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71)。这可谓他的反抑商思想的典型言论。历代都有思想家对统治者的抑商政策提出批评。如南宋叶适针对汉初贱商之策,公开宣称:“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72)到明清之际,黄宗羲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73)。还有如东汉王符、唐代韩愈、宋代苏轼、欧阳修、陈亮等等。这些思想家的反抑商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治者的决策,而且与商业资本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共同对决策者发生了效力。所以,自唐中期到宋代以来,大多数王朝的统治者已不公开采取抑商政策。完全可以这样说,“重农抑商”思想如果在唐宋以前尚有一定市场的话,到宋明以后则渐渐地被人们所淡漠。尤其是张居正“利农资商”政策的推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层面上对农商关系作了总结,并成为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种由反抑商思想所引发出来的“重农而不抑商”或“重农而又恤商”的思想,已经通过统治者的经济政策贯穿于人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了。
注释:
① 应邵:《风俗通义·祀典》。
② 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思想首先由战国初年的著名政治家李悝提出,如刘嘉:《论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工商思想和政策》,载《中国经济思想史论》第139—14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首先由商鞅提出,本文采后说。
③ 《商君书·徕民》。
④ ⑤ ⑥ ⑧ 《商君书·垦令》。
⑦ ⑩ (11) 《商君书·外内》。
⑨ 《史记·李斯列传》。
(12) 《商君书·弱民》。
(13) 《韩非子·五蠹》。
(14) (20) (21) (62) (63) 《汉书·食货志》。
(15) (47) 参见李俊源、王相钦、庞蕴生主编:《中国商业史教程》,第63、237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16) (19) 《史记·平准书》。
(17) (66) (71) 《史记·货殖列传》。
(18)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22) (58) 《盐铁论·通有·本议·轻重》。
(23) (35) 《文献通考》卷14《征榷一》。
(24) 《汉书·哀帝纪》。
(25) 《昌言·损益》。
(26) 《太平御览》卷828《资产》引《晋令》。
(27) 《三国志·善和传》。
(28) 《旧唐书·曹确传》。
(29) 《旧唐书·高宗纪》。
(30) 《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
(31) 《旧唐书·中宗纪》。
(32) 《旧唐书·辛替否传》。
(33) 《资治通鉴》卷242。
(34) (59) (69) 《新唐书·食货志》。
(36) (37) (67) 《宋会要·食货》17之13,17之13,17之41。
(38) 童书诚:《中国商品经济史》第2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39) 陈珑:《四明学尧集》卷5《熙宁奏对日录》。
(40) 吴慧:《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十二讲》,第244页。
(41) 《元史·世祖纪》。
(42) 《元史·食货志》。
(43) 《马可·波罗游记》第111、176页。
(44) 《许鲁斋集》。
(45) (46) 《明史·食货志》。
(48) 《明隆庆实录》卷7。
(49) 这是州县对进入地方市场货物所征收的税,相当于宋代的住税。
(50) 《清朝文献通考》卷26《征榷》。
(51) 摊丁入亩法,康熙五十一年(1712)开始实行,规定以上一年的人丁数(2462万)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标准,把丁银335万两固定下来,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与原先赋税相比,这一措施有利于劳动人民。此法在康熙时试行,到雍正时进一步在全国推广。
(52) 王守:《长芦盐法咏略》。
(53) 《清朝文献通考》卷33《市籴》。
(54) 《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55)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第634页。
(56) 《新唐书·刘晏传》。
(57) 《文献通考》卷20《市籴一》。
(60) 以上材料均参见殷宗法主编:《中国税收通史》第222—30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月版。
(61) 《通典》卷11。
(64) 《晋书·食货志》。
(65) 《旧唐书·武承嗣传》。
(68) 《宋史·食货·商税》。
(70) “反抑商思想”,这一概念是由复旦大学叶世昌先生首先提出来的。它区别于学术界对历史上此类观点的流行概括,也区别于将此类思想与近代重商主义混淆的说法,本文借用此说。
(72)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史记·书佚》。
(73)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标签:桑弘羊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盐铁专卖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工商论文; 商业论文; 法家论文; 西汉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