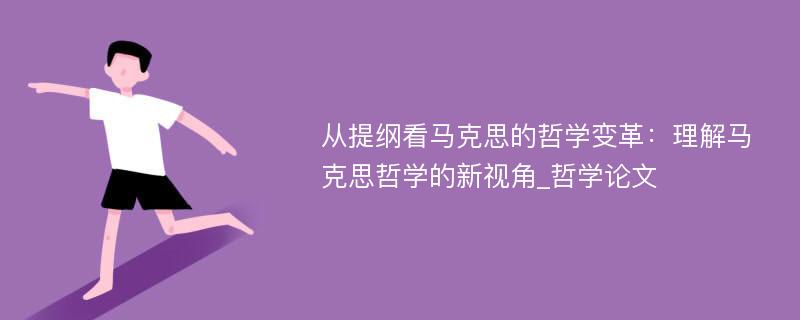
从《提纲》看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提纲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5X(2012)05-0069-04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其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认识马克思的任何思想的前提。从根本上说,哲学变革是哲学观的变革,哲学转向是哲学观的转向,哲学冲突是哲学观的冲突。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正本清源式的探究。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和直接地论述过自己的哲学观,因此,我们只能从其浩瀚的思想宝库中发掘并建构它。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一文是我们研究马克思哲学变革和马克思哲学观最为珍贵、最为集中的思想资料。本文正是以“提纲”为文本依据,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进行深入探讨,也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一种全新解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索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两种解释路径,一种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主题的转换”,另一种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在于“哲学方式的转换”。与之相应,其实形成了三种关于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不同理解:第一种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归结为哲学的主题的根本改变,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1]或者“把关于‘世界何以可能’和‘自由何以可能’的理性思辨,革命地变革为关于‘解放何以可能’的实践哲学”[2];第二种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归结为哲学方式的转换,即从“思辨的形而上学”转换为“实践”[3];第三种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归结为既是哲学主题的转换——即“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也是哲学方式的转换——即从“思辨形而上学”转换为“实践”[4]。其实,这两种转换所要表征的都是近30年来学界用以标志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践转向”。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或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理解这个问题,离不开两个基点:一是哲学发展史这个历史基点。离开这个基点,怎么可能得出马克思哲学的“变”和“革”呢?二是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这个文献基点。离开这个基点,我们谈的还是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吗?因此,离开这两个基点,关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任何讨论都将是纯粹形而上学思辨式的呓语,对探讨和解决问题都将无济于事。
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这两个基点是统一的——马克思本人在其“提纲”中正是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阐述自己对哲学的独特体认的。在他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马克思在这里其实总结了哲学史上三种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一是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一是从主体的、能动的形式去理解;一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与此相应,我们还可以得出对对象或现实,以及人的三种不同理解。
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前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别是机械唯物主义,统称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旧唯物主义的理解形式。这种形式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既成的”、“给定的”东西。在这里,主体对对象或现实只是被动地接受、反映,而没有从“主观方面”、“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把握。这是对对象或现实的一种“纯物质的”理解和把握,一种抽象的理解和把握。这里的“现实”不是真正的现实,而是一种无现实的人存在和活动于其中的现实,因此,只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这里的“人”只是作为对象或现实的对立物而存在,没有主观性、没有能动性、不是从事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人,而只是一种“纯物质的”人——一种片面的、抽象的人。这种理解形式要么坚持客体至上原则,完全敌视人,要么坚持自然至上原则,关注的只是抽象的人[4]。它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
从主体的、能动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唯心主义的理解形式。这种形式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精神、理念或自我意识,完全否认客体性或直观性。在这里,只是片面地发展了主观的方面或能动的方面,将主观的、能动的方面和客体的、直观的方面割裂开来。这种理解是对对象或现实的一种“纯主观的”理解和把握,同样是一种抽象的理解和把握。这里的“现实”也不是真正的现实,也是一种无现实的人存在和活动于其中的现实,当然也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这里的“人”只有主观性、能动性,只是从事精神活动而不知道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人,是一种“纯主观的”人——同样是一种片面的人、抽象的人。这种理解形式要么坚持观念至上原则,追求绝对化的理念或自在之物,要么坚持自我至上原则,追求个体的自我意识[4]。它同样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
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是新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形式。马克思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感性的人——现实的个人——实际从事的活动建立的东西。在他看来:“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6]这里,对象或现实其实被看作是现实的个人——感性的人——在实际从事的活动中创造、构建、占用并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结果。这种理解既体现了主观的方面——能动的方面,又体现了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超现实的人及其实际从事的活动的客观根据。离开了现实的个人实际从事的活动——感性的人的活动——,无论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体的、能动的形式去理解,都只有抽象的、虚构的对象或现实。这里的“人”是实际从事活动建立对象或现实的——感性的——、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有着具体和丰富的生命特征的现实的个人——感性的人。这种理解形式坚持“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至上原则,是在关系中、过程中、活动中理解和把握人及其对象或现实的。它真正关怀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
关注现实、批判现实、反思现实其实是一切形态的哲学所共有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才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是由于不同形态的哲学关注、批判、反思现实的形式不同,从而导致其所关注、批判、反思的现实也不同。诚如前文所述,一切旧唯物主义由于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关注、批判、反思现实,因此只能把现实理解为“既成的”、“给定的”东西,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只是一种“纯物质的”——抽象的、虚构的现实。一切唯心主义由于只是从主体的、能动的形式关注、批判、反思现实,因此只能把现实理解为精神、理念或自我意识,同样排斥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只是一种“纯主观的”现实,也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现实。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于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关注、批判、反思现实,因此把现实理解为由感性的人——现实的个人——实际从事的活动建立的东西,承认并关怀现实的人或人的现实,所关注、批判和反思的现实才是真实的现实。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旨归在于他对“现实”的理解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形式去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并把对象或现实理解为由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建立的东西。这正是马克思哲学观变革之所在——一种新哲学观的确立。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区分三种理解对象或现实的形式,以及对对象或现实和人的三种不同理解上。在《提纲》中,他在其哲学观变革的基础上,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视角,对一系列问题做了重新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活动”的理解进行了分析、批判。费尔巴哈由于不能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批判、变革对象或现实的活动——甚至将这种活动贬低为“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不能在批判、变革活动——“对象性的活动”——中把握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企图确立的感性客体其实并不具有可感性,只是理论活动的纯物质对象或现实——既成的、给定的对象或现实。感性的人的活动的“革命性”、“批判性”在他那里被消解了,理论活动成为脱离实际对象或现实的纯粹理论活动。
其次,马克思探讨了“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5]问题。思维的真理性,即思维的现实性或现实力量,也叫思维的此岸性,在思维中不能得到证明,只有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才能得以确证。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此岸性是一个永远不能得到确证的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再次,马克思讨论了“环境和教育的改变作用”问题。马克思批判了环境和教育改变人的纯客观或纯直观的唯物主义学说,认为这种学说的必然后果就是“一部分人凌驾于社会之上”。殊不知环境也只有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才成为环境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也都是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才成为自身的,离开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环境和教育本身都无法理解。环境和现实的个人的改变都是在感性的人变革对象或现实的活动或实践中发生的,三者是一致的。
第四,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还原为世俗世界的同时,认为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革命性、批判性意义,因此,不能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中寻求通过消灭世俗家庭——消灭资本关系——来从理论上批判和实践中消灭神圣家族的途径。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对“宗教上的自我异化”的分析上,再无法前进一步,根本不懂得如何通过消灭这种自我异化来实现感性的人的本质和自由发展。
第五,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把抽象的思维归结于感性的直观的同时,认为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并不是具有此在性和可感性的感性,这种“感性”依然是抽象的。而真正的感性则只能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来理解和把握,只能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建立的东西,或只能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本身。二者是一致的。
第六,马克思在肯定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5]的同时,认为费尔巴哈由于不懂得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历史性,只能把宗教情感作为独立的东西来把握,为了说明这种独立的宗教情感的本质,只能思辨地“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存在,并只能把这种抽象的个体的人的本质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理解为“类”本质——“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因此,费尔巴哈所批判的是人的抽象的类本质,而不是人的现实本质。人的现实本质只能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历史地去理解,它是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感性的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或实践,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他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决定着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又决定着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即他的现实本质;而且这种现实本质还是在感性的人的历史活动或实践中动态地形成的本质。因此,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本质应该归结于批判感性的人的现实本质。
第七,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理解宗教的本质,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宗教情感的真正来源。正是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感性的人才把世界区分为对象世界和自我世界,宗教情感正是在对象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感性的人的情感在自我世界中的自慰式的实现。因此,理解宗教情感要从理解感性的人的情感入手,理解宗教的本质要从理解感性的人的现实本质入手,批判宗教的本质要从批判感性的人的现实本质入手,而这一切只能从感性的人的活动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中得到说明。
第八,马克思在批判宗教的本质的基础上,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样态决定着社会关系的样态,进而决定着社会生活的样态。理论活动的神秘性也只有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得到破解和合理的解决。
第九,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或直观的唯物主义只能把个人和市民社会看作是“既成的”、“给定的”对象,“至多也只能”确立个人和市民社会相对于思维的先在性,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不能把感性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因而不能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理解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的社会。
第十,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它的立脚点只能是由许多单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由于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出发,它的立脚点则是现实的个人——感性的人——在其活动或实践中通过发生一定的、普遍的、稳定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最后,马克思在具体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哲学观与一切哲学家们哲学观的差异:哲学家们或不知道感性的人的活动或不懂得感性的人的活动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对待世界只能停留在不同方式的解释上;而马克思不仅在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中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改变世界。因此,哲学家们的世界对他们而言只是“既成的”、“给定的”对象世界,马克思的世界对他而言则是不断生成中的变化着的对象性世界。
总之,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实践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或确立新哲学观的真正基础或“抓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实现了对生活世界的透析,为人类思想史和实践史谱写了划时代的篇章。
注释:
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