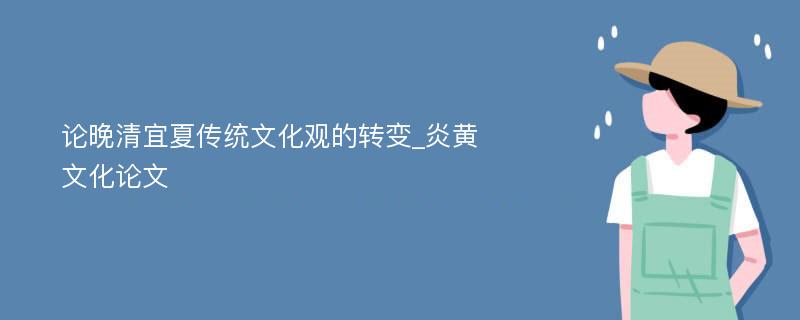
试论传统夷夏文化观在晚清的蜕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试论论文,传统论文,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考察传统夷夏文化观在晚清蜕变的历史轨迹,从一个方面揭示中华民族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心路历程。
一、传统夷夏文化观在19世纪40至90年代的消退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晚清中西文化冲突,与以前历次文化冲突均有所不同,它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其一,此次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的外来文化,已经不再是历史上重复出现,而是在时代性上要大大高于自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其二,此次文化冲突并不像以往那样,是在一个较为平和的条件下进行,而是伴随着西方列强武装侵略中国、企图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刻背景下进行的,这使得西方文化能够借助于资本主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而充分发挥其巨大的冲击力量。应该说,对这场文化冲突所具有的残酷性、持久性,都是当时中国人无法预料到的,也正因为无法预料,才使得此次冲击给予国人思想上以极大的震撼,促使人们从被动变主动,实现思想观念的逐步更新。
概括起来看,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传统夷夏文化观在新的文化观念的不断冲击之下,总的趋势是处于消退之中,走向解体而未解体。这可以分三个方面看:
第一,华夏地理中心论被新的世界地理观所打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首先冲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教条束缚,掀起一股“悉夷”“知夷”、编纂舆地著作之热,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探索世界地理高潮更是持续不断,一大批有关著作相继出版,有华衡芳与玛高温合译的《地学浅释》、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以及此时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和其它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相关地理书籍等。
这些地理著作对国人的启蒙作用主要在于:首先,地圆说、地动说、日心说的输入与传播,帮助国人破除了“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等陈腐的天文地理观,树立了进步的宇宙观念。魏源在其书中介绍了日心说,徐继畬则介绍了地球的形状,李善兰更为全面地介绍说:“西士言天者曰:恒星与日不动,地与五星俱绕日而行,故一岁者,地球绕日一周也,一昼夜者,地球自转一周也……歌白尼(今译哥白尼)求其故,则知地球与五星皆绕日……刻白尔(今译刻卜勒)求其故,则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奈端(今译牛顿)求其故,则以为皆重学之理也……由是定论如山,不可移也。”(注:李善兰《谈天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7。)上述这些新的天文地理概念的输入,无疑大大改变了人们思想中存在的传统观念。随着旧的地理观的动摇,新的进步的宇宙观念的形成,为文化观念的彻底更新提供了前提。其次,先进地理知识的输入,使人们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诸国之一,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国力上都不是世界中心,中国居于天下地理中心之传统观念彻底动摇了。再次,新的国家观念的初步确立。美国学者勒文森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注:勒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1卷第100页,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他的分析是颇具见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人的视野逐渐开阔,提出了一种蕴含着地理与政治双重意义的新的“天下”观。如薛福成认为,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再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到了今天,又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注:《薛福成选集》,第5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鸿章、王韬、郑观应、郭嵩焘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应该说,这种“华洋并列”、“中外联属”的新“天下”观与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即天下”的“天下”观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它已经初步具有了以近代进步的世界地理观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观念。人们已经意识到,天下已经不再是中国“大一统”的天下,中国已被迫融入世界大潮之中,只能作为万国之一而与列强竞争。
第二,华夏统治中心论被打破。传统夷夏文化观,把民族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文明与野蛮、高贵与卑贱的关系,而缺乏视天下各民族为人格平等民族的理性认识。清王朝在康乾时代,通过所谓的“十全武功”,建立了符合传统夷夏观念的所谓天朝朝贡体制与天朝统治秩序。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清王朝君臣极力地维护这种等级秩序,所谓“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启边衅”,在一些有关“天朝尊严”的中外交涉中(如谈判地点、礼节、使节问题等),严格固守定制。但这种“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中国中心”统治论,毕竟是过去封建时代所形成的落后意识,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武力压迫之下,它被无情地粉碎了。首先,从1840至1895年这几十年间,过去的藩属国琉球、越南、缅甸、哲孟雄、朝鲜先后被资本主义列强所蚕食、鲸吞,所谓的天朝朝贡国体系解体。其次,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武力压迫下,清王朝被迫在礼节、使节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有关条约中规定,以后清王朝与各国外交官之间“往来俱用平行礼”,这在当时士林中还引起强烈地反响,有人这样说:“《春秋》之所最重者,冠履之分;所最谨者,华夷之辨……今督抚之尊不止古大国诸侯,竟与犬羊之逆用平行礼,此断断不可者又其一也。”(注:沈衍庆《上大府请拒英夷和议书》,《槐卿遗稿》,第78页,台北文海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被迫在中英、中美条约中写下“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注:《中外旧章约汇编》第一册,第102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嗣后中国大臣与合众国大臣公文往来,应照平行之礼”(注:《中外旧章约汇编》第一册,第102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等,西方列强提出的使节驻京、外国使节觐见清朝皇帝用鞠躬之礼的要求也被同意。上述规定虽然是炮口下产生的苦果,是不平等的制造者要求的“平等”,但是它毕竟曲折地反映了“落后必然为先进所代替”这一条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随着认识的进步,旧的天下观念的破除与新的国家观念之初步确立,人们不再把西洋看作是中国的传统属国,而以一种切乎实际的、平等的、开放的态度看待民族之间的关系。
第三,先进之士对华夏文明中心论的批评和突破。传统的夷夏文化观从“中国中心”论的立场上出发,否认其它民族文化的价值,更不承认有向他民族学习的必要。但这一颟頇自大的心理随着鸦片战争的发生而有了改变。在鸦片战争中,一个拥有五千年泱泱文明的大国却被一个向来被中国人视为“夷狄”的英国所打败,这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痛心和反思,诚如冯桂芬所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林则徐、魏源等人痛定思痛,开始积极地、主动地认识西洋文化的冲击并寻求应变之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又一次惨败,促使国人文化意识进一步觉醒,人们的视野进一步开阔,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西方文化之进步性。如冯桂芬就勇于坦承中国之“不如夷”:“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左宗棠认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27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692页,台北文海版。)。薛福成也说:“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自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注:《庸庵全集·文编》卷2。)他们纷纷批判守旧派此时仍然在坚持的“夷夏之辨”。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有许多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上的落后与现实中对外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沉沦,问题的关键已不是中国看不起西洋而是西洋看不起中国。郭嵩焘指出:“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华人也,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注:《郭嵩焘日记》(三),第43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何启、胡礼垣也说:“其待华人也,有以畜类待之,而不以人类待之者矣。其视华人也,有以鬼物视之,而不以人物视之者矣。”(注: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新政真诠》初编。)上述结论对固守夷卑夏尊观念的人们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具有振聋发馈的作用。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倡导学习西学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中本西末”、“中道西器”、“中体西用”等一类主张,要求用“西学”来补救“中学”,实现中国文化的调整与更新。自冯桂芬首先揭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这种以西卫中、以西补中的文化运思方式就得到时人的赞同和效仿,如王韬主张“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强调“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认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无疑是对华夏文明中心论的一种否定。过去被视为毫无价值可言的夷狄文化得到了公开的肯定,这在传统文化发展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尽管他们只是把西学放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但毕竟说明人们已放弃妄自尊大的虚骄心理,公开承认外来文化的长处,由此可见时人对华夏文明中心论的部分突破。
二、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对传统夷夏文化观的扬弃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基于西方先进观念的输入与国人对中国屡屡落后挨打之现实的深刻反思,传统夷夏文化观的两大基础——华夏地理中心主义与华夏统治中心主义已经动摇,另一基础——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也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不过,传统文化有一个极其突出特点,就是儒家伦理观对各种思想的深刻渗透。儒家把中国社会看作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又把周围世界看成是伦理教化的世界,所以伦理价值观也一直是传统夷夏文化观的重要依托,是凝聚民族力量和规范民族行为的基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已经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深深扎根于华夏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这就使得所谓道德优越、文化优越的意识在中国人心目中特别强烈,面临新的观念的冲击,它依旧会不时地改换形式显示其顽强的力量。洋务运动时期,以倭仁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强烈反对“师夷长技”,其理由就是“立国之本,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某些顽固派还错误地认为随着海禁大开,中国之“圣教”必将盛行泰西:“盖尧舜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系以不蔽者也……今此通商诸国,天假其智慧并火轮舟车以速其至,此圣教将行于泰西之大机括也。”(注:李元度《复友人论异教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无须多言,顽固派的文化优越感是多么强烈而未曾动摇过。不仅如此,当时即使是力主“师夷长技”的洋务派知识分子,亦多少存在着一种文化自大意识,此时普遍主张的“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说,就是这一意识的有力表现。进入90年代后,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仍然有相当的张力,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依然以“中国文明甲于天下”而自鸣得意,如他们说:“合五洲之大势而论,人类至众者莫如中国,良以地居北温带之内,气候中和,得天独厚,而开辟又在万国以前,是文明甲于天下。”(注:《非幼学通议》,《翼教丛编》卷4。)而名噪一时的洋务派后期领袖张之洞,也强调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规范“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注:张之洞《劝学篇》之《同心》、《明纲》。)。同样是一副华夏文明优于外国的自大心态。
与此相反,19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与进化论的传播,传统夷夏文化观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新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那里,已经被突破,或者说实现了转化。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先进之士民族意识的觉悟,“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声喊大地”(注: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1号。)。严复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之导言及本论,改名《天演论》翻译出版,首次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至国内,“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注:严复《天演论》译序。);康有为在此时也极具独创性地提出“公洋三世”进化论,强调从“据乱世”(君主专制)到“升平世”(君主立宪)再到“太平世”(民主共和),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普遍规律。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与进化论的推动之下,维新派的民族文化意识大大提高,这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人类公理的角度出发,打破对儒家三纲五常的迷信。谭嗣同以近代的平等观批判儒家的纲常礼教,认为“五伦”之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四伦都讲尊卑,应该否定,只有“朋友”一伦“最无弊而最有益”。严复则运用进化论、民权说为武器,强调国为民有,君仆臣主,主权在民的思想。其二,突破“中体西用”的局限,强调中西学的会通。梁启超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想,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这种中西学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放弃以往的“体用”、“体末”之类的二分法,而强调“通”。其三,把文化改造与政治救亡密切联系起来,认为振兴民族文化与改良政体密不可分。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此时发起成立了“保国会”等政治性组织,倡导“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等。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维新派是以比较平等的态度看待中西文化关系的,他们已经基本脱离了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
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批判与超越传统夷夏文化观的同时,其文化心态又表现为两种发展趋向:其一,从自大走向自卑,推崇西方文明。甲午战后,国人受战争的刺激,逐步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倾慕西学,如梁启超所述:“数月以来,天下移风,千万之士人……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注:《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一部分维新派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将中国落后之因归结为文化的落后,如严复认为,西方“无法”“有法”均胜过中国:“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其民长大鸷悍既胜我也,而德慧术知较而论之,又为吾民所必不及。”(注:《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11页。)其推崇西方文化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甚至有人主张“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注:樊锥《开诚篇》,《湘报》第3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这恐怕就不只是推崇,而已经具有欧化主义的味道了。其二,以文化民族主义来振兴民族文化,抵制西方文化侵略。康有为、梁启超在倡导“保国”、“保种”的同时,也提出“保教”的主张,认为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大肆扩张,已经威胁到了儒学的生存地位和国人对固有文化的认同,主张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来改造孔教,抵御西方的宗教侵略。这种政治与文化合一,以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超越了此前封建顽固派狭隘的文化排外主义,也克服了洋务派知识分子忠君与救国的矛盾,把晚清中国人民反对西方侵略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华夏中心主义的终结,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传统夷夏文化观的历史也可以就此划上一个句号了。
三、结论
通观夷夏文化观在晚清60年由盛到衰、最终趋于消退的历史轨迹,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1.社会经济的变迁,是传统夷夏文化观最终走向消退的根本原因。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儒家伦理观念在近代的变迁历史时,曾精辟地指出:“夫纲纪本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说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诗集》,第10~1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不仅如此,实则包括夷夏文化观在内的许多传统思想在近代的命运都是这样。从本质上看,夷夏文化观作为古代中国人处理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典型思想,它是与当时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自足性,铸就了整个民族经济的封闭性、自足性。整个民族的商业交换活动不发达,不存在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标志的全国统一市场,更没有向外的经济扩张与利益追逐要求。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各民族之间是不存在通商、贸易关系的,有的只是朝贡与羁縻的关系。在晚清,这种落后意识在统治者身上还表现得相当突出,清政府屡屡拒绝与西方列强进行通商贸易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天朝物产丰盈,原不藉外夷互通有无”。但是,晚清中国的现实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打破民族之间的堡垒进行全球性的扩张,中国已不能自外于世界。鸦片战争已经把中国牢牢地纳入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封建统治者要想维持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已不可能。中国要想摆脱窘境,唯有抛弃固有的民族偏见,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开始“师夷长技”,引进了西方的经济技术,夷夏文化观的坚冰已被部分打破;维新时期,国人又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样板,引进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君主立宪制度),夷夏文化观归于消退就是必然了。
2.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是推动晚清国人文化观念更新的巨大力量。在晚清,国人所体悟的最大变化,无疑就是中国民族生存环境—天天恶化、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如何尽快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国,成为一代代先进之士奋斗不息的目标。西方列强的侵略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固然使中国危亡日益加深,但另一方面也促使国人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从林则徐到康有为,先进的中国人就是从战争失败的痛苦中进行反思,从传统文化的内部自省,到世界文化的横向参照,从对夷夏观的初步怀疑,到对其最终的摈弃乃至超越。在这一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认识过程中,救亡图存的意识无疑是推动国人文化观念变迁的强大动力。
3.民族主义,是晚清国人在摈弃夷夏文化观后的理性选择。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基础之上所表现出来的要求全民族政治与文化统一的一种观念和行为,它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和忠诚于“民族国家”。实事求是地说,古代中国人并不缺乏共同文化的认同,以华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夷夏文化观,突出强调儒家思想的价值,使儒家思想在古代实际上扮演着维系国人认同的角色。但是,传统夷夏文化观将民族意识与忠君意识、伦理道德观念杂糅在一起,把维护皇权体制与儒家伦理观念不被澌灭作为民族的最高追求。将文化生存置于民族生存之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人对整个民族政治命运缺乏自省。进入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意识匮乏,从而无法以坚强而有效的共同政治认同去凝结国人。面对外来威胁,国人唯一的防线,就是依靠文化上的优越感,来超越外来文明,用“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撸”这种倭仁式的文化排外主义政策作为抵御外来侵略的武器,其效用肯定是软弱无力的。19世纪90年代,随着进化论的传播,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摆脱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他们提出“合群保种”,以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共和国作为民族救亡的根本手段,同时改革传统经学,以西方基督教的模式改造孔教,来抵御西方的宗教扩张。这种政治与文化合一的民族主义,是晚清国人的一个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