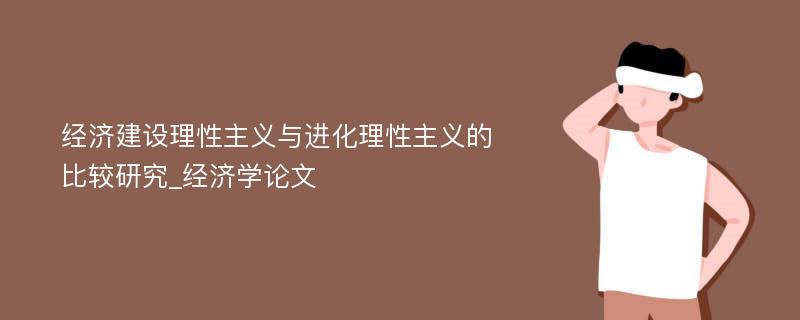
经济学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4-0055-05
有关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的讨论更多地限于社会学、法理学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但在经济学中却很少有专门的文献讨论进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问题。一直以来,在经济学研究中并不缺乏有关理性的讨论,但这种讨论更多地集中于经济行为个体的“理性”或者“有限理性”或者“非理性”进行,这种争论的结果是深化了对我们对理性的认识,而理性的内涵也逐渐丰富起来。但本文认为,仅限于考察微观经济个体行为的理性问题,尽管必要,但还显不足;而从人类整体层面的经济行为角度以及制度形成角度考察理性问题,可能对人类的自由和发展更有实际价值(意义),但这需要对经济建构理性主义和经济进化理性主义展开专门性的研究工作。
一、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
在哈耶克看来,曼德维尔(1705)提出的标准化社会经济科学模型(SSSM)是典型的一种建构理性主义(建构主义),这种观点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并对19世纪的李嘉图、边沁和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家形成重要影响。(注:根据哈耶克的理解,这种建构理性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而历史的考察功利主义不难发现,功利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用主义者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以及边沁主义者边沁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上,而这些古典经济大师却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变迁。)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基于这种建构主义的SSSM,经济建构理性主义学者最终推导出微观主体决策的理性预期模型和宏观经济政府的调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经济学的整个基石。
近年来兴起的实验经济学(注:这里的实验经济学是指运用实验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它通过在可控制实验环境下对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的分析和考察,以此来检验和完善传统的经济理论,并为政策决策提供相应的指导依据。实验经济学大师弗农·史密斯也为此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获得者是行为经济学加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结果倾向于在非个人的市场交易机制中证实建构理性主义,但在个人交易市场机制,尤其是两主体参与的扩展形式的博弈中,即当存在风险合作时,至少存在部分被试通过个体努力能够频繁获益的博弈中,建构理性主义能否得到证明还很模糊。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2003)认为,这种实验结论可以推动两方面研究的深入:(1)对博弈理论的建构性扩展,即主体的行为不仅要参考博弈的相互性问题,还须考虑到主体各自的价值判断和不同偏好。(2)对学习机制认识的深化,即SSSM模型的可预测性可以通过持续的试错适应过程来达到。
针对经济建构理性主义思想和实验经济学实验结论之间的矛盾,存在一种比较合理的替代性解释:对于重复博弈的社会交易主体来讲,信任、互惠和公平(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的社会化扩展要优于个体理性的深化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而信任、互惠和公平的社会化往往会导致交易主体之间的竞争优化为合作或共谋。实验经济学有关市场机制的实验中,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即如果实验参与者被置身于更逼近于现实市场的实验环境中,在所谓的双重叫价拍卖机制随机地分为买卖双方,并同时叫价(包括要约、递价以及进一步讨价还价)时,通过交易主体个体选择行为的交互性,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合作常常会发生。这种实验结果也与最大化团体福利的标准价格竞争模型相一致。
但一般来讲,经济建构主义理性具有关键的几个预设假定。第一,经济建构理性主义假设被实验的每个市场交易者都具有关于交易支付、获益以及其他交易者的所有相关信息,而且,信息是完全对称的。第二,经济建构理性主义“要求”每个市场交易者对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带来的结果具有超强的经济计算能力,而不会由于各种生理或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产生各种认知偏差,并进一步导致决策判断上的失误。第三,经济建构理性主义的实施尚须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变迁或者突变。比如对于那些突发性安排,即使原始的建构理性主义能够得以深化,相关机会成本和经济结构的挑战也需要考虑。
哈耶克(1967)提醒我们说,人类关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理论和思考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应用到了有意识的、刻意性的理智,但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过程中仍充斥和迷漫着下意识、本能和机械化的神经冲动,而它们却阻碍着人们充分有效地利用大脑的最稀缺资源——注意力和推理力。下意识、本能和机械化的神经冲动发生于大脑的生理运作也遵从经济化原理,没有一个人的大脑能够承受在自我意识的持续控制和谨慎计划下事无巨细地计算分析每天所有的问题,并予以强烈的关注。另外,脱离了语言工具的支持,就没有人能够完整正确地表述自己的观点、方法和决策,但语言本身是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的。这就正如一个购物者到超市购物,如果他完全依据建构主义理性的话,他将不得不对成千上万的商品进行仔细的观察和评估,并将之与自己的偏好和预算进行详细的对照和计算,那么这种经济行为付出的机会成本将非常高昂,所花费的时间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此刻,此人的大脑也会因此严重地耗损甚至崩溃。
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发现证明,在遇到不熟悉或者突发性事件时,人的大脑将首先求诸于有关决策背景,而这种背景将激发人体与之相关经历的大脑记忆,这些记忆会诱致大脑对不熟悉或突发性事件产生直觉式、启发性的认知以及构架式、经验性的判断。这个思维过程中,大脑已经自然脱离了个体有意识的、精确性的思维控制,而更多地求诸于下意识甚至无意识的经验和直觉。现代心理学和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甚至人们对直觉和经验的获取也并不是通过刻意的、专门的记忆或者学习达到的。比如就语言而言,我们的对发音、单词、语法以及句法的掌握,并不需要特殊的、直接的培养和教育,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暴露于家庭的交流和社会的交互过程中,连续地置身于语言对话的氛围中,大脑会“脱机式”地、自发地掌握语言的关键并予以运用,而不断的语言运用又会不断强化我们对语言的学习程度。
二、经济学中的进化理性主义
与建构理性主义截然相反,进化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于文化和生物的不断进化,无论人们的行动原则、标准、传统还是道德规范的形成,都遵从自然的、内生的进化过程。进化理性主义者利用理智——理性的解构——重构方法来审视更多基于经验和常识而为的个体行为。他们分析认为,利用建构理性主义工具来指导决策、来理解人类文化的发生过程、来发掘那些产生于人们的交互性而不是某些人刻意设计的文化和生物遗产中的规则、标准和制度里镶嵌着的、可能的智慧,都具有极大的约束性,甚至幼稚性。对于各种社会规则、标准和制度,即使人们能够发现和理解它们,但人们总是倾向于不自然地、无意识地遵循。这就是进化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真实的理性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
18世纪的进化理性主义先驱西蒙和休谟首先对人类理智的有限性、人类理解力的有效边界以及笛卡尔式的建构主义理性夸张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指正。休谟认为,理性仅仅是一种对自然发生着的制度的理智认识现象,而不是理智的结果,如道德规则。亚当·斯密(1776)在经济学中首先提倡了进化理性主义观点,他认为经济秩序仅可见于嵌套于现有的经济规则和经济习俗中的智慧形式中,而这些经济规则和经济习俗自然地发源于以前人们的社会经济交往和优化选择行为,也就是一种交易形式的优化劣汰过程。亚当·斯密的这种进化理性主义观点与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观点相左,后者认为如果某种观察到的社会机制可以发生作用,那么这种机制一定是前人基于特定的目的予以有意识的理性设计而成。
进化理性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尤以演化经济学为标志。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立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基础,运用生物学模拟方法,分析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与进化,以论证市场经济的可改良型。其中心论点是:社会经济中的规则制度非人为设计,它本质上是一个自发的动态进化与演进体系。而制度变迁或制度演进模式的差异主要是由惯例、文化传统、选择环境、历史初期条件等一系列自发性因素所决定。演进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包括纳尔逊、温特等人,但坚持进化理性主义的经济学家还包括就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创人凡勃仑、经济自由主义领袖哈耶克、现代比较制度学派的代表青木昌彦等人。(注:出于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定义和认识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家都认同或遵从进化理性主义。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宪政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转轨经济学相关代表人物对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尽相同。)
近年来,实验经济学中关于持续双重拍卖(CDA)市场机制的无数实验有效地证明了进化理性主义的合理性。在有关拍卖理论的经济实验里,实验参与者们最终的选择总是倾向于违背个体自我的起始意愿——自私心理和机会主义理念,而逐步适应性地走向合作利用那些能够提升团体福利的经济交易形式。而且,这一实验结果并不随着实验环境和交易机制的改变而变化,即无论是封闭的出价机制(sealed bid)、公开的报价机制(posted offer),还是在其他类型的持续双重拍卖机制,都可以凸现实验参与者的进化理性主义。这一分析结果,已经超越经典博弈理论基于预期效用模型对博弈主体行为的有限解释,因为即使考虑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个体决策者的自发性思维计算也不得不协调地遵从相关的制度安排——社会化计算和交互性考虑,以获取更高的交易性收益。
深入探究和认识潜在的真实的大脑的运行过程,对于强化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很有裨益,也有利于我们摆脱建构理性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固有的局限性。这方面,经济学家西蒙(1976)基于经济行为人自身信息的非完全性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较早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定。他认为个体决策者只有有限理性,只能进行次优选择——追求较满意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希勒和姆里纳赛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则基于现代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启示,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他们认为,人的情绪、性格和感觉等主观心理因素会对行为人的决策构成显著的影响效应,而经典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理论、贝叶斯学习和理性预期是无法对个体行为人的真实决策过程进行有效描述的。这点,正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1986)所言:“由于大量的心理实验分析结论和理性公理中的一致性、次序性和传递性原则相违背,而且这种违背带有系统性、显著性和根本性,因此,客观上需要新的经济理论对行为人的决策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和更稳固的支持。”(注:基于西方心理学对现代经济学渗透力度的强化,出现相关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性学科是不足为奇的。)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济个体的有限理性行为还会基于一定的心理感染和信息传染机制,导致经济群体的认知出现系统性偏差,并进一步引起“羊群行为”甚至集体无意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建构理性主义将受到根本性挑战,甚至对经济进化理性主义也构成潜在性威胁。
三、两种理论体系的比较及其意义
总体来讲,遵循建构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不对经济主体(包括家庭、厂商和政府)的理性进行限制,认为通过经济主体的理性计算,可以获得关于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建构社会经济制度所需的全部信息,因而社会经济制度是设计的产物。而进化理性主义则明确指出理性的限度,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主体之间存在互动,即秩序形成过程是非确定性的,是经济主体的理性所不及的。社会经济秩序是各种经济主体参与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专门的经济主体,如政府设计的结果。
经济建构理性主义不注重经济个体的差异,并把复杂分解为简单。这一点正如迈因策尔(1999)所言,“人的行为如同遵从一定运动数学定律的机械系统中的元素一样,是规则的,可预见的。如果起始条件和环境都是已知的、可测量的,那么就可以确信,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个体行为就如同气体中的分子那样,其行为是确定论。”在这样的假定下,无差异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的、相互分离的经济行为,并不存在由于他们之间多维的、非线性的互动而影响和改变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米塞斯(2001)认为,新古典理论对于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的分析和讨论,都以既定的制度规则为前提,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在新古典理论中是作为一个场所、一种机制而出现的。在市场这种既定的设置下,各种经济主体进行交易,其交易行为的选择与市场的演化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性,因此,经济学中的制度演进被分离,经济主体的行为也日以机械和呆板。
经济进化理性主义者则认为简单的、无差异的经济主体假定并不现实。实际交易中的经济主体有着不同的偏好、赋予不同的资源并有着不同的效用函数(经济最大化抑或其他效用最大化)。布坎南(1991)说,“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即没有目的、功能,也没有意图。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多元的经济主体实施差别化的、动态的经济行为,实际上已经参与到了经济系统从而经济秩序的选择中,而经济系统和经济秩序的选择和再选择,又会影响到并决定着经济主体的下一步经济行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发生和发展。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对经济主体与经济秩序之间的互动性作了进一步解释。符号互动理论强调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开放性、社会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将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中的个体行为沟通起来,将社会经济结构看作是许多个人理解与行动的结果,将社会经济过程视为是主观意义赋予客体并做出反应的过程,他力图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分析来理解人的行为,从而了解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个体,个体又如何作用于社会经济,以及这个相互决定的过程如何发生。坚持演化理性主义的符号互动论奠基人米德(1934)就认为社会不是“存在”的,而是随着互动中的人们的行动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是“发生”于互动中的个体之间的事件之流。
总体来讲,在文化和生物进化过程中,秩序形成的关键在于存在一种产生多元化制度、规则的机制和一种对这些多元化制度、规则予以适应性选择的机制。但建构理性主义的优势在于它仅仅可以促进多样化制度、规则的产生,而对于理解和应用多样化的制度规则并且予以优化选择,却能力有限。而这一点,恰恰是进化理性主义的比较优势。
遵从经济学中这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一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会导致我们对现实的经济实践产生不同的认识,这对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尤其显得有意义。经济转型前的中国无疑是遵循建构理性主义的,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计划主义配置、对社会财富的整体性持有以及对经济主体的普遍化控制都体现了建构主义理性(政府)对自我经济发展预测和社会制度设计能力的自信,而建构理性主义的政府也因此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中心决策主体。而基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至少在某种程度可以证明建构理性主义的不足和缺陷。不过,这种建构理性主义危害所诱发的政府起初被迫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仍然是由政府首先驱动和规划安排的,也就是说政府还是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尊崇建构理性主义。
但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建构理性主义在经济社会思维中的中心地位却开始渐进地让位于进化理性主义。这是因为“转型期”的社会经济行为具有“过渡性”特征。人们的行为模式还普遍缺乏“稳定性”,协调各种行为交互作用的许多制度不是尚在建立就是完全缺失。同时传统价值体系早已瓦解,新的价值体系却因文化转型的过于迅速而难以确立(汪丁丁,2003)。这种转型期经济行为主体特有的价值多元化趋势和交互不稳定性特点恰恰符合进化理性主义的条件,也就是说多元化的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态博弈本身就构成着社会和市场的逐步演化,而这种演化正在或者已经超越建构理性主义政府的预期视野和把握能力,政府的行为至少将被迫向市场看齐并因此得到规范(这一点,建构理性主义政府可能不愿意看到,甚至开始就没有想到)。比如仅从经济法的构建和完善来看,其实施已经不完全不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了,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各种经济主体博弈行为的分析将成为这种经济法律制度是否有效推行和发挥作用的关键。因为,从经济法的法理本身来讲,要想切实达到某项经济法规建构和实施的目标——有效规范平等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能否对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进化过程准确把握才是关键。对于这一点,建构理性主义立法者能力是有限的,而像进化理性主义者学习才是正途。
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过程极其复杂,对现实中国未来市场和政府间的交互效应问题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这是不争的事实。仅从这一点来讲,经济进化理性主义可能比经济建构主义理性更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