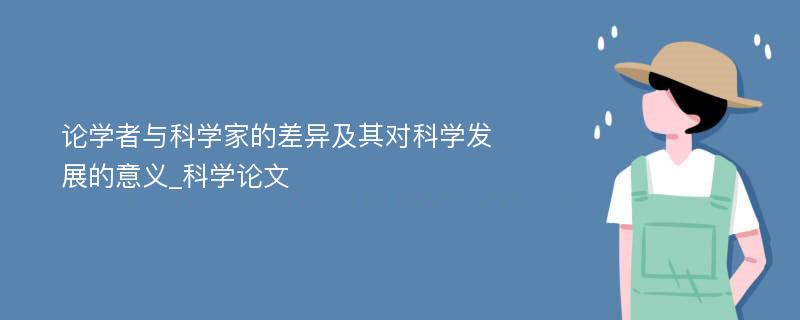
论学者与科学家的区别及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科学家论文,学者论文,区别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当前,无论在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确实存在着对“学者”与“科学家”概念含混不清的状况。廓清这一概念,区分两者的不同任务与研究方法,对高校规范不同人才标准,培养适应人才,具有现实意义。作者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其论证是否确切或完善?我们希冀有更深入的研究,并欢迎不同观点的辩争。
“学者”和“科学家”,都是表称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概念,对两者的本质含义及评价标准,理当有明确的界定。从知识社会学来看,这不单纯是称谓问题,而是一种人才规范标准的表征。其规范标准,既是社会评价人才的尺度,也是科技人才努力的目标。
我国对“学者”与“科学家”的涵义混淆不清,似乎有区别,又可等同;似乎“科学家”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但又大量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似乎两者都系高级科技人才,却又划分高低层次。《辞海》1979年修订版中,没有“科学家”词条,只有“学者”词条:“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小学生也算学者?做学问是否即科学研究?都不清楚。这些混乱,反映了我国科学观念的薄弱和模糊。考查“学者”与“科学家”的性质和任务是否不同,辨明学者与科学家的区别不是概念游戏,而是关注对科学发展的意义。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则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的问题。
一、学者与科学家的不同任务
人类的知识不断积累,需要汇集、整理并传授给新一代,于是产生了专门从事知识工作的人;新一代的成长也需要专门进行学习的时间。汉语用“学者”总称这两种人。后来为了把学生与学而有成者相区别,才以学者专指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英语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译为“学者”的Scholar一词,旧时即“学生”,后来指某一学科学而有成者、教授。显然,学者的本质含义是指掌握了特定门类的高深知识,从事知识的加工整理并有建树的人。
科学家称号是在“科学”这一特定概念产生之后的西方出现的。英语的Science(科学)一词,最初指自然科学,具有专门技术、精确、严格等意义。后来把一切符合这种要求的系统知识称为科学或学科,组成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或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从事这种科学工作的人称为科学家(Scientist)。科学家突出的特征有两点:一是生产知识的人,二是有解决问题的技术和能力的人。学者与科学家,两者的任务不同,社会作用不同:
学者的任务和具体作用归纳为三点:(1)汇集和整理已有的知识,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2)对已有知识中不明晰不可靠的部分,进行诠释、考证;(3)发现和提出知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或者预测知识体系的发展趋势,推动进一步的研究。三种作用中能有一种以上的才可称为学者。并不是一切能够照本宣科讲授一门课程或七抄八拼编出一本书的人,都可划到学者范围,也不应再分大小学者的层次。否则就没有高级科技人才的质的界线了。
科学家的具体作用也可归纳为三点:(1)解释过去不能解释的现象,生产新知识;(2)创立能够重视综合已有知识或者预测未来的理论;(3)把新知识转化成生产力,发明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或者应用新知识推进人的社会活动,解决社会操作的难题。三种作用中能起到一种以上作用者配称科学家。并不是一切能够应用已有的科学技术,制造出产品、设计出工程、控制金融和市场的人都可称科学家,而且又去分大小科学家,丧失质的界线。
学者是整理加工人类的已有知识;科学家解决人类的未知问题,生产新知识。这样的区分标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适用,可以克服只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科学家称谓的无理状况。
以任务和作用的不同指称学者与科学家,就可以使两者的区分不致成为宿命的或终生的。当学者发现已有知识体系的问题和缺陷,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弥补这些缺隙,从而生产出新知识的时候,学者就转变成科学家。科学家必须先学习,掌握已有知识,无疑曾经是学者;他解决某个未知问题,为人类知识宝库贡献了新知识而成为科学家。
在人类科学知识的生产、传续、发展的三个环节中,科学家担负着生产和发展科学知识的任务,学者负担着使科学知识提炼和传续的任务。问题在于,如果学者太多而科学家太少,科学必然不发达。尽管靠学者可以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也能实现现代化。但是,一个不能为人类科学宝库贡献新东西、把科学推向前进的国家,能称为科学发达吗?能真正站到先进前列吗?这是必须区分两者任务和作用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二、学者和科学家不同的研究方法
我国的学者传统极其强固,一整套缜密的“治学方法”经由各级学校的教师灌注于学子的心灵深处,常不自觉地走上学者之路。不重视吸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突出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就是自然科学本身,到了中国学者手中也畸变成大量的学者式研究。因此,辨明学者与科学家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进一步了解学者与科学家的区别。
1.学者的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论经数千年锤炼,已形成完整的体系。简要地说,动机目标方面已形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方法上包括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五方面;从思维上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剿说、毋雷同”等等。搞了几千年,似乎仍然没有老子孔子博大精深。原因在于千百年来的学者都局限于研究已有知识,衍义也好,发微也好,都在如来佛的掌心中。从学者型研究生到学者,研究过程大体一致: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写出心得。功夫在于对资料的分析,学者研究方法的核心是思辨方法。
由于人脑100多亿脑细胞可以进行无限的联结组合,思辨是一种简单易学而又优劣殊异的方法。只要掌握概念、判断、推理的基本逻辑规则,便可以十分规范地进行思考,得出见解。如果充分发挥联想,巧妙运用不同推理技巧,更可以产生独出心裁的高论。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准确性、严格性较低,一个稍微复杂的事物,100个学者可以产生100多种见解,见仁见智。例如老子的《道德经》不过5000字,古往今来无数学者注、释、考、辨、发挥、引申,研究论著累计达到5000万字也不是极限。在知识量剧增的近现代,学者们更是忙乎不完。某国科学家创造了一种新知识,即刻可以出现一人译介,十人评述,百人引用的景象。
学者研究大多运用两种思辨:一是最大限度地综合、概括、抽象。综合各家学说,概括各国的研究情况,找出趋势和规律。二是最大限度地演绎、引申、发挥。用哲学观点演绎推理是最常见的:多种矛盾、主要矛盾、矛盾主导方面、矛盾转化等,并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和描述耗散结构,大讲能量的输入输出及平衡态。学者的方法以高大全取胜,因此流传着“小人物专写大文章”的诀窍。
2.科学家的研究方法
科学家是面对未知问题,并要实实在在去解决的。比学者对已有知识的加工要困难得多。首先是没有现成的资料,已有知识顶多能提供某种借鉴,需要探索;其次是对解决问题的尝试要进行检验,严格测定效度,不能像学者那样通过思辨推理就能自圆其说的。
从科学家型的研究生到科学家,研究过程也大体一致:提出未知问题;尝试解决;检验并得出结论;新的未知问题。这个过程显示出科学家永远处于探索未知问题的过程中。一旦没有问题,科学家的使命也就完结,虽然他凭籍已有的知识仍然是学者。
科学家也要思辨,但与学者的思辨有显著不同。第一,分析和综合两种思维方法都要用,但主要靠分析研究事物,不断深入事物的内层。第二,归纳和演绎都要用,但主要靠归纳。
科学家对于思辨的结果,总要千方百计追求实证。这是方法上与学者最大的、最本质的不同。因为“科学”的含义就是准确、严格、可靠。它的身价不在于学者说它如何了不起,而在于用它去解决问题时真实地了不起。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必须具有这一品格。杨国枢等台湾学者撰写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一书给科学作出界定:“科学是以有系统的实证性研究所获得的有组织的知识”。并说:“只有从实证性研究获得的知识,才比从经验、神学、伦理学、哲学等其他途径获得的知识更正确可靠”。科学曾经纠正了人们对自然、对社会的许许多多来自经验及逻辑推理的错误结论。假如单纯依赖思辨,便可能依据旧观念中的错误结论继续往前推理而走得更远。因而纯思辨的产物不能算是科学。
科学家面对人类未知难题,不仅专攻一点,而且要把某个特定的因素隔离出来,控制条件,孤立的、静止的、定性的、定量的考查,然后才考查各因素间的联系。科学研究方法中,更为独特而有效的是打破常态进入事物深层。常态下的事物,靠观察和已有知识就可以说明。而事物深层的机理,不用极端的研究手段是无法得知的。例如对于水的认识,几千年都停留于常态和表面。只是在搞清了H[,2]O分子结构时,才开始真正了解它。重水D[,2]O的发现,又揭示了性质不同的另一种“水”。科学家们为了打破常态,刻意创造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密、超薄、超导、高真空、失重、核裂变、核聚变等各种极端的方法,从而揭露出物体深处的特性,获得崭新的知识。因此,英国科学家兼科学哲学家Holvey对科学作了更本质的解释:“科学就是设法走到事物的极端去,以发现经验所不能发现的东西。”就是说,科学不停留于常态、常识、常理。要深究事物,冲破已有知识的束缚,走向极端去研究是最有效的途径。
有人质疑:自然科学诚然如此,社会科学则不行。因为社会本身就是各种复杂因素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整体。中庸、协调、平衡乃古今政治家奉行的原则。所以,必须全面、辩证地研究社会。这种质疑,是把对现实社会的全面管理和对社会的科学研究混为一谈。罗马尼亚社会科学院院长基亚维斯库沉痛总结几十年的教训道:“我们总想把社会全面地说清楚,结果是全面地说不清楚。”事实上,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否定了质疑者的疑虑。马基雅维里关于政治权术的研究,卢梭关于社会契约的研究,圣西门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大卫·所罗的无政府主义对政府功能的研究,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研究,列宁斯大林关于国家和专政的研究等等,都同样是设法走到事物的极端去,才深刻揭示了社会某一方面深藏的、经验所不能认识的东西。今天的社会科学同样需要打破常态的极端研究才能发展。
三、区分学者与科学家对科学发展的意义
对学者与科学家不同任务作用、不同研究方法进行区别,旨在调整科学人才的结构比例,按不同方法和要求培养不同的科学人才,并采取不同的评价管理措施。
1.明确区分学者与科学家的不同任务,才能真正加强科学家式的研究工作
知识的生产和发展显然是“源”而传续仅是“流”,理当大力加强科学研究生产新知识。从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进步所需解决的问题来看,也理当大力扩充科学家的队伍去研究解决社会实践难题。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当学者,坐在书斋里研究加工知识,而只有极少数人在真正生产新知识,势必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是缓慢的。
明确界定什么叫科学研究又是十分必要的。国外严格的定义如下:“科学研究是把某一科学领域的前沿向前推进一步的工作”。据此,一项科研课题至少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指得出前沿在哪里?二是准备推进到哪一步?知道了前沿,但不清楚往什么方向推进,仅在前沿的内侧巡视一番,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也仅属于学者的工作,尚未真正进入研究。
现实中把学者汇集加工知识,乃至掌握知识的作业,也称为科学研究,导致极大的混乱:以现成且有定论的资料编本教材叫科研;翻译介绍某种国外理论叫科研;重复外国人的一项实验得到同样的数据(或稍有差异)也叫科研,引进一项新技术属“国内首创”。澄清这种混乱,有利于促使研究者把精力真正用在科研工作,产生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2.采用不同的方法培养学者和培养科学家,造就更多科学家
本科以下的学生,无疑可以按学者治学的方法训练培养。研究生以上,应该明确区别是培养学者还是科学家?如系培养普通教师、编辑、文史资料人员等学者型人才,自然可以按照加工知识的治学方法。诸如大量阅读、处理资料、综合概括、辨析论证等等。如系培养科学研究人员,则应该侧重于了解前沿,提出问题,以尝试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训练。文理皆然。
问题在于,科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总体上是因循我国传统治学观点设计的。如强调基础扎实研究生还要上许多门课、读许多的书;都要花许多精力收集古今资料;论文强调引证,注脚越多越显功力等等。迟迟不进入研究课题,与“研究生”名称不符。有人用埃及金字塔说明基础的重要。其实,金字塔是科学诞生之前的蠢笨杰作:5万多平米底面,堆了330多万块巨石,才垒了146米高。而艾菲尔铁塔按需要打基础,高320米,总重不过9000吨。对基础的分歧在于:学者讲究渊博,科学家需要精专。所谓“博而返约”仅是学者之通。今天又有人从“学科渗透”为“博”找理由,殊不知渗透是为了突破前沿。总之,培养学者或科学家确应采用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能造就更多的科学家。
3.以不同规范评价和管理科学人才,有效促进科学发展
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和管理要求,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尤其在一元化体制下,更能驱策所有科学人员。以发表论文的篇数和刊物级别“算工分”,大家就努力写文章。以多少万字的著作为晋升条件,出版的著作便越来越多“裹脚布”。需要花长时间大力气突破的前沿性问题、特别是成败难卜的问题,则很少有人愿意去解决。为了激励科学研究,试订了各种考评方案,但怎么也得不出更合理的标准。当我们把学者的和科学家的工作区别考评时,规范标准便能切合实际,而且可以使更多的人向科学前沿挺进,促进科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