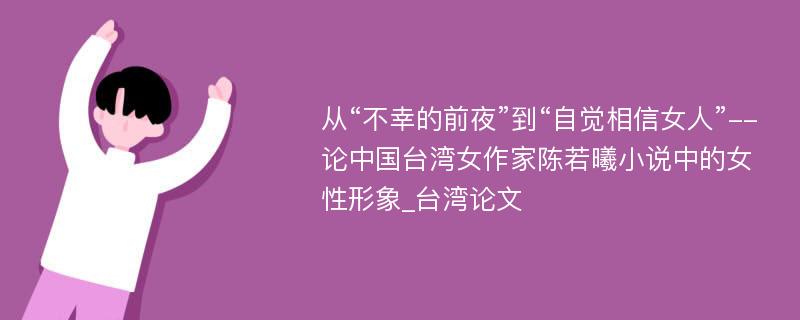
从“不幸的夏娃”到“自觉的信女”——论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女论文,女作家论文,夏娃论文,中国台湾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国台湾女作家陈若曦无疑是一位“社会意识强烈”的作家。她虽然很早就开始写小说,如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发表于中国台湾《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上的《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辛庄》、《最后夜戏》、《妇人桃花》等等,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与评论界的很大反响。真正使她声名鹊起、享誉文坛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次以小说的形式向外界披露“文革”内幕的《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作品。此后,陈若曦一改她“年青时最推崇写作技巧”的小说写法,“但求言之有物,用朴实的文字叙述朴实的人物,为他们的遭遇和苦闷作些披露和抗议”①。人们无论是推崇她、赞扬她,或是研究她、批评她,甚至围剿她,往往都基于同一个理由:社会意识强烈和触及现实政治。因而,人们看陈若曦的小说,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作者是一位女性作家,而将“《尹县长》、《耿尔在北京》、《地道》等男性或中性观点的处理”②来评价其整个小说创作。
这无疑是一种误解。笔者以为,虽然作家的性别不应该也无必要成为判断其作品优劣的标准,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成功女性比比皆是层出不穷的社会中,然而,心理学所揭示的男人与女人在观察世界、反映事物的用脑方式、心理特点方面的某些差异,注定了男女作家在描述现实、刻画人物以及观察角度和写作方法诸方面的某些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有时显得十分细微、似有若无,实际上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就这一点而言,人们仅仅把陈若曦当成一位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家,而并未意识到她同时也是一位关注女性命运、生存现状和生活方式的女作家,实在是一种误会。虽然她的小说并不像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那样专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的李昂等那样高扬起“新女性主义”的猎猎旗帜。其实,从陈若曦以描写妇女生活、探讨女性命运及其生存现状为主的数十篇小说中,亦不难看出她的“女性意识”。
平心而论,陈若曦描写妇女生活、探讨女性命运的数十篇小说,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思想深度等方面,其艺术水准方面的参差不齐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她笔下的人物形象的认识。其最早的旧作《灰眼黑猫》,发表于1959年3月出版的中国台湾《文学杂志》;而最近的长篇《慧心莲》,则于2001年2月出版。从1959年至2001年,时间跨度长达42年。42年自然并非弹指一挥间,其间不仅作者的经验、阅历和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变化,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概括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灰眼黑猫》到21世纪初的《慧心莲》,陈若曦笔下的女性形象,大体上经历了从“不幸的夏娃”到“落难的尤物”再到“自立的主妇”和“自觉的信女”这样几个既是社会历史的也是女性心理的变化阶段。
悲剧命题:“不幸的夏娃”
第一阶段“不幸的夏娃”,是指作者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创作的《灰眼黑猫》、《最后夜戏》、《妇人桃花》、《邀晤》、《乔琪》等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按其身份、受教育程度而言,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都市中的知识女性,如《乔琪》中的乔琪及其母亲、《邀晤》中的仰慈;另一类则是社会下层的各种妇女,如《灰眼黑猫》中的文姐、《最后夜戏》中的金喜仔、《妇人桃花》中的桃花等。实际上,后来陈若曦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一直未超出这两类人物的范畴,只不过后一类妇女大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而已。从这些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虽然她们的身份、性格、地位以及文化程度各个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不约而同,即命运的不幸。无论是被父母之命误嫁朱家而受尽折磨以致发疯夭折的文姐(《灰眼黑猫》),还是随着歌仔戏的没落而不得不骨肉分离的金喜仔(《最后夜戏》);无论是始乱终弃、阴阳隔绝以致被死鬼缠身的桃花(《妇人桃花》),还是大学刚毕业,就随母亲和媒人一次次相亲,为的是“好好地结个婚”的仰慈(《邀晤》),可以说,在主宰自己的婚姻、命运和前途方面,这些女子无一例外都是不幸者。社会、历史、环境、封建习俗和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女子的悲剧,正如作者借《灰眼黑猫》中文姐的好友阿蒂之口所说:“想到她的悲剧,我不禁深深怀疑我们现在的风俗与制度。在大都市里的人一定不会想到封建的残余在这穷乡僻壤仍有这么大的势力吧!”小说中被视为“不祥之物”的文姐死了,尸体连婆家的大门都不让进去,令人想起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褶裙》中那个身份卑微的收房丫头死后的遭遇。然而,陈若曦笔下的“灰眼黑猫”显然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而是同时也具有一种象征意味。小说一开头就有一句谶语:“在我们乡下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灰眼的黑猫是厄运的化身,常与死亡同时降临。”因而,当童年时代的文姐偶然把风筝线套上小猫头颈之时,她的厄运就已被注定,成为一个无法扭解的“死结”。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那种令人不可捉摸的神秘感,而在于对造成文姐之不幸命运的“主宰”的诅咒,于是我们听到了作者借阿蒂之口发出的强烈呼问:“我不觉深深诅咒所谓的命运,我奇怪难道真没有人逃出命运的安排?果真有命运,谁是主宰呢?”
曾经有过女人想跟命运抗衡,例如《最后夜戏》中的金喜仔。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宝,算命的说这孩子天生的“过继命”,不送给别人恐怕养不大,她竟摇头说:“我不信!”然而,在歌仔戏日趋没落、观众日益递减的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她实在无法两全:
在这个歌仔戏末落的时候,戏旦已经远非昔比了。十年前,旦角由她挑,唱一台戏的收入可以吃喝一个月;现在老板只要不满意,可以随时解雇她。她早已看出这个连环锁:生存,吸毒,生存……它紧紧锁住了她,再也逃不掉。③
所以,等待金喜仔的最后命运,还是骨肉分离,把亲生儿子送人,否则她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如果说,文姐、金喜仔的不幸命运,基本上是时代、习俗、环境和社会现实给生活于乡村的下层妇女带来不幸的命运的话,那么,乔琪的不幸命运,则来自其母亲在婚姻破裂后对前夫的仇视、憎恨的报复心理的后遗症。表面看来,乔琪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与文姐、金喜仔截然不同,她生活在吃穿不愁的富裕之家,经常受到母亲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关爱,又有陆成一这样死心塌地的异性追求者,不像仰慈那样大学刚毕业就一次次“邀晤”,只为了“好好地结个婚”④。她大学刚毕业便准备飞向新大陆留学深造,实在是人人羡慕的幸运儿。然而,随着小说对其内心世界的层层披露,我们逐渐明白了这个患有自恋症与“世纪病”的年轻女孩的不幸。原来,15年前父母离异、母亲再嫁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使她无论在家中还是在人群中都备感孤独与寂寞。就在她翌日飞赴新大陆的前夜,她也“丝毫感觉不到喜悦”,“有的只是困惑和莫名的踌躇”。小说中几次浮现出她儿时“孤独得仿佛被遗弃在旷野里”,“最难捱的寂寞,斩之不尽,驱之不去,像埋伏的奇兵,随时都可来袭”的记忆画面。正是这样一种挥之不去、招之即来的痛苦不堪的儿时记忆,造成了乔琪日后许多非理性的冲动与神经质的任性。为了急于“摆脱这个家,摆脱台北这个小地方”,甚至不惜嫁给一个她“当然不爱”的40岁男人。当其婚礼被迫取消之后,她的“神经质,带着悲剧性”的“疯狂”发泄到了极点。事实上,小说中有着“神经质,带着悲剧性”的女子又何止乔琪一人呢?她母亲的内心实在比她的女儿更加痛苦不堪,只是平日不像女儿那样容易随时发作罢了。小说的真正高潮是在女儿接到生父的电报,希望她赴美“经东京祈下机一晤至祈至盼”之后,平日温柔体贴、百依百顺的母亲竟一反常态,蛮不讲理地要求女儿“不要下飞机”,“不要去看他”,女儿哀求道:“我们只是见一面,十五年只见一面呀!”不料母亲竟然捏紧拳头,面容扭曲,眼中冒火,浑身颤抖:
“……你那天杀的父亲……毁灭了我的爱情……现在又来抢我的孩子……呵,我憎恨你!我永远憎恨你!别永远得意,我不相信我会永远失败!听着,我决不放弃,我宁肯,呵,我宁肯……宁肯杀了你,也不愿意让他抢去!”⑤
正是在这个充满紧张感的戏剧性场景中,作者写出了一个女人在婚姻破裂之后对男人产生的极端仇视、憎恨甚至不无歇斯底里的报复心理。这里虽未竖起女性主义的旗帜,却埋伏着日后“杀夫”的心理动机。因此,在陈若曦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中,《乔琪》是女性主义意识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强烈的一篇。它不仅反映了父母离异对于一个9岁女孩的心灵戕害及其后的恶劣后果,而且揭示了婚姻破裂带给母女两代人的幻灭感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我毁灭的命运悲剧。
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悲剧命题,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台湾女性文学作品中,是十分罕见的。可惜陈若曦很快就自动放弃了这种对人性弱点的拷问与女性心理的透析的艺术追求,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笔者以为,她后来的许多小说,包括享誉文坛的《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等,就其对人物心理的探究和分析之深度而言,没有一篇能超过《乔琪》。
谐剧人物:“落难的尤物”
1962年秋,陈若曦在赴美留学之后,就中止了中文小说的创作(谁知这一中止,竟长达12年)。她于1965年获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后,1966年便偕其丈夫经由欧洲赴中国大陆。然而,恰逢“文革”爆发。在北京、南京蹉跎了7年之后,1973年她拖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家四口移居香港。这段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对于一心想“报效祖国”的陈若曦及其家人来说是不幸的;然而对于小说家陈若曦而言,却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机遇。她在“文革”中经历的那些人和事,在她离开大陆之后仍在脑海中萦回不已。收进《尹县长》集里的作品,均是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除《尹县长》之外,包括《晶晶的生日》、《值夜》、《任秀兰》、《耿尔在北京》以及稍晚些时发表的《尼克森的记者团》、《老人》、《地道》、《春迟》等。
陈若曦重新执笔写小说,并不意味着12年前“最后夜戏”的重新粉墨登场,而是意味着对“最推崇写作技巧”的小说写法的改弦易辙。于是,《尹县长》等作品便成为她“力求客观、真实”的代表之作。确实,“文革”中所发生的许多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似乎不需考虑什么“虚构”情节,便可构成一部写实主义小说。因而陈若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比之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小说,就人物心理的深度以及对女性地位、命运及其生存现状的关注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然而,这些“坚持写实主义”的作品,毕竟确立了作者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而对它们的小说技巧之成败得失的考虑便在其次了。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首先是从人的尊严被践踏、人的本性被扼杀、人的存在被忽视的人道主义立场,而不是从女性的地位、命运及其与男性的关系来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因此,这个时期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往往扮演着非女性即中性甚至“雄性化”的角色。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位亲自上门动员辛老师家拆毁晒衣架的居委会主任高嫂(《尼克森的记者团》)。不仅辛老师的丈夫、堂堂七尺须眉闻其声而色变,承认“这个女的我最怕看到”,唯恐避之不及;就连嘴巴不软的辛老师本人,也觉得这是个难缠的角色。在这个除了生育六个孩子外彻头彻尾雄性化的“母大虫”身上,折射出极其丰富的政治、社会和时代的内蕴。也只有“文革”,才会使这个“书倒没念多少”的婆娘,成为男男女女谁见了都害怕的政治动物。
不过,生活中毕竟并不全都是高嫂那种畸型的政治动物,即便是在“文革”那种非人道、非人性的非正常时期,也还是有作为“男人的一半”的女人存在。在“四五”期间去天安门凭吊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后遭到告发、被迫写“交待”的老人,他的妻子亲手为光了一只脚回来的老伴纳鞋底的行动,无声却是有力地表达了对丈夫的精神支持(《老人》);虽离过婚且相貌平平,但为人谦和、心地善良的李妹,正是她的出现,使心灰意冷的洪师傅真正感受到了女人的爱,最后他俩被误关在地道中双双毙命,仍然留下了以血书写的“我们相爱,不是自杀”的爱情宣言(《地道》)。
在陈若曦那些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中,实在极少写得生动传神而又富于女性魅力的人物形象。那几位以作者自身经历、感受为原型的知识女性,如《晶晶的生日》中的文老师、《任秀兰》中的陈老师、《尼克森的记者团》中的辛老师等,都算不上是血肉丰满、形神兼备的女性形象。唯一的例外倒是《查户口》中那个落难的“尤物”——因偷汉而被周遭的人们骂为“妖精”的“潘金莲”——彭玉莲。这个女性气息十足的人物的出现,给陈若曦那些硬梆梆而又色彩灰黯的“文革”小说添加了一抹柔亮而又缤纷斑斓的油彩。
这是个绝不与周围人们相混淆的抢眼的女人。在这篇题目显得相当政治化的小说中,作者恰恰显示了对一个女人的形体、神情、穿着等观察的细致入微:
说来彭玉莲并非什么美人,个子生得很矮小,不过她善于保养,注重穿着,身材总显得很匀称;特别是胸部,高低起伏,曲线突出,越发引人注目了。她的头发一向找鼓楼的一家大理发店修剪吹风,一样的短发齐耳,但她的总是蓬松有致,显得与众不同,女孩子们都管那叫海派头。皮肤黑黑的,鼻子微塌,一张大脸像圆盘,与她矮小的身材颇不相称;然而一双眼睛却生得又大又亮,且富于表情,顾盼之间,似有种种风情,男人瞧着,觉得扑朔迷离,很多女人自然是又嫉又恨了。⑥
然而,这位被她周围的常主任、施奶奶们视为眼中钉的“妖精”,不仅身处“文革”期间敢在穿着打扮上标新立异地显示其女性特征;更难得的是,作为“老右派”、“老运动员”冷子宣的妻子,一方面,她在男女关系上敢作敢为,以至成为常主任、施奶奶们虎视眈眈的“捉奸”对象;另一方面,她也不与常年在五七干校当“劳动常委”、未老先衰的丈夫“划清界限”,向他提出离婚要求;甚至“偷汉”的原因,似乎还与想帮丈夫的忙有关。例如,她当初与马书记来往,“是为了给冷子宣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人们“捉奸”未遂之后,其丈夫果真脱离了“五七农场”而回校教书。因此,这个落难的尤物身上所呈现的相当复杂的、既是人性的也是女性的内涵,使人想起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那些既让丈夫戴上绿帽子又让丈夫把银钱带回家的船上女人(如《丈夫》等)。
对于彭玉莲这样的女人,作者并未在小说中对其作出简单的道德评判和道义谴责,而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对她“与众不同”乃至与人通奸都给予了与周围那些嘁嘁喳喳、专等着看她当众出丑的婆婆妈妈们截然不同的宽容与谅解。这从那位不得不奉命“监视”彭玉莲的叙事者的态度上便可一目了然:“我除非吃饱饭没事干,才管这种闲事!”可以说,正是由于刻画了彭玉莲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使得《查户口》在作者所有的“文革”小说中显得别具一格。值得注意的是,此篇在写到她与丈夫冷子宣的夫妻关系时,也并未出现司空见惯的反目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的戏剧性场面。冷子宣在得知妻子对己不忠的实情之后,只是淡然地说:“如果彭玉莲要离婚,我随时答应,我自己绝不提出。”这句话中显然含有对自己长年在外当“劳动常委”而使妻子独守空房的歉疚与谅解。正因为这样,当他回到家那天,“彭玉莲满面春风地拎了一只老母鸡回家,拔鸡毛时嘴里还哼著曲子。邻居们竖长了耳朵听,可是到天亮也没听见一句吵嘴的声音”。这里似乎蕴含着作者对夫妻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即婚姻并不仅仅是一种两性关系的契约,更不应该只是对女人的贞操产生约束。尽管是在“文革”那样一种非人性的非常环境之下,“落难的尤物”也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出了某种自在的心态,虽然她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半夜三更穿堂入室的“查户口”。
活剧纪实:“自立的主妇”
1979年,陈若曦应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之聘,全家由加拿大移居美国。此时,中国大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已经结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后,陈若曦作为海内外著名的作家,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她经常应邀回中国大陆或中国台湾访问、演讲,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展,生活的内容逐渐丰富。于是,我们在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所见到的画面便显得驳杂斑斓起来。撇开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突围》、《远见》、《二胡》、《纸婚》不谈,即便在她的短篇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空间及其经历的事件,也显然比她早期小说与“文革”小说要广阔和丰富许多。
值得注意的是,陈若曦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短篇小说,差不多都围绕着女主人公或在美国、或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遇到的不顺心的麻烦事来铺陈情节,展开对话。她的小说,从来也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品那样重视华人妇女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种种困扰。如《素月的除夕》,写中年妇女素月为了送两个儿子到美国念中学,本来计划是“等孩子们习惯安定下来,她便返台”,以便夫妻团聚。可人到了美国,才发现完全行不通,因而只得滞留在美国,一方面挂念家乡的多病丈夫,同时又整日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签证期满成为非法居留的“黑户口”。尽管美国的“蓝天如洗”,她却“只感到混乱和空虚”。再如《不认输两万元的话》中的老年妇女柯太太,当初为了来美和儿子团聚,倾家荡产才买下柏克莱的一栋公寓。不料抵美后儿子死于车祸,媳妇带着孙子改了嫁。于是她想卖掉公寓筹一笔养老金返回家乡安度晚年;谁知台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当初买下的公寓,十年后连本钱都不值。但如果不出卖的话,柯太太又面临着房客“合法”却不合理的荒唐要求和添人增丁的种种麻烦。所以她除了忍痛割爱卖掉公寓外,别无选择⑦。这两篇小说,十分细腻地表明了赴美后的中、老年妇女在现实中的困境。然而,严格说来,像上述的《素月的除夕》、《不认输两万元的话》以及写大陆赴美女留学生被骗而惨遭杀害的《到底错在哪里?》等作品,实际上并未表现出多少“女性意识”,因此,这几篇小说虽然都以女性人物作为其主人公,但反映的只不过是中国台湾的或中国大陆的居民赴美后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遭遇与不幸罢了,即使将其中的性别角色转换一下,这些问题(经济的或是种族的)也依然存在。
真正显示出当今华人妇女的价值观、人生观及其在两性关系中的变化的,是陈若曦描写各类女性人物对于婚姻、恋爱由被动到主动的态度的作品,如《我们上雷诺去》、《贵州女人》、《演戏》、《走出细雨濛濛》、《圆通寺》、《丈夫自己的空间》等小说。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仍然是两类: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和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劳动妇女。就传统的婚姻观、家庭观对她们的约束力而言,这两类女性人物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在自为的轻松。如《我们上雷诺去》中那个“身无分文便一个人从扬州跑到美国来”的原中学教师戚芳远,为了“想长留美国”而不惜以重婚做赌注,与一个75岁的吝啬老头“上雷诺去”注册结婚。理由虽是“因为她办离婚手续难”(她在国内有丈夫、儿子),但却很难从伦理道德或社会学意义上来指责她的重婚行为,因为她坦率地向女友承认:“如果有更好更快的办法,我今天也不会到雷诺来。你有一天会明白,我不是自私的女人。”当女友提醒她,她嫁的老头“也许还能活上十年也说不定——十年啊!”她竟回答:“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我都熬过来了。再熬十年……那也只是一眨眼的事。”⑧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清楚:只要老头一归西,她就立马把丈夫、儿子接来美国。这里绝没有父母之命的强制性拜堂,而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交易性注册:不存在悲剧,只是一幕既荒诞又现实的闹剧。
再如《贵州女人》中那个从贵州的偏僻山区嫁到美国唐人街来做餐馆老板续弦的原小学教师水月,也并不讳言她嫁给年龄与之相差近40岁的老头,目的“是为了个人出路。在穷乡僻壤,她看不到前途,恋爱遭过挫折,家里又欠债,无奈中才把希望寄托在这场婚姻上”。但对于水月而言,联姻决不等于禁欲,这是她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妇女的根本区别。所以,当年老体衰的丈夫不能与她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而那个在餐馆内打工,经老板主动请求才勉强答应每周一次来老板家代行丈夫之责的阿炳又要结婚的情形下,水月的出走便成了偶然中的必然。因为她无法忍受与丈夫之间没有夫妻之实的生活。无论是戚芳远也好,还是水月也罢,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念对她们都失去了往日威风凛凛的制约力,她们在婚姻的选择上已经成为自在的女人。作者对这些在传统的封建卫道士眼里看来是道德败坏的女人身上,寄予了充分的宽容与谅解。因为在她看来,在当今世界,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女人作为一个人,当然有这样的权利,别人无从干涉,更不必横加指责。正如那位本想劝阻芳远与其姑丈结婚的女留学生小杨所说:“结婚是两厢情愿的事,局外人说好说歹又有何用?”
当今华人女性不仅在婚姻选择上持越来越自由自在的态度,而且在对待家庭关系、甚至对自己所嫁非人,往往也抱着不愠不恼、和平共处的宗旨,这在妇女没有取得经济独立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圆通寺》中有两位对比强烈的女性,虽然身份、地位和所受的教育程度差别很大,但都是经历婚姻不幸的女人:在美国执教的“我”,离过三次婚,结果连对唯一的儿子也不得不放弃抚养权;而“我”离开20多年后再回到中国台湾,却发现嫁了一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丈夫的表姐,“哪儿像亲戚说的‘遇人不淑’、‘独自拉拔三个孩子长大’的可怜人形象呢?”表姐生活得充实而又忙碌,难怪她把那个“不负责任的丈夫”视为可有可无之人了。这里,仍然是婚姻的不幸,但却不再有乔琪母亲那种离异夫妻之间鱼死网破的仇视、憎恨与报复,原因其实很简单: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大都自食其力,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因而婚姻幸与不幸,丈夫好与不好,已经不再是妻子全部的生活内容和唯一指望,那种因所嫁非人而郁郁寡欢、以泪洗面的苦命妇人、可怜女子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正如作者在《女性意识》一文中所说:“始乱终弃、家庭暴力、婚外情和离婚后生活无依的恐惧。这些已不仅是男女平权之争,更重要的是妇女自己的心理建设了。”⑨
正因为当今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和经济能力的独立,所以在对待“第三者”介入或是丈夫变心、婚姻破裂方面,也变得比以往要冷静、客观得多。《演戏》中的丽仪,五年前就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只为避免伤害女儿的幼小心灵而未搬出丈夫的家,彼此分房而居。这里再也看不到夫妻之间战争的硝烟,小说以十分平和、宽松的氛围,反映了这对貌合神离的离异夫妇之间理智而又自在的生活方式。当然,对于丽仪而言,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精神上她都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和前夫一样,她既有离婚的自由,也有再嫁的权利。所以,当她小心翼翼地向女儿解释“离婚并不可怕”而得到女儿的赞同时,她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同住一个屋檐,还是另起炉灶,对她已无区别。重要的是,她获得心灵的自由,今后不必演戏了”。
同样,在《丈夫自己的空间》里,辛辛苦苦拖儿带女在温哥华为丈夫“圆移民梦”的杨太太,发现丈夫在中国香港有了外遇,便赶回来想挽救自己20年的婚姻。谁知丈夫却振振有词:“你在温哥华有自己的事业和儿子,我在香港也享受一点……自己的空间。”于是,杨太太明白了她和丈夫之间的婚姻无可挽回。这里,没有妻子寻死觅活的哭闹吵骂,也没有没完没了的纠缠不清:“杨太太相信,她能在异国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她也能做出最好的选择。”⑩
正如作者所言,“如今婚姻不必是‘终身大事’了,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能够独立和自我满足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做‘人’比做‘女人’重要多了”(11)。
也有女人在爱情与婚姻的权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第三者”,如《走出细雨濛濛》中那个曾自觉自愿地甘当有妇之夫的情妇并历时达8年之久的“她”,在明白自己所爱的男人只不过是一个既怕离婚影响其仕途,又想继续占有其感情的伪君子时,不禁躬身自省:“她问自己,怎么会有今天呢?是他还是自己的错?”于是,结局不言自明,“她有信心,自己会走出这片濛濛细雨”(12)。
“走出濛濛细雨”,这无疑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第三者”的女性自我醒悟的象征。遗憾的是,陈若曦1994年赴港后所写的几个短篇,如反映中国香港日益严重的“包二奶”问题的《重振雄风》(13)、反映女性“雄化”与男性无能的《我的恶梦》(14)等,都不能算是成功之作。这恐怕与作者抵港后比较注意沸沸扬扬的社会问题的“热点”,未能就此进行深入的探究与周密的艺术构思所致。因而,这几篇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某些社会问题的形象图解。
歌剧上演:“自觉的信女”
“走出濛濛细雨”之后的女性,该走向何方呢?作者直到20世纪末对此都没有提供新的答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她们不会再回到“灰眼黑猫”的时代去,听任不幸的婚姻和命运的宰割;虽然她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第三者”,但她们不会让自己永久地背着不光彩的十字架。因为,她们作为自在的女人,既可以“上雷诺去”,也可以到“萧邦的故乡”(15)去。
果然,1995年以后定居中国台湾的陈若曦,在21世纪初奉献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慧心莲》,并在其中对于婚姻不幸、命运多舛的中国台湾女人重新寻找人生道路及其生命意义作出了新的抉择与诠释。《慧心莲》写的是一家三代女人命运多舛的曲折故事,几位主角都是女性。母亲杜阿春是一个典型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家庭主妇。她年轻时未婚先孕生下了两个女儿美慧和美心,不料女儿的生父暴病身亡,没有任何名分的母女三人连亲人最后一面都未见到就被赶出家门,连一点抚养费都得不到。女儿的身份证上注明“父不详”。为了生存,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外省来的“罗汉脚”——一位当年从大陆到台的军人李忠正,又生下了儿子继光,正如她所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们这一代,十个女人有九个半是为了饭碗”(16)。但此后,因夫妻性格不和终至“家破人走”,两地分居,一家人分成了一半“女儿国”和一半“男儿国”。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在老姐妹林姐的感召下成了乐善好施的信教者,“已经把佛堂当作自己的家了”。而两个身份证上注明“父不详”的女儿美慧和美心,在婚姻爱情上继续上演着母亲的不幸悲剧。
美慧高中一毕业就匆匆嫁给了王金土,儿女双全却常常莫名其妙饱受丈夫的虐待,以致不得不抛下儿女逃出婆家寄居别处,丈夫则借口她不履行同居义务而向法院申请离婚,在她未收到法院通知书的情形下,离婚成了自动判决生效的既成事实。她万念俱灰,甚至一度割腕自杀,终至一心出家,削发剃度,成了法号“承依”的僧尼。念经拜佛,似乎成了她唯一的精神解脱,“因为好多部经里都提到念经的功德,其中之一是来世不生为女人”(17)。妹妹美心天生丽质,活泼可爱,成了中国台湾闻名遐迩的电影明星,追求者甚众。但一心追逐爱情的她与母亲当年一样,爱上了一个姓吴的有妇之夫,并生下了儿子阿弟,虽然姓吴的按时支付儿子的抚养费,但儿子身份证上与自己一样,仍是“父不详”。天有不测风云,年幼的阿弟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不幸夭亡。悲痛无比的美心终于看破红尘,在捐出亡儿的30万新台币丧葬费后也一心遁入佛门。
时代终究不同了,如今的中国台湾,皈依佛门已不再是青灯古刹、苦度余生,而成了一种人生的选择,甚至成了一种把握或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尚”。正如美慧的女儿慧莲所说:“现在的年轻人想出家的多着哪!我自己就觉得是很好的生涯规划和选择”(18)。她大学毕业后也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不仅自觉成为法号“勤礼”的佛门弟子,还被派往中国大陆浙江天台寺取经游学,而她的男友则选择成为天主教的修士。
在杜家三代女人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因为家庭破碎而心灵扭曲的乔琪母女那种歇斯底里的自暴自弃和疯狂发泄,而是以一种平静、宽容的人生态度安之若素,闲庭信步。最重要的是,她们有了一种情感寄托与人生信仰。因此,承依(美慧)皈依佛门后被派往美国留学,返家后成了海光寺的“上人”(住持),连她母亲都引以为豪:“当年那个柔弱、悲恸到不想活的少女,如今已修成一位富有慈悲和智慧的尼师了。”(19)妹妹美心在经历了儿子亡故之后一心向往遁入佛门清净之地,却不料竟遭遇道貌岸然的“金身活佛”的性骚扰,她在百口莫辩之下像当年她姐姐那样割腕自杀,生还之后通过诉诸法律,终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最后,杜家三代信女,齐齐出现在中国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救援现场,她们成了万众敬仰、慈悲为怀的救星。
所以,在陈若曦笔下,21世纪的女性之路,其实有许多条;“条条大路通罗马”,就看她们怎么往前走了。
注释:
①陈若曦:《陈若曦自选集·后记》,《陈若曦自选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第235页。
②吴达芸:《自主与成全——论陈若曦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陈若曦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③陈若曦:《最后夜戏》,《陈若曦自选集》,第149-150页。
④陈若曦:《邀晤》,《陈若曦集》,第32页。
⑤陈若曦:《乔琪》,《陈若曦自选集》,第135-136页。
⑥陈若曦:《查户口》,《尹县长》,台北:远景出版社,1976年,第61-62页。此篇收入《陈若曦集》时,文字略有改动。
⑦陈若曦:《不认输两万元的话》,《王左的悲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第119-128页。
⑧陈若曦:《我们上雷诺去》,《走出细雨濛濛》,香港:勤十缘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⑨陈若曦:《女性意识》,《星期天周刊》(香港)1995年3月19日。
⑩陈若曦:《丈夫自己的空间》,《王左的悲哀》,第137页。
(11)陈若曦:《女性意识》,《星期天周刊》(香港)1995年3月19日。
(12)陈若曦:《走出细雨濛濛》,《走出细雨濛濛》,第8、10页。
(13)陈若曦:《重振雄风》,《星期天周刊》(香港)1995年1月15日。
(14)陈若曦:《我的恶梦》,《皇冠》杂志(台北)1995年1月号。
(15)陈若曦:《啊,萧邦的故乡》,《王左的悲哀》,第157-166页。
(16)陈若曦:《慧心莲》,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17)陈若曦:《慧心莲》,第47页。
(18)陈若曦:《慧心莲》,第223页。
(19)陈若曦:《慧心莲》,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