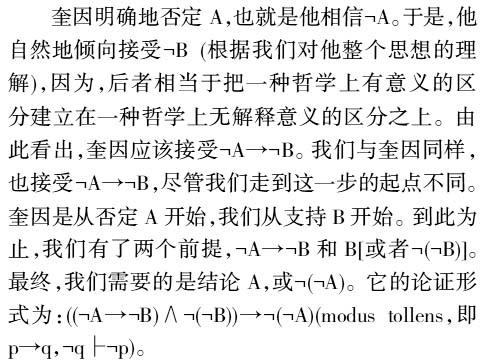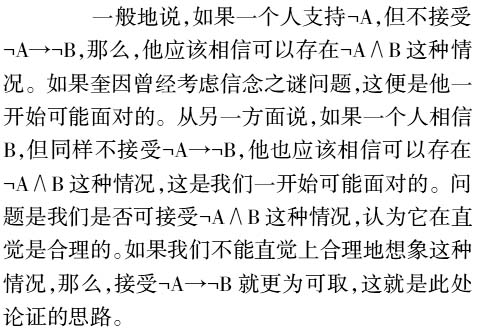分析性与信念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信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6 文献标识码:A 这篇文章专门讨论S.克里普克(S.Kripke)的信念之谜是否会在分析语句中产生这个问题。假如结果是否定的,那么,这个结果就可能表明分析性概念或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是一个哲学上有意义的区分。我们最终的结论是:通常我们认为是分析的那些语句,确实不能产生信念之谜,或至少看不到以克里普克所举例子中那种方式产生信念之谜的希望。相反,对于我们通常认为是综合的那些语句,则完全可能产生克里普克的哲学之谜。因此,在进行必要的论证之后,我们可以断定,在是否存在产生信念之谜可能性这方面的区别,是对分析与综合区分存在的一个支持。为描述简便,我们把哲学家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存在分析与综合之区分这个断定叫做“断定A”,把以下大家还不熟悉的断定叫做“断定B”,这个断定是:以是否可以产生信念之谜为标准,恰好划分出两个独立的语句类,一类是我们通常认为是分析的语句,另一类是我们通常认为是综合的语句。同时,为避免论证中不合法的循环,在使用“分析语句”这个词组时,我们一般是指人们通常认为的分析语句,而并不事先假定分析语句的存在,也不假定“分析语句”这个词指称某些哲学家赋予了特殊哲学涵义的语句。 在本文的论证中,两个概念具有基础的意义。在对信念之谜产生条件的分析中,我发现实际上有两种对翻译起约束作用的原则。一个原则是在实际的翻译中,被实施翻译的那些人所坚持的原则,另一个原则是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之外,从客观角度评价翻译的人所支持的原则。不同于在克里普克典型例子中所使用的综合语句,对分析语句,一个掌握了相关语言材料意义的人(在此,“掌握”的标准并不需要比克里普克在描述其典型例子中所实际使用的标准更高),如果他诚实地且有理性地使用语言,将会在两个原则的意义上都做正确的翻译。其结果是,在分析语句的使用中,并不会有信念之谜的产生(B真)。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有如下进一步的推理:如果B是真的,且“

蕴涵

”也是真的(这一点正文中有相应的论证),则根据规则(modus tollens)A也是真。这个最终结果的哲学意义依赖于信念之谜是否真的是一个哲学之谜,如果是,那么,在关于信念之谜的一个结果上所得出的A,也非常可能有哲学意义。于是,在上述假定之下,这个结果可以理解为在W.V.奎因(W.V.Quine)的攻击下,辩护分析与综合区分的一种尝试。 一、关于翻译的两个原则及对信念之谜的解释 在《信念之谜》这篇文章中,克里普克给出了他的翻译原则:如果一个语言的一个语句在那个语言中表达了一个真理,那么,它到任何语言的任何翻译也在翻译语言中表达一个真理。①使用这个翻译原则和去引号原则,②在把信念赋予一个有能力的诚实的说话者(先后说两种不同语言)的过程中,克里普克表明了信念之谜产生的可能性。实际上,克里普克的翻译原则有两种用法,或者,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两种不同的理解有实质的不同,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两个不同的翻译原则。第一个原则可以叫做“主观翻译原则”:如果一个有能力的说话者认为一个语言L的一个语句S表达L中的一个真理,那么,他诚实地接受为S任何其他语言L′中的翻译的任何语句S′,也必须是他认为在L′中为真的语句。第二个原则可以相应地叫做“客观翻译原则”:如果一个语言L′中的一个语句S′是另一个语言L中的一个语句S在L′中的翻译,那么,如果S在L表达了一个真理,S′在L′中也表达一个真理。从克里普克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他第二种涵义上(即客观涵义上)使用翻译原则。通常,翻译者在日常的翻译中实际上只是使用了主观的翻译原则(尽管在多数时候,他们也许认为自己使用了客观原则,或同时使用了两个原则)。作为实践的参加者,他们通常只是把被翻译语言中他们认为真的语句翻译成翻译语言中被他们认为真的语句。他们所接受的主观原则阻止他们把被翻译语言中的真语句翻译成目标语言中的假语句。 当然,正常情况下,日常说话者也接受那个客观的原则,并在评价翻译的结果,或反思翻译本身时使用这个原则。存在着一种可能,当客观的观察者知道正确的翻译是什么的时候,实践的翻译者并不具有同样的知识。信念之谜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认识上的不对称的可能性。因此,两个原则应用的条件和方式是不同的。根据客观原则,如果两个语言的两个语句真值不同,那么,一个语句就不可能是另一个语句的翻译。此时,如果即使翻译者认为两者均为真,并借此进行翻译,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事实上错误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第二个原则是元翻译的原则,它不用来指导或限制翻译,而用于评价翻译的结果。 为后面讨论的方便,除克里普克的原来的“佩里与伦敦”的例子,再引入一个关于自然类语词的例子。③设想张三是一个理性的信念持有者,并且是正常的汉语的说话者,但他此时只会说汉语。他原来一直听说一种生长在欧洲的花叫做“郁金香”。我们知道(但张三不知道)郁金香在英语中叫做“tulip”。在他听到的信息的基础上,他诚实地认同汉语的句子“郁金香是美丽的”字面上所断定的。根据去引号原则和克里普克所定义的翻译原则,张三相信郁金香是美丽的。后来,张三有与克里普克的佩里相似的经历,在伦敦的一个贫民窟他以直接的方式学会了英语。张三在这个地方所见到被叫做“郁金香”的花都是色彩单调、无精打采的(也许是因为无人照管,也许因为品种不佳),于是他诚实地认同英语句子“Tulip is not beautiful”字面地所断定的。根据去引号原则,他相信郁金香不是美丽的。由此得出,理性的说话者相信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于是产生了信念之谜的另一个实例。 在克里普克“佩里与伦敦”的例子中,如果佩里本人只使用主观的原则,他不可能接受从法语词“Londres”到英语词“London”的翻译(即使在他成为双语的说话者之后)。与此类似,在我关于张三的例子中,张三也不可能接受从“郁金香”到“tulip”(即使在他成为两语的说话者之后)。这是因为,尽管他们分别认为法语的句子“Londres est jolie”(意为伦敦是美丽的)和汉语的句子“郁金香是美丽的”在他们的母语中是真的,但佩里并不认为英语句子“London is pretty”是真的,同样地,张三并不认为英语句子“Tulip is beautiful”是真的。由于主观翻译原则会禁止这样的翻译,所以不会有导致矛盾的翻译实际发生。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使用客观的翻译原则,再加上去引号原则,他将不得不说佩里和张三两个人事实上同时相信相互矛盾的命题。客观原则的判定与这里是否有实际的翻译过程无关,只在另一个语言中有一个语句与被翻译语言的相应语句同义,就存在一个翻译。 信念之谜本质上是两个判断之间的不一致的结果。以直觉上正确的标准,我们可以判定佩里和张三两人都是理性的。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说一种语言时,在反思后应该不会诚实地断定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但是,使用某些直觉上正确的原则,我们确实可以从他们实际说出的语句推出一个矛盾。并因此似乎不得不说他们是非理性的。从两个翻译原则的角度来说,分别使用两个原则将得出不一致的判断。主观原则并不允许从“Londres est jolie”到“London is pretty”或从“郁金香是美丽的”到“Tulip is beautiful”的翻译。但这本身并不能阻止两对语句的“客观的”翻译,但客观翻译却导致理性说话者相信语句S和它的否定

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后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和正确性并不依赖于说话者意向或他们对语义知识的掌握(以及他们是理性的这种关于个人的认知性质),而只依赖于客观的真值或语句的语义内容。在“客观的”视角下,结论只取决于事实上如何。由此能想到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语句,对它们来说,此种令人困惑的结果并不会发生。这是下面将要回答的问题。 二、分析语句与信念之谜 假如存在分析语句,奎因的例子“单身汉是未婚的”应该是这样语句的典型。反对分析性的人会说,即使这样的语句也不是分析的。现在我们不准备立即回答分析语句是否存在的问题,而要转换视角去讨论另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同的问题,即由分析语句是否可以产生信念之谜的问题。直觉上说,我们比较倾向给予否定的回答。观察产生信念之谜的那些作为例子的语句,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哲学之谜的产生中,说话者完全是正常的、理性的,特别是他们并没有犯语言的错误。当佩里生活在法国,他是个正常的法语说话者。他去英国并学会了英语之后,他同样是一个正常的英语说话者。他像他的邻居一样,以正常的方式使用“London”这个词。 克里普克风格的信念之谜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在考虑单个语言,也就是没有实质的翻译的情况下,说话者并没有犯任何语言或逻辑的错误。第二,说话者事实上说了某个语言中的一个语句,并且事实上也说了那个语句在另一语言中的客观翻译的否定。第三,一个使用克里普克的翻译原则(我们意义上的客观的翻译原则)和去引号原则的人,将判定说话者相信一对相互矛盾的命题。可是,对于类似于“单身汉是未婚的”这样的语句,第一和第二个条件是不可能同时被满足的。因此,当要求前二项条件同时被满足时,则第三个条件不可能被满足。如果佩里正确地使用英语,在反思后他不可能说“单身汉是结了婚的”。除了在引语等特殊情况下,如果他真的说了“单身汉是结了婚的”,他就不可能是在正确地使用英语。与此不同,当佩里说“伦敦并不美丽”时,他在说正确的英语,尽管他此时仍相信法语句子“Londres est jolie”所表达的命题。在仔细地考察自己对语言的使用之后,佩里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语言上的错误,他的邻居也会有同样的结论。相反,如果他像克里普克假设的那样是一个合格的英语说话者,当他说了“单身汉是结了婚的”,并仔细检查自己的语言使用,他将发现自己在使用语言上犯的某种错误,他的邻居也将得出同样结论。 一些描述论者也许说,佩里的例子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之谜产生,真正的问题只是佩里没有掌握足够的语言知识,比如没有充分掌握语句中那些专名的弗雷格意义或描述。克里普克反驳说,掌握这些描述需要知道类似(伦敦)是英国首都这样的描述意义,这会产生类似的问题,比如“英国”这个词的描述也成为必要的知识。似乎不掌握它们仍可能产生信念之谜。④克里普克看到,这将走到那个老问题,有没有不包含专名或自然类词的纯描述或性质。⑤ 能否达到纯描述的最终层次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无论如何他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主题。但这个问题有可能使人们产生一种希望,是否存在一类在描述上足够简单明确的语词,由它们所组成的语句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决定了此类语句不可能产生信念之谜。如果这个想法确实有道理,那么产生与不产生信念之谜的划界处可能不在分析与非分析的语句之间,而在某些特殊词汇所组成的语句与没有这些词汇的语句之间。 如下三类词各有其明显的特点,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在语言哲学中所关心的名字。第一类就是日常的专名,比如“伦敦”。第二类即所谓“自然类语词”,比如“郁金香”。第三类是人工物的名字,或者社会与文化存在者的类名字,比如“铅笔”,或“单身汉”。最后一类似乎更有可能满足我们的希望。一个分别在英语中掌握了“bachelor”,又在汉语中掌握了“单身汉”之意义的人(当然,也假设他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英语和汉语),不大可能在英语中诚实地认可语句“Bachelor is unmarried”所断定的内容,而又在汉语中诚实地认可语句“单身汉是结了婚的”所断定的内容。换句话说,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他必定犯了语言或逻辑的错误。当这个过程中有实际的翻译发生,则他必定违反了主观的翻译原则。这个事实使得人们有可能倾向于给出一般的结论。其实,克里普克在这里也显示出某种乐观的情绪。在《信念之谜》中,他说过,像“幸福”、“医生”等等这些词,说话者在反思之后就能判定它们是否与另一个语言中的相应的词同义,因此,对这些语词对,产生信念之谜的路将被封死。⑥初看起来,这个结论有可能是对的,但仔细观察,也许情况并不如此。 我们注意到,在前面关于单身汉的例子中,我们实际上使用了由这个词组成的分析句,因此,一个掌握了相应语言的人,会拒绝“单身汉是结了婚的”这样的语句为真。相反,在佩里和伦敦那类例子中,我们使用的语句都不是分析的,于是使用客观的翻译原则和去引号原则,就会构造出信念之谜。可是,一旦对“伦敦”这样的词,我们把注意力也转向一般被认为是分析的语句,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让我们来看“伦敦是一个城市”,或“郁金香是一种植物”。显然,如果你确实有资格声称掌握了汉语中“伦敦”一词的意义,你起码会知道伦敦是一座城市,而不是一块门板。你不可能语义上正确地说“伦敦不是一座城市”。事实上,在反思后,你也不可能认为你字面上正确地说了“伦敦不是一座城市”这句话。S.布莱克本(S.Blackburn)以类似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布莱克本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委员会,那么,你就不可能是在谈布莱克本。⑦佩里去了伦敦以后,如果真能被称为学会了“伦敦”这个词,他就不可能诚实地认可“London is not a city”所断定的。但是,同样是学会了这个词的他,仍能诚实地认可“London is not pretty”,且未犯任何语言上的错误。主观的翻译原则使得佩里拒绝从“Londres est jolie”到“London is pretty”,但没有什么阻止他诚实地认可他认为“London is not pretty”所表达的内容。对于语句“London is not a city”,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以掌握“伦敦”一词的意义和用法,佩里就有足够的理由阻止他自己诚实地说“London is not a city”因为在事实上他并不同意这个语句所表达的,去引号原则在此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此时,即使是客观的翻译原则也不能迫使关于说话者的解释陷入信念之谜的困境。 阻止信念之谜的关键在于“伦敦不是一个城市”本身是矛盾的(分析句的康德定义之一,就是否定它会导致矛盾),因为是一个城市是“伦敦”一词的意义的核心部分。如果佩里是真正掌握了相应语言的说话者且是理性的,反思之后他应该意识到这个矛盾(这里,我未加论证假定了正常说话者关于意义的一种认知能力,即说话者对同义性和语言表达基本意义的把握。假定这个原则的一个理由是它在直觉上的合理性,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的这个假定实质上并不比克里普克在构造他的例子中所做的类似假定更强)。这意味着,可能是这么回事,仅仅因为以上的语句是分析的,并因为分析的都是先天的,这一点阻止了佩里诚实地断定“London is not a city”这个语句的否定,从而阻止了信念之谜的产生。 设想有些人仍被克里普克关于“单身汉”之类的词组成的语句不产生信念之谜的结论所吸引,他们也许说,对于所有的分析语句,信念之谜不会产生,且对于所有包含上述第三类词语(“单身汉”、“医生”、“幸福”等等)的句子,无论它们是否是分析的,信念之谜也不会产生。因此,产生信念之谜的可能性独立于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对此类说法,这样的句子是明显的反例,“单身汉喜欢郁金香”,“单身汉喜欢吃苹果”。如克里普克和普特南已经指出的,由含有自然类语词的语句可以构造出信念之谜(限制条件是这些语句并不是分析语句)。进一步设想,这个人可能这样来应对,他说,如果你考虑“单身汉是幸福的”,或“单身汉是自私的”,则情况就会有不同。但是,这些语句仍然不属于可免除信念之谜的语句的集,它在构造一个信念之谜的实例时,所增加的只是困难的程度。同样地,在使用这样的语句构造信念之谜时,不必假设说话者犯了任何语言或逻辑的错误。 此时,这个人可以再走一步,他也许说,“幸福”或“自私”这些词的意义并不像“单身汉”或“医生”那样,是简单和明确的。后一类词是普特南所说的“单标准词”(one-criterion terms)。单标准词的特点是,它能以明确和精准的方式来规定其应用的充分必要条件。⑧于是,他可能建议说,尽管不存在普特南意义上的精准描述来判断“幸福”何时能应用于哪一个单身汉,如果考虑那些只含有单标准词及一些语法上的辅助词或量词的简单的语句,有希望发现支持克里普克想法的结果。现在,考虑语句“每一个单身汉都是一个医生”,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但非分析的语句。此人力图表明,即使是这样的非分析的语句,由于其中所出现的语词的特殊性,也不会产生信念之谜。我对这个提议之正确性持怀疑态度。主要原因在于,我对所谓“单标准词”的存在性有疑问。普特南强调这类语词在应用条件上的简单和明确,我怀疑就应用的广泛可能性来说,会有一种词只能有明确而简单的应用。尽管在语义上可能有一些词只能简单的且准确的定义或约定,但简单而准确的意义,并不等于有简单而准确的应用,更不用说只有一种可能的应用。对于“单身汉”,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它是否是可应用于某类人,比如它是否能在一些语境下适用于老年丧偶的男人(当然它在另一些语境下也许可以),这显然并不是“单身汉”这个词有语义上的歧义。不但如此,英语中的“bachelor”是否能无区别地翻译成汉语中的“单身汉”或“光棍汉”也是一个问题。能否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形成比较确定的规则,本身是一个问题。对于上面的这个论点,即一些由单标准词组成的非分析语句也不能产生信念之谜的论点,我不能宣称我已经有了决定性的理由给予拒绝,而只是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因为,要有进一步的论证,要有关于语义学与使用之间关系的详细讨论。⑨ 我们试图到达的初步结论是:存在着两个语句类,一个是从它们可以产生信念谜的语句类,另一个是不能产生这个哲学之谜的语句类。设想语言L中的语句S属于第一个类,而T是从L到另一个语言L′的客观翻译。通过T,S被翻译为L′中的语句T(S)。对第一个语句类,我们已经发现了与信念之谜的讨论有关的下列事实: 1.无论是在S中,还是在

中,不存在任何语言学方面的错误。 2.此点是可能的,在掌握了所涉及的语言表达的意义后,一个说话者经反思诚实地认可L中的S和L′中的

,而没有对他以前的信念有任何改变。 3.一个根据正常的标准是理性的说话者,在反思后并不认为在他所认可的S和

之间,或两个语句所表达的信念之间,有任何矛盾或语言学的错误。分别在L和L′中的理性的掌握了语言的单语的说话者,在反思后将认为他本人是理性的,且在他的话语中,并没有矛盾或语言的错误。⑩事实上,他诚实地说了

,并在同时拒绝了从S到T(S)的翻译。但使用去引号原则和客观翻译原则的双语观察者将从他在L和L′中所认可的,推出他相信一对矛盾的命题。(注意,在这里主观的翻译原则并不允许客观翻译原则所允许的翻译)。 4.分别正确地掌握在L和L′中相应语言表达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使他拒绝说那将导致矛盾的语句。 与第一个语句类相对照,设想语言L中的一个语句S(属于第二个类,而T是从L到另一个语言L的一个客观翻译。通过T,S[被翻译为L′中的一个语句T(S′)]。对第二个语句类,我们发现了下列不同的事实: (1)必然地,至少在S′或

的某一个中,存在着语言错误。 (2)这是不可能的,掌握了相应语言表达的意义,说话者却在反思后诚实地认可L中的S′和L′中的

,而没有改变他以前的任何信念。 (3)如果一个说话者按照正常标准是理性的,且他分别认可L中S′和L′中的

,那么,他将在反思后认为他自己有一个矛盾的信念,或犯了一个语言的错误。分别在L和L′中掌握了语言的单语的理性说话者,在反思后将承认他本人说了一个在语言上错误的句子,或有一个矛盾的信念。事实上,他并没有说

。他没有说这个语句要么是因为,他对主观翻译原则的使用允许他从S′到T(S′)的翻译,并因此而拒绝说

这个语句(前提当然是他同意S′所表达的),要么是因为他的语义知识使他直接看出

是矛盾的。在这里,主观与客观的翻译原则事实上允许同样的翻译。 (4)有分别地正确掌握所涉及的在L和L′中的语言表达的意义,是说话者拒绝说出那些导致矛盾的语句的充分条件。 假定不同的语词的类不是决定两类不同语句的条件,或者,那些看起来最不可能产生信念之谜的语词所构成的非分析语句都不能避免信念之谜的困扰,那么,一个看起来相当自然的分类应该实质性地相关分析语句与综合语句的区分。因为在使用两类翻译原则时,分析与综合两类语句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和特征,恰好分别符合于上述两组事实。当然,这个自然的结果仍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三、信念之谜的可能性和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存在 如果信念之谜真的是哲学上重要的,那么,在产生这种哲学困惑的可能性上的区分当然也应该是重要的。进一步,如果这个可能性上的区分又最终依赖于或至少密切地相关于另一个长期以来在哲学上充满争议的区分,那么,这就可能为后一个区分的存在及其有意义性提供一种可能的支持。这一步恰是本文希望达到的目标。 根据上一节所得出的那个相当自然的结果,我们知道,不可能产生信念之谜的语句类与所谓“分析语句”的类恰好是外延等同的(这正是在本文开头所给出的断定B在外延意义上的描述),我们应该记得,断定A就是分析与综合之区分合理存在。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想使B比较强地支持A,必须在两者之间有比较实质的关系。根据分析语句与综合语句的不同性质,在直觉上似乎有理由相信A→B。然而,即使A→B是真的,当假设B为真时,也不能决定性地支持A。因此,有理由考虑更强的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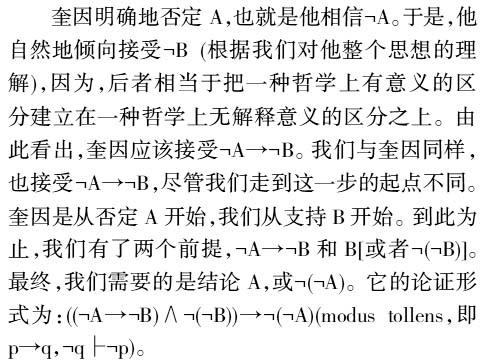
这个论证形式是有效的,关键要看两个前提是否有足够理由。第二个前提是在上节论证过的,在此我们假定论证是有效的,接下来需要的是考察第一个前提是否有好的根据。在我看来,支持这个蕴涵关系的最主要理由是拒绝它会产生解释上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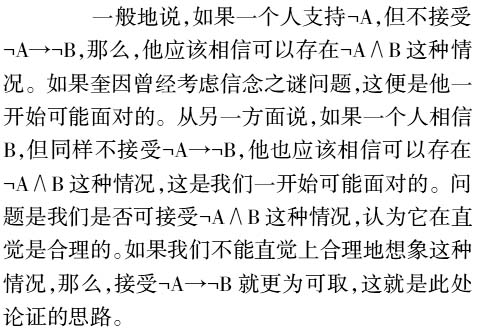
无论如何,想象任何人可以合理地支持

和B同时发生这个信念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一个人认为A是真的,即这里没有分析与综合在哲学上有意义的区分,他就没有恰当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以是否产生信念之谜为划分标准的两个类恰好就是分析与综合两个语句类。外延的同一是偶然同一,可以想象有这种情况,但对信念之谜,说两对概念只是偶然地外延同一,显然并不符合于实际的情况。因为,正像我们在上节的分析中所描述的,信念之谜的产生的可能性确实实质地依赖于分析与综合两类语句在语义上的不同性质。况且,更一般地说,为什么一个在哲学上无意义的区分,却可以说明另一个在哲学上有意义的区分(比如信念之谜或不同翻译原则的使用),这本身就有解释上的困难。 对任何支持

或B,但拒绝

→

的人,他不得不承担这个解释上的重担:为什么分析与综合作为一种哲学上有意义的区分并不存在,但另一个哲学上有意义的区分却实质地依赖于上一个区分核心内容,或者他必须说明分析与综合语句的性质对信念之谜产生可能性的影响只是表面的。为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他不得不努力找寻导致B的某种隐藏的理由或原因,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对这种隐藏的理由或原因是什么有任何最基本的观念。在这方面,接受B并接受

→

的人就轻松得多,因为,为什么B的自然的解释,甚至最好的解释就是:A是真的。尽管A为真究竟以什么具体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了B,细节还是有待补充的,但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给了B一个直觉上自然合理的解释。 四、两个可能的反驳及我的回应 对前面的论证,有两个目前可想到的可能的反驳。可能有人会说,这里的论证依赖于翻译原则的使用,但正如克里普克所说,即使只使用去引号原则,信念之谜也照样可以构造出来,也就是说,使用翻译原则并不是产生信念之谜的绝对必要的条件。我的回答是,翻译原则对于语言使用及意义的表达来说是根本的,它贯穿于语言的解释与理解等的过程中。尽管,在许多时候,翻译原则在表面上不起作用,也没有通常的翻译发生,但并不等于在此时翻译原则完全是无关的。在克里普克关于皮特和帕多夫斯基的例子中,只有一个语言被涉及,而且对同一个人只有他的名字本身出现,并没有它在其他语言中的任何翻译被涉及。在此时,为构造信念之谜,“只有去引号原则明显地被使用”。(11)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把这种情形理解为发生了在同一个语言中的翻译(homophonic translation)。像克里普克本人也同意的那样,只有一个语言相关的这种情况,完全与原来伦敦和佩里例子中的情况并行,同样,两者中的问题也是并行的。(12)如果皮特和帕多夫斯基的例子只是原来有翻译原则介入的那类情况的特例,并无本质不同,那就没有理由相信会有本质上不同的分析和结论从这个特例中得出。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可能的反驳。索萨声称,“信念之谜是一个本质上的弗雷格歧义”。(13)如果替代克里普克的去引号原则,我们使用具有去除歧义功能的新原则,或者,替代有歧义的名字,我们使用不同的名字代表不同的弗雷格涵义,则信念之谜就不会产生。于是索萨坚信,信念之谜只是穆勒主义(Millianism)的结果。(14)类似地,W.塔什克(W.Taschek)也倾向于把信念之谜归结为某种特定的、不正确的哲学立场的结果。如果坚持弗雷格的涵义概念,则不会有信念之谜来打扰我们。(15)如果此二人的说法是对的,信念之谜就只是表面的困难,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难题,或者需要哲学来处理的重要现象。当然,如果此二人的说法是对的,本文所做的工作就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就是想通过一个有意义的哲学难题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内在关联,来说明分析与综合区分可能的合理存在,如果所说的哲学难题本身只是一种错误理论下的幻觉,那么,它与另外的哲学问题的关联的存在性和有意义性将失去基础。这肯定是一个更实质性的反驳。我的回答归结为如下三点。 第一点,提出质疑的人所依据的弗雷格主义,本身与穆勒主义相对立。尽管我在基本精神上也许赞成弗雷格的语义学,但毕竟两个对立理论的对错仍是没有定论的。即使他们的论证是对的,其结论也是有条件的,即如果弗雷格理论是对的,信念之谜就不会产生。由此可见,这个反驳由于其所依赖之条件是否成立尚存在争议,至少在目前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第二点,克里普克的信念之谜尽管描述了一种看起来令人困惑的情形,但在这个描述中,克里普克并没有使用一些直觉上奇怪的准则。他对理性的人,对掌握语言(语言能力),对诚实性等等概念都没有特别新奇的理解。尽管不能说这些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确实具有直觉上的基础。因此,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强的理由断言他所描述的情形是肯定不会发生的。相比之下,日常说话者完全掌握弗雷格意义,即使弗雷格本人也不要求的。因为弗雷格明确知道,对日常语言,这种要求通常并不能实现,比如对“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日常说话者会有五花八门的理解。这部分的原因可能在于日常语言并不是一种完美的语言,(16)也许还要加上日常说话者大体也确实不是“完美的”说话者。至少,索萨等等哲学家对日常说话者的要求,并不会比克里普克的假设更接近真实的语言现象。这就是在全文的论证中,我们并没有要求比克里普克的条件(关于理性、关于理解、关于掌握语言等等)更高的条件的部分原因。 第三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一个日常说话者真像反对者们所要求的那样,掌握了有关语言表达的独一无二弗雷格涵义,且假定他们是理性的,并愿意遵守P.格赖斯(P.Grice)的那些会话准则,当然就不会有信念之谜产生。这就如同日常认知者如果都满足笛卡尔对确定知识的准则,就不会产生怀疑论者的诉求一样。也许,我们不需要否认,索萨的去引号原则(the principle D’(17))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信念之谜的产生。尽管如此,信念之谜的关注之点,或者说他引起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什么资源对于防止信念之谜是足够的,而且如果它所描述的情形真的可以发生,或者这个谜是真正的哲学困惑,怎样去解释它。显然,日常说话者并不满足索萨等人所设定的条件,比如知道弗雷格涵义,并因此知道翻译与被翻译者之间的同义性。但即使如此,只是分析语句,两个翻译原则将导向相容的判定,同样的说话者就不会去说那些有可能导致信念之谜的相关的否定语句。因此,我们的分析和结论并不建立在假设理想说话者的基础上,而是在日常说话者的基础上,也许大多数分析语句存在的拥护者将更看重这样的论证。正像我们不能通过说,如果人们满足笛卡尔的知识标准,怀疑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难题,来否定怀疑论的哲学意义,我们同样也不能通过说,如果人们满足索萨等哲学家的标准,信念之谜就不会产生,来否定信念之谜的哲学意义。 虽然索萨对于说话者关于弗雷格涵义的认知要求不是普通说话者,甚至不是那些使用分析语句的普通说话者所满足的,但他的质疑使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可能分析语句具有的先天性质,是阻止信念之谜产生的关键要素。于是,P.鲍格西安(P.Boghossian)关于认识论分析性的理论有可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发掘B为真的理由。但由于本文有限的目标,我们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18) 五、结论 本文的第一个结论是,存在着一些语句,信念之谜不可能由它们产生。并且,如果以产生信念之谜之可能性为划界标准,那么可准确地区分两个不同的语句类,一类正好是分析语句的类,另一个是综合语句类。由第一个结论和一个直觉上合理的前提(即如果没有分析与综合在哲学上有意义的区分,则也不会有以同样区分为基础的产生与不产生信念之谜的语句集的区分),第二个结论是,在信念之谜真的是一个有意义的哲学之谜的假定下,那么,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哲学区分。自然,我们可以看出,最终的结论导向了一个关键的哲学争论,它给了想要拒斥奎因之否定结论的人一个可能的支持。 注释: ①S.Kripke,“A Puzzle about Belief”,in Meaning and Use,Avishai Margalit e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250. ②Ibid.,pp.248-249. ③克里普克本人认为含有自然类语词的语句也可以类似地产生信念之谜,见S.Kripke,“A Puzzle about Belief”,pp.264-265;并且普特南给出了一个例子,见H.Putnam,“Comments”,in Meaning and Use,Avishai Margalit e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p.285-286。 ④S.Kripke,“A Puzzle About Belief”,pp.260-261. ⑤Ibid.,p.262. ⑥S.Kripke,“A Puzzle about Belief”,p.264. ⑦S.Blackburn,Spreading the Word:Groun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larendon Press,1984,p.338. ⑧H.Putnam,“The Analytic and the Synthetic”,in Mind,Language and Reality,Philosophical Papers,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67. ⑨见拙著《语言、意义、指称——自主的意义与实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⑩D.索萨(D.Sosa)认为,对克里普克论证具有实质意义的是这个假设,在佩里及其他类似例子中的行为人是理性的。见D.Sosa,“The Import of the Puzzle about Belief”,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105,no.3,1996,p.373。 (11)S.Kripke,“A Puzzle about Belief”,p.266. (12)Ibid.,p.266,而且,克里普克也在同一篇文章中明确说道:“即使我把去引号技术只使用于英语,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可以被认为隐含地援引了翻译原则,也见S.Kripke,“A Puzzle about Belief”,p.251。 (13)D.Sosa,“The Import of the Puzzle about Belief”,p.396. (14)Ibid.,p.401. (15)见W.Taschek“Would a Fregean be Puzzled by Pierre?”,in Mind,vol.97,no.385,1988,pp.99-104. (16)见G.Frege,“On Sense and Reference”,in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second edition,Peter Geach and Max Black eds.,Basil Blackwell,1960,p.58,以及该页的注释。 (17)D.Sosa,“The Import of the Puzzle about Belief”,p.395. (18)鲍格西安关于认识论分析性的论述,可见P.Boghossian,“Analyticity Reconsidered”,in

,vol.30,1996;“Analyticity”,in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Bob Hale and Crispin Wright eds.,Blackwell,1997。
标签:信念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语言描述论文; 郁金香论文; 伦敦论文; 佩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