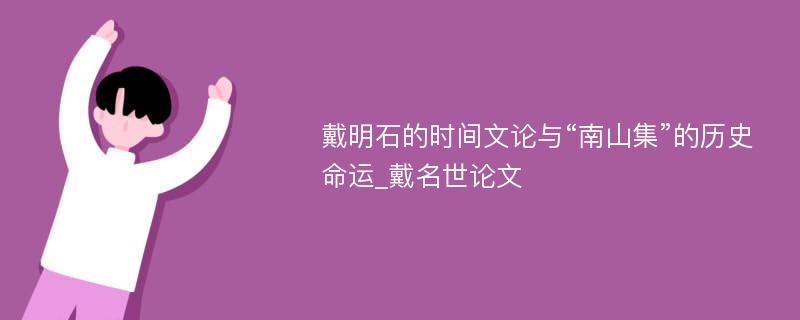
戴名世的时文观和《南山集》的历史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山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戴名世论文,时文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4)01-0053-05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戴名世和他的《南山集》更多地被与康熙年间那起轰动全国的文字狱案联系在一起,而作为文学的《南山集》和它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阅读这部历经风雨后残存下来的文本,就会感到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像戴名世的遗民情绪、民族情结、对清王朝的大不敬等等,至少在今天的残编中要找到蛛丝马迹是非常困难的。晚清学者陈衍即表示了对戴名世遭文字狱一事的困惑:“康熙间,桐城戴名世《南山集》之狱,论者冤之。曾翻其全集中,并无可罪语。或曰,以《孑遗录》命名得罪也;或曰,即为‘南山’之名,取义雄狐,刺内乱故也。然余尝为马通伯跋名世墨迹诗册,乃送其师张相国予告归里者,五言古八章,所言亦太无顾忌矣。”[1]陈衍认为,从这八章诗看,其中表露出的对功名富贵的蔑视,即已经触清王朝之大忌而足以构成文字狱。虽然陈衍所引戴名世诗之来源不明,现存署名戴名世的《古史诗箴》当为伪托,但陈衍所指出的避世、愤世心态在文字狱中的作用确实是值得注意的。“南山”,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陶渊明和他的南山,想到戴名世屡屡提及的醉乡、睡乡、忧庵、褐夫等等而非“雄狐”。
一、时文与古文:话语表述和精神象征
戴名世生于顺治十年,明清易代之时17岁,已足以体验亡国哀痛,特别是祖父辈的言行,对戴名世必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曾祖遭逢国变,薙发为僧,隐居龙眠山而终,而其父将难言之遭遇,发为悲怆沉郁之诗文,甚至有“吾死,祸必及子”之谶语。[2](卷1)除了《孑遗录》,戴名世的《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等文也都对明末抗守之事作了详细的记载。虽然这些文章采用的是大清的年号,将亡国的责任主要推到像阮大铖这样的奸臣,钱谦益这样缺乏气节的文人,以及所谓的“流贼”身上,但在对扬州之难的叙述中,在对史可法的崇敬中,仍隐隐可见作者的民族情感。他为明朝皇帝开脱罪责:“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将明王朝之灭亡归于冥冥中的天命[2](卷13)。在游记散文《兔儿山记》、《游西山记》中,戴名世想到了繁荣承平时期的明王朝,想到了那个时期的君主。在一系列文章中,他表彰了在明清之际保持忠节的大臣甚至平民。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作过于夸大的理解。实际上,所有这些都与文人情怀的抒发联系在一起,出于文人维护道统的责任感,文人失志的哀痛以及由此引发的愤世嫉俗。而所有这一切,戴名世都以时文和古文的对立概念表达出来。
在戴名世的文章中,时文与古文是两种观念的表达。戴名世承认自己也写过制义之文,而且他的时文还受到时人的推崇,但他一再表示自己写作时文只是偶一为之,而且是为了教授生徒以糊口[2](卷4)。他的本愿是成一家之文,而要成一家之文,首先要遵守圣人之道,“余之为是也,非苟易也。根柢于先儒理学之书,未之敢失也;取裁于六经诸史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未之有遗也。”[2](卷4)而时文显然是无法负载如此重任的。虽然古文与事功之间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毕竟古文还接近于学。而所谓的学,具体地说是“辨道术之邪正,明先王大经大法,述往事,思来者,用以正人心而维持名教也”,“彼时文之士,制科之徒,曾有一于此乎?”[2](卷3)因此为时文甚至不能称为读书,所为之时文也是臭败不可近。他比较古文与时文说:“夫文章之事,学问中之小者,制举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2](卷1)
但是戴名世对时文如此深恶痛绝,除了由于时文的空洞无物,时文的臭腐不可近,主要还是因为时文与世俗功名的紧密联系。很多富有经世才能的文人由于不善于场屋之文或者由于场屋衡文准则的偏颇而郁郁终生。那些一时侥幸以制举之文发家的无德无才之人却高居上位,居然以学者自居,而世俗之人也竟然认为侥幸中举者是真正的读书种子,这必然使得像戴名世这样的怀才不遇者难忍心底的伤痛。“世俗之人第从事于时文,以期得当于制科。久之,果得当焉,则众相与贤之,以为是人也读书于是乎为有成矣。”[2](卷4)于是“士之研精覃思从事于场屋之文以应科举,其得之者,往往登高第为大官,流俗之人相与艳羡之。”[2](卷4)而获取官位者,惟一关心的只是世俗的虚名和富贵,儒家济世的理想主义精神显然是他们不关心也不理解的。况且,就制举文自身来说,“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2](卷4)因为有司衡文准则之失,天下之正味遂不入于考官之口,“谁实为之,而使羊之皮得施于首而驴之足得独骋于市也。贵者贱之,贱者贵之,而所举之士其中遂多有为世所耻笑鄙夷而不足齿者。”[2](卷4)
时文的盛行和腐朽被与世风的衰朽联系到一起。戴名世将自己穷愁的遭遇归因于世风的败坏:“余生抱难成之志,负不羁之才,处穷极之遭,当败坏之世。”[2](卷1)在这样的时代,诗文也不能不衰亡。甚至认为“世道之敝,不复有有志之人生于其间”[2](卷2)。在这种靡败的世风中,“礼义仁让先废于士大夫之间”[2](卷3),士人所为之文也就理之全无。戴名世无奈地说,他不幸生在这样一个“天下弃学”的时代,“世所谓学,不过呫呫讽诵,习为科举之业,曰‘是乃学’而已,此学之所以废也。”他有志于明道,尽到了一个儒者的责任,至于不为败坏之世所用,那只能是此世的不幸,“非儒者之命之艰也”[2](卷3)。世风的败坏和时文的兴盛与真文章的失传紧密相关,他注意到了浙江黄岩一带的文风至清代已经衰微已甚,而“沿至于明兴,而流风余韵犹有存者。”[2](卷4)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当时之世已经是“大道沦散”。文风的败坏与士人的堕落有关,而主要表现为文章与名利富贵的紧密关联,而文体也必然随之败坏不堪。他由诗文的命运预言了世道的最后覆亡:“呜呼!世之学为文为诗者,举未有能读书者也。不读书而乾坤或几乎息,其荒芜榛莽而不可救者,又岂独诗与文为然哉!”[2](卷2)
据戴名世说,即使是时文自身,在清代也走向了衰败。八股时文产生于明代,至于经义文则更早。但前代经义文和论并重,而至清代经义文之腐烂渐及于论,“于是乎经义与论且同归于臭败而后已”[2](卷4)。前代君子如归有光、艾南英亦写时文,但“君子者,沉潜于义理,反复于训诂,非为举业而然,引申触类,剖析毫芒,于以见之于举业之文,实亦有与宋儒之书相发明者。”[2](卷4)戴名世认为明代文章盛极一时,“当其设科之始,风气未开,其失也朴遬而无文。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来,趋于文矣,而其盛犹未极也。”而自天启、崇祯之后,文愈变而愈下,至清则已经臭腐不堪卒读。他解释“时文”之意:“制义者,与时为推移,故曰时文。时之所趋,遂成风气……于是乎数十年而变,或数年而变,或变而盛,或变而衰,往往相为倚伏。”[2](卷4)而清代正是其衰微之时。
在戴名世的叙述中,古文和时文是他独特的话语表述形式,成为两种精神的象征,同时是时代风气和文运的表征。像他自己这样具有经世志愿的文人,要通过对文运的挽救来挽救世运,但这种努力和自信只能使他陷于孤独。他感叹“当今文章一事贱如粪壤”[2](卷1),他的独到的文章“不悦世俗”,其蔑视世俗的自傲引起时文之徒的嫉恨。他感慨万千地说:“仆茕茕一书生耳,年少身贱,而慨然有志于文章之事,其见恶于时文之徒且十余年于今矣。”[2](卷1)他将那些得意的时文称为“紫色蛙声”,把那些所谓才士对真文士的嫉恨称为腐鼠之嚇:“今之所谓才士者,吾知之矣,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间,而世之论才士者必归焉。今之所谓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时,便佞也而喜其适己,狼戾阴贼也而以为有用。士有不出于是者,为傲,为迂,为诞妄,为倨侮,而不可复近。”[2](卷5),面对这样的形势,深感“悠悠斯世,无可与语”的戴名世“绝意交游,自甘废弃,思古人而不得见,往往慷慨悲歌,至于泣下。”[2](卷5)
戴名世之所以如此慷慨泣下,是因为从文章的遭遇中,感到了士人命运的悲凉。这种文运的衰落,具体表现在士人地位的衰落,士人品格、尊严的丧失,而最后是原始儒家精神和责任感的丧失。在堕落斯世,正直士人济世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是如此脆弱。为了生计,即使是最具责任感的文人也不得不放弃或搁置了理想。这种崇高理想与卑微现实的矛盾,使得像戴名世这样的文人时时遭受心灵的煎熬。戴名世承认自己难以“穷而不怨”。他甚至从《易经》中看到了作者的忧患,而称其为抒情之书:“大抵贤人君子,遭世末流,胸有郁勃感愤,借《易》以致其扶阳抑阴之意,是亦出于忧患之所为也。”[2](卷3),戴名世分析了士人治生艰难的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故读书之士所以治生者,舍树木无他策焉。”[2](卷3)在这样的时代,已经没有王公大人愿意供学者资用以使其极意于学了,像扬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后之学者,其所遭之变,所遇之时,不同于古之人者多矣,然则余且抱无涯之志而莫之遂也。”[2](卷5)这样的感叹是基于自身的切身感受:“余脱身游,或教授生徒,或卖文制碑,东西奔走,何啻二三万里。所与士大夫交游颇多,然无度外之人为一悯其穷而援之者。”[2](卷10)在这样的时代,卖文谋生已是不可能了:“今且世事愈变,文章更无所售,虽狡谲谀佞之徒皆易术以去,而余抱区区无用之学,举世不知之技,以浮沉于游士幕客之间,所谓操隋侯之珠而以弹雀者也。”[2](卷11)当戴名世想到自己年近五旬,仍无数亩之田可以托身,只能佣书客游,闭门著书之志可能无法实现时,慨然至于泣下。他由迫于生计冒亏折之险改而经商终潦倒终身的文人身上想到了文人的孤独和窘迫:“噫吁嗟乎!士而贾兮,叹世态之纷纷,吾求士于吴之市兮,谁与怀古道而轶群。”[2](卷9)他将士人的厄运归于所谓的天道或天命,而所谓的天命与士人之命的关系是:“世之盛也,天下之命生则君子生,天下之命富贵则君子富贵。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命为命,而以天下之命为命。苟其不然,则君子死,则君子贫贱。君子死而小人必生,君子贫贱而小人必富贵。小人生而天下皆死,小人富贵而天下皆贫贱。此如阴阳寒暑不可假易,出于自然之理,一定之数,而莫之或爽者。”[2](卷15)在《笔赞》中他更直接地说“我生不辰”。
在这样的情势下,戴名世这样的文人怎能不佯狂歌哭?戴名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忧庵”,他解释说:“五行之乖沴入吾之膏肓,阴阳之颠倒蛊吾之志虑,元气之败坏毒吾之肺肠。纠纷郁结,彷徨辗转,辍耕陇上,行吟泽畔,或歌或哭,而莫得其故,求所以释之者而未能也。”[2](卷14)而这种“忧”是无法解释的。他对刘伶、阮籍等人于醉乡中解忧表示怀疑:“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其有忧焉,抑亦不必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所以戴名世也就不打算向醉乡中寻求解脱,而天下之人却都入于醉乡,“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像戴名世这样的“不入而迷者”反而受到这些荒惑败乱的真正的醉乡之徒的嘲笑。戴名世希望的是真正的解脱,在他看来,甚至庄子的蝴蝶之梦也过于纷扰了。戴名世表示要学习陶渊明,做一个真正的隐者:“余久怀遁世之思,嗟宇宙无所为桃花源者,何以息影而托足!”[2](卷10)但即使有蓼庄这样的世外桃源,戴名世也无法实现自己的隐居之愿,直至垂暮之年,买山而隐也还只能是一个模糊的梦:“呜呼!余怀遁世之思久矣,辗转未遂,至是垂暮无成,万念歇绝。他日人见有衣草衣,履芒鞋,拾橡煨芋而老于此间者,必余也夫,必余也夫!”[2](卷10)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心中虚构一个桃花源:“岁几更欤,代几变欤,不知也。避世者欤,避地者欤,不知也。主人失其姓,晦其名,何氏之民?曰无怀氏之民也。其园为何?曰意园也。”[2](卷14)
二、以时文为古文:文化意蕴与个人悲剧
戴名世的所有感慨几乎都与他的时文理论紧密相关,他甚至认为只有消灭时文才能光大儒学,挽救世风。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戴名世调和的努力,毕竟他生活子斯世,需要有所依托。戴名世一方面对时文进行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努力将时文纳入古文的范畴,争取给时文一席之地,那就是所谓的“以古文为时文”:“夫所谓时文者,以其体而言之,则各有一时之所尚者,而非谓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为之也。今夫文章之体至不一也,而大约以古之法为之者,是即古文也。故吾尝以谓时文者,古文之一体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为时文,此过高之论也。’其亦大惑矣。”[2](卷4)所谓“以古文为时文”就是指以古文之法代替时俗的八股文法,而其真髓是以古文之法发明圣人之道。戴名世进一步论述说:“今夫文之为道,虽其辞章格制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此自左、庄、马、班以来,诸家之旨未之有异也,何独于制举之文而弃之!”[2](卷4)他将时文之法概括为三点,即道、法、辞。基于这样的理解,戴名世干脆把写作古文的经验教给那些向他请教时文作法的后学。
戴名世的“以古文为时文”一方面是出于文人责任感的挽救文运的努力,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与时俗的妥协。但是这种适应世俗社会的努力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困窘的境遇使他变得愤世嫉俗,疏远世俗社会的主流,而这种疏远和旁观者姿态的批判,又使得他难以改变困窘的境遇。如此形成潜在的恶性循环,使戴名世最后走向与时俗的对立。这种与时俗的妥协直到戴名世的同乡好友方苞的后期才取得了成功。从方苞及其后继者的古文理论中,可以看到时文与古文交融的痕迹,更可以看到戴名世的影子。如言之有物,文品与人品,文章与精气神,文章与抒情,文章与义理,文与质,文与魂,文章与训诂,文与法等等桐城派文章家反复阐述的理论,戴名世都有初步的论述。戴名世以道家的精气神概念论为文之道,“精”即删削尽糟粕、煨烬、尘垢、渣滓以及邪伪剽贼,而只余雅与清;“气”指充塞于两间,洋溢与文章之外的浩然正气;“神”则“出乎语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径之先”,“寻之无端而出之无迹。”[2](卷1)他将“言之有物”视为为文之根本,所谓“物”何指?“夫有所为而为之之谓物,不得已而为之之物,近类而切事,发挥而旁通,其间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谓物也。”[2](卷1)他注意到了方苞文风之转变,由“发扬蹈厉,纵横驰骋”而转为“收敛才气,浚发其心思,一以阐明义理为主,而旁及于人情物态。”[2](卷3)他将“义理”和“训诂”并提:“君子者,沉潜于义理,反复于训诂,非为举业而然,引申触类,剖析毫芒,于以见之于举业之文,实亦有与宋儒之书相发明者。”[2](卷4)戴名世解释“理”说:“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今夫天地万物莫不有理,文也者为发明天地万物之理而作者也。”[2](卷3)质与平受到戴名世的推崇:“质者,天下之至平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夫为文而至于质且平,则其品甚也,于奇求奇者非奇也。”[2](卷3)文章有魂:“凡有形者之谓魄,无形者之谓魂。有魄而无魂者,则天下之物皆僵且腐,而无复有所为物矣。今夫文之为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谓魂者,出之而不觉,视之而无迹者也。”[2](卷3)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戴名世将为文之要归纳为道、法和辞。“道”具载于四子之书,可参考宋儒的阐释;“法”包括行文之法和御题之法。所有这些,在桐城派主将那里都有详尽的论述和具体的实践,是戴名世和方氏父子的切磋为桐城派作了意义深远的铺垫。但是,戴名世和后来的桐城派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比如桐城派的旗帜“义理、考据和辞章”在戴名世那里已经初具雏形,但与桐城派不同的是戴名世对训诂考据又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儒学“乱于鄙夫小生之训诂与科举之业”[2](卷3),将训诂和举业一起称为俗学[2](卷15)。显然,戴名世对考据学的轻视源于对流俗的对抗,因为训诂学已经和举业一样,有渐成致功利富贵之手段的趋势。而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将理学意义上的义理、渐成流行之势的考据学以及辞章之学融合为一,也显示了适应时俗的倾向。在桐城派的后继者身上,个性、自我体认的自觉与世俗之间的矛盾仍然会以不同的形式在文章理论和实践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激烈的程度已经远远逊色于戴名世了。
以时文为古文的调和努力的失败,促使戴名世对儒学采取一种矛盾心态。这里有必要谈谈戴名世的思想。戴名世对佛教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自孔子没而出而惑世诬民者有两家,曰老,曰佛”,其中老子之言颇有可采,庄周、列御寇之流实际上是一些“悯世之昏浊,为呫洋自恣以适己志”的文人学士,相比之下佛教更为浅陋惑人。然而他又表示,相比之下,宁愿与浮屠氏游而非儒者。他解释这种矛盾的举动时说,当世的所谓儒者或“相与叛圣以媚佛”[2](卷3),或“剽窃餖飣,背义伤道,汩没其中而不知出”[2](卷4),皆“龌龊无可当意”,他自己这样的真正儒者自然要受到当世所谓儒者的畏恶。戴名世显然是以儒家正统传承者自居,他检点前代的儒学,对欧阳修的从祀圣人孔子表示怀疑,对从祀的王守仁、陆九渊更加以批判[2](卷15),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儒家学说的精髓,甚至走向了背叛。戴名世认为,儒家学说的精髓应该是经世,所以他称赞不从事于科举而对阴阳、历数、乐律、兵法之类皆穷其元本而臻其微妙的刘继庄为真正的读书种子[2](卷5),对当世儒者轻忽关系民生经济的算数之学表示不解[2](卷5),还认为《易经》实际上是圣人经世之书。
戴名世自诩为韩愈文统和道统的继承者,“数千年而得韩愈,又千年而得先生。”[2](卷15)然而在这个文运、道统日益没落的时代,正统儒者只有穷愁潦倒。他感慨说:“以道之衰,而人情之陷溺也,天下方且在呻呼啽呓之中,而一二羁穷少年,枯槁老衲,相与痛哭于山砠水涯之间,事故有不可解者。”[2](卷5)他由文章、诗歌的衰落推导出世道的败落,称所处之世界为“败坏之世”,反复强调自己为微子之后裔[2](卷3),而他自己不幸也生活在如微子时的“大道沦丧”的时代。他说:“是故讲章时文不息则圣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扫除而更张之无疑也。”[2](卷5)又说:“是近在中国之内,辟地万里,胥标枝野鹿而衣冠文物之,是在命世之王矣。”[2](卷15)言外之意,真正的王者或命世之王还没有出现。这无疑是对清王朝正统地位的怀疑,这才是深触了满人之大忌。
戴名世的悲剧实际上是一个士人的典型悲剧。他对世运和文运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固执地坚守儒家的正统,将文运置于世运之上。在他看来,文风不仅是社会治乱的表征,更直接决定了时运的兴衰。所以他将文学作为批判社会的工具,对为统治者所认同的、千千万万士人浸淫于其中的时文作无情的批判,并进而将矛头指向凭借时文得以显名的官僚,把自己摆到了堕落文人、官僚和八股取士制度的对立面。这种文化精英的姿态,加上天生的为困窘境遇所加强的孤傲,成为他立身于败坏世道的精神支柱。那些以时文而侥幸的官僚士大夫们眼见着戴名世“沉沦于千寻之渊,鲸鳄之窟,而水族万怪争来吞噬”,竟然吝于伸出援助之手[2](卷1),这让戴名世对悠悠斯世彻底丧失了希望。他对官僚士大夫将爵位权势带进文章之学表示强烈的不满,嘲笑他们的文章将很快臭腐,指责身居高位者不能挽救文运,不能树立真正的功名,只知道博取富贵和虚假的名声,讽刺堕落文人的依阿苟且,讥刺士大夫的无知和无耻,如此等等。戴名世实际上是以个人的力量对抗整个官僚社会。虽然戴名世自己所说的受天下人嫉恨可能有所夸张,但引起很大一部分人的反感是毫无疑问的。都御史赵申乔参戴名世的罪名是:“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这种指责显然是有的而发,有感而发。穷困潦倒的境遇加强了他的愤世嫉俗心态,促使他走向和社会的对立,而他的以古文挽救世运的理想也就成为泡影,他只有叹息“我生不辰”,将满腔的悲愤化为更强烈的批判。他将毁坏世风的时文作者比作学舌的鹦鹉,预言它的覆亡,“一旦摧残,觅家不在。”[2](卷15)不幸的是,鹦鹉日耀其光彩,而真正遭到摧残、人亡家破的,却是这末世的凤凰。
收稿日期:2003-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