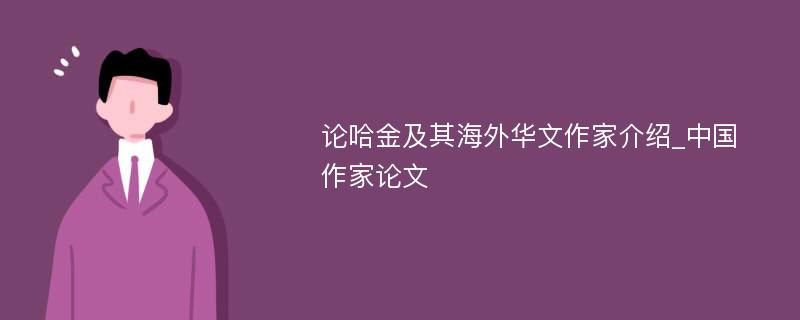
谈哈金并致海外中国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作家论文,海外论文,谈哈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华人新移民在北美、澳洲、新西兰等地急剧增加,从他们中间涌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作家。这些“第一代华人新移民作家”不同于新、马、泰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作家”,他们前半生在中国度过,移民后或加入所在国国籍,或继续持中国护照,绝大多数坚持或只能用中文写作,写中国事情,谋求在大陆及台、港、澳三地发表,许多人因为在居住国的“文化悬空”处境而自愿认定是“中国作家”。他们和国内作家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移民”身份(有的已经在90年代后期回国)。对这一群体只能以“中国作家”视之。这里的“中国”不单就国籍而言,亦不限于“文化中国”范畴,乃是国籍和文化的杂糅。
哈金也是“第一代华人新移民作家”中的一个,但他的情况有些特殊。迄今为止,他主要以英文发表作品,能够和所在国文化界沟通,为所在国读者和文坛广泛承认并获好评,其作品目前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以“翻译外国文学”——“美国文学的一员”——被介绍进来。因此,他的身份有些复杂,你也可以说他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但我不知道大多数美国读者是否仅仅将他视为美国作家,也许不太可能,因为哈金基本只写“中国人的故事”,而让美国人假装“忘记”他的中国背景恐怕也难。
哈金1956年出生于辽宁,服军役六年,先后在黑龙江大学、山东大学获英语专业学士、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他在中国生活了30年,完成了从小学到研究生的漫长学业。哈金敬佩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在他这个年龄已经完成了不朽之作《都柏林人》,形成了终生不改的人生观与个性。如果哈金对乔伊斯有足够认识,对作家这个行当有足够自觉,应该不会夸大赴美后学习、工作与创作在形成其基本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哈金的书全写中国,中国的军队与军人,中国的乡村与农民,中国的城镇与市民。小说中的时间则从童年(60年代初)直到80年代中期。
从哈金自己的立场来看,2005年初他发表了《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清楚表明他渴望——至少十分愿意——和众多“中国作家”对话,“不管人在哪里”,都希望和全体中国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齐追求“伟大的中国小说”,一同争取“中华民族的主要作家”的桂冠。[1] 所以,至少在目前,说哈金仍然是一个中国作家,大概没有问题。
怎样看待作为中国作家的哈金呢?
首先,哈金很忠实于自己在中国的生活,试图真实地记录在作品里。就我看过的最好作品《等待》、《池塘》来说,他也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度:因为忠实地收集了记忆的残片,清楚地记录了生活的一角,从而让读者由此及彼,联想到比作家记录的那一角更广阔的中国生活的其他方面。
但包括《池塘》和《等待》在内,哈金的小说,一般都不具有我们在读杰出文学作品时经常遇见的内涵丰富的神秘性,那种不妨称之为“意义的黑洞”的东西。他的“中国人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但也只是传奇而已,而中国又是最不缺乏传奇、逸事、趣闻的国度,中国读者早就在乘火车蹲马桶时被这类东西喂饱了。哈金那些可以让美国人惊讶的精心之作很难触动中国读者。他写了我们熟悉的故事——以美国作家班培养的一丝不苟有板有眼的笔法写来——却没有在此之外提供我们不熟悉的、足以触动我们、震撼我们的东西,那种超出“中国人的故事”之外或蕴涵于这些故事之中的审视中国的别样的目光和心地。哈金的英文到了可以用英文写作甚至可以每年用英文教美国孩子写作的程度,他本应该提供给我们这些内容,而不必费老大劲累巴巴地从美国出口转内销,述说一篇又一篇国内读者早就熟悉的、略无余味的“中国人的故事”。
有种看不见的东西将他一丝不苟描写的“中国人的故事”包裹起来,使得我们只能就故事看故事,不能发生额外的联想。故事写得中规中矩,清晰,准确,生动,主题鲜明,用一句话就可以完整无误地概括。向别人转述哈金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一桩省力的事。《池塘》写基层领导粗暴野蛮,个别怀才不遇的人有理有力有节地进行反抗;《等待》写某些单位和地区的特殊政策与风俗习惯十八年如一日阻拦无爱的夫妻离婚、相爱的男女结婚,当事人在旷日持久的等待中被扭曲,以适应典型的中国生活的规则。中短篇小说就更简单了。中篇《纽约来的女人》、《牛仔炸鸡进了城》反复暗示的无非是中国老百姓对非我族类的可笑的歧视。另一个以唐山地震为背景的关于偶合家庭的中篇,内容全隐括在标题“活着就好”里面了。讲述苏童、余华式的乡村少年成长经历的《皇帝》的结尾,则有这样的“总结陈词”:“一年过去了,我们一个个离开歇马亭,去为各式各样的皇帝效劳”……简单得可以,不留一点空白。
哈金在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挑选细节、避免重复等方面确实懂得节制,不乱套,不含糊,不让你觉得别扭或不知所云。但缺乏余味,主题简单直露,也是这种笔法必然的结果。
再如风景描写,这在哈金小说中是“体制性的”。每当人物遭遇某种困难,每当小说叙述即将“出戏”,哈金总要让人物——也让读者——将视线从具体情境挪开,欣赏一段他准时奉献的风景描写,好像足球比赛的中场休息。这些风景描写与故事情节不相干,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他的思想和文字顿时“跳出来”了,即不再拘泥于具体情境,可以将读者带到一个高层次。这样的风景描写,偶一为之还真有点神来之笔,但一而再再而三,在应该“跳出来”的地方千篇一律来上那么一段似乎大有深意其实毫无意思的貌似超脱的风景描写,性质就变了:变成不折不扣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变成一味搪塞。
哈金作品“隐含作者”的意识水平和故事中的人物若即若离,甚至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哈金作品“隐含作者”和小说人物的眼中看见的,无非就是6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人的意识。收在《好兵》里的中篇《辞海》结尾写书呆子周文转业时,一直保护他的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梁部长”送给他一支笔和一番勉励的话,周大受感动,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豪,挥动革命之笔,战斗终生”。隐含作者自然不等于周文,但隐含作者始终不出场,并非反讽叙述的需要,因为直到故事结束,除了“写实”,并无一点反讽气味。隐含作者的不出场只是因为没有出场的必要——他没有什么和人物不同的特别的意识需要投射在小说叙述中。这就是哈金的问题。他的故事陈旧,意识也一样苍白——基本和书中人物没有拉开距离。
我从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的《光天化日》中选出《新来的孩子》、《皇帝》,从《新郎》中选出《武松难寻》、《破》、《旧情》,从《好兵》中选出《空恋》、《辞海》和《证据》,我以为是比较好的作品。① 在这些中短篇小说中,哈金表现了底层中国人的善良与忍耐、卑微地对生活的盼望,常常被捉弄的可怜的爱情,以及出奇的愚昧、迷信和残忍。但除了哈金特有的稳健、简捷和清晰的笔法之外,他开掘这些主题时所达到的深度远在方方、余华、苏童、朱文、韩东之下,而方方、余华、苏童、朱文、韩东的笔法乃是这些作家暗中摸索的结果,很少一成不变的体制性因素,其中显示的才华气质,不是哈金平淡无奇的文字可以相比。
无论对中国当代生活的体验还是“笔法”本身,哈金如果脱下美国货(英文写作和美国作家班的笔法)的外壳而和国内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无优势。
说哈金没想法,当然不是向他要求思想家的思想,而是指他的故事无法为我们提供看待中国生活的新角度并由此发现中国生活的迄今尚未发现或尚未说出的问题。他只会“写实”——美国学者赞扬他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坚持古典的写实作风——却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把思想的探针伸向实际生活之外,来一点灵魂或艺术的冒险。收在《新郎》中的《武松难寻》我觉得是他最好的短篇,他写中国人不讲道理,自己差不多也有点不讲道理了。但最后他还是要讲道理,把一切都驯服在简单的、美国读者一望可知的道理上。也许,他怕他的不讲道理会让美国人吃不消?还是他根本就没有“不讲道理”的本钱?
他以坚实的写实基本功描绘了不少“中国人的故事”,力求结构完整,细节丰富,贴近自己的生活记忆。除了简单直露没有余味这个基本缺点之外,在叙述的技术上面,还真难找到他有别的什么明显缺陷,这就足以让他和那些一跑到国外就以为可以瞎写一气的“第一代华人新移民作家”拉开很大一截。哈金身在美国,并没有按照自己也不太理解的美国观念来贩卖经过一番粗俗的图解和歪曲的中国故事。他没有用女权主义、家族史、“文革”受难之类在“第一代华人新移民作家”中流行的观念和题材来取悦不明就里的美国读者。一丝不苟的“写实”笔法,为了不向自己也不了解的思想屈服而宁愿没有思想:这两点,是哈金用英文给美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哈金作为中国作家被引渡回国,接受国内读者评判,就须换一把尺,光有以上两点显然还不够。
前面简单比较了他和国内一些优秀的同龄作家,现在不妨再拿他与日本的村上春树作个比较。哈金是整个脚板着地在邯郸学步,村上则跳芭蕾,永远踮着脚。哈金只摹写他认定是实有的事,像老实的搬运工只敢搬运别人指定的存放在某处的打好包的货物。村上瞧不起这些,他只写脑子里构想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只须和大多数人认定的实际生活有一个相切点——芭蕾舞演员的脚尖只须和地面有极小然而足以支撑并运转全身的接触点——即使是大家认为实有的生活,村上也要加工一番,变得和构想出来的东西差不多。高明的作家写头脑里构想的图景,并享受这种创作自由;平庸的作家则害怕这种自由,构想不出任何有趣的东西,只会“写实”,也就是复制。
没余味,是因为没想法。没想法,是因为没有产生想法的思想活动。没思想活动,是因为找不到思想上的敌人,不知道究竟应该抓住中国心灵的什么东西开掘下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哈金与他所钦佩的青年乔伊斯最大的不同。哈金在中国的生活阅历绝不会比二十来岁的青年乔伊斯逊色。但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我所以一开始要弄清哈金的身份原是为此——哈金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能抓住中国人的身体而抓不住中国人的感情以及比感情更深刻的灵魂。感情只对人,对最近的世事,灵魂则向着类似哈金在作品中描写的广阔而无言的世界的风景开放。
教育背景不允许中国作家这样做。中国作家从小就并不生活于中国的精神传统以及这个传统的现实处境中。这一代人所接受的虚伪的教育,一开始就毁掉了他们的大脑,等他们长大成人,懂得思考,要求“睁了眼看”,第一步必须医治头脑,祛除已往教育放进去的垃圾。这往往需要努力一生。等到把垃圾祛除,才可以用独立的意志、眼光、心胸来打量世界,说出独立的作家应该说出的话,也就是“自己的想法”。这该是多么漫长、艰辛、充满无数半途而废的可能性的道路。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普遍长于“写实”而不敢“写虚”,也就是只能写贴近肉体的事情,而不敢探索灵魂的深远。比如哈金写《等待》,写《池塘》,里面的人物的内心都很浅,很容易见底。见底以后,还要写那么长,文字就不得不始终停留在表面。于是《等待》写一场离婚案件之艰难,就非得老实巴交地写上18年才肯罢手,《池塘》写“丰收化肥厂”的厂长与党委书记今天坏笑着迫害职工邵彬,明天还是坏笑着迫害邵彬,双方作为人的存在一开始就凝固了。
我所以不满哈金的就在这里。“写实”,依靠生活经验的积累,“写虚”,则必须跳出经验,跃上更高层面,和某个具有确定性的精神传统对话。我们佩服鲁迅《故乡》系列的“白描”功夫,但为什么同样是“白描”,是“写实”,同样是写“故乡”的各色人物,现代文学史上只有鲁迅才一直占据不可动摇的高度呢?因为在鲁迅的整个文学工作中,“写实”和“白描”只是表面的技术,他用这技术所要表现的是他对人物灵魂的理解,是他对人物背后中国的精神背景的理解。即使他在写鲁四老爷时并没有怎么“写实”,也并没有怎么“白描”,只是寥寥数笔的点染乃至脸谱化的交代,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人物而想像他所依附的某种为鲁迅所深恶嫉视的幽暗的中国精神的背景。鲁迅始终和在他那个时代依然显得相当强大的中国的精神背景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他自己的文学精神也就在这种对话关系中诞生——绝不仅仅仰赖他的“写实”与“白描”!
文学精神的诞生,必须以作家和某种确定性的精神传统构成积极的对话关系——赞成或反对——为前提。从单纯物质性的生存中产生不了精神的新苗。那种以为只要生活经验丰富就有资格成为作家的信念乃是长期误导作家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迷信。因这迷信,中国作家往往被自己落入的生活圈子所局限,找不到积极介入中国精神的恰当的基点,因此再怎样高明的“写实”,也会蜕变为无法触动心灵的看过即忘的传奇。中国作家或者可以像哈金那样建构各自的“木基市”,却很难写出各自的“都柏林”或各自的“鲁镇”。
“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先后三次遭遇了它的精神基点。第一次是“五四”一代作家与深入骨髓的中国传统“自啮其身”式的抗争,第二次是“五四”以后直到今天众多作家与不断对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命运的叩门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之磨合,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对并没有因为信仰危机而展露真容的革命传统的反思。这三次未必在时间上先后发生的中国作家与某种身体内部的传统之力的冲撞,乃是中国新文学得以灵光闪现的三大精神基点。新一代作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苦苦寻求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基点,我看到这种寻求异常艰辛,他们的写作普遍呈现出巨大的盲目性与不确定感。他们有太多太沉重的直接来自当下生活的材料,却缺乏某个可以消化和统领这些材料的先验的思想框架。
我是在这样的“精神的背景”之下理解哈金小说的思想贫乏、简单与直露的②,在这一点上,哈金和国内的许多同龄作家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应该充分理解哈金的特殊的困境。他可以熟练地运用外国语言写作,却很难轻易获得外国人的意识。即使终于获得了外国人的意识,也很难用这样的意识来反观中国。又因为他身在外国,脱离了国内生活每天压在我们肩头的真实的重量,脱离了中国作家群体心心相印、寻找背景依托的精神运动,就很容易两不着边,既难以获得异质文化的意识来梳理自己的中国记忆,又无法从本土当下的生活和不管怎样总算挣扎于其中的本土知识分子的精神运动中汲取同情的力量。对外既隔膜,对内亦脱节,因此不管在文学描写的技术上有何种突破,在文学的真正内核——对精神背景的突进和对自我意识的建构上,却很容易缺氧乏力。
这并不是因为海外中国作家特别无能,而是处境决定的。我不想夸大当代中国意识和世界人类精神的隔膜。这种隔膜实际存在着,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为消除这种隔膜所做的工作,海外华人群体的精神运动,实在可怜,远远比不上“五四”直到三四十年代先贤们曾经取得的成就。那时留学生可以不管外国大学的学位,混个“克莱顿大学的文凭”也老大不情愿,他们敢坐在公寓里自己用功,直接和所在国的精神界对话。现在留学生一下飞机就掉进所在国的学院体制和学术规范,能够不淹没就很不错了,思想的对话谈何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无勃兰兑斯所谓的“侨寓文学”的原因。中国现在只有“侨寓学术”(原谅我又杜撰了一个新词)。哈金属于这样一个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处在这样一个海外华人精神运动的序列,只能在“写实”上努力不落人后,如果我们不满于此,要求他或别的海外中国作家以挟泰山而超北海之势,像鲁迅当年所提倡的“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P56),岂不滑稽?
什么时候哈金走出海外华人作家的尴尬,摆脱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褊狭,在中国生活之外获得别样的眼光,他或者可以把“木基市”写成他自己的“鲁镇”、“都柏林”。现在他只能身在美国,倚赖他作为一名中国人在80年代以前就已经养成的心地和眼光,用美国人并不复杂也不高明的技术,复制着平淡无奇的“中国人的故事”。
但听说他以后准备少写中国,开始写美国。不知这个消息是否可靠。倘是真的,我的预言只好提前落空了。
注释:
① 本文涉及哈金作品的中文译本《等待》,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其他全部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
② 《精神的背景》是张炜发表在2000年第1期《上海文学》上的一篇文章,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我在这里只是纯粹的字面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