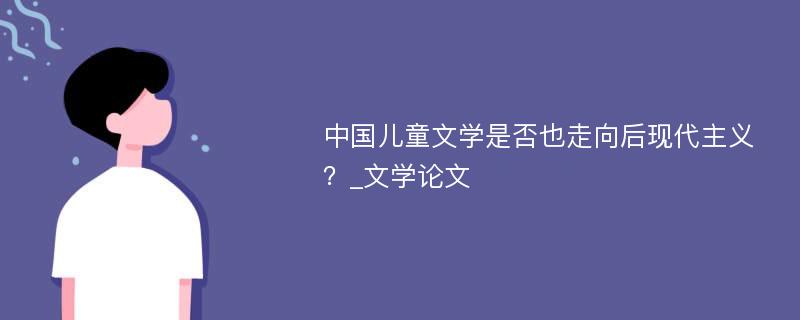
中国少儿文学也在走向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也在论文,中国论文,少儿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早听说广东的李国伟同志在创作一种“少年自我历险小说”。无缘得见,也不大好想象。近日找来作者的几本小说读了一遍,尤其是读了,《狮面神像》开首的一段话,方明白其大概:“我们通常看到的小说,都是用第一人称‘我’、或第三人称‘他’作主人公,但自我历险小说却用第二人称‘你’。所以,当你打开自我历险小说时,读者‘你’便成为书中的主人公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必须由‘你’来推动,‘你’的历险渴望,便在这种直接的参与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阅读时不必按页码顺序来读。困为,在每一页的结尾都如来到岔路口,为你设置了数个不同的抉择。‘你’必须根据情节的发展,选定下一步的情节路径,不同的抉择,会把‘你’引向不同的结局”。(《巨人》1993年秋季号)
但读完小说,我却很有些失望。
“自我历险小说”是以读者完全认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为基本前提和主要特征的。但恰在这一点上,“自我历险小说”能否成立是很成问题的。人物(如小说主人公)是小说的构成因素,内在于作品,而具体读者是外在于作品的。阅读时,读者借助想象进入作品,他首先认同的是隐含读者,即作家通过具体的题材、主题、情节、结构、语言等为读者设置的理解整个作品的位置,而不是人物或叙述接收者(这种认同也不是完全的,无条件的。因为,如果完全地无条件地认同了隐含读者,读者便失去了对作品的批判性)。正是通过这一位置,读者才与叙述接收者及整个艺术世界发生关系。一方面,他要进入艺术世界、感受、体验具体的人物、环境、事件;另一方面,他又要与艺术世界保持某种距离,以便对艺术世界进行观照、反思甚至批判。就是进入艺术世界,他也不只是认同某一人物(即使这一人物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而是要从一切可能的视角观照、感受、体验所有的人物、环境、事件。即是说,在整个艺术欣赏的过程中,读者的观点都要保持有可以移动的自由。或者在艺术世界内都自由移动,一会儿贴近这一人物,一会儿贴近那一人物;或者在故事内外移动,一会儿站在故事里面,一会儿站在故事外面。用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说,叫能入能出。能入,才有对人物及整个艺术世界的真切感受和体验;能出,才有与艺术世界的距离,才能站在一定距离外对艺术世界和作家对艺术世界的创造进行观照、审视甚至反思、批判。“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只出不入和只入不出都是违反艺术欣赏规律的。现在,所谓的“自我历险小说”不仅要求读者完全地进入故事(只入不出),而且要求读者完全地认同某一人物,将自己化身为故事中的历险者,这就不仅取消了读者观照、反思、评价整个艺术世界的权力,也取消了读者从除了主要历险以外的其他视角感受所有人物、事件的权力,其实是将读者的视角强行地限制在作品中某一具体人物的极为狭小的视角里。这一要求不仅是难以做到的,也是不可取的。
这一要求在所谓的“第二人称”小说里尤难实现。按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的辩证,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并不确。因为叙述者倘要自称,还是都要用“我”的。现在人们所说的“第二人称”小说,其实是在小说中设置一个有形的叙述接收者,即作品中的“你”(通常是故事中的某一人物),作品就是叙述者向这个有形的叙述接收者讲述的故事(通常是他自己的故事)。如班马的《鱼幻》、《迷失在深夏古镇中》等。由于有一个有形的叙述接收者,故事是对这个有形的叙述接收者讲述的,隐含读者与叙述接收者在作品中被鲜明地区别开来了(在其他小说中,这二者的区别存在但不鲜明,很多时候还无法区分地重迭在一起)。这样,当叙述者向叙述接收者叙述故事的时候,读者被明显地置放在“偷听者”的位置上。读这类小说,读者是比读任何其他小说都更能感到自己是一个“观者”、更能感到自己与叙述接收者、人物及整个艺术世界的距离的,因而也是更难认同故事中的人物、将自己变成故事中的“你”的。我读《狮面神像》,就感到一面有一只作家的手将我使劲地压向人物,一面又有一种从自身产生的力使自己顽强地从人物身上浮现出来。不知作家压着读者的手是否也感到这种反向的浮力?
“自我历险”云云很难成立。对于《狮面神像》等作品,“少年自我历险小说”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名称。据我看,《狮面神像》等小说的特点并不在所谓的“自我历险”,而在情节发展的每一关节点上设计不同的选择,使故事因读者的选择的不同有不同的方向,最后导致不同的结局,出现“看了一本书,也就等于看了许多本情节不同、结局不同的书”的现象这一点上。以此为着眼点,我觉得也在进行类似试验的夏辇生将她的作品题为“魔方童话”倒是一个不错的名称。据说,现在的电子游戏也常常设计不同的程序,让游戏者在每一关节点上都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引出不同的发展方向和结局。那么,将《狮面神像》等作品称为“电子游戏小说”也是可以的。或者,干脆,根据这类小说在具体操作上与儿童搭积木游戏的相似,称其为“积木小说”也许比称其为“自我历险小说”还恰当些。
二
但是我决不想因此而否定《狮面神像》等小说。正名,只是表明我觉得应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一些作品。
和以往的小说相比较,《狮面神像》等小说有哪些新特点?
最明显的特点自然在其情节结构方面。结构是作品的内形式,一部作品有怎样的形态,主要是由其结构决定的。而在小说中,结构主要体现为情节的安排。以往的小说,不管它们之间怎样差异,一般都有稳定的结构和情节,作品也正是通过自己的情节、结构建立起自己的艺术世界。但《狮面神像》等作品却将这基本的小说艺术原则打破了。通过在情节发展的每一关节点上设置不同的发展方向,情节的下一步发展交由读者自己选择,不同的选择获得不同的故事,出现“看了一本书,也就等于看了许多本情节不同,结局不同的书”的局面,这就整个地颠覆、消解了作品的情节和结构,使情节、结构向碎片化的方向转化,成为可由读者任意拆卸、组装,没有确定形态的东西。你可以说作品中没有故事,也可以说作品中有许多故事;你可以说作品中有许多中心,也可说作品无中心。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犹如一堆积木,你可以从中选出一些部分按照某种原则搭成一座山、一道桥、一座宫殿,也可以从中选出另一些部分按另一原则搭成一个人、一匹马,一头大象,每一种选择及其创造的结果都是合理的、平等的、决无对错之分。如果说作品中由许多选择构成的故事都是复制,那也只是一种没有“原本”的复制。以往小说中相对完整的艺术世界基本不存在了。
情节是小说的逻辑面,它规定和体现着小说的意义指向 消解了小说的情节、结构,也就消解了小说的意义,消解了作品的深度模式。以往的小说,包括那些最冷静、最客观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是有着自身意义和深度模式的。它们都将自身的艺术世界看作某种符号系统,借助这个符号系统,对它意指的现实界进行象征、隐喻,并作出阐释。比如“真实性”这一传统小说都极为重视的美学范畴,就主要是以艺术世界与其意指的世界的相符及艺术世界对现实世界阐释的深度为主要标准的。《狮面神像》等作品消解了作品的情节、结构,读者可以象搭积木、打扑克、搓麻将一样任意创造作品的结构形态,原作品自然不可能有自身相对确定的意义,犹如一堆积木、一副装在盖子里的扑克牌、一盒麻将没有自身的指涉意义一样。既然没有相对确切的指涉对象,作品的深度模式也就不存在了。“真实性”云云也就没有意义了。但这决不是说这类作品成了超现实的东西。恰恰相反,由于取消了人物、故事的符号性,取消了作品的深度模式,艺术世界彻底平面化,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在取消艺术世界符号化这一点上,《狮面神像》等品与神话有相似的地方。但神话是将现实界提升为神话,而《狮面神像》等作品则是将神话降为现实界。
这其实也消解了作家。作家创造了作品,作品也创造了作家。在具体作品中,作家是因其艺术世界而存在的。具体地说,作家的形象、声音是通过作品的整个艺术世界的描写,尤其是通过情节结构的安排、叙述者的语调等表现出来的。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越单一越稳定。作家的声音越强、形象越鲜明。反之,作家的声音便越弱、形象便越模糊。《狮面神像》等颠覆、消解了作品情节、结构,将作品变成一个包含了许多碎片、片断,类似积木扑克牌麻将的东西交给读者,至于用这些碎片、片断去组成什么,则完全由读者自己决完,作者的作用至多是通过对具体片断的设计对故事的整个方向作了某种暗示、建议而已。以往那种作家在作品中的主导地位被彻底地颠覆和消解了。这是一个读者的世界,一个没有上帝没有权威的世界。“作家退出小说”、“作家死了”,这些长时间以来一提起就让许多传统小说家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在这里终于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消解了情节结构,消解了意义,消解了深度模式,消解了作家,作品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只能是游戏。这点,《狮面神像》的作者说得直言不详:“自我历险小说可以当你故事来读,也可以当你游戏,一个人,甚至几个人、几组人一起玩”;“小说的情节发展,必须由‘你’来推动,‘你’的历险渴望,便在这种直接的参与中得到最大的满足。”犹如买来一盆积木,一副扑克牌,一副麻将,一台电子游戏机,它的制造者便退隐了,留下的至多是某种一般性的游戏规则,游戏者遵照这种一般性的游戏规则进行操作,无庸置疑地成为游戏的主体。因为游戏规则只是一般性的规则,给游戏者留出很大的发挥余地,在游戏规则的范围内,游戏者利用游戏器具可以变出无限多的花样来。一付扑克牌共有几张,大致怎么玩法是确定的,但每次的排列组合却是新的,一次新的排列组合就是一个新的创造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新的创造性的操作中,游戏者获得情感的、智力的、生理的、心理的满足与愉悦。《狮面神像》等作品的阅读策略与此相似,只不过搭积木等用有形的物质性的东西进行操作,而这些作品的阅读用想象性的故事片断进行操作罢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儿所说的“游戏”与新时期所说的“游戏”内涵上的不同。在新时期少儿文学中,“游戏”也是一个一再被人们提及的概念。但在哪儿,“游戏”主要是就表现对象而言的,是作为题材范围的新开拓被带入作品并得到首肯和张扬的,目的在于突破以往少儿文学狭隘僵化的描写空间及在意义上对人的束缚,将读者从一种完全受动的感知模式中解放出来,总体上依然是一种深度模式。但在这儿,游戏却真正还原了它的本真内涵。游戏就是游戏,玩就是玩,此外再无别的指涉或隐喻。卡西尔说:“按照席勒的说法,审美观照或审美反思,是人对宇宙采取的第一个自由态度。‘欲望总是立即抓住它的对象,反之,反思则把对象移开一段距离,并且籍着使对象摆脱情欲的贪婪而使之成为反思自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儿童的游戏中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种‘自由自在的’、有意识的和反思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游戏与艺术的分界线。”(《人论》第211页)这种距离感和反思态度在《狮面神像》等作品中已淡然消褪。于是,艺术与游戏的界限也消失了。读《狮面神像》等,获得的只是娱乐和消遣,艺术的美感蜕变为游戏的情感。
解构、非中心、平面感、程序化、可操作性、游戏、情感……这些不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最典型的特征吗?“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认,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它终止了一切诗意唤神的本性,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走向了精神的荒漠和不确定性的平面。”(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12页)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继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文化思潮,主要在二战以后萌生、兴盛起来,短短时间内,波及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它既脱胎于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如果说现代主义主要是精英文化,侧重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拒绝、反叛、消解,后现代主义则主要是大众文化,侧重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接受、妥协,在放逐对终极价值关怀的同时知足常乐。它是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相对稳定、物质生活有较大提高、一部分人安于现状急于消费享乐的情绪的反映。这一文化思潮在80年代后期影响中国文化,出现中国的先锋文学大量使用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段的艺术景观。通过李国伟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思潮已渗透到少儿文学领域来了。
其实还不止是李国伟的创作。只要稍稍放大视野我们便会发现,就在最近几年,类似或接近《狮面神像》的作品其实已一再地出现。如夏辇生的“魔方童话”,结构形式与艺术趣味与李国伟的小说一般无二;郑渊洁将童话创作与玩具制造结合起来,文学就是工业和商业,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已失去界限;还有大量的探险小说,传奇小说、侦探小说、动物小说、玩具式图画书及层出不穷的儿童科幻片、卡通片之类,内容有一,形式不一,但都以放逐终极价值、追求消遣娱乐、向现代化的文化消费靠拢为主要特征。将它们放在一起,说中国少儿文学中也在兴起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甚至说它们正在为文革后的中国少儿文学划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恐怕并非无稽之谈吧?
我以为,这才是《狮面神像》等作品出现的真正意义。
三
但我们仍不应忽视“少年自我历险小说”这一命名。虽然它名不符实,但却不是没有意义。它反映着作者的一种艺术意识。体现在作品中,就使作品有一种既属于后现代派文学又与传统文学相联系,既不同于传统文学又别于一般的后现代版文学的特点,这是我们认识现阶段中国后现代少儿文学不能不予注意的。
这突出地表现在《狮面神像》等与传统的历险小说的联系上。历险小说,如某某历险记、某某奇遇记这类在少儿文学中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其基本特征就是以一连串引人入胜的情节将读者带到故事中去,让读者在想象性的奇遇中获得一种超越平凡生活的快感。作为后现代派少儿文学,《狮面神像》等在其主要方面与传统历险小说是不同的。通过消解故事,强调读者的主体性,将艺术也看成是读者自由创造、自由操作的世界,作品否定了故事的客体性。但通过将作品命名为“自我探险小说”,通过让读者认同故事中的某一人物,将自己当作故事的主人公去历险,作品又千方百讦地让读者相信有一个作为客体的故事的存在,并希望读者全身心地沉浸到故事中去,将想象中的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去感知。作为这一矛盾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作品对故事消解的不彻底性。如前所述,《狮面神像》是一部积木、扑克牌式的作品。通过在情节发展的每一个关节点上设置不同的发展方向由读者去选择,每一选择形成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平行的,平等的,没有对错之分,这样,“看了一本书,也就等于着了许多本情节不同、结局不同的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很难说《狮面神像》等作品对故事的消解是不彻底的。但是,没有对错之分并不等于没有重要和次要之分。我们在这儿所说的《狮面神像》等作品对故事消解的不彻底性就表现在它们在消解作为“原本”的故事,使其变成许多可以组成一个个故事的“碎片”的同时,又通过自己的设计,向读者暗示,读者的选择及其构成的故事其实是有主次、好差之分的。在《狮面神像》中,少年历险者在一尊狮面神像的牵引下深入一个原始部落的世界,途中多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将主人公引上不同的道路,形成不同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有些以主人公中途折回告终,有些以主人公迷失荒野告终,有些有主人公被坏人杀死告终。而最复杂的一个,是以主人公历尽艰险打到以此神像为图腾的部落,弥合部落中两派人的分岐、争战,实现民族和解,他们将神像作为礼物送给小主人公,小主人公又将其带回国交到中国官员手里为结束的。谁都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是作品中最重要的故事,也是作者希望读者能够选择的故事。由此影响到作品的意义层次。如前所述,如果作品真的消解了作为“原本”的故事,一切都由读者自由创造,作品也就没有了所谓的意义。但在《狮面神像》中,由于还存在着一个“主要的”故事,与这个“主要的”故事相比,其他选择构成的故事还不能与它达到真正的平等,作品整个就必然还存在着某种来自作者的意义指向,如赞扬勇敢、机智、正义、民族团结、民族间的友好之类。而在李国伟以外的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那里,这种不彻底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虽说他们都在用自己的作品引导读者在一片能指的天地中进行游戏,让所指的一再延搁出现,但始终没有废弃对一个所指的出现的承诺。总想暗示点什么,隐喻点什么。说到底,还是留恋或不敢公然放弃那个深度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少儿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羞羞答答的后现代主义。
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却从一个侧面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真实而生动的写照。关于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人们一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二是文革后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的背景。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单一的。西方后现代派文学本来就不绝对地纯净,也不可能绝对地纯净。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有“反”的意思,也有“在……之后”即延续的意思,与传统文学,尤其是俗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它们无论在意蕴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常常表现出矛盾的特点。这种矛盾性在经过中国人的读解特别是“误读”以后变得更加突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是地域上的差异也是发展进程上的差异。西方已是后工业社会,而中国尚处在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期,当我们以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去观照、借鉴别人的成果时,“变形”常常是难免的。新时期初期我们甚至没有区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时当作现代主义介绍的许多作品后来发现其实是很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而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甚至更为复杂。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相对淡化,商品经济组织社会生活的使用日益突出。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商品化,文化工业化,传媒大众化,一部分人突然膨胀起来的超前消费等,确给后现代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但同时,中国毕竟是一个正在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各种经济成份并存,各种生产方式并存,一元化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后现代主义对于多数人还只是一种奢侈,如此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后现代主义之花只能如一位突然富起来了乡下女子,浓妆艳抹珠光宝气下透发出来的依然是她长期所处的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形成的粗俗与土气。目前中国后现代主义少儿文学的特点自然也有来自少儿文学自身的原因。后现代主义文学以亚文学、俗文学、大众文学为主要阵地,而少儿文学与这些文学的联系向来特别紧密。了解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目前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少儿文学主要是历险小说、侦探小说、动物小说之类了。所以这些,都使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少儿文学显出极为复杂的面貌,显出一些非驴非马、亦土亦洋的特征。这种现象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中国后现代主义少儿文学植根在现代的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国文化的土地里,出现时间虽短但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冲击了以能指──所指二元对立为基本构成模式的传统文学,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在中国少儿文学中开避出一片新开地。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它将仅在,它将发展。随着中国向商品经济社会的迈进,随着中国向世界文化的靠拢,它将进一步普及。它对传统文学的冲击也会越来越强烈地在人的感觉中表现出来。但是,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看到、承认后现代主义少儿文学将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如何在美学上对其进行全面、正确的评价并不是一回事。后现代主义文学毕竟是一种以俗文学、大众文学为主要阵地的文学思潮,它不是强调对生活超越而是满足对生活接受,不是呼唤神性而是放逐神性。它对应人们及时行乐愿望,在正确的消解一元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整个消解了作家,在正确地肯定游戏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整个放逐了对终极价值的关怀。这些都是真正的文学难以接受的。人们也许会责备我们,说这是从精英文化的视角看待大众文化。但精英文学也好,大众文学也好,但凡文学,与一般游戏总该有起码的界限。就个人而言,我崇尚文学的超越性、诗性,崇尚文学的唤神性质。至少,它不应在大众的狂欢声中消融自己。或许,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都有自己的领域,它们可以竞争但不能彼此替代。在未来的岁月里,它们都有理由得到发展,不要一者的发展以另一者的被吞噬为代价。这话听来有点可怜兮兮,但愿我们的忧虑是多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