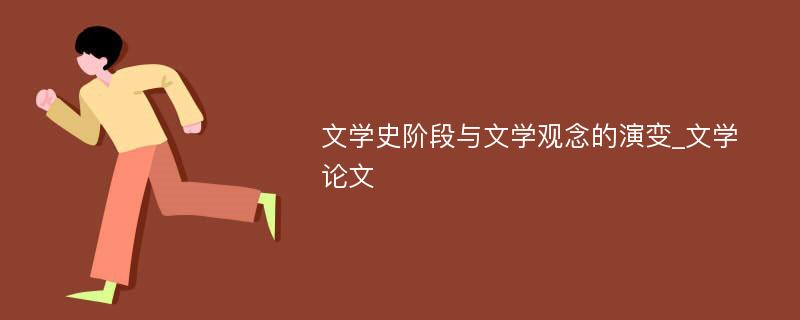
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观念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6-097-003
由《复旦学报》发起的文学史分期讨论的专栏已经进行了两年,除了其中有三期是关 于文学古今演变的话题外,其余都是围绕了文学史分期的研究和讨论。这个栏目本来是 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阶段的文学史现象,两位专栏的主持人也都分别在 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里成为学科带头人。在第一期的开场白里,主持人明确批评了 “以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习惯以朝代分期”的传统思维模式 [1],意思也是想引导作者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规律作出某种新的分期的探讨。 可是很奇怪,在专栏里所发表的论文内容,大多数是围绕着20世纪百年文学而展开,而 古代文学的分期问题除了有个别的学者提出“近世文学”的概念外,没有进一步涉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意想不到”(注:章培恒、陈思和《<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 期论集>序》,复旦出版社2001年出版。主持人解释其原因是因为2001年正好是新世纪 的第一年,所以“吸引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新世纪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阶段的到来。 ”)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史为什么需要分期?一般来说,讨论文学 史的分期必然地包含了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视角的改变。如果意识不到这种改变,那么 文学史只是一种文学资料的自然排列,无以成史。《复旦学报》设专栏讨论文学史的分 期,也许无意中印证了这样一个时代的需要:新的世纪来临,20世纪文学自然而然有了 一个结局,那么,无论继往,无论开来,都需要对此有一个总结和了断,总结是为了更 加认清过去一百年文学的性质和特点,而了断则为了告别上一世纪的文学而开创新世纪 的新格局(我注意到,专栏里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讨论90年代是否能够成为现代文学的下 限,也就是反映了这种急欲创新的心理)。其讨论的潜在目的仍然受制于社会性的传媒 炒作的话题,仍然体现在文学以外的社会功利性目的上,对文学自身的规律关注不够。 这么说来,如果讨论文学史分期是意味着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研究视角的变化,那么,这 次专栏所讨论的话题由整个中国文学史分期的缘起到归于20世纪文学史的分期讨论(注 :这场讨论原来的专栏为《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其中有一部分论文汇编成论文 集出版时改名为《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表明了目前学术界对中 国文学史的研究还远未自觉到文学观念改变的需要。虽然目前的教科书市场上文学史著 作汗牛充栋,但大多数还是停留在人云亦云的抄书水平,很少有学者曾留意于建构新的 文学史框架和探讨文学史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看,不仅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从人性的角度来探讨文学规律和分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次文学史分 期讨论的专栏开设,也确实有某种前瞻性。
章、陈两位先生主持的文学史分期讨论的专栏虽然没有能够进一步激起学术界对文学 观念和文学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转换的关注,但仍然前瞻性地提出了新的问题。因为,把 话题集中在对20世纪文学史分期的讨论本身也说明了一种学术的趋向,虽然它不可避免 地带上了世纪之交的时代传媒的烙印,但也包含了学术界对过去这一世纪文学的外部原 因和内部原因的比较彻底的反思。这个反思可以追溯到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重写 文学史”的提出,最初提出这个口号自然更多是包含了政治上正本清源的性质,但是不 能否认,拨过于强化文学史的政治性和党派性之乱,自然包含了返回文学史的历史性和 审美性之正途[2]。因此,从当时的一些文学史讨论来看,在现实功利的背后仍然依托 了学者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研究视角上的新的认识。
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起先不是方法论的,而是一次旨在消解近现当代 文学学科界限的学术革命。之所以称作“革命”并非耸人听闻,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引 起了学术界对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理性反思。这种对文学史 的反思里还包含了对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给文艺带来的创伤的反思。无论是“20世纪文 学”的概念还是“新文学整体观”的视角里,都隐含了一种意思,即中国文学发展到19 49年以后,无论从作品的思想艺术方面还是知识分子的心态方面,都进入了一个低谷阶 段。“五四”和新时期两头辉煌的对照衬托了中间阶段的苍白,这勉强用哲学规律来解 释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完了一个“之”字型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陈思和先生的《 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圆形轨迹》一文用“圆形轨迹”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与此相应的 是文学观上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视分期问题,而占主导地位 的是“一种将政治社会进程与文学进程直接联系,以文学社会政治性质作为依据的文学 史框架”[3]。因为这前提有一个不证自明的文学观念:文学是一个时代的反映,即一 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按照这样的唯物主义观念,时代在进化中,文学也在相应的进化 中,那么,20世纪的现代文学一定比古代文学进步和美好,1949年的当代文学也一定比 “五四”为标志的现代文学进步和美好。所以编撰文学史只要按照各个历史阶段来分期 ,没有必要独立地单分出一个文学史的分期标准。现当代文学以1949年为界,正是这种 无视文学独特规律的文学观念的反映。在当时,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者有的曾 把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作为一个文学阶段,视其为左翼文学阶段并把这阶段的特征一直 延续到“文革”,而“新文学整体观”论者也把分期划在1942年,也是延伸到“文革” ,两者都是有意淡化了1949年的界限,把“文革”时期文学所呈现的劫难史与历史根源 联系起来,追溯到早期的“革命文学”或者解放区文艺的阶段,这样一种分期是否合理 暂且不论,是否同样反映了政治性标准下的文学史反思也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论 者们在当时都反复说明他们正在依循文学史自身的发展规律讨论分期,在他们看来,文 学史的分期标记包含了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的互动演变,而这种文学史演变本身则仍 然是反映了政治性的变化的后果,当时的学者们就是这样用分期的变换来说明五六十年 代的文学低谷是怎样出现的。
当然这样急功近利的目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其背后隐含了更为深刻的文学观念的 变化。在接下来的关于现代文学上限的讨论中,虽然各家学说都没有明确说明,但已经 包含了对文学史的不同理解。20世纪文学史是一个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同步发展的 文学阶段,不少学者把中国社会特殊的现代性开端同它与世界所发生的关系联系起来, 譬如20世纪中国文学论者把现代文学的上限定于上一个世纪之交而不是“五四”,显然 是上一世纪80年代弥漫学术界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世界发达经济水平所产生的危机意识 为标记的,这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从过去习惯于把“五四”作为现代文 学的起点到转向世纪之交,在文学观念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即把完全政治化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视为文学起点,改变为把国家民族的现代进程作为起点。我们可以从 世纪之交的许多事件来看这种迹象:1894年甲午战争给中国士大夫们带来根本性的危机 意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启蒙西方思想的高潮、1899年林琴南翻译出版《巴黎 茶花女遗事》带来的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高潮,1902年《新小说》的出版,带来小说界 革命的高潮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可以归结为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性进程以后的思想文 化的反映。与这一系列以本世纪初为开端的文学事件被重视相关的还有国际汉学界出现 的一股尽量消解“五四”新文学的开创性意义的思潮,如王德威教授著名的“没有晚清 ,哪来五四”一说,这种观点影响到国内的文学史分期的研究,就是现在有关现代文学 史的研究很少再以“五四”为开端。但这种以国家民族现代性进程为视角的文学史分期 仍然是着眼于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上来论证的。我们姑且称作国家现代性的标记。
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又有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分期的观念逐渐浮出海面。如郜元宝先 生把1907年作为现代文学的上限,他取证于鲁迅当时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一批论文 是具有“现代精神和现代形式的独立的文学创作”,显现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制高点[4 ]。这种分期虽然有些独辟蹊径,自然又带有明显的90年代注重个人的现代性的因素。 这种因素在章培恒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文得到了非常完整的阐述。他 把新文学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三大要点: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 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的潮流,对世界现代文学中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 潮流中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对文学的艺术特征高度重视,并在继 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在这方面作了富于创造性的探索。”[5] 而在这三者中,追求“人性的解放”又是尤其需要关注的。由此而来的文学史分期,章 先生也是界定在20世纪初,即20世纪文学是一个自成阶段的文学,其理由与郜元宝先生 的理由相近,但在具体分期的观点上比郜先生宽泛得多,也更有说服力;其结论与80年 代偏重于国家现代性标准的分期方法差不多,但其背后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我理解章培恒先生提出的“人性的解放”,虽然已经有呼喊了近百年的历史,但它仍 然是一个没有被完全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新的高科技时代和商品化市场化潮流极大地 刺激了人们的欲望的时代里,人性的异化正是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 ,一方面是人们从传统的文化观念里走出来,开始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正常愿望与追求 自己的正常欲望,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但另一方面又在作为现代化标记的物质 刺激和欲望诱惑下,在高科技所刺激出来的野心和贪婪下,人性又可能进入另一轮新的 异化,同样也在丧失自己的异化,同样也在丧失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文学总是最敏感 最尖锐地提出隐含在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人性异化问题,其实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优 秀艺术作品中,真正能够倾诉灵魂深处的痛苦的艺术创造,多半是这类灵魂自我挣扎中 的声音。它不但可以用来解释现代文学的特征,还可以用来解释正在进行中的当代文学 的特征,也可能会继续成为未来文学的一个标志。
从完全政治性到国家现代性再进入人的现代性,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深刻反映了文学观 念的演变,这是上一世纪90年代学术走向的一条主线,我们从专栏文章中所讨论的现代 文学上限的各家观点中,虽然没有明说这些变化,其实基本趋向是一致的。当然,把个 人的觉醒、自我的发现、人性的解放作为一种文学的标志性分期仍然会有许多复杂的问 题有待于解决,而且也不能成为唯一的文学分期方法,但这次讨论中提出这个问题并直 接向传统的文学史分期观念挑战,必然会像“重写文学史”一样,进一步激起学者们的 思考和探索,推动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2-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