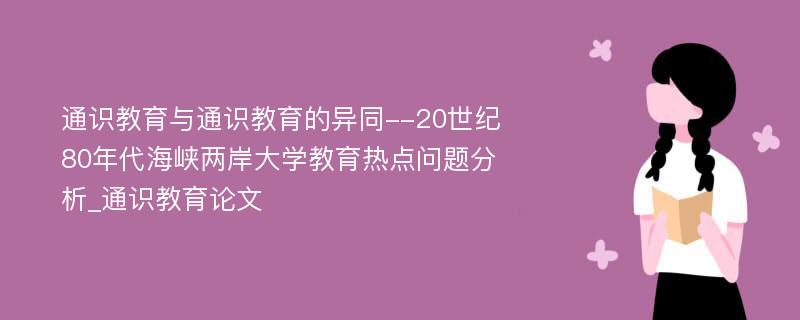
通识教育与通才教育异同论——80年代海峡两岸大学教育一个热点问题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才论文,异同论文,海峡两岸论文,热点问题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0多年的分隔,使海峡两岸学者在继承、运用先人留下的语言文化遗产上发生了些许微妙变化,有时也受制于各自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一些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提法、概念常见诸报刊。我国台湾省“通识教育”与大陆“通才教育”虽渊于同一历史源流,兴起于80年代,但其当代学术内涵就不完全相同,对通识教育与通才教育这一10年前海峡两岸高等学校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一回溯与比较,不仅有助于促进海峡两岸高等教育理论界的交流与借鉴,亦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强调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实质内涵。
一、历史源流与当代学术分野
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无论东方或西方,萌芽期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培养统治阶级与上层社会子弟(如中国的‘士大夫’与古希腊的‘自由人’)。这类教育无不强调广博的学识,巨大的人格力量与健壮的体魄,课程内容也以文艺、哲学、伦理学、美学、辩论术及射御体育为主。人们一般也认为,通识教育或通才教育的提法可以追溯到希腊的“自由(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的涵义,首先是不同于狭窄的专业教育,而是使个人的身体、道德和智慧得到和谐发展的教育。其次,在和谐发展中,理智的发展最为重要。因为“自由人”的一切行为都应受理智的指导。所以“自由教育”的最终目的应是发展理智[①]。可以说,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是数千年来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其实质内容却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无数先哲对“自由教育”锲而不舍的追求总是一次又一次给艰难长成中的人类带来新的曙光与希冀。纵观自古华夏古希腊以来的中西方文明进程,几乎在每一个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自由教育”(或谓博雅教育)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总是被高高张扬。不论是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文艺复兴,还是在资本主义勃兴的19世纪中叶《大学教育的理想》那振聋发聩的呼唤;亦不论是在令人窒息的科举氛围中诗歌词赋、琴棋书画那关不住的繁荣,或是在列强炮口下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学为体”(尽管历来贬多于褒,但它仍然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精神)的谏言……。
回顾近代的中国大学教育史,以社会为本,突出专业教育的教育价值观始终占主导地位。正如台湾一位学者所分析的:“把大学教育定位为专业知识教育,可谓有史已久。这样的教育理念产生,应当是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屡受挫于西方强权的历史经验有关。自晚清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总以为中国之所以不如西方,莫过于富国强兵、经世济用的科技上面。为救国而强国,学习西方科技之学,于是被中国人认为乃不二法门。观念之所及,大学被看成是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场所。”[②]基于因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追赶世界科学发展水平而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中国的著名大学教育家不约而同地用了“通识”或“通才”来考察、评价理想中的培养目标。这可以从近代中国思想家普遍引用最多的儒家经典《易》中,找到其理论上的源头。何谓“通”?《易·系辞上》称,“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显然,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家看来,莘莘学子唯有“通”,也即不仅应掌握先进的器识(科技水平),还要有中国人应该具备的见识(人文精神),方能肩负时代重任迎接挑战,重新确立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以“行以求知知更行”自励的陶行知先生,以“教育独立,兼容并包”独树一帜的蔡元培先生,以“南开精神”名震海内外的张伯苓先生,以“清华”为毕生奉献之所的梅贻琦先生,或蒋梦麟或竺可桢或傅斯年或胡适之……他们是中国人在见识与器识上能够“往来无穷,推而行之”的典型人物,也是近代中国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通识”或“通才”教育青史留名的教育家。从一定意义上讲,今日海峡两岸高等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就是他们的直接传人。
综观海峡两岸80年代有关通识教育或通才教育的讨论,至少在理论上还不曾对半个世纪前中国大学教育家的“见识”有多大的“突破”,可见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是亘古不变中外皆然的。
然而,80年代海峡两岸高等教育“通识”与“通才”理论的再度兴起却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与社会背景,其学术内涵与实质亦因此而有所不同。众所周知,中国大陆自50年代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高等教育在改造旧教育的同时,也按照前苏联模式来兴办我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事业。大学全部由国家兴办,人才的培养也完全纳入国家计划,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与社会的变革,完全依附于计划体制的大学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产品经济过分强调人才培养对口与分工,培养“规格”越来越窄,“一考定终身”,不仅压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影响了学生的潜力的发挥,也使大学本身成为了政府的附设机构,学校的活力亦无从谈起。在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中,面对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现代“教育观”、“人才观”的讨论波及上上下下各行各业。“拓宽专业面”、“着重培养大学生能力”等口号很快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各种改革措施也应运而生,如重新实行“学分制”,设立“双学位制”、“按系招生,不分专业”等等。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通才教育”才又一次成为大陆高等教育理论的“热点”。
40多年来,台湾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的道路,其经济的成长举世瞩目,但所谓“台湾经验”并没有给台湾大学生的素质提高带来福音。不少大学生不懂过去不问未来只顾现实利益,被有的论者称为“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或“平面人”,师生之间“劣币驱逐良币”(严格的教师学生敬而远之,马虎者门庭若市)的现象已见怪不怪,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演变成重商心理弥漫下唯“财”是举的“学以致财”。“台湾经验”中的负面影响——暴发户心态也深深影响了当代大学生。西方社会“科技日愈膨胀,人文渐趋萎缩”的现实更带来了所谓雪上加霜的影响。不仅民间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当局和大学行政官员也挠头不止,若无对策。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困境中,为追求所谓“富而好礼”的未来社会,以“人文精神滋养科技”,以“通识教育”来实现“人文主义教育的理想”在80年代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可以说,台湾“通识教育”追求的是“识”,大陆“通才教育”追求的是“才”,这决非掉书袋在抠字眼,而是各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二、学会关心:通识教育与通才教育的共同趋向
如上所分析的,比较海峡两岸对大学生“通识”与“通才”的理解,两者虽然在历史涵义上同出一辙,但是就现实理论内容上大有区别。对此,我们可以透过海峡两岸学者的具体论述作进一步的分析。
现任台湾省“教育部长”的郭为藩先生认为,通识教育只是人文教育在课程结构上的具体化。他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时撰著了一部在台湾影响颇大的《人文主义的教育信念》一书,书中提出了人文素养应涵盖的6个方面。无独有偶,80年代几位大陆学者在谈到的21世纪高层次人才素养时也提到了6个方面,将二者略作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到10年前两岸学者之间“通才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理论区别:
1)敏于观察、勤于思考,具有问题意识;2)能透过口头或文字条理清晰地表达思想与感受;3)对精致文化由衷的喜爱并懂得鉴赏;4)关切当前人类生活的重大问题并具有通识;5)对本国文化与历史传统具有起码的了解;6)对外国文化价值能适度的尊重。[③]
1)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素养和知识;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并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工作。2)要知道他所在的世界,熟悉世界的地理环境,各国的人情和经济;也就是要知道世界各国的历史。3)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的科学技术成果有个了解;能通晓科技新闻和各种成就的信息。4)要有文学艺术修养,要会运用形象思维解决抽象思维所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要会在实践和知识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作出判断。5)要懂得点军事科学;要有战略、战役和战术观点。6)要懂得卫生和锻炼,身体健康也可以益智。[④]
尽管上述例子中台湾与大陆学者在“通”与“博”方面有许多共识,但大陆学者显然更关心的是未来高层次人才在实践中如何发挥才智的问题,所谓“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作出判断”等等不无功利色彩和工具主义的倾向,这有其时代特点与历史局限。而台湾学者则主要着眼于受教育者个人人格与见识的陶冶和完善,与古代“自由教育”思想似乎更显一脉相承。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类似于台湾学者所激烈怦击的教育弊端也逐渐抬头,市场经济对大学教育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忧虑。“通才教育”理论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当看到有识之士在为今日我国大学生历史文化知识的欠缺而痛心疾首之时,我们仿佛又听到当年康有为痛斥八股文取士制度,“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争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谈矣。……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地理,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⑤]”亦如同身处半个世纪前赫钦斯校长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身体力行的同时大声疾呼“教育是要培养人格,不是人力”的场面。
但回顾80年代海峡两岸高等教育界在“通识”与“通才”方面所作的努力,似乎同样都落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其实际效果都远低于最初的设想,令人遗憾之处甚多。
台湾“教育部”于1983年开始实施《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规定各校必须在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社会与哲学、教学与逻辑、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7大基本范畴中开设选修科目,而每一位学生必须在28个共同必修学分之外,另外选修4至6学分的通识教育科目,理工、医、农学院学生应修习人文、社会或艺术方面的科目,文、法、商学院学生则应修习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或艺术方面的科目。这项措施颁布伊始,的确使人为之振奋,但诸如《婚姻与家庭》、《职业生涯辅导》、《家政学》、《妇女与社会》、《家庭计划》……乃至《口腔学》、《宠物保键》、《宝石学通论》、《畜牧学》、《造船工程概论》、《中国水利史》等所谓“新鲜、实用、有趣”的通识课程一开,竟使得台湾学者纷起而讥之。通识教育并非“统统懂一点”,更非“统统认识一点皮毛”。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博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大学实施的通识教育,既无意义,也没有效果,只在字眼上作文章。”[⑥]
也且不论80年代我国大陆高校校园内能够开出的着眼于“通才教育”的自由选修课少之又少,就所谓“文理渗透”原则而言,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向理渗易,理向文透难。诸如造就“T型”、“粗胚型”、“复合型”人才;或培养这“能力”那“能力”等等的热闹讨论常常亦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
看来,“通识”与“通才”教育既非一蹴而就,也不仅仅是大学教育之事,关键还在于学校教育这一神圣的事业如何对从“人之初”开始,一直延伸到明天就要步入社会的一代大学生施加的长期与整体(综合)影响力之强弱。台湾学者针对台湾通识教育发表的一些言论是发人深思的,“透过通识课程的实施,培养学生对于人生根本性的问题,例如生命意义、国家处境、政治社会问题、文明演进、时代变迁、自然科学……等,具有基本的识见以及能清晰思考、客观判断、流畅表达的能力,这种基本识见和能力的培育,若能在学生青少年时就开始建立基础,则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容易奏效。[⑦]”“通识教育之目的乃在于透过适当之课程的设计,使学生对人、社会、与自然的诸现象有一通盘,初步之知识上的认识,以助益形塑有追求真善美之理想的能力和意愿,也有助于培养具自我反省、精进能力之独立自主人格,同时,更重要的是,协助学生对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更为宽广的体认。……具独立判断之人格为目的来提供具统整、周延的知识。因此,通识教育的内容必得经过精心、系统的设计。然而,很显然的,教育部(指台湾‘教育部’——引者)与各大学并没有这样的认知,只做概括性的学分规定。在缺乏规划、而且适任师资普遍不足的情形下,大学的通识教育变成仍然屈服在专业教育主导下的附属品,它只是聊备一格,完全丧失了平衡专业教育在基本教育理念上的所造成之缺失的作用。[⑧]”反观我国大陆教育界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小学关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呼声之所以很快在大学教育界激起反响,引发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系列讨论话题,即深刻地反映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建立在中小学素质教育基础之上这一客观事实。从80年代大陆有识之士所积极倡导的“通才教育”,到今日世人皆为之瞩目的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讨论,既是符合逻辑的升格,也是近代中国著名大学教育家关于“人”的培养观念与思想的继续。
展望未来,笔者以为通才教育、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追求将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面前找到自己的契合点,即造就一代青年“学会关心”全社会与全人类。
“学会生存”作为一个大教育的目标与口号,曾在国际教育舞台活跃了近20年,但近年来人们已明显感到了它的不足与局限。“学会关心”应该成为21世纪教育的主题已越来越引起各方的关注。所谓“关心”,就是要教育青年一代从只关心自我的圈子跳出来,关心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如“关心国家、社会、经济和生态利益”,“关心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可以说,“学会关心”是人类在全球性危机困境不约而同作出的抉择。
“学会关心”首先要使青年一代正视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现代神话幻灭这一现实。
“学会关心”还要使青年一代意识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冲突的种种可能性并不会因为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信息社会的到来而减少。
“学会关心”的基石是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试图割断民族与国家连接自身的血脉,象极少数所谓的“民运精英”所鼓吹的那样,立誓成为“世界公民”是决不可能的。正如台湾一位学者所说的:“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非西方人)如果说对这一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混合着我们祖先之血泪的历史足迹没有一点起码的常识和历史存在感受,那谈什么通识呢?[⑨]”
因此,不论是追求“识”还是“才”,海峡两岸的高等教育界都应在教育青年一代“学会关心”上作出更大的努力,不论是对大陆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还是台湾蓬勃壮大的新生代,使他们能够从急功近利的社会层面影响中解脱出来,在了解那“混合着我们祖先血泪的历史足迹”基础上开拓视野应当是“通识”或“通才”教育应走的方向,大学之所以应当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因为唯有坚持“高深”方能够诱导每一位青年学生跳出自我的小圈子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和关心集体、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命运,成为能在未来社会中挑起大梁名副其实的“精英”。
注释:
① 《教育心理辞典》,福建教育出版社,第792页。
② ⑧ 叶启政:《理念被架空的高等教育》,《台湾高等教育白皮书》,(台)大学教育改革促进会编著,1993年。
③ 郭为藩:《人文主义的教育信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6页。
④ 曾德聪、雷德森:《科学技术教育学引论》,福建教育出版社,第276页,1990年。
⑤ 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摺》。
⑥ 引自《高教研究文摘》1990年第1期,汕头大学高教室编。
⑦ 黄俊杰:《提高大学通识教育的境界》,载《风云书系35》,风云论坛社。
⑨ 引自《高教研究文摘》1990年第1期,汕头大学高教室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