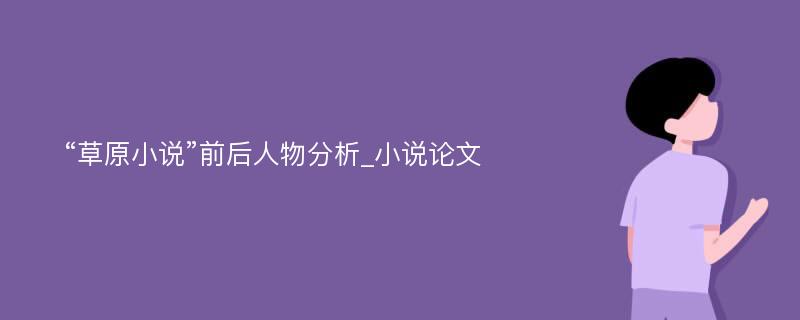
前后草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物形象论文,草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1)04-0080-05
笔者把当代蒙古族小说分为两部分,其标准有二:一是时间标准,解放初至文革前十七年为前草原小说;1984年至今的小说为后草原小说。二是所谓“前”与“后”,各指一种精神与价值模式[1]。前草原小说的风格较统一,人物多为工农兵,主要是“牧民”,创作方法为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基调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等等;后草原小说则没有明显的统一性,其中包含迥然相异的各类小说,但“牧民”小说仍是占相当地位和数量的小说。虽然都是写“牧民”,前后草原小说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不同时期的“牧民”形象分别表现和代表着不同的文学观念、创作宗旨和创作目的。因此,对“牧民”这一蒙古族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前后草原小说以及当代蒙古族小说的发展流向。
一、前草原小说中的“牧民”:让人仰视的“牧民”——一维构成的性格
从作家主观因素看,前草原小说的作家们解放前基本都亲身参加了各种战争和运动,有着不可忘怀的深刻历史记忆。解放后,他们又都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这种经历、职务和身份都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使他们的人生态度包括创作态度,始终与现实政治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他们对文学的认识有着很强的社会功利性。尤其不能低估第一次和第二次文代会的影响。第一次文代会特别强调了文艺作为政治工作有利武器的“优良传统”[2],并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中国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作家以最大努力去贯彻执行之。这不仅开启了新中国文艺的主流,也当然地开启了当代蒙古族文艺的主流。而第二次文代会要求的在塑造英雄时要“有意识地忽略英雄人物身上不重要的缺点”等意见[2],也成为前草原小说家在他们开始创作时所面临和接受的文学观念。扎拉嘎胡在总结蒙古族前十七年小说创作时,也实事求是地肯定解放区文艺成为这一时期蒙古族文艺的“催生婆”,这时期小说与当时全国文学发展相一致,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身体力行,并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内地汉族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内容主要为对“解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歌颂[3]。这样,便形成了前草原小说在塑造人物上以表现“牧民”(工农兵)尤其是具有先进世界观、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牧民为主,小说以歌颂、肯定的态度对待这些主人公,以证实和体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他们具有崇高、忘我和无私的精神与品质,反映和表现出的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属性,完全没有人性中的弱点和缺陷。前草原小说让人们强烈感受到的是对“牧民”的敬仰、赞扬和崇拜。
从性格构成看,这些牧民形象基本是一维构成的性格,“他们最纯粹的形式是围绕着一个概念或素质塑造出来的……他就是这个概念本身”,这就是福斯特所谓的“扁的人物”[4],即是说他们或者表现正面品性,或者表现负面品性。这种二元对立的艺术思维模式,甚至在人物相貌上也有一定规定,好人高大英俊,坏人丑陋委琐。因此,这些人物有时会显得脸谱化。
这时期小说努力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性格的丰富与生动,而是主题与题材的意义。玛拉沁夫在《茫茫的草原》下部后记中反思了50年代小说创作的模式:“……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习惯(是的,我只想说那是一种习惯),按照最初的总体设计,把故事写完了,如果说得再直率一点……近似于这样一种模式:在战场上进行了一场决战,我们胜利了,敌人失败了……于是乎,随着战斗或战役的结束,作品的矛盾冲突结束了,艺术情节结束了,人物命运也全结束了。”正如玛拉沁夫所讲,小说不是从性格自身的多重性以及性格与性格之间的相悖去表现对生活的理解和判断,而更多的是将人物附着于外在的政治事件、运动或政策,战斗(或事件)结束了,人物命运也结束了。小说不执著于性格,也难看到性格发展必要的推进过程。敖德斯尔1987年发表在《草原》上的一篇题为《关于创作典型形象问题》的文章中说:“什么是性格冲突呢?真正的性格冲突,归根到底是世界观的冲突。”把性格冲突看做是世界观的冲突,认为性格自身、性格与性格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斗争,矛盾斗争只是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中的问题,这种认识在前草原小说中是很普遍的。因此,即使有一些缺点错误,也属于脾气(比如急躁粗心等等)方面或者好心办了坏事一类,是外在于这个性格的东西。这样,错误缺点就成了对完美性格的点缀,是使这个性格更加显得本质化的手段。
衡量一部小说的因素很多,性格的单一或复杂、平面或立体等等都只是这些因素中的一项,当然不能否认这是很重要的一项。除此之外,性格的鲜明程度,性格所涵盖的历史意蕴等等,也是衡量小说的一个标志。小说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性格,如果作家的才能能使小说的其它部分,比如情节的生动与否,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及宽度,主题和题材的严峻及深刻,立意与哲理的深邃,以及语言、叙述方法等等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那么,这些生动的部分就会激励和推动另外不那么生动的部分而使人物活泼起来。所以,后来一些小说中的“圆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比前草原小说中“扁的人物”更令人激动。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还要看到的是这些英雄模范是“欢乐”的英雄模范。谢冕认为从5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营造着一个“欢乐王国”,“这个时代的文学普遍表达了冬天过去、春天来临的早春情调”。他指出,50年代炮火硝烟虽已散去,但生活的矛盾、冲突、阴影正在悄悄生成,而社会政治要求文学的却仍是“要它作为工具无条件地礼赞和肯定前者所展开的业绩,而且为此规定了描写的调子和底色,”“我们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时代的文学做成一个铺天盖地的欢乐颂,而要在文学中驱逐那怕是一丝云翳的哀愁”。前草原小说也确如谢冕所说的:“这种心境凝聚在作品中成为基调,甚至本身就是作品的内容。”[6]我们看到,即使在60年代初的大饥馑时期,小说中的牧民也仍然是欢笑的,他们没有哀愁、痛苦、愤怒和烦恼。不能说当时没有个别作家及作品表现出了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总的来看仍未脱离那个时代的整体风格。这是时代所然,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条件去强求这一代作家。
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归于文学“大一统”、“一体化”是自觉和自然的。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现在看来虽然有些失之单薄,受时代局限和当时思潮影响也较深,但我们仍不能否认前草原小说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以及他们所开创的“草原小说”、“牧民小说”这一风格及传统。我还想借用谢冕的一段话:“如今看来,我们在这一时段为中国文学积存了可贵的社会——文学的实践经验,这里的经验是一个中性的词,既说明实践中的获得,也记载实践中的丧失。当代文学的确为文学历史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本’。这些文本既是社会行进的生动记录,又为文学的变异提供了见证。”[7]而前草原小说的经典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后草原小说的“牧民”:走下神台的牧民——多维构成的性格
“牧民”走下神台,成为可以平视的人,始于80年代中前期。随着计划经济逐步转入市场经济,人们对“商品”的认识也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得到了最直接最具体的理解:不仅社会的发展,个人的生存也从来都是以经济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根本动力的,虽然不能排斥意识形态的作用。讨论人之初究竟性善还是性恶并无意义,但人最深最底层的欲望和要求,却在这时伴随着物质对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升到人的现实生活和人的意识层次上来。物质对精神的反作用、物质对人原始意识的诱惑;物质对人品、人格的拷问;以及人的心灵暗室中的丑恶、人性中的缺憾和弱点等等,都在经济活动及经济思想中暴露出来。后草原小说的着眼点不再仅仅从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角度,即不再仅仅从主题题材、政治热情等方面来界定作家及作品的责任与意义,而开始转向对人和人性的关注。在经历了文革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后,他们意识到人性的完善和完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又由于历史的惰性与惯性,在自强不息、坚如磐石的民族意志与精神之外,人还杂有不同程度地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与铸造的恶劣的“国民性”和人性的缺陷。这时期的小说家于是对文学作品中长期存在的那些满口豪言壮语的英雄感到疲惫和厌倦了。与前草原小说只谈阶级压迫和斗争,不谈人世的邪恶与痛苦不同,后草原小说不谈阶级,却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上谈邪恶,谈人性的不完善,谈个体欲望与现实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相对前草原小说的牧民是欢乐的英雄,后草原小说的牧民则显得悲观。
这种对人性负面的描写,始作俑者是白雪林的《兰幽幽的峡谷》(以下简称《峡谷》)。当时批评界对此众口一辞的意见是认为它表现了善与恶之间的斗争,我始终对这种看法持相反态度。善恶斗争主题并不是这篇小说在当代蒙古族小说史上的意义,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第一次写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牧民”,它正视和承认了一直处于让我们仰视地位的“牧民”性格中,也存在和可能存在着一些负面、消极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如前草原小说那样只是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或者脾气秉性的问题,而是承认牧民作为人,精神和性格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缺憾和不足如怯懦、委曲求全,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萎缩,虽然小说是将此文饰为“善良”去表现和描写的。甫澜涛回归大草甸令人震动地表现出人对“商品”撕去温情面纱露出的堕力所感到的震惊和恐惧,尊严与人格已不再是人所追求的精神和意志,在物质——金钱面前的堕落、贪婪以及世俗气,让我们看到人性中那不堪的一面;乌雅泰的《草人泪》则表现了一种精神和物质都很贫穷的小人物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和人走茶凉的寡情薄义,这一切都反映出了畸形的和不完满的人性。这些完全不同于前草原小说的“牧民”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真实人性的复杂。牧民们尽管有质朴、厚道、韧性、克勤克俭、忍辱负重等等美好品质的一面,有心胸博大、自然坦荡、豪放不羁的自由性格,但是,游牧的经济方式注定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传统的游牧经济方式养成了他们涣散、缺乏自觉,缺乏严明的组织性、纪律性,而长期封建王公制的社会形态,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们性格中某种屈从、盲目、麻木、缺乏独立性等等的缺憾。这些倾向和缺憾又都不仅束缚了他们的精神,而且沉淀在他们的灵魂里,成为民族性格、个人人格的一部分。
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机制的调整,传统游牧经济方式向现代商品经济方式的实质转变,从整体上动摇的人们的心理秩序、道德观念就难免给人们带来许多失落、不适,甚至反感。尤其是蒙古民族历史上没有经过商,落后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们站在文明的门槛外,而历史上汉族奸商对牧民的欺诈和盘剥,又都使“无奸不商”的看法成为蒙古民族长时间对“商品”、“经商”进行判断的价值尺度。这样,对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经商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牧民,更多表现出的就是不屑和鄙视。这时期的小说如《沉寂的昭谷敦》、《期待》等都对这部分人流露了一种毫不掩饰的仇恨。虽然这些小说批判的是这些消极现象,实际却是一种在千百年沿袭的生活信条受到冲击时难免出现的失望情绪的流露。挣钱、经商的商品意识像海潮一样席卷和吞没了从来都不齿于作商人的牧民,人性变得越来越难以理喻、难以把握。往昔的淳厚善良倏忽逝去,旧日的单纯明朗被撞破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沉甸甸的感觉渐浓渐深地跹绻于无奈的惆怅中。而另一方面,人对物质——金钱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又是任何人所无法抵御的。这时期小说中,新的观念、新的文化总是以新异事物比如打火机、摩托车等等方式进入草原,这一切都在述说着由于内地与牧区、商品经济与自然畜牧业经济之间存在着实际利益上的不均而感到的空茫和不平。
“牧民”终于回到生活和我们中间。他们就是我们周围人群中的一个,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包括那些不能原谅的错误,也是我们或许会犯的。这些“牧民”形象不再是一种根据有很明确指向性、规定性的概念或理念进行“提纯”、并淘汰了所有有碍这种指向性、规定性的因素的人物,他们没有被有意识地忽略,不管是否是“合理的缺点”,均被不留情、不掩饰客观地表现出来,即使对“英雄”和“正面人物”,也不再对缺点表现出谨小慎微的回避。命名与价值判断出现了分裂、分离和悖逆,正面人物也可能会有一些通常被认为是道德缺陷的问题,如季华的《灰腾梁人物》中葛林的婚外恋情。面对爱情、金钱或者职务的升迁,故事的叙述一点点拆解了他们曾经的神圣与崇高。这都使这时期的小说多少表现出了某种后现代的特征。
小说人物开始打破一维构成的僵局,透露出性格趋向多元复合的走势和信息,一批立体的“圆的人”相继出现在蒙古族小说中。
以《峪谷》为例。善良并不是扎拉嘎性格构成的惟一因素,也不能以善良解释他的性格。当善良和道德以自抑的方式限制着美好纯真的感情时,“善”所负荷的道德操守就显得抽象和空泛,它迷失了人的本性,不仅压抑了人的自然本性欲望(对具体爱的要求),也压仰了人的精神(对爱的追求)。但不管是压抑了哪一者,都是对人性的禁锢和扼杀,这时的“善”便因为包含了许多自虐的成分而成为人性因素的束缚。从抽象意义说,善与恶是对立的。但从人本身说,人性中善与恶的品质与成分却又会是同时具有和存在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单个,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摆脱兽性,问题只在于摆脱得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孤阴不生,独阴也不生。对立的因素不仅会奇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这两者间也会有一个广阔的地带的。这绝不是说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而是说人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的宇宙,具有最大的复杂性。扎拉嘎就处在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悲剧境地,任何一方的所得(无论得到杜吉雅还是得到道德),都是以另一方的所失为代价,不同选择的结果都可能对对方是恶而不是善。《峪谷》正是写了这样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扎拉嘎。哈斯乌拉《两匹马的草原》中的舍布格,敖·奇达布日《遥远的腾格里》里的葛根活佛就更复杂了。在他们身上,灵与肉仿佛被割裂成了两半,他们始终处在灵与肉的厮杀和搏斗中。类似这种复杂多面的“圆的人”,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
这些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一言概括,他们很难用好与坏来做二值判断。世界上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因素,对立是所有存在物的始基。人也同样,也是无数对立两极的合成,我们在任何人的身上都可以发现这种对立的因素。而“圆的人”比“扁的人物”更能吸引人,也正因为这种性格更符合生活的真实。
[收稿日期]2001-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