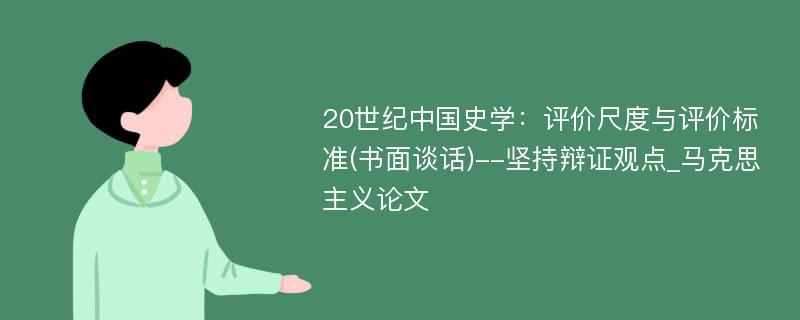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笔谈)——坚持辩证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尺度论文,中国论文,评价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6-0005-13
坚持使用辩证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是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准则。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既取得了丰硕厚重的成果,也走过了曲折坎坷的历程。100年里产生了众多杰出的史学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他们都程度不同地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作出了贡献。近几年来,学者专家或撰著宏文专著,或发表言论、 接受访谈,研究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这个课题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这些总结与研究工作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些问题上,以全面的、辩证的观点看待20世纪中国史学,仍然是值得坚持和重视的原则。
以新中国建立为标志,20世纪中国史学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应当是以新历史考证学为主流,同时期还有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受西方史学思潮影响而出现的其他史学思潮和流派,但主流趋势可以概括为新历史考证学。后一个时期则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界崇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及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新的探索,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特色,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依然居于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回顾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评价与研究活跃在20世纪中国史坛的史学家和史学思潮流派时,如何更好地使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如何避免片面化、绝对化?对这个问题处理的恰当与否,不仅在以往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时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而且在今后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时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前半期,以王国维、胡适、陈垣、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等史家为代表,在历史考证学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新历史考证学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具体到每个人、每一家,他们的治学方式、治史观念以及政治态度,也都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如王国维提出并使用的“二重证据法”,胡适以所谓“科学方法”为中心对考证方法论的论述,陈垣在历史文献学领域的考证及对传统考证方法的总结,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提出及对古史的考证,陈寅恪的诗文证史及对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的考证,傅斯年对史料发掘与考证的重视及其开创的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开拓性贡献等等,都取得了各具特色的成就。他们在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上也不一致,胡适、傅斯年等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顾颉刚、陈垣等人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表示过对唯物史观的倾慕与重视,或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自内心地表示要从头学起。应当承认,不论他们对唯物史观持何种态度,与他们以考证为基本方法的治学方式及取得的成就上并无多少直接联系。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十几年中,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度受到了批判,当时的形势是,除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外,其他的观点、方法都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所谓资产阶级史学,而资产阶级史学又被看做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的,因而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样绝对化地看待以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然有失公允,不仅简单地否定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绩,而且也不是全面地、辩证地认识问题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摒弃了那种将所谓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了一个更为实事求是的认识,相应地,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也得到了重视与肯定。然而,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怀疑、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否定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我们认为,在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的时候,过去简单地否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成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一些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成就的观点,同样也违背了以辩证的观点认识问题的基本原则。
譬如,有一种观点把新中国建立前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说得一无是处,还有一种观点是用“战时史学”将其概括和定性,强调其为战时政治服务的政治性,而对其学术价值提出疑问。有些人试图用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人在著文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过程时,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加阐扬,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甚至未置一词,完全漠视其存在的基本事实。
这里涉及到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亦成为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因素。历史学科的本质决定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但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研究必须遵循严谨科学的学术规范,这样才能够求得历史的真实,认清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但是任何时代的历史学研究都是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尤其是在对历史研究价值判断的层面上,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历史学的研究也会与现实发生密切的关系。同样,史学求真与史学致用也不是对立的,致用是以求真为前提,不能强史以就我,但史学不能只限于求真。绝对化地看问题和相对主义地看问题都有片面性,但实事求是、坚持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20世纪产生、发展并逐渐壮大起来的,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确立起主导地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与中国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也是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联系的。为了解救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由此走上了它的曲折发展的历程。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一段时期更为强调史学致用的功能,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譬如抗战时期的通史性著作、解放战争时期的近代史著作,毋庸讳言,这些论著确实因为时代的烙印而有损其学术性,在今天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有所损害,但也不应该因此而将其学术方向说得毫无价值可言。唯物史观的引进,使中国史学在历史观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历史观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加深刻地说明了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变化。评价与认识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应当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需要一个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在实际上则应当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失误与教训需要反思和总结,但是以偏概全也不是辩证地看问题的方法。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国史坛,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发展,真正能够与历史考证学相抗衡,并引起以历史考证学见长的史学家重视的,可能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历史发展过程,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归结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力图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是不同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这些都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史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理论深度、思维方式、研究观点与研究方法等学术层面,都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积极的影响在中国史学今后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还将不断地体现出来,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创新。
在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上,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考证学仅重视求真而忽视致用、马克思主义史学仅重视致用而忽视求真,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没有忽视史料,他们本人都具有扎实的史料功底,他们在具体的研究中也都充分显示出了这一点,他们还曾专门论述史料和考证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辩证地、全面地评价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同样十分重要。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唯物史观得以广泛传播,历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自5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的思潮,以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简单化、片面性等错误,都给史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些错误,在当时就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识到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极力予以纠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开放的、宽松的、良好的发展局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对17年中国史学的总结与反思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不是短时期的,但是不能就此将17年中国史学看得一无是处。譬如有一些观点把17年的中国史学看成是单一的、苍白的,说17年的史学研究是把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阶级斗争史。这样绝对化的看问题恐怕也不是正确的。只要实事求是地认真回顾一下17年史学的研究内容与成果,就可以发现,那时的历史研究内容并不是今天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单一,研究气氛也绝不是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紧张。笔者曾经专门就50年代初期的史学刊物《新史学通讯》(即《史学月刊》前身)进行了考察之后发现,这份刊物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涉及到了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及考古学等,内容包括历史人物、经济制度、历史事件、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变法改制等方面;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也包括了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各阶段。《新史学通讯》对当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公式化等偏差与不足作了积极的批评与纠正,刊登了许多史学专家和一般读者的各种意见,呈现出十分热烈的讨论局面。(《<新史学通讯>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可以认为,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史学 界致力于建设的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与格局,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明显的进展,马克思 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后的中国史学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明显的。然而有人在论述20世纪 学术发展时竟对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或视而不见,或全盘否定,在一些标榜所谓学术自 由、学术多元的人看来,似乎使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都可以讨论、都可以 尝试,惟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历史研究肯定就是错误的。这样就从一个极端又走 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是我们在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时所应当避免的不良倾向。
20世纪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家,评价他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目前也出现有较大分歧。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炒作代替不了客观的评价。盲目信从附和某些海外学者的观点,缺乏深入分析、没有认真在材料上下工夫便轻发议论也不可取。对胡适、陈寅恪等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评价,对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评价,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评价,都不应该脱离当 时的历史条件,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
收稿日期:2003-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