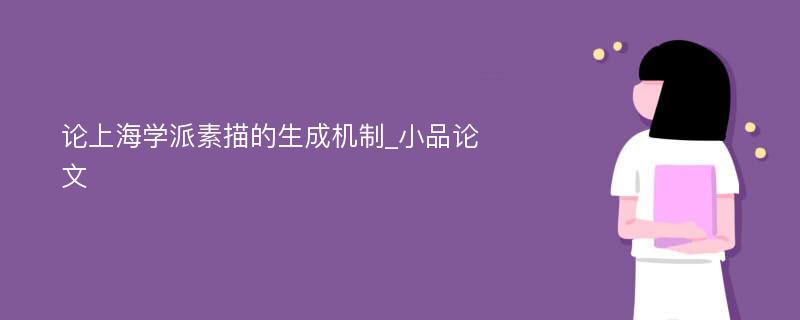
论海派小品的生成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小品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派小品(注:此处指除小说、戏剧、诗歌外的文体,即广义散文。),是指出现在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文坛,在近代城市型俗文化——海派文化熏染下,具有现代都市市民文化性格和人生态度的作家,而对都市生活的情感体验的真实记录。这些作家有30年代就出名的叶灵凤、施蛰存、穆时英、章依萍、章克标、钱歌川等;也有40年代大出风头的张爱玲、苏青、徐 、无名氏等。这些作家创作了大量小品,大多发表在《论语》、《宇宙风》、《人间世》、《现代》、《文饭小品》、《天地》、《杂志》等海派性质的刊物上,后都相继结集出版。海派小品在现代散文小品里属市民散文小品一路。它的诞生,意味着散文小品领域“都会诗人”(注: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719页。)的缺席状态终结。我们知道,当时在上海的小品派别,除海派小品外,还有新月派绅士小品、左翼战斗小品、论语派幽默小品、立达派为人生小品等。为何独独海派小品是市民小品,本文试图从其生 成机制回答这一问题。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产生与发展都不是与世隔绝而存在的。可以说,海派小品是都市商业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作为现代商业文化儿女的文人对文化选择的结果。海派小品的生成离不开社会现实(包括读者的生成)、作家主体、小品观念发展等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
首先考察海派小品产生的社会现实因素。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的初具规模,上海市民社会的产生和迅猛发展及市民的文化需求,是海派小品生成的社会现实基础。
都市发展的初具规模。上海自近代开埠以后,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短短数十年内,近代性质的都市开始产生和形成。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迅速崛起为现代经济大都市。据民国24年的《上海市年鉴三·土地人口》(注:上海通志馆编第2页。)记载:
年份 1930 1931 1933
人口 314万 330万 340万
汽车 8000辆10000辆
12000辆
新出现的工厂、商店、银行、饭店以及舞厅、酒吧、咖啡厅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市,形成更加发达兴旺的上海,更加沸腾的都市生活。40年代,上海处在孤岛沦陷区的独特环境里,政治控制的弱化与商业的强化,使上海都市出现了畸形的繁荣。
随着上海都市的产生和发展,继之而来的是上海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市民的文化趣味与需求的产生。所谓市民社会,是指相对自由的商品生产行为构成独立的社会运行机制,又往往与城市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市民社会产生的一般机制是,完备的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普遍化联系在一起,商业机制要求私人的生产、交换、消费活动摆脱政府的干预,并取代政治机制对社会运作的支配。人们不再对政权负责,而只对商品行为负责。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可以脱离政治社会而独立存在,成为一种普通而现实的社会形态。
现代都市不是像古代城市那样由于政治、军事等因素而促成的,而是由商业经济因素而形成的。都市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商业机制的作用。完备的商业机制对上海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上海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分开,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当然,西方在沪地自1843年(清道光23年)开辟的租界(后来租界面积不断扩大,开辟租界的国家也不断增多),其先进的社会组织建构和新型的市民文化,在上海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桥梁和榜样的作用。
上海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审美文化的分化。在市民社会里,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体制文化与代表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文人文化逐渐消退;而代表一般市民意志的市民文化迅速兴起。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分离,市民根据自身状况在文化上提出需求。借用柯灵在《孤岛回忆录·小引》中的话“思想领域没有真空,表达人们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可换成:市民的思想没有真空,表达市民心声的文学也没有真空。显然,市民文化既从政治社会中分化出来,那就不可能再遵守政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不可能满足主流文化。市民社会里,市民文化服从商业经济机制,使其精神产品商品化,大众化,以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遂使文人文化、体制文化不断消退。
市民文化是市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给市民意识的繁衍提供了相当宽阔的温床。市民意识是由一系列复杂的价值趣味混杂而成的,其内涵呈模糊性,外延呈松散性。同样,市民文化的审美需求也是异质杂多,不断变化,几乎不能用某种定型的模式概括。但尽管如此,市民文化的审美要求总还有一个主导趣味倾向存在。这种主导趣味的倾向,是由市民社会本性(即满足个体生存需要和个人主义原则)和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社会的亦中亦西、亦旧亦新,缺乏相应公民文化等特点所决定的。当时上海市民的审美文化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市民的审美文化对政治的日益疏远;二是市民的审美文化从内容到机制表现出彻底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倾向;三是上海市民的主体素质决定审美文化的感官化、粗俗化,嗜奇尚异的倾向。
市民审美文化需求的特点,确定了产生在紧张、高速、拥挤、狭窄的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环境里的市民文化大致取向:在闲暇之余,但求放松,移情宣泄。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文化里,虽不乏有探索人生的严肃主题,有“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传统修身要求,但仍以闲暇生活和娱乐文化最为兴盛,宣扬“人生不乐也徒然,死后一文不带去”的极端享乐主义的欲望等等。
其次,在市民社会里,海派作家对都市商业文化的认同,主动迎合市民文化和审美需求的态度是海派小品产生的主导因素。
在商业化的三、四十年代上海大都市里,城市一方面带来的是秩序、速度、物质财富、科学精神、求实气质等;另一方面,城市的机械文明、金钱崇拜,导致生活紧张、私欲膨胀、道德沦丧、犯罪率递增,丧失了人性的爱心、道义、善良、真诚等。城市里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正如马克思所论的“资产阶级在它已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完全破坏了,它无情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的关系,除了残酷无情,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对这种近代上海都市的文化现实,海派文人在《良友画报》上做了形象的描绘:
侥幸的心理,麻醉的享受、金钱底诱惑——这,都会的刺激,代替一切正当事业的热情。跑马、跑狗、回力球……。少数的代价,作为多数的博彩。矗立云霄的摩天巨厦,象征着金钱的威力。道旁的巨幅广告、啤酒、五加皮的刺激,舞场里,狂热的爵士音乐,恐怖的、侦探的、冒险的影片。在每一间戏院里轮流发出惊人的巨吼。还有加插的少女舞蹈,冶荡的舞姿、女人旗袍开叉的高度发展、肉的跳动、性的刺激……。
社会的不安使酒精般的刺激强烈的加增,建设的雄心,爱好的热情,在失望的绝境下,完全沉沦在这麻醉漩涡中去了。失败者的自暴自弃,灰心者的逃避现实,愤世者的憎恨报复……全溶合在这刺激的大洪炉中。于是,来了抢劫和被抢劫、奸淫和被奸淫、杀人和被杀……。(注:《良友画报》第85期第14版。)
同时,都市也带来作家身份、地位的改变。晚清的废除科举,断了文人的公职人员之路,而城市又使传统文人由单一公职人员变成自由职业者。与此相应,他们的文化身份也经历了转变:由英雄到市民或普通人。当作家是公职身份时,他保持着某种超越个人利害的社会眼光,传统的无可更移的公职生涯又训练了他们对整个社会与整个民族的责任。这种英雄主义的眼光和责任,已经积淀为中国文人(包括现代作家)的某种血缘,一种与生俱来的集体记忆。然而,当这群有“英雄情结”的现代作家走进近代都市的时候,他们就面临着与文人传统相敌对的环境。中国近代城市是由商业而兴起的,商业在城市的发达,使市民形成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的交往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每个人都成为契约化的法人。这是对人与人关系的革命性改变。这种契约化的法人对官僚化的集体记忆所带来的英雄身份具有强有力的腐蚀作用。这种人际交往关系和作家新获得的自由职业一起,使作家由古典英雄变为新型市民。人的市民化,一方面由于利益的相互性和职业自由性使他们的人格和权力得到了有力的维护,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另一方面,作家不得不自己谋生,而且是通过与他人利益的交换方式谋生。即使从事写作,这种在文化人看来是高雅的精神活动和千古事业的行为,在近代城市环境里日渐变得与商贩的营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为了谋生,现代文人不得不承担个人谋生的卑微和庸琐,不得不忍受个人谋生的困苦和艰辛。城市剥去了他们头上的光环,还给他们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这种现实对从来就是救世主或风雅名士的中国文人阶层来说是残酷无情的。(注:参读李书《都市的迁徙》第二章《小说家的身份革命》,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
面对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的上述文化现实、市民的文化性格和都市作家自身的文化现实处境,现代作家的反应是强烈的。他们这群深受传统经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总把城市想象为异己存在,对市民的文化趣味则取轻蔑的态度,视其为下里巴人,不屑一顾。他们终以自己拥有的文化尺度观照都市,显示出都市文化和市民文化的负面价值。于是诅咒都市是罪恶享乐之所的文章急剧增多,从《子夜》到《日出》,大部分新文学作家都嫌恶上海。上海几乎成为荒淫无耻、邪恶堕落的同义词。(注:有意思的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中间,几乎没有人不对上海十里洋场的畸形文化深怀厌恶。周作人把“上海气”说成是“买办流氓和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和风致”(引自《上海气》,收入《谈龙集》,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157页)。 鲁迅在论述上海文艺发展时干脆以“才子加流氓”立论(参读《上海文艺之一瞥》,收《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版第291—303页),最有意思的是原来也不属于旧派文人的刘半农,一到北京以后马上瞧不起上海,为了表示对郭沫若的轻蔑,便称他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而郭沫若也引以为耻,他从日本乘船一进黄浦江,首先感到的是“在行尸走肉中感受一点新鲜的感觉”(参读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版1970年第68、78页),30年代茅盾更是批评上海的都市文学以“消费和享乐为主要色调”,呼吁左翼作家应该去改造它(引自《都市文学》,《茅盾全集》第9卷第67页,人民文学版1961版)。)
在这样一片“围剿”上海滩的大文化背景下,来看海派作家与“上海”对话的独特性便十分显然。正如吴福辉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再也没有一个流派的作家能像海派作家那样“放弃旧标准,引进新的(对中国应属于异端)都市文化价值观念”(注:吴福辉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14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也如张爱玲所说的:“现代文明,无论它怎样有缺点,我还是从心底里喜欢它,因为它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注:胡览乘《张爱玲与左派》,载《张爱玲与苏青》第16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6月版。)的确,海派作家努力以都市人的身份,以新的尺度,通过创作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与都市对话,发表了他们的言论,表现了他们的都市体验和领会到的都市现代美,反映了三、四十年代都市人的某种生存境界和人在其中的生活状态。
海派作家对都市商业文化认同和对市民文化亲近的态度,当然离不开海派文化的追求时尚、标格创新的精神对海派作家的影响,但更多是由作家自身的政治态度、自身意志和经济大都市的生存规则和都市文化氛围的宽松性所决定的。一方面,这群浸身于都市工业文明,比大多数人提早进入摩天大楼、霓虹灯、玻璃丝袜、“飞机头”组成的流线型生活的海派作家,在政治上没有认同左翼作家和革命作家的意识形态,或认同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施蛰存曾表白道:“我从‘四·一二’事变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行动。我们三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引者注)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注:《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在思想上,也缺乏理想的目光和理论支点来对抗(透视)都市。叶灵凤叹道:“我没有自振的勇气,我也没有能力拯救他人。”(注:叶灵凤《春蚕》。)钱歌川说,机械文明时代“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时代,它剥削了我们古来的各种信仰,又夺去了其生命,却未给我们以新的信仰。”(注:钱歌川《女人的时代》。)在生活上,“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到职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注:苏汶《文人在上海》载1993年12月1日《现代》第4卷第2期。)为了生存, 这群远离政治而又缺乏理想目光的海派文人在商品经济律和世俗享乐色彩的影响下,认同了都市的商业交换规则,自觉把其作品纳入商品经济轨道,作为谋生的手段,“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注:苏青《自己的文章——代序》。)这样创作出来的小品,自然是迎合市民文化需求,照顾读者的审美趣味的,但我们不该忘记,左翼作家、为人生派文人其时大部分就整日生活在上海都市里,而且他们的情况正如苏汶所描摹的海派文人一样,“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他们都是中国的职业作家,在文学立即进入书籍市场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但左翼文人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理想支撑,为人生派文人有自己的民主主义理论和儒家人格的操守,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会像海派作家那样投入市民的怀抱,迎合市民的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都市的商业文化,虽然带来丑恶,但同时也带来人的自由、平等、享乐等人性解放。不可否认,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束缚相比是一大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近代商业城市的确是大大缓解了社会对人的控制,现代法制的确立,使市民的思想和行为得到极大放松。古典乡村式的法律有明显的道德迫害性质,法与道德以某种方式合二为一了。近代城市中的法律却放弃了其道德职能,把原来由刑具掌管的东西交给舆论,而近代城市居住的分散性使道德舆论乃至法律的约束力量大大削弱,互不相识的环境使人便于隐蔽自己,使人的许多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的释放找到了空间。姚公鹤《上海闲话》里有段文字可资为证:“又每见上海社会中发现伤风败俗之事,一般舆论必曰:此幸在上海耳,若在内地,即使幸逃法网,亦不免为社会所不齿,可以在上海如此,而在内地则如彼?……维持风纪,在野为士大夫之责,而在上则行政官吏之责也。上海以租界故,华官无绝对负责之人,租界政权操之外人。以甲国人谋乙国之根本问题,但由于法纪上无其他危险之发生,则社会公安而外,无复有第二之目的。”(注: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0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置身于此种环境中, 如鱼得水的海派作家就不可能像京派作家那样,无论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显得与城市文明格格不入,对乡村文明投以温情脉脉的目光,把它当作精神家园,而海派作家则是情不自禁地对城市投以爱与倾心。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海派作家便机敏而趋时地认同都市文化。“譬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春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汽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注:穆时英《黑牡丹》。)然而又心存困惑。因为海派作家终究还是文人,还是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着“士”的血液。他们居住城市,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市民文化,同时又葆有知识者的清明意识,他们又是市民又是知识者,后一种身份决定了他们有限的归属。文人文化的传统性、思考性及文人文化在上海各种文化冲撞面前的困窘性,都使他们对都市商业文化认同的同时又心存困惑。可以说,他们对都市文化态度是困惑中认同。
海派作家认同都市文化及对市民文化亲近的态度与市民的文化审美需求相契合,遂萌生了海派小品。
再次,海派小品产生也是现代小品观念发展的结果。
散文小品,中国向来有两大观念,一是言志,另一是载道。在封建社会里,散文小品的载道观备受推崇,“言志”的小品观常遭贬斥。即使“言志”也常言“士大夫”之志。到“五四”,由个性觉醒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破裂投射到小品观念上,“言志”小品观得到应有的重视,“言志”的题材范围也不断扩大。加以海派作家文化身份的市民化,遂使海派小品的“言志”,由只言“士大夫之志”向言“市民之志”的转换。
由于海派小品是一种都市的市民小品,又产生于十里洋场,难免染有西崽相、商业气、媚俗气等。所有这些,相对于传统的散文小品和当时其他类型小品来说,都是怪胎一个。知识阶层的人们对其不可宽容,大肆讨伐,致使在30年代中期,爆发了“京海论争”。海派文学(小品)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系统理论支持,一直处在被审判的位置,但由于市民阶层对其产生、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有力支持(主要指读者方面),才使海派小品艰难地发展下去,到40年代,产生了像张爱玲那样不容忽视的海派小品文大家。还有海派小品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京派在客观上的支持。尽管京海小品在内质上不属于同一类型,但它们远离政治、注重身边琐事、闲适等方面却可为同道。“京海合流”后,虽然田鸡黄鳝两分明,但毕竟是做成了一碗。(注: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6卷第3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京派在客观上为海派小品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意义的帮助,诸如理论依附、发表园地等,同时还为其艺术风格注入新的内质。
由于海派小品生成于独特的文化语境里,其文化意蕴与审美特征在现代散文史上是独特的。它有别于现代散文史上的其他类型小品,诸如与乡土文化相对应的京派小品,与革命文化相对应的左翼小品,与儒家文化相对应的为人生派小品,与以绅士文化相对应的新月小品等等。因其文化意蕴和审美特征不是本文所论范围,将在另文中论述。(注:参读拙作《试论海派小品的多重文化意识》,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