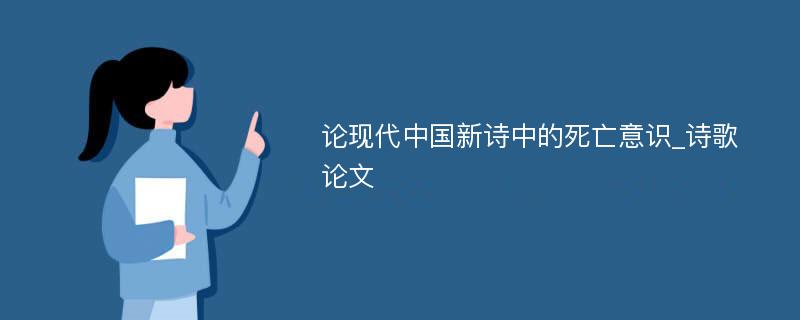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中国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5-0147-05
死亡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可以相信,只要人类的生命还无法避免走向终结,死亡都将 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真正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品格的萌生与发展因素,与其说是源于文学主题的历时态迁演,还不如说是由文学“ 文本书写方式”与“文本表达效果”所决定与推动的。本文以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 作为观照对象,希望在古今中外文化、文学背景的聚焦下透视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以 期揭示出中国现代新诗“现代性”品格熔铸与生成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尽可能地突破 诸多二元对立的述史模式,力图从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对峙与融合之中走上综合 性阐释的路径。
一
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包含的死亡意识属于古典形态的认识论范畴。大略言之,计有以 下四种:
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死亡的认识是现实性和伦理性的。孔子绝不是日 本学者今道友信所说的“没有关于死的言论”[1],他是从真理追求和道德人格实现这 两方面来探讨死亡意义的。《论语·卫灵公》宣扬“杀身以成仁”,认为死亡并非无意 义的肉体消亡,而有更大的价值存在,那就是“仁”;《里仁》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将死亡的价值定位于对真理即“道”的追求之上。正是这种基于死亡伦理性的价值 体认,沉淀为中国人的内在文化心理,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爱国主 义篇章。
这种注重死亡价值意义和伦理精神的诗歌写作路径,对战乱频仍中忧国忧民的20世纪 热血诗人们来说,仍不失为一条首选的可行路径。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经常可以读到这 样的作品。如郭沫若《湘累》:“我们为了他——泪珠儿要流尽了,/我们为了他—— 寸心儿早破碎了。/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微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你 们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郭沫若经常以屈原自况,而屈原的忠君爱国精 神在传统中已经成了一种文化象征,表明诗人郭沫若对于爱国传统的自觉归依。《凤凰 涅槃》中的凤凰,为了打碎这个“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茫茫的宇宙 ”,不惧自焚的结果——“死亡”,而且欢乐地高唱。从诗歌创作流派而言,20年代的 普罗诗派、30年代的中国诗歌会、40年代的七月诗派等,诗歌创作中的死亡意识,都是 这种注重死亡的价值意义和伦理精神的高昂的超越式书写。七月派诗人写到死亡,目的 并不在于思索、表现死亡本身,不是要去思索和表现死亡以后的状况,其出发点是要赋 予死亡以仇恨的意义,要“以生命为誓”,去争“自由的旗帜”,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战 斗精神和革命者的乐观情怀。应该说,在现代特定年代的风云岁月里,这种对于死亡的 超越式书写与对于生存的热烈追求,是代表着时代主流精神的,同时也暗含了中国传统 文化主流对于死亡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更加富有历史依据与现实意义。
第二,道家文化之于死亡意识的辩证性思考和主体性体验。老庄承认死亡的客观性,认为死亡是无可回避的生命自然现象,如《老子》七十六章所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坚强”;同时又认为死亡之外存在着一种超现实、超物质的不死精神,如《庄子·齐 物论》所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 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消解了死亡与生存的严格对立性,在思维上构成相通合一的 共同体。老庄的死亡意识是辩证统一的,其绝对的相对主义方法论为等生死、齐万物建 构起一座永恒的精神庙宇。老庄的死亡意识富于审美化的诗意,没有严整的逻辑秩序可 供寻觅。其时空观念不是物质或物理形态的,而是富有自由象征、随意想象的特质。道 家视生死为可以自由往来、绝对同一的两个存在场,在他们笔下,死去的骷髅仍可复活 ,真人是“不知说死,不知恶生”的精神长存者。道家文化中关于死亡的思考之于后世 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它的崇高的超越性和浪漫的诗意冥思。
不少中国现代诗人视死亡为“美”,刻意挖掘死亡的“形式美”,达到“恶之花”的 美学效果,这种追求有其外来影响,但道家文化的潜在作用还是巨大的——它为类似创 作作了心理与理论的预设。朱湘《葬我》:“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 绿荷叶的灯上/萤火时暗时明——//葬我在马缨花下,/永作着芬芳的梦——/葬我在泰 山之巅,/风声呜咽过孤松——/不然,就烧我成灰,/投入泛滥的春江,/与落花一同漂 去/无人知道的地方。”(1925.2.2)死亡在他笔下成为一个美好的过程,一幅画,一首 浪漫恋曲。即使是闻一多在悼亡他早夭的女儿立瑛的三首诗《忘掉她》、《也许》、《 我要回来》中,他也将死亡写得极富美感,如《也许》:“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不 许清风刷上你的眉,/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撑一伞松阴庇护你睡,/也许你听这蚯蚓 翻泥,/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便很 难从新月派诗作中读出常人对于死亡势所难免的伤感与悲痛。这种死亡书写方式,与道 家文化视死亡为与“此在”人生相通的“彼在”世界观念相一致。
第三,杨朱立足于现世肉身感官体验享乐主义的为我、贵生和享乐的死亡意识。这在 注重群体性伦理的传统中国,是被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身却有真实人性的现实依据,它 作为潜在的思想之流涌动于中国人的心灵沟壑,数千年而不绝,实无异于一剂反抗“群 众狂热专制”的清醒药。《列子·杨朱篇》说:“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 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又视“丰屋美服,厚味姣色”为生命的最高追求,“有此 四者,何求于外?”死亡会消解一切,包括所有的生命差异性,死亡来到之前的所有功 利行为,都是无意义的、违反生命本质的,这就使杨朱把为我、贵生、纵欲、享乐当作 生命游历的价值坐标。
20年代汪静之呼唤情爱的诗是“惊世骇俗”的,如《别情》:“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 ,/甜蜜不过的嘴呵!/醒来却没有你底嘴了,/望你把你梦中的花芭似的嘴寄来罢。”《 伊的眼》:“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体现了五四时期青春期特点、在保守派看来无异于“兽性冲动之表现”,其实是以 对现世人性的肯定、对僵死情感的嘲弄而具备了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第四,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观念。佛教把死作为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止点, 以死为圆心,画出了精致完美的思想体系圆圈,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都归于死亡,由此 达到无上觉悟,最终成“佛”。对生活在无边苦难深处的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佛国的 神光毕竟可以作为一种安慰的幻影而占据心灵空间的重要地位。
佛教的死亡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留存于现代知识分子心中。宗白华小诗《夜》: “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里,/随着星流。//一会儿,/又觉得 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里,/在里面灿着。”这种对于人类头上星空的观照 ,就是较典型的佛教思维。冯至《十四行集》之二一:“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只 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孙玉石认为“传达了诗人对生命本身 存在意义的哲理深思”,“这种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终极性思考,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 哲学的色彩”[2]。“灯”是佛教文化的一个中心意象,照耀着“此在”的人生,是光 明佛国的象征。诗人期待着借“此一点微弱的灯红”,来“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灯”在此处实际上成了现实人生的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希望。再如废名的《海》、《掐花》、《妆台》、《灯》、《星》等诗和戴望舒的《古意答客问》、《古神祠前》、《 我思想》、《眼》、《灯》等诗,都渗透了禅意与哲理。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现代诗 人尤其是在现代主义诗人的笔下,多有对于佛教意象与佛教思维的借鉴,如废名、九叶 诗人等的诗就是如此。但作为原生形态的佛教文化与佛教思维毕竟已被改写,“综合性 ”是处于历史长河下游的现代诗人们创作的总体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对现代主义诗歌 创作多样的阐说是有价值的。
二
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现代性”,并不能经由传统文化、文学所自然生成。任何 一种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异质性”变化,都需借助外力来完成。托马斯·库恩认为,科 学史上每当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总会出现新的“规范”(Paradigm),其作用在于为研 究者提供一种“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在学术演进的关节点上,历史总会推出某些 代表性人物来建立“规范”。建立“规范”的学者必须具有两个特征:一、在具体研究 上以空前成就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二、规定了一门科学的研 究范围,并在该领域内“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织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 决的问题”[3]。在中国传统诗歌成为一种自足性体系时,需要外力来打破旧有平衡, 并借此来推动新诗的生成。
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书写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诗潮,主要有唯美主义和存在主义 诗潮。
唯美主义诗歌的核心观念有两个:一是以丑为美,二是“向死的冲动”。其代表诗人 波德莱尔一反浪漫主义诗人专注于对自然的热情歌颂和对心灵的高度赞美,把笔触伸向 社会人生的种种病态和丑恶,化丑为美,培育出超凡脱俗的艺术之花,开辟了艺术审美 的新天地。他献给情人的《腐尸》,以自然主义的准确性描写了一具既脏且臭、布满蛆 虫、已经溃烂的腐尸,把它和美女联系起来:“两腿翘得很高,像个淫荡的女子/冒着 热气腾腾的毒气,/显出随随便便、恬不知耻的样子,/敞开充满恶臭的肚皮。”这种书 写方式,为他赢得了“恶魔诗人”的桂冠。
李金发“受鲍特莱与魏尔伦的影响而做诗”[4],诗作中经常可以读到这类唯美主义式 死亡书写。死亡之于诗人的意义,是一种“传情达意”的媒介,是一种“象征物”。“ 死亡”意象充溢于他的诗中,其真实含义往往令人不可把握。《有感》打通生死大关, 视“生命”为“死神唇边的笑”;《死》直接赞美死亡:“死!如同晴春般美丽,/季候 之来般忠实,/若你设法逃脱。/呵,无须恐怖痛哭,/他终久温爱我们。”难怪周敬、 鲁阳说:“读他的诗,总感觉到好像是在抚拭一具僵尸,或走进一座冰窟。”[5]李金 发诗歌中繁密的死亡意象、厚重的死亡意识,充满了对于死亡本身的颤栗与讴歌,而这 些一直是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视为典型的“现代”情绪的反映——生活不过只是“死 神唇边的笑”!
在冯乃超的《死亡摇篮曲》、《死》、《冬夜》等诗中,死亡有一层特别的色彩:“ 纤纤的玉手哟/给我鲜花插坟头。”——死亡是与爱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死亡便显 得富有超凡脱俗的诗意了。诗中的死亡不是现实中的死亡,也不代表诗人面对死亡而对 苦难人生的思索,而是幻想中的死亡,是以死——时间的终结来换取爱情的永恒,是对 无爱人生的厌倦,对永恒爱情的追求,只是这种爱情因为受制于苦闷的时代而无法实现 ,只能采取变态的方式来抒发而已。
受存在主义哲学、诗学的影响,中国现代新诗中出现了许多富于存在主义死亡观念的 诗歌。本文以九叶诗派作为中国存在主义诗歌写作的代表,而九叶诗派死亡意识则以穆 旦最为强烈、最富于代表性。我对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库》[6]中的《穆 旦卷》进行统计,发现几乎每首诗都写到了死亡,其死亡书写密度之大,令人感到惊讶 。
穆旦的死亡意识贯穿于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他30岁生日写的《三十诞辰有感》:“然 而暂刻就是诱惑,从无到有,/一个没有年岁的人站入青春的影子,/重新发现自己,在 毁灭的火焰之中。”全国解放后,他于1957年创作《葬歌》以表示要与过去的自己彻底 告别,“‘哦,埋葬,埋葬,埋葬!’/我不禁对自己呼喊;/在这死亡底一角,/我过久 地漂泊,茫然;/让我以眼泪洗身,/先感到忏悔的喜欢。”这其实是诗人的“夫子自道 ”,可见他此前的诗歌写作中是充溢着怎样密集的死亡意识,以后他创作了一些歌唱新 社会的诗,如《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但到1976年他又开始书写死亡,《停电之后 》写到停电后诗人点燃蜡烛,第二天发现“小小的蜡台还摆在桌上。/我细看它,不但 耗尽了油,/而且残流的泪挂在两旁:/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夜间,/有许多阵风都要 它抵挡。/于是我感激地把它拿开,/默念这可敬的小小坟场。”可见只要穆旦进入自由 的诗歌创作状态时(“反右”与“文革”当然算不上是自由创作时代),自始至终都要写 到死亡,都要包涵死亡意识。
纵观穆旦的诗作,他的死亡书写包含七个方面:一是对死亡与爱情的思索,认为死亡 是人类的必然归宿,在死亡面前,万有都不值一哂,包括爱情在内。《劝友人》:“于 是你想着你丢失的爱情,/独自走进卧室里踱来踱去。/朋友,天文台上有人用望远镜/ 正在寻索你千年后的光辉呢,/也许你招招手,也许你睡了?”二是思索死亡与新生的关 系。《玫瑰之歌》:“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期待深 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三是以死亡为人生苦痛的最后解脱。《 在旷野上》:“然而我的沉重、幽暗的岩层,/我久已深埋的光热的源泉,/却不断地迸 裂,翻转,燃烧,/当旷野上掠过了诱惑的歌声,/O,仁慈的死神呵,给我宁静。”四 是既以死亡为超脱,那么,死亡就不可怕,不需要眼泪。《活下去》:“活下去,在这 片危险的土地上,/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当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 /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残摧毁凶残,/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了却又死去,/那永恒的人。 ……/孩子们呀,请看黑夜中的我们正怎样孕育/难产的圣洁的感情。”五是视死亡为对 土地与神的回归。《奉献》:“他的身子倒在绿色的原野上,/一切的烦忧都同时放低 ,/最高的意志,在欢快中解放,/一颗子弹,把他的一生结为整体,/……其余的,都 等着土地收回,/他精致的头已垂下来顺从,/然而他把自己的生命交还/已较主所赐给 的更为光荣。”六是对死亡进行了辩证思考。《森林之魅——祭康河谷上的白骨》:“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 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 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七是 也反映了苦难人生之于死亡的无奈。《苦闷的象征》:“毁灭的女神,你脚下的死亡/ 已越来越在我们的心里滋长,/枯干的是信念,有的因而成形,/有的则在不断的怀疑里 丧生。”
总之,穆旦充满着死亡意识的诗歌创作,充分发挥了形象思维的特点,追求知性与感 性的融合,注重象征与联想,让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强调继承与创新,民族传统与外 来影响的结合,不愧为现代知性诗创作的成熟之作,这其实是得益于血与火相交织的中 国40年代的惨烈现实的。
三
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具备哪些品格?为什么会在现代中国的特定时空中产生如此复 杂的死亡意识?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死亡意识时所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我认为,多义性与综合性是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典型品格。多义性指诗人创作中 的死亡意识客观上表达出来的复杂效果与多重含义,它导致了诗作解读上的困难,是“ 历史”与“现实”、“本土”与“西方”多角度的客观投射,是现代新诗的主要文本特 征。综合性指诗人面对古今中外的丰富诗学资源时所采取的主体能动的整合性吸收,体 现的是诗人面对客观的作为“物”而存在的诗学资源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多义 性与综合性分别从客观与主观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复杂品格。
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多义性特征具有普遍性,在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等众多 流派中十分明显。限于篇幅,此处不作详论,只集中讨论新月派诗人的创作。
首先,死亡表现为一种“美”。如新月派诗人就经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 达到“恶之花”的美学效果。朱湘《葬我》视死亡的意义是一个美好的过程,是一幅画 ,是一首浪漫恋曲。闻一多《梦者》、《剑匣》、《烂果》、《末日》、《死水》都将 死亡写得凄迷动人。徐志摩《秋月呀》、《希望的埋葬》写死后“冷骸也发生命的神光 ,/何必问秋林红叶去埋葬?”死亡在他们笔下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很难从中读出常人对 于死亡势所难免的伤感与悲痛。这其实就是唯美主义的死亡观,在西方唯美主义诗人笔 下,对死亡的唯美主义式书写司空见惯。中国诗人不同于西方诗人之处在于对死亡作了 东方化改造,更加贴近现实,少了些“以恶为美”的“恶趣”,更加贴近中国本土现实 和东方阅读心理。我本人并不同意某些评论家的“新月派的唯美主义是伪唯美主义”的 论断,相反,我一直认为,对于原生形态的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的适合于本土特征的改 造,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不仅不是“离经叛道”式的“伪”理论,而且是 在更高层次上的“真”,因为它适用于创作与接受的现实。试问离开了创作实践与接受 主体,还有什么更加客观的评价标准?
其次,在闻一多等的笔下,死亡也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具有鲜明的目的论意义。《红 烛》将红烛分为“躯体”和“灵魂”,躯体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烧出灵魂:“烧罢!烧 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留别日本》、《问谁》、《为要寻一个明星》等诗作中, 死亡是一种为要实现理想所必然付出的代价,诗人为之欢呼歌唱,“水晶似的光明”在 “黑夜里”的“尸首”倒下之后终于出现,死亡是生命的最终完成,也是理想实现的必 要代价。
再次,他们将肉体实存看成是对灵魂的束缚和监禁,肉体既然是一种负担,那么,便 经常会产生“向死的冲动”。闻一多《宇宙》说“宇宙是个监狱”,《美与爱》、《心 跳》、《红豆》等表达了欲冲破束缚、奔向自由的强烈意志。《死》这样表达诗人强烈 的为了爱情的“向死的冲动”:“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 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
综合性是现代新诗史上主体意识特别强烈的诗人的共同创作特征。如果说对于现代新 诗的解读还存在着见仁见智的殊异之处,那么从诗人的诗论中则可以看到现代新诗追求 综合性的整体化努力向度。
李金发在其第二本诗集《食客与凶年》自跋中说:“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 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万合,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 极了的,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 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 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7]穆木天继续沿着这一思路,认为“李白是大的诗人,… …读李白的诗,即总觉到处是诗,是诗的世界,有一种纯粹诗歌的感(觉)”[8]。梁宗 岱“对于诗的认识,是超过了‘中外’‘新旧’和‘大小’底短见的”[9](p35),他对 “二三千年光荣的诗底传统”发表了关于传统与现代、创造与继承的精辟见解,指出“ 目前底问题,据我私见,已不是新旧诗底问题,而是中国今日或明日底诗底问题,是怎 样才能够无愧色去接受这无尽藏的宝库底问题”[9](pp30-31)。这些都表明在中国新诗 的开端处,就已经注重对于中外古今的诗学资源进行合理的综合了。龙泉明在《中国新 诗流变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新诗的三次综合过程,认为20世纪20年代新诗的 第一次整合的代表性诗人是郭沫若,30年代新诗的第二次整合的代表性诗人是戴望舒, 40年代新诗的第三次整合的代表性诗人是艾青[10]。我认为,其拓荒性贡献就是其以“ 综合性”切入诗歌研究的独特角度,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比研究结论更有意义。杨匡汉、 江锡铨、王国绶等学者在《中国新诗史写作探讨》[11]中评价此书时也有类似的观点。
中国现代新诗中的死亡意识是富于综合性的,戴望舒《祭日》、《老之将至》、《小 病》、《有赠》写死亡如写生前。死亡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生前的“寻梦”,也就 是追求的过程,反映了他对死亡的知性思索。《寻梦者》:“你去航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霜花》、《断指》反复诉说了关 于于死亡的知性思索:追求是有代价的,死亡是有获取的。40年代后,他的死亡意识发 生了转变,《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示长女》等表达了某些 人的死亡是为了更多人更好地生存,这种豪情是属于40年代的,是以40年代特殊战斗岁 月作背景的,但仍可以从他30年代的诗作中找到发展的根据与理论源头,这是30年代戴 望舒对死亡意义进行知性追问的必然结果。其死亡意识从历时态来看,综合了唯美主义 、存在主义、泛政治主义的“载道”观,民本主义、自由主义等多种诗学、哲学观念; 从共时态来看,在某一时期偏重于对死亡意识的“载道”、意义的求索时,也整合了唯 美主义的诗性追求。其他诗人如艾青、九叶派诗人等也都在综合古今中外的诗学、哲学 观念上狠下功夫,构筑了中国现代新诗死亡意识的综合性特征。
作为“客观效果”的多义性往往与作为“主体努力”的综合性紧密相联,要对二者作 出严格区分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凡是具有多义性特征的诗歌往往表明该诗的创作者 作出过综合性的努力;凡是主观上追求综合性的诗人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在诗歌创作中表 现出多义性特征。
现代中国特定时空为何会产生如此复杂的死亡意识?
首先是时代的原因。中国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三个方面的转型,即从 群体到个人,从伦理到审美,从情感到智性。传统的中国人对于死亡问题基本上还是持 漠视态度,“对于人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谛的置若罔闻是中国人思想中最可悲的一点, 多神论和无神论的调和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这种观念:肉体可以没有灵魂,灵魂可以没 有精神,精神可以没有生命,宇宙可以没有源头,世上可以没有上帝。”[12]也就是说 ,我们缺少的是追索源头的那种形而上力量,缺少指向终极意义的坚定策略。在这种混 合杂乱的思想体系下,薰蒸培育出来的只能是无可无不可的判认、游移不定的灵魂,也 即鲁迅所说的“无特操”的人格。在这种背景下,现代转型就显得格外重要、也格外沉 重了。重个人、重审美和重智性是现代人思维的“现代性”,这样就从古代的自然本体 论转向了现代的认识论,并借助于语言学的转向,从传统的“文言”转到了现代的“白 话文”。传统的文言是一种书面化的“语言”,而现代的白话文则是一种贴近大众口语 的“言语”,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变实际上是一次伟大的革命。现代社会毕竟转 向了人类存在本身,可以称之为“人类学的转向”;而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变, 则是将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可以称之为“语言学的转向”。关注人类自身,使用日 常语言,就使得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观照获得了某种可行的路径,于是,死亡意识受到 了诗人们的重视,并得到了“现代性”与“本土化”的重塑。
其次是现代诗人们主体意识的强化与个性的极端张扬。我一直认为,敢于直面死亡, 书写死亡的人必定是人格意志格外强悍的人。现代诗人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闷,率先唱 出死亡之歌,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实都是这个时代“苦闷的象征”。威廉·赫 兹列特在《席间闲谈》(1821)中说:“在常态下,天才是一种较为固执己见而不那么多 才多艺的东西。它具有十足的排他性,分外任性、古怪、独特。它做某件事是由于它从 不涉足别的事情;它在某种追求上卓尔不群是由于它对自身以外的任何杰出成就视而不 见。它恰好与变色龙相反,因为它从不凭借别人的什么东西,而反倒把自己的色彩贡献 给周围;或者,它也像萤火虫,在四周朦胧的暮色中和知性的夜幕下,放射出一小圈璀 璨的光芒。”[13]然而,就是这一小圈照耀了整个黑暗时代的璀璨的光芒,成为了中国 现代诗歌史的整体象征。
最后是历史的积淀与诗人的主观性整合。中国现代新诗中的死亡意识既是历史流程中 处于下游时段的文化沉积,同时也是现代新诗人们主观整合的综合化结果。“人性的法 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而且,一旦当他达到了 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进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身的 主宰”[14]。中国现代新诗人对于死亡作了有力度的思索,他们凭着厚重的死亡意识, “就从这时候起成为了自身的主宰”,或者说是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思索历程……
收稿日期:200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