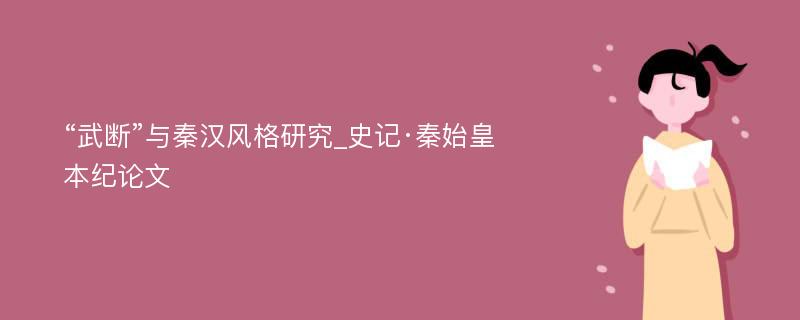
《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现存资料来看,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当以蔡邕《独断》为最早。该书卷二论官文书四体曰:“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揭开了文体学研究的序幕。此后,略晚于蔡邕的曹丕著《典论·论文》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略举四科八种文体,以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西晋初年陆机著《文赋》又标举十体,并对各体的特征有所界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此外,像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直至任昉的《文章缘起》(注:中华书局影印元刻《山堂考索》本。其真伪颇多争论。同门傅刚《〈文选〉与〈诗品〉、〈文心雕龙〉及〈文章缘起〉的比较》(收在《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迎平《〈文章缘起〉考辨》(收在《古典文学与文献论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均认为《文章缘起》为任昉作,其说可从。)、《文心雕龙》等均有或详或略的文体概论,条分缕析,探赜索隐,奠定了中国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萧统广采博收,去芜取精,将先秦至梁代的七百多篇优秀作品分成三十七类(注:通行本三十七类,但是根据南宋陈八郎宅刻五臣注《文选》,还有“移”、“难”两体,这样就有三十九体之说。)加以编录,因枝振叶,沿波讨源,成为影响极为久远的一代名著。从蔡邕《独断》到萧统《文选》,前后绵延三百多年,中国文体学最终得以确立。
《独断》始见于《后汉书·蔡邕传》。《南齐书·礼志上》:“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据此,蔡邕《独断》至少在晋宋以来已广为流传。唐代《日本国见在书目》杂家类著录《独断》一卷。注云:“今案蔡邕撰。”(注:《古逸丛书》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影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据此推断说:“《独断》集外别行见于著录者,莫先于此。其云‘今案’者知其前不著录撰人也。”说明唐代已经有了单行本。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经解类著录:“蔡邕《独断》二卷。右汉左中郎将蔡邕纂。杂记自古国家制度及汉朝故事,王莽无发,盖见于此。公武得孙蜀州道夫本,乃阁下所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礼注类著录:“《独断》二卷,汉议郎陈留蔡邕伯喈撰。记汉世制度、礼文、车服及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礼乐。舒、台二郡皆有刻本。向在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后错互,因并存之。”《玉海》卷五一“艺文”类著录:“《蔡邕传》著《独断》、《劝学》。《书目》二卷,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其书间有颠错。嘉祐中,余择中更为次序,释以己说,故别本题《新定独断》。《光武纪》注引之。”《书林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著录“淳熙庚子(七年),舒州泮宫刻蔡邕《独断》二卷。”此本或即陈振孙著录的“舒、台二郡皆有刻本”中的一种,说明宋代流传的刻本《独断》,均署名蔡邕,没有异议。历代著录,或经解、或礼注、或杂家,显示其内容颇为驳杂,但是,大多言而有据。《四库提要》以为“是书礼制多信《礼记》,不从《周官》。若五等封爵,全与《大司徒》异,而各条辞义与康成注合者多,其释六祝一条,与康成六祝注全符。则其所根据当出一书。又《汉书·舆服志》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是书则谓高七寸,前后出四寸,此词小异。刘昭《舆服志》注引《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则作三公九,诸侯卿七。建华冠注引《独断》曰:‘其状若妇人缕鹿。’今本并无此文。又《初学记》引《独断》曰:‘乘舆之车皆副辖者。施辖于外乃复设辖者也。’与今本亦全异。此或诸家与人援引偶讹。或今本传写脱谬,均未可知。然全书条理统贯,虽小有参错,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证之渊薮也。”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可以证明《四库提要》的论断是有其根据的。如《独断》记载:“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根据敦煌汉简:(1)“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稽首再拜上书。”(2)“名状,其秩命士以上,先以闻,以明好恶,臣稽首以闻。”王莽时有五威将军、五威将帅等职,又称五百石官曰命士,所以根据简文中的职官名称,知其乃新莽时之简。这两支简出自敦煌,从行文看,前一简是臣下对皇帝的章奏文书,当属边塞官吏奏章的草稿,边塞官吏不在朝官之列,故言“稽首再拜”。后一简止言“稽首”,或是朝官奏章经王莽批准,然后以诏书形式下达至边郡的。两份奏书中皆不再用“昧死”一词。这里足以证明蔡邕《独断》所论为完全准确可信(注:参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薛英群《汉简官文书考略》,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独断》的文献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
蔡邕生活在东汉末期,年青时曾从东汉一代名儒胡广问学,年近不惑又进入东观,参与《东观汉记》的写作(注:参见拙文《蔡邕行年考略》,将刊于《文史》总62辑。)。诚如蔡邕本人自述,对于秦汉史料,他可谓穷尽“二十年之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续补《汉记·十志》。六年中,他潜心研读,与当时大儒卢植等人商讨学问,最终接近完成了有关东汉典章制度的重要论述,这就是著名的《十意》(注:《十意》见《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蔡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云云。以意逆之,或许还有《地理意》,然只字未传。《十意》,《隋志》已不著录。但是,唐宋典籍尚多征引。)。因此他的有关秦汉史料的论述,包括文体的分类和文体的界说,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本文立论的基础。
需要有三点说明:第一,一种文体,随着时代的变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趋同分化的变异。因此,研究文体学,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其材料的取舍论证,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不能没有根据地利用后代材料来推断前代的文体特征。具体说到秦汉文体研究,虽然《三国志》、《后汉书》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两书的作者(包括注释者)已经生活在文体学方兴未艾的时代,他们所记载的传主的著述情况,往往是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很难反映秦汉士人的文体观念。因此,对于秦汉文体材料的取舍,只能参照秦汉时代的著述,譬如《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以及秦汉时代流传于后世的单篇文章。第二,文体的分类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可以依据功能上划分,比如说实用性文体或非实用性文体;也可以参照授受对象上划分,譬如发布对象,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或平辈之间;也可以从不同的应用场合来区分,甚至还可以从发表的不同方式来确定。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对于各种文体的要求和重视程度是颇多差异的。就秦汉时代而言,文体的观念还没有后世那么明确,大多数文体还是以应用为主。《独断》所论有两大类,一是皇帝发布的诏书,二是大臣呈递的章表书记,这两类之外的一些重要文体,《独断》没有论列,我们就只能根据蔡邕本人的创作并结合有关史料钩沉索隐,略作商讨。第三,明清以来,《独断》版本较多,可惜迄今未见今人整理本出版,本文所论,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独断》(注:对于此书版本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见拙文《蔡邕著述摭录》,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为基本史料,同时,以蔡邕的创作为参照,进而推论秦汉主要文体的源流及其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二
天子独用的文体有四种,《独断》卷上记载说:“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这四种文体始于汉初。《文心雕龙·诏策篇》:“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所谓汉初定仪则,始于汉高祖刘邦五年,叔孙通制定礼乐制度,至七年始成定制。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陋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其具体内容多已失传。孙星衍《平津馆丛书》辑录有汉官七种,其一即叔孙通《汉礼器制度》一卷、《汉官》一卷。但是没有关于官文书的记载。《汉书·高帝纪》五年诏注引如淳曰:“诏,告也,自秦汉以下,唯天子独称之。”《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元年九月辛未诏下有章怀太子李贤注:“《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从下引蔡邕文字来看,《汉制度》与《独断》颇多相近之处。蔡邕的老师胡广著有《汉官解诂》、叔父蔡质著有《汉官典职仪式》。这在《后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及《太平御览》等书中多有征引。蔡邕的论述或许参考了他们的论述(注:按:《汉制度》之名,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续汉志》补注引谢沈书曰:“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因以为志。”说明蔡邕的论断多借鉴胡广、蔡质等人的论断。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汉官七种》辑录有胡广《汉官解诂》一卷、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
1.策书
《独断》曰:“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丈,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释名·释书契》:“策者,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可见策书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对于形制颇有讲究。“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其次,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再者,应用于不同的场合,其主要功能是封赏大臣就国时用的文体,“约敕封侯”犹如后世策封。《汉书·武五子传》载武帝于元狩六年立齐怀王刘闳、燕刺王刘旦、广陵厉王刘胥时有“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诫焉”。后来策文多所分化,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策析为十类:祝册、玉册、立册、封册、哀册、赠册、谥册、赠谥册、祭册、赐册、免册。这种分析的确有些琐碎,就文体学意义上说,有些是可以合并的,但是从这种分体也可以说明策书的变化。但其基本特征不变,如哀策文依然要用篆体。《后汉书·礼仪志》为皇帝送丧礼:“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李贤注:“晋时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有两行科斗书之,台中外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也。’检校果然。是知策用此书也。”但是赐策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譬如策文大约就是如此。《文章缘起》以为始于汉武帝问三王策文。由此衍伸,又有大臣的对策,如汉太子家令晁错的贤良对策,董仲舒的对武帝策问等就是。《文选》特辟策秀才“文”一类,推终原始,均由策书而来。
2.制书
《独断》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宫,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者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如章怀太子李贤注引《独断》曰:“制诏者,王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诰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裴骃《集解》引蔡邕的话说:“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张守节《正义》:“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珊瑚钩诗话》:“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谓之制。”据此,具有法度意义的命令称为“制”。不过,对于现存史料考察,秦代和西汉,制书往往与诏书并称,称“制诏”。如《汉书·文帝纪》:“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从现存材料来看,区别在于发布的对象和发布的方式。《史记·秦始皇本纪》所称“命为制,令为诏”,前者以公告形式颁行天下(如《文选》所载武帝两篇诏书),在各地方州郡及中央所直属的部门均可以见到这种诏书。如汉简中见存大量诏书多是这种作为法律条文保存下来的。后者以帝王命令形式通告某官(如武帝《诏李陵》),当时也称曰“手诏”。《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有《高祖手诏》一卷。这类手诏中的部分内容被认为有教化功能的,也可以传布天下,如酒泉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制诏皇太子书,据考证是汉武帝遗诏(注:参见《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宋明帝给王景文的《答王景文手诏》和《赐王景文死手诏》也是如此。两者的区别大约如此。故《文选》收录诏书,并没有制书,是可以理解的。
3.诏书
《独断》曰:“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可见是告百官的文书。任昉《文章缘起》:“诏,起秦时。”这是对的。张守节就曾指出:“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说文》无诏字,当是后起字。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称:“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诏,历代因之。”吴讷之书尽管博而寡要,而这段话是对的。《释名·释典艺》:“诏书,诏,照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汉书·高帝纪》五年诏下颜注:“如淳曰:诏,告也,自秦以下,唯天子独称之。”西汉诏书多由皇帝自己起草(注: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二专论“诏”体,以为始于汉代。《廿二史劄记》卷四“汉帝多自作诏”条也有详尽的考证。)。后来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诏书多由尚书来负责起草。诏书的收集整理最早是秦代中央机关保存。《汉书·杜周传》:“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陈梦家《汉简缀述》记载居延地湾出土的甲2551扎,是施行诏书的目录。敦煌HH.1448号诏书,又见于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只不过抄写了半篇多一些,说明当时诏书在不同州郡都存在着有关的档案。到了曹魏,诏书的收集与整理应归于秘书监。
4.戒书
《独断》曰:“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又称戒敕。《文心雕龙·诏策篇》:“戒敕为文,实诏制切者。”可见是对于各地太守的命令。
此外,《独断》还记录了“天子命令之别名”,即命、令、政:“出君下臣名曰命”、“奉而行之名曰令”、“著之竹帛名曰政”。可见当时各种文体的区分十分明晰。
三
蔡邕《独断》卷上记载大臣呈递文书也有四种:“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文心雕龙·章表篇》:“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
1.章
《独断》曰:“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当是谢恩时作也。《文心雕龙·章表篇》称:“章者,明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其特点是“对扬王庭,昭明心曲”。任昉《文章缘起》认为上章始于“后汉孔融《上章谢太中大夫》”。其实蔡邕有《戍边上章》就是这种“昭明心曲”之作。这篇文章作于光和元年,蔡邕四十六岁。由于犯颜直谏,被流放朔方,故作此文,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续补《汉书·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后汉书》本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这篇文章披肝沥胆,近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2.奏
《独断》曰:“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当是按劾时作也。《论衡·程材篇》:“进退失度,奏记言事。”《后汉书·班固传》注:“奏,进也。记,书。”这种文体,秦时称奏,《文心雕龙·章表篇》:“秦初定制,改书曰奏。”奏以按劾。按《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奏事二十篇,原注:“奏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同时,或曰奏记,或曰上书,或曰奏札,或曰奏状。如汉代董仲舒有诣公孙弘奏记,任昉《文章缘起》以为奏书之始。此文仍存于《古文苑》卷十,题《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后汉书·百官志》:“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后汉书·班彪传》李贤注:“汉官仪曰: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
3.表
《独断》曰:“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口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当是陈请时作也。《释名·释书契》:“下言于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又曰上,示之于上也。又曰言,言其意也。”任昉《文章缘起》以为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表》为这种文体的最早创作。让表,始见于汉东平王刘苍《上表让骠骑将军》。表的核心还是表明心迹,故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称:“表者,标也。”用“表以陈请”最为明晰。多数奏表是以公开形式上呈的,或陈请,或让封,或推荐。如张溥编《蔡邕集》中《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表》、《尚书诘状自陈表》、《表贺录换误上章谢罪》等就是陈请表;《荐皇甫规表》、《荐太尉董卓表》等就是推荐表;《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再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让尚书乞在闲冗表》等就是让封表;《巴郡太守谢表》、《辞金龟紫绂表》(阙)等就是谢恩表,等等。大臣奏表还有一种更加公开的上书方式,就是露布。《三国志·王肃传》注引《世说》:马超反,劫贾洪作露布,钟繇识其文,曰:“此贾洪作也。”《文章缘起》引此以为露布之始。其实,露布之名,汉已有之,但非专用于军旅,而是一种公开上书的激烈方式。《汉书》记载,何武为刺史,劾奏属吏,必先露章。《后汉书·礼仪志》:大丧则“诸侯王遣大夫奉奏,吊臣请驿马露布”。又汉桓帝时地震,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露布又谓之露版。《文心雕龙·檄移篇》曰:“露布者,盖露版不封,播诸视听也。”(注:有关露布的研究,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一“露布”条。)还有秘密上奏的形式。《后汉书·蔡邕传》:“又特诏问曰:‘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郡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史载:“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就是说,“其言密事得皂囊盛”者,近臣也不得而闻。但是曹节却偷看了蔡邕的奏章,结果,蔡邕以此获罪。在《尚书诘状自陈表》中,蔡邕抱怨说:“臣实愚赣,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尽心之吏,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公孙瓒初平二年上书讨伐袁绍文中有“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之句,章怀太子李贤注:“《汉官仪》曰: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表启的特点诚如《文心雕龙·奏启篇》所言:“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其文体除开头结尾有所要求外,行文用散体,唐宋以后多四六体。
4.驳议
《独断》曰:“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赣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当是执议时作也。《文心雕龙·议对篇》:“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这种文体是否始于汉代,尚可讨论。《韩非子·存韩篇》在韩非上书秦王后,“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下臣斯。臣斯甚以为不然”。李斯作《上秦王驳议韩非书》。题目虽然是后人所拟,但是,其内容正符合驳议的要求。《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难夏育请伐鲜卑议》,设五不可反对出兵征讨,用来反驳夏育的《上言讨鲜卑》表。《宗庙迭毁议》等均属于驳议一类。此外,蔡邕的《历数议》、《答斋议》、《和熹邓后议》、《朱公叔谥议》等可谓事切情举,文洁理辨,符合《文心雕龙·议对篇》“动先拟议,明用稽疑”的要求。
除上述四种文体外,还有所谓的笺、启、封事等。据《宋本东观余论·跋钟繇贺捷表后》考证,“古人笺启多不用年,至表奏则与笺启异,其称年无疑”。《东观汉记》卷一:“(建武)七年正月,诏群臣奏事无得言‘圣人’。又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里封事,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诣北军待报,前后相尘,连岁月乃决。上躬亲万机,急于下情,乃令上书启封则用,不得刮玺书,取具文字而已。奏诣阙,平旦上,其有当见及冤结者,常以日出时,驹骑驰出召入,其余以俟中使者出报,既罢去,所见如神,远近不偏,幽隐上达,民莫敢不用情。”王益之《西汉年纪》卷十九:“又故事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诏:“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章怀太子注:“宣帝始令群臣奏封事宜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后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拥蔽。”其形式大同小异。大臣往下发布的文字有教、令、文等。《文选》卷三十六引蔡邕《独断》曰:“诸侯言曰教。”《文心雕龙·诏策篇》:“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珊瑚钩诗话》:“出于上者谓之教,行于下者谓之令。”《后汉书·荀韩钟陈传》:“时中常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陈)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李贤注:“檄,板书。谓以高伦之教,书之于檄而怀之者,惧泄事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通鉴》胡注曰:“郡守所出命曰教。”
这类章奏等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格式要求。《隶释》卷一著录《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即《乙瑛碑》)后考证云:“予家所藏石刻,可以见汉代文书之式者,又《史晨祠孔庙碑》、《樊毅复华租碑》、《太常耽无极山碑》,与此为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国,二也;郡国上朝廷,三也。”高文《汉碑集释》称:“奏牍文移,每言一事,再三繁复,钞录原文,汉时已然,可与《史记·三王世家》参看。”《敦煌汉简释文·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收录奏书103枚,大约就是这些奏书的副本。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综论》有“居延简所见汉代典章及公牍中习俗语”,对于敢言之、敢告卒人、粪土臣、唯官移、状辞、劾状、上言变事等常用台头作了较详尽的考释,此不赘述。
大臣奏书不一定都要自己写作,捉刀代笔在两汉并非稀罕。因此,两汉就出现了一些以写奏书出名的文人。《东观汉记》卷十九:“蒋迭字伯重,为太仆,久在台阁,文雅通达,明故事,在九卿位,数言便宜,奏议可观。”《后汉书·文苑·葛龚传》:“葛龚字符甫,梁国宁陵人也。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著文、赋、碑、诔、书记凡十二篇。”注:“龚善为文奏,或有请龚奏以干人者,龚为作之,其人写之,忘自载其名,因并写龚名以进之。故时人为之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不过,这终究不是办法。阳嘉元年左雄上书就要求“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说明对于文吏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能笺奏”。
四
《后汉书·蔡邕传》称其“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后汉书》虽然成于刘宋时代,其中所涉及的文体观念,难免有后人附加的成分。但是,《蔡邕传》中所谓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等文体在秦汉时期确实已经为当时士人所熟知,所掌握,可以说是当时的主要文体。
诗赋同源而异流(注:《释名·释典艺》:“诗之也志之所之也,兴物而作,谓之兴。敷布其义,谓之赋。事类相似,谓之比。言王政事,谓之雅。称颂成功,谓之颂。随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均源于先秦。《文章缘起》说四言诗始于前汉楚王傅韦孟谏楚夷王诗当然是不妥的,因为四言诗体早就见于先秦,这是文学史的常识,不必赘议。同时,任昉又说:五言诗始于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六言诗始于汉大司农谷永,七言诗始于汉武帝柏梁殿联句。这三种诗体具体始于何时,目前还有较多异议,但是其盛行于两汉,则是毫无疑问的。五言诗起源于两汉,材料斑斑,不胜枚举。孔融《六言诗》共有三首。七言诗即使不是始于汉武帝柏梁殿联句,也不会晚于张衡的《四愁诗》(注:参见拙文《七言诗渊源辑考》,见《玉台新咏研究》上篇,中华书局2000年版。)。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专论上述诸体诗的缘起,认为多兴于两汉,此说是可以成立的。《蔡邕集》中有四言诗(如《对答元式诗》)、五言诗(如《翠鸟诗》)、六言诗(《初平诗》)的创作,一般的文学史多有论列。其它文体,就蔡邕的创作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等。
古代帝王祭天时刻石纪功,碑文或始于此。作为纪事之碑似乎始于秦汉。李斯刻石曰碑。汉惠帝有四皓碑。见任昉《文章缘起》。与此相关的有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墓志铭等,大多始于秦汉,《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庐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赵翼《陔余丛考》“碑表”条认为始于秦汉。汉代碑碣,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发端起例,辑录考释,清人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踵武前贤,集其大成。近世发现的碑碣文献,又有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高文《汉碑集释》等,将汉碑文献网罗殆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读过之后,我们发现汉碑大多有这样几个相近的特点:第一,叙事简略;第二,文字古朴;第三,格式定型。这也难怪,倘若碑板文字洋洋洒洒,动辄千言,势必给镌刻者带来难度。故文字尚简,是其基本要求。然而,时易世移,蔡邕生活的时代毕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浮华相尚,雕丽为文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蔡邕的碑板文字也不免染上浓重的时代色彩。譬如在行文中注重隶事用典,遣文造句追求工丽华美。诚如《文心雕龙·诔碑篇》所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根据张溥编《蔡邕集》,今存蔡邕碑文凡三十六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刘勰提到的《太尉杨赐碑》、《陈太丘碑》、《郭有道碑》、《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公碑》等,将其视为蔡邕碑文写作的代表。对此,笔者另有《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专门论述。
诔,作为一文体,早在先秦即已出现。《周礼·大祝》称:“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茕茕予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汉代之诔,任昉《文章缘起》认为始见于汉武帝《公孙弘诔》。此篇已经失传。《东观汉记》卷七:“平原王葬,邓太后悲伤,命史官述其行迹,为作传诔,藏于王府。”无论谥与诔,均由朝廷出面,故《白虎通·谥》曰:“诸侯薨,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遣大夫会其葬而谥之何?幼不诔长,贱不诔贵,诸侯相诔,非礼也。臣当受谥于君也。”《汉书·景帝纪》载,中元二年(前148)“癸巳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应劭注:“皇帝延诸侯王宾王诸侯皆属大鸿胪。故其薨,奏其行迹赐与谥及哀策诔文也。”颜师古注:“诔者,述累德行之文。”本来是帝王重臣所作,后来则下移。这些都是有制度保证的。但是到了东汉后期,私谥之风盛行。如蔡邕等人为朱穆议谥就是典型一例。
铭的本意名,即将祖先功德警语等刻于器物上,用以借鉴。故《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释名·释典艺》也说:“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汉书·艺文志》有《皇帝铭》六篇。《孔丛子·巡守》:“子思游齐,陈庄伯与登泰山而观,见古天子巡守之铭焉。陈子曰:我生独不及帝王封禅之世。”任昉《文章缘起》认为铭文始见于秦始皇登会稽刻石铭。《陔余丛考》卷三十二“墓志铭”认为始于汉代。在汉代,铭文最多的是李尤、班固、崔瑗等。而最有名望的是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蔡邕集》中有十篇:《黄钺铭》、《东鼎铭》、《中鼎铭》、《西鼎铭》、《朱公叔鼎铭》、《胡太傅祠前铭》、《京兆尹樊德云铭》、《樽铭》、《警枕铭》、《盘铭》等,其中《朱公叔鼎铭》“全成碑文,溺所长也”。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说的蔡邕的碑、铭、赞等文,实际上文体大体一致,于此可以得到印证。蔡邕另有《铭论》专论铭文的特点。后来陆机《文赋》更明确概括为“铭博约而温润”,李善注:“博约谓事博文约也。”即纪事简约,文辞温润。
赞,《释名·释典艺》:“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文心雕龙·颂赞篇》:“赞者,明也,助也。……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文章缘起》也以为司马相如《荆轲赞》为赞体最早创作。《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荆轲传》五篇,班固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可惜此文已经失传。此外,刘歆还作《列女传赞》。赞的特点是四字韵文,“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蔡邕集》有《焦君赞》、《太尉陈公赞》、《琴赞》等三篇。
连珠,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历历如贯珠,故谓连珠。傅玄《叙连珠》称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文心雕龙·杂文篇》谓“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此后,这种文体在东汉章帝之世盛行一时。班固、贾逵、傅毅三人受诏而作,而蔡邕《广连珠》又踵事增华。班固喻美辞壮,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蔡邕言质辞碎。在文学史上,连珠体创作最有名的莫过于陆机《演连珠》五十首,见《文选》收录。此后,谢灵运《连珠集》五卷,刘祥《连珠》十五首,陈证《连珠》十五卷,黄芳《连珠》一卷,梁武帝《连珠》一卷,和者数十人。台湾学者廖蔚卿在《论连珠体的形成》、《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艺术及其影响》(注:廖蔚卿的系列论文见所著《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大安出版社1997年版。)等文对这种文体的缘起、特点以及重要作家、作品等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很值得参看。
箴,《文章缘起》谓这种文体始见于扬雄《九州五官箴》。《文心雕龙·铭箴篇》称:“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蔡邕有《衣箴》、《女箴》。此外,还有《女训》、《女诫》也是这类作品。
吊,也始于汉代。《文心雕龙·哀吊篇》:“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沉膇。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可见,吊体,均本于贾谊之《吊屈原赋》,皆有感而发。蔡邕有《吊屈原文》,也是这样一篇作品,称得上“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
论,《释名·释典艺》:“论,伦也,有伦理也。”这种文体虽然始于先秦,而且《文心雕龙·论说篇》也认为先秦文字优于两汉,但是蔡邕的《正交论》、《桓彬论》、《明堂月令论》等仍有其独特的价值。朱穆著有《崇厚论》,以老庄为核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与此相似的还有《后汉书·朱乐何传》李贤注所载之《绝交论》,亦矫时之作。“蔡邕以为(朱)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李贤注详引蔡邕《正交论》。梁冀当权时,延笃也作有《仁孝论》。见《后汉书·吴延史卢赵传》。这些作品,风清骨峻,堪称一代名文。
五
根据张溥编《蔡邕集》,除前面论列的文体之外,还有书、颂、记、祝、诰、对问、设论、章句等文体也应提出来加以讨论。这些文章的命名虽出于后人之手,但是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相关资料足以证明这些文体也多盛行于秦汉。
书札是一种古老的文体。《释名·释书契》:“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1975年11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西侧睡虎地发现古代墓葬,其中十一号墓出土秦代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支(另残片八十余片),内容大部分是秦的法律条文和公文程序。墓主据推测是一个叫“喜”的男子,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并曾治狱于鄢,是秦的地方官吏,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注:详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经过整理编为《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四号墓出土了木牍两件,正反两面都有字迹,是黑夫与惊两人写给衷的家信,其中一件保存较好,另一件下半残缺。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字考释以及法律文书方面,这的确是全新的内容。周凤五《从云梦简牍谈秦国文学》着重分析了四号墓中《黑夫尺牍》和《惊尺牍》内容及形式上的特点,具体而微(注:详见台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古典文学》第七集,学生书局1985年版。)。居延汉简中很多书信,表现了戍守西北边地士卒的心声。如《居延汉简合校》10.15:“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甚苦。塞上署时,愿幼孙少妇足衣强(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综论》作“弥”)食,慎塞上,宣幸(陈直作“毕”)得幼孙力过行边,毋它急。/幼孙(陈直作“都”)以润月七(陈直作“十”)日,与长史君俱之居延,(陈直有“言”字)丈人毋它急,发卒不审(陈直作“得”)得见幼孙不(陈直有“也”)。它(陈直无此字)不足数来/记,宣以十一日对候官未决,谨因使奉书,伏地再拜,幼孙少妇足下。朱幼季书,愿高(陈直作“颜亭”)掾幸为到临渠燧长,对幼孙治所□书,即目起,候官行兵(陈直作“矣”),使者幸未到,愿豫自辩(陈直作“辨”),毋为诸部殿……”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综论》“西汉书札的形式”云:“两汉人的书牍,现两《汉书》各列传所载主要在保留文章,对于书牍上下款式,皆被删除。只有《文选》,尚保存一部分原形,例如《太史公报任安书》,首云:‘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末云:‘谨再拜。’至曹魏时,笺启用于长吏,笺皆称某死罪死罪,启皆称某某启。《文心雕龙·奏启篇》云:‘启者闻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奏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云云。《流沙坠简考释》释二、杂事类八十七有‘时尽有入出复白谨启’残简。《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54页第二十有‘掾杨善谨启’残简,皆属吏用于长官者,包含有章表性质,与私人往来书牍,尚不相同。友朋通讯,则改称某白。”而且汉人比较重视书写较好的书信。《汉书·游侠列传》:“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至于居延简书牍上下款形式,与古籍所载不同之点,亦分别如次:一伏地再拜,二称白,三称叩头,四称坐前及叩安。“从上列四种形式分析,以某伏地再拜,或某伏地再拜请一种最为普遍,敦煌简亦然,知为西汉中晚期书牍之通例,为汉代古籍所未详。坐前及上叩大安,已与后代之称阁下及书尾问安之习惯相似。”杨树达《汉书窥管》引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一云:“古人往来书疏,例皆就题其末以答,唯遇佳书心所爱玩,乃特藏之,别作柬以为报。晋谢安轻献之书,献之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汉人藏遵尺牍,亦爱其笔画也。”
颂,渊源于《诗经》颂体。诚如《诗序》所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屈原有《橘颂》。《论衡·须颂篇》:“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邪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汉代颂体始见于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已经录入《文选》。蔡邕的颂体创作《京兆樊惠渠颂》最有名,特别是序,比正文长两倍,论述农田水利的重要性,歌颂了京兆尹樊陵命伍琼开掘樊惠渠、使卤地化为良田的事迹。所以《文心雕龙·颂赞篇》称:“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此外,《东巡颂》、《南巡颂》、《陈留太守行小黄县颂》、《颍川太守王立义葬流民颂》、《胡广黄琼颂》、《祖德颂》、《五灵颂》、《麟颂》等九篇也多文辞清烁,敷写似赋。
记,是先秦史学的著述形式。《释名·释典艺》:“记,纪也,纪识之也。”这种文体,记载各国大事,以祭祀和故事为主。关于战事以及政事的记录,便是“史”;关于祭祀仪式程序的记录,积累起来,形成通例,便是“礼”。《礼经》原有“记”的性质,因而战国秦汉的学者解释《礼经》的书籍通称为《礼记》。礼乐密切相关,记录典礼仪式必涉及乐歌,因而又产生了《乐记》(注: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记,通常有两种格式,一种前书月、日,不录发文官府的全称和首长人名。另一种前书月、日、官职、人名等(注:《敦煌汉简释文·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辑录记体凡96枚,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蔡邕有《车驾上原陵记》属于祭祀仪式程序的记录。
祝,祭词。《说文》:“祝,祭主赞词者。”《玉篇》:“祝,祭词也。”也认为是祭祀之文。《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孔颖达疏:“王命有司作策书,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读此策,唯告文武之神。”《周礼·春官》:“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卢: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这种文体的特点,刘勰概括为:“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蔡邕集》收录的《宗庙祝嘏辞》、《九祝文》、《祝社文》、《祖饯文》、《禊文》等六篇多作于迁都长安之后,乃奉董卓之命而作。按照《文心雕龙·祝盟篇》的要求,颇有距离,难怪要为后人诟病。
诰,任昉《文章缘起》云:诰,汉司隶从事冯衍作。按《后汉书·冯衍传》:“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禄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李贤注:“衍集有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李贤又云:“衍集有《问交》一篇、《慎情》一篇。”蔡邕《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黄氏神诰》也是这类作品。
对问,这种文体始于宋玉《对楚王问》(注: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有《策问与对策》一文,对此论之甚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蔡邕集》有《答诏问灾异八事》、《对事》等。《文心雕龙·杂文篇》论三种文体,其一即对问,其二为七体,其三为连珠。在对问下,所列举的是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崔骃的《达旨》、张衡的《应闲》、崔寔的《答讥》、蔡邕的《释诲》、郭璞的《客傲》等。而刘勰所论的前三篇,又都收入《文选》,归入“设论”体,紧接在“对问”之后。可见,《文选》与《文心雕龙》对于这两种文体的认识是有区别的。所谓设论,也就是一问一答的方式,就形式而言,对问与设论没有多少区别。蔡邕的《释诲》,“体奥而文炳”。即文思深刻,文采粲然。其实刘勰所列举的这些创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抒发作者怀才不遇的情绪。蔡邕二十七岁被迫应征到京城为新贵鼓琴,霖雨泥泞,心绪黯然。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述行赋》,称病而归,继作《释诲》来用老庄思想自慰。
此外,汉代为儒家经典作注疏的新文体,即注疏体,主要有故、传、说、记、章句、笺等,而蔡邕只有《月令章句》一种。《说文》:“章,歌所止曰章。”“句,曲也。”钱穆谓家法即章句,是汉宣帝时兴起的一种著作形式。徐防作《五经宜为章句疏》,见《后汉书·邓张徐张胡传》:“永元十年,迁少府、大司农。防勤晓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诏书下公卿。”而汉人最为重视的故、传、说、笺等,蔡邕反而没有著作。从文体的写作可以推断蔡邕是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并不是一个恪守传统矩矱的经学家。诚如洪业《礼记引得序》所称:“蔡邕长于文史,不以经学名家。至其所为《明堂论》,征引及《周官》及《礼记》古大明堂之礼,则非笃守《今礼》者也。夫校订官立《今礼》而委之好习古学之人,则笃守二戴之经者时无闻人,而贯通今古之学已成风气欤?”
从秦汉文体学,甚至还可以扩大一点说,从先唐文体学的发展来看,至少可以注意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古代文体在秦汉时代已经初具规模。《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论述各种文体多达五十余种,作者本着“原始以表末”的原则,推溯源流,将各种文体的起源、流变以及重要作品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其中除少数文体如“启”类出现于汉代以后外,多数重要作品均产生于秦汉(注:二十一篇中,《杂文》中细分“对问”、“七发”、“连珠”;《诏策》中细分“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教”;《书记》中细分“谱”、“籍”等二十四种。)。这种观念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看法。甚至像《文章缘起》论列八十五体,就明确标明始于秦汉者六十七体(注:除前面已经论列之外,尚有玺文、反骚、白事、移书、序、志录、誓、明文、解嘲、训、辞、旨、喻难、谒文、悲文、祭文、哀词、离合诗、图、势、约。)。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文体的分类不尽合理,譬如将扬雄《解嘲》与崔骃《达旨》分列两种文体,似乎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是他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秦汉以后,文体观念日益明确。第二,在唐前士人心目中,实用性文体与抒情性文体并没有明显的泾渭之分,都为他们所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应用性文体更能得到时人的重视。第三,无论是哪一种文体,尽管其形式多有变化,但是对于文采的要求始终是一贯的。如前所述,就是一些应用性很强的文体也多讲求文采。
综上所述,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代基本定型。
标签: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文; 三公九卿论文; 独断论文; 汉朝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后汉书论文; 叔孙通论文; 文选论文; 东观汉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