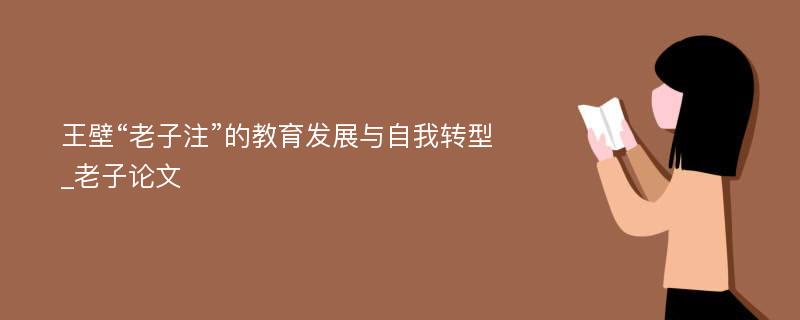
教化与自化在王弼《老子注》中的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弼论文,老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6)04-0068-07 《老子》文本处处渗透着对作为治者的侯王进行教化的意味,除了教化,《老子》中还明确出现了“自化”的表述,教化与自化在《老子》中分别指向侯王和百姓两个群体。《老子》对侯王进行教化的言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却几乎未言及对百姓之教化,依《老子》的表述,在百姓身上实现的是“自化”,一种似乎无需借助任何外力的自然而然的实现。然而,在《老子》看来,百姓的自化实际上要以侯王的自我完善为前提和基础。亦即,《老子》将社会得以治理的重心放在侯王身上。王弼的《老子注》大体上延续了这样一种论述格局,但又不是一味地重复,而是将其以更为概念化、理论化的方式呈现,《老子》关于教化与自化的论述正是被统摄在王弼提出的“无”的概念及“以无为本”的命题之下,而这些核心表述的产生乃基于“有形”“无形”之辨。可以说,王弼对“形”的理解和论述撑起了他要建构的新的理论言说系统。本文乃基于王弼对“形”的论述来看《老子》有关教化与自化的论述如何在一个更为理论化的言说系统中进一步展开。 基于“以无为本”“崇本举末”的立论,王弼对“形”之限与蔽加以剖析。在他看来,儒墨名法杂诸家思想均属于滞形离本,缺乏一种立足于“无”的更高视野,因此难逃片面性。鉴于此,王弼自然不能完全赞同未能超越“形”之限制的儒家教化。然而,一方面是批判,另一方面却在思想中处处渗透着对治者进行教化的意味。王弼对治者的教化以“体无致虚”为立论根据,主张教化应时刻不离“体无”之根本。相对于儒家的礼乐教化,这貌似是一种“非典型”教化,然而,从两种教化所期冀实现的目标而言并无二致,王弼早已将儒家经由礼乐教化实现的理想纳入到其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他更强调一种自然而然的实现。此外,对教化与自化的诠释特色还表现在王弼更加注重并强调从根源处着手,主张在“未兆”“未始”之时要戒慎,用他自己的表述,即在“未兆”“未始”之时的“存诚”“推诚”。“诚”是治者必须持守的原则,这一原则又意味着将包容、尊重百姓的个体特性作为百姓实现自化的前提加以强调。 一、“形”之限与蔽 1.“有形”与“无形”之辨 如果说王弼对《老子》的诠释特色在“本末”“有无”之辨的话,对“本末”“有无”之辨的论述则是基于对“形”与“无形”关系的阐释来建立。①《老子指略》②开宗明义说: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1](P195)③王弼认为,有一“形”即可定一“名”以与“形”相对。反之,“无形”便“无名”。因“万物之宗”不具备一特定之“形”,便无法给予其一“名”,则“万物之宗”即为“无形无名者”。 这作为“万物之宗”的“无形无名者”就是《老子》哲学所特别看重的“道”,而在《老子注》中,王弼则是将“道”视作对“万物之宗”的称谓之一。他说: 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老子指略》) 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同上) “道”,称之大者也。(同上)据这些表述看来,“道”不再是《老子》文本中那个对宇宙终极实在的最高指称者,而变成了尝试对“万物之宗”有所言说的称谓之一。因此,虽然《老子》和王弼《老子注》均以“道”来指称或提示宇宙终极实在或“万物之宗”,但显然“道”这一表述在《老子注》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它不再是《老子》中那个统称之“道”,而是与“玄”“深”“大”“微”“远”等言说相并列,它们都被看作循不同视角对“万物之宗”的称谓。换言之,《老子注》所言之“道”的内涵乃在“万物之所由”这一意义上得以固定,其内涵则比《老子》中之“道”狭窄许多。正因为这样,王弼说: 言道则有所由,有所由,然后谓之为道,然则道是称中之大也。不若无称之大也。(《老子》二十五章注) “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老子指略》)“道”乃“未尽其极”,自不适合用来指代终极依据。王弼则以“无”取代《老子》中“道”的象征和地位,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命题。[2](P99)④将“无形无名者”演绎为“无”,乃基于“万物之宗”之“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老子》十四章注),这个注解非常精辟,它提示了“无”比“道”更高明的地方即在于“通”“往”,这种“通”与“往”正是将《老子》思想中消弭事物界限,强调事物间在其根源处相互联系的一面提炼性地呈现出来。 “无”即“无形”,⑤亦即“本”、即“母”,与《老子》文本相比,王弼注特重“形名”之辨,从阐述对“形”的认识和批判着手,阐论“崇本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观照“以无为本”。 2.道之与形反 在《老子指略》中,王弼围绕“形”的性质和局限有所评论。他说: 形必有所分。(《老子指略》) 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同上) 无形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同上)王弼认为,最危险的莫过于“见形而不及道”(《老子指略》),也就是说,只见到具体事物之外在表现,却未能懂得作为事事物物的根源之道,这无异于“用其子而弃其母”。对“形”的不信任,在一个面向看是由于“形”意味着“分别”和“限制”,更深层的原因是“道与形反”(《老子指略》)。事物的根源和实质往往与其表象(“形”)相反,如果执滞于表象(“形”),很可能与“道”背反: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尅,乃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为存,以其不忘亡也;安者不以安为安,以其不忘危也。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老子指略》)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必然有胜极而衰、衰极而胜的可能,任何一个面向的状况之中都有潜在的向其反面发展之“几”。⑥因此,如果一味地安于现状,未能洞悉并时刻戒慎事态向反面发展的可能,则必然会面临更严重的危险和不安。所以,更确切地说,论述“形”之蔽的实质指向了批评对“形”之表象的迷惑和执滞,王弼最担心的是对“形”之执滞造成蔽于一曲: 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老子指略》) 执滞于“形”无疑会造成对道的片面认识和理解。王弼对法、名、儒、墨、杂诸家的批评与这一表述是一贯的。他说: 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同上)按此,法、名、儒、墨、杂诸家都只是对社会的一侧面之“形”(不齐同、不真、不爱、不俭啬、不美)有所见,进而据所见之“形”来采取对治举措(刑以检、言以正、誉以进、矫以立、总以行)。殊不知,这些对治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生巧伪、失理恕、争尚起、乖违作、秽乱兴)。此即“每事各为意,则虽辨而愈惑”(《老子指略》)。对此,王弼进一步评论说:“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物失载,未足多守也。”(《老子指略》)“子”即“形”,“母”即“无”,“物失所载”即“失载于无”。如果只停留于对“形”的认识,不明了“形”背后的“一统之道”的话,则每一种对治之方都有局限,因为每种对治策略都只是建立在片面认识的基础上,缺乏一种全局视野,那么,此类对治策略很可能令事态发展至背道而驰、甚至失控的境地。 “道之与形反”的命题,最终要揭示的是: 安者实安,而曰非安之所安;存者实存,而曰非存之所存;侯王实尊,而曰非尊之所为;天地实大,而曰非大之所能;圣功实存,而曰绝圣之所立;仁德实著,而曰弃仁之所存。(同上)实现“安”与“存”,“侯王之尊”与“天地之大”,“圣功之存”与“仁德之著”,都不是在“安”“存”“尊侯王”“大天地”“立圣功”“著仁德”等方面用力的结果,反而是不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结果。“安”与“存”,“侯王之尊”与“天地之大”,“圣功之存”与“仁德之著”,无非都属一“形”之表现,依王弼所见,执著于这一“形”,便同时就伴随着有蔽于这一“形”的危险。因此,他继而指出: 既知不圣为不圣,未知圣之不圣也;既知不仁之为不仁,未知仁之为不仁也。故绝圣而后圣功全,弃仁而后仁德厚。夫恶强非欲不强也,为强则失强也;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有其治乃乱,保其安而乃危。(同上)王弼反复强调的是,崇尚或推举“圣”“仁”,其实很容易导向“圣”“仁”之反面。有鉴于此,则应“取天地之外,以明形骸之内”(《老子指略》)。“形骸之内”的表述很可能是王弼受了庄子的影响。庄子特重“形骸之外”与“形骸之内”的对比,⑦王弼所说的“天地之外”即“形骸之外”,即“形”之外,即“无形不系之道”。[1](P63)⑧此即是说,要对“形骸之内”的“形”取得了解,并不是对个别之“形”本身有多么透彻的把握,而是要取得对作为“天地之外”的“道”理解,只有理解了“道”,才能对“形骸之内”的诸“形”有统贯的把握。“天地之外”是“形骸之内”的根本。“形骸之内”是“子”,“天地之外”是“母”,按此,法名儒墨杂诸家所关注和对治的问题均属“形骸之内”的某一面向,然而,他们越是看重“形骸之内”的某一个面向,却越易陷入蔽于一偏的境地。 有关“形”的讨论,王弼与庄子有颇为相近的旨趣。只是庄子否定“形”的态度更为坚决,由于王弼所要批判的是“滞于形”之蔽,因此,“形”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仍保有一席之地,这跟他提出的“守母以存子”的命题是一贯的。存“形”的前提是“以无为本”。只要在“无”的视域内,“形”即可得而存。按此,法名儒墨杂诸家所倡导之价值(齐同、真、爱、俭啬、美)也只有在“无”的视域内才能得以全安。 《老子》所反对的并不是诸家所倡导的价值本身,而是反对将这些价值特加推崇,以及为实现这些价值所各自采取的一些特殊的途径和方法。对此,王弼说: 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绝盗在乎去欲,不在严刑;止讼存乎不尚,不在善听。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老子指略》)“邪”“淫”之产生,表面是“邪者”“淫者”的所行所为,但起邪淫之根源,却并不在他们自身。因此,若只是以“善察”和“滋章”来对治“邪”“淫”,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同理,“严刑”和“善听”亦非“绝盗”“止讼”的根本之道。在王弼看来,对治“邪淫”的根本之道不在“攻其为”“害其欲”,亦即是说,不是针对邪淫之表现而加以对治,关键是在“邪淫”之“未兆”“未始”之时即使人“无心于为”“无心于欲”。 从王弼的立场来看,儒家的教化方案无疑是滞于“形”而不见“道”。“兴仁义”之儒家教化乃针对“薄俗”加以提倡。然而,问题在于,执定于“薄俗”之表象加以对治,本质上未能有见于问题之根本,这将造成任何一种对治都是徒劳的,不但未能解决问题,甚或愈演愈烈。 摆脱对“形”的执滞,站在“体无”的高度,则儒家认为通过礼乐教化才能实现的仁义礼敬,在王弼看来都会自然而然地充满世问: 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尚焉,义则竞焉,礼则争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老子》三十八章注)这段文字是王弼总结形名之限、阐论仁义礼敬之自然显尚的最经典论述。 王弼试图通过对“形之限与蔽”的剖析来指出儒家教化之治标不治本,这种演绎虽未超出《老子》文本的基本立场,却对《老子》的观点给出了更理论化、更系统性的诠释和说明,可谓是《老子》思想的深化。 二、治者之教化 《老子》视对治者的教化明显重于对百姓之教化,认为对治者的成功教化乃是百姓自化的前提和基础。王弼在其注中继续贯彻这一立场,在讨论治者的工夫论时,他的概括是应在“未形之时”“存诚”,这可以说是他从对“形”的论述出发,以理论化、概念化的方式诠释《老子》思想较为典型的例证。引入“诚”的概念则是王弼注《老子》的一大亮点。 1.“体无致虚”之“玄德” 就《老子注》而言,当有关“本末有无”之辨的论述落实到人世层面时,其字里行间的政治哲学意涵极为鲜明,关于政治的讨论则有相当大篇幅是围绕治者应具备的品质展开的,《老子》称之为“玄德”。对此,王弼注说: 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有德无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老子》十章注) “玄德”体现为“有德无主”。基于“不塞原”“不禁性”“不宰成”的行事原则,让物“自生”“自济”“自长足”,所以,虽然德之功成,但施德之主却不见。这就是治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治者行不言之教,其所以能成就对百姓的教化之功,前提在于治者能够先行体道。先行体道的治者并不是作为一个如儒家所推举的有德者之楷模,以其人格魅力和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感化百姓,或者说,这在王弼看来并不是令百姓自化的关键环节,最重要的是治者能够深切理解怎样的治理原则和态度才是对百姓最好的。因此,在《老子注》中阐述理想的治者行事原则的篇幅颇多。 首先,王弼强调治者的自我教化是全部教化的起点。他说: 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老子指略》)“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指示出“己”之责任重大。《老子》七十五章注又说: 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从上也。(《老子》七十五章注)如果说“必求诸己”适用于对治者和百姓的共同劝诫,则七十五章这段注明确地指出在上位的治者需要对民之僻及治乱之兴负责,治者的行为乃是一切治乱之起点。 其次,既然治者的行事关系重大,则必须保证其行为适当。然而,在王弼看来,治者并非圣人,治者之行事未必能时时处处合于道,甚至相反,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犯错,因此更有必要对其加以教化。对于“为何要进行教化”这个问题,王弼的立论乃基于其对人性的理解。他所理解的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他说: 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盲、聋、爽、狂也。(《老子指略》) 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能使之正者何?仪也,静也。又知其有浓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辞不生;若全异也,相近之辞亦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异,取其共是。无善无恶则同也,有浓有薄则异也,虽异而未相远,故曰近也。(《论语释疑·阳货》)可见,作为自然本性之性无所谓善恶,却有浓薄之异,浓与薄之分别就在“逐欲迁”抑或“欲而不迁”。逐欲而迁就是对性的过度满足,逐欲不迁就是对性之适当满足。对性的过度满足就与自然相背。基于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老子》和王弼都对过度之欲非常警惕,在他们看来,治者之自贵、自见、自恃之根源都是由于过度欲望使然,一旦这种过度之欲萌生,则必会发展出躁欲、威权,直至愈演愈烈。⑨所以,对治者而言,《老子》和王弼总是提倡不自贵、不自见,一方面肯定治者的基本欲望应该得到满足,同时又时刻戒慎过度欲望的发展,这是《老子》和王弼强调自我限制和规约的思想根源。 其三,在《论语释疑》中王弼将避免“逐欲而迁”的原则归纳为“仪也”“静也”,“仪”即“以自然为仪”“以自然为法”。[3](P3)在《老子注》中,治者自我教化的根本原则表述为“体无致虚”,这两种表述是相通的。如果说“见素抱朴”“处虚”“守静”“守柔”“不争”“去欲”等表述在《老子》中可以理解为是面向世间所有人之教化的话,相同的表述在王弼的诠释语境中则多指向治者。他说: 圣行五教,不言为化……五教之母,不皦不昧,不恩不伤……治不以此,则功不成。(《老子指略》)“体无致虚”,即治者之“德”需与“无”同体,“以无为心”“唯道是用”: 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朴之为物,愦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老子》三十二章注) 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 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 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老子》三十八章注) 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緜緜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老子》二十三章注) 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穷极虚无也。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于不穷极也。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用之于心,则虎兕无所投其瓜角,兵戈无所容其锋刃,何危殆之有乎!(《老子》十六章注)总之,王弼认为治者之行事应以自然无为为根据,达至这样的境界,然后乃能与天地合德。 2.“未形之时”的“存诚” “无”不仅蕴涵着“抱朴无为”,还特别提示着“未形之时”。因此,“体无”还意味着在“未兆”“未始”时之戒慎: 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如斯而已矣。(《老子指略》) “未兆”和“未始”就是《周易·系辞上》所说的“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之“几”,王弼在《论语释疑·述而》中说“《易》以几、神为教。颜渊庶几有过而改,然则穷神研几可以无过”。明白了《易》中所说的“几”“神”就可以无大过了。“几”指的即是未发之际。《老子指略》又说:“察见至微者,明之极也;探射隐伏者,虑之极也。”(《老子指略》)“至微”“隐伏”亦指向“未兆”“未始”。 “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意思是说,教化的症结不在于直接对“为”有所加码。比如,人之为恶,解救的办法并不在于对为恶之人加以重刑,也不在于以道德说教去改变为恶之人,关键在于让为恶之人无心为恶,若使为恶之人无心为恶,则需“谋之于未兆,为之于未始”,也就是在恶行发作前就要做一些事情。在“未兆”“未始”时的作为,其目的则是使人“无心于为”,在一开始就让人“无心作恶”。所以,与其高举仁义来敦促薄俗之人,不如在初始时就以见素抱朴的态度来促使人之笃实之心更加纯粹。因此,邪、淫之产生根源都不在邪、淫之人身上,闲邪、息淫之道并不在善察、滋章,而在于存诚、去华。 在“未兆”“未始”时之戒慎,更具体而言就是“存诚”。“诚”在“未兆”“未始”时就要加以善养,而不是等到“不诚”的情况出现才以“善察”来对治。王弼说: 各任其贞事,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 在“用其诚”的前提下,则仁义礼敬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毋需特加倡导。此即仁义礼敬之基础在以“诚”为本。这一思想在《论语释疑》中亦有相应表现: 夫推诚训俗,则民俗自化;求其情伪,则俭心兹应。是以圣人务使民皆归厚,不以探幽为明;务使奸伪不兴,不以先觉为贤。故虽明并日月,犹曰不知也。(《论语释疑·泰伯》) “推诚”之“诚”即“用其诚”“闲邪存诚”之“诚”,是令“民俗自化”的前提。“不以先觉为贤”,就是不以“先觉”为“形”,即不令“先觉”作为一特定之“贤”被标举为一特定之“形”。 对治者之教化强调“以无为心”“唯道是用”,站在“无”的高度,王弼所阐发的教化并非针对某一特定之“形”的对治方案,于是,王弼所谓的教化跟他所批评的其他诸家之教化存在着本质差异。 三、百姓之自化 描述治者与百姓的关系,从中可见治者教化与百姓自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在《老子注》中,王弼沿着《老子》的思路反复论述治者之行事方式决定了百姓的回应方式,他说: 夫素朴之道不著,而好欲之美不隐,虽极圣明以察之,竭智虑以攻之,巧愈思精,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则乃智愚相欺,六亲相疑,朴散真离,事有其奸。盖舍本而攻末,虽极圣智,愈致斯灾。 夫镇之以素朴,则无为而自正;攻之以圣智,则民穷而巧殷。故素朴可抱,而圣智可弃。夫察司之简,则避之亦简;竭其聪明,则逃之亦察。简则害朴寡,密则巧伪深矣。(《老子指略》) 又说: 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睹形见,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则大伪生也。(《老子》十八章注) 治者行为失当导致百姓亦以巧伪应对,一方面,这表达了治者需要进行自我约束,另一方面,治者之自我教化是百姓自化的前提和基础,百姓之能否实现自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者的行事原则。王弼在“常使民无知无欲”下注说“守其真”(《老子》三章注),又将《老子》之“愚民”诠释为“无知守真,顺自然也”(《老子》六十五章注),这首先指的是“治者守其真”,其次才是百姓“守其真”。更进一步,他将治者最基本的行事原则具体阐释为“不假形”“不以形制物”“不以形立物”(《老子》十七章注)、“不以形割物”⑩、“不立形名以检于物”(《老子》二十七章注)。这些表述跟“因物之数”“因物之性”“因物而用”“以天下心为心”乃一体之两面。 治者只有对此深切理解并切实实践,百姓之自化才得以可能。就此意义而言,向治者阐述“自化何以可能”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教化。一切有关自化的阐述亦即对治者教化之依据。因此,“自化”在“教化”一义统摄之下。 就“治者之自我教化”与“百姓之自化”间的关系而言,治者之成功自我教化始终是首要问题。王弼以“推诚以训俗”为“忠”,以“观民之俗以察己之道”为“恕”,(11)如果说这两方面都有强调在治者方面做工夫的意味的话,后者的表述则更突显了在治者与百姓的关系中治者的责任。治者之无知无欲、体道而行、“以天下心为心”最终即导向百姓之自化。在王弼注中,往往述及治者行为的文字后面紧接着就是对此类效果的描述: 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老子》十章注) 物事逆顺反覆,不施为执割也。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老子》二十九章注) “物性自得”即百姓之性自得。《老子》中“自X”的表述非常多。如“民不令而自均”“物自宾”(《老子》三十二章注),又如“自化”“自济”“自长足”“自定”“自正”“自朴”。这些都是对物事或百姓而言,这些表述有尊重个体特性、包容个性的意涵,这种意涵早已是治者无为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自化”即自其性而化。相对而言,《老子注》中也有很多“不自x”的表述,这一表述的主语是治者,用以表述治者的自我约束。“自”与“不自”即分别指向本文所讨论的“自化”与“教化”。 总结而言,笔者尝试探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王弼《老子注》并未实质上脱离《老子》的基本立场的话,那么,它在推进《老子》思想方面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笔者以为,贡献即在于王弼有意识地进行概念性、理论化建构的工作,使得《老子》思想向“哲学性”的方向迈进。 收稿日期:2016-02-20 注释: ①王弼注特重对“形”的论述,且比《老子》文本要丰富得多,《老子》文本中“形”字只出现过一次(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而《老子注》提及“形”有24章之多(一、四、六、十四、十五、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五十一、五十五、五十八、六十四章)。此外,与“形”相关的概念有“状”“象”(四、十四、十五、二十一、三十五、四十一章),与“无形”相关的概念有“精象”“大象”“天象”(四、十四、十六、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章)。 ②本文中,笔者以《老子指略》为王弼作品加以援引。 ③以下如未经说明,均引自楼字烈校释之《老子道德经注》。 ④刘笑敢先生说,以“无”为明确的专门性哲学概念是从王弼开始的。这话大体不错。 ⑤此处并非以“无形”定义“无”,而是说“无”具有“无形”的面向和特征。 ⑥范应元在注《老子》三十六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时说:“天下之理,有张必有歙,有强必有弱,有兴必有废,有与必有取,此春生夏长,秋敛冬藏,造化消息盈虚之运固然也。然则张之、强之、兴之、与之之时,已有歙之、弱之、废之、取之之几伏在其中矣。机虽幽微,而事已显明也,故曰‘是谓微明’。”“几”即潜伏在其中的发展趋势。 ⑦《庄子》中有很多篇章论述了形骸之内外,如《德充符》即集中地列举了若然形残德全之人,通过“形”“德”的对比,来彰显庄子对德的重视,对形的鄙弃。 ⑧王弼注《老子》二十五章“强为之名曰大”说:“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定之所由,则系于大。夫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为之名曰大’。” ⑨对此,《老子》七十二章注说:“清净无为谓之居,谦后不盈谓之生。离其清净,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1](P179) ⑩“割”这个字也在王弼注中提到几次,非常形象。又有学者说“割”即“裁”,也就是以特定的标准或制度去裁剪规限事物,因为标准、制度很大程度上即代表一偏之见,那么,这个结果自然是不好的,自然是违背老子和王弼主张的自化原则。 (11)余敦康《魏晋玄学史》,页276。“观民之俗以察己之道”出自王弼《周易注·观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