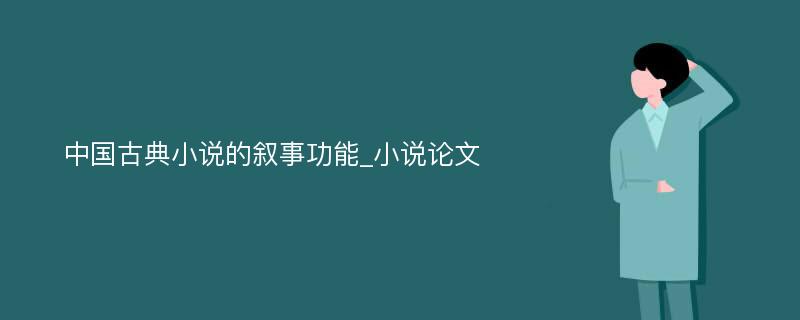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目论文,古典小说论文,中国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叙事是小说艺术的灵魂。徐岱先生在《小说叙事学》中论云:“叙事之于小说犹如旋律节奏之于音乐、造型之于雕塑、姿态之于舞蹈、色彩线条之于绘画,以及意象之于诗歌,是小说之为小说的形态学规定。”①的确,小说艺术世界的呈现皆本于小说叙事世界的建立。那么,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体制要素的一部分,处于叙事世界中的回目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一、回目:作为预叙
关于中西方小说艺术特点的不同,自从这两种叙事文体邂逅以来,已有无数贤哲发表过精辟的论断,知新室主人(周桂笙)所引其友徐敬吾之喻极有趣味:“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②中西文化中的两类艺术形成了意味深长的交叉:中国园林素以回环往复、曲径通幽著称,《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写贾政等人初游大观园时云:“遂命开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即揭出此点。然而,中国在园林审美方面有意的“叙述控制”却并未贯彻到小说世界中来,正如西方叙事文学此种特点也并未统摄其园林布局一样③。
对其原因,徐敬吾提出了解释:“盖以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则往往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所论亦称有见,然尚不完全。在笔者看来,还当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回目体制有关——也就是回目所具有的预叙功能。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小说的叙事特性也与时间有密切的关系:相对于小说故事的发生时间而言,叙述者如何安排他的叙述顺序,即让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形成怎样的关系,是决定小说叙事世界面貌的基础。在小说艺术中,两种时间同步发展的常态叙述称为顺叙,但倒叙与预叙的设置却更能体现作者对小说艺术所付出的努力——法国叙事学学者热奈特定义倒叙为“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预叙为“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
可与前引徐敬吾比喻相互映照的是,正是这两种不同于一般“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带有技巧性因而也更深刻地彰显着作者对叙事艺术的把握与控制的叙述方式,在中西方小说文体中的应用却恰恰各有所趋:热奈特本人也承认预叙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要比倒叙少见得多,并解释说“小说‘古典’构思特有的对叙述悬念的关心很难适应这种作法,同样也难以适应叙述者传统的虚构,他应当看上去好像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现故事。因此在巴尔扎克、狄更斯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预叙极为少见”④。他的看法一如回目中使用人名代称的理由一样,即“古典”小说作品需要保护构思中的悬念在不到揭出的时候一定不可先行泄露。当然,这种认定事实上并非一个真命题,因为二十世纪以后的现代派小说已经举出了无数反证。不过,热奈特进行这一论断时并非没有注意及此,所以,他才更确切地说是“小说‘古典’构思”——然而,中国古典小说却又给他以另外的反证:在此叙事传统中,预叙的使用更为普遍。在《叙事学导论》里,罗钢先生已指出了这一点⑤,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对此作了深湛而富于理论色彩的研究,他从“殷墟甲骨卜辞”中看到了预叙“最初的形态”,《左传》中大量的预叙正是源于这些“卜筮和预言”,并进一步指出正是中国叙事“在宏观操作中充满对历史、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才使得预叙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强项。
事实上,在传统的小说叙事行为中,恰是倒叙造成了悬念与“闷葫芦”,预叙则在很大程度上揭开了小说的谜底,使情节一览无余:这也正是中西方小说呈现出徐敬吾所云差异的主要原因。自然,我们指的是古典的、传统的小说叙事,因为“尽管由于预叙事先揭破故事的结果,破坏了读者发现最终结局的阅读期待。但它却造成另一种性质的心理紧张”,预叙的这种特点随着西方小说现代叙事技巧的自觉与成熟以及小说读者审美期待的进步成为制造另一种悬念的手法:它虽然预示了结果,但小说的艺术核心已不在结果,而在通向这一结果的过程,所以,结果的提前预告不是缩小了而是开拓了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其实,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就已出现了这样极富叙述智慧的预叙艺术,如杨义先生对《红楼梦》“是诗,又是哲学”的预叙的称扬,他指出“太虚幻境的预叙”,“让主人公在初涉人生之时,就以迷离恍惚的梦幻状态,与他不能参悟的人生终局的判决打了一个照面”,那些判词都是“暗示性预叙”,并“渗透到全书的行文脉络中去了,成了章章回回若隐若现的叙事密码”,“这段预叙把人生行程与提前叙述的人生结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动人心弦的象征诗一般的审美张力。它提供了预叙充满命运感的诗化和哲理化的经典形态”⑥。当然,《红楼梦》的预叙还有更复杂的形态,比如全书开始时的神话结构是不是预叙呢?更进一步,与《石头记》文本相表里的脂批常以知情者的口吻提到后文情节,如果从中国传统小说文体的角度来看,作为小说世界一部分的评点,是否也是预叙呢?此外,《红楼梦》中为人熟知的影子说以副喻主,“晴有林风,袭乃钗副”,是否也有预叙的成分呢⑦?这些都是应该探讨的问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小说以前,古典小说中个别作品的预叙在艺术上达到了现代叙事技巧下方可取得的效果,但却仍是不自觉的,这只是作家艺术直觉的灵光一闪。因此,在我们面对古典小说的论述中,所讨论者仍为传统形态之预叙。
热奈特在定义预叙时使用了“一切”这个词,他对《巨人传》、《弃儿汤姆·琼斯史》乃至于狄更斯与雨果的作品应不陌生,所以,西方小说标目若的确“提及以后事件”,自当属于预叙:虽然它们并不在叙述流程之内。可见,在界定者那里,预叙应当也包括标目这种形式因素。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与西方小说标目在文体功能上是相同的(虽然二者有更深刻的不同):回目都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句,概括叙述一段情节;一般而论,回目的设置又均位于每回正文之首,在本回情节尚未展开的时候,读者已经读到对其概括的回目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也是“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之一,即预叙。
回目都是以一个单句或一联偶句来简要概括本回即将发生的故事内容:翻开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读者们会依次看到“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回目,在尚未进入小说正文的叙事世界之前,读者已粗略了解到相应回次的故事内容,在阅读过程中,因已有叙事进程提供的悬念,每回回目的预叙功能就更为突出,如第六则之末董卓欲行废立之事,袁绍反对,二人相峙,就在剑拔弩张的关头,此则结束,读者们自然急切地想知道结果,袁绍性命如何?董卓究竟能否得逞?翻过一页,不必看正文便已知道,董卓已经得逞了,因为第七则回目云“废汉君董卓弄权”;然这一则又以曹操出计诛董卓为结束,不知所出何计,但下则回目“曹孟德谋杀董卓”一出,读者也即明白……如此连环往复、直至全书结束。
重要的是,不仅每回的回目置于本回之首从而对本回故事进行预叙,而且,全书的回目还会集中为目录置于书前,有的作品除此之外在每卷前还有本卷的目录,打开目录,即可提前知道它的情节发展——应该说,在这种标目体制中,全书故事被不同层级的回目重复预叙、反复皴染,因而,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因为它一方面在每一个结点设置秘密,但紧接着便会揭开秘密。
不过,中国古典小说回目体制的预叙功能是一把艺术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向潜在的读者提供了更多有关叙事世界的信息,从而使读者的选择可更明确,也使其对此叙事世界的进入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
首先论述其“利”。
关于叙事学,西方叙事学家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它的命名者托多洛夫代表,他们的“叙事”指称着人类的一切叙事行为;另一种以热奈特为代表,他们把研究限定于文学的叙事⑧,二者各有所凭亦各有所获。如果持前一种观点来看待叙事,那么,也就可以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预叙。比如对一部小说的评论与宣传,这其实也是对这部作品禁锢在文本之内的叙事进行了一种广义的“预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文化传播意义上的“预叙”行为不但使已经读过此作品的读者、也使那些正要阅读或根本就不会去阅读的人对它有所耳闻、有所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接受。
相应的,与中国古典小说回目这种预叙形式相类的书名其实也是一种预叙,它也从特定的侧面预先揭示了叙事世界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小说书名大多为主人公的名字,有时还附加行动的描述,颇类于我们论述回目时指出其对于人名的重视,而恰恰是使用了回目体制的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以人名为小说书名者(见下文之注),它们的人名都排列在回目中了。
两种形式的预叙对读者来说都极为重要,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是否进入某部作品叙事世界的决定。不过,就第一种文化传播意义上的预叙而论,中西方的差别并不在叙事文学的体制之中;叙事文学内部体现出中西方差异的却是书名及标目一起组成的“标目预叙”。
西方的小说文本提供给读者的只有一个作品名称(也偶有例外),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评论与宣传(面对数量巨大的叙事文学作品,能够得到文学史及其他形式评论的毕竟是少数),读者面对的就只有书名:早期的《巨人卡冈都亚之子,狄波莎德王,十分有名的庞大固埃的可怖而骇人听闻的事迹与勋业纪》(即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作品《巨人传》第一卷)、《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帕梅拉,又名美德受到了奖赏》等作品透露的信息要稍多一点;此后的《爱玛》、《简·爱》、《艾凡赫》、《高老头》、《茶花女》、《包法利夫人》、《娜娜》、《约翰·克利斯朵夫》、《罗亭》、《卡拉玛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珍妮姑娘》、《马丁·伊登》等等就只提供了主人公的名字⑨;与此同时,《傲慢与偏见》、《情感教育》、《萌芽》、《一生》、《死魂灵》、《罪与罚》、《战争与和平》、《第六病室》、《红字》、《美国的悲剧》等等就连主人公的名字也没有了,作品名称随着叙事艺术的演进转向了情节的暗示与抽象哲理的概括(这同时也是西方大多数小说标目的特点)。它几乎没有为潜在的读者提供多少选择或放弃阅读尝试的理由:拿到这样的作品后,读者对书中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决定进入还是退出便有了更多的偶然性。当然,上文所举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这种耳熟能详实与评论有关,对于一些次要作家的作品,读者突然面对时的无从把握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如爱德华·利顿的《夜与晨》,这个作家与这部作品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会感到陌生⑩,如果一个读者拿到了它,面对着“夜与晨”,他仍然缺少做出决定的理由。
中国古典小说却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在于它的名称——尺幅太小的命名体制不可能容纳过多的信息——而在于它所拥有的标目体制:回目。中国古典小说中,几乎每一部章回小说都将全书划分成大致相等的段落,每个段落都会有概述故事进展的“回目”,读者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翻阅目录来为面前的作品定性,然后决定是否要进入阅读——即使最后决定放弃,他通过这一选择过程仍对此书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也是作品传播过程中预叙功能的一种创造性应用。
如果抛开文化传播意义上的预叙,仅从这一点来看,读者选读西方小说的过程颇有些“盲人骑瞎马”的味道;而中国古典小说与读者的关系则更为明朗一些,因为在他做出决定之前,作品的回目已最大限度将故事内容告诉他了——这有点类似当代一些小说作品封面(或扉页、封底、书舌)上的内容简介,但比那个欲言又止的简介更全面、详尽。也正因此,回目在中国古典小说体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曼殊所云“回目之工拙,于全书之价值与读者之感情最有关系”(11),亦有此意。
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预叙体制的“弊”。
如果把对一部小说的阅读看作一次艺术世界的探险乃至于冒险的话,那么,中国古典小说所培养起来的读者们也许会缺乏一些勇气与耐心,其成因自极复杂,有民族文化的因素,也有对文学理解的差异等等,但是,回目的预叙体制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这种体制养成了对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听众或读者需要在一个艺术事实发生之前便得到一定的提示信息,如果没有,面对无法把握的艺术世界,他们可能会难以接受。《红楼梦》第五十四回有一段描写,恰为这一状况的写照:
一时歇了戏,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儿进来,放两张杌子在那一边命他坐了,将弦子琵琶递过去。贾母便问李、薛听何书,他二人都回说:“不拘什么都好。”贾母便问:“近来可有添些什么新书?”那两个女先儿回说道:“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贾母问是何名,女先道:“叫做《凤求鸾》。”贾母道:“这一个名字倒好,不知因什么起的,先大概说说原故,若好再说。”女先儿道:“这书上乃说残唐之时,有一位乡绅,本是金陵人氏,名唤王忠,曾做过两朝宰辅。如今告老还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唤王熙凤。”
古代说书既是章回小说的抚育者,在章回小说走向辉煌之后也受其赡养,故此节完全可以用来佐证读者对章回小说的接受。中国人习惯于听老戏,也习惯于听旧说,这实际上已经反映出了欣赏的因循。不过,偶尔也会想有新的尝试,所以贾母问“近来可有添些什么新书”,紧接着便问名字——她接触到了第一次预叙,觉得“倒好”,但理由还不充足,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预叙,“不知因什么起的,先大概说说原故”。这是中国古人欣赏叙事文学的惯例,仿佛现在的学生课前要先预习课文——它自然能帮助我们理解课堂的讲述,但也抹去了听课时的紧张,因为面对的东西并不陌生,所以,预习的结果也会纵容思想溜号或思维惰性。
此处所论尚为表层,进一步看,还可以发现,此种倾向无论是因读者的口味引导了作者的创作还是作者的追求培养了相应的读者(两者或许似二而一),总之,它与其他因素一起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特点:因循过多,缺少艺术世界中的远征与新拓。西方大部分小说文本给予读者的仅仅是一个信息量极少的书名,简单的书名后隐藏的东西在阅读之前无法预知,因此,读者的阅读过程便是与这一叙事世界中的人物、情节、沉思猝然相遇的过程,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式阅读其实关联着相应的创作机制,因此,作者的创作也尽量避免程式成规,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拥有了生机勃勃的新陈代谢。
二、回目:作者的声音
叙述句式回目具有预叙功能,如“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是一个叙述句,也是一种事先讲述。但此句中也有不参与预叙的成分:如果把中间的“毒”字去掉,上面的功能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种非叙述成分,也是王力先生所定义的描写句的成分,是“描写人物的德性的”(12);在吕叔湘先生则属表态句的成分,是“记述事物的性质或状态”(13)。如此,我们就需要讨论回目中此类成分的功能。
叙事文学作品的叙述者是否需要或是否可以在其作品中直接表现出对作品人物、情节的看法,在叙事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是有变化的。西方早期小说作品中,这种不是以形象及情节呈现而是以作者突然现身来讲述的情感判断屡见不鲜,直到十九世纪,才有小说家有意识地把作者的声音从叙事世界中隐藏:福楼拜正是因此而成为一名划时代作家的,他曾宣称:“用物理学家在研究物质中所表现的公正性来探讨人的灵魂,我们就将前进一大步”,艺术只能“用一种不动感情的方式,即物理学的精确性”来获得(14)。法国当代作家梅尔勒评价《情感教育》说“这本十九世纪的小说宣告了二十世纪小说的诞生”(15),也是基于这一意义的表达。美国学者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提到,“从福楼拜以来,数量惊人的作家和批评家都一致认为,这种直接的、无中介的议论是不行的”,然后他介绍了四种小说艺术的“普遍规律”,其二便是“所有的作者都应该是客观的”(16)。当然,通过布斯的著作也可以看到,此点实非铁律,关键在于怎样把握叙述者声音在小说艺术上的出现,而不是讨论哪一种声音应该被排除——这是叙事技巧自觉与成熟后西方小说的艺术事实。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也有大致类似的发展历程。杨义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中存在着叙述者“隐而不退的叙事谋略”(17),即人物的开场白。它们大都有为人物定性的意味,并非人物自然语言,如杨义举出马致远《汉宫秋》中毛延寿上场的例子,仅引其上场诗四句就可明了,诗云“大块黄金任意挝,血海王条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那管人唾骂”:这样渗透着价值评判的评语当然不会是毛延寿的自贬,而只能是作者的“借体显灵”。早期小说作品亦如是,这同样源于某种表演成分:因为早期小说是从说书人的场上表演过渡而来的,自然把说书人经常间插的评判带入了文本(18)。
不过,随着小说艺术的进步,中国古典小说也与西方小说一样,开始半自发半自觉地禁止作者直接出现在作品的叙事世界里。因此认识还处于朦胧之中,故无法作出明确的时间限定,但至少在《金瓶梅》里便已开始了——它正类似《情感教育》,很多学者即曾在这一意义上赞誉过它艺术上不同于当时小说古典特征的“近代性”或“现代性”(19)。
此后,小说创作的这一特点在小说评点者那里得到了关注。例如《儒林外史》中“最早而影响最大”的卧评便多次指出作品中没有显示作者个人判断的叙述。如第四回的回末总评云:“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笔为之,必且曰:看官听说,原来严贡生为人是何等样,文字便索然无味矣。”(20)此评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尤为确切。二十世纪初,黄人在《小说小话》中对章回小说创作这一进展作了富有理论性的论述:
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实事,未必尽肖其言。即先后绝不矛盾,已觉叠床架屋,毫无余味。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见,如《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21)
这正是从小说创作经验中总结出的艺术规则。
上文所辨者,都是属于叙事世界内部叙述者身份显现与否的问题,而在叙事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并不被纳入叙事世界的形式,比如布斯在对作者声音的辨别中首先指出“必须除去所有对读者的直接致词”(22),致词是西方小说文体的惯例,中国古典小说向来无之,但也有不参与叙事的形式,如书前的序言、书中所附人物表或绝大部分插图(23),甚至某些演义小说后有关主人公的史料附录:在这些形式中,致词与序言一样,都有作者的出场——所不同者,西方的致词为作者对他的保护者、家人、朋友、或与此作品相关者的题献,中国的大部分序言却恰相反,一般都是作者朋友的介绍或评述。此外,还有一种形式时或流露出作者的判断,也即吕叔湘所说的“表态”,那就是回目。
回目不能说决不参与叙事:前已论及它的预叙功能,而且它对叙事进程也有影响;但也不能说它确定参与了叙事,因为就一个固定文本而言,如果去掉所有回目,从叙事角度而非艺术角度来看,并无影响,那么,它确与上文所说“对读者的直接致词”一样,是叙事世界的附加物。但正是这样的形式——确切地说是本部分开始时所指出的表态句式回目——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世界之外发出了作者的画外音。
我们可以《红楼梦》回目为例探讨之。俞平伯尝云:“即以回目言之,笔墨寥寥每含深意,其暗示读者正如画龙点睛破壁飞去也,岂仅综括事实已耶。”(24)那么这里的“深意”究竟是什么呢?
俞平伯在谈及《红楼梦》回目时,以治经史归纳义例的方法举出十六例,其第十五例为“回目直书,正文兼用曲笔之例”,所举为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觉大限吞生金自逝”。此回目之用字,显豁直截地表示出作者的感情,在《红楼梦》正文之中的确少见。不过,俞平伯仅为举例示义,循例以观会发现,这种表示作者判断的“直笔”在《红楼梦》回目中数量不少。如第十二回云“毒设相思局”、十五回云“弄权铁槛寺”、三十三回云“手足耽耽小动唇舌”、五十五回云“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欺幼主刁奴蓄险心”等等均是,这些回目中体现出的作者判断在正文中均无踪影,读者只能通过正文提供的情境去寻绎“毒设”与“弄权”。由于作品提供的仅仅是剧中人物的生活状态,读者对同一情节的阐释就会出现合于自己接受经验的差异,这种差异本来无法得到作者的仲裁,因为在古典小说艺术中,高明的作者只让情节与形象说话而不是自己喋喋不休,但在某些情况下,作为画外音的回目却恰恰显示了作者的“表态”。比如上举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一事,恰是生活复杂性之一例,可以稍加分析。
根据情节的脉络,我们知道宝玉挨打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琪官事、一是金钏事,作品中也有明文,“贾政一见,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这句话中的“荒疏学业”四字或亦表现了贾政怒而牵涉的心理真实,但主要却不过是曹雪芹整齐骈俪之填充,当不得真。在这两个原因中宝玉自己只知前者,贾环则知后者——事实上,贾环不仅知后者,且与其母赵姨娘一起炮制了后者,他告密时的“听见我母亲说”到“我母亲告诉我说”,把一个“强奸不遂”轻轻移于宝玉(巧的是,金钏之触怒于王夫人,其因却在于“你往东小院子拿环哥儿同彩云去”一语)。焙茗似乎二者皆知,但也仅知金钏的事是“三爷说的”,不知这一“说”实还有复杂的关系;对琪官事的推测并不可靠,因为紧接着袭人便把从焙茗处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宝钗(这一情节似乎过于依赖袭人作为“行动元”的功能而忽视了其“角色”特征(25),以袭人谨慎周到的性格,当不会如此),宝钗回家责问薛蟠,薛蟠“急的乱跳,赌身发誓的分辩”,作者也叙述云“其实这一次却不是他干的”——不过薛蟠的“发誓”与作者的叙述也未必就是实情:前者有意瞒过或无意忘却、后者使用“画家烟云模糊”(26)法都有可能。至于王夫人、宝钗诸人就更是多方忖度而不得要领了。读者似乎清楚得多,但细细品味此二事,其重要程度仍有差别:第一件事后贾政“气的目瞪口呆”,第二件时则已“气得面如金纸”、“满面泪痕”——当然不否认第二次有情感强度的叠加,但也可以设想,如果这两件事次序颠倒一下,贾政的反应顺序是否还会由“目瞪口呆”到“面如金纸”?其实,我们停止正文的分析,则可从回目中听到作者自己的声音,即“手足耽耽小动唇舌”,本来此回贾环进言只占很小的篇幅,且在忠顺王府索人之后,却竟挤入回目之中,可见作者强烈的感情倾向,此八字也明显表示出了对贾环进言的态度。鲁迅云“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主要在于其“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27),这已成为评价《红楼梦》的经典论断,但实有例外,比如贾环及赵姨娘,曹雪芹从未给过他们一点光彩——顾颉刚先生曾怀疑“曹雪芹的穷苦,是给他弟兄所害”(28),由此,我们便也更能理解作者的倾向了。
此外,《红楼梦》回目中人名前形容词的使用也透露出了作者的苦心,如“贤袭人”、“勇晴雯”、“愚妾”、“刁奴”、“敏探春”、“时宝钗”、“慧紫鹃”、“慈姨妈”、“苦尤娘”、“酸凤姐”、“懦小姐”等。他们在百万言的巨著中有很丰满的刻画,但由于作者写出了生活的原生态与人物的立体感,故对许多人物的许多行为,读者意见纷纭,甚而达到“遂相龃龉,几挥老拳”(29)的地步,因此,回目中透露出的作者“表态”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对袭人、宝钗形象的评价,历来毁多誉少。如果能够“回到《红楼梦》本身”,不以任何先验的政治、道德标准(这些标准实际上都容易时过境迁)来做过滤镜的话,应当承认,宝钗与“副宝钗”的袭人,虽然不同于黛玉与黛玉“影子”的晴雯,但也是一种美——两种不同极致的美在贾宝玉的生命理想乃至于《红楼梦》的审美理想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她们都终归陨灭。在回目这个画外音中,作者用“时”、“贤”的用语表态,就很说明问题(30)。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问题。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与高鹗第一次将《红楼梦》刊刻出来,补出后四十回,以成全璧,学界对其体现出来的思想的保守与平庸多有指摘(31),梁归智对后四十回之“独立的美学系统”也有深刻的论述与阐发,他同时指出从后四十回的回目亦可看出对原本“悲剧的异化”,如“奉严词两番入家塾”、“老学究讲义警顽心”、“博庭欢宝玉赞孤儿”等十余则,均体现出道德伦理与宗教迷信的倾向(32),这自然也有回目“画外音”表现的成分——只是与曹雪芹的声音颇不协调。还有一点更值得关注,即程本对前八十回原本也进行过一些修改,其中包括部分回目(33),这些回目中,恰有个别改动也表现出了这一点。如第十七、十八回,早期的己卯本与庚辰本多未分开,总回目云“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后来的本子则多分为两回,并各有回目,程本第十八回云“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有正本的刊印者狄葆贤在此有眉批将其与戚本回目对照,戚本下句为“助情人林黛玉传诗”,狄氏认为“今本回目易以‘天伦乐宝玉呈才藻’字样,是以红楼为伦理学书矣,一何迂腐至此”(34),而程乙本与程丙本的目录及程丙本的正目又作“天伦乐宝玉献词华”,从其改动也可见,此回目正为刊刻者所加,并非如他们自己宣称的有“全璧”、“原本”为据。狄氏此评仅讥下句为“伦理学书”,其实,上句不也是颂圣奏章么!第九回改“恋风流情友入家塾”为“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实亦同样呈现出“博庭欢宝玉赞孤儿”之类的迂腐气息。
当然,回目的画外音功能并非《红楼梦》所独有,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体制中的一贯传统。如《三国志演义》的“废汉君董卓弄权”、“张辽义说关云长”、“废献帝曹丕篡汉”(35)等,《水浒传》的“淫妇药鸩武大郎”、“施恩义夺快活林”等,《英烈传》云“元顺帝荒淫失政”、“真明主应瑞濠梁”等。近代以还,作者的主体地位及创作情绪逐渐强化,此倾向愈加明显,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云“彻底寻根表明骗子穷形极相画出旗人”、“恶洋奴欺凌同族人”等,作者的声音过于强烈,鲁迅评之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至“近于谩骂”(36),亦有此意。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这种特性并非偶然体现,它的存在有文化渊源上的必然性——即史官文化中流泽甚广、根深蒂固的“春秋笔法”。
关于此,俞平伯亦指出:“以纲目来比,则回目似纲,本文似目。以《春秋》来比,则回目似经,本文似传。”对古典小说回目影响甚大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及朱熹的《通鉴纲目》即十分讲究笔法,金毓黻曾有论述,并云其“故大书以提要者谓之‘纲’,仿《春秋》之经也,分注以备言者谓之‘目’,仿《左氏》之传也”(37),那么,作为牢笼于紫阳《纲目》的小说回目,其中寓有春秋之笔意,不亦宜乎!
不过,此之“春秋笔法”只是说明小说回目显示作者态度的文化血缘,并非指认其功能与面貌。其实,将潜台词隐于丰富的文化传统之内的春秋褒贬与通俗小说的功能并不完全契合,如果说早期尚“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三国志演义》用“废”、“篡”、“弑”等字还有春秋之余韵的话,那么,此后的作品便无法以这种精雅而“迂回”的隐喻来打动市井读者了,所以,紧随《三国志演义》而响应的《英烈传》回目就呈现出“元顺帝纵欲骄奢”、“太祖皇濠州应瑞”式的直截面貌,为适应通俗化的需要,作者们将精巧的隐喻变为了明白的判断。
注释:
①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②饮冰等:《小说丛话》,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③有趣的是,中国的园林艺术却曾经对英国艺术产生了影响,范存忠在《中国园林和十八世纪英国的艺术风尚》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参见钱林森编:《中外文学因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67页。
④[法]热奈特撰,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第38-39页。
⑤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⑥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第156-157页。
⑦拙文:《十二金钗归何处——红楼十二伶隐寓试诠》(《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期)提出“红楼十二伶”实为“金陵十二钗”的整体隐寓,也就意味着前八十回中十二伶官的结局应为十二钗命运终局的一种预叙。
⑧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第1-3页相关论述。
⑨这是西方长篇小说最常用的命名方式:中国人姓在名前,而西方大多数是名在姓前。这表明在中国,宗族与群体永远高于个人,西方则更关注个体——此即是西方小说多用人名为书名的文化基因。其实,林纾的翻译就很典型地表现出了这两种差异:将《艾凡赫》译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尼古拉斯·尼古贝》译为《滑稽外史》、《汤姆叔叔的小屋》译为《黑奴吁天录》、《堂吉诃德》译为《魔侠传》,均以群体性的类名代表了个体的人名。也许他是无意的,但正是这种无意恰体现了不自觉的文化修正。
⑩事实上,中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虽有研究,但一直不知其原本,直至韩南《论第一部汉译小说》一文发表后([美]韩南撰,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130页),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利顿及其《夜与晨》。
(11)曼殊:《小说丛话》,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第89页。
(12)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引自《王力文集》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3)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引自《吕叔湘全集》第一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14)转引自[美]布斯撰,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15)参见[法]福楼拜著,冯汉津、陈宗宝译:《情感教育》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16)(22)[美]布斯撰,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第19页,第75页,第19页。
(17)参见杨义《中国叙事学》,第239-241页。
(18)参见孟昭连、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2页、第255-257页。
(19)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便认为《金瓶梅》比《水浒传》、《西游记》等伟大,因为那些作品不是近代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郑振铎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卷第425页)。
(20)引自(清)吴敬梓撰,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21)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页。
(23)之所以说“绝大部分”是因为仍有例外,如《红楼梦》中通灵玉与金锁的图式;西方小说亦有之,如法国小说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马振骋译:《人的大地》,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尼格的《五号屠场》(云彩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其中作者自绘的插图都参与了叙事。
(24)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三十三·谈〈红楼梦〉的回目》,引自《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27-766页,下引俞平伯关于《红楼梦》回目的意见均据此,不另注。
(25)法国叙事学家格雷马斯认为小说人物有二重性:一是“行动元”,即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二是“角色”,即人物的性格特征。参见格雷马斯:《行动元、角色和形象》,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26)此为甲戌本及靖藏本之脂砚斋评语,参见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2页。
(27)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引自《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
(28)引自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通信》,《俞平伯论红楼梦》,第7页。
(29)(清)邹韬:《三借庐笔谈》中载其与友人许伯谦因尊薛与尊林而“几挥老拳”,“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2-833页。
(30)对于宝钗、袭人,薛瑞生:《冰雪招来露砌魂——论薛宝钗》及《洛浦空归泪有痕——论花袭人》二文均有通达深湛之析论,参见《红楼梦谫论》,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396页,第483-487页。
(31)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共分四编,后三编均设有对后四十回的“价值评价”部分,可参看。
(32)参见梁归智:《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248页。
(33)程本不同类型版本回目的对比情况详见徐有为、徐仁存:《〈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第四种程刻本》,引自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349页。
(34)参见曹雪芹著:《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影印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09页。
(35)毛宗岗评本回目改动后画外音的强度更大了,周兆新即曾指出“废献帝曹丕篡汉”与“汉中王成都称帝”之变为“曹丕废汉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的明确表态(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05页),此类例证在毛本回目中颇为普遍。
(36)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引自《鲁迅全集》第九卷,第291页、第345页。
(37)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页。
标签:小说论文; 红楼梦论文; 中国古典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古典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读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情感教育论文; 曹雪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