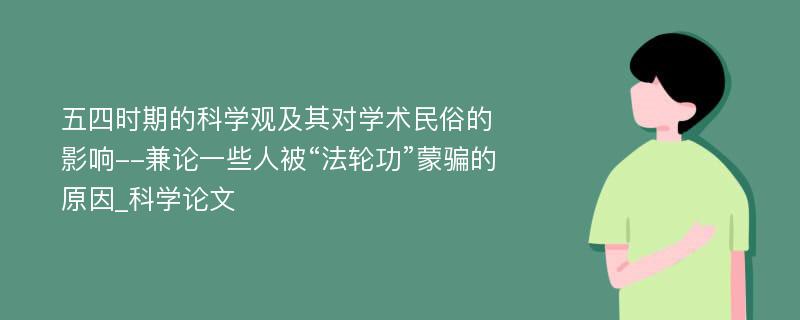
五四时期科学观及其后来对学术和民风的影响——兼论部分人被“法轮功”欺骗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轮功论文,民风论文,学术论文,原因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着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反对封建迷信、盲从和武断,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以及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以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医治当时中国的种种痼疾,为拯救中华民族,功不可没。特别是一部分先进分子在文化大论战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由崇拜资本主义文明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结论。因此,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说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 第669—700页。)所以,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不仅如此,五四运动还对学术和民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当时人们对科学认识的角度,粗略谈一下看法。
一
大致说来,五四时期的民主主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社会体制问题,科学要解决的是思想和实业问题。正如陈独秀在为《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所说:“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当时, 进步的知识分子企图借助科学来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社会进步,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振兴中华。一批留美学生创办了《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把科学的功能概括为四点:
其一,“科学之有造于物质”,即科学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发展。对于这点,陈独秀、郭沫若都曾论及。连反对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的《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也不得不承认,“十九世纪科学大兴,物质主义大炽”。“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即以科学的手段,实现吾人经济的目的”。(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载《东方杂志》14卷4号,1917年4月。)
其二,“科学之有造于人生”,即科学有助于人的健康。胡适曾从人对自然的认识论述了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以前人类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讨自然界的秘密,没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残酷,所以对于自然常怀着畏惧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为人类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依靠一种超自然的势力。现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质力,上可以飞行无碍,下可以潜行海底,远可以窥算星辰,近可以观察极微。这个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经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个少年的革命诗人曾这样的歌唱:‘我独自奋斗,胜败我独自承当,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这是现代人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注:《我们对待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页,1926年7月。)胡适喊出了“人格神圣”、“人权神圣”的口号,瞿秋白则说:“科学使人享法律上的平等”。(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
其三,“科学之有造于知识”,即科学能破除迷信,激发人们前进。蔡元培曾说:“一切科学皆为增进知识之需”,(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载《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 )胡适则直接把求真理与破迷信联系起来,认为“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禁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注:《我们对待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第 4卷第83页,1926年7月。)
其四,科学可提高人的道德水平,使人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促进和平。瞿秋白说:“颠覆一切旧社会的武器正是科学”。“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注:《东方文明与世界革命》,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
五四时期,科学还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因此,它与旧的传统文化是冲突的,从而产生了新旧之别,时人汪淑潜说:“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甚而至于交际酬应,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上自国家,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现新旧二象”。(注:《新旧问题》,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政治、学术、道德视之为新,把当时中国的政治、学术、道德视之为旧。激进者主张倡新弃旧,如陈独秀等;温和者主张新旧调和,主张倡新改旧,如蔡元培等。尽管有杜亚泉等保守派坚持旧传统,反对科学的思想,但是,科学的新潮流已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无法阻挡。在科学新潮流的影响下,儒家的独尊地位丧失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直受压抑的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重新以平等的地位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一些儒家大师为保住儒家的霸主地位,将科学和民主的内容兼容到儒家体系之中,这便产生了一个新儒学派。
从社会发展来讲,提倡科学与提倡新学是统一的,代表了当时进步的潮流。但是在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中,新学派反对旧传统有力,但对西方文明审视不够,许多倡新学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为反旧学,讳言新学之不足;另一方面象胡适等人却觉得没有资格对新学妄加评论,从心理上形成了一种不如人则不便批评人的惯性思维,于是赶时髦、赶潮流之风盛行,坐下来冷静思考探求是非者视为不合时宜。此风影响至深,甚至在我党历史上也有所表现。每逢刮起“左”、“右”之风时,许多人因怕不合时宜而不敢将符合科学的意见讲出来,有些讲出了科学的意见者也大都被抛到了时风的对面,从而使科学在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的争斗中受到玷污。近年来,中国又刮起了“气功热”。利用气功强身健体,古代早已有之,一些道教徒、佛教徒也重视气功,但他们的气功学说中搀杂了许多迷信的东西。所谓气功治病,其机理无非是“三调”,即调心、调身、调气,也就是心意入静,身体放松,调整呼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在唐山开办气功疗养所的气功师刘贵珍在其所著的《气功疗法实践》一书中说:“气这个字,在这里代表呼吸的意思,功字就是不断地调整呼吸和姿式的练习,也是俗语说的要练得有功夫,将这种气功方法用医学观点加以整理研究,并且用到治疗和保健上去,去掉以往迷信糟粕,因此称为气功疗法。这种称呼,它既合乎实际而又易教易懂,易为劳动人民所接受,古代传留下来的导引法、内养法、吐纳法、内功、深呼吸、静坐呼吸、养生法等,虽名称不同,均属于气功之前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强身健体,各种功法应运而生。在“气功热”的大潮中,李洪志炮制了“法轮功”,采用了少量气功动作,却充实了大量的迷信学说,利用人们强健身体的心理,披上所谓真、善、忍的外衣,形成了一套歪理邪说。我们的一些同志也在气功可治病的时髦之风中,不再认真审视“法轮功”的邪说,一些共产党员也忘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分析其唯心主义,做了“法轮功”的俘虏。
二
五四时期已经对科学的功能有了初步的认识,因此便开始重视科学的精神,讲究科学的态度。
郭沫若认为:“科学的精神在追求普遍妥当的真理,科学家的职志也在牺牲一切浮世的荣华而唯真理之启迪是务。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向着真理猛进的精神是英雄的行为,而他们超然物外的态度也不输于圣者之高洁”。(注:《论中德文化书——致宗白华书》,载《创造周报》第5号,1923年6月。)胡适说:“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注:《我们对待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页,1926年7月。)而要探求真理,就要破除迷信和偶像崇拜,陈独秀说:“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注:《偶像破坏论》,载《新青年》5 卷2号,1918年8月。)他强调:“用科学解决宇宙之谜”,“必以科学为正规”。(注:《再论孔教问题》,载《新青年》2卷5号,1927年1 月。)新潮社的重要人物毛子水对科学精神解释说:“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能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见,择善而从。这就是科学的精神”。(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载《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 )由此,不固执,破除迷信,追求真理就成为五四时期的人们对科学精神的理解。
要讲究科学精神就必须讲究科学的态度,陈独秀认为:科学的态度就是“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使主观思想合乎客观实际,以达到“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注:《再论孔教问题》,载《新青年》2卷5号,1927年1月。)从科学的客观态度出发, 陈独秀又说:“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吾人之於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古今中外之别也。”为追求科学的客观,陈独秀提出了为学的三戒,即:“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注:《随感录》(一),载《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总之, 当时对科学态度的理解就是主观符合客观。
现在,讲究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五四时期却并非如此。在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中,一大批人仍然抱残守缺,对科学持拒斥态度,《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撰文多篇,大讲西方科学传来中国带来的害处,疾呼不可把科学的学说视为信条。薛祥绥在《讲学救时议》一文中说:“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仪亡”。进步的知识分子高举着科学的大旗,战胜了封建礼仪的卫道士,以科学代替了经学,将科学提升为一种正面的价值体系,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这的确是一场思想上的大革命。但是,科学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为实用而求知,二是为真理而求知。中国的传统是讲究“经史致用”的,革命者高举着“科学”、“民主”的大旗以“救亡图存”,将科学的思想和当时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为救中华而求知,求革命真理,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了革命家。另一些人也曾高举过“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他们寄希望于“教育救国”或“技术救国”,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技术专家或教育家,做了共产党的同路人,为开创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些人,在五四时期也高举过“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但是,他们只是为了求知,从学术上求真理、真知。五四运动初期,他们是革命的同路人,后来因联系政治与联系学术的分野,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主张多讲问题,少讲主义,他们确实脱离了政治,离开了革命斗争的前线,但其却比较多的强调了学术的独立。学术独立者既要求在学术上从经史致用中解脱出来,又要求在学术上不受制于独断的教条,不盲从外在的权威,有人称这些人是学院派人物。学院派人物后来的发展比较复杂,又由于他们背离了中国革命的主文化,过去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对他们某些是的成分也极少评议。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历史,总结中国革命主文化形成中的曲折历程,也评论学院派人物的是非功过,这本来是可喜的现象,但却不能忽视腐朽的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对科学的冲击,不容忽视五四时期对科学的不成熟或粗浅的理解对当今的学术和民风的影响。
三
五四时期相当一批高喊欢迎“赛先生”的人,其初衷只是出于“船坚炮利”的工具理性,比较看重“为实用而求知”,而对科学的精神真谛尚未有明确的认识。从上层社会来看,科学家们关注的是技术,哲学家们热衷的是思辨逻辑。而下层社会的中国老百姓的大多数对科学知识的认识一直比较缓慢,特别是中国的农民,直到20世纪70年代对科学种田的认识依然很肤浅。因此,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科学的普及并没有带来科学理性的昌明。科学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5页。)通常以两种方式对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第一种是技术性的,即“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87页。)第二种是教育性的,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对社会精神生活发生影响。由于科学精神在社会中有两种表现形式,所以科学既可以作为“科学—技术—生产”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一种物质力量,又可以作为“科学—理性—世界观”系统中的要素,表现为一种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的重新提出,人们对科学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已经认识得比较清楚。为了发展经济,为了物质的实用而求知,钻研科技,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是,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认识和重视却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本来,在存在着奴役、剥削和阶级对立的文明时代,科学和道德这两项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往往处在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状态之中:在封建社会中其落后腐朽的伦理道德常泯杀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但与此相伴的则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卑劣的贪欲”所导致的道德危机。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两千余年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时刻侵袭着我们,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仍不间断地向我们进攻。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坚持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并且强调我国社会的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吸收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但是,改革开放在引进许多先进的技术和思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进了一些泥沙,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同时,在当前,我国社会又处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型中,在结构型和体制转轨齐头并进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社会利益分配的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趋向的复杂,从而形成了对主文化的一种挑战。我们的许多党员和群众,在国内外各种思潮的冲击下,价值观混乱了,坚持主文化的意识淡薄了,科学的理性、科学的世界观忘记了。于是,近年来,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了许多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愚昧落后现象,如看风水、星象测命、巫术治病、画符念咒、拜神祭鬼、建庙修坟,选“黄道吉日”,抢“吉祥数字”等等伪科学、反科学的现象有所抬头,李洪志的“法轮大法”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钻了空子,利用人们希望强身健体的心态,宣扬了一套粗俗的唯心主义、有神论,否定、贬低一切科学真理,使一些善良的老百姓上当受骗。
近年来,社会上又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科学精神的学说,把科学精神分成近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后现代精神三种形态。认为“近代科学精神是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也是近代社会机械力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特点的反映。近代科学精神的一个总的特点就是与人文精神相分离”;“现代科学精神则是在现代科学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它反映了现代知识中,关于自然的认识和关于人的认识的相互关联,也表现了这个时代人类日益意识到自己与周围的环境世界息息相关的特点,因此,现代科学精神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与人文精神的交融。”“后现代科学精神”是“一部分人文学者对近现代科学非人化批判中引申出来的对科学精神不同的价值观,它多少是崇尚怀疑、多元、不确定性、主体性、人性化的,从‘自然的返魅’和‘科学的返魅’中来表达科学与人生的关系,因而是一种哲学性的反思和解释”。(注:肖峰《科学精神的三种形态》,载《新华文摘》1998年4期。 )从对这科学精神的三种分法来看,近代科学精神虽不可取,但比较客观地总结了当时的情况,符合五四时期的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现代科学精神也基本符合现状。然而,后现代科学精神消除了科学与人文的区别,使科学精神回到了主客不分的原始模糊状态,从而使一些相信后现代科学精神思辨哲学的学者们也掉进了“法轮功”的圈套。
科学在技术性方面表现的比较明显和直观,而对于人类心灵的作用,或者说科学对于理智所产生的影响则常被人们所忽视。一些科学家以懂科学自居,但他们不太看重科学对世界观或理性的影响。牛顿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但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信奉上帝。可是在他认为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能够作用的太阳系范围内,他绝对不允许上帝或其它神秘的力量插手。在科学与愚昧迷信之间,精神世界里的许多愚昧落后现象,都是在“科学知识尚未插足的一些领域里”发展起来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184页。)牛顿对万有引力颇有研究,所以,迷信无法插足于其中,然而却插足了其精神世界之中。少数技术专家、研究思辨哲学的专家之所以被“法轮大法”所骗,大概与之同理。因此,“法轮功”事件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要重视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更要重视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要重视科普教育,更要重视唯物主义教育;要重视科学的技术作用,更要重视科学对精神的影响。这些教育不仅要在全民中进行,而且更要对学者们的某些盲点有较清醒的认识。
标签:科学论文; 科学精神论文; 道家气功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新青年论文; 陈独秀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