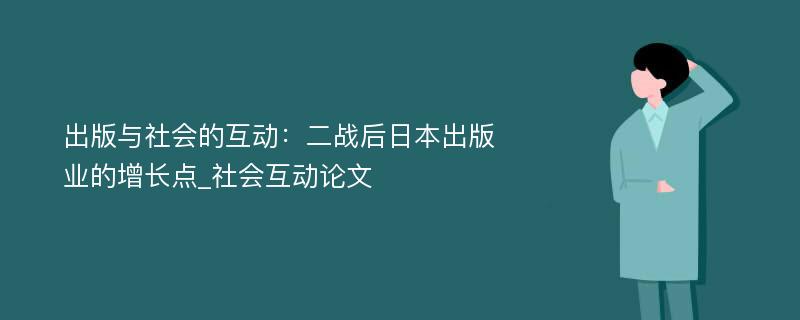
出版与社会的互动:战后日本出版业的生长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长点论文,出版业论文,互动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想像的共同体》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格外强调出版物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即“印刷品(print as Commodity)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的关键”。就出版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说,安德森借用了培根的话,也就是说印刷术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
安德森还具体地论述到,一旦出版业作为资本主义的企业形态被确立下来以后,书籍出版商便在不停地拓展着自己的市场,印刷商纷纷在欧洲各地建立分厂。到17世纪时,拉丁文市场已出现了饱和状态,这时书商们便开始寻求用方言写作的廉价书市场。宗教改革和行政方言的发展把神秘的拉丁文从出版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在新教与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争夺人心战”中,新教正因其深谙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日益扩张的方言出版市场之道,因而基本上始终采取攻势……最能让人体会这种受困的心态的是弗朗索瓦一世在1535年恐慌地下诏禁止在其领地印行任何书籍——违反者处以绞刑。①
日本政府对印刷媒体的控制
不论是在西洋还是在东洋,人们对出版之于社会的影响的认识是共通的。在战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同),日本政府极为重视对出版社传播这一媒介形式的控制,早在1896年的民法中就有对损害名誉、侵犯个人隐私权者要给予赔偿处罚的款项。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为了规制出版市场,日本政府废除了旧时暂定性的出版条例,颁布了新的出版法;在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一年,日本政府又进一步对杂志的发行市场进行了整合,加强了对杂志销售业的管制,让销售者缔结不得降价出售的协定;在对俄宣战的1904年,日本的学校开始使用由国家统一编制的教科书,在历史上这可以说是统一国民思想、形成一致对外的意识的一大举措。在1907年的刑法中有禁止在出版物上刊登淫秽性文字和图画以及进行贩卖的条款;在1910年的海关相关法案中有禁止进口有破坏公共安全和败坏风俗的文字图画的规定。②
尽管日本在1893年和1909年分别制定了《出版法》和《新闻法》,但在这些法令中也都赋予了政府对其相应的掌控的权力,这样,政府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采取取缔和禁止发行的措施。根据上述法律,出版社在出版图书时,要向内务省提出出版和发行申请。并且,出版物在发行之前,出版社必须将两份样书呈交内务省警保局。在出版杂志和报纸时,首先要在创刊前把申请书呈交警保局,在获得许可后,方可出版和发行。而且,在杂志和报纸出版后,还要将样本送交内务省、当地地方官厅和地方法院。并且,对内容涉及时事的杂志和报纸,地方官厅还要向其征收保证金。日本政府不但对出版物实施严格的事前限制和检查措施,而且对出版之后的出版物也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如检查当局发现有不利于政府的内容,便要对作者、编辑和出版者进行处罚。这种处罚有时还要涉及印刷者。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大众传媒在政府的权威面前完全没有独立性,有时甚至要变成政府的传声筒,尤其是在日本发动对中国侵略战争以后,为了加强对于情报信息的管制,以实现其统一思想的目的,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体都被整合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1933年,日本内务省又重新调整了出版审查制度,加强了出版业审查的力度,采取了对于未经许可的出版物予以重罚的措施。同时政府查封出版机构的权限也得到了扩大。1936年,为了有效地控制言论和出版界,日本内阁成立了专门负责情报的委员会;到1940年时,日本政府又在内阁情报部设置了报纸杂志统制委员会,并确立了赢利杂志基本上不予增加的方针;为了找到对大众媒体进行管制的法制上的依据,日本政府分别制定了《电影法》(1939年)、《报纸等发布限制令》(1941年)、《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1941年)、《新闻事业令》(1941年)和《出版事业令》等。
在日本出版传播史中,“横滨事件”是广为人知的。1942年八、九月号的《改造》刊登了《世界史的趋势与日本》一文。尽管该文通过了情报局的审查,但在一个日本陆军军官读了该文后,认为这是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由此,日本的特高科便马上采取行动,对作者进行了拘留和审讯。后来,特高科又进一步对与此有关联的改造社、中央公论社、日本评论社的编辑进行了拘捕。在审讯过程中甚至进行逼供,致使中央公论社两位年轻的编辑惨死在狱中,而其他编辑获得释放则是在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之后。
战后日本印刷媒体的相对自立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媒体进行了强行改革。1945年9月24日,占领当局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关于将新闻界与政府分离开来的指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废除与言论自由相关法令,这些法令包括:1.报纸法;2.国家总动员法;3.报纸等刊登禁止令;4.新闻事业令;5.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6.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施行规则;7.战时刑事特别法;8.国防保安法;9.军机保护法:10.可疑文书取缔法;11.军用资源秘密保护法;12.重要产业团体令及重要产业团体令施行规则。
并且,在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21条中规定,政府要保障国民的集会、结社及言论和出版等一切行动的自由;不允许政府对出版物进行检阅和审查,通信中的隐私也不得予以侵犯。在上述新宪法的保障下,日本国民初次获得了出版和言论的自由,以往由日本政府所强行施加的对出版、发行的各种管理制度也不复存在。由此,战后出版业的发展和产业化的实现也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
自此,日本媒体的自立也就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尽管后来日本政府曾几次试图控制媒体,但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保护,其目的都没有达成。1949年1月,吉田茂曾试图强行通过《选举特别法》,该法令的目的在于维护既有的政治格局,要求媒体不得公开宣布支持某一候选人。其实这一法令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在日本媒体界人士的一致抗议下,该法令最终没能得以实行。
在美国结束了对日占领、日本恢复了主权之后,吉田茂又于1952年提出要重建内阁情报局。该提案也同样在媒体界人士的反对下被否决了。
总的说来,日本大众传媒在战后发生的最大变化是,政府不再直接地控制媒体,基于各种制度性和法律上的保障,日本的大众传媒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第四种权力”,在对事实进行相对客观的报道的同时,对政府行为有一定的监督作用。
在1974年在10月版出版的《文艺春秋》11月号上,刊登了两篇有关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文章,一是立花隆所写的《田中角荣研究》,二是儿玉隆也写的《替田中角荣炒地皮的女人》。《田中角荣研究》一文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的财产的来源和幕后复杂的人事关系。10月20日,在该文刊出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就此事进行提问时,田中勃然大怒,由此,该事件开始引起新闻界及舆论的关注。而且在国会上田中也接连受到一连串的追问。《田中角荣研究》一文的发表最终结果是导致了田中角荣的辞职。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这一事件是由杂志所揭露出来的,而并非是消息最为灵通的日本的报界。
战后日本出版业能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传媒与政府机构的分离有直接的关联。在战前,出版和新闻业多依附于政府,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出版社,往往要受到政府的镇压和禁止,这种压制无论对繁荣新思想和新文化,还是对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战前,日本出版业的另一个特征是“官商”的盛行。一些出版社,虽然起初是民办的,但随着其与体制一方的不断接近,逐渐带有明显的官办性质。严格地说,这种出版社就是“官商”。讲谈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前,由于印刷纸张紧缺,配额是由政府来决定的。讲谈社采取了出版“报国”的经营方针,积极从事对外侵略战争的宣传,在获得了政府的赏识的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印刷用纸份额,因而在其他出版社纷纷被政府取缔或难以得到印刷纸张的情况下,讲谈社却一举占有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大发战争财,大肆进行愚民宣传。由政府所扶持的这种“官商”在出版界处于垄断地位,使得出版业失去了竞争和发展的机会,其危害作用是极大的,其受益者只有“官商”。在日本战败之后,人们要求严惩讲谈社并将其称为“战犯出版社”的原因也在于此。由战前日本出版业与政府的关联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出版与政府有了直接挂靠,那么出版业也便失去了其作为一种产业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对企业注重自由“竞争”和市场原理的原则性的干扰,势必要破坏出版业作为企业发展的正常进程。战前日本出版业的现实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社会互动的经营理念
与战前相比,发生在战后日本出版业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版业被产业化,开始按照市场原理来运营。在市场的压力下,日本出版业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寻求更大的读者市场,尤其是在电视于1953年开播后,不少人视出版业为斜阳产业的情况之下。因此,在这种现实下,日本出版业实现了转型。用清水英夫的话说,就是把出版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来运营。只是,清水认为这种经营理念的形成是由于受到了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于由美国在战后日本所实施的改革;另一方面是由于战后日本的出版业在发展上以美国式的经管理念为模式。“日本和美国的出版界尽管在历史和结构上都各异,但日本在战后始终在忠实地追随美国。这也可以认为是‘什么都是美国式’的‘出版’版本,至少就把出版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来运营而言,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美国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模式。”③清水英夫指出,战后日本出版界的最大特征之一是由书籍出版型转换为杂志出版型。用另一种表述方法则是,由小范围传播变成了大范围传播,发生了由质到量的转变。也可以说是由精英文化变成了大众文化。
清水英夫认为最能体现由书籍出版型向杂志出版型的转换的,便是出版杂志的出版社完全掌握了出版界的主导权(Leadership)。而且,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出版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史。这便是以出版书籍为家业并将其作为出发点的出版社和以出版杂志为出发点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平凡社、筑摩书房等出版社属于前一种类型,而讲谈社、小学馆、文艺春秋等出版社则属于后一种类型。从经营状况来看,后者显然要比前者有更高的利润和更可观的发展前景。而且,就与社会的互动来说,后者则更具可塑性。在日本,为了推销图书,出版业要支付巨额的宣传费用,在1960年前后,在周刊杂志兴起后,随着广告被大量投放到周刊杂志上,出版社的广告收入才超出广告支出。
也几乎是在上述时期,日本图书和杂志的销售额的比率大致为4:6,但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基本持平,在1975~1978年间,与杂志相比书籍稍有上升,但在进入1980年以后,又回到15年前的状态。对此,清水英夫的解释是,杂志在60年代起到了牵引车的作用,书籍在70年代开始呈现明显优势,进入80年代以后,杂志又再次居于主导地位。清水还进一步指出,就日本出版界的情况来说,在1979年和1980年,不单是杂志销售额在回升,新的杂志也纷纷创刊。尤其是在1979年有194种杂志创刊,在1980年有230种杂志创刊。自日本战败以来,这是一种值得注目的现象。一般说来,在社会的转换期,杂志的创刊会变得非常频繁。现在的经验说明,杂志起到了新时代的探测器的作用。
周刊杂志之所以能为战后日本的出版业带来发展的契机,成为战后日本出版成长的起点,其最大原因就在于出版界认识到了社会对信息的大量需求,这一发展空间,因为处在经济起飞前的日本,产业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城市化也正处在发展之中,对处在社会变动期的人们来说,最需要的也许就是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周刊杂志作为满足从前对信息的需求的载体便应运而生。创刊于1956年的《周刊新潮》,产生于日本经济起飞的前夜,当时正在发生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人们对信息和娱乐都有迫切的需求。《周刊新潮》则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这一社会需求。此外,该周刊是由出版社创办的,与以往报社的周刊多做新闻追踪相比,《周刊新潮》所涉及的范围则更为广泛,其内容触及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从事深度报道的特长也使其获得了更多的读者群。周刊的出现,还促成了一种文化意识的形成,这便是“一周文化”(Weekly Culture)的观念的出现。因为在以报纸为中心的时代,人们对“周”并没有一种特别的意识。对于“周”的概念的形成,电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电视节目也是以一周为单位来编制的,可以说《周刊新潮》与电视共同促成了一周文化感觉的形成。④
得益于战后的民主化改革和产业化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日本的道路和交通设施都得到了良好的改善,其标志性的事例是新干线于1964年的开通。交通的通畅也使日本基本上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差别。发达的社会基础设施是日本周刊杂志兴起的条件。有一种说法是,住宅建得越远,杂志的印数也就会越多。这里说的是,人们离上班的地点越远,也就会把更多的乘车时间用来阅读杂志。为了推广和宣传杂志,周刊杂志社还采用了报纸上登广告或在四通八达的电车内做广告的方法,使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周刊杂志的存在。当人们在看了周刊杂志刊登的杂志封面上的标题后,往往会产生购买的愿望。并且,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杂志的固定读者。通过设计和编排每一周的话题,周刊杂志便在一定区域内获得了固定的读者群,由于这些读者群所关注的话题是相同的,因而通过阅读杂志很容易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和价值观念,周刊杂志起到了使全国或某一地区的人同时关注一个共通的话题的作用,这对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让国民获得有益的信息有一定积极作用。从杂志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的变化,杂志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逐渐由以往的报道型、解说型转换为信息提供型。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周刊杂志和月刊杂志有时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且其读者群也具有相互交叉的一面。
此外,有必要提及的是,就图书与报纸和杂志的互动来说,日本出版业所做的尝试也是甚为成功的。其做法是在各大报包括第一版在内的版面的下端刊登大量的只有出版物名称、作者名和出版社等简短信息的广告。著名出版家吉田公彦曾告诉过笔者,在报纸上刊登这种广告,对日本出版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由上述考察可以发现,战后日本的出版业在编辑和经营理念等方面与战前都大为不同,而且,这种不同的根本之处也许在于出版与社会的互动方式的差异。经过战后改革,日本的出版与社会变成了双向的互动关系,由此,出版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的平台并拥有了新的社会功用。
标签:社会互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