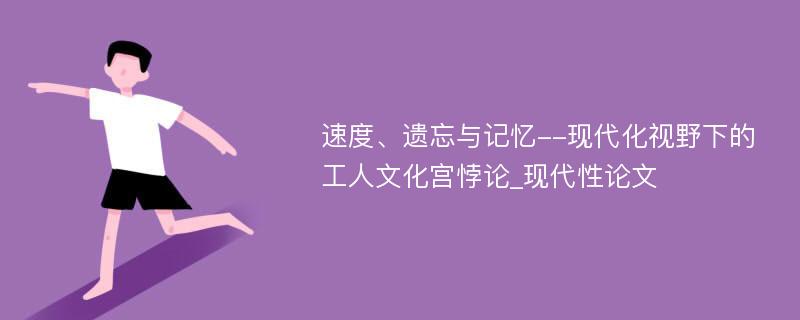
速度、遗忘与记忆——现代性视域中工人文化宫的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现代性论文,文化宫论文,悖论论文,工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人文化宫①地处昆明市中心地带,两条主干道,北京路和东风路在此交会。所占据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当时独一无二的高度与规模,使工人文化宫从诞生伊始就成了昆明的地标性建筑。这里不仅是市民娱乐、休闲、学习的场所,而且是地州云南人来昆明必然的“朝圣”之地。笔者幼年时也曾多次随父母来昆明,工人文化宫以及其广场前大圆盘一样的喷泉成为笔者对昆明最不可磨灭的记忆。 但工人文化宫所独具的这种重要性,恰恰也为它多舛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历年来昆明市的改造、扩建,北京路、东风路这两条主干道都首当其冲。对这两条路的改建虽未必直接伤及工人文化宫,但周边的环境早已沧海桑田。2007年底,昆明市政府着手筹划要在工人文化宫所在地的东风广场建设城市中央公园和CBD,这就宣告了这一代工人文化宫终于要走向终结。2011年12月15日,和工人文化宫隔东风路遥望的市政府大楼率先被爆破;2013年9月7日,爆破的对象变成了工人文化宫。可以说,在这样“过渡、短暂和偶然”的大环境里,工人文化宫的命运其实早已注定。 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探讨空间变更这个表象背后隐藏着的机制。晚近关于记忆的研究表明,任何一种建筑或客体,实际上都是人类记忆的载体,人类社会的建构、文明的传承都有赖于这些载体和它们所承载的记忆。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一方面,人类越来越意识到记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些载体却面临着被大规模拆除的厄运。人类社会也由此面临着从记忆到遗忘这样的重大转向。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转向?本文认为,这既意味着现代性在其蓬勃发展中不断遭遇其自身蕴含的悖论,也意味着社会的建构原则发生了变化。 一、工人文化宫的悖论 在现代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工人文化宫的命运呈现一个奇特的悖论。一方面,正如《人民日报》提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缺钱缺文化”使生存成为全国工人文化宫普遍须要面对的难题,②昆明为这个难题给出了“拆除”这个答案;另一方面,在得知工人文化宫即将和昆明说再见之后,市民们的愁思纷至沓来,他们纷纷倾诉“自己与这幢老楼的浓厚情谊”,内容涉及电影、溜冰、画展、围棋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热情的消息获知者号召市民去祭奠即将逝去的大楼。③ 围绕着工人文化宫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行为:前一种行为指向短暂,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生存的困难,进而导致拆除,都足以说明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社会的演变迫切地需要以新代旧;后一种行为则指向短暂的对立面,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建造—拆迁—建造”的轮回中,人们总是试图为生之艰难找到永恒。 这不是一个特例。无论是这栋已经被拆除的大楼,还是正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中纠结的它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同伴们,都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现代性在其蓬勃发展中遭遇的自身的悖论,也就是短暂和永恒并置、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共存的悖论。波德莱尔的名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④正是对此的最佳写照。波德莱尔的话深刻揭示现代社会偶然、短暂的精神特质,并具体地体现为对新的追求。但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在于……从过渡中抽出永恒”。⑤尽管现代性通过偶然、短暂不断提升人类社会的更新速度,并凭借提升的速度否定了永恒的意义,但隐藏于短暂、过渡背后的,是人类对永恒的向往。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层面来解读工人文化宫悲剧命运的成因。从表层来看,这是因为随着北辰财富中心、金鹰、金格中心等兴起,人们的消费、休闲有了更多的选择,昆明形成了“无处非中”的格局。在更深的层面上,北京路、东风路不仅象征着繁华,而且象征着繁华是经由速度的提升而获得的。正如鲍曼指出的:“当空间被控制着,空间才真正是被占有着,而且对空间的控制,首先即意味着对时间的驾驭。”⑥换言之,正如周宪以“速度政治”所揭示的那样,现代社会里形成了无处、无时不在的对速度的体验、褒扬和崇拜,速度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时间现象,而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观念”,速度是支配我们日常行为的价值判断。⑦笔者以为,速度政治进一步催生了“地理/空间政治”,如果说空间具有某种价值分类的标准,且这种标准是复杂的,那在速度政治的推动下,在速度、空间的合谋下,这种分类标准就逐渐单一化,形成了简单的新/旧的二元划分,粗暴地把新置于旧之上,又通过新排斥了旧。具体而言,新就意味着重要、先进,也就唯有那些象征着最新的事物才有权利占据最核心的位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工人文化宫为何必然会被放逐。事实上,在昆明本地媒体甚至大多数市民心中,它是“一群退休的老年人跳跳舞、下下棋、打打牌的地方”,⑧换言之,它象征着过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就必须被剥夺占据核心位置的权利。 但不同于一般的建筑,这座因名称中有“工人”两字而显得与周围繁华喧闹的世界格格不入的建筑在很长时间内,在昆明市的集体、个人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简单地说,它为市民活动提供了场所,同时它自身也是市民活动的目的。从《云南日报》刊发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窥见工人文化宫为何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从建筑样式上来说,1985年建成的工人文化宫一举夺得当时“全国大中城市中最高、最宏伟的工人文化宫”的桂冠,其高度、外形、色彩等诸多方面都为国内罕见。建筑内装的三部电梯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坐电梯甚至成为当时昆明最时髦的事。1990年代,工人文化宫更广泛地渗入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承担各种培训工作外,市民还在这里游戏、跳舞、对歌、看电影、恋爱。⑨在“思想不集中,想着文化宫”这样略带戏谑的说法里,完全可以看到工人文化宫具有的中心地位,它无处不在,在市民生活中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同时也表征着昆明人对这座城市的认同。如果把眼光投向更广的云南省,工人文化宫甚至还是当时云南人心目中大城市的象征。一位从文山来的马先生在回忆时提道,16岁那年在工人文化宫楼顶领略到的昆明夜景让他真正找到了大城市的感觉,工人文化宫的高大、昆明城的美丽从此在他心中定格。此后他周游世界,登临上海东方明珠塔,日本东京市政厅大楼、法国巴黎凯旋门,虽有种种领悟,却都敌不过当年在工人文化宫顶层的心潮澎湃。⑩毫无疑问,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能提升昆明市民的自豪感,进而更凸显了工人文化宫的重要性。 透过这两层含义,我们可窥见现代性的另一面。如果说速度政治把时间的中性意义赋魅为褒扬的、肯定的话,那它进一步导致了对未来的崇拜和对过去的遗忘。但对过去的遗忘是否就是现代性的全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人们试图在快生活、快节奏的时代重新发现慢生活的意义一样。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在竭力推崇朝向未来的线性时间观念的同时,也发现了过去、记忆的重要性。随处可见的博物馆、纪念馆,无处不在的怀旧情绪,无一不标示现代人对记住过去的渴望,对过去的重新发现。相比于“过渡、短暂和偶然”所揭示的一切都以速度、效率为衡量标准的去人性化的一面(启蒙现代性),对过去的记忆则几乎是浪漫的、审美的(审美现代性)。不可否认,启蒙现代性总是试图以工具理性来统摄现代社会,然而它越试图有所作为,就越容易引起审美现代性的抵抗。在抵抗中,审美现代性总是把启蒙现代性丧失的过去一切视为美好,由此在启蒙和审美现代性中形成张力。(11) 工人文化宫身上所形成的显然正是这种张力。正如上文所说,速度的提升导致了周围空间的变化,速度和空间的合谋更使文化宫被视为落后的;然而吊诡的是,它从1985年到2013年这近30年里陪同昆明市民经历的一切,使它成为美好过去的象征。这种张力导致了在面对工人文化宫(将)被拆除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时,昆明市民普遍持有矛盾的态度:对新、更新的追求已经深入人心,它直接体现为“跨越式”发展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席卷一切;然而,过去虽然是必须抛弃的,却因其融入市民的生活中而是美好的。正如一位市民所说,“其实昆明并不比其他地方对新东西的需求少,只是说,我们还不够”;同样是这位市民,又把被她定义为自我满足、没有危机感、懒散、缺乏上进心,唯一的好处就是适合养老的传统昆明,视为一种无可取代的记忆。(12)这位市民可能没有意识到她话里的矛盾,即对新的追求会使记忆成为玻璃上的水痕,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从记忆转向遗忘 现代社会对速度的崇拜催生了无处不在的对记忆的渴望。我们应该承认,对记忆的渴望极其依赖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正如周宪所言,“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对启蒙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又依赖于这种现代性”,(13)没有启蒙现代性对新的崇拜,现存的一切就不会以旧的名义被摧毁。对它们的哀悼、怀念,乃至现代社会中普遍弥漫着的怀旧情绪都会失去存在的根基。如果工人文化宫没有被拆除,是否会引发昆明市民大范围的怀念和哀悼?笔者以为是不会的,就像我们手里正在使用的锤子,只有在它坏了的时候,我们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如果工人文化宫没有被拆除,人们仍然会在那里散步、下棋、约会,但不会刻意地、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回忆工人文化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里记忆以近乎泛滥的各种形式存在;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博物馆、老照片、纪念馆,甚至各种打着“怀旧”旗号的酒吧、茶餐厅、主题餐馆、旅店如雨后春笋一样勃发。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什么形式的记忆,建筑也好,某个其他事物也罢,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空洞的。我们之所以借助它们来记忆,实质是人类赋予了这些事物意义。开普勒认为,记忆需要某些可以让回忆固着于其上的结晶点,“某些日期和节日、名字和文件、象征物和纪念碑或者甚至日常物品等,”都可以充当记忆的结晶点。(14)结晶点实质上是记忆的媒介,借助这些媒介,人们才可以重述记忆。因此,记忆或对记忆的重述实际上是一种叙事,它既受到媒介的限制,也受到叙事发生的时空结构的限制。反过来看,这些媒介也因此获得了意义,这也就使怀旧得以实现。 针对工人文化宫有两种不同的记忆叙述形式,也可以说,工人文化宫提供或被赋予了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意义。第一种意义侧重个人体验,这也正是现代性追求速度、把社会纳入其工具理性的规划中时忽略掉的东西。云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单晓红在博客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她在工人文化宫度过的整个青年时代。文章的最后,她说道:“我所有关于童年、少年的梦境,都是文化宫对面那个大院,都是那个广场,都是那一个个灯柱。”(15)著名诗人于坚在其富有影响力的《昆明记》末尾则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书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我毕生热爱的故乡,我生命的摇篮、世界和坟墓。”在这篇文章里,于坚还回忆了他所生活的武成路在难以逃避的拆除中,往昔精致的雕梁画栋和相关的回忆都被无情地扫入了垃圾堆。他借一个法国人之口斥责道,这里的人“都疯了”。这篇散文问世时,工人文化宫还矗立在昆明市中心;十多年后,它遭受了和于坚所惋惜事物的同样命运。在这十多年里,昆明变得焕然一新,但正如于坚所说,“那城市中似乎没有过生活和生命”。(16) 第二种意义表征着昆明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身份。在回忆中,昆明知名的文化人徐刚重构了昆明的独特身份:“以文化宫为中心,隔着东风路,西北角的老百货大楼,东北角的邮电大楼,和方圆几百米的地方,简直就是昆明的‘缩写’。那时候的工人文化宫之于昆明,就等同于故宫之于北京。”他这就赋予了工人文化宫极为独特的意义,以至于在它被拆除之后,昆明就失去了地标式建筑。(17)工人文化宫之所以能成为地标式建筑,不仅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还因为其他诸多原因,如它远胜国内大部分工人文化宫的高度、造型等。更重要的是,它是昆明甚至是云南省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全面开启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标志。工人文化宫所在的这块地基上,最先耸立着第一代工人文化宫,1970年时因要建造红太阳广场和纪念馆而被拆除。1985年,拆除了政治色彩浓厚的纪念馆,修建了(第二代)工人文化宫。前所未有的高度、三部电梯,这些表征着现代的因素促使工人文化宫从高度政治性向经济性转变。正因为有这样的转变,市民才走出了无处不在的决定他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日常生活。从此之后,发展、日新月异成为这个城市的主题。我们可以说,从此以后,现代性或社会由鲍曼所说的固态逐渐转向了液态,从笨重转向了轻快。 这种转换为记忆带来了意想不到但也是必然的冲击。鲍曼这样解释液态的现代性:液态现代性“是一种缩短持久性时间跨度的能力,是一种对‘长期’加以淡忘和并不在意的能力,是一种集中关注对短暂性瞬间性而非持久性加以控制的能力,是一种为了为其它类似短暂和应该立即消耗掉的东西清空场所,而能轻快地清除已有事物的能力”。(18)在这个转变下,任何事物都是可替代的,而且新的替代品出现的概率和频率也在迅速增长。它导致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任何即将被替代的东西都是超期的,都是不能再满足当下社会的需求的,甚至有可能沦为贫乏的征候。既然如此,记忆和对记忆的渴望所隐藏的对永恒的追求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负累,对永恒的价值判断也就由肯定转为否定。 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关注的对象从记忆和永恒性转向了当下与瞬时性,“除了可得到的机会范围的扩大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积聚成或形成他的生活轨迹;机车刚刚向前移动几步,铁路就被摧毁了,脚印就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东西刚刚堆放到一起,它们就土崩瓦解了——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忘记”。(19)记忆的对立面,遗忘也由此被重新评价。如果说传统社会对遗忘的评价是负面的,那遗忘在现代社会里获得了正面价值。大卫·格罗斯的观点十分精辟,他指出:“遗忘是一种比记住更好的品质,它可以使人开启新的可能和方向。”(20)遗忘被塑造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它首先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把个体从过去的创伤、焦虑以及历史中解放出来;其次,它是再生性的,遗忘过去为未来开启了新的可能。或许可以这样说,对速度的崇拜造成了遗忘的提速,遗忘则反过来促进了速度对现代社会的控制。在这个视域里,我们就可以理解第一部分最后提到的市民的观点。尽管传统昆明是无可取代的记忆,但它和对新的追求之间的矛盾会否定这些记忆,亦即转向肯定遗忘,肯定对新的追求。 就此来看,工人文化宫的拆除是必然的。如果我们把工人文化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那它开启的只是早期(固态)的现代性,但也必然导致了向液态、流体的现代性转变。这也就使它必须接受这个结果: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它自身也被现代性吞噬了——正如上文引用的文献所说的,现代昆明缺乏的是新,而不是对过去的怀念。这在工人文化宫原址的重新设计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迟至2013年才被拆除,但早在1990年代,昆明市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把工人文化宫这一片区打造为CBD。更值得注意的是,拆除之后,原址上不再修建任何地表建筑,只设有地下商场和停车场。(21)新的工人文化宫将远离它的两个前任驻守近50年的东风广场。这意味着,这个环境将成为一个彻底陌生的环境,关于这里的记忆将全部被摧毁。尽管第三代工人文化宫在人民东路196号拔地而起,尽管拥有同样的名称,但地址的变迁、周围环境的变化,正如(规划中的)红太阳广场转变为东风广场导致其身份和意义转变一样,诸多元素的变化使同名的两栋大楼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些变化暗示甚至强迫我们必须遗忘。 三、遗忘的悖论 遗忘被赋予积极价值,导致了一个新的悖论:尽管它已经脱胎换骨,人们却仍然抗拒它以正面形象出现。单晓红在其博客中提道,“对于一个从小在(工人文化宫)那里长大的人来说,这种改变是好还是不好,面目全非的改造和建设,是迷失还是重构,五味杂陈,说不清道不明”。(22)单氏所言颇为隐晦,却可以见出在迷茫、困惑的情感背后,隐藏的是对工人文化宫被拆除这一事件的抗拒。这也是大多数对启蒙现代性持警惕态度的学者的共同态度,他们甚至把遗忘被赋魅后导致的现象称为“未来教”。与之相比,这些学者更愿意承认记忆的积极价值,人们也热衷于在遗忘已经大行其道的现在重新发掘过去和记忆的价值。阿斯曼甚至赋予了记忆浪漫色彩,由于附着于某些具有超时间性质的载体上,记忆就有了“回溯性观照”能力,它可以瞬间穿越千年,使人们重新获得失落已久的时光。(23)基于此,我们就需要重新辨析遗忘与记忆的关系,以及在转变中,遗忘到底有什么变化,它的正面形象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毋庸置疑,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遗忘被视为消极的、负面的,数典忘祖是对此的最佳写照。遗忘之所以被视为负面的,原因在于记忆才是一个社会正常的建构法则。记忆在人类社会演变中承担了重要作用,它可以帮助人类传递知识、技能和更为重要的信念和价值观。无论是中西哲学家们都强调了记忆和过去的重要意义。老子、庄子、孔子三位都把过去视为黄金时代,柏拉图也强调了回忆在真理探索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王羲之所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唯有过往的一切才是今人和后人面对世界时须要效仿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遗忘显然是对记忆的正面价值的破坏,也是对正常社会的破坏。 但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实:即便在记忆主导的古典社会里,遗忘在人类历史中仍然承担了重要作用。尽管历史往往向我们呈现关于过去和记忆的向度,然而在我们记住某些事件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对另一些事件的遗忘。即使在明显的如父子这样的继承关系中,遗忘仍然伴随在记忆左右。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与记忆共生的遗忘逐渐浮出水面,并获得了正面价值。鲍曼就指出,“历史也是一个忘记的过程”,(24)海德格尔把人类规定为“向死而生”的此在之时,也就肯定了未来对人类的终极意义。斯蒂格勒更是认为,除神话传说之外,种族统一体别无其他共同起源,任何除神话传说之外的起源都只是约定的、短暂的。相反,“决定一个种族统一体的是……一个共同的未来的关系,这个共同的未来的效应造成了一个共同发展的现实”。(25) 在这次转变中,遗忘彻底从记忆手中接管了对社会的规划,人们不再祈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是把可实现的乌托邦视为社会演变的根本动力。这个变化毫无保留地呈现了启蒙现代性对空间的强大规划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启蒙现代性许诺了一个美好的、可实现的未来。在这个美好愿望的推动之下,工人文化宫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迁到了新址,并被更名为新工人文化宫。在此,无论以什么理由被迁至新址,原址及其周围的商业氛围被用于CDB规划,工人文化宫的演变都清楚地呈现了基于工具理性、经济效益的启蒙现代性的精密计算。而这种精密计算又直接表现为对工人文化宫的否定。在这种规划中,不止是工人文化宫,而是任何一种空间都已经沦为固定资本,“在资本折旧和转移的加速趋势中,空间亦成为‘随用随扔’物,就如在一般消费过程中的商品以及一般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和工具”。(26)换言之,在遗忘的主导下,尽管仍然存有记忆,但它只能是对遗忘的象征性的、仪式性的抵抗。 在工人文化宫的演变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遗忘的动力,以及记忆对遗忘的抵抗。市民在缅怀第二代工人文化宫时,常常会提及第一代工人文化宫。它们无论在地点上,还是在命名方式上,都呈现极大的继承关系。可以说,第一代到第二代的演变是从高度的政治化转向全面的现代化,它所标志的是固态现代性的到来。在这个背景下,工人文化宫仍然以记忆为其主导。但第三代与前两代的关系不同于前两代之间的关系。首先,第二代工人文化宫已经被彻底抹平,地表不再兴建任何建筑,第三代彻底搬离了这个区域;其次,这也是第三代工人文化宫指向遗忘和未来的最鲜明的特点,即以“新工人文化宫”为名。这个命名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策略:在名字中保留了“工人文化宫”仍然试图保留从前两代传承而来的记忆,但搬离东风广场使这种继承关系成为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以“新”为名更加消解了诸代工人文化宫间的继承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彻底把这个关系象征化。而在象征化的背后,隐藏的则是遗忘和对未来的向往。实际上,在新工人文化宫“尊重场地历史文脉,体现历史沿革,与未来周边环境协调一致”(27)这样的设计理念中,“与未来周边环境协调一致”才是重中之重,其中隐含着的对未来的执着才是这栋大楼的秘密。 对于一贯以记忆为基本架构原则的人类社会而言,这样的转变可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同时也就为我们带来了亟须解决的众多难题。如果说记忆为人类社会的演变塑造了某个曾经确实存在过的典范,那否定记忆、赋魅遗忘则取消了这个典范以及它们拥有的示范性意义。乌托邦固然被树立为今时今日的最终归属,但它毕竟是不存在的,因此其示范性意义是可疑的,其是否能成为模仿对象也是可疑的。对此,鲍曼有很精到的见解,他指出,把未来视为社会演变的内在动力的问题在于,对未来的崇拜“将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伦理引导到了一片没加标注的、未加开垦的版图,在那片领土上,学到的和处理生活事物的大多数习惯,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作用和意义”。(28) 基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关于工人文化宫的两种叙事为何如此执着地建构起一种几乎稳固的记忆与身份,以及在这两种叙事背后,为何隐藏着普遍的焦虑和不安。 在遗忘的驱动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在当代中国体现得更为明显。速度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耦合,使速度政治在经济这杆纛下呈现更为合理的一面,同时也就为因此而导致的空间的变化蒙上了一层合理面纱:以经济发展为名的大规模拆建最终将带来美好的生活。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和遗忘许诺的美好未来相比,剧烈的空间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难以承受之重。斯蒂格勒正确地指出了种族统一体的本质“只是暂时的,因为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29)究其根本,种族统一体的可变本质被蕴含在可见的延续中,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可见的变化着的本质正是德里达意义上的延异。正是这种延异的本质,才使我们具有辨认我们的来源、历史合法性的能力。问题在于,剧烈的变化使这种可见性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习惯于在历史延续中辨认当下和未来的人们,已经无法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去,甚至也看不清自己的未来。 这种模糊正是导致人们焦虑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也使遗忘在摧毁过去的同时,催生了后者对它的无处不在的抵抗。无论是基于个体体验的叙事,还是基于昆明与其他城市的整体性区别的叙事,实质上都是对遗忘的抵抗。二者都提供了个体或群体与某个固定空间或建筑的相对稳定的联系。在这个联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个体将情感投射于其上的这个对象。对象的超时间性赋予了记忆超时间性,同时也就赋予了叙事者一种固化身份。阿斯曼甚至认为,由于附着在稳固的媒介或建筑之上,记忆与身份就有了超越情境的能力,(30)即在代际间传递的能力。就更广阔的昆明这个地理空间来看,就意味着: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呈现的某种相似特征,如心理、语言、文化,往往和他们共处的某个空间有关。 最终,我们可以这样认识遗忘:当我们选择了遗忘某些事物的同时,也就选择性地记住了另外一些事。这个悖论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建构方式,鲍曼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新的方式,他援引德波的话说,“人们像他们的时间超过像他们的父亲”,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信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两大支柱。(31) 四、结论:未竟的现代性 三代工人文化宫的命运十分清晰地呈现了现代性的各种悖论,以及这些悖论的转变。总的来看,它们是因启蒙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对社会的规划,以及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抵抗所产生的张力而导致的。在遗忘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审美现代性对它的抵抗也越发激烈。可以看到,对遗忘的抵抗并非徒劳无功的,尽管遗忘有效地改变了社会建构的方式,记忆仍然参与到社会建构中来。相比于前现代社会,记忆参与社会建构不再是清晰的、延续的,而是模糊的,甚至可能是断裂的。 吉登斯对这种改变持乐观态度,他把未来视为反思现代性的要素,因此,尽管关于未来的理论有严重的反事实性质,但我们仍然须要正视可供选择的未来,“传播它们会有助于实现它们”,我们只须“创造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模型来”。(32)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或许一种成熟的现代性能带给人们美好的未来,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以工人文化宫的拆建为表征的遍及昆明甚至遍及当下中国的大规模拆建现象,那就会对此持十分警惕甚至保守的态度。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展现了当下中国仍然处于未竟的现代性时期。具体而言,如何反思启蒙现代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防止权力机构强势制造遗忘),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的演变中为遗忘(以及速度)与记忆找到一个平衡点,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①如无特别说明,“工人文化宫”指刚被拆迁的昆明第二代工人文化宫。 ②胡洪江等:《工人文化宫很纠结》,《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第12版。 ③陆敏:《文化宫老楼说拆就拆,许多昆明人难舍难分》,《春城晚报》2013年8月11日,第7版。本文写作之时,工人文化宫已经被拆除,但这里引用的报道则是在大楼被拆之前发布的。 ④[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485页。 ⑤[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第484页。 ⑥[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180~181页。 ⑦周宪:《速度政治与空间体验》,《文化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344页。 ⑧李婧、熊明:《一座地标的过去与未来》,《云南日报》2013年9月6日,第9版。 ⑨李婧、熊明:《一座地标的过去与未来》,《云南日报》2013年9月6日,第9版。 ⑩韩正:《昆明工人文化宫寿命何其短》,《云南政协报》2010年12月27日,第5版。 (11)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10页。 (12)陈舒:《有一种记忆无可取代》,《青年与社会》2010年第3期。 (13)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第16页。 (14)[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1页。 (15)单晓红:《我的文化宫和广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ab48750101gdd3.html。 (16)于坚:《人间笔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321页。 (17)姚霏:《说吧,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第285~286页。 (18)[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第197页。 (19)[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第195页。 (20)[英]大卫·格罗斯:《逝去的时间:论晚期现代文化中的记忆与遗忘》,《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8页。 (21)李婧、熊明:《一座地标的过去与未来》,《云南日报》2013年9月6日,第9版。 (22)单晓红:《我的文化宫和广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ab48750101gdd3.html。 (23)Jan Assman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rans.John Czaplika,New German Critique,No.65,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Spring/Summer,1995),p.129. (24)[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第200页。 (25)[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62页。 (26)胡大平:《空间的废墟化与历史之蚀》,《文化研究》第10辑,第359页。 (27)朱冰:《昆明地标建筑迁建28日起底》,《云南经济日报》2009年11月26日,第A1版。 (28)[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第201页。 (29)[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第62页。 (30)Jan Assmann,"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Memory Studies,eds.Astrid Erll,Ansgar Nünning,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8,pp.110-111. (3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第202页。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6,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