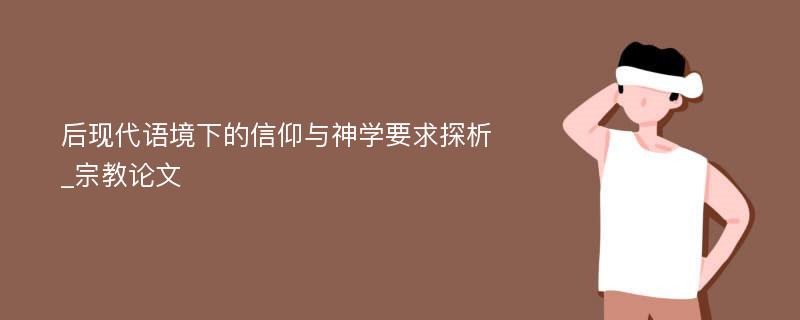
后现代语境下的信仰诉求与神学探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学论文,语境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信仰与神学之间有一条微妙的分界,如果没有宗教的产生以及它所面对的封闭困境,神学或许无以发展。神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宗教的挽救和补充,这一点在20世纪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如布尔特曼所认为的,企望现代人在不发一言的前提下就完全接受上帝,相信圣经中那些类似神话描写的故事,似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神学的意义在后现代语境更加凸显出来。
信徒的上帝不可言说,而神学家的上帝是必定要被言说的。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应该修正的卡尔·巴似的两难处境。卡尔·巴特说:“作为人,我们不能言说上帝;而作为神学家,我们应该谈论上帝。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应该和不能。”这确实是神学家的尴尬,如果他们同时又想成为一位宗教信徒的话。因此,这里的“人”应该改作“信徒”,更为恰切一些。因为对普通人(无宗教信仰者)而言,上帝只是一个语词,就如桌子一样,是在日常语言中可以使用的,不存在能不能言说的问题。
现代主义者希望通过为世俗知识和启示双方都规定出一种不同的认识依据的方法,来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这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显然走不通。这种批判的张力正是后现代语境下神学发展的内在动因,而这种发展的意义便在于神学通过其自身发展历程,从神出发,经过对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论证,最终导出在后现代语境下“精神信仰”的不可或缺性。
早期的神学命题,是对上帝这一本体的寻求,论证其存在和本质。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个方面论证,明显可见以理性论证信仰的痕迹。而这五个方面的论证仍然有预设的前提,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当尼采否定了一切必然性、因果律之后,这种论证的前提消失了,结论自然显得不足信了。本体论的论证,无论经过多少次的往后推断,仍然有一个肯定后项存在的前项,它的存在还有一个前项为其前提,这种无限制的后退只能导致两个后果,(1)得出一切源于虚空的结论。(2)显示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人有不能认识之物。前一种结论带来虚无主义的兴起,后一种结论潜藏着使神学又回到宗教“惟信”的封闭性之中的危机,因此两者都为当代神学所不取。
因此,20世纪的神学已经不再去论证“上帝是否存在”,而更多的从人与神的关系中,去寻找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缺失的“确定性”。这种对“确定性”的需求和追寻,在我看来,就是“精神信仰”。它确是一种信仰,但不同于宗教信徒对上帝的信仰。不管是把它称作神学家的上帝,还是称作彼岸世界、终极关怀,它的实质都是一种对“确定性”的需求和追寻。
我更愿意把神学看作是一种境遇化的神学,它总是当下性的,它面临的是时下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这种相遇使得神学不得不带有浓厚的境遇化色彩。在20世纪这个非理性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一切似乎都处在解构之中,后现代一词标志着对差异性、模糊性、多样性的强调,从福柯到大卫·特雷西,都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否定的确定性存在的态度。事实上,这又掉入到另一个本体论论证的陷阱之中。确定性是否存在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论证,大卫·特雷西已经从历史、语言的层面否定了确定性的存在,“神学家永不可追求确定性,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以试探性的方式追求相对的充分和足够。神学家也逃避不了影响所有言谈的多元性和含混性。他们也只有通过对所有宗教上的终极希望作批判性的检验来试着憧憬某种可以信仰的希望。”
既然神学是人去言说上帝,那么人的存在是神学必然关注的一维。20世纪的神学应该说更多地关注了人的存在,人不能生活在虚空之中,沉重之轻固然让人不能容忍,轻之沉重更加让人无法承受。因为人是有理性思维能力的,虽然康德已经论证了它的有限性,但它毕竟存在,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因而人总是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求一种意义,使人自身得到一种确定性的确认。即便是那些宣称生活在虚空中的人,这种虚空本身也是其自身存在的一种确定性确认。人们不要求知道这种确定性本身是什么(人们也不可能知道),但我们知道自我存在需要这种确定性,追寻这种确定性,因而它必然存在。
确定性是一种意向性的存在。它存在于人们意识的意向性之中,它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实存,而是在人们意识的指向性中存在。这种确定性规定也正是神学所必须追寻的,因为神学的对象是神和人的二维结构,在这两维之间存在着一种批判的张力。极端性地倒向其中任何一维,最终都会导致神学的堕落。因而,神学家的责任更是努力在这种二维体系结构之中寻求确定性,以达到一种动态制衡状态。所以,巴特的危机神学、朋霍斐尔的“非宗教性”神学诠释、布尔特曼的生存神学、蒂利希的系统神学,所有神学家的这些看似各异的努力,都在寻求那位神学家的“上帝”,——对确定性的需求和追寻。可以说,宗教信徒是“惟信”上帝,神学家是通过自己的神学论证而“依赖上帝”的。宗教信仰是一个直线进程,而神学信仰是一个曲线演变性进程。最后,神学家也回到了上帝,貌似殊途同归。但我们前面论述过,这位上帝与信徒的“上帝”是截然不同的,神学的意义也就在这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显示出来,它明显高于那些封闭、陈腐的教规教条和仪式仪礼。
神学家的“上帝”推广到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身上,便是所谓的“彼岸世界”,“终极关怀”,也就是人类的精神信仰诉求。神学家更多地是从神学的二维体系中寻求确定性,而人类则是为了自身存在寻求确定性。“如果世界进程直接地、毫不错谬地遵循了正义的规范,那么也就没有对信仰的需求;那意味着我们生活在天堂里”,恰恰相反,在20世纪的整个背景下,谈论正义、真理、希望都是一种奢论,然而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解构一切的完整背景了吗?在这种彻底解构的前提下,我们还能找到自身存在的确认和意义吗?尼采宣称要重估一切价值,但据此认为尼采相信自身存在不需要确认和意义,认为尼采没有信仰,是错误的,他毕生都在论证的三个核心“生命哲学”、“权力意志”和“永恒循环说”,不正是他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体认吗?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建立一套信仰体系,因为显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尼采。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诉求,都需要寻求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判断。在20世纪,这便是一种对确定性的需求和追寻,人要有对自身存在的确认,这一确定性最后可退守的根基,才能面对后现代语境下对确定性不同层面的解构风潮,才能守护自身存在。
20世纪神学家们的神学论证与人们的信仰诉求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它们共同指向对确定性的寻求,如果说雅典与耶路撒冷的上帝是不同的话,这里的上帝却是合一的,它便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