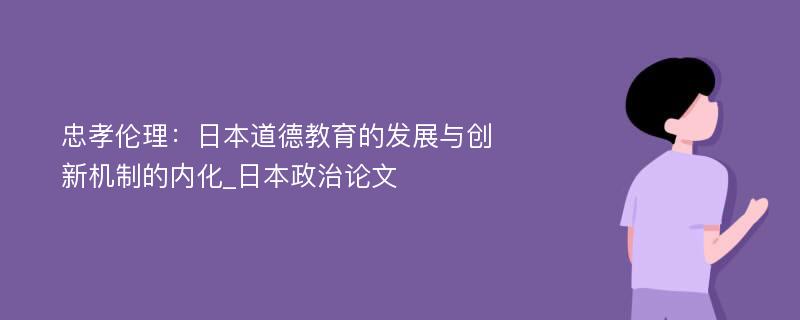
忠孝伦理:日本道德教化的展开与创新机制的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化论文,日本论文,伦理论文,忠孝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G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887(2006)02-0091-04
忠孝观念作为日本社会系统的中心价值,对于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的当下状态有着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忠孝观念有助于维护日本社会的高度统一,有助于日本经济实体内部的团结协作,是“保驾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因素”①。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忠孝观念使日本社会的垂直整合得到强化,服从命令成为绝对的行为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1]。从精神伦理同社会结构的局部结合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忠孝伦理在日本教化过程中却导致了另外的结果。从忠孝伦理的发展路径上看,日本的忠孝观念源于日本宗教的世俗化,是同其民众与国体的一体化而存在的,它在事实上对形成日本特色的高效、实用的创新机制起到了内化的作用。
一、儒教伦理:日本的忠孝伦理及其辩证关系
源于中国儒教传统的“忠孝观”在日本得到了适应性的发展,以忠孝为伦理的体系中,居首位的当然是忠,而与忠紧密相连的便是孝。忠是作为一个大和子民的首要政治义务,是对至敬者;而孝则是一个家庭成员的第一家庭义务,是对至亲者。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孝先于忠;在以政治价值优先为特征的日本,忠却优先于孝。在日本,忠与孝之间并不矛盾,培养孩子之孝,是为了成人之后尽忠,孝强化了忠。而且,忠与孝联系得非常紧密,几乎是同一的,“孝子门前求忠臣”便是忠孝辩证关系的精辟体现。
同中国儒家伦理的根源一样,日本的忠孝观念也来自于民族的血亲观念。早在公元初期,大和民族就巩固了他们在中部日本的统治地位,并已经形成了太阳女神和天照大神为统治一切神和大和民族的神圣祖先的神话传说。对于日本人来说,人的肉体乃由父母分出,父母及祖先皆是家族之神,孝顺父母、敬畏祖先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日本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祭祀用的小神龛,每天都要祭祀祖先。日本国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创始人丸山敏雄认为“这种对双亲和祖先的真情和尊敬自古以来被称作‘孝’,是道德之本。”② 这种对父母的尊敬和对祖先的祭祀可以使人时常记起血统的神圣以及家族成员对它的义务。
在日本,“忠”的血亲源流在于天皇的种族高贵性。日本人把天皇纯正的血统泛化为大和民族的神性,是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神及民族的代言人。因为“在最广义上讲,家族和国家是同一的,皇室就是主系家族,而所有日本人的家族都是其支系家族”③。日本学者吉田松荫(1830—1859)曾这样描述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统治者抚养人民,人民则报答统治者之大恩大德。统治者与人民为一体(君臣一体)。对统治者之忠诚与子女对父母之孝乃为一体和同一物。”④ 值得一提的是,当对天皇的高度尊敬在跟忠与孝相关联时,国家的概念便产生了一些变化。血亲关系和政治关系相融合,作为养育者的神性被替换成政治权威。神、天皇、君主及父亲倾向于被当成等同的东西。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单一的亲族。天皇就是“神”,就是“君主”,就是民族家族之“父”。人民即是崇拜者,是臣民,是儿女。忠诚便是“大孝”,献身父母则是“小孝”,小孝只是为了能履行大孝而存在。这样,回报天皇之恩的义务便超越了其他一切义务之上。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孝顺父母(及祖先)、忠于主君、效忠天皇是每个日本人的天命。这一思想不是把社会视为一种必须维系的和谐均衡,而是倾向于将社会看作是在履行对上司义务的单一方向上的运动。至此,“忠”与“孝”便超越了血缘关系而具有了共同体的属性,从而便同组织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家、组织与国家:日本的忠孝观念的继承与展开
日本忠孝观念的形成是同日本宗教的世俗化过程相一致的。日本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其中,神道教和佛教都将神视为大慈大悲的高级存在者,这包含了要求信徒忠诚和报恩的义务;心学教导悟性与无私地献身,并通过强调家臣的忠诚与无私的巨大重要性来强化权力的扩大;而儒教的《孝经》得到了尤为广泛的传播。例如,孝谦女帝(治世749—758)曾要求每个家庭必备一册《孝经》,学校要讲授《孝经》。对《孝经》的重视,或许可以看作是“孝道”在日本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的一个尺度。孝是仅次于忠的最高道德,也就是说,宗教使家族本身渗透了政治价值,并成了政治形态的一个缩影。所有的宗教行动,无论是报恩还是要求个人醒悟,首先要求采取的是履行自己在世俗中的义务形式,仪式、祷告或冥想对于首要的伦理来说,均居于其次,这是日本宗教的潜在影响之故。总之,日本宗教精神的首要伦理即是指履行世俗中的忠(政治义务)和孝(家庭义务),它为企业服务和创新奠定了价值基础。
众所周知,宗教的社会功能是为社会的中心价值提供一系列的终极意义。当人面临终极挫折时,宗教能够提供终极力量来满足人的动机需要。同时,它对社会系统中的紧张积蓄也有消解作用,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宗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江山社稷的有效工具。在统治阶级的推行下,日本宗教逐步与世俗伦理相结合,忠孝观念成为日本宗教的核心教义。这样,宗教通过社会中的主要集体——国家与家庭——被认为既是世俗的组织又是宗教的组织这一事实,为中心价值系统提供了一系列终极基础。履行对父母(及祖先)和政治权威的义务便被赋予了终极意义,保证了未来的祝福和庇护。所以,对这些集体及其首领的忠诚不仅具有世俗的意义,而且具有终极的意义。
儒教的“家、国、天下”的理念在日本发展为“国民一体”的伦理观,并强化了忠孝观念。早在幕府时期,由于天皇——幕府——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力分化,忠诚观念的对象性并不明确。“忠”通常讲的是对自己的主君的忠诚,而当时的“主君”一词在其意义和内容上都是模糊的。随着“尊王”口号的提出,忠诚观念的对象逐步指向“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⑤——天皇。对天皇颁布的政令,所表现出的尊敬之情,证明了人们对政治权威盲从程度。高度的公共秩序是这种盲从的另一个例子,就像武士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后,甘愿剖腹自杀以示忠心那样[2]。
“国民一体”的彰显在明治维新前后达到了极至,民族主义思想在日本深入人心,忠君与爱国在本质上被合而为一。这一变化使日本人民对统治者采取完全服从的态度,而且这种服从是出于自愿的。归根结底,是因为日本国的概念就是把宗教的、政治的及家族的思想不可分割地熔铸在一起,神、天皇、人民在意志上达到了同一。“这依据于民众与政体一体化的事实。民众感到他们自己被认为是国体即国家政体——一个极重要象征的一部分……民众作为国家(国体)的成员,通过与国家一体化来获得满足,并分享国家的威信与意义,因此,他们感到政治权威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便自愿服从政治权威的要求。”⑥ 意志的同一、利益的统一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君与国的忠诚,使个人同集体(小到企业单位,大到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创新的主观意愿与个人的背景统一起来,家庭、组织和国家乃至君主被统一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天人合一”思想在日本被增加了新的环节,即“天”(国家君主)和“人”(个体)之间的组织,儒教思想得到了新发展。
三、日本的忠孝伦理:促进创新的内在性动力
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将会是一位真正忠诚而孝顺的人。”⑦ 学问被赋予了很高的价值,就像尊重书籍和对教育、老师的尊敬所表明的那样,但这学问被放在为忠孝目的服务的前提之下。忠孝观念不但已经渗透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领域,而且还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激发大和民族的创造精神,其作用更是独特的:
第一,忠孝观念对于集体最终目标的关注,是日本创新机制的核心。
在日本人看来,集体的目标是最高目的,个人及子集团的目标必须严格服从于集体目标。当集体有着明确的系统目标,且该目标对所有人都明了和有意义时,个人与集体的同一化的过程将会变得最为强烈,人们将用关涉到集体目标的强有力和持续不断的行为来表现这种献身。
首先,“对集体首领的忠诚和对卓越的系统目标的忠诚之要求,可以压倒对和谐的关注,推动旧的社会形态的分化瓦解,推动旧的集体的分化瓦解以及抛弃旧的陈规陋习。在不破坏中心价值的情况下,这种潜能有助于形成积聚的社会变革的动力与能力。”⑧ 因此,最终推翻幕府的运动是以两个明确有力的目标即尊王和攘夷为特征,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为一场武士阶级领导的社会变革运动,明治维新的动机首先是政治上的——恢复皇权、驱逐外敌,而其根本是经济上的——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并利用他们新创建的现代化国家机构,来为达到增强国力的第一目标服务。在这里,集体目标再一次显示了它的无上权威。这一点在家族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优秀的表现显然是对子女的要求——否则可以因其无能或任性而遭到废谪。而支配人即“总经理”如果能更积极主动地去履行集体目标的话,那么为了实现目的,在管理决策过程中支配人甚至可以代替具有法律地位的主人。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如果旧的意识或旧的制度妨碍了集团目标的实现,那么,人们就会创造出新的意识或机制来替代它们。这使社会系统的创新与变革成为可能。
其次,日本人忠于上级、忠于天皇,但这并不是因为对象的人格魅力,而是由于对象的地位及其命令对于实现集体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处于社会系统顶端的天皇和政府因集体目标的绝对权威性而具有高度的整合能力,这样,政府对于科学技术创新的目标导向就显得十分有效。例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提出了“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战略目标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并且于2000年提出日本“50年得30个诺贝尔奖”的具体计划。这一目标立刻引起日本科学界的积极响应,至2003年,日本得诺贝尔奖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2个,仅最近3年就有4人获奖。近年来,日本的论文产出数量和引用数量也都迅速增长,1996~2000年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文数量占到世界总数的9.38%。显然,“忠”于集体而非“孝”于个人的“忠孝观念”成为催生创新能力的内在动力。
第二,忠孝观念重视业绩,能动地转换了“职分”的概念,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原动力。
日本人的忠是建立在报恩这个深层次文化基础上的。“恩”的概念源自我们业已分析过的血亲关系和宗教教义。人的一切皆是祖先和神的无限授予,忠孝的义务也是天定的,因而,当然是无限的。而当同“职分”、“业绩”相关联的时候,忠孝观念又被赋予了深层的意义。
忠孝义务与职业相结合就产生了“职分”的概念。日本社会中,“职分”意指“职业并不仅仅是目的本身,而是社会的一部分。人的职业应是履行他对社会所负有的义务,应是他所发挥的作用,这一作用使他所受的社会恩惠得以合法化”⑨。出色地完成工作、达到集体目标,就是履行上天赋予自己的义务,是自己获得社会权利的前提。因此日本人特别强调对工作的恪尽职守。这种恪尽职守观念和责任感是如此强烈,以致它很类似于新教徒的“天职”观:“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⑩ 对于日本人来说,工作本身并不是价值,而作为对集体的无私奉献的一种表现时工作才有价值。
“业绩”是一个与“职分”密切相关的名词,它是作为衡量一个人对其职业是否忠诚及忠诚程度的可量化标准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对职员表现的高度评价意味着与其相关业绩的比较——只有在本职工作中做出良好业绩的职员才算履行了忠孝义务。应该注意的是,在日本,忠诚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恭敬和献身,而是与成功和奋发努力相结合的能动的服务与表现。“职分”概念与“业绩”价值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就要求人们在工作中为实现“业绩”价值而不断创新、埋头苦干并且严格遵守交易中的正直纪律。
“职分”和“业绩”的优越性使日本人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专注于本职岗位的技术革新,以期望更好地履行天定的职分。这已经渗透到日本人的价值观里面。例如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小柴昌俊在2002年东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就说过:“决定人的一生的,也许不是学习,而是积极工作的态度。”今天,在日本比较富裕的情况下仍普遍出现“工作狂”和“过劳死”的现象,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许多普通技术人员也拥有自己的多项专利,因为创新本身就是履行忠孝义务的途径之一。这样,创新活动本身就获得了世俗和宗教的两重意义,也就成为人们不断从事创新工作的原动力。这实际上同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分析日本的企业文化特征是一致的,即创新的企业文化精神同日本民族的伦理价值密不可分[3]。
第三,忠孝观念造成了个人与集体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效应,这有利于降低创新活动的“摩擦成本”。
创新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或系统行为,它一方面要服从于创新主体的目标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创新主体内部以及创新主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固有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制约。如果创新主体内部没有有效的整合机制协调各子系统之间的利益和行动,那么,“由于利益格局变动所形成的技术创新行动的阻力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摩擦成本’,无疑造成了创新主体在资源上(如时间、物资和人力等)的浪费。”(11) 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创新活动及其制度化过程。因此,任何一种创新主体内部都需要这样一种整合机制: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模式,而且使人们之间在创新活动中的沟通、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可预期方式实现。
而忠孝观念为日本社会形成高效的整合机制提供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使个人与集体紧密结合,呈现“机械团结”的状态。机械的团结也就是一个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合形式,贝拉认为“这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或许是主要的整合机制”(12)。它使日本社会各个单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创新主体易于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日本企业里上下级关系被称为‘亲分’与‘子分’,‘子分’可获得‘亲分’的扶助与支持,同时有义务为‘亲分’随时效力。”(13) 在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这种自上而下的有序的“纵式结构”,是“文明开化”之后忠孝伦理与现代西方组织学原则的融合物,有利于降低创新活动的“摩擦成本”,从而提高创新主体的运行效率。
四、结语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为日本的忠孝观念同创新的关联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由忠孝观所形成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已经成为日本创新的关键性要素。且不论这些社会资本“嵌入”(embeddedness)创新机制的直接作用,它们在潜在影响和政策创新等方面的作用也同样令人不能小觑,正如简·弗泰恩所说:“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库存’。它是公司建立有效合作关系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一项更具合作性和积极性的联邦政策。”(14) 在日本,因为忠孝观而赋予的社会资本特征比弗泰恩的建议更加具有成功的几率,因为政府政策在视“国民与政体为一体”的日本更加容易被通过和实施。
毋庸置疑,忠孝的伦理观在创新上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如强调“报恩”使创新活动带有被动色彩、强调“表现价值”而使追求理论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强调“秩序”而加重了社会的等级制度,使日本的创新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等[4]。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忠孝观念的正功能后果及其实现条件,也要看到其负功能效应及控制手段。可以说,日本创新机制的出现和成功固然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忠孝观念不能不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赵虹:《略谈日本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精神的作用》,《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51-54页。
②龚颖,余勇:《幸福之门——日本国社团法人伦理研究所的组织、理论和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③④⑥⑦⑧⑨(12)R·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三联书店,1998年,第26页,第128页,第30页,第23页,第24页,第141页,第42页。
⑤R·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9页。
⑩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57页。
(11)冯鹏志:《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机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4期,第21-28页。
(13)陈志军:《日本企业文化中“内和外忠”的思想启示》,《立信会计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第46-49页。
(14)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