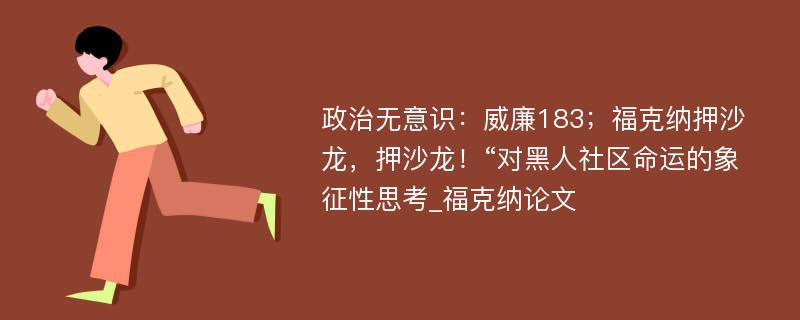
政治无意识:威廉#183;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对黑人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龙论文,象征性论文,威廉论文,黑人论文,沉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种族问题,国内外研究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不同程度阐释了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种族歧视的憎恨与谴责。然而,一个重要的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就是,如果他在先前的《八月之光》等小说中已经把种族冲突所带来的血淋淋的后果清楚地展现给了读者,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他更倾向于向读者揭示种族问题演化的一般规律以及他作为现代作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表现出的政治行为,即“政治无意识”。“政治无意识”现象是指对某个政治群体中的个体而言,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受其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经典著作《政治无意识》中对政治无意识作过精彩的论述,认为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即文化文本(或文学文本)容纳的是个人的政治欲望:“一切文学,不管多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①因此,通过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对《押沙龙,押沙龙!》中黑人群体命运进行象征性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透彻地领悟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种族主义所进行的沉思。
一、对于种族主义起源的沉思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知体系,类似于哲学或社会政治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以一定理论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具有强烈的主观意图——论证或争取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同样,作为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是因为政治因素在文学作品中居于优先地位,同时又处于文本最深层的无意识状态,其性质和功能主要由具有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决定,因此,种族问题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就种族权力来说,大多数西方政客认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所谓的精神和文化学家的观点,认为黑人被歧视的原因在于白人有能力和权力这样做,其根据是人类的本性就是歧视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另一种是所谓的社会与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黑人奴隶的地位和白人至上的特权都是无法理解和预知的社会现象,其根据是权利和财富被集中到由白人组成的阶级手中,先天的不同、权利和动机都影响了黑人的发展。上述两种观点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缺乏相应的说服力,因为福克纳把塞德潘祖先生活的山区描写为“乐融融”的世界:白人和黑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紧张关系,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相互通婚,彼此争论,没有聪明与愚笨之分,肤色对他们显然没有任何影响,相反,贫富差异悬殊的白人之间的冲突成为美国南方社会最头疼的问题。这一点,从福克纳的另一部作品《下去,摩西》中也可以看出:
那第三种人,比起与他们不同种族的人来,与他们肤色相同、身上流的血液相同的人到更像是外人,——这种人又有三部分人组成,彼此各不相同。(277)②
这里所说的“第三种人”即白人穷人,虽然他们与富裕白人的肤色一样,但却生活在南方社会的最底层。从美国历史来看,这种现象也的确存在,如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弗吉尼亚生活着大批的贫困白人,他们为生机所迫,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导致了种植园主雇佣贫苦白人的工钱要比雇佣黑人雇工的价格低得多。对于直接目的为获得经济利益的种植园主来说,雇佣劳动力并不在意其肤色,他只关心谁能给他带来最大效益;同样,对于被雇佣的贫苦白人来说,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报酬,也不会在意与自己处于同等被雇佣地位、却不能给自己增加工资的人的肤色。这样,贫苦白人更容易与处于同等地位的黑人联合起来,反对上层白人的剥削。1676年的弗吉尼亚的贫苦白人在纳撒尼尔·培根的率领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向人们揭示了受盘剥的贫苦白人很容易与自由黑人联合起来,以图改变美国南方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政治无意识在其形成的客观过程中包含了某些不自觉的因素,称之为“政治无意识”因素,这些因素常常在适时的环境中发生作用,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条件。当南方历史发展到托马斯·塞德潘生活的时代,由于黑人人数的剧增,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处于领导地位的上层白人看到,如果穷苦白人与黑人继续联合,其社会地位随时都会发生动摇。为了消除这种潜在的危险,他们向穷苦白人灌输白人与黑人在遗传基因、智力发育、道德修养等方面存在差异的思想,威胁穷苦白人如果继续与黑人联合的话,白人的血统会被黑人的血液所玷污,并最终导致白人世界的堕落。在“白人优等”的幌子下,南方上层白人瓦解了穷苦白人与黑人的联合,人为地为穷苦白人提供某些权力和待遇,同时相应地剥夺了黑人的权利,结果穷苦白人只能依附上层白人,被迫抛弃与自己经济地位相同的黑人。至此,我们看到《押沙龙,押沙龙!》与先前小说不同之处在于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已经清楚地阐释了南方人难以回避的关于种族意识的起源,明确表明了南方的种族意识是南方上层白人为维护其统治而强加于黑人和穷苦白人身上的枷锁,其目的是为其政治利益服务。正如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人类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人类在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都必然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③同样,《押沙龙,押沙龙!》也告诉读者,南方上层白人为了确证自我身份,人为建构了他者,即黑人。
二、对于种族分离目的的沉思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其特殊的政治利益决定的。塞德潘的种族意识同样如此。随其家族从山区搬到弗吉尼亚的泰德沃特地区后,塞德潘开始了解到白人与黑人的差别。从自己的姐妹身上,他观察到:
某种肤浅、平板、默默地观看黑鬼的方式,那是他那几个姐姐和别的一些她们类型的白人女子看黑鬼的方式,不是怀着恐怖或是畏惧而是一种主观设想的敌对态度,生成这态度也不是因为有任何确知的事实或理由而是出于一种感觉,从白人也是从黑人那里一代代传下来的感觉。(186)
塞德潘姐姐对黑人的反感加深了塞德潘对白人与黑人之间对立关系的认识,并注意到了一些白人居住的房子和黑人奴隶的住所虽然一样破烂不堪,但不同的是白人的房子上点缀着自由的光环,黑人奴隶的房子却结实和干净。穷苦白人和黑人本来属于南方社会下层阶级,日常生活中的差异自然存在,但在南方上层贵族控制之下,穷苦白人拥有自由,没有经济地位;黑人经济上勉强比白人好一些,但却失去了自由。因此,可以说,无论是自由的光环,还是结实和干净的房子,都是南方上层贵族从政治上在穷苦白人和黑人之间人为制造的紧张关系。
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往往通过集团(或阶级)利益反映世界和说明世界,因而,特定社会集团(阶级)常常利用政治利益这个杠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南方上层贵族赋予了穷苦白人殴打黑人的自由,如塞德潘的父亲曾兴奋地告诉他:“俺们今儿晚上把佩蒂伯恩家一个黑鬼猛抽了一顿。”(187)同样,塞德潘也这样告诉康普生将军说:“你知道你可以揍他们……他们不会还手,甚至都不抵挡。”(186)穷苦白人可以在自己感到不满意的时候选择自由离去,但对于黑人来说,很可能被当作猎物被追逐、押回,甚至作为警诫被屠杀。因此,当塞德潘试图通过那座豪华大门的时候,并没有在意黑人守门人,遭到拒绝后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为此,他离开泰德沃特来到海地,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白色肤色所具有的政治利益是确保他挤入南方上层社会、实施自己“宏伟计划”的唯一资本。塞德潘成了种植园的把头,监视黑人奴隶,并告发了黑人奴隶的起义计划。福克纳通过塞德潘早期种族意识的变化提醒读者:穷苦白人无法直接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上层社会白人身上,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发泄到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黑人身上。
塞德潘的父亲也是如此。这个出生在山区的穷苦白人非常善良,即使在到达泰德沃特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后都不会欺负任何人,他认为:“真实的黑鬼,活的人与活生生的皮肉,他们在感受着痛苦、在扭动与呐喊。”(187)然而,后来他却参与到殴打、体罚黑人奴隶的事件之中。在他看来,黑人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抽象体,沦为了其发泄自己受压抑的愤怒的对象。有些读者认为,福克纳叙述穷苦白人和黑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作品的讽刺性,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南方战前的历史上,穷苦白人与富裕白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穷苦白人必须强迫为富裕白人效忠;而穷苦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穷苦白人和黑人的完全隔离,结果是上层富裕白人从根本上动摇了穷苦白人与黑人联合的可能性,把穷苦白人阶层拉拢到了自己身边,并从精神上桎梏了其行为。即使那些对黑人或者对自己社会地位感到不公平的人,如小说中穷苦白人沃许等,都无能为力。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只能像塞德潘的父亲一样,充当上层白人的工具,把自己的愤怒和挫折发泄到与其一样不幸的黑人身上。
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强调了潜在的政治阐释是解读一切文学文本的大前提,这为理解《押沙龙,押沙龙!》中南方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福克纳多次有意识地探讨过南方种族意识对南方人行为方式的影响,阐释了被压抑和被替代的种族无意识发生作用的形式,如《喧哗与骚动》中杰生对黑人的蔑视、《八月之光》中珀西·格利姆的种族仇恨等。然而,对于生活在海地的塞德潘,福克纳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那样带有严重的种族主义思想的白人,而是一个依附上层白人并始终与黑人打成一片的穷苦白人形象。塞德潘在坚守自己“白人”价值的同时又较为“人性”地解决了与黑人的关系。这一点,从他处理与前妻尤拉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他抛弃尤拉的原因在于他知道,在南方种族主义者眼里任何带有黑人血统的人都会被认为是黑人。与其父殴打黑人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尤拉身上,而是归结到那个在吊床上睡觉、给他带来侮辱的上层白人身上,因而发誓要像这个上层白人一样拥有宏伟的庄园和一群前挤后拥的黑人奴隶。为此,他抛弃了只有十六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妻子,但作为为补偿,把自己在海地的家业留给了她。叙事是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通过塞德潘对其前妻的态度,福克纳告诉读者,塞德潘抛妻离子的做法是被迫的,具有典型的社会性,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黑人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
三、对于种族对立的沉思
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形态极力探讨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而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和伪装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因而形成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④从《押沙龙,押沙龙!》情节来看,塞德潘与《八月之光》中的乔·克里斯默斯的情况一样,他在到达杰弗生镇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甚至还有人怀疑他带有黑人血统。然而,他的命运和乔的命运完全相反。当镇上大多数的白人以敌对的眼光看待塞德潘的时候,他却忙于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用神秘的手段从一个印第安酋长手里攫取了大片土地并神速地建起了庞大的百英里庄园,迎娶商人柯德菲尔德的女儿,邀请人们到其庄园做客,迫使镇上的大多数人,如康普生将军和柯德菲尔德等接受他,并认可了他作为白人的特殊身份。对此,就连塞德潘的妻妹,罗莎·柯德菲尔德直到1910年与昆丁·康普生谈话的时候,都无法理解南方上层社会对塞德潘的接纳。在她看来,康普生将军和她的父亲柯德菲尔德是两个受人尊敬的南方上层人物,在杰弗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可能接受一个与自己背景完全不同且与黑人奴隶不分你我的外来人。然而,塞德潘确实做到了,他娶妻生子,拥有大片土地和大批黑人奴隶,俨然成了南方上层贵族中的一员。
当两种意识形态接触并发生碰撞之时,居于主导的意识形态,必然以自身的尺度衡量处于劣势的意识形态。塞德潘聪明之处在于他在抛弃南方传统观念的同时,又显示了处理种族问题的机智和能力。杰弗生大多数白人居民对黑人有一种自然的憎恨,认为白人比黑人优越,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和黑人奴隶之间没有距离,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之间的唯一不同是他领导着他们,并像一个部落首领一样,通过赤手空拳地搏斗,获得自己的位置。在此,福克纳为读者塑造了一群“魔鬼”的画面:一个强壮、狡诈的恶魔首领率领一批装备优良、死心塌地的黑人追随者;他们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破坏土地、庄稼、商店、房子,可能去偷盗货物、金钱,甚至可能杀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社会群体啊,又有谁能制止这种对南方上层社会的威胁呢?如果南方社会拒绝接受塞德潘,那么南方上层社会就会面临包括失去领导权在内的很多社会问题。正如康普生先生所揭示的那样:“任何人只要看看他便会说,只要有机会和有需要,此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和乐于去干的。”(35)单从这一点来看,康普生和柯德菲尔德对塞德潘的认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人一方面声明塞德潘是个白人,另一方面极力创造条件把他拉拢到自己身边。正是借助于这种上层社会的声明和接纳,塞德潘获得了自己所渴望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完成了其“宏伟计划”的第一步。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选择也许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塞德潘充其量不过是受几个黑奴拥护的外来“魔鬼”,但作为创作者的福克纳并不这样认为,他把塞德潘送到海地,提及到海地黑人奴隶通过激烈的起义试图推翻统治阶级,用血淋淋的事实警告了南方上层社会。事实上,南方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如在1822年丹麦·维奇领导了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奴隶起义;1841年135个黑人奴隶劫持了一搜驶往新奥尔良的船只,改道去了西印度群岛;1859年约翰·布朗联合10个白人,领导黑人抢占了哈普斯渡口。特别是1831年的奈特·特纳领导的弗吉尼亚黑人暴动,这次暴动发生的时间恰好是塞德潘进入杰弗生镇的时间。奈特·特纳领导的暴动和塞德潘生活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理解康普生将军和柯德菲尔德的行为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接纳塞德潘不仅体现了作品中南方上层贵族的大度,而且与阻止其进入杰弗生相比,对康普生将军和柯德菲尔德之流来说担负的风险小得多。塞德潘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了解南方社会的利益规则,利用了康普生将军和柯德菲尔德的矛盾心理,促使他们在考虑种族问题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来选择个人经济利益和南方白人的统治利益。
在文学批评中,政治无意识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使批评家们回复到被压抑和被淹没的基本历史文本的表面,来探索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作品的有效途径。在福克纳看来,虽然塞德潘拥有的金钱和势力使自己爬上南方上层社会,但镇上的人并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因此,福克纳在众多场合下把他描写为带有很多缺点的南方社会下层人。从罗莎“他不是一个君子”,到康普生将军“他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的评价,再到多数的描写和诅咒,“这个东西长的眼睛就像黑煤块安在生面团上一样”,福克纳始终把他与凸眼、安斯·本德伦、弗莱姆、斯诺普斯之流的穷苦白人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都存在道德和性格方面的缺陷。福克纳把塞德潘归于这一类人,表明了作为穷苦白人的塞德潘与南方上层贵族存在本质的区别。虽然在种族主义者眼里,南方人仅仅分为黑人和白人两类,但无论是康普生将军,还是柯德菲尔德,都没有真正认可塞德潘在南方社会的政治地位。这种矛盾的心态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南方种族意识是按照居于统治地位的南方上层白人的价值观来划分的,而种族对立归根到底是一种政治权利的较量。
四、对于种族主义消解途径的沉思
政治行为的社会合理性程度,或者一个政治实体行为的进步性质,一般说来是由其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的性质所决定的,主要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主体的利益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相一致的程度。与其生父塞德潘一样,查尔斯·邦来到密西西比时也没有显赫的社会背景,然而,杰弗生的居民显然对他更具有好感。在他们眼里,他那“举止从容安详,气度傲慢豪侠”的处事风格使塞德潘看起来“妄自尊大简直是拙劣的虚张声势,而亨利则全是个笨手笨脚的毛小子”(58)。就连康普生先生也不得不承认邦更像“一个年轻的罗马执政官在做一次他那时代时兴的‘壮游’,到自己祖父征服的野蛮人游牧部落中去”(74)。福克纳不惜大量笔墨详细地描述了邦所具有的“高贵性”:从日常的言谈举止到在内战中的英勇表现都堪称为南方社会的上等人或社会精英。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邦的身世无人知晓的前提之下,邦周围的人对他的印象和看法都是出于个人的想象和感受而已,没有任何外界赋予的附加条件。康普生先生对邦的身世产生过怀疑,但他仍然告诉儿子昆丁:
而你爷爷也不清楚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告诉孩子他是,必定是,一个黑人,他还不可能听说过也不可能明白‘黑鬼’这个词儿,他甚至在他掌握的那种语言里都找不到相应的说法,他出生与长大……不具有更高的精神价值。(161)
康普生先生的观点反映了包括福克纳在内的绝大多数南方人的思想,表明了种族意识是在人们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影响下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在运用其政治权力并使其发挥它所期望的政治作用的过程中,在通常的情况下,都要求它的个体在政治上必须与其领导集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意志和行为在政治上必须是高度统一的。同样,如果人们不去强调种族之间的差异,种族意识就不复存在。康普生先生的父亲康普生将军也是这样认为,他送给邦一些钱,告诉他要马上离开密西西比,因为“且不说你是什么人,只要你置身在陌生人中间,在不认得你的人中间,你就可以想当什么人就当什么人了”(165)。
康普生将军的观点也是对南方种族思想绝对性的挑战,反映了在很多富裕的白人贵族身上南方种族意识并没有决定他们的行为。他们没有把带有黑人血统的邦当作一个奴隶,也并没有像塞德潘父子那样禁止他进入塞德潘百英里庄园。康普生将军告诉邦,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像其父塞德潘本人那样保持自己白人的身份。邦并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继续要求得到塞德潘的认可,并试图通过获得平等的权力来得到朱迪思的爱情,但他最终因势单力薄,缺少了像其父那样足以震撼和动摇南方上层社会的实力,因而注定会失败的。
“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⑤福克纳在塑造邦个性方面可谓是费尽心机,他让邦成为了南方道德的典范,承载了其挑战南方种族偏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种族冲突。与泰德沃特的贵族不同,邦不是只知道躺在吊床上或骑马到处闲逛,而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赢得了周围人的尊敬和爱戴,并在战争中因作战勇敢被擢升为指挥官。他的言谈举止深深地打动了朱迪思,即使知道他带有黑人血统,她仍然一如既往地照顾其黑人儿子。与塞德潘不同的是,邦所获得的一切荣耀和地位都与其财产无关,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修养取得的。虽然后来知道亨利很有可能杀死自己,但他还是拒绝了来自新奥尔良律师的帮助,并在去塞德潘百英亩庄园的路上,把自己带有十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妻子的照片放在自己口袋里,目的是为了在自己死后不会引起朱迪思难过。通过对邦正面的描述,读者很容易意识到福克纳实际上是把塞德潘和邦进行对比,因为作为穷苦白人的塞德潘在得到康普生将军等人的认可后“飞黄腾达”,而作为富裕“白人”的邦在遭到塞德潘的拒绝后走向死亡。
塞德潘拒绝接纳邦为自己的儿子,因为在他看来,血缘上的认可实质上推翻了他本人建造百英亩庄园的目的,他会不顾一切地保护这种排斥黑人权利才能获得的种族特权,因而不可能把带有黑人血统的邦看成其王朝的继承人。这是塞德潘王朝崩溃的致命成因。福克纳在小说中多处设想过:如果邦能得到塞德潘认可的话,那么美国南方就成为了一个和谐、祥和的典型区域了。然而,邦最终没有在福克纳善意安排的南方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他的死表明了他对南方种族意识的彻底叛逆,也体现了福克纳对南方传统思想的沉思。南方社会的秩序,如很多人引以为自豪的白人家长制,都是建立在野蛮法则的基础之上,许多下层白人和黑人都没有资格进入到上层社会,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和能力,而是在于他们肤色的不同。为确保南方上层白人的特权而牺牲黑人的权利,这是南方的历史罪恶,也是南方社会的毒瘤,只有根除了种族主义思想,南方的未来才能充满阳光。
伟大的作品很难将其归结为某种统一的意义。它们既是各种欲望的综合,又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的记录,因此,叙事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并不是清晰可见,常常被无情地驱入深层,最终变成政治无意识。福克纳凭借自己的想象把读者带到一个大多数密西西比居民看似陌生,但又确实参与其中的故事。这一故事清楚地反映了南方种族意识的孕育和发展,即南方白人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无意识积淀的过程——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南方上层白人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剥夺黑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人为地为穷苦白人提供了某些种族特权。这种把穷苦白人与统治阶级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加剧了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无论是黑人,还是穷苦白人都会像《押沙龙,押沙龙!》中穷苦白人沃许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镰刀砍死塞德潘,推翻上层白人的统治,建立种族平等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福克纳借助南方种族政治无意识化的过程,展现了自己作为20世纪作家的胸怀和先见之明,为南方民族融合指明了发展方向。
注释:
①④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9,72,67页。
②William Faulkner,Absalom,Absalo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86)。凡本文中只标页码处,均出自该书;文中的翻译部分,引用或参考了李文俊先生翻译的《押沙龙,押沙龙!》,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③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后记,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4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