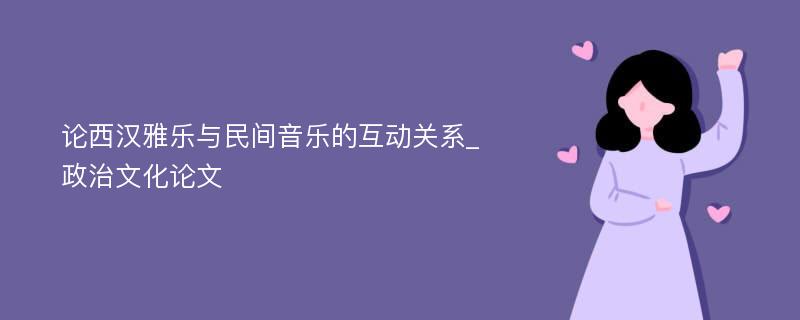
论西汉雅乐与俗乐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乐论文,互动关系论文,西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衷与职能
关于乐府署的设立,《汉书·礼乐志》云: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童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泰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又《汉书·艺文志》云: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武帝当初设立乐府的目的是为了现实郊祀的需要:“民间祀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1 〕乐府本身的职能即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而展开的,采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为中央政府服务。《汉书》上说的“赵代秦楚”只是大致说法,实际的情形是,乐府采集范围远远超过这些地区。从班固的叙述来看,当时对于这个举动的理论解释是“观风俗,知薄厚”。这个解释很明显是把乐府和古代的采诗制相比较,所谓“观风俗,知薄厚”即是源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见解。班固的看法暗含着一种历史的对比:由于采诗观风被当做是一种了解民风民俗民情的有效途径,是政治清明的表现,武帝设立乐府署很显然也是一种清明的政治举措。
但过去面向民间的采风运动,在武帝时变成了乐府的生产活动,包括引进异域新曲,令诗赋家、乐家作辞曲及增设乐府员工等等。如果按照上述班固的理论,这种大规模的活动正好与大一统政治的壮大声威相一致,应该得到更大规模的继续。不过,从乐府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却是另一种相反的结局,这是发生在西汉末的哀帝时代。《汉书·礼乐志》云:
是时,郑声尤盛。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然百九渐渍日义,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这段话点出了俗乐发展的迅猛势头,在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所奏的罢乐府名单中,总共829人的乐府员工,可罢免441人,超过半数。说明俗乐发展经过武帝时的推波助澜,其流传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压倒雅乐。所以,《汉书·礼乐志》云:“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同时,我们也可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到关于乐府理论上的矛盾说法,为什么民间的俗乐既可以被当做是“观风俗,知薄厚”的良好教材,却又是“淫僻之化流”的渊源所在呢?在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与害教化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度”?换言之,为什么“观风俗,知薄厚”的乐府活动会发展到现在的“浊源求清流”的荒唐结局?为什么可以补察时政的采风运动在他们眼里却成了解构政权的一种手段呢?
雅俗的混合
按照原始儒学和西汉经学的理解,雅乐和俗乐是截然分开的,该用雅乐的地方,是绝对不能使用俗乐的;该用俗乐的地方,也禁止使用雅乐。显然,这话是在俗乐产生以及得到相当发展的情形下说的。如果按照原始儒学的观点,严格地讲,俗乐是根本不应该产生的,它的产生就是大逆不道的事。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2 〕就是把俗乐——郑声放在颠覆国家的大原则上说的。
但在西汉,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虽然当时掌管雅乐俗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机构,太常掌管雅乐,乐府掌管俗乐。可是我们发现,西汉的雅乐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汉书·礼乐志》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太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因此,雅乐的掌管已经失去了意义的阐释能力。汉初,叔孙通“因秦乐入制宗庙乐”〔3〕,就说明他是在改制雅乐, 原始的雅乐已经面目全非。从高祖到景帝时用的“武德、文始、五行、昭德、四时、盛德”虽然也算雅乐,仅仅是由于在重要的典礼场合,用雅乐是最根本的要求。但这些雅乐,都是自制的雅乐。
这种情形会使得人们抱这样的怀疑态度,西汉自制的雅乐果真是真正的雅乐吗?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像郊祀宗庙乐本属于雅乐范围,其中必须包含祭祀祖考这样的内容,但我们却看到武帝因得大宛宝马而作《天马歌》,大臣汲黯对此大不以为然地说:“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耶?”〔4〕
这只是从内容上说的,在曲调上,关于雅乐的纯粹说法也值得推敲,西汉的祭祀《十九章》之歌也是以俗乐的乐律加以改制而成,当时作《十九章》之歌的代表人物是李延年,而李氏恰恰是时新曲调的代表。“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5〕又比如, 关于《安世房中歌》的制作,《汉书·礼乐志》云:“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这种情形表明,经学上认为的雅乐与俗乐之间绝对分立的界线并非不可逾越。像祭祀宗庙这样庄重的场合都可以用俗乐的话,其他的娱情享乐的场合更可以使用俗乐了。因此,到了西汉,雅俗混合可以说是音乐界的一大特色。
这种混合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俗乐对于雅乐的渗透作用,我们看到,尽管理论上强调重雅乐轻俗乐,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不能贯彻这个原则。因此,我们在汉人的评价中看到对这个现象的批判: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也,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汉书·礼乐志》)
雅俗的混合让我们看到现实中不得已的苦衷。明明是为了现实制乐的需要而设立乐府来更好地采集民间俗乐,却又要在古代的传统中寻找理论的依据。从汉初几十年的文化建设这一现实来看,对于文化传统的继承由于政治动荡的缘故而无法提到议事日程〔6〕, 也只有在武帝之后,这些措施才由于国力的加强与政治的一统而得以实施。不过,可供统治阶层选择作为范本的文化传统只能在先秦的理想政治中去寻找,这在武帝的天人三问策中表现得极其明显。汉初那些有远见的政论家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都把先秦三代特别是周代的德治传统作为参照。所以有关文化的建设问题,他们的许多措施都是仿效周代的,如封禅、立太学、设乐府等等。可是乐府的设立可能和别的文化措施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先秦的雅乐到汉初已经消失,唯一的办法只能根据时乐加以改造,而这点又与雅乐的理论相违背。
乐府的设立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通过它和民间通俗文化的关系而看到古代王政清明的“采风”运动的影子,另一方面,又以经典乐教理论重视雅乐轻视俗乐的态度来批评乐府采集俗乐而造成的对雅乐的冲击与破坏。所以在班固的评论中,即有“观风俗,知薄厚”的赞扬,又有“淫僻之化流”的批评。
这种矛盾表明,新的文化建设虽然有恢复古代理想传统的原望,但时移世更,这种愿望显然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新的文化建设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满足当下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李延年“承意弦歌”,所谓“承意”,即承武帝之意,由此,为当朝统治服务的色彩是极浓厚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如何能够与古代“观风俗,知薄厚”的采风运动相比呢?正是由于这点,我们看到,要在乐府署的设立以及乐府署的乐歌创作中看到古代传统的实现是何等艰难。
乐教的失败
传统儒家对于乐教的重视是极为明显的,在孔子之时,音乐界就出现了“诸侯僭越,新声流行,雅乐衰败”〔7〕的情形, 这和孔子的儒道思想是相矛盾的,所以在《论语》中有许多批评性的话语,并且进行“正乐”的实际工作。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8〕因此,乐教是致王道的一项重要内容,《礼记·乐记》云: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9〕
以汉代的情形而言,由于雅俗的混合使得乐教理论在实际中处于尴尬的地位。既然汉代的雅乐已经参杂着俗乐,那么,用于乐教的范本也就不是“治世之音”。更为甚者,虽然正统观念对乐府的普遍看法是,俗乐的发展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可是实际上,俗乐还是依然我行我素地向前行进,到了最后,宫廷中到处都是郑声流行。按照经学的逻辑,这些俗乐都应该废止,而我们却看到“湛沔自若”的真实描绘。并且,统治者本身也对这种情形持默许态度:
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馈铜丸以谪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10〕
史丹虽然以委婉讽谏的方式进行劝说,但他和元帝的心里都很明白,要以乐歌代表陈惠和李微来代替经学大师匡衡为相国是不可能的。可另一种情形也很清楚,废黜陈李二人也是不可能的。《本纪》载“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元帝自小受儒学教育,不会不知儒学的道德主义精髓,也不可能不知道在雅乐和俗乐之间的取舍。但实际的情形表现得恰恰相反。面对这样的情形,如何能够实行乐教功能呢?
乐教的失败让我们看到经学理论的失败,看到经学道德主义的失败。在西汉末期,面对外戚宦官专权以及土地兼并等一系列影响政权巩固的社会政治问题,经学已经显示出捉襟见肘的窘态,经学家及士大夫们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固然尖锐,而实质上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史丹作为太子师傅,在太子登基后,他的主张(限民田)也由于外戚的反对而归于失败,经学的致用思想到了此时显然宣告破产。同时,经学内部也经历了重大的分化,不仅今文经学在走向烦琐的章句之学,而且,古文经学的兴起让许多经学家原来的学术体系以及价值判断标准遭到严峻的挑战。所有这些都表明经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一百年前经学初立博士时英姿勃勃的情形相比,此时的经学正显示着江河日下的颓势。经学家们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和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不得不考虑自己及所属文化的出路问题。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西汉末经学的努力是如何趋于失败的,实际的情形是,外戚一以贯之地在专权,王权旁落,王政中衰已成不争事实。特别是经学内部,有些人“能够利用他们的儒家学说的知识来为其卑劣的行为作动听的辩护。”〔11〕在王莽时期,经学成了篡权夺位的护身符。而此时正是经学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情形与经学本身的二元对立倾向有密切关系。由于它关心的是此在世界的事,可是作为判断标准的却是内在道德律,二者之间本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只能由政治经济方面的基础去解决,而不能靠道德基础来解决。在《盐铁论》中,我们看到贤良文学反对大夫们的观点竟然和现实情形相差的那样遥远——他们持之为据的几乎都是古代的例子,以致于发展到西汉末,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汉末的儒学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经学大师们比以前更多,道德主义的观念被更多的人接受下来,可是,社会渐渐不安,统治政权日趋一日地动摇起来。这种情形并没有给那些经学大师乃至王权统治者作一面反思的镜子,并没有检讨长期以来对于儒学的信念是否正确——道德主义真的是统治政权的有效手段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西汉末经学高举重雅乐、轻俗乐的旗帜来反对世风的衰败固然不错,然而,并没有深入地审察俗乐本身所包含的与雅乐的共通的思想内涵,这正是经学作为道德文化必然有的优越感及缺乏反省精神所致。我们将在下面看到,那些俗乐对于世风的批判与经学思想强调的理性精神并无二致。但这种特点在西汉经学的观念里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看待,人们总是把俗乐归类到败坏风俗,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角度上而心存蔑视。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俗乐对于雅乐也是一种适时的补充,不仅在于曲调上能够为当朝统治提供服务,而且在精神上也与经学的许多观念保持一致。因此,当西汉的乐教理论以及经学思想把立足点定在雅乐上而忽视俗乐的作用时,这个立足点以及缺乏自身反省精神的特点也恰恰是我们批评的出发点。
俗乐的审视
因此,我们对于俗乐的审视不是从经学的眼光来看,因为这样将导致对俗乐精神的忽视,也不是取相反的另一极端,认为俗乐和雅乐是背道而驰的,而应当从它本身的特点出发来加以考察——这个本身的特点是如何一步步地证明俗乐为整个西汉社会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食粮。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理解俗乐的文化精神。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民间的乐府诗歌里,经学文化的二元对立是如何得以克服的。在西汉的民间乐府诗中,显示出既与宫廷文化毫无瓜葛,也与学院传统相距甚远的特点。它们是下层平民百姓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之总结,它们用自己的语言及想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及理想,以粗糙的、直率的尖锐笔法来描写现实,表现下层人民的艰辛。他们的情感是真诚的,态度是明朗的,他们对历史很少作深邃的反思: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疆,苏合弹,左手提疆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乌生八九子》
此诗极言人生寿命定数,以南山岩石之乌,摩天高飞之黄鹄及沉落深渊之鲤鱼为喻,说明生命终究不以各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无论怎样聪明和狡猾,也难逃定数。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安之若素的生活态度。如果一定要给这首诗寻找古代的思想渊源,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道家思想,对于熟读老庄学说的读者来说,“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正是“不以死死生,不以生生死”的绝好注解,但这种看法并不能说明民间乐府的诗歌精神特质以及和经学文化的背逆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生活态度对于经学的道德和理性来说无疑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也正是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才被揭示出来,不仅民间平民百姓对待生命采取如此从容的态度,而且,在经师士大夫身上也能看到这种情形。他们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经常会在作品中表达出另外一种心情,这种心情与《乌生八九子》表达的是那样相似,以致于我们在看惯了他们充满理性及道德意味的论说之后,竟然发现他们思想心灵的另一面还有一股内在的情感潮流在激荡。
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民间乐府文化还隐含着经学文化所缺乏的生活整体论观念。这种整体论的观念除了接受伦理道德可以导致善的结局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把人们的生活方式统一为一个整体,这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本身既包含了对感性生活的重视,也包含着伦理道德的理性观念。我们除了看到《江南》这样的诗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民间诗歌,它所隐含的批判精神和道德观念与经学文化一直强调的竟然那样相似,以致于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正是这些平民百姓对于生活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比起那些地位更高,更具有文化修养的人们来得更为彻底全面:
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天下为卫子夫歌》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
——《长安慰为王氏王侯歌》
上述二则歌谣系针对外戚而发,在现象的描述背后实际上暗含褒贬精神,这种褒贬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对外戚奢侈或专权的批判。它与经学思想的批判性是一致的,在《史记》和《汉书》中,我们看到许多引用民间歌谣的例子。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下层百姓用自己朴素、粗糙的语言表达出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经学文化来得逊色,从而成为他们写作的极好素材。
这些特点正是经学文化对待民间文化时经常忽略的,也是民间文化常盛不衰的生命力源泉。因此,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乐府署吸收民间歌谣乐曲来制乐时,除了为现实的需要外(如制订宗庙乐、祀乐等),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民间歌谣的思想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思想不仅来自民间百姓,而且也代表了统治阶层那些更具修养的人们的许多观念。因而,当西汉末哀帝罢乐府时,“豪富吏民,湛沔自若”的情形恐怕就不能单凭道德的普遍沦落就能解释清楚的了。更为合理的说法应当是,当西汉的社会政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经学无济于事的时候,人们此时反而在民间的通俗文化中找到生活的另一种态度。
我们可以杨恽的《拊缶歌》为例,这是西汉为数不多的以民间歌谣形式表达自己政治失意的代表作品: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与上述的“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在情感逻辑上有相通之处,讲的都是对待生活的一种不必强求的态度。《汉书》本传说杨恽,因政治上的缘故被黜归家达三年之久,其友人孙会宗劝其修身养德,不可自甘放纵,恽不听,以此歌作答,等等。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出经学所不能包容的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可以诗歌创作来代替政治上的自劾行为或者说道德的自我修善,另一种做法更为极端,在诗歌作品里表达个人的内在情感需要,而不必以道德为指归。这种情形在西汉经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像韦玄成的《自劾诗》那样的例子。因此,杨恽的诗歌事件为我们提供了看待民间乐府诗歌的另一个角度。毕竟,在魏晋以及后来,这种例子就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特征的隐逸观念的产物。
这就是从杨恽的事例中得到的启示,民间文化是经常被精英文化所蔑视的。艾略特在谈到这点时不无感慨地说:“在有些我们蔑视为原始落后的社会中,社会—宗教—艺术的复合结构却起着作用,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在更高的水准上力求达到的。”〔12〕西汉的乐府制作让我们看到民间文化的可贵力量。他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以及隐含的褒贬精神都使得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迈进。它的反作用力是不能低估的——每当经学文化陷入困顿的时候,与之相对的民间通俗文化在保持社会不再萎顿,人民生活不再疲乏方面所做的努力。它所包含的社会—艺术—道德的复合结构使得生活总是具有崭新的意义。这应是我们在注重西汉经学文化影响力时要经常提醒自己不该忘记的。
注释:
〔1〕《汉书·郊祀志》
〔2〕《论语·阳货》
〔3〕《汉书·礼乐志》
〔4〕《史记·乐书》
〔5〕《汉书·佞幸传》
〔6〕班固《两都赋·序》云:“大汉初定,日不暇给, 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7〕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见《古史辨》第三册。
〔8〕《论语·子罕》
〔9〕又见《毛诗序》
〔10〕《汉书·史丹传》
〔11〕《剑桥中国秦汉史》,第831页。
〔12〕见《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