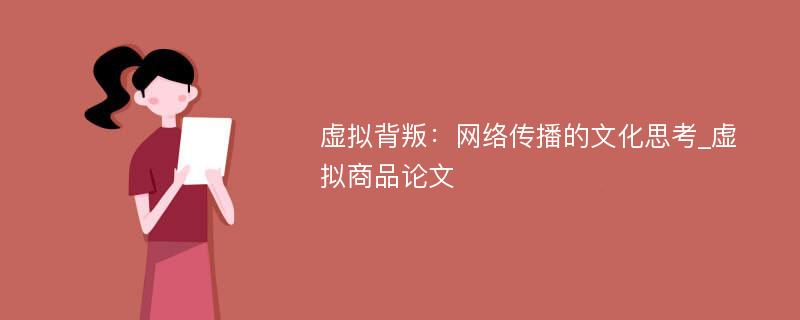
虚拟的背叛:网络传播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络传播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1)04-0108-06
从计算机网络研究的现状来看,大致有两种研究视角和价值趋向:一种认为,计算机网络是纯粹的信息技术现象,因而计算机网络研究应该从纯粹技术论的角度与特定领域加以进行。这其中的亲技术派对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欢欣鼓舞,认为计算机技术为解决当前和未来的一切问题提供了答案。而恐技术派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认为技术是危险的,计算机网络对人类社会生态的破坏与其科技的尖端发展成比例。另一种则认为,计算机网络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现象,它还有许多非技术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甚至构成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特征,因此不能从纯粹的技术论观点与角度来研究计算机网络。
美国休斯敦大学的C·怀特和T·沃尔克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技术现实主义”立场,认为“正由于技术是无生命的,因此难免带有偏向性。伴随着对它有意识的利用,会出现许多无意造成的后果。包括技术在内的每一种工具都会改变它的使用者。而随着使用者个人的改变,他们所属的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认为,“技术现实主义”的社会研究观点应该遵循技术和社会研究一体化的原则,对技术进行有意义的批评分析(注:White,Cameron and Walker,Trenia,Technorealism:Addressing the Issues of Technology in Social Studies,http//www.cssjournal.com/journal/cwhite99.html.)。
加拿大社会学家麦克卢汉在1964年的《理解传媒》一书中,对传媒在全球的快速传播所带来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这种传播形成了全球的普遍的经验和普遍的意识,加快了“地球村”的到来。80年代以后,当代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的大众传播理论更把传媒看作是促成后现代性和后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在他看来,当代传媒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
本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谈谈计算机网络作为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它的虚拟空间所带来的文化形态的变迁及其影响。
一
我们知道,从最早的冷战机器逐渐演变为快捷演算工具,进而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的传播媒体,计算机网络在今天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发展的高潮阶段。人们已经发现计算机网络是分享数据、组织专业讨论、与同行保持联系和散发文献资料的一种交流工具和传播媒体。因此,人们在享受计算机网络传播带来的先进、方便、快捷的同时,当然更愿意相信:计算机网络为人类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更是由于其新的传播媒体而带来了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
实际上,任何新技术的产生、传播和利用都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社会文化环境不仅提供了人们选择某项技术的标准与方式,而且随着这种技术制度化及其秩序体系化的形成,还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生活空间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正像德国技术哲学家F·拉普所谈的:“实际上,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注:(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因此,尽管计算机网络最初表现为一种技术现象,但这种技术现象本身并不脱离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整体系统之间的互动与关联。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因而也就必然地进入社会、文化的分析批判的范围中。这也正符合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研制者阿瑟·W·伯克斯所认为的:“现在的计算机已经连接成为网络,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网络。计算机通讯构成了我所说的复杂的自主系统的一部分。这就构成了人类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的基本形式。这也是一种支配我们社会方式的新的文化。”(注:转引《计算机革命四十年——阿瑟·W·伯克斯访问记》,《世界科学》1995年第8期,第7页。)
加拿大科幻小说家W·吉布森在1984年出版的小说《精神漫游者》中使用CYBERSPACE一词概括了计算机网络空间,有人译为“赛伯空间”或“赛博空间”等。与吉布森在其他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让漫游者感到痛苦而绝望的技术文化空间不同,计算机网络空间给漫游者以虚拟的自由王国。在这一空间中的人类行动,无论是电子邮件、网络讨论、文件传输、远程登录和万维网浏览等,还是以其为基础的更为发展的网络传播行动形式,都不具有现实物理空间中社会行动的可感触性和客观实在性,也不同于现实行动的时空位置与物理形态。用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的话说,计算机网络空间是由比特构成的,比特与原子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电子文化批评家南帆更是把它扩展为概括性的话说:“网上的生存是一种没有重量的生存。”(注:南帆《没有重量的空间》,《电影艺术》2000年第4期,第70页。)可以说,计算机网络空间为人类提供了虚拟的、独立存在于现实空间之外的另一空间,没有地域距离的行动场所。这是一个新型的行动空间和一个新型的行动方式,因此这是一场相当彻底的革命。
从技术层面上看,计算机网络空间是作为一种以计算机技术、通信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网络化、虚拟化的多维信息空间。计算机网络世界中的虚拟空间,是一种符号化的图像和信息存储库。在这样的行动空间,符号化的虚拟图像与历史上的图像创作——比如照相机、录像机、摄像机都是靠真实的现实的光线与感光底片的相互作用来工作的——全然不同,它第一次不是借助于光线,而是用抽象的数学语言的形式来创作,有人比喻说是“用思想的光线”(注:《技术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第1版,第97页。)。以往的图像只是展示一个真实或抽象的原型的窗口,它可以说只是形象的再现,本质上是二维的。但这种虚拟的图像由于构成图像的语言特点,图像与原型总在相互作用,而且,虚拟图像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空间、一个场所,人们可以在里面探险与相遇。同时,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所熟悉的信息接受、处理、传播方式和信息本身的生产和存储方式都将以数字化形式出现,它是建立于以光速运动的比特及其特殊的数字化的信息的生产、存储、传播、交换和控制之上,并通过这一系列的数字化的过程而反映出来。在形式上,计算机网络空间是虚拟的。
然而,每一个网络的用户坐在计算机前,通过击键也能够在其他人的“意识”中漫游。他们的意识进入了电脑空间的一个“真实”的地方。所以,从功能效应上看,它又是真实的,是一种人际思想与情感交流的领域,只是它是与现实真实世界不同的交流方式。在计算机网络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信息能够以光速在网络上进行传输,从而极大延伸了人们网络活动的空间。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康德意义上的空间——是人们经历的先天条件:没有空间就不可能有在其中的经历。可是,虚拟空间不同,它不是经历的条件,它本身就是经历。虚拟空间可以随着人们对它的探索而产生。正如有人说的“虚拟图像的世界比我们的视线广阔……”(注:《技术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第1版,第98页。)。虚拟空间不是真实的,是摸不着的,但又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能包容我们与其他人意识的产物,并能同时被多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分享。
在这虚拟的计算机网络空间,一个行动者与其他人的交往主要通过数字化文本,通过文本传播信息、描述心情与交流感情。与人类的具有实体性与可感知性的一般性社会行动不同,计算机网络传播行动只存在于以数字化的形式而存在的信息或比特的结构之中。尽管对日常交往中物理空间可察觉的感受的缺乏可通过文本式的模仿,但文本的感受毕竟是有限的,况且这种“模仿”本身也是数字化的(注:如在网络上,人们常用“:-)”来表示玩笑和幽默,用“:-Q”表示抽烟。)。在这种数字化世界的环境之中,人们的特殊的社会行动即网络传播行动也就成为了一种虚拟的行动。正如有人说的,当信息形态由模拟化转变为数字化,具体事物便可能成为虚拟的。
说到计算机网络传播的新型文化空间,比尔·盖茨把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比喻为一条不断延伸的“未来之路”,尼葛洛庞帝用“数字化生存”来展示网络化社会丰富多彩的新界面,艾瑟·戴森甚至直接为人们编程出版可无限升级的“数字化时代的社会设计原则”。事实上,这种以网络为技术和文化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网络空间已经引发着一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只要上网漫游,人们便会立刻察觉到这场变革真的随着鼠标的点击、沿着电话线汹涌而来。美国作家凯蒂·哈弗纳和马修·利昂曾经用文学的语言比喻网络虚拟行动的迷人和浪漫:网络的浪漫,不仅在于如何创建、如何运作,还来自于它的如何被使用。“就像美国高速公路系统一样,它的浪漫不是由第一个推算出如何给公路定级或者马路中间弄上黑顶或涂上线条的人创造的,而是第一个像詹姆斯·迪恩那样,沿着第66号国道,开一辆敞篷旅游车,放大自己收音机的音量,去享受一段好时光的人创造的”(注:(美)凯蒂·哈芙纳、马修·利昂:《术士们熬夜的地方——互联网传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美国传播学者J·M·凯利从媒体与文化关系的角度认为,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递,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到人们所构造和维持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之中。因此,在他看来,传播活动旨在定义人们活动的空间和人们在这一空间扮演的角色,从而确立社会的关系和秩序,确认与他人共享的观念和信息。研究人的传播活动就是研究文化(注:转引自石义彬、单波:《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5页。)。
从这种传播理论的逻辑上看,我们研究计算机网络传播活动,应该更要注意于文化意义和社会话语的诠释,研究计算机网络传播活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维度等与作为传播载体的计算机网络的发明和应用的关系。因此,围绕计算机网络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探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开启全面研究网络和网络化的新“界面”,从而真正理解计算机网络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意义与矛盾所在。
二
作为信息交流的传播媒介,计算机网络传播技术所带来的人类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与以往传播媒介发展史上的任何一次新的传播媒介的诞生都更具革命性。
H·A·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可分为以时间为重点的媒介和以空间为重点的媒介,由此规定社会流通知识的数量、性质以及社会的形态。在H·A·英尼斯看来,文字记载在石头、黏土、羊皮纸上的时间媒介,虽有耐久性,但不适用搬运;而纸草、纸的空间媒介轻便,能搬运。古代帝国,无论东西方,都依存在这一轻便、易携的空间媒介中。“时间的媒介制造出地方割据的等级制社会组织,空间的媒介造成中央集权的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注:(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第30页。),而新的电通讯技术于19世纪出现后,对于传播空间的扩大堪称革命性的科技开发,“各种媒介文化同各种社会形态也是对应的——口头文化象征着部族社会,活字文化所代表的是作为同质化个人的集合体的近代社会,电视文化则产生出将地球全体居民连接起来的大部族社会。”(注:(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第30页。)如果我们同意H·A·英尼斯把媒介发展与社会生存空间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那么,今天的计算机网络虚拟化空间带给我们便是一个自由的、虚拟的计算机“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们可以聚集在虚拟空间中做游戏、工作、恋爱、贸易甚至战争,整个地球都是虚拟空间,地图变得同大地一样真切,只是这张地图不是真实的而是虚拟的。个人计算机使用者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进行实时连接,在文本的王国里探索。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几何空间被计算机空间代替,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更加复杂而又丰富的世界。从传播技术发展史上看,无论文字印刷、影视广播,还是其他的传播手段都是一种与现实关系的生产与表达,它们作为人类的媒介系统都是局限于传统语言学理论体系的语言符号指称意义对象的关系之中。语言符号是以往传播媒介的中介系统的标志,它是内容的表现,是对现实的再现,是第二位的。这种传统语言学的理论窄槽显然无法容纳计算机技术传播环境下的语言功能的变化。当然,语言是有意识的行为的工具,但是,语言的更为关键的作用在于对语言主体的构建。美国的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时代》考察了新的传播技术诸如计算机网络、虚拟现实等等电子媒介的新发展,并提出新的“信息方式”改变了我们的交流习惯与传播方式,进而对我们的身份进行深层的重新定位。“电子的介入使得语言的传播复杂化,并颠覆了总想把语言的作用限制为一种简单的表达媒介的语言主体。”(注:(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第一版,第18页。)传统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倾向都是以现实性世界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应该说,随着计算机数字化方式为人类提供的虚拟空间的发展,“虚拟”这样一个在传统哲学观念上与“实在”、“现实”相对应的人类行动的范畴或维度真实地呈现出来,也使我们对虚拟文化及其形态有了一个判断与认识的机会。
虚拟空间通过数字化方式的存在,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哲学必须面对和思考的课题——它“否定了我们的一切从现实性出发的传统思维方式。换言之,虚拟开拓了人的思维空间,使现实性或现实本身变成了小概念”,“虚拟展开了其他未被选择的可能性,并在虚拟中使其成为虚拟空间的真实,这便大大开拓了人的选择空间”,因此,“虚拟本身以及虚拟如何进行,虚拟将导致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生命方式的何种革命,这是哲学必须进行研究和回答的;同时,虚拟将形成人类的各种关系的变革。这一变革的特点以及与传统的关系,它将导致人类走向何方?总之,由于虚拟的真实性,我们将面对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生存革命和哲学革命”(注:陈志良:《虚拟:哲学必须面对的课题》,《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第39页。)。
荷兰当代哲学家C.A.冯·皮尔森在谈到今天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的变化时认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关于文化战略的变迁,他的《文化战略》给出了新的三段论的简化模式:1.神话的(原始的)阶段,以“那个”(that)为特征,即以对存在本身的敬畏为特征;2.本体论的(科学和技术的)阶段以“什么”(what)为特征,即以研究某物是什么为特征;3.功能的(系统-信息的)阶段以“怎样”(how)为特征,即以研究人同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为特征。他认为,在神话阶段人同宇宙是统一的,或者说人的世界同神的世界是互渗的;在本体论阶段人同周围世界拉开了距离,有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有了透视和个人精神的分离的领域;到功能阶段人消融在发挥功能的关系网络中了(注:(荷兰)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对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持有的一种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因此,当代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计算机网络带来了这样一种行动和思维方式,它的焦点可以说既不在于人与其环境的分离,也不在于那种直接被环境完全控制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构成关联的思维,它的中心特点不是参与和距离,而是关系。当我们点击鼠标,漫游网络虚拟空间时,毫无疑问,传统的人类知识发展图式显然不能理解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这种“关联的思维”了。虚拟空间的文化形态显然也不是本体论阶段的知识图式所能整合的。一种并不以对客观实在性的参与或与其距离作为关注点、而是通过数字化语言的关系构成的文化,已经在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存在。
1936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曾经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表示了巨大的震惊,在他看来,机械复制废除了作品的“原真性”,不再是具有神圣的宗教式的礼仪意义,作品脱离了时间空间的独一无二性之后成为复制品,作品的展示价值超过了膜拜价值。尽管如此,本雅明显然无法对其后的计算机网络空间的虚拟的社会文化形态做出更多的阐释。这可能如麦克卢汉所说的:“我们从拼音文字技术演变而来的知识,不能对付这一新的知识观念”(注:麦克卢汉:《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制。在许多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制和整个社会权力机制都是以语言机制、文化机制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现实”,它的存在也是个人与世界的想象关系的一种,从这一意义上说,在网络社会中,虚拟的活动同样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然而,正如上文所说的,计算机网络与以往传播媒体不同,它与社会生活现实的关系不是一种反映或表述的关系。用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的话说是一种“拟仿”(simulation)。生产或表达、反映或表述的问题,涉及到形象与符号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但“拟仿”完全不同,它“不与任何实在产生关系,它就是它自身的纯粹拟像(simulacrum)”(注:J·鲍德里亚:《拟仿》,纽约,1983年版,转引自《商品拜物教之镜》(王昶译)。)。拟像,是没有原作、没有真迹的“超真实”(hyperreal),它来自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生产和消费,即所谓数字化、完全信息化时代。在这一“超真实”的时代,对本质与表象理论化探询不再有意义。在这个世界,一个不存在现实被召唤出来,“不再有主体、焦点、中心或边缘;只有纯粹的弯曲或循环变化。不再有暴力或监管;只有‘信息’,秘密的恶意,连锁反应,缓慢的内爆(implosion),空间的拟像,在那些空间中真实效果变成了嬉戏。”(注:J·鲍德里亚:《拟仿》,纽约,1983年版,转引自《商品拜物教之镜》(王昶译)。)因此,意识形态批评(ldeoloqiekritik)不再适应,因为“意识形态对应的是用符号来背叛实在;而拟仿对应的是实在的短路和用符号来重复自身”(注:J·鲍德里亚:《拟仿》,纽约,1983年版,转引自《商品拜物教之镜》(王昶译)。)。
在研究当代社会文化形态与转型问题时,让·鲍德里亚提出了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命题。这一社会转型,意味着从物的消费这一经济行为转向了物的形象的消费这一文化行为。“消费”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根本特征,人们通过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来确定自己,同时社会意义也由此产生,可以说,形象符号的生产、传播、消费已经成为控制和组织当代社会的一个基础。“社会关系的象征性毁坏并不主要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的,而是由对符码的控制来决定的。”(注:J·鲍德里亚:《拟仿》,纽约,1983年版,转引自《商品拜物教之镜》(王昶译)。)所谓商品拜物教的最后阶段是将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形象,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正是揭示了这一问题。然而,对计算机网络虚拟图像的崇拜是否可以说是所谓拜物教的深化和当代转换呢?!
在谈到后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时,利奥塔曾经认为,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话语,大大改变了知识的地位和世界的图景。80年代以来,让·鲍德里亚从生物基因学、仿生学、全息理论、计算机模拟等当代最新高科技手段所造成的时代境况出发,提出的由“符码”、“拟像”、“超真实”、“内爆”等重要理论概念所构成的全新经验领域和社会类型,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典型的由“符码”与“超真实”、“拟像”与“类像”、传媒与信息共同构成的一个后现代社会。应该说,让·鲍德里亚以独特的视角透视了后现代主义社会以“虚拟”代替现实的境况,用他的话说是,在这样的人类境况中,虚拟的社会现实变成了一种“完美的罪行”(注:(法)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第一版。)。尽管90年代以来的网络虚拟空间对人类状况的强烈影响已大大超出了让·鲍德里亚的理论想象,但是,让·鲍德里亚对现代传媒的富有启发性和深入的分析,对我们认识计算机网络虚拟空间的传播文化命题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发。
数字虚拟化的时代,人类的网络化生存将彻底实现。一个虚拟的世界代替了真实世界,生存也变得更为简易,人们只要接上电源可以自由地在虚拟的空间中满足欲望、安然度过自己的“美丽的新世界”(注:(英)阿道斯·赫胥黎的小说《Brave New World》中描绘了在未来社会中,技术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在改变人类的基因与生理存在之前,科技已能改变人类的“人性”存在。)。
然而,当物转换为物的形象和符号,当我们的目光只是朝着等待我们去开启的虚拟图像的可能性大门,当人类逐渐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我们似乎应该保持一种必要的清醒。我们如何才能保证自己不会陷入美国学者普特南所说的“缸中之脑”的困境?——“一个人(可以假设是自己)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起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一台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输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对于他来说,似乎人、物体、太空还都存在,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都可以输入。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被截取记忆,截取掉大脑手术的记忆,然后输入他可能经历的各种环境、日常生活。他甚至可以被输入了代码‘感觉’到他自己正在这里阅读一段关于有趣而荒唐的假设的文字:一个人(可以假设是自己)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起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一台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输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注:转引自戴锦华的《文化研究面对后现代噩梦》。)
收稿日期:2001-0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