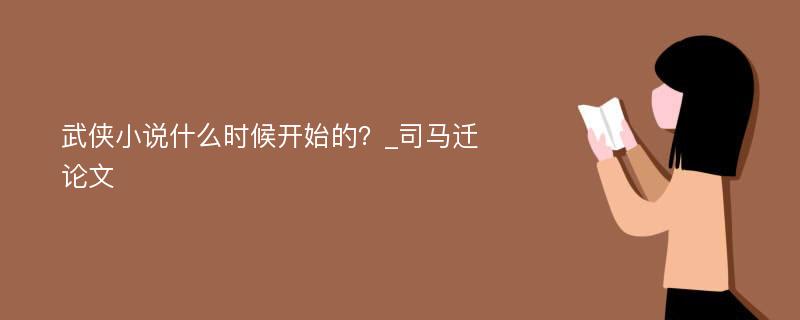
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端论文,武侠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4)03-053-011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目前,走近这道风景线观光的游人越来越多,神州大地刮起的一股“武侠小说热”,正方兴未艾,势头很猛。
汗牛充栋般的各种武侠小说集,正在日夜狂轰滥炸,挤兑着人们的眼球,数以万计的武侠电影、电视剧和它们的碟片、光盘等,正和“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一起,走进人们的业余生活;稚气未脱的“武侠迷”们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地摊和网吧中,经常乐而忘返;以武侠小说名家命名的武侠“茶馆”已经开张,“有限责任公司”也已挂牌西子湖畔,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的不在少数……。
这股“武侠小说热”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二十个年头。由于媒体、出版家和企业家的推波助澜,近来还看不出有走向衰落的迹象。相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它又高擎市场经济的大旗,正大步迈进在产业化的新征程中。
回顾武侠小说近二十年走过的学术之路,我们还是颇感欣慰的。尤其是对古代游侠和新派武侠小说名家(包括传记和作品)的研究,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也不可否认,从总体上说,我们对武侠小说的研究,还显得过于薄弱。特别是对一些读者甚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似乎还注意得很不够。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也即“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的学术命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武侠小说发端于何时?
中国武侠小说究竟发端于何时?对此问题的回答,目前的学界大约有四种观点。
(一)先秦说。
其首倡者是美国学者刘若愚先生,他在《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一书中说:“把历史上的游侠写进小说,最早大概要数《燕丹子》,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公元前三世纪的真品,由太子丹的门客编写。”持此观点的还有罗青先生。他认为《庄子·说剑》是“涉及武侠的长篇作品”,“最接近现代小说规模。”
(二)两汉说。
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王海林先生,他在《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一书中认为,汉代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事迹”和《吴越春秋》中的“越女试剑”(有人又把它定名为《老人化猿》)的故事,己足“可以视为武侠小说。”
(三)六朝说。
持此观点的是海外学者崔奉源先生。他在《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一书中说,中国小说“始于魏晋志怪”,而它们当中其实已有“很标准的侠义小说。”
(四)唐代说。
持此观点的是我国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他在《中国武侠小说总论》一书中说:“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
以上四种说法,皆转引自徐斯年的《侠的踪迹》一书。学者们各持己见,聚说纷纭,迄今尚未达成共识。其重要原因是缺乏对武侠小说作品判定标准的把握。我认为,明确这一点,是极有意义的。我们如果对武侠小说作品的标准还不明了,又如何能判定其发端呢?
我以为,要判定某篇作品是武侠小说,起码要符合以下四条基本标准。
(一)武。作品中要有兵器,尤其是早期的武侠小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人物行动的道具。离开了它,我们很难把它称为武侠小说,也不容易把它和其它样式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
(二)侠。作品中要有武侠人物。所谓武侠人物,是指小说中的人物应具有“扶弱抑强,见义勇为”等基本的侠义精神,他们属于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系士林的性情中人。
(三)小说。作品中要有故事、有情节,符合叙事文学的基本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历史著作相区别,在创造人物、描写环境和叙述故事发展时,应有某种程度的艺术虚构,不能完全照搬真实的历史。
(四)独立成篇。既然称为武侠小说,应是独立的文学作品。那些依附在历史著作中的,或者是诸子著作中作为作者说理而列举的比喻、寓言和人物故事等,是很难称得上是“武侠小说”的。
诚然,判定武侠小说是否成立的标准还有很多,但这四条,无疑是最基本的。离开了它,我们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学之海中就会迷航。
下面,我们试把学者们论述武侠小说发端的四种观点简单地剖析一下。
先说“先秦说”。
刘若愚先生提到的《燕丹子》小说,我们将会在后面作详细说明。此处暂不赘述。不过,说“这部小说是公元前三世纪的真品”,恐怕是猜测之辞。据笔者的意见,此小说大约撰成于东汉末年。作品旧题是燕太子丹撰,显然是作者的假托。翻检历史文献,其最早的著录见于《隋书·经籍志》:“燕丹子一卷”。而《汉书·艺文志》未录。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它在班固的时代尚未成书。东汉时,王充的《论衡·感虚篇》和应劭的《风俗通义·正失篇》都有太子丹受质于秦,后逃归燕国的怪诞记载,与今天我们所见的文本文字有较大不同,可见,此时这部小说尚未定形;而西晋之张华的《博物志》中的文字,除个别字句外,却与今本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小说《燕丹子》的写定,乃在魏晋以前,或者说是东汉末年。今存《燕丹子》三卷,乃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其内容与一卷本全同。刘若愚先生的“先秦说”,其主要的缺陷恐怕在于对《燕丹子》成书时代的误判。
至于罗青先生提及的《庄子·说剑》,看来要认定它是一篇武侠小说作品,存在着许多困难。
《说剑》的作者不是庄子,而是他的门人或是崇拜者。文中多次直呼其名曰“庄子”,就是例证。它成于何时,还应探究。
更重要的是,《说剑》不是一篇独立的文学作品,其体裁被作者冠以“杂篇”,而从具体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它和《庄子》中的其它作品一样,是一则说理文或曰论说文。叙写庄子受太子之命,前往赵王府劝说赵文王停止门人间的斗剑。庄子在执行劝剑的使命时,为了加强说服力,提到了“剑道”,并以剑作比喻,力图达到目的。所以,说《说剑》是一篇武侠小说,甚至认为它是“涉及武侠的长篇作品”等,显然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
不过,从武侠小说史的发展来看,《说剑》在说理作比的过程中留下的若干有关游侠之“剑”、“武”等的珍贵资料,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说剑》展现了王公贵族“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真实情形。其文开头就说:“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正是在这种危难时刻,太子要庄子前去劝剑。庄子既至,“王乃校剑士七日,死伤者六十余人。”最后,赵文王接受了庄子的劝说,“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也”。[1]唐代陆德明之《经典释文》于此引述司马彪的话说:“忿不见礼,皆自杀也。”上引的这节文字中,一方面以赵文王“喜剑”为例,说明当时养“私剑”的真相。他有“剑士”和门客三千余人,天天练武,不惜草菅人命,造成了“国衰”的严重后果。当时游侠之盛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剑士”们暴勇好斗的性格特征。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任侠”,而只要是为了博取主子的欢心,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说剑》强调了“剑”和“剑术”在武侠中的重要性。文章写到庄子佩宝剑,穿剑服去见赵文王时,遭到询问,话题乃从“子之剑何能禁制”开始。庄子张口就滔滔不绝说:“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2]然后大谈什么“天子剑”啊、“诸侯剑”啊、“庶人剑”啊,等等,在其一番大谈剑道的“高论”下,赵文王被说服了。从这类文字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当时剑术的高明,游侠的技击水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而且已有比较成熟的理论性之总结。另一方面,以剑来治国,也表明“武”在社会中的作用已和政权的巩固相连接,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有所裨益。
第三,《说剑》开创了人物形象描写的先例,为武侠小说中的人物登上文坛作了预演。作者在文章中借用太子之口说:“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3]唐人成云英对此解释说:“发乱如蓬,鬓毛突出,铁为冠,重下露面。曼胡之缨,谓屯项抹额也。短后之衣,便于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愤然窒胸,故语声难涩。斯剑士之形服也。”这就把武侠人物的形象描写具体化了。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描写,虽然面目迥异,千变万化,但其最早的源头却来自于庄子的《说剑》。这也说明《说剑》在武侠小说史研究中是不应该被人遗忘的。
尽管如此,倘把武侠小说的发端归结于《说剑》,也是很难服人的。我们不妨把它的出现,说成是“孕育了武侠小说的产生”,似乎更加符合实际。
下面再说“两汉说”。
王海林先生把《史记·游侠列传》之“郭解事迹”和《吴越春秋》之“越女试剑”两篇视为武侠小说,我们以为其理论依据也很不足。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惜篇幅,将《游侠列传》中有关“郭解事迹”部分的全文迻录在这里: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立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值。”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郭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待吾去,令淮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房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这段文字有声有色地记录了游侠郭解的音容笑貌和行动、语言,既有故事,又有情节,武侠人物也贯串其间。司马迁运用优美通俗的文字,栩栩如生地叙写了郭解一生的主要事迹。从表面上看,似是一则完整的武侠小说。然而,这里迻录的部分,出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一书被历代学者公认为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其《列传》部分,包括《游侠列传》在内,都是一种历史著作。司马迁在这里所记录的一切,都是历史上郭解的真实事迹。尽管他在叙写这一切时,运用了相当优美生动的文字,也无法否定它本为历史学著作的原貌。即以《游侠列传》来说吧,它作为《史记》的一百二十四卷、《列传》之六十四而呈现在世人面前。全部《游侠列传》的文字中,除了上引“郭解事迹”以外,还有游侠朱家和剧孟的事迹,关于他们的篇幅还要短小。而在这三人的事迹前,还有司马迁的大段文字。他从引述韩非的“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开始,阐发了自己的游侠观。其中说:“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他是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而紧接上文叙写朱家、剧孟和郭解之事迹的。在郭解事迹之后,司马迁又紧接着记录了当时关中“为侠者极众”的事实,并一一列举其名,是“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耳,曷足道者!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这里说得非常明白,皆是为了证明“乡者朱家之羞”而写。尤其是在《游侠列传》的结尾,司马迁特地加了一节“太史公曰”,专评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4]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了一个事实,上引“郭解事迹”,虽然貌似一则独立的武侠小说。其实不然。它是一则历史人物的真实生平传记,乃作者为论证其游侠观而列举的一个典型例证。尽管司马迁笔下的这一武侠人物,具有游侠的相貌、言行和故事。如若把它视作我国武侠小说的发端之作,无疑是一种不应有的误读。
在崇信“两汉说”的学者中,还有人以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为证,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和《游侠列传》一样,《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也称不上是武侠小说。尽管后世有不少作家从中撷取过创作的素材,把其中的几个故事改编成一则则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但《刺客列传》本身却只能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创作题材的“母本”,而非文学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在此辨明的。
还有不少学者在提到“两汉说”时,把“越女试剑”的故事作为例证,认为它是一则真正的武侠小说。它见于《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吴越春秋》一书也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是一部史学著作。在今存之数万字的篇幅中,区区三百余字,只能作为作者叙写史实时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仅以《勾践阴谋外传第九》来说,全篇就有七千余字,《越女试剑》也只是其中小小的二十分之一,不要说独立于全篇,就是说它独立于《勾践阴谋外传第九》,也很难自圆其说。我们又怎能把它称为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发端之作呢?
关于“六朝说”和“唐代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崔奉源先生所说:“其时,已有很标准的武侠小说。”
那么,我国武侠小说的发端究竟在何时呢?
我的回答是:东汉末年。其代表性的武侠小说是《燕丹子》。
《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
我们之所以认定武侠小说的发端是东汉末年,是因为那个时代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小说《燕丹子》。
关于《燕丹子》的成书年代是东汉末年,这一点上文已作过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下面着重说明《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是一条悠远辽阔的大河,唯有时光会磨灭她的鲜艳的色彩,但也绝不能阻挡她的奔腾向前的根本方向。我国的小说和武侠各自从悠远的历史年头走来,相互交汇融合在东汉末年,其结合体和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则是《燕丹子》。
在《燕丹子》之前,我国小说的萌芽已露端倪。先秦时代,它还是市井闾里间的“丛残小语”。可是到了汉代,它已冲破厚实的土壤,长出了一片嫩绿的幼苗。《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以及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一书中辑录的不少作品,则是她生机盎然的证明。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刘向的《列仙传》、郭宪的《洞冥记》等小说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虽说其中有的是“旧题”和托名之作,但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还应把它们视为是汉代小说。
在《史记》、《汉书》等文学性较强的历史著作影响下,汉代模仿其中的《列传》等人物传记而创作的、以摹写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小说应运而生。比较著名的有伶玄的《赵飞燕外传》和班固的《汉武帝内传》等。这类小说所写,虽然都是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但其内容除了来自于历史的真实外,还揉杂进了民间流播的各种传说故事。作者在题目上分别标明是“外传”和“内传”之类,就是为了表示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区别。如班固所撰《汉书》第六卷之《帝纪》六,是有关汉武帝刘彻的历史传记,主要记述他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史实,而同样题作班固撰写的《汉武帝内传》,却把这些史实撇过一边,另辟蹊径,主要叙写了西王母和汉武帝的相会之事。作品描写了七月七日两更夜后,西王母降临汉武帝宫殿,两人同食仙桃,并饮酒数巡,“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钟,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侍女阮凌华拊五灵之石,侍女范成君击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侍女安法婴歌《玄灵之曲》”等等。这类内容,主要来自民间的丰富想象,况且作者在描写时,采用华丽的文辞和赋体文学排比、对偶等各种夸张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比史书更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分,把汉代小说的创作推向前进。
这些都可说明:小说在汉代已经萌生。这是武侠小说得以发端的文学土壤。
武侠小说的发端,也离不开任侠之风在全社会的普遍流行。而这种任侠的社会氛围,在汉代已是前所未有的浓烈。
和汉代开国皇帝相争江山的“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充满任侠之气的悲剧英雄。他在乌江岸边演出的那幕人生之剧,不知曾震撼过多少人的心灵,一声“力拔山兮气盖世”,把这位失败者的豪雄和无奈又表现得何等淋漓尽致。
项羽的部下有位将军,叫季布,一生“为气任侠”,在楚汉对峙中,率部攻城掠地,几次打败汉军。刘邦对他恨之入骨,在项羽死后,曾以当时最高的悬赏——一千斤黄金——捕捉季布,并且昭示全国,谁要是藏匿了季布,就要满门抄斩,一个不留。季布闻讯后,东躲西藏,最后来到鲁地的一位朋友朱家的家中避难。朱家是个任侠之人,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并且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洛阳,请刘邦少年时的好友夏侯婴出面去“打通关节”,替季布说情。刘邦被朱家恳切的言辞所打动,终于下令赦免季布。
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汉代任侠者的故事之一。类似于朱家这样的豪士,在汉代社会真是数不胜数。动荡的岁月,为任侠之士创造了用武的机遇。据彭卫《古道侠风》一书的附表一,[5]乃主要根据《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作了一个不很完全的统计,可知活跃于汉代社会中有名有姓的游侠就有一百四十余人。他们之中,既有贵族,又有平头百姓,尤其是在群雄争战的年头,他们更是驰骋于各地,如鱼得水,一展人生,大多建立了丰功伟绩,所以人们对游侠们充满了仰慕之情。无论是市井细民,还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文人墨客和商贾豪门,都对游侠十分同情、信任和爱戴,甚至抱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态。
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司马迁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为游侠树碑立传,并且他把游侠分为“卿相之侠”和“匹夫之侠”,虽然没有对此作深入的说明,也没有具体指明历史上或者当时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游侠之士的归类,但这种分类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甚有裨益。
这是武侠小说能够在东汉末年诞生的重要社会基础。
面对盛行于世的游侠,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司马迁等人,开始对这一社会现象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之撰写,就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之一。差不多每一部论述武侠小说或是《中国游侠史》之类的专著,都对这一《游侠列传》十分重视。因为司马迁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游侠的界定概念,也有的学者把这种界定概念又称为品行规范。其实,用何种定义在这里并不显得太重要,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的“游侠观”,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大体上都能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先看《游侠列传》中的这段话: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和韩非相比,司马迁在对游侠的看法上,和他有着天壤之别。从上引的话来看,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主要还是着眼于他们的品行规范方面的。这种品行规范大体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讲求信义。这是游侠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正是游侠为人称赏的主要之处;
(二)轻财好施。这是游侠人格魅力的基本要求。他们绝不为财伤生,或者爱财如命,拒绝赚取那些不义之财;
(三)扶危救难。这是游侠牢记心头的重要准则。他们劫富济贫,仗义疏财,助人为乐而又爱憎分明,绝不屈服于黑暗的邪恶势力;
(四)广交朋友。这是游侠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他们以义为本,忠于朋友,可以为弱者两肋插刀而不皱一下眉头,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崇从“出门靠朋友”的江湖信条;
(五)悍勇无比。这是游侠安身立命的重要条件。他们武艺高强,以力取胜。一切任侠行动离开了它,就只能是嘴上说兵,枉费心机。
诚然,这几种品行规范,又是相互渗透,互相融通的。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问世后,游侠的品行规范已有了基本的标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定型。人们在衡量游侠的所作所为时,在心中也有了一杆“标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虽然对游侠作了基本的肯定,但也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味赞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这劈头一句,如实地反映了司马迁的真实思想。身在封建社会中的他,虽然接受了黄、老之学,但传统儒家的思想也在左右着他的世界观。他认为,游侠是在封建社会中滋生的特殊人群,他们的行为,常常要“不轨于正义”。也就是说,司马迁对游侠的行为,并非是一切都很赞成的。这正体现了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知。他遵循写史须“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基本原则,运用历史观点力图把游侠的直实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诚然,在专制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对“不轨于正义”的行为,是否一定是“恶”,对其应作何种评价,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司马迁对游侠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也还可以再作深入的讨论。目前有若干著作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廉价地送给司马迁许多溢美之辞。我认为,这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肃的学者对此应当审慎对待之。
从《游侠列传》中的这段话来看,司马迁主要是从游侠的个人品行和人格的角度来赞美他们的美好品德。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也活现了古代游侠身上的基本精神。后世的文学家们,也大多根据这些品行准则,来创造各种各样的武侠人物,而读者对武侠小说中人物艺术形象的评判,也大多依据这一标准来定夺优劣。
司马迁为何能独出机杼、从个人的品行和人格方面来界说游侠的定义呢?下面的一段同样引自《游侠列传》的话,也许可以揭示这一谜底:“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这最后的一句话曾被大多数的学人所忽略。其实不应该。我们仔细探究之后就可发现,司马迁在此特别强调了“人”,而这一个“人”字,却是统治者十分忌讳的。在专制政治下,谁会把你当一个“人”来看待呢?如果我们联系司马迁的身世和“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的艰难处境来看,其答案亦不言自明。他认为,茫茫宇宙中,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所以,人格不能被侮辱,人的尊严不能被践踏,人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人的生命更不能被残杀。这种对“人”的认识,渗透在司马迁的人生历程中。而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他的理想王国之反差,却是如此地强烈,“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董份的这一看法,真是一针见血。我们读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须用心灵去读,才能真正触摸到作者的生命之脉搏。
这种比较成熟的武侠理论的探讨,为武侠小说在东汉末年的兴起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正是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之下,于东汉末年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武侠小说《燕丹子》。它的诞生,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新篇章。
《燕丹子》:我国最早的武侠小说
《燕丹子》全篇所叙,乃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其内容梗概略谓:燕太子丹入秦为质,因秦王无礼,设法归燕后,罗致勇士,似期报复。其傅麴武劝阻无效,只得荐田光于丹。太子厚待田光。田光因自己已年迈,无法效力,又转荐荆轲,荆轲得太子丹三年的极度优厚礼遇,决心入秦为其谋刺秦王,以死相报。太子丹于易水为荆轲及其副手武阳送行。荆轲临行前,高歌一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其时,“为壮声则怒发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入秦后,荆轲以秦之仇人樊於期的首级与燕督亢地图作进身之阶,获得秦王信任。于是,他借献图之机,“左手把秦王袖,右手嚬其胸”,拟杀秦王。后来误中对方缓兵之计,反受其害。临死,“荆轲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6]
《燕丹子》叙述的“荆轲刺秦”的故事,在历史上实有其事,它发生在先秦时代。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权刚建立不久之时,广大民众中对此有着巨大的新鲜感,所以在秦汉时期的社会上流传很广。今存的汉代石刻中就有“荆轲刺秦”的画像。而司马迁的《史记》之《刺客列传》也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并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7]其后,刘向《列士传》、邹阳《狱中上书自明》、王充《论衡》、应邵《风俗演义》等书中都有荆轲刺秦故事的记载。特别是应邵,生活于东汉末年。他撰写的《风俗演义》一书,其辑录的故事大多由民间搜集而来,其中也有流播于世的荆轲刺秦故事。他把这则故事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后,还对它加以直接的评论说:“丹畏死逃归耳,自为其父所戮,手足圯绝,安在其能使雨粟其余云云乎?原其所以有兹语者,丹实好士,无所爱吝也,故闾阎小论饬成之耳。”[8]这里明说它来源于“闾阎小论”,也即市井坊间的“丛残小语”,可知它在成书时,已经过相当时间的街谈巷语的流播。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有“道听途说者”的编造、附会,并进行各种艺术加工,使这则故事的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情节也更加曲折、生动,其至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荆轲也摇身一变而成了燕丹子。因此,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小说《燕丹子》,实际上是一则长期流传于民间,并经过艺人加工改编后写定的文学作品。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其文彩诚有足观,而词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9]
今存《燕丹子》,为上、中、下三卷本,完全符合上文我们所说的衡定武侠小说的四条标准。全篇首尾完整,不依附于任何史书,是一则独立的武侠小说。其中有着较多的艺术虚构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将《燕丹子》和《史记·刺客列传》所叙之荆轲刺秦的本事作一仔细的比较,两者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它们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对此,曹亦冰先生撰写的《侠义公案小说》一书已说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叙述手法上,《史记》采用人物传记的写法,文章一开头,介绍刺客荆轲的姓名、籍贯、生平、爱好以及活动简况等;而《燕丹子》则采用小说的手法,故事一开头就开门见山,抛出矛盾的焦点,拉开燕丹子和秦王之间的斗争序幕。
(二)故事情节增加了十多处,如燕太子丹质秦归燕之事。《史记》只是一笔写过,而《燕丹子》在此增加了三个情节。一是燕丹子的求归遭到了秦王的无理阻挠;二是秦王在燕丹子的归路上故意设卡;三是客观上的障碍“关门未开”,他只得装作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又如荆轲在田光的举荐下去见燕丹子,较之《史记》,小说增加了两个情节:一是“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二是燕子丹“置酒请轲”,“太子起为寿”,并由燕国卿士夏扶以“乡曲之誉”为题激诘荆轲等等。再如,燕子丹厚遇荆轲之事,《史记》写得十分笼统,而《燕丹子》却写得十分详细、具体,增加了黄金投蛙、杀马进肝,断美人手等细节,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最后一节“图穷匕首见”,叙写荆轲与秦王展开正面搏斗,是全篇的关键情节,《史记》采用通常纪传体编写之现场记实的手法,而《燕丹子》则采用了文学创作的手法,按照作者的主观愿望去安排情节。例如,他让荆轲劫持住了秦王,并加以责数,以让读者得到如愿以偿的审美愉悦等等。
(三)增加了作品的浪漫色彩和具体描写的成分。如“乌即白头,马生角”,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而小说作者却把它当作理想写入作品,以帮助太子丹实现回归燕国的梦想。再如秦王接见燕使的场面,《史记》写得十分简略而平淡,而燕丹子则写得十分隆重、宏大,这有利于塑造荆轲和秦武阳的艺术形象。
(四)调整了情节的前后顺序,并对人物对话的内容也有所改变,使其适合小说的创作特点。如《史记》写燕丹子见到荆轲后,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分析了形势,并提出以武力胁迫秦王的计划,然后笼统地写了燕丹子厚遇荆轲的话;而《燕丹子》则不是这样,写两人相见后,燕丹子先设宴为荆轲接风洗尘祝寿,再具体写他厚遇荆轲,然后写荆轲备受感动,决心要为燕丹子“当犬马之用”,然后再写燕丹子分析秦强燕弱的形势,并提出具体的行刺计划。这种写法,不仅使作品的文学色彩加浓了,而且也揭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更加符合侠客义士的性格特征。
我完全同意曹先生的这些看法,之所以在这里如此不厌其烦地将《史记》之《刺客列传》和《燕丹子》作比,其意当然不在评判两者的高下优劣,事实上,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各自有不同的写作之路。《史记》为《燕丹子》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而武侠小说《燕丹子》的创作则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它提炼、加工,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经过反复的锤炼后完成的。归根结底,我们只是想证明:《燕丹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燕丹子》最为人称道的是它为我们塑造了先秦时代的游侠群像。
从这篇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贯串全篇的中心人物无疑是燕丹子。小说从他“质于秦”的逆境生涯开始,写他不甘忍受屈辱而逃归燕国,并发誓要报仇雪恨,乃至寻觅刺客对秦王行刺,最终由田光引出荆轲,两人从会面到相识相知,以至授以重任,最后不幸失败的全过程。在作者的笔下,燕丹子是一个颇具正义感的少年英雄。为了雪耻,并实现灭秦的宏愿,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实行“行刺”的极端手段,四处网罗能担此重任的游侠,从田光到荆轲,他都给予了优厚的礼遇。然而,他又是一个心胸偏狭,急于求成的青年统治者,血气方刚,不善忍耐,又较少心计。为了复仇,这类性格的弱点被他的礼贤下士、谦虚求士所替代了。小说较好地展现了燕丹子求贤若渴的任侠形象。他在逃归燕国后,先问计于麴武,得到了田光。小说描写他见到田光时,“侧阶面迎,迎而再拜”,并安排他居以上馆,“三时进食,存问不绝,如是三月。”也正因此番盛意感动了田光,由他荐举,把荆轲推上了前台。燕丹子把荆轲奉为上卿,两人会面时,益发谦恭有礼。为了博其欢心,拼命迎合他的意志,不惜采用黄金投蛙、杀马进肝、断手盛盘等各种手段,以示厚爱。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燕丹子,完全是一个真实生动的“卿相之侠”的艺术形象。
作为“刺秦”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荆轲,是《燕丹子》主要描写的武侠英雄。在他身上,集中着作者的人生理想。荆轲出场前,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他作了充分的渲染。他虽然是个威武的勇士,遵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准则,但他很有头脑,决不会鲁莽从事,在激烈的诸侯争战中,学会了理性处事。在没有深入了解燕丹子的诚意和真正目的时,荆轲并不轻易答应他的要求,表现出可贵的成熟和智慧。直到燕丹子降尊纡贵,亲自为他驾车,并陪同出游和“置酒高会”,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实际行动表明诚意。经过三年的多方面考察,荆轲看出了燕丹子是值得为之赴汤蹈火的人,才决定为其“当犬马之用”,入虎狼之国去行刺秦王。尽管“刺秦”没有成功,荆轲也碎身于秦王殿上,但这位武侠英雄的壮举,至今还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燕丹子》功不可没。
此外,小说中的田光和樊於期,也都是响当当的武侠英雄。他们为了使刺秦事件成功,甚至不惜主动捐献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小说中的这些艺术形象身上,作者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数语,但透过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武侠英雄来到了人们面前。
为了凸现荆轲这位武侠英雄的豪气,《燕丹子》的作者比较重视场面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如下一节可为佐证:
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二子行过,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二子。
这就是很著名的“易水送别”,作者用传神之笔,把它描摹得如在目前,读着它,人们完全能切实地感受到当时多么悲壮的场面和气氛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不知曾震撼着多少读者的心灵。荆轲则“起为寿”,高唱着悲歌一曲,而“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的送别场面以及两人“终已不顾”以及夏扶“刎颈”相送的情景,历历在目,无不令人热泪盈眶。
在展现荆轲“刺秦”时的沉稳、机智和忠勇的过程中,作者还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使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更显高大,小说描写荆轲和武阳带着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的地图来到秦王殿前,秦王中计,眼看“刺秦”大计就要成功,作者突然笔锋陡转:“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这一反常表现,使得“秦王怪之”,引起他的警觉。而荆轲面对这突然变故,非常镇定、沉着,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相反,他机智地用言语为秦武阳作了掩饰。直至“图穷而匕首出”,他和秦王在大殿上作殊死搏斗:
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荆轲还一一数斥秦王的罪恶。这和武阳的“大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荆轲临危不惧的大智大勇也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使《燕丹子》赢得了“古今小说杂传之祖”[11]的美誉。
《燕丹子》的问世,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
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题材,大多离不开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作大背景,这一点,在今天饮誉华人世界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响。武侠和历史的结合,《燕丹子》开创的这条艺术道路,正日益焕发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不过,各种著名的历史事件只是为武侠人物的施展拳脚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艺术的虚构却令人眼花缭乱,引导着读者进入一个个神秘的武侠王国。追根溯源,其和《燕丹子》有着各种自然的“血缘”关系。
《燕丹子》在思想上也有着崇群体、抑个体的鲜明时代特征。为了成就“刺秦”的事业,田光可以不惜捐躯,“吞舌而死”。临终,他对荆轲说:“盖闻士不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时,言:‘此国事,愿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仅仅是因为太子丹的一句话,就献出个人宝贵的生命,似乎太不值得。这表明,在《燕丹子》产生的年代,人的个体的生命意识还很薄弱,或者说,在那时人们非常重视群体的利益,为了打消燕太子的忧虑,减少“刺秦”大事的泄密可能,田光毅然慷慨捐躯。另一武侠英雄樊於期也是如此。他是秦王的仇人,荆轲在作“刺秦”的准备时,为了能取得秦王的信任,就前去劝说樊於期说:“今愿得将军之首,与燕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必喜,喜必见轲。轲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数以负燕之罪,责以将军之仇,而燕国见陵雪,将军积忿之怒除矣。”在荆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樊於期“扼腕执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闻命矣’。于是自刎,头垂背后,两目不瞑。”他奉献了自己的头颅。又一条鲜活的生命牺牲在“刺秦”的事业中。且不说直接担负“刺秦”重任的武阳和荆轲,仅田光和樊於期两人而言,在小说中是作为正面人物被多次颂扬的,他们的壮举,也获得了作者的倾心赞扬。
这说明:在那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中,有不少人认为,人的生命虽然是很重要的,但只有国家或群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两者相比之下,个人的生命显得无足轻重。为了实现国家或群体的利益,个人应该无条件地奉献宝贵的生命。在个人意识尚未觉醒的时代,这诚然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时代的悲剧也由此而产生。
[收稿日期]2003-11-24
标签:司马迁论文; 史记论文; 文学论文; 游侠列传论文; 刺客列传论文; 读书论文; 庄子论文; 列传论文; 吴越春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