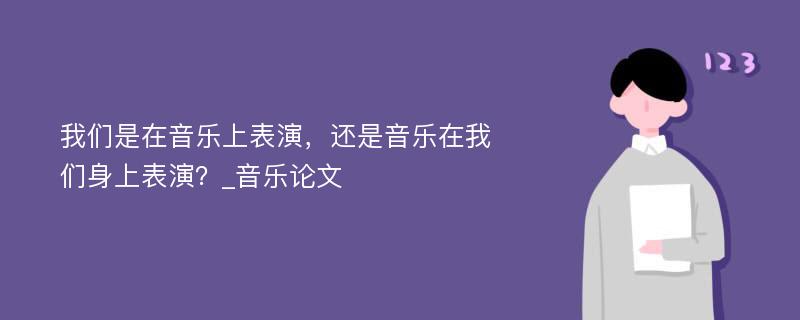
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着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几天,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来信说:“曾经有一个晚上,我听贝多芬的《月光》后,坐在床上痛哭,悲痛欲绝,因为那个优雅的年代永远不会再有了!”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灵魂和思想同时猛地触动了一下。我给朋友回信说:“还是少听音乐为好,因为你理解音乐,但是音乐并不一定理解你”。
我的话听上去有点令人费解,什么叫做“你理解音乐”和“音乐不理解你”?前一句是充满感情的安慰语言,后一句却是富有理性思考的意思。朋友对音乐的感受触动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人听到音乐时,竟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经验,那么这种经验所说明的,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请容许我绕一个圈子来谈这个问题。
很久以来,人们对于自然事物的认识一直在相反的两极之间徘徊。一是觉得,“宇宙遵从恒定不变的规律,一切事物都表现为完全确定的客观实在”;另一认为,“根本不存在象客观实在那样的事物,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想想也真有意思,这两种观点如同南极和北极,虽然截然不同,但是却又是存在于同一个地球上,二者缺一不可。前一种思想是造就人类的科学产生的根基,而后一种思想是推动人类的科学发展的力量。那么,在“科学产生的根基”和“科学发展的力量”之间,谁又更重要些呢?这,变成了一个“鸡”和“蛋”的悖论式的怪圈游戏,“规律”和“变化”成了无休止的科学战争的主题。
是否可以超越这样的无益争论呢?是否有另一种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可能呢?
我正在读一本叫做《Nature's Numbers》的书。在《自然的数》命名下,这本书另有一个副标题:数学想象的虚幻实境。书中有一章为“变数的常数”,其中作者提到了有关对牛顿的认识问题。他说,对许多科学家来说,牛顿代表着一种理性战胜神秘的辉煌。但是,作者引用了John Maynard Keynes的著作《Newton,the Man 》来解释了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牛顿。Keynes说:“牛顿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教我们依照冷静的、没有感情色彩的理性去思考问题的理性时代的第一人。相反,牛顿是最后一个以超越一万年前开始建立我们求知传统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可见的智慧世界的大智者。”
Keynes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认为在牛顿的数学里,我们发现了他向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他超越和统一了“刻板定律”和“灵活可变”这两种世界观。这种思想告诉我们,所谓的“定律”和“变动”是可以共存的,“定律”产生“变动”,反命题亦然,即“变动”推动“定律”。
绕了这样一个圈子,我想揭示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想说的是,音乐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应该类似于Keynes阐述的牛顿开创了人类综合地来认识世界的例子那样,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这两者是可以统一的。
对音乐的认识和理解和科学一样,人们走过了一个从本体论的“内学”到文化论的“外学”的过程。传统的音乐本体论所关注的仅仅是音乐作品本身,即音与音之间的纵横关系。关心的是音乐“是什么”,是一个在狭义上的“是什么”。这种意义上的询问,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认为是唯一可行的,而且对于那个技术层次上“是什么”的回答也是满意的。例如,读者们习惯于阅读“小调性质的第一主题需要一个关系调上的第二主题来呼应”之类的文字。然而,本世纪以来,人文思想开始经历一次深刻的转折。观念开始改变,思维方式开始改变,思想认识开始改变。对音乐的理解也是随着这些对人自己、对他的文化的理解的改变而提高的。波斯音乐中复杂的调式体系、印度Raga音乐中十二微音系列与生活、生存、生命观念的复杂关系、中国古典戏曲中一套又一套的象征性脚色制和脸谱寓意等,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歌剧和交响乐不是人类唯一完善或复杂的音乐形式,贝多芬的音乐是人类的精华,但是他的音乐语言并不是世界性的。音乐人类学是建立在对音乐的新认识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对人类任何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询问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怎么样”产生、传播和作用的,由此来解答音乐“为什么”在不同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功能等。文化论的“外学”给予了音乐本体论很重要的补充,它说明,不同的民族和社会中的不同的文化、习俗、观念、信仰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某一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风格。
然而,文化论并不是一个“定律”,它只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理解音乐所含有的“真理”的一种途径,反映了人类的思想和意识作用于音乐的方面。那么反过来,音乐对文化、习俗、观念、信仰也同样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另一个层面上对音乐本体的再认识具有新的意义。
讨论音乐与对它所作用着的环境的关系有点象小说创作中的物质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作家王安忆《小说的物质部分》一文中所叙述的一些体验对我们的音乐讨论会有启发。王安忆说,她在创作长篇小说中,有时会被迫地要求寻得一种具有实体性、规范性的手段。当她想找而又找不到时,发现,小说是有科学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我的理解是,这种“科学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就是小说自身的生命结构。它的人物、情节和不断发展的故事,以及故事和故事的连接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小说的内在结构和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本质和规模。毫无疑问,音乐的创作也是一样。进一步,回到前面的论题,我想讲的是,关于音乐与对它所作用着的环境的关系,同样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数千年前的今天,黑人、黄人、白人之间没有邮件往来,没有电话通讯,没有电视宣传,更没有E-mail的同步传递,我们的祖先们各自在地球的东西南北“闭门造车”开创人类的文明。然而,让我们后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在东西两端几乎同时发现了“三分损益”(见于《管子》)和“五度相生”(相传Pythagoras提出)的法则,从而产生了一样的五声七音,用这五声七音各自在不同的文明里琢磨着不同的音乐。“三分损益”或“五度相生”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规律的发现。“三分损益”和“五度相生”产生五声七音的法则靠的是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三的天然数学道理,就象黄金分割规律,它们不是人类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类的文明逐渐找到了大自然的生命原则。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学比例形成的五声七音为人类带来了音乐,自有了音乐,她为人类造就了五彩缤纷的文化。这是一个反命题,也即音乐与人类的另一个方面的关系。
再补充两个具体的小例子。
中国文化离不开中国文人士大夫;而中国文人士大夫又缺不了琴棋书画。汉字“琴”,既代表音乐,也是所有乐器的总和,而且特别指的是古琴。古琴是最古老、最纯正的中国乐器,在它身上集聚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古琴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
“高山流水”的古琴故事,大家听得最多,还有其他很多有关古琴的轶事。传说,“竹林七贤”的嵇康在遭司马氏之害而“问斩东市”临刑前,安然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另一种传说,陶渊明“挂印归田”后,他在屋内墙上挂了一张无弦琴。“高山流水”和《广陵散》的故事讲的是古琴与文人间的生死之缘;而“无弦琴”的传说给予人们的启示是古琴的象征含义,即它的力量不在于声音而在于精神。
文化象征意义如此之深的古琴,就其发生的原理而言全然不是精神性,而是物质性的。古琴音乐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泛音音色。这一次的声音构成不是纯粹的截段单项数学比例规律,而是物理共振法则。泛音是琴弦的各部分同时以1/2、1/3、1/4、1/5等分段振动产生的结果。泛音系列形成的是纯律,古琴音律和其十三徽音位,以及它的音乐就是在这样的物理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物理原则建立之后,古琴的发展使得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它音乐自身的价值,由物质转变成了一种特有的中国文人文化的精神。
古琴音乐的文化象征性并不是虚无的,它的“非”音乐的意义是在对音乐声音本身品质抠刻地追求中建立起来的。古人冷谦对琴声提出“十六法”: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幽、奇、古、澹、中、和、疾、徐;另一重要古琴美学家徐上瀛提出“二十四况”: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远、速。这么些古琴音乐美学范畴是在一整套复杂的琴音演奏规范中提炼出来的。首先是琴的音色的构成,包括散音、按音和泛音;其次是一百多种左右手指法规范,比如,仅是左手的装饰音“吟”、“长吟”、“游吟”、“略吟”、“猱”、“及猱”、“注猱”等等就有三十多种;再是用指也有“上弦”、“和弦”、“修指”、“搭弦”、“按徽”、“发声”、“取音”等要求。
只有在掌握了良好的演奏规则,产生了优良的声音品质,才能达到那一系列的审美意境,才能体现“大音希声”的哲理。《高山流水》和“无弦琴”给予的文化含义和力量都是在音色、音符、音乐的前提下产生出来的。庄禅的哲学赋予了古琴音乐以外的东西,而古琴的音色、音符、音乐又提供了庄禅思想无限的空间。为什么人们不在二胡、笛子上下“十六法”、“二十四况”的功夫,道理就在古琴本身的声音品质、演奏规范、音乐内容和形式决定了它的地位和价值。
音乐的琴弦还对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另一个科学发明产生了作用。1714年,英国的数学家Brook Tayler发表了小提琴弦的振动基频与弦的长度、张力和密度关系。1746年,法国人JeanLe Rond d'Alember 证明了小提琴的许多振动并不是正弦驻波。1748 年, 瑞士数学家LeonhardEuler在Jean Le Rond d'Alember的基础上,提出了“波动方程”。 随着对琴弦振动的不断了解,过了几年,科学家开始了对鼓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小提琴弦是一条曲线,是一维对象,但是,多维对象也是可以振动的。从此,人们开始离开了音乐,完全转向了物理。波动方程还被运用于电学和磁学理论,从而使人类文明大为改观,由小提琴弦到基频振动,再到波动方程,又到电磁波,最后发明了录像机。这是音乐作用着人类的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好例子。而且,从现在看来,录像机的出现又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进一步的积极作用。它们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再到物质再到精神的循环过程。文化是音乐的根基,音乐同样也是文化的源泉。
给读者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1996年的春天,在肯特大学修我的博士学位的最后一门课。这个课叫做“田野实践”。我和两个美国同学挑选了一个美国黑人的教堂作研究考察的内容。通过对这个“田野”调查,我们的感受很深。他们的礼拜仪式完全是在音乐中进行的,牧师的布道和教徒们的应答都是以音乐歌唱的方式来完成的。除了相互问候和用餐之外,整个礼拜天都是在演唱中度过的。对他们说来,没有了音乐就等于没有了礼拜,没有了歌唱就没有了上帝与他的信徒间的沟通和交流。在他们看来,音乐不是象我们所说的那种艺术的东西,而是真正的一种表达他们用语言不能表达的“语言”。通过这样的“语言”,他们才能直接地接受上帝对他们的旨意。他们觉得,人类之所以有音乐,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用来交流的。文字和语言是人类间使用的工具,而音乐是自然界本身就具有的,是上帝给予的。只有用音乐这样的“语言”才能消除人类与上帝之间的隔阂。他们一再强调,因为是音乐才有了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确对音乐有着不同一般的直觉。只听演唱录音,一般人都会认为是一个职业音乐家合唱团演唱的。可是,事实上,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受过专门的音乐训练。然而,他们对演唱的声音的掌握,对声音音高准确性的掌握,对节奏时值的掌握,对和声音程的感觉,对音乐感情的表达等,远远超过某些音乐专业人员。所有音乐作品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然而,却没有人学过作曲,更没有人看过和声书。这些歌中有一些还运用了复杂的和声,远关系转调。他们没有人认识乐谱,他们完全靠记忆,靠感觉来演唱。他们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音乐是怎么样来的,只知道是上帝派遣的天使带给他们的,“一觉醒来,歌就在那里了”。
根据半年的参与他们礼拜活动的经历,我发现,“上帝派遣的天使”其实是他们自己。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和晚上是他们音乐排练的时间。在排练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提高演唱能力,不断地在修正歌曲的旋律,不断地改动和声的组合。这样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不自觉的,而对于我们外来的观察者来说,他们的对音乐、节奏、和声的执着是一种在宗教精神的感染下反过来升华宗教精神的刻意追求。当然,这种刻意追求是本能的、靠的是先天的直觉,但却是完全按照声音的物理规则、音乐的自然逻辑进行的。在排练期间,他们的活动是声音的劳作过程,而到了礼拜天的礼拜堂里,他们的声音便成为了宗教和文化。
这个经历告诉我们的是,宗教带给了他们音乐,音乐又回过来创造了他们的信仰。探讨“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论题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调整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和方法。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人的特征问题。大意是,浮在表层的感情和思想,只不过三、四年;气质性的可以持续二十、三十或四十年,要等一代人过去,它才会消失;再深一层的是时代的精神,它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格、人品;更深的层次是民族性和文化的产物,它是哲学、道德和社会的总和。用这样几个层次来看音乐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们应该看到音乐和人类之间最本质的东西,它们是没有属于与被属于关系的障碍的,这种本质是永恒的。音乐和人类之间永远保持着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作用着音乐,音乐也作用着我们,它们是统一的,不能分隔开来孤立看待的。对它们关系的认识要有牛顿超越和统一两种世界观的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的知识、智慧和胸襟就有一个新的高度。
想到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中的“上一层楼”在哪里?也就是问,诗人当时是在哪一层楼?依我看,他做诗时已经在了楼阁的最高一层。但是,他却“欲穷千里目”,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这“一层楼”是诗人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和要求。虽然在唐诗三百首里,诗人王之涣仅为我们留下这一首,但是,这一首成为了千古不朽之作,因为作者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认识高度,他的诗才与李白、杜甫的诗文相提并论了。五言二十字留给后世不仅是知识和智慧,还更有胸襟和境界,这才是该诗的最深层的意义。
这“上一层楼”也就是我们认识音乐和人类关系所需要的知识、智慧、胸襟和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