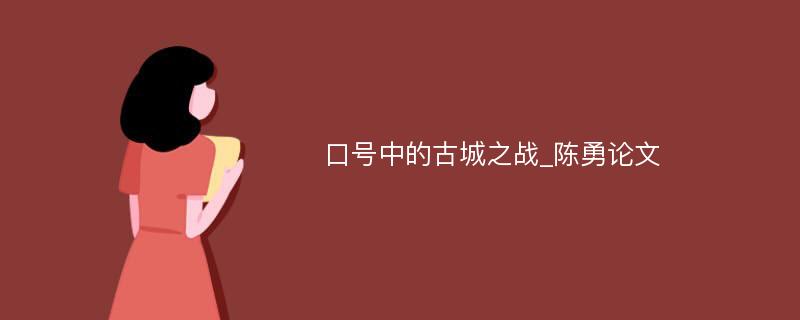
古人争夺战与口号里的城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争夺战论文,古人论文,口号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人争夺战
2010年5月29日,河南南阳30名小学生在卧龙岗前齐诵《出师表》,“示威”抗议新版电视剧《三国》将“诸葛亮躬耕地”设计为襄阳,现场还有人砸毁电视机并征集游客签名,以示拒看新《三国》的决心。
一部电视剧引发故里之战“连锁反应”——河南永成、安阳和安徽亳州争曹操;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全民动员找刘备墓。
最近的焦点名人是朱熹。为贺朱熹880岁大寿,福建尤溪、建阳、武夷山和江西婺源四地合开了一份40亿元的“寿礼”:其中包括投资4.16亿元的尤溪朱熹故居景区二期工程等项目,投资11.2亿元的建阳朱熹墓道神碑、朱熹祠堂、朱熹广场、半亩方塘等;投资3亿元的武夷山“理学圣地”游览区、“邹鲁渊源”游览区、朱子生活体验区、宋朝风情一条街;而江西婺源婺女村旅游休闲度假区、朱子龙尾砚文化园、文公湖度假村等项目总投资达24.45亿元。
“周作人曾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文化学者陈勇不无戏谑地指出,“如果地下有知,很多古人都会对这句话感同身受。”
向古人要GDP
盘点一段时间内卷入故里之争的地点,可以归纳出“大省小城”的特点,屡屡参与竞争、乐于曝光的多是地处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选秀一样,它们要的就是借此“出位”。通过争赵云故里的激烈对抗,河北临城和正定果然一夜成名。
然而无论是提高知名度还是优化环境,最终动力都来自于经济利益驱使。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就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习惯用数据说话:“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但靠古人营销城市并非没有代价。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名胜风景区”、湖南株洲“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项目,计划分别投资4.4亿元和100亿元,而这两个地级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分别是17.5亿元和100.33亿元,上述项目就要占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两个项目分别占地3000亩和2970亩,对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亩的湖北、湖南省来说,这3000亩地,相当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积。
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
一个寂静的山谷,一间始建时间相当于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驳的楼梯,游客会发现一台电视机孤零零地播着flash,讲述13位修女饥荒年代在这里收容逃荒者的故事。这是一处英国“景点”。
“中国游客觉得不可思议。”刚探访过该景点的东南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喻学才说,因为中国人看多了“大投入生产出的大文化”。动辄数个亿投入旅游文化项目,即使在一些贫困地区也不鲜见。河南鹿邑花2亿为老子修明道宫和太清官,安徽涡阳建一个老子骑青牛铜像就花了120万。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当代人有时想动用自己的财富与实力,来打造场面宏大的古代文化价值。但人们看到的只是铺张的建筑样式,绝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
喻学才也有类似体会:就像京剧只有“一桌二椅”,舞台上东西越多,戏剧精神就越少,艺术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赶上舞台呢?”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汉唐建筑都恢复起来,大兴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劳民伤财的做法。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拥而上争夺名人故里,充分说明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严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实质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阴影。
城市旅游规划到底要向传统学什么?
“首先是多读书,现在的不少地方官员学历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参与多个城市旅游规划的文化学者如此评价。白居易营造庐山草堂,苏东坡经营杭州西湖,柳宗元设计万石亭,这些“开发者”本身就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
当然,古人做这些设计开发,只图风雅美名,并不关心投资效益,现在搞历史资源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喻学才说,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领导者更精准地确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旅游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遗产保护。瑞典历史学教授巴克特曼说,欧洲争名人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瑞典有38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诺贝尔学堂”等招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在德国,歌德有两个故乡,马克思有三个。
同样是为了吸引游客,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争的不是这些大师的故里何在,而是竞争谁对他们的遗迹保存得多、保护得好。而且,他们也不会动用纳税人的巨额款项率意而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筑。
口号里的城市
今年1月,合肥推出城市旅游口号:“两个胖胖欢迎您”,当地媒体街头调查显示,此口号遭多数市民反感。3月,宜春旅游政务网打出口号:“一座叫春的城市”(目前已改为“一座春的城市”)。“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常常是某地政府刚刚花大力气大价钱树起来一个口号,马上就被网民解构得体无完肤。
据长期关注城市形象研究的文化学者陈勇介绍,中国内地大小2000多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几乎都在绞尽脑汁地设计与营销城市,除形象广告、征集市歌、申遗、改名、选形象大使、建地标外,对于征集城市口号也热情高涨。
无比正确的废话
陈勇告诉记者,整理当今国内的城市口号,会发现很少有能划到四类之外的:
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这个最简单,有什么出产,有什么产业,填上就得。
二是由苏杭领队的“天堂在人间”,天堂、仙境、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焦作山水,人间仙境”(焦作),“东方不老岛,海山仙子园”(浙江象山县);“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等等。其实把某某之都,直接改成某某天堂,一般都无不可。
三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成功,引发“山水类”口号扎堆:“福山福水福州游”;“奇山秀水绿南宁”;“多情山水,天下洲城”(长沙)。以中国的地貌,大部分城市要找出些小山小水都不难,这些山水是否有代表性?还是和房地产开发商宣传用的山水家园、山水花苑一样,只是个噱头?
四是给西方地名做陪衬。如在宣传中自比“东方日内瓦”的地区,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还不算自称“东方小日内瓦”的,以及把发展目标定为“即将建成东方日内瓦”的。
在陈勇看来,上述现象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发展向西方看齐的努力和与西方文化抗衡的心态,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中国城市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甚至是极度自卑。
在2008年的一次旅游专家座谈会上,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魏小安指出:“城市口号最容易变成正确的废话。”“要么因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惯性而显得很“虚”,要么出于市场利益诉求而太“实”,这是目前城市口号的两种极端化表现。”陈勇说。
失落的城市精神
定位混乱、推广不力、缺乏国际视野、设计粗糙、公众参与度不足,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彦平给城市口号总结了这些病症。口号,就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参考该定义,目前中国的城市口号大都难担这一重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解释说,城市口号出现克隆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城市的今天不了解;二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之路也不了解。
西方著名学者斯宾格勒说:“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在顾晓鸣看来,我们需要的是精神追求,一种崇高感和超越感,提炼形成主题词的形式,让口号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科研处处长梁保尔告诉记者,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根本价值的追求,是内化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法则。城市精神需要通过有代表性的符号解读出来,而城市口号最具代表性。“动感香港”这个口号很成功,因为它体现了香港工业、经济和文化的动态与香港人的活力。”
前提是“酒要好”
陈勇说,一些名不副实、有悖于文化内涵的口号,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不仅对城市建设没有推动,反而对城市形象产生负面作用。如“生态型城市”的提出,并不适合所有的城市。即使初始条件符合,根据发达国家经验,真正实施并达到效果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此类漂亮口号只会助长城市发展的浮夸风气。
城市口号应该是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不仅包含历史文化基础,还必须有群众基础。刘彦平对在城市口号的塑造中民间参与严重不足表示担忧。他认为,城市品牌的实质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对城市历史的自豪感、对城市发展前景信心的综合表达。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所以城市品牌从设计、管理到增值,都应有市民的参与。
对大城市来说,依托雄厚的财力和发达的传媒广告业,宣传、营销自己的口号并不难。然而营销只是推广、辅助手段,不能解决城市精神重塑的大问题。如何利用历史文化激活城市的生长动力,凝聚城市精神才是根本。“酒好,还需要吆喝。但前提是:酒要好。”包亚明说。
(原文标题:中国183城市欲建国际大都市名人故里争夺成风,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