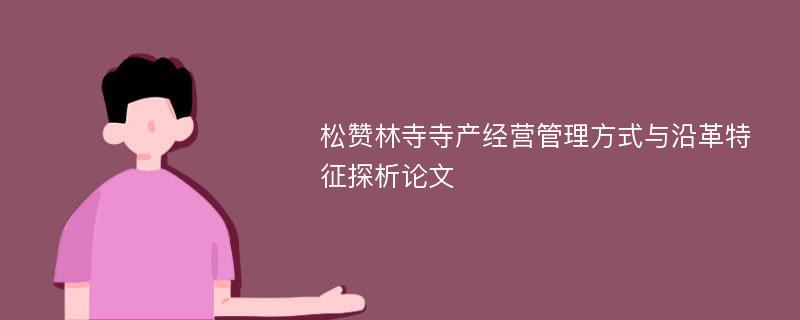
松赞林寺寺产经营管理方式与沿革特征探析
次仁卓玛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 松赞林寺作为云南藏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始建之初得到五世达赖喇嘛和康熙皇帝的支持,规模逐渐扩大并成为云南藏区政治、经济中心。松赞林寺自始建以来,寺院经济呈现出收入来源广泛且数量庞大的特点,寺院也因此逐渐形成体系化的财产管理部门。本文旨在以历时性的角度,对不同历史背景下,松赞林寺寺院财产管理部门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松赞林寺在区域内政治、经济地位发生转变后,寺院内部财产管理部门的应对措施与变革;以及当前寺院财产管理部门的相应调适制度等进行梳理,从而为新时期藏传佛教寺院财产管理制度的良性发展提出相应启示。
关键词: 松赞林寺;财产管理;变革
佛教自七世纪传入西藏以来,经与苯教的碰撞融合,逐渐形成藏传佛教。八至十世纪,从迪庆境内德钦县奔子栏镇达日村曲赤塘崖壁上的莲花金刚、莲花观音、四臂观音石刻造像可以断定,藏传佛教已经传入云南藏区。[1]十三世纪起,藏传佛教教派中的宁玛派正式到四川、云南藏区为主的康巴藏区传法,宁玛派大成就者藏登作畏的大弟子嘎当巴·德协西巴(bkav gdams pa de bzhin gshegs pa)来到康区建立宁玛派寺庙。此后,噶举派、萨迦派等也逐渐传入云南藏区。
明至清初,云南藏区为丽江木氏土司所统治。木氏土司自元、明以来,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与扶植,并以守边的名义向北扩展势力,将迪庆地区全部乃至巴塘部分地区、理塘部分地区及昌都部分地区等滇、川、藏交界毗邻地区占据,木氏土司控制这些藏区的时代,在历史上被称作“木天王时代”。[2]随着木氏土司在这一区域的政治势力逐步深入,该区域的宗教关系也由于木氏土司的信仰推动而发生了某种的变化,主要表现就是丽江木氏土司崇信噶玛噶举派(俗称白教),并推动其教于云南藏区和纳西族地区,使之弘扬于滇西北一带。
梳弄的手停了下来,他握紧我的手:“无双姑娘只是暂住在西厢而已,况且她是皇上让我照顾的人,怎会是我的妾室?”
丽江木氏土司早期信仰的并不是藏传佛教,但早在公元十五世纪西藏噶玛噶举派红帽活佛二世喀觉旺布(mkhav spyod dbang po)(1350~1405 年)和黑帽活佛七世曲扎嘉措(chos grags rgya mtsho)(1454~506年)时期,木氏已逐渐与噶玛噶举派缔结法缘关系。在木氏的扶持和帮助下,噶玛噶举派在此区域内讲经说法、招收弟子、兴建寺院。金沙江以北中甸、巴塘、理塘等康藏地区已为该派教区,即使在边远的木里也已有噶玛巴寺庙5座。[3]而至笃信佛教的丽江土司木增在位时期(1597~1646年在位)时,六世红帽活佛却吉汪秋(chos kyi dbang phyug)(1584~1635年)常年在丽江驻锡,这一阶段对于噶玛噶举派兴盛发展起到了非常的作用。
至明末清初,西藏受噶玛噶举支持的藏巴汗政权对格鲁派的长期压制,最后导致格鲁派援引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军事势力,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将藏巴汗政权消灭。同时固始汗帮助五世达赖喇嘛和格鲁派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由此整个青藏高原的政治、宗教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固始汗及其后裔的支持下,格鲁派迅速发展,并伴随着和硕特部蒙古势力进入滇西北,顺势助格鲁派传布于云南藏区。和硕特部和格鲁派的传入,打破了原有的丽江木氏土司和噶玛噶举派在政治和宗教上统治云南藏区的格局,后者反抗前者的斗争不断出现。
以不同时期松赞林寺财产管理部门的沿革来看,寺院的财产管理部门具有不同阶段特点。在新中国成立民主改革进行前,松赞林寺以收取皇粮、教民的实物地租、债款利息及商业获利为主要收入来源。封建的经济收入形式,决定了洛章、觉夏和西苏三个财产管理部门的剥削性,寺院财产管理部门不仅对寺院财产进行管理,并在民间进行高利贷等业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区经济的正常发展。寺院财产管理部门人员主要以利益包干制度为原则,滋生了管理部门内部贪污腐败的现象。
如果每天摄入钙的量不超过2000毫克,理论上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每天补充超过1200毫克的钙,却得不到充足的维生素D来帮助吸收,钙的吸收率就会较低,对于身体来说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一、松赞林寺成为云南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藏历土阴羊年(1679年)至铁阴鸡年(1681年),大寺在中甸城北落成,由五世达赖喇嘛赐名“噶丹松赞林”,并派弟子穷结巴阿旺南杰(ngag dbang rnam rgyal)出任首任堪布(掌教)。在大寺建立之初派举玛倾则管理寺院,划300户为僧众供养户,70户为大寺掌教处供养户。松赞林寺的建立得到清王朝的支持,康熙皇帝赐名“归化寺”,颁发330本度牒,并降旨从当地所收赋税中支付皇粮及银两以供寺院香火。
由于清政府对格鲁派的支持,松赞林寺享有政府发放的“皇粮”、“衣单”、“供品”如下:年发青稞一千七百零四京石四斗四升五合,衣单银三百三十两(新中国成立前折为云南半开发,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币放给);供品银八十两(同前);酥油三千九百五十七斤四两五钱;土布四百五十四件十八方;山羊毛毯一千三百二十七托四尺五寸;沙盐八京石三斗九升五合二勺;生铁二百七十四斤十三两五钱;铁斧十六把;龙巴纸(尼西生产的书写藏文纸)九千张。[5]
在松赞林寺的重建恢复阶段,寺院财产构成以及收入内容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寺院内部的财产管理原则也在国家的引导下的新时代背景中找到新的定位。重建的财产管理部门在组织原则上与西苏、觉夏机构相同,寺院财产管理内部人员依然从各大康参中推选,但经推选后以出纳和会计的分工类型进行管理工作。
寺庙不仅享有当地所供的香火钱,大小中甸地区还对其承担着相应的劳役和物供。松赞林寺僧众供养户、大寺掌教处供养户三百七十户除去承担寺院的乌拉、差役、打杂、背水等劳役外,还承担不同的物税。寺庙附近的六个村庄共有麦地二百余顷,每年向寺庙上交青稞二百余石。
以小中甸地区为例,承担松赞林寺的赋役十一项“该地区每年上缴寺院用于点灯、打酥油茶的酥油二百五十饼,买柴用的酥油一百一十五饼;每年上缴青稞二十八万石;全年不同时期举行的法事活动鸠嫩会(念经)、俗嫩(抗雹灾经)、细都错(念太平经)、东吹(人畜太平经)、勒楚会(念抗麦锈病经)念雅拢(念驱鬼经)、能打(念除病经)、五谷会(活佛讲经)等都需要按人头向松赞林寺上缴不同数量的酥油、奶渣、茶、盐、沙糖、腊肉、炒面、麦面、牦牛等”。[6]
在20世纪90年代初寺院复建工作完成,松赞林寺重新成为区域内民众信徒聚集的宗教场所。在这一阶段中,财产构成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以及信徒供养。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十世班禅大师发表文章关于扎什伦布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试点的总结报告》,在文章中提出藏传佛教寺院可以通过从事农林牧副业生产、兴办社会公益和服务事业等实现“以寺养寺”的目的。在“以寺养寺”口号的号召下,松赞林寺从财产收入类型以及财产管理方式都产生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变革。
我们今天从博物馆和遗址里看耀瓷八百多年的烧造历史,它们无声地堆积着,却又突兀地相互叠加涌动,仿佛争先恐后想要倾诉些各自的前尘往事。那些凹凸不平的纹路,有的甚至依然夹杂着大块的泥土。耀州青瓷的缘起缘灭,都已在止歇于这些裂痕深处。釉水不再流淌,它们静默在青瓷体内,与遥远的记忆抵牾抗衡。
以松赞林寺每年的青稞收入来看,每年至少累计三百万斤,而放青稞的利息为百分之十五(一年借二十筒,年利三筒),借期为六个月。就放青稞一项的利息收入,约合4654.8石,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松赞林寺仍掌握着约十万斗青稞。[7]而银钱债则因为不需要抵押而在民间盛行,直到解放初期,寺院的银钱借贷系统在民间仍然有重要的影响。“银钱债则是月利二分,年利二十四分,向喇嘛寺借贷一般不需要抵押品,有子在寺内做喇嘛的比较容易借,借的时间和数目好商定。”[8]寺院的高利贷由于其被赋予的神圣性和特殊性,而遍布于云南藏区的各地方及各阶层。
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为保护寺院利益,促进寺院在地区中的政治经济影响,颁发了一系列特殊法规和执照。允许松赞林寺运用寺院基金经营商业,并对寺院经营的产业免征税收。在这样的条件下,松赞林寺寺院商业异常活跃。“僧商从西藏购来卡叽布、手表、靛蓝、黄十字香烟、毛毯等印货及西藏氆氇、褥子、金边帽、麝香、鹿茸、黄金等货物,或转口丽江、下关、普洱、保山,或在中甸销售。入藏货物有茶叶、红糖。珠宝、火腿、粉丝、白酒、木碗、铜器、铁器、瓷碗等。从中甸运往丽江、鹤庆、保山则多为皮毛、麝香、虫草、贝母、竹叶菜、酥油等等。”[9]由于云南藏区连接滇、藏、川的有利地理位置,松赞林寺成为了三省贸易的中转站,僧人经商的现象蔚然成风。自清康熙年间至清光绪年间,松赞林寺僧人形成三十多个财物集团,九十六万元的资金(半开),还拥有2300多头骡马进行商业活动。
自松赞林寺建寺之初,在格鲁派的直接引导和清朝的政策支持下,成为云南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从其经济来源及构成情况而言,数目巨大且种类繁多,渗透在由高至低不同社会阶层之中。对于财产进行管理、分配和运行的要求,催生了松赞林寺内部严密的财产管理机构。
二、清至民国时期松赞林寺寺产经营管理方式
松赞林寺作为格鲁派寺院,其寺院建制仿照拉萨格鲁派三大寺。寺院内部由都康(扎仓大殿)、吉康宗喀巴大殿)、祝康(释迦牟尼大殿)、扎拉菊(护法神殿)、八大康参、活佛静室、僧舍等构成。寺院的最高组织为扎仓大殿,在大殿的周围分设八大康参。
西绕嘉措曾在《松赞林寺史略》中对八大康参进行详细介绍:“八大康村:东旺(gter-ma)康村,亦名赞桑康村(btsan-bzang),位于寺院东头东旺康村的僧人,除法事外,长于经商,因此该康村为寺中富有康村之一……扎雅(brag-g·yab)康村。位于寺院西头,四层楼,楼顶有金铜所制屋脊宝瓶、佛幢、牦纛……独客(rdo-mkhar)康村。位于扎仓左侧,紧靠扎仓。四层楼,面积仅次于扎仓,独客康村建得最早、文物最丰、势力最强……吉底(rgyal-sde)康村,亦称昌都康村,与昌都强巴林寺有密切关系,该康村位于寺院南边,即金瓦殿前方,面积小于以上诸康村;该康村的特点是供奉昌都帕巴拉活佛像……卓(vgang)康村,位于扎仓前方,三层楼、面积小于吉底康村;楼顶装饰与吉底康村同,有一部丽江铜版《甘珠尔》被视为寺宝,但在历史上的一次战乱中遗失……乡城(cha-phre)康村,在扎仓左前方,属中等康村,楼顶装饰和各种文物器具与青底康村相等……荣多(yang-thang)康村,位于扎仓和独客康村正前方,规模与独客康村相近,楼顶装饰和法器、唐嘎、经典等与东旺康村相等……龙巴(rong-pa)康村,位于扎仓东侧,即独客和乡城康村之间,规模与荣多康村、东旺康村相仿,各种装饰、法器、经典、唐嘎等亦大体相同。”[10]康参下一级组织为密参,密参仍按僧人的籍贯编组,几个自然村的僧人组成一个密参,密参是寺院中最基层的组织。
而在低一层级的组织康参内部,收入不需要上交扎仓可以在内部进行分配。康参内主要由格干管理康参内部的行政、经济、宗教活动;康参念哇主要管理康参内的高利贷业务,在康参内担任念哇也是日后竞选扎仓之下觉夏、西苏念哇、聪本的资本;聪本,即康参内的僧商,利用康参内的高利贷利润等进行商业活动,为康参谋利。
当问及“你知道超市中商品上的条形码表示什么含义吗?”时,国际贸易专业55%的学生表示知道,市场营销专业84%的学生表示明白;当问及“你知道如何来评定茶叶的质量吗?”时,国际贸易专业42%的学生表示知道,市场营销专业79%的学生表示知道如何评定茶叶的质量;当问及“你知道如何来鉴别涤纶、锦纶、腈纶吗?”国际贸易专业12%学生知道如何来鉴别这几种纺织纤维,市场营销专业46%的学生知道如何来鉴别这几种纺织纤维。
寺院堪布为松赞林寺的大掌教,秉承主寺活佛行使宗教事务大权。在堪布上任后,从各个康参中指定嘎尊1人,念哇1人,聪奔1人,仲译1人,组成大寺最高权力机关“洛章会议”的常务机关,处理全寺行政、经济、宗教及外交方面的日常事物。洛章念哇主要负责征收70户“拉迪”(大寺掌教处供养户)的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并通过洛章的资金来进行商业和高利贷业务。洛章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洛章的日常开支,以及每年夏季和冬季由堪布主持的两次法会中,提供全寺僧人的伙食。
觉夏是松赞林寺内扎仓下设专门的财产管理部门,由第哇2人,念哇2人,聪本8人组成。觉夏主要负责征收300户“吹迪”(僧众供养户)的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领取政府的各项补助并颁发定额僧人的皇粮。觉夏念哇和聪本通过觉夏的资金和粮食进行商业和高利贷业务。觉夏负责扎仓全年的日常开支,包括每天提供僧众的三顿酥油茶,以及扎仓内的灯油开支等。除此之外,觉厦每年要交给扎仓的两个扎玛(扎仓炊事管理员)232驮酥油;觉夏念哇和聪本每人每年需聪奔每人年交酥油8驮(每驮25饼,每饼2斤),念哇每人年交酥油4驮,共计72驮。[11]
西苏原为管理寺院公共财物收支机构,主要管理农牧饲养、印经等事务,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松赞林寺内与觉夏组织并行的机构财产管理部门之一。机构内设第哇1人,念哇1人,聪本8人。西苏念哇主要收取属寺①的贡赋,并专事高利贷业务和商业活动,为松赞林寺聚集财富。西苏承担每年正月举行的默朗钦波(宗教祈愿大法会)时,全寺僧人的生活开支。西苏念哇每年交酥油4驮, 聪本每人年交酥油8驮,计收68驮。
在清朝“金字招牌”扶持下,松赞林寺僧人在都康、康参领导下进行经商、放贷等活动,寺院逐渐成为地区内最有权威的经济实体。服务于寺院的马帮、商铺汇集于松赞林寺附近的村落中,久而久之这一区域便成为了整个县城中最为繁盛的街子,至今仍为称为“小街子”。在寺院的僧人群体内部,原生家庭富裕的僧人,依靠家中富足的供养消除了维持生活的负担,并且能够在一次次学衔晋升的过程中,完成一次次花销甚大的供养。原生家庭财况普通的僧人,在出家后完全靠寺院度牒份额及家中供养生活,若想要求学或供养上师,仍然捉襟见肘;家庭贫困的僧人则只能在寺院中承担杂物,维持自己在寺院中的生活,与真正出家人学经修行的生活相距甚远。原生家庭的状况以及封建时期寺院的学经制度也成为促使僧人经商,参与商业活动的重要原因。据寺院中老僧们回忆曾经的壮阔场景“寺院马帮的头骡已经进了康参的大门,尾骡依旧遥遥无法望见。”当年的场景已无法细致统计,但寺院主持下经济一片繁茂的景象至今仍可想象。
NF-κB信号通路在肾间质纤维化发展的作用研究……………………… 李 瑞,郭玉娟,范晴晴,等(1·43)
在封建王朝时期由于政治特权的保障,松赞林寺成为云南藏区最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实体。其内部享有供养户上贡的赋税,对外又进行各种贸易活动以及高利贷等经济行为。巨额的财产数目催生了不同层级的财产管理部门,将寺院经济的发展推向下一波的高潮之中,特权政治的保障促发了财产部门的发展,财产部门的运行又为寺院的政治话语权提供了稳固的基础。但与此同时,财产管理部门虽一定程度上发挥职能,但内部管理仍然存在明显缺漏。大宗的公共财务收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使得寺院财产管理部门成为各个康参竞争的“肥差”。仅靠“在佛祖面前起誓”等行为来保证贪腐行为的避免,仍然说明寺院对财产管理部门监管的缺失。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寺产管理发展
自松赞林寺建立直至新中国成立民主改革年间,松赞林寺内部一直维持着两级财产管理部门的运行。时代的变革对于寺院的发展而言,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新中国建立后的民主改革将松赞林寺寺院经济财产管理部门,推入了“先破后立”的阶段中。
民主改革的实行,对于松赞林寺旧有的政教、经济等多个方面的特权制度进行废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性作用。松赞林寺不再是云南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中心,由松赞林寺老僧、当地老民和土司构成的“吹云”会议制度②,完全被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制度取代。③
松赞林寺逐渐完成由政教中心向纯粹宗教场所的转变,寺院内僧人数量由1955年所统计的1329人减少到1959年的336人。寺院经济也在这一时期发生重大转变,僧人划归到不同公社中参加劳动。以1959年松赞林寺的农业生产情况来看,僧人共开荒477亩,种青稞、小麦、荞子三类作物共产2582斗,净重77461斤,当时寺内共有僧人353人,每人平均分218斤,没有牲畜也没有其他副业。④寺院供养以及实物地租、劳役地租被取消,聚积财富的放贷业务被取缔,导致了寺院内部特权经济全面崩塌,原有的两级财产管理部门逐渐萎缩但依然存在。时至1963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宗教以及宗教职业人士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对象,云南藏区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松赞林寺财产管理部门随之消亡。
(一)1982年宗教政策落实后的寺院经济管理部门重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和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国家政策的制定,民间宗教信仰活动逐渐趋向正常,奠定了云南藏区境内藏传佛教寺庙的恢复和重建的基础。在国家财力支持、当地信教群众的捐助以及僧人自食其力下,对“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松赞林寺进行复建。
1982年,松赞林寺克斯活佛担任管理小组组长,湎英则担任副组长,并从八大康参中,各自推选出一名代表,最后由政府任命成立寺院管理小组。寺院管理小组三年一任,可以连任。最初成立的寺院管理小组不仅负责寺院重建、僧人管理的具体事宜,还包括寺院重建经费的筹集、寺内的财产管理等所有事务。
复建初期的松赞林寺百废待兴,随着寺院收入的恢复成立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财产管理部门。这一阶段寺院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国家对宗教组织启动国家财政赔偿。主要针对寺院的建筑、宗教器物和僧侣个人住宅和公私财物被没收的进行退赔,人民公社、生产队等无偿占用寺院公私财产的进行退赔,并将原来属于寺院的草场、经济林等承包给寺院使用;政府和相关部门资金和物资的支持;信教群众的捐助;以及寺院僧众参加劳动所得。
重建阶段的松赞林寺褪去了所有封建时期的特权,作为新时代的宗教场所,寺院内部财产体量相较于政教合一时期无论种类、数量都要精简得多。新成立的寺院管理小组仅对寺院内部事务负责,寺院内部财产也由寺院管理小组任命的会计和出纳负责。
在1984年至1989年间,松赞林寺在各方支持下逐渐完成扎仓、文殊菩萨殿、以及八大康参的复建工作。随着松赞林寺规模逐渐扩大,寺院财产收入来源中,除上述组成部分外,信教群众供奉的香火钱⑤成为寺院财产主要构成之一。复建工作完成后,寺院进入到正常运转阶段。寺院管理小组规模也相应完善,寺院管理小组由寺院管理会代替,成员由松赞林寺活佛、在任堪布、八大康参各康参两名代表(卓康参和乡城康参各一名代表)组成。寺院管理会(简称寺管会)具体负责寺院建设、僧人管理制度制定、寺院财产管理等事务。
任务链:任务型汽车英语教学中的任务并不是孤立的。教师设计任务时要考虑前后单元和整个课程的总体要求,注意内容的顺序和衔接。比如客户接待、汽车介绍、购车推荐、价格协商、签署合同这些单个任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任务链,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汽车销售能力。因此教师选择活动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活动的复杂程度和难易程度,还要考虑活动的主题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跳出单元限制,在模块内合理调配和组织,建立活动的内部联系和前后衔接关系能够确保语言课程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二)新时期松赞林寺的财产管理机构形成
松赞林寺除享受流官政府所定额发放的香火钱、衣单银等之外,还有权在云南藏区直接收取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即寺院收取的草地税,按所产的酥油形式缴纳;高山牧场税按牧户乳牛产奶旺季最高日所产的酥油、奶渣缴纳;山场林地租税按每年每户缴纳一驮或几驮柴为数。实物地租还包括松柴、青草、干草、栎柴、红土、白土、蔓菁、牧马费、信差费等。劳役地租则由每个村轮流负担,主要为寺院扎仓和觉夏从事扫地、扫雪、背水、刷墙等杂务。高额的政府拨款和物产收入为松赞林寺发展寺院经济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除去正额收入外,松赞林寺还利用寺院累计的青稞、银两等进行放贷。寺院的高利贷业务成为了累积财富的途径。
3.2 普通高校的师资力量有待提高,专业的定向运动制图人才需要大量培养,以满足学生对定向运动的专业人才需求。
4.宋·淮南马并《游金庭观》:“右军学业隐林丘,世隔年馀景尚幽。苔锁一泓残墨沼,云遮三级旧书楼。欣逢羽客开金阕,快睹仙童侍玉旒。自怪今朝脱凡骨,飞身得向洞天游。”[7]2427
在“以寺养寺”口号的号召下,松赞林寺通过旅游业发展与寺院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2007年4月,成立了松赞林寺景区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属于国有企业,主要对松赞林寺为中心的松赞林景区,进行保护、开发、经营及管理。在景区公司成立后,每年景区门票收入中的22.5%返还给松赞林寺寺管会,成为“以寺养寺”的重要经济收入⑥,也是现阶段松赞林寺财产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
同时,景区现代的运营模式为松赞林寺的财产管理制度规范化也起到了影响作用。在景区公司的引导下,寺管会建立新型的财产管理制度⑦,松赞林寺财务管理制度参照机关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进行,设立对公账户。所有寺院款项由对公账户收入或支出。并将增加会计、出纳为各两名。在财务处理过程中,寺管会主任、会计、出纳分别设有账本。在寺院的日常支出中需要寺管会主任、会计、出纳三方签字后有效。在寺管会明确财务管理制度,有利于合理分配寺院经济收入,制定合乎寺院经济发展的经济活动计划,并使寺院经济收入能够合理地分配、消费,使寺院能够正常运转,并开展宗教活动。
各个康参财务系统相对独立,康参的收入主要由康参内部的香火钱为主,康参内僧人轮流值班管理香火钱,康参内部由格干、各巴(老僧)对香火钱进行分配。随着现阶段松赞林寺各康参僧人数量增多,信众供养体量增大,康参内部也依照寺院现代财产管理机制进行改革。以独克康参为例,独克康参在2010年开始进行重修,由康参内僧人担任建设指挥长,但所筹得建设资金由所辖教区成立财务管理部门,严格按照机关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进行,财务并不由僧人管理。
为了解上海市崇明区的肺结核疫情特征,分析疫情变化走向,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本地区肺结核防治策略提供依据,现将上海市崇明区2016至2017的肺结核疫情分析如下。
新时期现代财产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寺院民主管理机构的深化发展,两者并行促进了寺院的综合发展。随着财产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相应加快了寺院内部制度化管理的进程。
四、余论
(一)松赞林寺财产管理机构的时代性特点
在藏历第十一饶迥木虎年,也就是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中甸发生了当地以噶玛噶举派寺院为主的地方势力反对和硕特部蒙古统治的乱事,这实际上是一个教派之争的事件,也是松赞林寺建立的根本因素:“迨至木虎年(1674年,康熙十三年)由巴塘方面加以重视,寺院更加兴旺。继而由于嘉夏寺(嘎玛噶举寺院)为首的建塘僧人等自取灭亡,反对西藏法王(指固始汗),恶意制造事端,祸延整个康区噶举寺院,深受罪孽惩罚。继后,红坡寺、德钦寺、奔子栏大雁湖寺(今东竹林寺)等少数僧人也卷入事件。”[4]格鲁派立即调派青海和硕特部台吉率领的蒙藏部队进入中甸平息,噶玛噶举派等其他教派僧兵在战斗中一触即溃。教派变乱平息后依五世达赖喇嘛之命,云南藏区境内红坡寺、德钦寺、东竹林等数十座噶举派、宁玛派及苯教寺院全部关闭或改宗格鲁派,并解散僧人,各派寺院财产没收并集中于筹建当地格鲁派的第一大寺院——噶丹松赞林寺。
民主改革完成后,寺院经济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松赞林寺的一切宗教、政治、经济特权废除,寺院原有的财产管理部门也在民主改革后进入了“先破后立”的阶段。而进入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寺院不复存在,寺院财产管理部门化为乌有。
松赞林寺逐渐发展为云南藏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寺院建制规模宏伟、僧人数量庞大。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独立经济体,松赞林寺财产大规模累积,在这一时期寺院内部也形成了严密的财产管理机构。都康作为全寺最高机构,统管全寺佛事活动、形成最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决策,领导全寺八个康参。同时,在内部设有专职的财产管理机构,对寺院财产、经济进行统一分配管理。康参作为相对独立的寺院构成部分,内部存在一定数量大小不一的经济团体,康参内部的经济组织相对于寺院的扎仓来说相对独立。松赞林寺寺院财产管理部门主要分为两个层级的组织。最高一级组织依托于寺院扎仓而建,内部有洛章会议机构(也称作喇章)以及觉夏、西苏为构成部分;较低一级为康参内部财产管理机构,此机构较为灵活,建制模仿觉夏、西苏,管理康参内部财产并不受扎仓管辖。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后,松赞林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型寺院。寺院在政府相关部门、信教群众等的支持下,完成寺院重建工作。并在寺院内部进行民主管理,设立规范合理的财产管理部门,对寺院财产进行有效、合理地分配,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从松赞林寺财产管理机构变革看寺院管理制度的变革
寺院财产管理机构作为寺院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在不同时期、背景下的变革也反应了寺院制度整体的变革。在封建王权阶段,松赞林寺是区域政教合一的中心,无论在宗教或是政治、经济上都占主导地位。这一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寺院内部财产管理制度的高度的自主性和稳定性。松赞林寺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实体,其发展方向对于整个地区具有主导性作用,内部的财产管理机构的产生和发展都服务于寺院本身的政教中心地位。
而自封建王权时期直至民国,松赞林寺都持有各项特权并保持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而当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的阶段,松赞林寺财产管理机构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变革本身是被动性。特权地位以及特权财产构成的覆灭使寺院被迫转向改革,财产管理机构的萎缩也折射出了寺院在新阶段无法适从的状态。在紧接着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寺院内部一切机制最终消亡。
而在新时代松赞林寺重建完成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寺院内部以财产管理机构为代表的制度变革呈现出了主动性的特点。寺院在“以寺养寺”的口号下,寺院成立了松赞林寺景区保护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财产收入来源上实现多元化,并引进财产管理制度,在原有制度上加以改革并完善,形成了新时代具有寺院特色的财产管理制度。从财产管理制度的变革也反应出寺院整体在新时代背景下变革的主动性。
(三)新时期对寺院财产管理制度的启示
松赞林寺从建立之初成为云南藏区政教合一的中心,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后最终形成了寺院财产管理制度的转型。而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松赞林寺的寺院财产管理制度调适具有启示意义。
一是完善财产管理机构的健全,有利于以寺院财产管理机制的健全带动寺院整体的发展;吸收寺院原有财产管理机构组成的精粹,完善改革成为健康、透明的新型财产管理机构,使寺院内部保持活力和动力。同时,以寺院内部财产管理的合理化促进僧人内部民主管理等深层改革的落实,带动寺院内部整体的良性循环。
二是在完善财产管理机构健全的同时,协调寺院在宗教场所功能与经济收入之间的平衡;在贯彻“以寺养寺”政策,扩展寺院财产收入的同时,根据现代财产管理制度的科学管理,对寺院经济发展作出规划并合理分配使用财产,将寺院宗教场所的功能放在重要位置,注重传统并安排相应佛事活动,着重协调经济收入与宗教功能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松赞林寺在中甸境内还有两个属寺百鸡寺和大宝寺,两个寺庙本不为格鲁派寺庙。在1674年迪庆境内藏传佛教教派叛乱后改宗格鲁派,并成为松赞林寺属寺。
②“吹云”会议,为统治全体僧俗人民的最高组织形式,会议每3年召开一次,商讨行政、宗教、军事有关的大事。
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信息化资源具有信息容量大、智能化、虚拟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于延伸感官、扩大研修规模和增强研修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网历经十几年的资源积淀,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的课程资源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补充,有的课程设计者挖掘教材中存在的“空白”,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的网址,推荐网上下载的文献,以弥补教材的“不足”;有的课程设计者将西城区教育研修网作为资源平台,组织教师开展主题研讨,利用视频案例资源进行网络研修,分享教学设计、课件及研究成果;还有的课程设计者充分发挥常规研修和网上研修相结合的优势,为教师校本化和个性化的自主研修提供便利。
首先,各地方BIM联盟为各地方政府BIM政策及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大量智力支持。其次,凸显企业在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采用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人才引进等方式,提升了企业BIM应用能力。第三,通过示范项目总结应用经验,通过宣传推广提升行业影响,通过交流培训培养人才,不断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最后,结合各地优势资源和工作基础,促进了各地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联盟成员分工合作和有效衔接,如通过建立BIM实验室、开展校企合作等方式整合资源建立共性平台,推动了产学研各机构在战略层面紧密合作。
③对松赞林寺进行改造的方面包括:破除寺院土地、森林、牲畜等生产资料的封建所有制,以及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制度;推翻对于人民群众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消除寺院的封建管理制度,如管家制度、等级制度、处罚制度和大小寺院的隶属关系等;不再允许寺院内私设法庭、监牢和刑法,干涉民事诉讼等多个方面。
推进管理会计在全面预算管理中的整合,还应该注重将企业的管理会计、预算管理以及绩效评价体系系统的整合,通过企业全面预算分解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明确企业的阶段性目标,根据企业战略目标的推进实施,对企业经营发展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掌握分析,同时设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准确的掌握全面预算的绩效情况,进而以绩效考核为企业的全面预算执行情况以及目标完成情况提供准确的依据。此外,还应该将绩效考核情况与企业内部的奖惩机制挂钩,更好的促进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目标的实现。
④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工委统战部:《中甸县归化寺历年农业生产情况》,1964年3月,此数据为2017年调研时所得。
以各个消费项目的人均消费支出与各个产业的人均GDP之比作为基本指标,分别构建和谐模型的标准指标体系和实际指标体系。
⑤松赞林寺的香火钱来源主要是扎拉菊、文殊菩萨殿、扎仓以及百鸡寺、大宝寺两个属寺。香火钱由“康桑”(值班僧人)保管并在每年固定的日子上交寺管会,再由寺管会统一分配支出。“康桑”每年一换,在上交年度香火钱时,需在大殿佛祖前起誓,保证香火钱已如数上交。
⑥在景区的经济收益办法中提出:一是以寺养寺费用;二是松赞林寺僧侣学习深造费用;三是奖励基金,即对寺院管理和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僧侣给予深造费用。资料来源:香格里拉县松赞林寺管理局《工作手册》,2007年;2017年6月调研所获资料。
⑦一是为了使寺院集体财产、宗教文物、法物不损坏和流失,使物资财产妥为保管和使用,今后无论大寺、各康参、所属各殿值班以及堪布,寺管会换届交接都必须按照本规定执行;二是寺院财产包括房产、文物、法器、供品、经书、经卷、唐卡、佛像、塔以及日常生产生活用具和一切宗教设施和旅游设施;三是物资财产实现专人保管,合理配置使用,做到物资财产的安全使用,防止流失或被盗,特别是宗教文物法器。物资财产必须造册登记,实行明码标价,说明物资财产的来源,时间年代,财产归属,配置地点以及使用或保存状况等建立详细的物资财产台帐,主管人员一年内必须向寺管会报告物资管理及基本情况。换届时必须进行清仓核资,办理交接手续;四是建立物资财产借还制度。凡属寺院物品借用必须在本寺范围内,不得随意向外人租借寺院物品,本寺内租借物品必须按时归还,如有损坏照价赔偿,并收取一定的租用费;五是寺院财物购置必须建立协商制度。购置1千元/件以下的物品,由主管人员请示寺院财物主管批准,1千元至1万元以内,由寺管会集体研究批准,1万元/件以内,由寺管会集体研究批准,1万元/件以上的经寺管会研究后报经寺管会主任批准。香格里拉县松赞林寺管理局:《工作手册》,2007年6月,此数据为2017年于松赞林寺管理局调研时所得。
参考文献:
[1]李钢.踏寻雪域遗珍·迪庆藏族自治州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纪实[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2.
[2]冯智.明至清初云南藏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J].中国藏学,1993,(4).
[3]阿旺钦侥.木里政教史(藏)[M].鲁绒格丁,等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4]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驻昆办事处编.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藏文和译文合编)[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003:175.
[5][7]七耀祖,西洛嘉初.中甸噶丹松赞林概述[A]//迪庆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迪庆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Z].昆明:昆明西站彩印,1990.
[6]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60.
[8]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编辑组.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102.
[9]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甸县志[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660.
[10]杰当·西饶嘉措.松赞林寺史略[J].中国藏学,1995,(2).
[11]绒巴扎西.近代云南的藏族寺院经济[J].云南社会科学,1999,(1).
作者简介: 次仁卓玛(1991-),女,藏族,云南迪庆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7级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族社会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