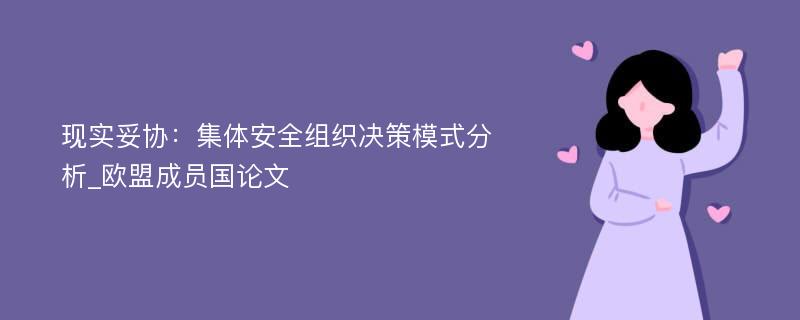
向现实妥协:对集体安全组织决策模式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论文,现实论文,模式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单凭一个国家的能力很难应付可能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于是在安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只要存在共同需要或利益的地方,我们就能发 现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成员国牺牲部分主权参加国际组织,原因之一是希望可以从中获利或避免独自承担损失的风险。例如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是为了使本国融入世界经济,享受自由、公平的贸易秩序;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了规避汇率、金融风险等等;参与联合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安全,降低安全成本。作为现有国际社会中最高层次的政治系统,国际组织的作用和权威是通过其积极参与国际关系、解决现实问题而体现的。对于成员而言,参与这一政治系统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其决策以权威形式分配有价值的东西”。(注: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页。)由于国家理性显然是希望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国际组织的决策,掌握利益的分配,它们的围绕权力安排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在国际组织的制度上,所以其决策也往往是利益权衡的结果。现代国际组织的体制设计虽然受到日益普及的民主观念的影响,但在核心决策权的分配上,权力结构的影子依然清晰可辨。本文选取了集体安全组织,试图通过对其决策模式的历史发展、沿革的分析对此作一说明。
一、国际组织的决策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组织是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国际行为体。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名义上它能够不受其它行为主体的支配和控制,独立做出判断和相应决策,(注:Richard W.Mansbach,The web of World Politics:Non-state Actors in the Global System,Englewood Cliffs,NJ,Pretice Hall,1976,pp.3—5.)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组织的权威来源于主权国家让渡于它的部分主权。由于现有国际体系承认并尊重各国的平等,所以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非常看重平等的价值,力求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然而,国际组织不是世界政府,由于仍然缺少一个核心的权威,国家自然差异很大,利益考虑的出发点各不相同,而且是由国家独立、直接做出决策,所以要在各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公意”就具有相当的难度。国际组织的生命力与其对成员的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否及时、迅速地对事态做出准确、适当的反应。因此,国际组织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权力配置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也就是国际组织在核心问题领域的决策。
国际组织的决策是从国内社会治理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从没有脱离国内政府的影子。只不过,国内决策中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官僚机构等等被单一的、相似的、由它们组成的国家所取代。相对于国内社会形形色色的个人或利益集团而言,国家及其行为的相似性要大得多。在今天国际组织所规范的重大利益中,国家是最复杂的“单位”,它们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和协调造就了国际组织的重要决策。与国内社会相比,在形式上国际组织决策的公共选择过程也许更民主,因为:首先,名义上平等的国家都可以独自根据“国家理性”参与决策;其次,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象在国内决策中仅仅凭借纯粹的行政优势而取得对一项决策的垄断地位。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社会的等级结构较国内社会更加鲜明。在纯技术领域的国际组织中,国家可以靠科技进步、创新性或先发优势垄断某项新技术、新工艺的标准而在此类组织中获得控制地位;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国家可以借助经济实力,为该组织提供的“公共货币”的数量获得优势;在国际政治、安全组织中,拥有强大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的国家显然是此类组织行为的规范者以及目标的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即使是在一些纯粹以某种道德诉求为基本目标的非政府组织中,其关键成员的背景也决定了究竟是何种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在其中起主要作用,而且在这样的组织中非道德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因为隐蔽而更具欺骗性。更为重要的事,国际组织的决策是不同国家(集团)、不同的利益之间的权衡。在许多问题上,国际组织不需要考虑所有国家的建议或方案,而只要考虑到当事国以及有相关利益的大国或地区大国就可以了。这些国家才是把握组织决策的关键性变量,因为它们的观点不仅将影响到该组织的决定,还将影响到这个决定的执行,也就是决策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现代国家体系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而国际组织由于高度浓缩了国际社会,所以权力结构——国家在特定领域的实力对比直接塑造了特定的国际组织的决策。
美国学者本尼特认为:“只要没有一种既不同于主权国家,又拥有权力或手段,作出或实施能够影响大多数国家决定的机构,那么世界上许多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处理。”(注:A.L.Bennet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Principles and Issues,Prentice Hall,1991,Vol.4.)国际组织的出现代表这种努力的一个成果。不过,人类不可能脱离国内社会治理的经验和逻辑,凭空创造出一套国际社会的治理模式。集体安全被视为无政府状态到世界政府之间的中继站。(注:Inis L.Claude,Jr.,Swords Into Plowshares:The Problems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ew York:McGraw-Hill,Inc.,1984,p.246.)它希望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其核心是建立国际联合并以集体的力量保障和平的理念。(注:黄惠康:《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跨越边境的对安全的协调和管理,是现代国际组织的滥觞。集体安全的思想虽然着眼点是安全领域,但是它的触角往往涉及到国家利益的许多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体安全的制度发展为现代国际组织,以及国际事务的系统化管理奠定了基础。但是,国际组织在国家传统利益范围内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挑战国家长期形成的、排他性的权威,其难度可想而知。通过对集体安全组织在微观层次上的观察,我们将能够再次领教权力观念的深刻影响。
二、集体安全组织决策机制的演化
集体安全的孕育与发展趋势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即与政治现实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最初不切实际地强调“平等”到渐渐侧重“效率”。反映在权力安排上,就是决策权掌握在谁手中。
1.早期的理想化设计
但丁在13世纪所设想的“世界帝国”(注:《论世界帝国》是从英文版转译过来的中文书名,但其拉丁文书名应为《君主论》。参见但丁:《论世界帝国》[M],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出版说明第4页。)显然是对“罗马治下的和平”的渴望,但丁对罗马帝国情有独钟,设想中的世界秩序也是君主制的。此后很少有人敢于大胆地设想帝国式的国际治理模式,因为但丁过于理想化的设计在1648年以后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中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有莫顿·卡普兰设计的国际系统模型中的“等级统治系统”才与之有某些相似之处。
但丁之后,孕育中的集体安全的决策体系大多突出了民主与平等。无论是选择国家还是以民族为基本单位,它们都是以来自所有成员国或按人口比例选举的各国代表组成的一个普遍性机构为其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策。杜布瓦、克吕舍的欧洲联盟方案、亨利四世的“大设计”以及圣皮尔的“欧洲和平备忘录”都是如此。这个权力机构不但要负责立法,而且要对国际争端做出裁决。显然,早期的设计并没有考虑到或者说忽视了国际政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对国际组织行政的设想几乎是设计者对其理想化的国内政治制度的再现。不过在18世纪以前,这些设想无一例外被人斥为空想。只有佩恩的欧洲和平计划提到应根据各国的领土、贸易等典型的构成一国“权力”的指标决定一国在国际议会中的席位,这实际上是有限制的国际民主,是对事实平等的修正。这种意见此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2.设计思想的修正
19世纪中直至国联成立之前,许多可以称为集体安全雏形的设想都不再以纯粹平等为基础。布伦奇利与洛里默的欧洲联盟方案就不约而同地区分了大国和小国,前者设想在联盟的所有机构中大国的投票权几乎都是小国的两倍;而后者则给定了大国拥有的投票数,规定小国的投票权由大国根据小国的国际地位来决定。这显然是向现实妥协的结果。权力分配“大国化”倾向的原因是17世纪以来的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欧洲的命运实际上就是由大国支配的。国际组织的方案设计如果忽视这个现实,注定将不会取得成功。
一战前后的“和平主义”风潮对集体安全的完善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个时期,酝酿中的国际组织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欧洲组织,组织的设计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符合国际政治的实际,国际组织的独立政治人格逐渐摆脱了对国际法的依附。组织内法律与政治功能的划分逐渐明晰,政治功能的独立性越来越突出。也许是由于所谓的民主国家增多的缘故,在对国际组织的设想中,对国际法、道义、民主的热衷相比于一、两个世纪以前似乎并没有丝毫的减退。但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和欧洲的方案,我们就能发现明显的不同。可以这样说,欧洲保守重实际,所提方案更现实;而美国对欧洲的“权力政治”充满不屑,所以理想主义色彩较浓。(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27、33、207—227页。)其中的“美国保障和平同盟方案”和欧洲的“费边社方案”就体现出这个特点。它们几乎设想到了构成以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所有主要机构,但是后者却突出了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8个国家的地位,无论是在代表机构、执行机构、司法机构中,大国都将占有优势。
3.向现实妥协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普遍性集体安全组织诞生的催化剂,不过它却是美国与欧洲两种观念混合的产物——欧洲希望以此重塑均势,而美国则可能真的希望建立一个体现“全人类利益的共同体”。但是,国联的建立过程足以显示出人们指导思想的混乱,凡尔赛会议设立了58个委员会讨论各种问题以便使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关注,但是最终决定会议方向的却是最高委员会的五个国家。在国联的组织设计上,美国的观念占了上风,联盟无论大会还是行政院都是一国一票,而且所有投票的效力都一样;惟一能突出大国地位的仅仅是它们在行政院中拥有的常任席位。掌握集体安全决定权的是体现“代议民主”精神的行政院。其成员除了几个大国以外,剩下的都是由大会选出的,而且行政院的所有理事国都有完全平等的一票。对于非程序性的决议,任何一票反对都可以产生否决作用。长于权力计算的欧洲政治家是不甘于同其他国家一道分享权力的,于是体现国际社会民主的国联毫无效率可言,它长期以来只是一个摆设,真正在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仍是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调。
国联的决策机制几乎不可能使其对任何重大的安全问题做出决策,这是理想主义的一个深刻教训。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众多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有重大意义的组织几乎都摒弃了类似国联行政院体现完全平等的民主决策模式,而代之以有限的平等——即在民主决策的旗号下,根据本组织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选择对本组织有意义的指标来对国家在组织内的权力分配进行指导和调整。在这些组织内,一国一票的平等原则大多只有形式上或道义上的意义;真正起作用的是国家的实力,而且它将通过法律的规定融入组织的运行机制中,在决策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护另一种形式的平等。联合国集体安全的决策模式就是其具体体现。
三、现实的选择
否决权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响应。不过,作为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组织,要保证在国家最敏感的安全问题上做出决策,并保证决策得以落实,经验证明这是惟一选择。联合国在集体安全事务中起主要作用的机构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大会采取一国一票,一般提案简单多数,重要提案2/3多数的原则,这是联合国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不过这一民主模式显然因为大会只有建议权,最后的决定权和行动权掌握在安理会手中而减色。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按地域选出的成员国代表构成,其表决方式是有限制的多数原则,所谓的限制就是常任理事国在非程序事项上拥有否决权,显然在关键性问题上大国将握有主导权——联合国不可能通过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大国的提案,而能够得到它们支持的提案无疑将能够期望得到贯彻。这使得联合国集体安全的决策制度显然“贵族化”了。
哈斯认为,“个体的政治忠诚取决于他对机构功能发挥情况的满意程度。当国际组织负有国家的大多数功能而行为者又可以同时向几个机构表现出忠诚时,那么他才有可能对国际组织表现出忠诚”。(注:E.B.Hass,Beyond the Nation 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tanford,1964,pp.49—50.)这也许可以作为对国际组织的决策模式从“理想”到“现实”回归的一个功利性的解释。因为,人们数百年来对国家的忠诚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转移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实现人们基于相同的种族、血缘、法律的认同而获得的权利、安全感、满足感……因此,在国际政治中,“效率”成了检验国际组织存在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国际组织必须服从于权力结构的塑造。于是,决策权的配置也就成为确认该事实的一个明显证据。
因为安全只是国家利益之一,由于安全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这一范畴具有较强的特殊性;而且,全球性组织所能够获得的忠诚度往往是最低的,所以单纯考察集体安全组织也许会被认为有失公允。然而,应该注意到:首先,集体安全的发展脉络最为清晰、完整,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就是现代国际组织的起源,为现代国际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模型和参照;其次,自集体安全组织出现以来,国际组织才逐渐在国际关系中崭露头角,成为参与利益角逐的一个重要行为体;第三,安全是国家最看重的利益,其中的斗争更容易反映国际政治的结构,这一点能够在集体安全组织中得到深刻体现;第四,广义的集体安全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安全概念,它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的一个阶段,是同一定的经济、社会相联系的,集体安全组织的目标是成为世界协调的中心。因此,选择集体安全组织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即使选取其他的国际组织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下面就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国际组织为例进一步予以说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国际金融秩序,其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与联合国不同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衡量各国决策权的标准更为直接,就是“金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表决模式是典型的“加权表决制”。根据各国认购的份额,在规定每个成员国一定数量的基本投票权——保证每个国家起码民主权利之外,再依据各国认购的份额数增加该国的投票权,份额越多享有的权力越大。在执行董事会的表决中,每个代表投票权的大小都与其对应的国家或地区的份额总数相联系。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面上绝对多数的民主原则——一般需要2/3、3/4甚至4/5的多数才能通过,显然成为对权力结构的最好粉饰。因为在执行董事会的15个代表中,有7个国家因为其实力可以单独派出代表,做出决策需要的多数越多,这些国家越占优势。
欧盟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程度最高、职能最全面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理论上,区域组织成员属性比较单一,相互渗透的程度较高,组织整体利益与成员国利益容易达成一致,所以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相对而言最高,区域组织实现民主决策的可能性也最大。不过,经验证明它仍然不能摆脱权力的影响。欧盟组织机构的设置是以西方宪政体制为蓝本的。虽然直选的欧洲议会赋予欧盟以最高的合法性,但是国家主权的身影依然清晰。具体表现是,掌握欧盟最高决策权的是欧洲理事会及其委员会。(注:S.Stavridis (ed.):New Challenges to the EU:Policies and Policy Making,Dartmouth Press,1997,pp.72—76.)委员会的20名委员中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各2人,其他国家只1人。委员会的构成并非反映权力结构的最典型特征,因为尼斯首脑会议已经决定未来各国只派一个代表。另一个依据是欧盟的表决模式。欧盟理事会通过决议的方式有“协商一致”、“简单多数”、“特定多数”和“一致同意”。“特定多数”适用问题范围最广,各国的投票权也不同,英、法、德、意4个国家最多,其他国家依次递减。(注:目前是英、法、德、意每国10票,尼斯会议重新确定的是每国29票。选票分配详见冯仲平:“从尼斯会议看欧盟一体化发展趋势”[J],《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期。)适用“简单多数”和“一致同意”的时候,虽然每个国家都只有一票,但是前者只适用于程序问题;而对后者需要关注是其内容,它涉及共同外交和防务等国家的核心利益问题以及最重要的几个国家各自最关心的问题。正是因为大国的坚持,“一致同意”才能够继续在各国认为对其重要的利益范围内继续发挥影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尼斯会议上“特定多数”适用的范围得到扩大,其原因不在于增加决策的民主性,还在于担心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因为“一致同意”而影响欧盟的决策。此外,拥有最大合法性的“协商一致”其运作过程中,究竟哪些国家的意见将决定决策方向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联合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欧盟,虽然总体上其决策制度的设计都刻意体现“民主和平等”,但是一到权力分配的时候,一切的虚饰就被剥去。它们的表决方式虽然大体上都是“加权表决”,但还是有很大差异——其中所蕴含的民主和平等精神在逐步递减。除了一定的权力总是与一定的义务相联系这个解释之外,可以给出的解释还很多。组织内部成员国同质性越强,民主的气氛也就越强。以西欧国家为主组成的欧盟成员显然更平等,更民主,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区域性组织大多倾向于选择一国一票、协商一致或多数表决的决策模式。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垄断性并不比联合国安理会差多少,但安理会的大国特权却处于众矢之的的位置,原因何在呢?首先可能是各国在心理上对这两个国际组织的依赖程度不同,其次与它们的主要功能不同有关,第三是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一定金钱相挂钩的表决权相比,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显得过于突兀,过于霸道;最后可能与人们对这两个组织的期望及其发挥的实际作用之间的差异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了对极权的恐惧,使民主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国际联盟的教训也使国家明白了权力政治的现实。于是,新成立的主要国际组织似乎非常重视“民主”与“效率”的结合。战后国际组织的成功就是国际组织在决策方面的成功,这多少证明了权力的现实逻辑。就其决策模式而言,就是强调决策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结合。赫尼格将西方政治中的合法性定义为“不仅包括统治和决策的有效性,而且包括其公民在生命和利益受到影响时对统治的接受程度”。(注:J.Henig: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Butterorths Press,1972,p.171.)建立在西方政治理念基础上的国际组织,其合法性也可以从这两个层次来衡量:一是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法律承认以及该组织决策的有效性;二是国家对国际组织信念的忠诚,以及对不利于己的决定的服从程度。对于国内社会来说,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可以是“君权神授”、精英阶层的同意或者民意;相对单一的区域性组织的合法性可以是“出于共同需要的同意”,也可以是民意;但是现阶段,集体安全组织合法性却只能是其成员出于共同需要的同意。当国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参与国际组织的时候,也就对该组织的合法性予以了确认。但是在第二个层次上,国际组织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不要说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领域了,即使是对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敏感问题,国家接受国际组织的决定的程度都经常大打折扣。关键原因就是国家坚持主权不肯让步。为了增加决策的有效性,国际组织大多选择了从民主理念上后退而向“权力结构”妥协,除非它能够确定其成员对组织的价值追求有共同的认同,以确保国际组织的合法性。于是,这就导致了战后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组织的核心决策模式无一例外地建立在权力结构的基础上。集体安全的理想虽然对国际政治中的主权国家拥有高度的吸引力,但是终究不能脱离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