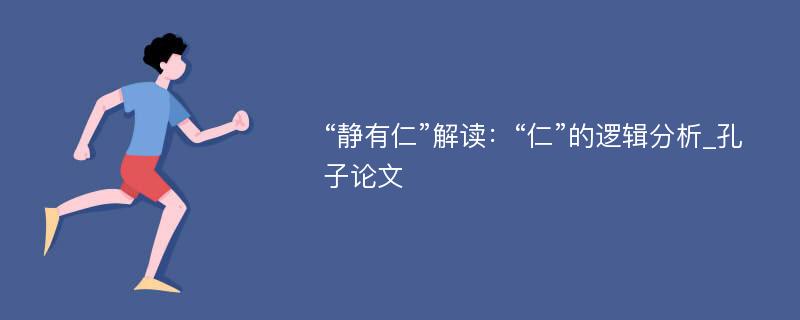
“井有仁”释——“仁”之逻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井有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如西方那样的“逻辑学”,但如果广而言之,我们不把“逻辑”解释为“必然性”或“固定形式”,而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说,逻辑是一种可能、一种视野。那么,我们在仁的视野中能看到什么?在我们传统思想——仁的思想中,虽然没有主客性、分析性和因果性等范畴,但仍然有其自身的视野。从孔子“井有仁”的论述中就能看到这种视野式的逻辑。原文如下:“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1]这显然是一个设为情景,我们把这样的情景称为“境遇”。在这样的境遇中,我们看到:1.“仁者”非人人之称,必有“仁者”、“无仁者”和“不仁者”之分,而“仁者”是以“无仁者”和“不仁者”为背景,所以仁者才成为众人的告难对象。2.“仁者”必有所担当,即“仁”必以一定的责任义务为内涵,否则何必告难于仁者。3.宰我设为此境遇的问题是,仁者担当责任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是否有告必应?若有条件,条件范围是什么?4.仁的本质是什么?为何孔子对如此具体的仁之行为未做正面回答?等等。从这一简单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产生这样的推论:仁的视野中包含着仁之所属,仁之意义,仁之困惑,及仁之本质等方面的内容。
一、仁之所属
仁之所属是君子。从孔子的言语中直接把宰我的“仁者”的称谓换为“君子”即可证明:所谓“君子可逝也……”但是,君子何许人也?仁如何从属于君子?首先,在《论语》中,君子的原坯应是日常俗人,即未从血统、种族、宗教、政治及经济等社会关系方面予以规定和限制,而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中的人之一员。但君子也是孔子所说的这样的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可以为仁,关键在一个“欲”字,人生几多欲,惟欲“仁”者为君子。由此可知,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既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又有对现实的领悟,即“仁”属于“人”,不是什么高不可攀、超出血肉之躯的神仙行为,凡有能力选择所“欲”之人,均有可能选择做仁人,一念之中,斯仁至矣。君子就是欲仁之人,若人人所欲皆为仁,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会到来。所以孔子倡导仁并未针对特殊者言,而是对人人而言。但是日常俗人不可能人人欲仁(为何如此,不在本文讨论内),这也是孔子所清楚的事实。尽管一般而言“为仁由己”[4],非为外界所驱,从而为所有人敞开可能,实质上只有有志于仁者才会走上通往“仁”之道路,才可能成为君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5]虽然原坯是日常俗人,但“欲”的内容不同,“志”的方向不同,就成为君子与非君子的区别。所以仁首先属于志于仁的君子,属于君子之“志”。
其次,一日志于仁就能成仁吗?显然不是。仁应是君子的终生皈依,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6]。但是,仁非事物,往往格而不致;亦非知识,经常学而不成。“巧言令色鲜矣仁”[7],“色取仁而行违”[8]亦非仁,仁是行,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9]。而这个“行”首先在于自我修行——因为仁属于君子之志,所以就要求君子自我先行,实质是心志先行,这就是修行的本质。所以孔子说要“克己”、要“居处恭”、要“出门如见大宾”、要“刚毅木讷”[10]等。这里所要关注的一点是,尽管心志先行是修行的本质,但“行”不是钻研,不是面壁,而是道路,仁的心志要通过行为来养成,没有行为不能成仁。所以曾子的三省才是以“谋忠”、“交信”和“传习”等行为为对象的反省自律。实质上,在《论语》中处处体现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1]的精神。所以仁属于君子的修行。
第三,君子的修行必须显现出来。仁的存在方式不是个人性质的,而是社会性质的,社会生活是仁存在的家园,仁这条道路是走在他人、家族和邦国之间的。所谓与人要敬、要信,与家要孝、要悌,与国要忠,与民要惠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2]尽管孔子对颜回困于陋巷不改其乐予以肯定,但那仅是对固守仁的心志的肯定,而不是仁的意义的发挥。仁若发挥意义,就必须将仁置于社会生活当中,即君子的修行必须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在孔子的时代,这个社会生活的范围就是他人、家庭和邦国。所以仁属于君子在社会生活中的显现。
故而可知,仁之初始属于君子,属于君子的心志、修行和社会行为。因此,社会生活中有仁者存在,并与无仁者(日常俗人)、不仁者(小人)区分开来。仁之可能范围系于君子的心志行为的可能范围,惟君子承担仁、施行仁,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宰我关于“井有仁”的命题正是在这个自明的前提下,设为一个告难于仁者君子的境遇。孔子虽然感到难以正面回答,但不能否定这个前提——君子是仁的所有者、发出者、施行者。
二、仁之意义
仁之意义就是“是人所是”。因而仁之思想与认识论思想中“是物所是”的目的迥然不同。“是物所是”即通过正确的认识(是)达到发现事物的规律并遵循规律(所是)。“是人所是”则意味着君子据他人之所需而成他人之所求,所谓“君子成人之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3]。所以,仁之思想的实质是这样两个方面:修仁与施仁。修仁是指仁之载体应如何获得仁,而施仁则是仁的发挥与显现,体现着仁之意义。所以说“非礼勿视”只是“为仁由己”的表现,虽大可称道,但毕竟仅是修身。要显示仁之意义则必须行仁,这就是孔子所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道理所在。行仁不仅是仁之意义所在,而且必然构成一种关系。但这种由仁而非由认识构成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由这种关系又使仁之意义具体地显现为一种什么样子呢?即要说明“是人所是”为仁之意义,必须回答下述三个问题:“是”者何人,“受者”何人,“所是”何事?
首先,何人去“是”,显然是君子。但君子在施受关系中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是“师—官”合一的身份,即君子要实行仁,就要使自身具有师长或官吏的身份,师长有德行才能教人,官吏有权威才能使人。在《论语》中孔子虽未直接明言君子是“师—官”的身份,但在仁之关系中处处体现着这一身份的特征及重要性。“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14]君子修己居仁,居仁的目的是为人,为人就是教人、导人、使人,这就是施仁。以敬、恭、宽、信行于人中,成为人群中的榜样;以孝、悌行于家中,成为家族中的榜样;以忠、敏、惠行于国中,成为官吏中的榜样。这个榜样并非只使人看,而是教人做,如此非为“师—官”者难以为之。所以即使没有现实的师长、官长之职位,仁者君子也是自我设为“师—官”,求为“师—官”。“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5]没有一定的社会名分的基础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即使圣者如孔子,也有待沽之叹。人们常说儒学是入世哲学,为何是入世哲学?怎样入世?一言以蔽之,仁之意义必须在施受关系中显示出来,而施仁、行仁则需要以一定的社会身份为基础。“师—官”这一身份是仁之要求,是君子所固求。“子曰:‘苛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6]这正是走向仁之理想的惟一道路。从这个角度讲,孔子的仁之思想的意义之一就是造就了一群伦理上自觉的人,他们以自身的修养为依据,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也许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师长、官长之地位或名分,但却永怀一颗教人、导人、使人,最终惠人之心志。所以,宰我“人告之曰”的假设,是完全合乎仁之理的,仁者君子就应该成为告难的对象,由此,体现出仁之关系的特征之一。
其次,“受者”何人,是指仁之受者的性质。仁,一方是设为“师—官”的君子,另一方是何人呢?在《论语》中我们看到有两类划分,一是日常俗人,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7]中的“人”者是也;二是家庭和邦国,所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中的“家”、“邦”是也。也就是说,受仁对象可以是人之个体,也可以是人之社会组织。但是,不论是从个体着眼,还是从社会组织着眼,受仁对象都没有具体的社会属性,如马克思所说“人之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样,有以血统、种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具体的社会属性。仁者君子没有从这样的属性中选择受仁对象。当然,不仁之人和无道之邦是仁者君子坚决反对和摈弃的,所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8]及“邦无道谷,耻也”[19]。但在仁者和不仁者中间,尚存在一个“无仁”的空间,尽管《论语》中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区分,但施仁必须以这种区分为前提。如果只有仁者与不仁者两种存在,那么仁者只有杀身成仁一条路,而无“立人”、“达人”的施仁之路。所以我们用“日常俗人”这个称谓来表明受仁对象是泛泛的对象,“家”与“邦”的概念也类此。很显然,这是一个从广泛的伦理角度,着眼于当下现实社会整合为出发点的思想。
再从受仁者的处境来看受仁之人的性质。受仁者必须在一种需求仁的处境中才构成受仁的条件。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孔,天下归仁焉。”[20]事实上能够做到克己的只有君子,换句话说,除君子外天下古今之日常俗人均不能克己,这样,无礼时礼不能得到恢复,有礼时礼亦可能遭到破坏。因为不能克己可能扩张一己,势必侵凌他人、疏远他人,使人之关系,乃至社会关系瓦解,最终一己不仅不能有所立、有所达,也同样会受到损害。所以说不能克己便是无仁的基本因素。仁者君子以克己的方式,以立人、达人为施仁的原则,满足日常俗人已立、已达的需求,从而构成受仁的基本条件。在这样的一个宽泛的条件中(甚至是无条件的),人人都可以,甚至人人都愿意接受仁者君子的仁爱。因而在宰我提出的“井有仁”的问题中,告之者、落井者的身份属性可以不计,在这样宽泛的受仁对象中,人人可以告难,这是仁之关系的特征之二。
第三,“所是”者何事,是指在施受关系中仁之形成。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从施仁角度看,既然仁有博施博爱的性质,那么“所是”之事就不会是一件具体之事,而是一项原则。证明有二:1.《论语》中对仁的表达往往举出具体之事,如孝悌、恭敬、言讱、处约乐及刚毅木讷等。但这些是仁的构成而非仁本身。事实上,正因为仁不是诸事之一,才能使符合这一原则的诸事显现出来。仁,作为君子的处世原则其本质表现为担当,所谓“当仁不让于师”[21]。这里的“当”解释为承担、担当,即为人、为家、为邦国承担仁之责任,因为无仁是普遍存在,所以不复辞让。这种担当责任绝非仅是解病痛、救灾难、济贫穷等具体事可以囊括,而是一种总的责任。2.从宰我关于“井有仁”的质询中表明,这个具体境遇的设置,其前提则是,若仁是具体之事,则不无疑难;而仁是一个总的责任,是君子的处世原则,才产生如何与具体之事结合、处置的问题。宰我正是依据原则而责问老师仁怎样在具体事件上体现。实质上,古今论仁都自觉不自觉地将仁当成一项原则来思考。
二是从受仁角度看,“人”是仁之方向,立人、达人、爱人、敬人、信人及惠人等等,都表明仁是使他人有所成、有所立或有所益,即仁的功能是指向他人而非自身。君子是仁的载负者,在他人所求、所欲的道路上行进;君子是仁的扮演者,在他人所求、所欲的舞台上演出,即通过成人而成仁是仁之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成人的方向中,既无宗教彼岸的世界,也无理想社会的摹画,而是在现实社会的具体境遇中使人受惠。忠、孝、爱、信等应表现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具体的对象上的具体的行为。所以,孔子提出的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中有“敏”一项,所谓“敏则有功”[22],大概就是要求君子要体察实情,即体察日常俗人之心,才能够实施忠、孝、爱、信之行为,才能够成仁。
三是从施受关系构成看,仁者君子如何体察日常俗人之欲而实践仁呢?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3]这就是说施受关系的构成,并在施受过程中,仁并不是根据一个完整的图式,如一种理论体系,一种社会模式的构想或一套宗教规矩等等,忠、孝、爱、信等并无具体属性,而是随所遇的环境、事件、条件及对象而定。这种境遇是一种具体的当下的社会存在现状,其范围可能很大,如家与国的治理;也可能很小,如亲戚、朋友之间的往来。所以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4]这里就把对待常人之态度与治国理家并为一谈。不论范围大小,境遇都是具体所遇,绝非乌托邦空想。因此在施受过程中,施者与受者的关系是以仁者君子推己及人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而且这种推己及人的方式,是在“能近取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说,施受关系是现实关系,这是仁之关系特征之三。
综上所述,从仁之功能——施受关系来观察,“是人所是”的具体意义表现为:造就了一批伦理上自觉之士,勾画了一个广泛的受仁对象,提出了实践仁的原则、方向和方法,换句话说,仁,就是这样显现出来的。实质上这是一条将仁的观念转化为仁的社会效应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由仁构成的关系实质上是行为关系,或者说形成的是行为逻辑,即仁者君子,用担当的行为,以近取譬的方式,满足日常俗人之所“欲”,这就是成仁之路。宰我“井有仁”的问题,就是对这个仁之行为逻辑的验证(其他弟子都是泛泛问仁,惟宰我设问检验仁),这里有仁者,有欲求(告),有近譬(井),仁者君子理应毫不迟疑地去从仁。
三、仁之困惑
众弟子问仁,孔子都做了正面回答,惟宰我问仁,孔子未做正面回答,为什么?因为众弟子问仁,涉及的是“什么是仁”或“怎么行仁”,属应然问题,而宰我的问题则是,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境遇,君子能否在这个具体的境遇中行仁、成仁。换句话说,依据仁之原则,仁从观念到行为有否必然性?它有确定的条件与确定的结果这种必然联系吗?有知识体系中那样的逻辑一致性吗?
表面看来,宰我的问题并非什么疑难问题,既然仁者君子的处世原则是担当仁之责任,那么他人有难理应予以解救,即使杀身也是成仁的光荣,为何有“逝”、“陷”、“欺”、“罔”的难堪出现呢?以至使后世儒者胡乱猜疑。但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知,仁作为观念上的原则仅是君子的心志,而仁若要显现、若成为行为则不仅是君子之事,必然涉及行为的条件与对象,困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仁的意义必然是仁的显现,而仁的显现则必然以具体境遇的施受关系为条件,宰我的设问,正是对这个关键所在提出质疑。
首先,仁固属于君子,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但仁的发出则需要一定条件。仁者君子自设为“师—官”之身份,以担当社会的拯救和教化责任。但是,“师—官”之身份能否得到承认或确认呢?这种承认和确认显然是仁者君子自身不能把握的,甚至是不可知的世界。孔子所说的“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中的“能”字,显然潜伏着对“不能”的担忧。“克己”对君子而言可以由己决定。“行仁”则非由己,以孔子之圣、孟子之贤终生求行仁之条件,惶惶于世,非无有愿,非无有恭宽信惠之品德,然而并无功名。所以孔子苦心提出“敏”为仁之一种,甚至孔子自己欲敏而行仁:“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5]这里的“坚”、“白”显然是辩辞,“系而不食”才是发自内心的忧叹。这就为后世儒者提供了借口,以“敏”求“师—官”之身份,名为仁者君子,却早丢掉了恭宽信惠之品德、之责任。仅西汉一朝,以经学为当世鸿儒、位居三公者如公孙弘、匡衡、韦贤等数人,无一“坚”、“白”者。[26]“敏”中包含着变通,包含着应和,所以历史上的仁者君子在社会实践中都处于两难境地:因“敏”而丧失仁之原则者有之,因固守仁之原则而困穷者亦有之。《论语》中孔子对奢华、僭礼但功业盖世的管仲说“如其仁”[27],对困守于穷巷陋室的颜回亦赞其“贤哉”[28],不正体现了在行仁过程中仁之原则和仁之功名的内在矛盾吗?即若求“师—官”之身份,或被“师—官”异化而失仁;若无“师—官”之身份,空有仁名,被世人逝、陷、欺、罔就会不可避免,仁之关系不能构成,仁之意义就不能显现。
其次,即使仁者君子具备了“师—官”这一行仁的前提条件,就能构成行仁的必然通道吗?仁的一头是君子,另一头是日常俗人,孔子搭建两者的方法是“推己及人”。但是,推己能否及人是值得考察的,因为这一方法的模糊点是“己”与“人”既同且异。君子之“己”必异于日常俗人,才构成“推己”及人的条件;君子之“己”必同于日常俗人,才构成推己“及人”的可能。按照《论语》对仁者君子的描述,君子是凡俗之身,即置身于当世的社会生活之中,而非超世的神灵或彼岸的使者;但仁者君子必有一颗圣贤之心,即是超越常人、克己博爱的人师民官。以常人之身体验、领悟凡俗之欲望,以圣贤之心疏导、教化凡俗之行为,这应是“推己及人”最理想的构建。但是,从仁者君子异于日常俗人出发,君子之仁是日常俗人所能接受的仁吗?从仁者君子同于日常俗人出发,日常俗人所求之仁应是君子应行之仁吗?何况“人”有不同等级、身份、利益、信仰等之区别。宰我的设问恰好切中了这个关键问题:施仁与告仁的矛盾。“虽告之曰‘井有仁’”,日常俗人说这就是仁,君子应答否?按照仁之所属是君子这一性质,君子是仁发出的根据,施仁是成仁的必然之路;按照仁之方向是日常俗人这一性质,常人所告是受仁的根据,解答告仁是成仁惟一道路。那么,何为仁之根据和判断标准?是君子的观念还是日常俗人的要求?在推己及人的道路上,似乎难以理清。因此,历史上君子与君子、俗人与俗人、君子与俗人等所言之仁、所求之仁、所行之仁各有不同。
第三,仁之困惑的基本原因,实质上是以行为关系为特征的“仁”缺乏确定的范围和独立的属性,因而不能以普遍有效的标准进行判断。在认识论中,事物的本质往往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或一定的条件下所独有的确定的特征,并能够通过“我思”的逻辑形式而把握的持续的客观存在。因此,事物才表现出规律性,认识者才有“是物所是”的遵循规律的行为。而仁则不然,没有确定一致的法则。依前所析,从范围方面看,在仁的观念中,其对象“人”是人之整体,即没有时空、属性等方面的差异;但在仁的行为中,其对象“人”则是人的具体存在,是境遇中的人,如“井”中之人。那么,从仁者君子的观念出发,以“担当”的原则,仁可适用于种种境遇。但实质上在仁的具体行为中,面对具体对象时,往往陷于某种境遇,或见欺于某种境遇。如,“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29]殷纣暴虐甚于虎狼,在这样的境遇中,这样的条件下,根本没有仁存在的可能,而与之讲仁,岂有不被陷害之理。这样的“井”必是陷阱。当然,仁之难行并非世人都如殷纣,更有许多现实之人从其自我的角度出发,对那广大无边的仁不能理解,无所需求,因而拒斥仁。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30]仁者本是爱人之人,担当责任之人,但在特定的范围内、条件下世人无所需求,仁无所意义,徒使仁者君子无所立身,无所适从。在这样的境遇中,无须有“井”,仁已被境遇所牺牲。从属性方面看,仁不是现成之事物,而是一种关系中的产物。而这种关系并非必然联系,而是系于关系双方的态度。态度一致,施受关系能够建立,仁能够显现,否则施受关系不能建立,仁不能显现。所以从施仁者角度,因其判断则有不施仁之行为。如,“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31]没有哪个统治者承认自己是无道之邦,但君子自有判断,故而避之。而受仁者也常常因其判断而远离仁,如,“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32]季桓子原初或想用孔子行仁,因女乐而变化,孔子不得已而离开。在施受关系中,没有认识论中那样主客分明的界限,没有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惟一的客观标准,而是恰恰维系于施受关系双方的态度,仁既不能单独属于君子(虽然由君子发出,但君子不能独立构成仁的意义),也不能单独依赖于日常俗人或某个境遇,而只能是双方“适宜”的关系,以及“适宜”的行为,仁才能够显现,才能发挥意义。所以,仁没有确定的范围,没有惟一判断的尺度,也就没有认识论中那样的逻辑性。故而君子之仁与他人所告之仁如“井有仁”也不能有必然的联系。
四、仁之崇高
仁之崇高是中庸,中庸也可视为仁的本质。只是这里的本质与认识论中“本质”不同。在认识中“本质”是相对于“现象”而言的。“现象”是指表面的、感知的东西,“本质”则是指概括的、规律性的东西。而作为仁的本质,中庸则不是指这方面的内容,而是指仁所操心的基本的和恒常的内容,以及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由于有了这样的操心内容,才有了如此理想状态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包含着崇高的倾向。
首先,谈基本的和恒常的内容。中庸者,“执其两端用其中”[33]之谓也。那么,仁所涉及的两端是什么?是“人之关系”的“关系”的两端。如,“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34]每一种关系都有相应的两端,但这里隐含一个前提,即只有在“关系”本身具有意义的前提下,关系的两端的保持才显示出意义。换句话说,仁所操心的基本的和恒常的内容是“关系”。由于人是社会性的共同存在,人先天也就存在于关系中,不论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实的人就是关系中的人。儒学把中庸称为天道或天命(“天命之谓性”)[35],实质上是指人之必然存在于关系中是不可逃脱的先天的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把“关系”设为先天的天命,维护关系的中庸之道才有理由被认为是天道。可以说“关系”是仁所操心的最根本的内容。
既然关系是天命,又何需要操心?又何以需要通过仁之行为加以维持?这说明在关系构成中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问题,时时危害关系,从而危害生存。《论语》中并未系统地论证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性,但从其中所提到的一系列现象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关系中的基本问题是差别——权力的差别,义务的差别。特别是在对君臣、父子关系的重视中,具有明显的对差别的关注倾向。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似乎表明,差别是固有的,总要有君,总要有臣,就像必然有父,必然有子一样。同时差别应是固定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就像父子关系一样不能调转。所以君的权力、父的威严天经地义,臣的忠诚、子的孝顺理所当然。当然君的责任,父的义务也同样不容忽视。可以这样说,儒学中关于“关系”的思想,不是指某种原则下(如基督教中在上帝面前)平等同一的结合体(逻辑上则表现为重言式),而是由差别构成的结合体。
仁所操心的内容是由差别所构成的关系的变动倾向,即虽然关系是固有的,关系两端的差别也是固有的,但差别的大小不是固有的,差别的转换是变动不居的。就像太极图中的阴阳结合体一样,阴阳双方不断消长、变换,特别是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更是社会生活中关系变动的生动写照。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藏着根深蒂固的变的思想,不是由特殊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由量变到质变或由谬误到真理的一系列过程,而是反复性变化。阴阳的结构不会变,但相互势力的消长、转换则变动不居。仁者君子认为社会生活中这种变动就是灾难。作为担当天下责任的仁者君子,能不操心这样艰巨的任务吗?因为日常俗人必然陷于关系中,必然陷于消长、侵凌、转换的冲突中(小人行为就是典型代表),必置关系于危险中(如己达而不欲人达),才需要超越关系的仁者君子担当仁责。
其次,仁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仁者君子所操心的内容是“关系”,其职责就是看护“关系”,其目标就是维持“关系”,更确切地说是维护当世已构成的关系现状而达到在世的安定。这里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当世性。不少人认为儒学有是古非今的倾向,实质上儒学重视历史有其原因。概括地讲儒学缺乏发展的观点,即在一种超现实的理想标准下对现实进行批判改造。儒学有的是因循损益的观点。“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6]因循在前,损益在后,如同父之传子、子之传孙一样。三年无改父之道,与因循损益的历史观是相吻合的。把关系对人之存在看成是一种天命,把社会关系看成是人伦关系的延伸,这样的历史观更像是一种自然历史观,而非理性历史观。那么,在这种自然历史观中当世性也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保持因循,才能保持稳定;保持因循,才能使损益顺利完成。仁,之所以有一个宽泛的、无所区分的受仁对象,与以当世性为根据,囊括了因循和损益两方面的历史观密切呼应,而与选择、批判的发展观相去较远。二是在世性,这里主要是指仁者君子所关心的领域是世间,即世俗性,而非彼岸世界、神灵世界或超越世界。日常俗人是恭宽信惠的基本对象,世俗生活是仁者君子置身的领域。那么仁者君子对于世俗的功名利禄等价值观,也是采取肯定的态度,只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7],而不是在神界的灵光下否定世俗的价值。对来世、彼岸或神灵世界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38]。仁的世俗性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安定性。儒学的历史观虽没有理想的发展方向,但却追求一种理想的状态,这就是安定。这里的“安定”意指人人恪守关系中的位置(君臣),享受应有的权利(如忠孝),履行应有的义务(如慈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39]。即从整体关系的稳定出发,通过克己的行为,使个体归属其位,达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安宁。
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这就是中庸,即以仁者君子的中庸之行为达到社会生活中的关系中庸化。所以,中庸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仁者君子的行为准则,其二是关系的中庸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因为仁者君子认为中庸化的社会依赖于仁者君子的中庸行为。即在仁者君子的看护下,以历史为平衡点,不使当世的行为过激;以恭宽信惠为价值观,不使世俗过分求利;以立人达人为导向,不使日常俗人过分沉溺私情。要调节这些关系,达到对立关系的中庸化,就要求真君子的真正的仁之行为既置身于关系之中,又超越于关系之外。素隐行怪,君子弗为,不偏激,不沉沦,中庸居之;在对待关系两端的冲突中,中庸待之,如尊君而限君,子孝而父慈的观点,即是教导双方达到平衡;在推己及人的方法中,中庸行之,既要择善而固守之,又要知言、知人、敏行,达到己与人沟通,以行仁道。实质上,以中庸为原则,仁者君子就是“公人”,不沉沦于任何一端。所以,中庸之为德,对仁者君子而言就是不断自我肯定又自我否定的困惑苦难之路,所以仁最终落脚于君子的修行是有其逻辑联系的,是一种必然的要求。这种以中庸为原则,在修仁、行仁和施仁的道路上通过不断自我肯定又自我否定的方式,以求达到风化世俗,使社会关系中庸化的目标,就是仁的崇高所在,也是仁的本质。仁者君子以“公人”的姿态出现,所以承担诸如“井有仁”之类的告难是其责任所在,孔子也未能有丝毫否定。但是,也正因为仁者君子是以中庸之道为行为原则的“公人”,在世俗关系中不沉沦于任何一端,因而不仅产生困惑,而且极有可能成为利害角逐者们逝、陷、欺、罔的牺牲品,如孔子所称的“殷有三仁”的遭遇。实质上,孔子对“井有仁”未做正面回答,也潜在包含着类似的忧虑。虽然如此,仍坚持“无求生以害仁”的行为,保持仁者君子崇高的思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