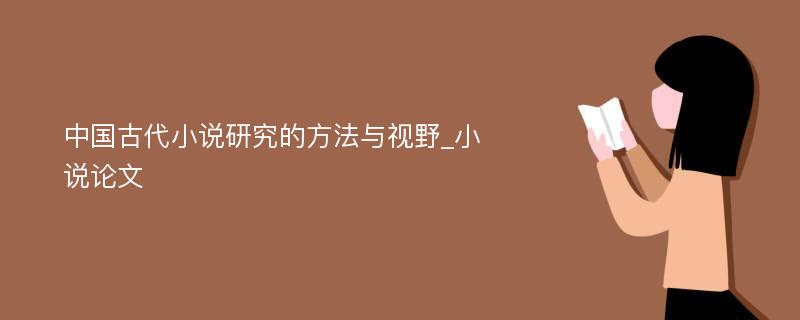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视野论文,方法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
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样,正处在变革与突破的前奏期,它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的极大勇气与高屋建瓴的极大魄力。正如近现代学者对古典小说研究的突破首先是对方法与观念的突破一样,当前的古代小说研究欲走出自我循环的窘境亦亟需方法与观念的突破,同时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也需要及时的整理与汲取。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向科学化、理论化、个性化迈进,从而在思维层面上校正自己的研究方向,为古典小说研究确立更高的学术标的。
关于小说史的撰述问题
这里所说的“史”大致有这几方面的含义:1.具体小说本事的流传发展及其与历史环境的相关互动关系问题;2.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它自身的分化与演进问题;3.支撑一部小说史的理论框架问题。这几个问题在更多的时候是杂揉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开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故的吴组缃先生有极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仅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是不够的,还要深入到野史、笔记等有血有肉的历史中去,“只有大量阅读当时人的野史、笔记,才能对当时社会历史、风俗人情、文化心理有真切了解”(注:引自齐裕焜《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百年学科沉思录》第3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事实上, 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示范性工作。例如对唐传奇的研究,陈寅恪、吴宓、刘开荣等人在三、四十年代即从唐传奇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唐传奇在题材与形式上所受佛教传经之影响、唐传奇与古文运动之关系等方面对唐传奇进行了视域广阔的研究(注:参见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287~29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又如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与陈大康《明代商贾与世风》二书以还原的方法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对于任何体裁的文学研究都是大有帮助的。无疑,今天的古代小说研究很需要借鉴这样的方法,从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许多问题用考证的方法不能解决,或许放在史的流程中反而能寻到答案。
关于小说文体的产生、演进及分化问题,除要钩索清楚各种类型的小说的源流、风格上的特征外,一些学者认为应格外重视小说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如文言小说与诗词曲文之间的关系,白话小说与戏曲创作之间的关系,小说批评与小说创作之间的相互推动问题,以及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相互转化问题等。深入地考察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在宏观的文学背景下勾勒一条血肉丰满、生气氤氲的小说演进之轨迹。
关于小说史应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框架问题,实际与文学史的撰述与研究关系极大。现代学者多用“进化论”或“因果律”来描述文学史的演化规律,这在观念上当然是一种进步。因为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上有一种独特的“文学退化观”,即“复古倾向”。这种贵远贱近的观念如不打破,文学史就无法撰写,甚至文学的发展也无从寻觅出路。但运用“进化论”或“因果律”来构造文学史也有问题,即二者都是在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却无法准确反映精神领域的活动历史。梁启超曾言:“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注:转引自《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由文言而白话,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势。但在描绘文学史或小说史的变迁中我们又必须面对这样的现象:即政论散文在秦汉兴盛,唐宋仍然不衰;小品文在唐末风行,却于明清再现光辉;文言小说兴于晋唐,颓靡于宋,至清代蒲松龄复臻于极致。这种精神领域活动中的跳动性与反复性无疑是文学史(包括小说史)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此外,对于建立中国独特的小说史学而言,不仅要考察文体演变与语言风格的转化问题,还存在着为形态语体各异、题材内容庞杂的古代小说进行理论上的界定与划分问题。学术界一致公认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一出即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除了当代学人陈平原所指出的“史识”与“艺术感觉”外,还在于其体系的科学与严谨上。如鲁迅将明代小说分为“讲史”、“神魔”、“人情”,将《儒林外史》归于“讽刺小说”,将《品花宝鉴》归于“狭邪小说”等,既不同于近代学者大贴西方标签式的作法,也不同于明清评点家常见的枝蔓芜杂而缺乏理论界定的分类,非常贴切而清晰。当然,《史略》一书也不是没有再发展、再提高的余地,除了因资料条件的限制与在所难免的个人疏漏所导致的某些结论推断不合事实外,在小说史内在发展的逻辑把握上与理论形态的建构上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总之,我们既应力求在可能多的资料发现与占有基础上客观地描述小说史的原始面貌,又要在多重线索与多维的交叉中为小说史的历史发展轨迹确立一理论主干与框架。这一工作当然是任重而道远的,所幸当前一些学者已在不同层面上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如分体的小说史、分题材的小说史与断代的小说史纷纷面世,整体的小说理论批评史著作也已为数不少,个别小说如《红楼梦》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史著作,关于中国小说研究史的著作已知的有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等。这一切工作的成绩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学者们终将奉献给世人一部博详丰赡、体大思深、成就卓著的中国小说通史。
材料考据与审美感悟的关系问题
自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科学研究的方法后,考证方法在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里影响深远。特别是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一扫昔日“索隐派”红学的牵强附会的谬误,确立了如何对《红楼梦》进行科学考证的门径与标尺,即“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应当说,在示范科学的研究方法上与开辟古代小说研究尤其是《红楼梦》研究的新局面上胡适居功至伟。但胡适的缺陷在于过多以材料的论证来代替全部的小说研究,对如《红楼梦》这样的作品的巨大美学价值与深刻思想内涵均缺乏应有的体认,以至于认为“《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猴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因此,“新红学”虽扫荡了“旧红学”,却并未在这历史学的研究基础上发生根本的变革。与胡适半师半友的俞平伯先生在很大程度上自觉地克服了这一缺点,如他认为《红楼梦》的创作风格是“怨而不怒”,就非常准确细腻,体现出一个文学家的修养。胡适的另一个学生顾颉刚曾在《红楼梦辨序》中评价他们的治学路数为:“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功。”标举以文学的观念来研究《红楼梦》,恢复其作为一部杰出文学作品应具的审美品位。
我们从红学研究史上的实践与争议中可以发现,古代小说研究必须解决好“文”与“史”的关系,考证与立论的关系,客观材料与文学感悟的关系。没有扎实材料基础上的考证,就没有确凿可信的立论;但如果只有考证,又可能陷入乾嘉学风的困境,缺乏宏观的史的眼光,也缺乏细腻入微的审美体验。当代一位学者就曾指出,古代小说的版本学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等综合素质的考验,直接涉及对作品内容与作者真伪的厘定裁决(注:刘世德《古代小说版本学的断想》,见《稗海新航》第4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意见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事实上一些卓有建树的大家也正是运用多方面的手段与依靠综合的素养积累在小说研究上取得了丰厚成果。
外来观念与固有学统的关系问题
古代小说研究受到重视始于近代,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小说为国民之魂”,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第一次在我国将小说分成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实际上已道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问题。但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缺陷在于一方面片面否定中国古代小说已有成就,另一方面又将所谓“新小说”的作用夸大到不合适的地步。这当然也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使然。在其前后如侠人、定一、陶祐曾等,一方面追随梁启超片面夸大小说的济世政治作用,另一方面在评价古代小说时又有着任意拔高、大贴标签的简单化毛病,没有以客观求实的态度研究古代小说,这也是由外来观念刚引入中国,尚未在更深层次上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实践结合的现实所决定的。
在引入西方观念研究古代小说方面取得实绩并具较大影响的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以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来印证“《红楼梦》之精神”,将作品与人生紧密地结合起来,既不同于蔡元培等以“考证之眼”读《红楼梦》,索隐本事,也不同于以往小说评点家的直感式的研究,而使小说研究具备了一些规范化、理论化的意义。特别是王国维将艺术区分为“优美”和“壮美”这两种美的状态,认为《红楼梦》即通过艺术地展现贾宝玉等人对生活之痛与情之痛的解脱,揭示出“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些见解无疑是超出前人,令人耳目一新的。此外胡适借鉴西方的“母题”或即“原型”理论,用史的眼光来研究《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也取得很大成绩。但综观这些前贤的探索与实践,不难发现其中也有不少不如人意处。如机械地套用某一种哲学或思想观念来观照一部几百年前的小说,削足适履之弊在所难免。一方面西方观念引入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有一个如何适应中国文学的土壤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西方文学批评的观念与哲学、美学思潮如何运用、如何与中国的固有学统相结合的问题。因为建立中国的小说史学与小说研究方法论体系是一个综合性大工程,包含着许多子课题。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文学批评系统中感悟式的评点多,逻辑性的推论少;又由于漫长的封建历史,上升到本体论、价值论的理论观念多为“原道、征圣、宗经”所笼罩,充满了“复古”与“拟古”的情调。倘若没有对西方平民文学的观念、文学为人生的观念及进化论观念的引进,从而对中国传统的“原道、征圣、宗经”进行一番反思和批判,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就无从谈起。当前的小说研究则在借鉴吸收国外新理论、新方法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如接受美学、语言学、结构主义等,加上“五四”时期即已广泛运用的比较文学、心理学、原型批评等观念,至少可以在古代小说研究的思维方式与理论视界上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但必须指出的是,“只有国学根基深厚又善于吸收世界进步文化的学者才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新学术流派”(注:黄霖、许建平《古代小说研究的大势与近观》,见《稗海新航》第14 页,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没有国学功底的严格训练,便谈不上对中国文学真正的研究,这种训练本身即包含有科学的因素,即一方面指对中国传统的经学、乾嘉学风在方法上的吸收与继承,另一方面指对中国传统自身蕴含的丰富思想宝库如儒、道、佛、宋明理学等学派的深深浸濡,从而为形成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中国文学研究与古代小说研究体系提供素养的积累。如果仅将时髦的西方理论观念简单地套入古代小说的研究之中,这只是皮毛的嫁接而决不可能深入到古代小说的思想底蕴,因而也无法为古代小说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研究者们应把握好外来观念与固有学统的关系,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追求与风格。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学习胡适、郑振铎等先生用西方的“母题”理论对古代小说还原、放大式的钩索与清理的实绩,力求真实地再现小说成书演变的历程;应学习萨孟武先生在研究《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长篇小说时表现出的社会学眼光与经济学头脑,具有一种犀利的思想锋芒。而另一个亦受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影响的李辰冬在《三国水浒与西游》一书中从作品来源的发掘、美感基础的阐扬与艺术造诣的批判这三个层面来分析古代小说,在一些局部问题上不乏新意与创见,但过于拘泥一种方法或体式,对于如《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名著而言是否仍嫌份量不足,尤其是作者自身的一些思想局限如过于强调所谓“资产者的意识”,究竟是否与历史现实、与著者原意相符,都很难令人信服。这里我们更欣赏鲁迅、萨孟武、孙楷第等人由小说及史的那种对中国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敏锐而深刻的穿透力。
在当前的学术界,古代小说的评价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许多一流的学者都很重视将小说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层面来丰富、开拓自己的研究视角与领域。从当前学术自觉与成熟的程度看,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会再有沦为诠释政治的工具的可能。可以说古代小说研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之中,但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拿出一流的研究成果,才不辜负时代与环境对我们的要求。而方法论的探索与突破正是尽快建构中国小说研究体系的必要前提。上述一些思考当然不能涵盖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的全部,但树立一定的原则与尺度,对于古代小说研究这样一个特殊的课题来说或可免思路窒碍、风格单调之弊,并时时保持一种敏感而永不满足的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