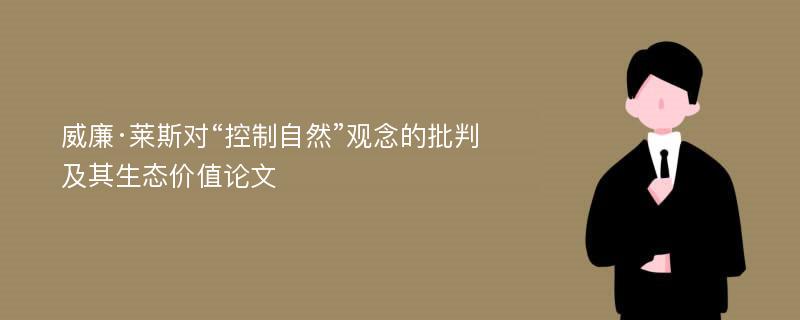
威廉·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及其生态价值
刘志清,苏百义
(山东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摘 要]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对“控制自然”观念进行了全景式批判,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造成了科学技术异化、消费异化,控制自然的实质是控制人,这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在当代全球性生态难题凸显的大背景下,威廉·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从多方面进行批判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关键词] 威廉·莱斯;控制自然;生态价值
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深入透彻地分析了“控制自然”的观念。“控制自然”观念起源于西方古希腊理性精神,是支撑工业文明的精神支柱之一,人通过理性可以认识自然、掌控自然,然后造福于人类。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进一步强化了“控制自然”的观念。为此,威廉·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控制人、消费异化及科学技术异化等消极影响进行了深入批判。
一、威廉·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
(一)“控制自然”观念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
威廉·莱斯深刻阐明:“‘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1]中译者序2在“控制自然”观念影响下,西方人从古希腊就开始了控制自然、征服世界的历程,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加剧了对自然的掠夺,从而导致环境承载力日益下降、资源约束趋紧以及生态危机持续扩大等生态问题。正如威廉·莱斯在《控制自然》中所说,人类曾以为地球上丰富的物质资源可以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乐观心态。人类不顾自然的承受程度而一厢情愿向自然伸手索取,这样控制自然肯定会造成人类获取资源与寻求发展希望的毁灭。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为自身生存适度去改造自然是人类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而过度控制自然、掠夺自然则会导致自然的报复,这是人类自我毁灭的途径,所以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对自然“服从”。人类不由自主陷入“控制自然”与“服从自然”的悖论。这一悖论根源于人的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矛盾。人的内部自然更多体现在自然生理需求上,也就是从人的肉体本性上来说的衣、食、住、行等生理需要。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基础上,才有了社会性的需要,即“外部自然”的需要。自然资源在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同时,也使人类在获得社会性需要的过程中得到符号性意义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人的灵肉矛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充分体现出来。威廉·莱斯认为,在控制自然观念中,将自然界作为纯粹人类的对立面来认识,这毫无疑问使人与自然相对立,不可避免地给人类造成诸多生态问题。“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意识形态,这种社会自觉地与过去作彻底的决裂,竭力追求推翻一切‘自然主义’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把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1]14
刘少奇于1932年冬离开上海前往赤都瑞金,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直至1934年10月长征撤离此地。由于他具有群众观点和全局观念,注重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善于把工会工作跟党和政府各项中心任务紧密结合,从而对革命事业多有建树,且留下了不少动人故事,兹选录数则以飨读者。
威廉·莱斯通过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梳理,得出了“在人类文明中首次出现控制自然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通过控制自然来控制人,从而实现其掌控世界的目的。
(二)“控制自然”观念的实质是控制人
威廉·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中曾说,发达国家正在自己的工业体系中测试生物圈存在的容忍极限。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极限具体是什么,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种道路走下去,达到或超越了生物圈的容忍极限才幡然醒悟的话,那时我们除了无法减轻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外,只能竭尽所能以灾难性的社会破坏为代价去把损失降到最低。“让人‘被逼无奈’的时刻甚至可能在我们还没有认真考虑之前就已经来临。”[5]120威廉·莱斯批判了人类造成的生态困境,为避免悲剧的发生,建议抛弃“控制自然”的观念,实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稳态经济模式,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在生产活动而不是在消费活动中获得满足,形成一种和谐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威廉·莱斯明确指出了消解生态危机的关键路径在于建构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这一观点对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威廉·莱斯指出:“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1]2实际上,就是将“控制自然”解释为一种人类自我控制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它的实现虽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但也从侧面给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积极启示。人类只有扬弃工业文明主导的“控制自然”意识,尊重自然,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困境。
其次,威廉·莱斯通过详尽阐述霍克海默的相关理论来解读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在逻辑联系。霍克海默强调“理性”成为一种为控制而斗争的工具是在启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类逐渐用疯狂抢占和掠夺自然资源、贬低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从自然界中获取超出人类自身所能享受的物质利益,这导致人类自身进一步强化了对外部自然的控制。霍克海默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阐发理性对外部自然控制与对内部自然的控制紧密地联系起来。伴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人类对自然控制不断加深,同时又造成对人的控制逐渐深化。对内部自然的控制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克己和本能控制。人类对外部自然的控制必然会逐渐侵蚀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撕裂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平衡,而对内部自然的持续克制就是要操纵人的意识及非理性欲望,并且对外部自然的控制和对内部自然的控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和不可分割的关系。威廉·莱斯强调,霍克海默将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紧密地联系起来,必定理所当然地把自然的反抗和人的反抗有机统一起来。霍克海默提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概念——“自然的反抗”来深入解析这一问题。威廉·莱斯认为霍克海默提出的“自然的反抗意味着人性的反抗,它是以长久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暴力反抗形式发生的”[3]。
广东盆距兰属盆距兰属(Gastrochilus D. Don),广东盆距兰区别于其他种的显著特征在于:植株下垂,茎较粗壮,叶镰刀状长圆形,长于5 cm,总状花序缩短,前唇光滑(封三,图Ⅳ)。我国广东、云南亦有分布。
(三)“控制自然”观念造成了科学技术及消费的异化
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是自然长期演化的产物,自然界先于人而存在,自然界对于人具有 “先在性”,同时,人的存在与发展又离不开自然,自然是遵循自然规律而存在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人们要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当然,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保留了人类的痕迹,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类要时刻牢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只有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才能根本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扬弃“控制自然”的意识,生态文明建设才是可能的。
威廉·莱斯指出:“物质生产越来越无限地发展,支撑这种发展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堪忍受:复杂的大规模的技术、较高的能源需求、生产和人口的集中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商品和花色品种日益繁多。”[4]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异化的消费生活方式,人们不得不在高生产、高消费中获得有限满足。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此创造更多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的多种需要,这是合理的、适度的生产和消费。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的数量和质量无限制、无休止屈从于满足人的需求。铺天盖地、琳琅满目的商品引发了人的消费欲望,刺激了人的贪婪,过度的消费奴役着人的灵魂和肉体,掩盖了人的真实需求,这就是所谓的异化消费。在异化消费的驱使下,控制自然的观念促使人类无止境地加强对自然的索取,生态危机在所难免。
二、威廉·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批判的生态价值
(一)尊重自然,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
首先,威廉·莱斯着重阐释了人类“控制自然”这种观念的负面效应。“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但使人们对自然的控制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又导致人们无法意识到人际关系中控制的存在”。[2]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终极目标不仅是要控制自然,而且还要将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视作满足人类无限扩张的物质欲望来加以占有和使用,把全部自然转变为生产原料。人类在“控制自然”观念引导下不断地激发自身的欲望,创造了虚假的生产和消费,他们竟然相信自己真的需要市场上供应的最新商品,致使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逐渐内化为合理的个人心理过程。强制性的消费行为破坏了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幸福,这种强制性意味着人控制自然的实质是人控制人。
为提高预测(分类)精度,降低误差,集成学习一般在降低平方偏差和模型方差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但是,一般来说,简单模型具有高偏差和低方差,而复杂模型倾向于具有低偏差和高方差[18]。
人类对自然控制的加剧必然导致对人自身控制的加深,从而导致人类非理性地使用科学技术,进而造成科学技术的异化。“不能将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与技术运用的合理性划等号。”[3]威廉·莱斯通过对代达罗斯故事的深入分析,得出科学技术不是造福人而是残害人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我们清楚地看到,剧毒、枪支、战争机械和这类摧毁性发明形成的行业已远远地超过了迈诺特尔所具有的残酷和野蛮。”[1]4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开展,科学技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发挥巨大能量。但在现今社会制度下,控制自然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其中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控制自然的重要工具,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的敌对的、异己的力量,对人类生活造成严重威胁和极其不利的影响,导致了科学技术异化。
(二)德法兼治,构建易于生存的社会
威廉·莱斯对“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分析之后阐明控制自然的实质是控制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在其全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控制的真正对象是人。”[1]1-2
3.3.1 重视需加强防寒。一些花卉在冬季寒冷季节易冻伤甚至冻死,做好防寒工作,有利于维护花卉品种。可采用将花卉转移至暖室或搭棚基本防寒措施。
如果人类社会只是按照资本逻辑进行生产和生活,忽视生态整体利益,对人类社会内部的公平、良知视而不见,特别是对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等深层的社会原因认识不足,从而导致对现存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弊端进行非理性维护,新的不公正也将进一步被创造出来,从而使最应该受惩罚者逃脱惩罚,最后也必然导致生态乃至整个人类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生态平衡也就无法真正恢复或重建。因此,只有德法兼治,彰显人类社会的公平与良知,从思想深处摆脱“控制自然”意识形态的困扰,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才能真正摆脱生态危机。
(三)科技创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未来大部分的科技创新,其目的将是协助实现这一目的,并与工业剩余废品在环境中积累的影响做斗争。”[5]129威廉·莱斯指出通过科技创新手段,降低商品在满足人类需要中的重要性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均能耗与物质需要,从而协助实现易于生存社会的目的,指明了科技创新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价值。
事实上,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一方面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则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健康。这就启示我们,必须要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创新科技、重塑自然,按照生态学的要求创建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3]刘美阳.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8.
[4] 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University of TorontoPress,1976:10.
[5]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M].李永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82( 2019) 06-0020-02
[收稿日期] 2019-09-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教学研究”(19JDSZK100)
[作者简介] 刘志清(1993-),女,山东高青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发展。
[通讯作者] 苏百义(1964-),男,山东泗水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农业生态文明。
[责任编辑:刘卫财]
标签:威廉·莱斯论文; 控制自然论文; 生态价值论文;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