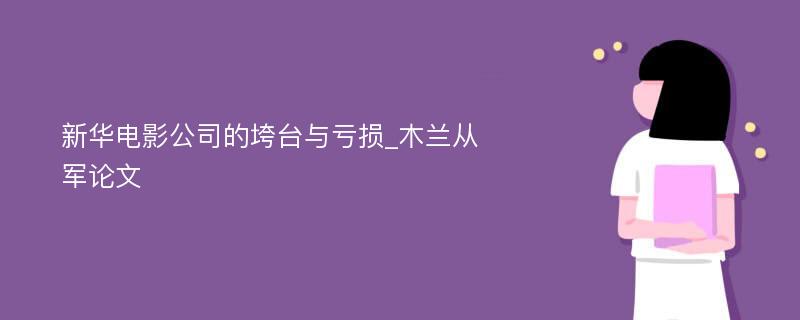
新华影业公司的沦陷与失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业论文,新华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孤岛”时期的新华影业公司接纳了众多优秀的电影人才,以当时雄踞上海电影业界之首的影业巨头的姿态引导了“孤岛”影像奇观的建设①。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早期电影已有的的类型片种的创作,同时也开拓了如动画长片等中国电影类型的崭新领域。为了生计而不可避免地,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众多电影也有讨好市场和迎合观众的敷衍之作,但是客观而言,新华影业公司整体上较好地延续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商业电影的脉络,并将之深掘和开拓,达到了一个电影公司在特殊时期发展的顶峰②。但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上海电影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用童月娟的说法,就是“我们也面临了抉择”③。 童月娟所谓的“抉择”就是要么与日本合作拍片要么彻底放弃的二元选择。其实早在日寇铁骑初入上海之时,就已显露侵吞上海电影业的野心。1937年12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电影组人员邀请“新华”、“艺华”等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宣布:上海各影业公司摄制或开映中国影片,事先必须到虹口东和电影院接受日军检查,通过后,可到日军占领区放映④。为了防备日本侵略者,张善琨把自己名下的三家公司均以美商名义重新在租界工部局登记注册。但是,日本和英美宣战之后,本来借着美日尚存的外交关系而托护于“美商”名义的中国联合电影制作公司这样挂着洋商招牌的电影公司,被日人视为“敌产”,反遭接管。当时,电影界的很多人只得放弃上海电影的资产,彻底不做了⑤。 日本方面屡次游说张善琨均遭失败,而这时负责上海电影接管事务的川喜多长政看到机会来临,就找张善琨谈话,这时张善琨躲避不了,只好见面。川喜多要他出来组织上海电影界,参加日方的电影机构。张善琨未作肯定表示⑥。 面对日本方面咄咄逼人的紧急情况,张善琨“找到了‘中统’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几位先生,请教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大家都走。如果我们再走了,就真的没有人做中国电影了,那么,上海电影界就完全属于日本人的,中国电影就完全缺席,为了保住中国电影的命脉,维持电影工作的任务,政府希望在电影界有人能做。”⑦根据童月娟的说法,张善琨为重庆方面做在上海的工作由来已久,“从日本人没有打进租界以前,重庆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就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善琨已经开始帮一点忙了……这样不断的帮忙,善琨也成了地下工作的一份子。因为有了这样的身份,他更要帮重庆方面在上海的工作了。”⑧从新华在沦陷后的表现来看,张善琨的确接受了“中统”方面的指示,新华影业公司在危机四伏当中“留了下来”,同时也开始了走向沦陷的路途。这其中固然无法否认张善琨在个人方面的屈服的原因,但是客观上,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脚,新华影业公司在上海电影史的撰述当中完全失落,并丧失了存在的立场。 一、个人经验与历史撰述 1939年3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部第四课长”高桥坦上校访问川喜多长政,其目的始于当时日本军要在“中支”,即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被日本军占领的地区通过电影想复兴民生并进行文化工作,将以设立一家电影公司。高桥就是请川喜多负责这家公司而来的。日本军之所以要选川喜多长政,一方面是因为进行人选的“内阁情报部”打听电影界领导层,他们大家全体一致推荐川喜多;而且川喜多是个中国通,中文非常好⑨。 川喜多后来在《我的履历书》上写当时的情况: 本来不想接受这项工作。因为我知道军部的方针和我的想法不一致。但,另一方面想如果我不去,到底谁去呢?要是那个人对中日关系没有信念也没有理解,他会听一部分的(疯狂)军人的话来做事。这样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因此,我提了条件:如果军部不要乱插嘴,大致上能够让我随心所欲进行公司运营,可以接受。(高桥)上校竟然全听我的要求了⑩。 川喜多长政此次到沪之时正是《木兰从军》在上海各家电影院线放映地如火如荼、大红大紫的时候。很快,日本计划用来控制整个上海电影业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影”)成立,“为了顺利地打开局面,川喜多没有在较为安全的日本人居住区虹口办公,而是插入孤岛,把办公室设置在位于共同租界的汉弥登大厦,开始进行中华电影公司的首项业务……而他看好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在孤岛舆论独领风骚的《木兰从军》”(11)。成立之初的中华电影公司成立时已拥有日本占领地区的电影发行权,日本方面的负责人川喜多长政想以《木兰从军》打开中华电影公司的发行局面,而他的文化中立的坚定态度也使得新华公司得以在物资生产资料充足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电影生产。当时川喜多长政对张善琨的承诺是: 第一,虽然无法避免日本军部审查影片,但如果审查过关,绝不改动影片的任何内容。 第二,提前支付片款。 第三,由于租界沦为孤岛后进口胶片困难,中华电影将从日本进口胶片和其他摄影所需的器材提供给中方(12)。 有电影研究者认为,川喜多长政的保证对于陷入困境的孤岛电影界来说,“无疑是有利无弊的。而张善琨向重庆方面汇报后,即接受了川喜多的条件。中华电影公司正式成立未满一个月,《木兰从军》就被运往南京做了特别公映,之后,该影片不仅走进了伪满洲和其他沦陷区的电影院”(13)。 以《木兰从军》这样寄寓强烈的爱国意识的电影打开了日军占领区的市场,日本的电影研究者认为,《木兰从军》之所以取得了那么的大成功,“这毫无疑义是民众借其故事想发泄他们的胸中郁愤”(14)。当时,由于《木兰从军》一片强烈的反抗意识,日军的审查果然发生争执,“军报道部(軍報道部)”支持放映,却“军事警察部(宪兵队)”彻底反对。结果“军报道部宣传班长(報道部宣伝班長)”、又是个小说家的伊地知进的主张:《木兰从军》和《教育诏书(教育勅语)》的一句“「发生紧急情况时,要对国家(社会)献给自己(一端缓急あれば义勇公に奉じ)」”的精神有相同之处,《木兰从军》是个爱国片;这终于使“军事警察部”同意了(15)。 川喜多把这部电影选为中华电影的第一放映作品,有他自己的意图——任何事开头最重要,他认为,放映《木兰从军》是对居住在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人民的最大服务。同时他肯定想通过《木兰从军》的放映让大家知道中华电影不是一家教条主义公司,如果中华电影不能放映《木兰从军》,会被中国电影界和中国人民抛弃。 但是随着时局的变迁,“中影”也慢慢朝着变成中日合资的“国策电影”发展,1940年12月25日,“中影”拥有了当时“南京政府”所赋予的独占发行权,范围包括了华中、华南、满洲与华北,掌握发行大权之后,“中影”进一步攫取了所有中外电影的发行大权,将发行“一元化”,然后开始集中全上海电影界的人力物力,实行全体主义的计划生产。 当时,日军已经全面占领租界,“孤岛”时期已然结束,“孤岛时期,虽然上海实际上已经沦陷了,但是租界里头表面上看起来改变不大;可是‘孤岛’消失,意味着新的制度也即将降临,新的拍片规则会出现——‘新华’要拍片,也将受到这个影响。更让我们担心的是,善琨早已经被日本人看上,成为统合政策中,一位来自上海影界、民间的‘中方’代表。这种事情实在让我们相当困扰。这样一来,可不像先前那样拍拍片子那么单纯了。但是真要继续留在上海拍片,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16) 除了童月娟女士回忆录里的一家之言,资深电影学专家余慕云先生透露,“中联”成立的内情和特殊情况或许可以作为相互佐证: 日寇攻占上海后(即日寇进占租界后),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军统头子之一的蒋伯诚和吴绍澍,分别在新华影片公司的负责人张善琨家中,召见留沪的中国电影工作人员,郑重指出,不要让敌人掌握上海的电影事业,让它像“满映”一样,大肆拍摄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媚日卖国电影。我们要把上海的电影事业掌握在我们手里。中国人要拍中国的电影。他们又说,张善琨之和日敌有了协议,日伪将不干预即将在上海成立的联合电影机构——“中联”,一切制片事务由张善琨主理。他号召大家都参加“中联”。张善琨也表示,“中联”绝不拍摄媚日卖国的影片。当时久困在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听了蒋伯诚、吴绍澍和张善琨的说话,相互交换过意见后,先后都加入“中联”工作(17)。 当然,张善琨是否是作为重庆方面的地下工作者在没有更详细的档案佐证的情况下,无法仅凭童月娟的一家之言做出定论,但是张善琨在与日本势力就上海电影业的周旋过程中的政治立场无法否认,尤其是在此过程中,重庆方面除给出“不能够撤退”的指示之外,并没有详细的斗争策略,而张善琨除了只能“一口否定”日本方面在整合全部上海物资和人员力量方面的希望而外,也提不出任何能够有效抵抗日本渗透的方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孤岛”消失。1942年4月,在川喜多的极力游说下,上海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孤岛”最有影响的制片人张善琨,在“保护上海影人”与“保存上海影业”的允诺下,终于答应与他一起“重组电影业”。由张善琨出面组织,新华、艺华、国华、华新、金星等12家上海的影业公司实行合并,改组为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联)。“中联”创业资金共计300万中储券,其中一半来自川喜多的“中影”,另一半来自新华、艺华与国华。于1942年4月10日成立的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由林柏生(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张善琨任总经理。从此,上海影业全部为日寇所侵占。 对于这一段历史,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史家和曾经与张善琨共同工作的电影业内的前辈都有自己的看法,傅葆石先生对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作过专题研究,从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地来审视上海沦落后的电影市场,对于川喜多长政的游说的详细情况,傅葆石先生有一番描述如下: 川喜多长政在支那派遣军总部报导部支持下,为使沦陷后上海的市面尽快恢复常态,力排华中派遣军各将领众议,宣布重开所有电影院,同时容许放映好莱坞电影(但当然没有新片上映)。川喜多长政相信“中国人只看中国人拍的电影”……他寻求中国电影工作者合作,因此他计划由日本管治,重组电影业。川喜多长政明白到要计划成功必须得到上海电影界有力人士的合作。 川喜多长政心目中的“有力人士”是新华电影公司的主持人张善琨。在谈到“中联”的崛起时,根据当时的上海日军报导部人员过久一记载,川喜多长政在“孤岛”消失的当天,连同其他“中电”人员如中国经理黄天始及黄天佐(此二人是自1937年便为日本人服务的影评人)往张善琨的影厂会见他。川喜多长政极力游说,为保存上海电影业,张应该积极活动,帮助他召集上海市所有的重要电影人开会。张善琨同意,并召集“艺华”及“国华”主持人一起参加会议(“国华”由资深导演张石川代表)。会议中,“中电”提出要中国影人继续经营电影,“中电”便提供资金及电影胶卷。此时上海已与海外市场隔断。资金、胶卷是上海电影业生存的命脉,但这三家公司只持观望态度。经过数月的软硬兼施,张善琨才答允“出山”……他同意与川喜多长政一起重组电影业。1942年4月,张连同12家“孤岛”电影企业组成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公司(简称“中联”),张善琨任总经理。官方的合并理由是“为了加强制片工作和对影人提供更大弧度的表演机会”。这个解释明显是生意术语,真正原因其实是把电影业中央集权化。“中联”实际是一家半官方电影公司,创业资金三百万中储券的一半来自“新华”、“艺华”及“国华”,另一半则来自“中电”。为表示公私机构的团结合作,11家电影公司的老板都在新公司拥有行政职位,汪伪南京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任董事长,实权却落在张善琨及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手中(18)。 定居在香港的陈蝶衣先生,是张善琨生前的老朋友,对张善琨为人和身世行状比较清楚。他在《张善琨先生传记:中国影坛巨人》一书当中,谈到张善琨在上海敌伪时期的情况时写道: 他(指张善琨)之获得“影戏大王”的称号,则是始于日寇侵华时期。我国的第一商埠上海沦陷以后,日本电影业的川喜多长政到了上海。川喜多在青年时期,曾侨居我国故都,肄业于北京大学,接受过华夏的文化教育。日本军部为了上海是各影片公司的集中地,企图加以控制,自然需要有个精通华语的人主持其事,于是责任落到川喜多长政身上。 川喜多获知上海的电影业中,有S·K(即英文善琨二字的缩写)其人,到沪后通过了相识者的介绍,与张善琨作了一次会谈,说明了他来华的任务。张善琨……终于冒了大不韪,接受了川喜多的敦请,负起了当时统一电影机构的任务。这一个统一机构初名中国联合影业公司,简称“中联”。后来又改名为中华电影企业公司,简称为“华影”。当时的三大电影公司“新华”、“艺华”、“国华”,都并入了这一个机构,由川喜多任董事长,张善琨任总经理。这是一个空前庞大的“电影王国”,隶属于这一个王国的工作人员,上自导演、演员,下至电工、木工,为数不下三千之众。张善琨之获得“影戏大王”的称号,即是在这一时期(19)。 从港台乃至国外学者的研究当中,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有着坚定的爱国情操,为保存中国电影业的命脉而与日本侵略势力周旋到底、消极抵抗的张善琨的形象,而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日本方面对于这段电影历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对于川喜多长政和张善琨的态度,清水晶在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一书当中这样写道: 当时90%的中国电影在上海拍的。制片厂都在租界和越界里。川喜多认为新公司的关键工作是给在日本占领地下生活的接近三亿的中国人民提供中国电影。要完成这个任务,最好引进有经验的导演和出名明星搭档的在上海租界拍摄的电影。 因此1939年5月份,川喜多开始与上海出名的制片人张善琨进行接触。张善琨是《木兰从军》的长期放映而成为顶级制片人的当时红人。川喜多想把《木兰从军》作为新公司放映的一部中国电影。 张善琨对初次见面的川喜多持了谨慎态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张善琨曾经拍过的比如《青年进行曲》的抗日电影。他怕新公司“中华电影”会干涉中国电影的自由制作。而且跟日本有密切关系,搞不好会被视为汉奸而夺命。 经过多次的面谈,张善琨开始理解川喜多的“鸽派哲学”。川喜多跟张善琨说,“如果我不接受这项工作,日本军部肯定找其他人,但这个人不一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方针。”这些话也可能起了使他下决心的作用。再说,对中国的制片人员来看,川喜多向张善琨提的条件就是有利,没有一个不利的。川喜多强调:居住在日本占领区的民众也是中国人,在那儿放映“孤岛”租界拍的电影,这对中国应该有好处。川喜多还跟张善琨约定:虽然无法跳过日军的审查,但绝不会有改编内容,“放映权利金”也首先会支付(20)。 川喜多长政开出来的条件无疑对于维持孤岛影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客观上的效果并不能消弭大陆学者对其在政治立场上的诟病,这不仅是出于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上的巨大差异,也来自长期以来主流话语空间的屏蔽和相关资料的缺失。 《上海电影志》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消失,上海影业全部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的情况的记载是这样的:“1942年5月,影商张善琨秉承日本侵略旨意,合并‘新华’等十二家电影公司,成立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共拍摄影片近五十部,1943年5月,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强化对上海电影的控制,又把‘中联’等三个机构合并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共拍摄影片八十余部。”(21) 张石川夫人何秀君女士的回忆录中也有她对“孤岛”时期的张善琨和她丈夫张石川的所作所为的看法。她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孤岛”消失。整个上海落入日寇之手。上海的电影事业时刻处于被他们吞并的危机中。不久,张善琨首先公开投敌。他奉日伪之命,把上海十二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伪“中联”),一些爱国电影工作者不甘心事敌,退出影坛。石川做不到这一点。几年前,他对蒋介石有着幻想,不肯出来侍候日本人,明星公司被他们放火烧了。现在,既是日寇强迫,又有张善琨带头,而且是所有大公司都参加了,天塌有大家。他也就半推半就,跟着国华公司进去,变成了伪“中联”的一员了(22)。 1963年2月出版的有关中国电影史的权威版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在论及“孤岛”时期的电影业及张善琨时,有这样一段话:“孤岛”消失后,上海的电影事业,包括放映、发行与制片三个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电影和苏联电影都不能公映了,代之而起的是日本电影。这时,伪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利用电影胶片来源中断,南洋航运受阻和各私营影片公司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拍片的机会,先以资金和胶片供应各公司,然后又进一步进行收买。新华公司的张善琨首先公开投敌,当了汉奸。接着,敌伪就指使他出面,在伪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下,于1942年4月,由“新华”、“艺华”、“国华”和“金星”等12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了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伪“中联”)。从此,上海电影业就全部为日寇所侵占,成为了“表面上”是“中国人的事业”的汉奸电影。 《中国电影发展史》对于这一时期张善琨和新华影业公司的作为的论断基本上作为“盖棺定论”,是大陆电影学界长期以来对张善琨进行认定的基本依据,尤其是对于在这一段历史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川喜多长政,1995年4月的《电影艺术》上刊登的《“友好”还是侵略——川喜多长政的电影文化侵略罪行》一文,将其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化侵略者,对其政治意义的关注超出其本身的文化范畴,可见,大陆以外的学者较为关注的历史研究的内容,虽然不能说为研究这一段电影历史完全还原出了一个“考古现场”,但是如果过滤掉其中包含政治批判话语,可以认定的是,大陆流行的电影史武断地将从“中联”到“华影”的这一时期当中张善琨为保全上海电影界所做的努力归入汉奸之流确实有失偏颇。 二、从“中联”到“华影” 当时与张善琨最有渊源的是川喜多长政,撇开浓厚的政治意味不谈,川喜多长政本人对于日本对上海电影界的控制是有自己的想法的。1938年12月,川喜多长政在《日本电影》杂志上发表了《电影输出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说:“我认为文化工作及国策方面最重要的是向东洋各国输出日本电影”(23)。对于实施和完成军方的任命的方针和办法,川喜多长政说:“我在上海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拍摄中国电影,为在占领区的近三亿的中国大众提供娱乐。但这是无论怎样有才能的日本人也是办不到的,我想最好是由被称作‘中国好莱坞’的设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电影工作者来拍摄影片……向占领区的电影院发行。”(24)他接受日寇侵华所实施的明目张胆的侵略、奴化政策在中国失败的教训,深知只有拍摄没有政治色彩、不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影片,在沦陷区的中国观众才愿意或易于接受,也只有拍摄这类影片,滞留在沦陷区的电影从业人员也才愿意或接受“合作”(25)。 川喜多长政走马上任担任“中联”副董事长、实权在手以后,坚决贯彻1938年10月在北平召开的“日本电影的大陆政策及其动向”座谈会的决议精神,一反过去日本电影公司在华所奉行的政策,不再拍摄内容有强烈政治宣传气味,如《东洋和平之道》那样赤裸裸鼓吹侵略中国的影片。而是改变策略,集中摄制所谓“以恋爱为中心”的娱乐影片,和所谓“大题材的中国电影”(26)。 而从商业角度而言,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那场侵华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当时日本、中国(包括汪伪政权)当局都面临物资紧缺、物价上扬和财政困难等棘手问题。电影既然是商品,就不能没有观众,就不能不考虑票房价值,川喜多长政明白个中道理。这样一来,就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以“生意眼”为名,坚持制作“意识形态上无关痛痒”的娱乐片。然而,执行了这样一种策略转变的结果,客观上却帮助了“中联”(张善琨和其他从影人员)和日军合作只限于为维持保存上海电影业,拒绝为占领军的宣传机器服务。对此,川喜多长政晚年的回忆录里说: “中华电影时代,合作者张善琨与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的二十年(昭和二十年,即1945年)春天,重庆方面来了特使,希望购买我们在上海制作的电影,并在非占领地区也上映。因为我们所制作的电影,没有任何政治或者说是宣传色彩,而主题歌也都已经在重庆方面很流行了,所以他们觉得即使在自由中国上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特使的到来,似乎是重庆方面要员宋子文的指示。 我将以张善琨为首的中国一流电影人之中的一大半都留在了上海,而现在这件事使得他们的立场也得以确保,对此我是非常高兴的,并且还豪言壮语地称“全面和平由电影界开始”,颇为得意。张善琨自然也非常高兴。然而,在那之后不久,张善琨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这又让我为难不已。之所以会遭逮捕,是因为重庆方面的上海地下工作总部被日军查抄时,发现了许多中华电影所制作的影片的剧本,由此也明白了张善琨与地下组织之间有联系。由于是在复杂的占领地区上映的影片,因此除了日军与南京政府之外,张善琨还顺便将自己制作的作品的剧本也送交给了重庆政府审查。我当然也是知道这件事的,但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反对的理由,就一直默许着。日本宪兵队会如此吃惊并将其逮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奔走为他辩解,还动用了关系,最后总算把他给弄了出来,而那时他已经被拘留了二十九天。”(27) 但是所谓“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和所谓“大题材的中国电影”在大陆学者看来则是完全不同的面目,《中国电影发展史》在论及“中联”在制片方针时说:日寇和汪伪为了迷惑中国观众,暂且搁下了如《东洋和平之道》那样明目张胆鼓吹侵略中国的影片,而集中拍摄了所谓“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和所谓“大题材的中国电影”。在1942年5月到1943年4月30日整整一年里,伪“中联”一共拍摄了大约50部影片,其中三分之二都是以恋爱家庭纠葛为题材内容的,如《香衾春暖》、《恨不相逢未嫁时》、《牡丹花下》、《芳华虚度》、《夫妇之间》、《梅娘曲》、《香闺风云》、《并蒂莲》、《水性杨花》、《红粉知己》、《情潮》、《断肠风月》等。此外,还有贩卖色情大腿的歌舞片《凌波仙子》,恐怖片《寒山夜雨》,滑稽片《难兄难弟》,侦探片《千里眼》等等。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甚至窜改了巴金的著名小说《春》、《秋》。 1942年10月,“中联”又由张善琨、徐欣夫等合作拍摄了一部叫做《博爱》的所谓“超特”影片。在这部影片里,他们通过11个故事片段,大肆鼓吹什么“人类之爱”、“同情之爱”、“儿童之爱”、“父母之爱”、“兄弟之爱”、“乡里之爱”、“互助之爱”、“朋友之爱”、“夫妻之爱”、“团结之爱”、“天伦之爱”等等顺民哲学,借以从旁宣传日寇和汉奸的所谓“中日提携”、“中日亲善”,反对当时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是一部为日寇侵略中国效劳的影片。继《博爱》之后,伪“中联”又与伪“华影”和伪“满映”合作拍摄了所谓“提携”影片《万世流芳》,影片利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崇高感情,打着所谓“清算英美侵略主义之罪恶”的幌子,歪曲林则徐这个爱国历史人物的形象,歪曲鸦片战争的历史,充满了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并且还大肆渲染三角恋爱(28)。 关于“中联”和“华影”这一时期拍摄的影片,《上海电影志》是这样表述的:“中联”和“华影”所摄影片,大多数是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庸俗之作。特别是1942年拍摄的《博爱》,由11个短故事组成,表面上提倡“人类之爱”,实际是附和“中日亲善”的反动观点,1943年拍摄的《万世流芳》,以林则徐禁烟抗英为题材,但肆意歪曲篡改,实际是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和英美作战的政治宣传。其后,“华影”还成立了“国际合作制片委员会”,与日本合拍了《万紫千红》和《春江遗恨》等,直接贯彻所谓“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张目。 尽管如此,这些为侵略者张目而拍摄的影片,包括《博爱》和《万世流芳》在内,没有完全达到日本人所要的宣传效果,遂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日伪当局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上海电影事业的垄断,指使汪伪政权颁布所谓《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实施所谓“电影的总体战”,把“中联”、“中华电影”和“上海影院公司”(这是在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接管英美商人财产的电影院后,组织的一家经营公司),于1943年5月合并为“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简称“华影”。使影片、发行、放映一元化,所谓“实施三位一体之电影国策”。“华影”成立后,也像“中联”一样,平均一个月出产三部电影,共有员工超过三千人(其中三百人为日本人)。由南京汪伪政权“宣传部长”林柏生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伪“中宣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冯节任总经理(执行董事),张善琨任副总经理兼制作部主任,另有三个名誉董事是褚民谊、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及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其他部门主要职位也是宣传部干事担任。从“中联”到“华影”的这一人事变化和结构安排看来,明显地可以看出,张善琨的权力进一步受到削减和限制。其目的也十分明显,是为了使“华影”比“中联”更屈从于日军的指使并为其侵华利益服务。 无论如何,新华公司在1941年12月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后并入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张善琨出任总经理时,作为独立的制片力量和经营主体的新华公司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新华影业公司作为一个经营实体在复杂而严酷的时代背景下的失落,这种失落既是在经营方针上的,也是在经营主体上的。而在其后的1942年4月,在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府的操纵下,新华、华成、华新、艺华、金星、合众、大成、华年、光华、天声等12家公司实行合并,改组为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新华并入日伪控制下的“中联”,作为独立的电影创作主体的地位不复存在,同时也丧失了其在民族意义上的所谓消极反抗行为的立场。1943年5月,与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影院公司合并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的事实,更成为大陆学者指证其附敌行为的最有力证据。 1945年出版的《民众周刊》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伪方电影界巨奸张逆善琨,偕其第三妾童月娟潜赴皖南屯溪,企图以投机手段化卖国行为于无事,公然下榻屯溪最高贵的旅社——皖南招待所,引起当地人仕一致愤慨。舆论界亦群起攻击,二十三日屯溪“中央日报”社论《严厉惩处汉奸》即指出张逆的罪行而请求政府法办,是日晚间张逆即偕童月娟并某经理共乘小汽车赴黄山“游历”,当为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在翌日晨电令黄山警局扣解。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张童两逆即由行署特务队押解抵屯后,张童等解送到江西长官部法办,张逆通敌罪行略举如下: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军获得侥幸胜利之际,张逆善琨向敌人献计,迫令华商各影片公司合并为伪中华影业公司,直接在敌人指导下作种种助纣为恶之麻醉及逆宣传。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伪组织庆祝“还都”周年纪念,张逆率领女明星陈燕燕等约二十名,迫令伊等以最浓艳之装饰同赴南京,参加“盛典”,并拍为新闻影片“以广宣传”。 (二)民三十二年间,张逆以“考察日本电影”名义偕同影星前赴东京献媚,以示“亲善”。 (三)张善琨领导之为“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所摄制“巨片”计有: (A)“万世流芳”——以鸦片战争为题材,作反英美宣传,帮同敌人离间我国与英美之邦交。 (B)“春江遗恨”——该片由中日演员合作拍摄,宣传“中日亲善”,歌颂“大东亚主义”,为道地之无耻反动之“宣传”品。该片拍摄时,一切材料均由敌方供给,敌方为拍摄该片,派来演员达一百余人。张逆以该片之拍摄,获得日方重赏,参加的落水明星亦曾得厚酬。 (C)“回头是岸”——以描写都市犯罪行为题材,作与敌人一鼻出气的宣传,该片剧本系由上海伪警察局防犯科供给! (D)其他为敌伪作丧心病狂宣传的新闻影片,其内容中伤抗战,献媚日人,无所不为其极。此外,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所拍摄的无政治性质之影片,均为麻醉人心、低级趣味的色情作品,用以推行敌人之“精神毒化”政策。 (四)张逆善琨早已与敌伪有往来,而未为外间人士所尽知,及至三十一年四月间,张因亏空日方巨款若干万元,无法偿付,乃将上海所有电影公司拱手送与日人。于是新华,国华,艺华,金星等影片公司,遂合并成为伪“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林逆伯生任董事长,日人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张逆善琨则就任“总经理”。该“公司”在张逆与敌伪合作下,即公开招股,由日伪投资雇用大批日籍职员,并由日大使馆管理之。同年九月间,张逆又将华商之电影院,沪光,新光,大上海,中央,明星等十余家,合并成立所谓“上海影院公司”,张善琨为“董事长”并兼“总经理”。 三十二年五月,由于张逆与敌伪之设计合作,又将日商之“中华电影公司”与“中华联合制片公司”及“上海影院公司”合并组成“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林逆柏生与日人川喜多长政分任“董事长”,张善琨仍为“常务董事”。当时该公司规模之大,实无堪匹,演员达三千余人,上海电影界至是乃完完全全,原原本本被出卖了,被控制于敌兵枪刺下了。 关于敌方文化宣传工作,张逆实是上海三年来最出力的一人,举凡敌方之反动宣传,张逆无不竭尽气力,大肆活动,在敌人所举行各种“祝捷”“反英美”大令中,张逆亦为最卖力的人,此皆张逆善琨为侵略者书忠的丰功伟绩(29)。 由此,张善琨先前经营的新华影业公司的全部努力也被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反民族主义的阴影。从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说,来自日本军方的压力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力量与无法左右的事实,而大陆史述所指的投敌,正是从张善琨与川喜多长政的交接开始。其实川喜多长政所处的那个位置确实是非常尴尬的,事实上他确实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来保留中国电影、上海电影的命脉,不让日本人介入与掌控制作,甚至由于在方针上的对立,导致他还受到了满映甘粕正彦那边的威胁。所以到后来中联、华影,他也是跟着时局在走,在大环境下做着小小的努力,但很多事情并不能如他所愿的,你想岩崎昶不也在满映监制过一些所谓国策片吗,他后来甚至都不愿意提起那些片子,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冲突的。 问题在于,川喜多他毕竟是个日本人,他所向往的是所谓“日中提携”,也就是和平共处,这与军方的目的既有重合之处也有相悖之处,军方是以征服为前提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而川喜多虽并不想要战争,但仍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所谓理想抱着期望,所以后来会和满映合作《万世流芳》这样的片子,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张善琨是他在上海最为亲密的合作伙伴,所以他对张尤为信任,认为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理想”,但就川喜多长政单方面来说这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张善琨究竟出于何意而同意与他合作的,深究起来,更多的是为了保全自己,以及上海电影业和那些从业人员。不过两人在那么长的合作期间,产生了深厚友谊,这是事实。川喜多长政对张善琨的肯定,是张善琨对于他对上海电影业的做法的支持与合作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他们这样做,保住了中国民族电影事业,所以在这个性质上,张善琨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毕竟与日本人合作,是极其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有性命之忧,战后也不免会背上汉奸的骂名,而张善琨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30)。 尽管在香港电影资料馆举行的有关童月娟女士的纪念活动中也曾引述杜云之先生在《中国电影史》第二册的中提及张善琨时的说法,他参加伪“中联”乃是获得国民政府的默许,出面收拾上海电影界残局而逼不得已做起汉奸。当时,他还和地下工作者保持联系的(31)。但是,“几十年来,一直有人说,张善琨手里是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默认’说,但始终没有见‘证据’拿出来;最近,在他死后数年又有人说有‘证据’了,但是,还是没有见到‘证据’。台湾出版的《中国电影史》(杜云之著,1978年4月版)也说,‘默许’他做汉奸一节,未得证实。”(32)未来不知是否有相关档案解密,以佐证这个说法,至少在目前看来,他的地位,依旧很尴尬。 注释: ①艾以.上海滩电影大王张善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0-90 ②参见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 ③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66. ④杜云之.中华民国电影史(上)[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318-320. ⑤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 ⑥杜云之.中华民国电影史(上)[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318-320. ⑦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66. ⑥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66. ⑨[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M].东京:新潮社,平成6年(1995):63-72 ⑩[日]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N].原载于[日]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中文译文由蔡剑平提供。 (11)晏妮.战时上海电影的时空:《木兰从军》的多义性[A].见:姜进编.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90. (12)[日]东和的半世纪[M].东京:东宝东和,1978:286;参见东和の半世纪1928~1978年の配给全作品の资料と、丰富なスクリ ン写真(豪华布张り希少大版美本)[M].东宝东和凳行,昭和53年。 (13)晏妮.战时上海电影的时空:《木兰从军》的多义性[A].见:姜进编.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91. (14)[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M].东京:新潮社,平成6年(1995):63-72. (15)[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M].东京:新潮社,平成6年(1995):63-72. (16)左桂芳、姚立群编.童月娟——回忆录暨图文资料汇编[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66. (17)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1-5卷)[M].香港:次文化堂出版,1996. (18)[日]辻久一.中华电影史话——一兵卒の日中映画回想记1939-1945清水晶校汪[M].东京:凯风社,1987. (19)陈蝶衣.张善琨先生传记:中国影坛巨人[M].大华书店,1958 (20)[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M].东京:新潮社,平成6年(1995):63-72. (21)《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23)何秀君口述、肖凤记.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A].原载《文史资料选辑》[M].第67辑,转引自《中国无声电影》[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1172-1176. (23)[日]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N].原载于[日]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中文译文由蔡剑平提供。 (24)[日]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N].原载于[日]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中文译文由蔡剑平提供。 (25)[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M].东京:新潮社,平成6年(1995):63-72. (26)[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M].东京:新潮社,平成6年(1995):63-72. (27)[日]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N].原载[日]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中文译文由蔡剑平提供。 (28)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113-118. (29)本刊资料室.张善琨通敌罪行[J].民众周刊,1945,2.见:贺圣遂,陈麦青编选.不应忘却的历史——抗战实录之三:汉奸丑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0)参见[日]清水晶.上海租界映画私史[M].东京:新潮社,1995;[日]辻久一.中华电影史话——一兵卒の日中映画回想记1939-1945 清水晶校注[M].东京:凯风社,1987;[日]田中纯一郎.川喜多长政[A].见:臼井胜美等编.日本近现代人名词典[D].东京:吉川弘文馆,2003:311. (31)杜云之.中华民国电影史(上)[M].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318-320. (32)朱天纬.“友好”还是侵略——川喜多长政的电影文化侵略罪行[J].电影艺术,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