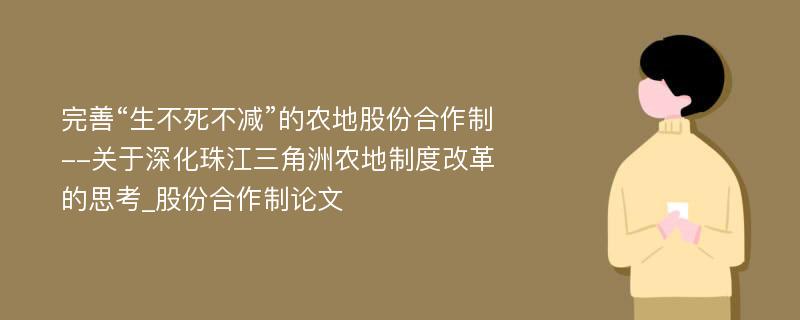
用“生不增、死不减”完善农地股份合作制——深化珠江三角洲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制度改革论文,股份合作制论文,生不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为什么“生不增、死不减”可以引入农地股份合作制
80年代中期以来,在神州大地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探索中,有两种制度创新形式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在贵州湄潭改革试验区推出的“增加人口,不再增地;减少人口,不再减地”(简称“生不增、死不减”),不仅在贵州全省风靡,而且在1995年新一轮承包期到来之际,被中央推荐给全国各地,虽不强求实行,但其被“提倡”,足以说明其制度创新的价值。另一个是广东南海改革试验区实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这里土地被价值量化,然后以股份的形式界定到所属社区成员的头上,虽然股份的界定只是书面的,但它替代了过去因人口变化而对承包土地实物的频繁调整;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土地的实物占有转变为价值占有,并且按股分红,这就成功地化解了工业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民既不愿意耕种土地,又不愿意放弃土地的困惑,促使他们放弃土地的实际占有,安心从事二、三产业,而土地使用权则要通过社区股份合作组织这个中介,按社区最大利益和效率原则进行流转,统一规划土地使用,农地交给专业农户或组织经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土地的科学使用和农地的经营规模及其效率。然而,与“生不增、死不减”走向全国不同,农地股份合作制至今仍主要出现于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特殊的经济条件—非农化的程度(农民愿意离土)和集体经济实力(离土照旧可以分红),使这一制度创新形式很难在其他地区发生。
如果说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推行其约束条件是苛刻的,那么“生不增、死不减”的约束条件就要相对缓和得多,这里关键的制约是:农民在分不到土地后是否有别的生路,土地所得(包括供农民家庭自己消费的农产品和商品农产品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地位。如果农民在分不到土地后,无法或很难谋求到农外的生活出路,如果土地基本是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农民就会坚决不放弃自己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之一的“天赋”权利。然而,在农地股份合作制实行的地方,恰恰这两个约束不存在了。首先,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民纷纷谋求农外就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将近2/3的农村劳动力都转移到非农产业去了,尤其是在一些农户家庭,由于青壮的劳动力就业于非农部门,无暇顾及土地经营;而土地不准撂荒,使他们有累赘之感,由于不能白白地把土地交出去,他们只好漫不经心,粗放经营。换言之,有没有土地对生活已无根本影响,只是不能轻易放弃这份权利。其次,由于主要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土地收入已变得微不足道。从实物上来说,农户家庭可从市场上以远比自己耕种成本低的价格买到家庭所需的一切或大部分农产品。如果考虑到机会成本,农民收益更高。从现金来说,由于土地的粗放经营,生产率不高,尤其是工农业行业收入的歧大差异,来自土地的收入对农户已显得微不足道。此外,在珠江三角洲迅猛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非农化而导致的地价上扬,农民要分享地价上涨的收益。由于土地股票分红基本上是农民参与利益分享的形式,因此固定股票,不再调整,实际上也就保证了农民的产权利益不因人口变动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事实上,这正是农民最为关心的焦点之一。因此,把“生不增、死不减”推广到农地股份合作制实行的地方,是完全有条件的。
二、为什么农地股份合作制需要引入“生不增、死不减”
现在,我们将要论证的是,在农地股份合作制下,有无引入“生不增、死不减”的内在需要。如果一种制度安排是人为移植的,脱离了实际需要,那么,在彼地是绝好的制度创新,在此地将是最糟糕的制度扭曲。因此,阐明农地股份合作制下,引入“生不增、死不减”的客观必然性,显得十分重要。
笔者近年来研究农地制度创新,曾反复强调农地股份合作制并未根除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端:土地是福利品而非稀缺资源。我们知道,土地股份合作制下农民土地股份的界定基本上是按照成员资格分配,即只要是所属社区的天然成员(即因生育和婚嫁),不论年龄老幼和时间先后,人人有股。至于个人对社区的贡献,仅仅体现在“成人一股,儿童半股”。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注意了拉开个人拥有股份的档次。但总的来说,通行的还主要是公平原则。此外,大多数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村,规定农户只拥有土地“书面”股权,并据以分红,对土地股票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转让,甚至不能继承。股票与生俱来,死不带走,充分体现了社区成员的福利原则。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却是严峻的:由于土地股权与社区成员资格紧紧连在一起,为了不放弃这份“天赋权利”,人们就不会轻易迁出社区,不招工、不进城,甚至女儿也不外嫁,大量“洗脚上田”的农民滞留在农村,不仅阻碍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制约农村发展,而且会滋生很多社会问题。而且,由于股票是不能流动的,股东也就失去了“用脚投票”这样重要的表态方式,因而在社区股份合作组织的领导和决策者有可能违背股东利益的时候不能进行监督,从而使股东拥有的本就脆弱的各项权利进一步受到损害。这种状况在行政组织还部分行使管理职能,行政领导人一身数职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赋予农民以真实的股份产权,农民可以自由处置土地股票,其限制顶多只能是控制土地股票流转的范围和拥有土地股票的最多数额。而要这样做就必然导致废除股份分配所据以的福利原则。换言之,引入“生不增、死不减”的机制,是内在的逻辑选择。这是因为,其一,如果我们要允许股权可以流转,就要赋予农民以土地股份的所有权。这样一来,也就意味我们不再可能对土地股票的分配进行再调整,因为重新调配股东权是对股东基本权利的侵犯。其二,如果我们不能再对土地股票分配进行调整,也就意味按照目前“成人一股、儿童半股”的分股原则,目前的儿童将永远拥有较少的股份。进一步看,那些社区的新出生人,尤其是那些未嫁娶和未出生人口,将无股可分,而这些人按照“天赋股权”的福利原则,本是可以分得一份的。由此可见,要完善农地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安排,增加制度激励,减少摩擦成本,必然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放弃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制度遗产——地权均等和土地福利。这就必然走向“生不增、死不减”。
三、怎样实现农地股份合作制与“生不增、死不减”的嫁接
用“生不增、死不减”改造农地股份合作制,是要在土地股权的分配上搞“一锤子买卖”。这是一种势在必行的选择,迟搞不如早搞。搞得越早,越能早日摆脱被动;搞得越迟,问题会累积越多,增大改革的难度。但是,考虑到制度遗产的刚性,也不要强行一步到位,而不妨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做法,逐步过渡。笔者的想法是,可以重新调整一次股份分配,尽可能照顾各方利益减少争执,以利改革推进;也可以留出一定的机动股,或是利用目前有的股份合作社存在的集体股,对新成长起来的人和新出生人口配给土地股份。由于这些人对集体财产的积累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可以调低对他们的配股份额。而对成人股不再调整调配,允许继承。把这个过程作为一个过渡期,让人们逐步去适应。一俟机动股或集体股分配完毕,即宣布今后不再分股。但可以视情况扩股。扩股最好不是人人有份,而是一股一份,以体现要素贡献,否则我们又将回到怪圈的起点。由于股票可以继承,新增人口将名正言顺地从其父辈那里获得产权。
最近,在珠江三角洲南海市里水镇的草场管理区,一些经济社已开始试行“生不增、死不减”的改革,其做法是将原属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现有固定资产和自有资金等以股份的形式全部折股量化,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全部股份一次性分配给组织内部农民个人所有,股权可以在本区内流动,可以继承。在股权配置上,承认差别,把原来10股为满股,改为20股为满股,以拉开股数档次。具体按三种股权配股:(1)基本股占3股,配股对象是截止1995年12月31日的人口。(2)承包权占3股,其中16周岁以上的配3股,16周岁以下的配2股。(3)年龄、劳动贡献股占9股,分两部份计算,第一部份从1982年开始,以承包责任田的期数计算股份,第一期配2股,第二期配3股,合计5股。第二部分按年龄、劳动能力、贡献大小计算,按年龄划分,共占9股,分18级,每级递增幅度为0.5股,16周岁以下每级相隔3周岁,16周岁以上每级相隔1周岁,43周岁以上为9股。把股权一次性配给农民后,不再作调整。对于以后新增的人口,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扩股。定期扩股对象是新出生及新嫁人的农业户口人员,新出生的配售5股,新嫁入的配售6股。考虑到村民的经济承受力,采用优惠办法,按照当时股值的30%计算。不定期扩股,由股东代表大会确定,章程来做具体规定。股权作为个人私有财产,可以在本区内流动。为了对股权流转进行管理,凡进行转让、赠送、抵押或继承的,必须到有关的管理机构办理手续,否则不予承认。
目前这一工作已经推开,由于重新配股充分保证了现有人口的利益,因而实施起来还比较顺利。但其运转怎样,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由此可见,只要充分考虑利益的均衡,寻求一种“帕累托效应”,农地股份合作制与“生不增、死不减”,可以实现平稳嫁接。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确保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合作经济性质,两点配套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土地股票只能在社区内部成员之间流动,合作组织应有监督权,也可以作为交易的主体;第二,应当严格限制个人拥有土地股票的最高限额,以防止少数人成为大股东而操纵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