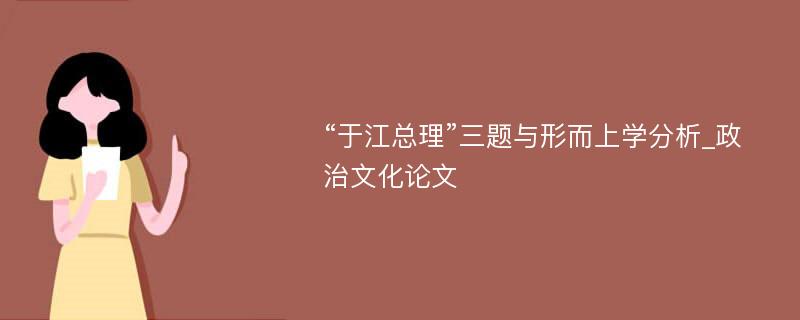
“王丞相過江”與玄學三題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丞相论文,與玄學三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一宗迷案,便是《世說新語》記録的東晋初丞相王導過江之後所談“三理”的解釋問題。王導(276-339),字茂弘,東晋初年的大臣,在東晋歷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任太傅、丞相,是東晋政權的奠基者之一。不僅如此,王導也是兩晋時期玄學與清談的重要人物,與名士深相交納。《世說新語·文學》記載: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①
《世說新語》此條可見于國內思想史、美學史以及各類文化研究專著等著作之中,對此條目的多次援引與說明,表明歷代學者對它所具有的史學價值與以充分的重視與肯定。但觀察其援引目的,則多數將此條作爲一條論據來佐證文章內容。如侯外廬先生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玄學思想的階級根源》一節中對三理有相應的論述②,李澤厚先生的《中國美學史》用《世說新語》這段話作爲嵇康《聲無哀樂論》的引入③,再如田餘慶先生的《東晋門閥政治》談及東晋永和玄學概况時對此也有所引用④,這些論著在相應的領域內都是比較經典與權威的文獻。另外,在其他一些相關論文中的引用也是比較常見的。可是從深入來看,這些文獻關于“過江”此條其中所反映的有關王導在選擇題目上的意圖,題目本身與現實背景之間的關聯以及它所反映的有關玄學、政治學等折射出的多方面問題略于綜合考辨,因而,這一迷團仍然存在于現有的研究領域之中,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本文試圖就這一難題進行分析與論述。
一、王導談玄的時代與家族背景
玄學與清談始于魏齊王曹芳統治的正始年代,後世稱作正始之音,在西晋末年盛行一時,代表人物爲王導的族兄王衍⑤,魏晋玄學是一種特定的融天道人生與政治哲學爲一體的思想體系,以舉本統末,協調名教與自然關係爲特點。而王導在過江之後好談玄學,將三理作爲談中樞機,與他所處的東晋特定情勢相關,也標誌著玄學與清談在東晋的嬗變。
西晋末年繼“八王之亂”之後,又發生了“五胡亂華”。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指出:“此蓋自初平以來,久經喪亂,民力雕弊,朝廷紀綱,亦極頽敗,其力不復能戡定北方,而僅足退守南方以自保,大勢所趨,非一人一事之咎。”⑥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晋王導之功業》一文中指出:“至南來北人之上層社會階級本爲住居洛陽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團,在當時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馬氏皇室既捨舊日之首都洛陽,遷于江左之新都建業,則此與政治中心最有關係之集團自然隨司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導之流即此集團之人物,當時所謂‘過江名士’者是也。”⑦顯然,“過江名士”已經成爲一個歷史現象及以王導爲首這類人物的代名詞。
東晋建立的初期,江東政局的確極不穩定。當時中原已被匈奴和石羯所占據,江東本是孫吳舊壤,根本不願意接受這個來自北方的新政權,吳會人士對南渡人士仍然抱著敵視的態度。《世說新語箋疏·方正》篇有這樣一段記載:“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熏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⑧王導爲了結援吳人,期冀儘快融入吳地當權勢力圈之中,却被吳人毫不客氣地以文化差异之由拒之門外。又《晋書·王導傳》載:“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⑨元帝與王導等衆北來士族過江左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局面,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南人對北方人士頗深的偏見。義興的士族周氏甚至企圖殺掉來自北方的官員並代之以南人。《晋書》載:“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馭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扎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廣德以應之。”⑩雖然由于周札的反對與告發而政變未遂,但吳地舊族對東晋政權的敵視是十分明顯的。這種狀况使新帝司馬睿和王導憂心忡忡。
面對此種內憂外患的複雜政治局面,過江後初任丞相的王導却倡導衆人清談不輟(11),這其中顯然含有深意。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晋王導之功業》一文中肯定:“江左之所以能立國歷五朝之久,內安外壤者,即由于此。若僅就斯點立論,導自可稱爲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孫亦得與東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廢興。豈偶然哉!”(12)王導作爲東晋政治與文化重鎮,他之“止道三理”,决非個人興趣所在,而是當時東晋過江後的各種現實因素在文化心理上的折射。要解析這種獨特之話語情狀,必須對這種情勢與背景作全面的回顧與分析:首先前面指出,東晋政局不穩,急需一個統一思想來籠絡南北人心。其次,南北士人在文化背景、生活習慣、言談方式等都有較大的差异,怎樣在“寄人國土”的情况下,從各個方面彌補南北雙方之間的縫隙,需要一個突破點,即發展共同的利益愛好與談題是關鍵。
我們知道,玄談是魏晋時期士大夫最重要的交游活動之一。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新語和晋人的美》附《清談與析理》一文中指出:“被後世詬病的魏晋人的清談,本是産生于探求玄理的動機。王導稱之爲‘共談析理’,嵇康《琴賦》裏說:‘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析理’須有邏輯的頭腦,理智的良心的探求真理的熱忱。”(13)而“論天人之際”當是魏晋人“共談析理”的最後目標。賀昌群先生指出:“由王弼而至于向秀、郭象、張湛、韓康伯,始貫通天道人事與政治爲一體,漢代王霸政治之說,乃得歸入于玄學本體論中,通哲學于政治之實踐,納政治于哲學之精微,在中國民族文化史上成一偉大崇高之思想體系,氣象萬千,而精義入神,此中華之所以爲泱泱大國也。”(14)賀昌群先生追溯了漢以來統治者的相關政治策略,分析自古儒道法術之政治理論的特點與實踐之利弊,最終指出,魏晋人是通過對天道人事的積極思考,從而給出世人對政治哲學理論探索的新思路與新方向。他對魏晋玄學政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最後甚至發出對世人誤解之深的質問:“魏晋清談之本旨,豈徒游戲玄虛離人生之實際而不切于事情也哉?”(15)
自魏晋正始年間,何晏、王弼倡發的“崇本息末”論及“名教出于自然論”後,嵇康進一步發展爲“貴無論”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但是,何、王所重視的是“聖人”、帝王的理想人格,帶有十分明顯的政治色彩。而阮籍、嵇康所重視的則是個體人格的絶對自由。阮、嵇之後的郭象也很重視莊學,但他對莊學的實質有嚴重的曲解,並且是以政治的“君人南面之術”爲其注意中心。這樣,從何晏、王弼、嵇康等人下來,到了西晋末年,玄學理論形態就思想體系而言已無所創建,東晋士大夫們的談辯只是對具體問題辨析更加深入。因此,我們要注意,王導談玄不可忽視他對前代玄學思路的繼承,也不可忽視其背後强大的家庭背景作爲影響與支撑。
漢末以來,學術的傳承除了師生關係之外,還有家族的文化傳承,即家學淵源成爲一種重要的傳承途徑。門閥士族的重要標誌,即是累代爲官與家學淵源的結合,既與西漢的經學傳承方式不同,也與唐宋之後的科舉制度下的學術傳承相异,這一點,前人多有所論及,並已經成爲學界之共識。因此,王導之于玄談三理的家族背景應首先與以充分認識。
王氏家族子弟多出類拔萃,涉及仕宦的人更是數不勝數。其實,早在魏晋時期的竹林七賢之一王戎(234-305)便可作爲王氏玄化的先導,他較早接觸玄學並將其納入到家族文化體系中,完成了由儒學向玄學的轉化。王戎十五歲時就被當時的玄談大家阮籍所賞識,並結成忘年交,這一時期玄學的主要命題還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雖然受阮籍嵇康的影響,王戎作爲這一時期琅邪王氏家族的重要代表人物,爲了維持和提升家族的門第聲望自然他要入仕,入仕就必須遵守社會秩序與道德倫理規範,也就不能把“名教”與“自然”相對立。因而,他沿著王弼、何晏的路子,采取以道釋儒的方式,把道家的自然無爲與儒家的倫理名教溝通起來,以調和個體與社會,自然與名教的矛盾。用名教主宰社會秩序,引導入世行爲,用自然保持精神愉悅,調節生活情趣,培育出世心境,兩者没有矛盾,存在合理,也没有本末的區別,因此,“名教”同于“自然”這種觀念更符合統治者的口味,也更有利于其仕途上的發展。所以,王戎的玄學思想主要特徵即表現爲協調儒道。
可見,早在王導之前,正始時期的家族領袖人物已經將這種政治哲學在嘗試運用了。作爲王氏玄化的先導,王戎無論是在玄學思想史上還是對其家族來說都意義重大,王戎提拔族弟王衍使其家族繼承玄脉,贊同儒玄並修合一的觀點,對其家族思想文化影響更大,此後的琅邪王氏人物多能遵循這一家學精神,堅持儒玄雙修,有力的鞏固了家族地位。因此,後人王導的儒玄雙修不可以簡單地看作當時社會普遍士人的風氣,它更離不開其淵遠流長的家學風邁,這是他政治理念形成的首要因素。處魏晋亂離之世,却能盡壽終正寢之命,王導能屈能伸的政治性格豈非更像王戎。
另外一位家族人物王衍(256-311)也要引起充分注意,山濤、羊祜這些玄學中杰出人物都曾高度評價他的風姿與才學。王導視其爲“岩岩清峙,壁立千仞”(16),王敦過江,還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17)但生活在西晋後期,王衍乃以何晏、王弼概括出的高度抽象的“無”爲理論依據而脫離現實,追求虛無玄遠,以無爲體,求得能無所不有。在王衍的倡導下,“貴無”論成爲一時的風尚。《晋書》卷三五《裴秀傳附裴頠傳》說他雖“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坐而論道,暢誤玄虛,逍遙自適,瀟灑風流。王衍以其玄學表現成爲中朝玄學領袖,引領一代風氣,在玄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並將琅邪王氏家族推向一流世族的顯要位置。所以王氏子弟如王導王敦等人對其不排除有標榜之意,但從中可以見出中朝名士領袖王衍對後來王氏子弟所産生的深遠影響。《世說新語》載:“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于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18)當時的王導不過跟著族兄一起宴飲,遇上了突發事件,王衍面對族人的粗暴舉動毫不在意,回到車上還攬鏡自照對王導說:“你看我的眼光,竟然超出牛背之上。”跟著這樣一位風度翩翩灑脫自傲的族兄,想必年輕的王導心中也會暗暗稱許乃至不自覺地效仿。
雖然,王衍祖述《老》《莊》乃其玄學特徵。但他對“三玄”之一的《周易》却研究不够,《晋書》卷四九《阮籍附從子修傳》載:“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没當見能通之者不’。”這是說,王衍當時談宗,對《周易》的理解還是有些吃力,不能了悟,希望有通此道的人給予指點。可見,王衍在三玄中對《周易》理解上的缺憾,他自己也深知無力深悟此道,所以他個人的整體氣質更趨向老莊的玄虛而缺少儒家支撑。雖玄談有道却政治無名,晚年他對自己的一生回顧也頗感愧疚。相比而言,王導政治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巧妙運用儒家思想,雖處“衰世頽俗”却也能力挽狂瀾,王導對玄談在政治上的運用比前輩更爲成熟、進步。
王戎與王衍,乃是魏晋時期琅邪王氏家族杰出的政治代表人物,他們各領風騷,在晋初與晋中後期延續並保持了王氏家族顯赫的聲位。對于後代子孫當受益匪淺。《世說新語》記載,曾有人到王衍家,見到王戎、王敦、王導,又見到王詡、王澄。出去便跟人說:“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19)王導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珠玉滿堂的仕宦豪族裏,其濃郁的學術氛圍與得天獨厚的文化環境,促使了一代名相的誕生。
《晋書》卷六十五《王導傳》評價:“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世說新語·德行》“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條引《丞相別傳》亦云:“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王導自小就“恬畅樂道”,這與其家族崇尚玄學的家風固然密不可分。長大後隨著家族談玄影響的積累與閱歷的增加,他已經逐漸形成自己的價值觀與認知體系。《世說新語·企羨》記載:“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已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20)可見,王導在西晋時對玄談已經很有造詣,獲得跟玄學大家交流的機會,乃至過江後回憶起依然悵惘不已。裴成公就是西晋時期被譽爲“言談之林藪”,並著有《崇有論》的裴頠;阮千里即以“將無同”的回答令王戎“諮嗟良久”的阮瞻。可見,對自己曾與著名的玄學名流共同談道,王導頗爲自詡。請注意,這裏用一個“數”字,表明這種場合不僅是一次兩次而是由來已久的,就是通過這樣對學問反復地切磋與琢磨,才爲後來他的玄學政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也可見,在中國歷史上,王導的風流首先體現在他的文化修養與執政行爲的和諧統一上面,表現爲一種自覺的政治文化理念。
二、王導對玄學“三理”關生之取捨
依照現代闡釋學的原理,任何接受與闡釋都有著明顯的主客性,中國古代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大體上說的也是這層意思。無論是正始玄學還是西晋郭象的玄學,主旨都在討論名教與自然之關係。而其本體論上的依據則是有無之辨。王導特殊的人生經歷與政治際遇,特別是他主政東晋政局時,作爲一名玄學名家與宰相,他的玄談有別于當時的韓康、許詢、衛玠等人,深含著政治與人生用意,取捨當然也就不同凡響。他選擇三理互補,作爲玄談核心,細究起來不,有著極深的藴涵。對此,我們不妨加以分析。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王導是一個悟性極高的人物,善于審時奪勢。王導談玄三理産生的東晋時代與魏及西晋末年有著明顯區別。《世說新語·規箴》:“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諮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21)這一條記載,揭示了王導在東晋初年以寬爲政的特點,不僅當時人人皆知,争議頗多,後世也多以此指摘王導。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晋王導之功業》一文中曾比較東漢末年曹操、袁紹兩人行政方法不同,“操刑綱峻密,紹寬縱大族……司馬氏本爲儒家大族,與袁紹正同,故其奪取曹魏政權以後,其施政之道號稱平恕,其實是寬縱大族,一反曹氏之所爲,此則與蜀漢之治術有异,而與孫吳之政情相合則也。東晋初年既欲籠絡孫吳之士族,故必仍循寬縱大族之舊政策,顧和所謂‘網漏吞舟’,即指此而言”。(22)陳寅恪對東晋建國初期之政策特點有此深入分析,認爲王導“憒愧”之政實乃有其深意。王導歷經西晋與東晋换代之際,于司馬氏的政治特點與政治操作有著切實的認識,其時北地胡羯强盛,江東實力均掌握在孫吳舊統治階級之手,若想在江左站穩,聯合江東豪族、士族是必然的思路,他學吳語,攀親戚,對吳人的籠絡可謂煞費心機。由此可見,作爲政治家,他只道“三理”其深遠的政治目的對上述情勢有著極强的針對意義。《世說新語》中此八字是關鍵,“宛轉關生,無所不入”,相信當時人們已對王丞相談玄這番意圖看得一清二楚。這其中的“生”,既是“國計民生”之“生”,也是家族與個人“生死存亡”之“生”;更是其“生生不息,勵精圖治”之“生”。這就是說,他做的官和以往家族仕宦成員大不同,既不同于王戎隨機應變也不同于王衍無所作爲,他要面對的是扶持孱弱的皇權,開拓一個新局面。
然而,《世說新語》記載王導過江後“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對魏晋玄風十分崇拜的王導爲何從衆多玄談題目中只拈其三者,其中蹊蹺,值得深思。有的學者曾說:“這一時期的玄學理論經過正始玄學、竹林玄學、尤其是西晋郭象對玄學綜合總結之後,玄學理論已没有多少可發揮的餘地。”(23)既然玄學的精華理論都在前人,王導必然要從前代的談題中找依據。這裏我們自然會發問,首先王導爲何從衆多題目中選擇這三理?其次,爲何他同時選擇兩篇嵇氏的文章來談,二者之間乃至二者與現實之間有何關聯?再次,擴大到這三理之間又有怎樣的聯繫?本文試從下面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1.我們先從史料記載的前兩篇文章入手,王導爲何連續選擇兩篇嵇康的文章作爲談題?
嵇康首先不僅是名士,而且是一位英雄有力之人物,在當時有著廣泛的影響,他爲曹魏政權的宗族人物,是曹氏集團中人,是司馬氏政權在當時主要的政敵之一。他在政治與文化上都有著巨大的影響,鍾會稱其爲臥龍,不是偶然的。嵇康又是一位多才多藝,在文學與音樂、書法上都有極深造詣的人物。如果說王弼、郭像是以思辨方式建構了玄理哲學,用以會通儒道思想,嵇康則是以生命體現了儒道爲一的真實內涵,雖然其逝也不免悲壯凄美,誠可歌可泣,爲魏晋的名士精神樹立了典範高標。因此,相對于王弼與何晏,他的人格魅力是光彩照人,輝映後人的。王導作爲稍後于他的名士與政治人物,儒玄兼修,對其傾慕有加,是很自然的。三理中取其二理,于作者的身份地位及影響也是有考慮的。又他的理論體現出既有著深厚的傳統根基,又敢于大膽的創新。這兩個特點,魯迅先生等人都有深刻的論述。“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然而,“魏晋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24)因此,瞭解嵇康的玄學論題,特別是最有影響的《聲無哀樂論》與《養生論》二理,就必須充分顧及這一特點。
先談《聲無哀樂論》,中國古代自先秦開始,就奠定了從天道自然與人倫秩序來觀察音樂現象的觀點,道家老莊的大音希聲,至樂無樂,儒家荀子的《禮論》、《樂論》,以及後來的《禮記·樂記》,就提出了大樂與天地同和的觀點,先秦的《國語》、《左傳》中音樂理論,以及秦漢時期的《呂氏春秋》、《淮南子》的音樂美學思想,無不秉承了這種文化思路,因此,中國傳統的音樂文化,是基于這種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思路與方法來看待音樂與政治與人生問題的。以和爲美,是中國古代將天道、社會與音樂統一起來的思想觀念。道家用音樂的無聲來說明無爲而治。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哲學中,用音樂的和諧來形容政治的成功,也是經常性的觀點。在《左傳》中就提到了晋文公的政治與外交非常高明,晋文公的中軍司馬魏絳足智多謀,在晋國成就霸業的過程中貢獻很大。晋文公因此把自己樂隊的一半賜給魏絳,並對他說:“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25)(《左傳·襄公十一年》)。用音樂的和美,說明政治的和而不同也是春秋戰國時期經常運用的觀念,如在《左傳·昭公二十年》齊相晏嬰所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26)另外,如《國語·周語下》記載單穆公極力反對周王鑄無射大鐘,他從管理學、心理學角度提出音樂必須“從和”的觀點。至于道家,也是用音樂的自然來統率教化,將教化置于自然之下,觀《淮南子》諸書,便可了然。
嵇康的思想博大精深,蓋源于此。他是從前人的思想資料中來出新自己的聲無哀樂論,有著明顯的現實針對性,這便是反對司馬氏集團的虛僞的名教之治。前面已經論及東晋的政治局勢,就作爲丞相王導談《聲無哀樂》從大的政治環境分析,他看中的乃是嵇康聲無哀樂論中所反映的“和”的觀點。基于“和”的觀念,嵇康在《聲無哀樂論》中系統地論證了他對樂的本質的看法。嵇康反復地講到了這種“和”的特徵,這就是“愛憎不栖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體氣和平”、“清虛泰静,少和寡欲”、“神以默醇,體以和成”、“性氣自和”、“情志自平”、“蘯喜怒、平神氣”等等。由于這種“和”超出了由名利、欲望的追求而産生的愛憎、憂喜,所以嵇康認爲以“和”爲本體的樂是“無關于哀樂”的。他在《聲無哀樂論》中反復地說明了這一點,始終堅持樂的本體是超出了哀樂的“和”,不是一般人情的哀樂。然而,顯然“和”是儒家樂論最重要的觀念,而嵇康對儒家强調中正平和的音樂對個人的修養上,能促進心氣平和,身心協調合一,進而將音樂施用于移風易俗的社會教育,期收感化、統一社會人心的主張,頗不以爲然。他將音樂的“和”從儒家所謂的人倫道德關係中掙脫出來,轉而緊系于與自然體性的永恒關係。在音樂的社教功能上,他認爲一般人民若有“和心”,自然能實現風俗至美。“和心足于內,和氣見于外”、“讬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于言,心感于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嵇康又借東野主人之口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27)這個“和”心便爲“無聲之樂”,推演到政治運用來說便是“無爲而治”,它是促成善良風俗的真正原因,因此,儒家似有倒果爲因之嫌。
2.那麽如何使人人具備“和心”,成純美風俗呢?接下來王導談養生便派上用場。養生論的史脉源于老莊。魏晋人處動蕩亂離之世,生命慮旦夕之危,對時局的壓力,生病的痛苦,心情的鬱悶,死亡的威脅等期望有所逃避,企圖養生長壽。而嵇康講養生之法是植基于探究人天生自然的性命之理,承順因循性命之理而輔養、導養之。他主張形神共養,以養神爲主,《養生論》中道:“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28)因爲神御形而特重養神。廣則從治國角度,養生意義重大,這裏認爲國之精神在于君之昏明,君主政治清明,猶精神之統一,可以統帥整體,使國家上下輯睦,百姓安居。所以“養神”是核心部份,是治國的關鍵,也是王導主清净無爲之政的重要理論依據。小則從每個普通百姓來說,可以從最基礎的養形做起,世俗的名利、喜怒、聲色、滋味、神虛精散是五大傷生害性的因素,務必要自制克服,才能達到嵇康所言的“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身而後生存”,甚至可“與羨門比壽,王喬争年”,達到長生不老之境界。這是王導對世人的期許,也是對自己的期許。于是乎《晋書》載:“導簡素寡欲,倉無儲轂,衣不重帛。”(29)他首先從自己做起,切實倡導起清心寡欲的養生運動,可稱得上爲朝野上下做出了表率。
這樣我們回過頭再看嵇康的樂論,“嵇康是從他對社會人生的看法,特別是從他的養生的觀點來看待音樂的”。(30)其實它明確地把“樂”與“養生”相聯,同時這“養生”的最高境界又在于達到個體人格的自由無限即所謂超哀樂的“和”的境界,這樣,嵇康就極大提高了個體在審美與藝術中的位置。與此同時,“樂”的意義與價值也就不象儒家所說的那樣,僅僅在于“成人倫,助教化”了。這兩者的論述,歸根到底,即是辯論有與無、自然與名教的立場問題。嵇康的政治史觀認同繼承了老莊,在《與山巨源絶交書》中他公然表明“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對老子而言,“道”是遍具一切,與物無對待的絶對存有,“道”的體性是不偏執任何一端之有的“無”。萬物與“道”原是無分化無利害對待,渾然一體的,這也就是嵇康所謂“大樸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難自然好學論》)的境界。嵇康的理想政治之目標,擇取老子簡易的無爲而治。然而對存矜尚之心、貪圖富貴榮華的現實之君,又如何可能接受這一理想,又憑什麽方法來實現呢?曾春海先生道:“嵇康以天下君位之設乃爲生民計,人民才是政治的目的,君長之制是促成這些政治目的所設立的政治手段,企圖以民本的政治價值觀來對時君進行理性的說服。”(31)
王導選擇了這兩個題目,既是對儒家思想的繼承,又融合了道家思想的精華,是對魏晋以來玄學精神的充分吸收從而形成自己的一套世界觀與方法論。“嵇康所說的樂的本體,即超哀樂的‘和’,實際上就是魏晋玄學所追求的這種人格本體”。一方面不難反映出他內心中對理想人格的向往與追求,對個體精神層次的修煉與超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他期冀借玄學理論可以實現政治抱負,《聲無哀樂論》裏指出:“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静于上,臣順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32)所以《聲無哀樂論》與《養生論》都以“和”爲最高境界,而在“無爲而治”的角度上是互辯互證的。政治生活中事從簡易,務存大綱爲的是消除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團結一切力量從而穩定人心,玄學是救急之需而具有現實功用。王導在蘇峻之亂後反對遷都之議中道:“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静,群情自安。”(《晋書·王導傳》)東晋新生政權的脆弱危如累卵,時局一旦觸發立刻可能土崩瓦解,對于這點,王導是十分清楚的。所以穩定壓倒一切,要利用玄學無爲寬恕“鎮之以静”的政治策略,從而才能實現封建國家的長治久安。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指出:“夫鎮之以素樸,則無爲而自正。”(33)因此,王導談《聲無哀樂》與《養生》從道家的因素,提煉出無聲之樂之于“和”,養生養神之于“静”的政治智慧來。他所抱有的南北士族融合,和平共治江左的迫切心願必然要通過以上二論助之成立,嵇氏的兩論可以說與其産生了强烈的共鳴。我想,這才是王導巧妙選擇此二題的宏旨。因此,嵇氏二論也著實不該單純地劃分其各自的作用,王導連續選擇兩篇嵇康的論文,其政治用意與政治見地不得不讓人拍案稱絶。
3.關于“言盡意論”,王導重提這個題目,和當年歐陽建反對主流反對非儒的用意既有相同之處,但也有明顯之不同。在時代上略晚于王弼的歐陽建(約267-300),著有“言盡意論”。他以“違衆先生”自居,而反對“雷同君子”們所贊同的“言不盡意論”。他的主要理由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兩者如聲之與響,形之與影,不得分而爲二,這樣言是可以盡到此意的。事實上,他意圖要駁的是如荀粲、蔣濟、鍾會、傅嘏等人對聖人典籍的污蔑“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三國志·魏志·荀彧攸賈詡傳》)歐陽建肯定語言是表達思想指稱事物的重要工具,意只能通過言表現出來,進而得出“古今務于正名,聖賢不能去言”的結論,要捍衛經典古籍尤其是儒家經典的權威性。可惜在玄風熾盛的社會思潮下,他的聲音並不是主流。
雖然在衆多題目中有很多關于《論語》、《春秋》這類正統的論題。但王導選中僅有二百六十八字的《言盡意論》,主要肯定它有著强烈的儒家色彩,另一重要原因則是它是一篇關于抵抗非儒態度明確的與時下關係最爲密切的文章。早在建武初年,他便上書元帝請建立國史和請修學校(詳見《晋書·王導傳》)。王導利用它來糾正玄風過盛的東晋社會思潮,這便與歐陽建不廢聖人之學的心情是一樣的。王導雖然醉心于清談,但並没有罔顧禮樂,上書所言皆是儒家正人倫,始教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晋書》載:“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眷同布衣,匪爲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34)這段記載不但表明了王導與明帝之間有著深厚的戰鬥情誼,更說明他心底對儒家思想的認同與尊重。王導堅持名教禮法要與自然與人情相結合的政治觀與人性觀,以此來調和皇權與世族,禮法與人情,家族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孔子也提出過“辭達而已矣”,言不盡意,書不盡言,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等互相矛盾又互相補充的觀點。一方面,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另一方面,意又必須用言文來窮盡。這本身是矛盾的,然而玄學的特點就是在互相矛盾對立的辯題中求得推進和真理性。真理與真理性是有所不同的,真理注重終極結論,往往導致僵化,而真理性則關注對于真理的方法與追求的熱情,對于終極結論並不感興趣,何晏嘗賞嘆王弼云,若斯人者,可與論天人之際乎!便是說明了玄學的特點與玄學家的可貴。《世說新語》中的記載名士玄學與清談,都没有最後的結論。王導對于言盡意的理解,不僅是說明言可以盡意,更主要强調言盡意而已,與他的點到爲止,留有餘地的人生與政治智慧與處世方式相同。湯用彤先生指出:“言意之辨,不惟與玄理有關,而于名士之立身行事亦有影響……學貴自然,行尚放達,一切學行,無不由此演出……由重神之心,而持寄形之理,言意之辨,遂亦和于立身之道。”(35)因而,此種“立身之道”也是王導在波譎雲詭的政治生涯中所反映的爲人處世之道,在他面對庾亮争權與陶侃非議時的態度上有充分的體現。最爲典型的一例《太平御覽》卷五九三引《語林》載:“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日不能見王公。”這種點到爲止從容不迫的優雅與其個人學養固然密不可分,但從中可以看出,王導政治城府之深,换了王敦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他對于諸事的處理,特別是在處理旁人看來無法調和的王敦與司馬氏皇族之間的矛盾時,將玄學運用得很成功,也因此留下許多被人非議的地方,比方說他過分袒護王敦等。儘管他從表面看來,一副謙卑有禮,超脫邁達的樣子,殊不知,他對玄學的領悟與利用其實無不關切著實際的人生。他那種玄學家超然世外的姿態也不過是其政治人生的一件避雨衣。
因此,我們要好好體會王丞相對于玄學政治前所未有的發揮。本文此前提到,以往的研究中,基本是把“三理”所體現的政治作用分開來談。我們更應看到,它們之間的交融。“儒學自有其社會作用,是玄學所不能代替的。玄學陣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對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含于玄學之中,或者尚獨立存在于玄學之外,繼續起著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國志·魏志·王昶傳》記載王昶誡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數當政居位的玄學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傾向”。(36)王導、謝安、庾亮都是這樣的人物。然而,王導無論在個人得勢或失勢之間,都很會把握分寸,力使自己行走于不敗之地。在政治領域,他則“非常冷静務實地選擇了有效協調社會秩序儒家學說作爲基礎,結合社會形勢利用玄學清净自然哲學服務于國家大政。王導兼治儒道的政治實踐,直接體現了東晋士大夫統一名教與自然理論探索的結果”(37),將有著强烈儒家色彩的《言盡意論》附著在《聲無哀樂論》與《養生論》後,實在不失爲周全之舉。把這玄學三題相連接乃是打通儒道兼治理論暢通無礙施行的最佳組合,也是王導爲東晋初期社會治理開出的藥方。
4.成帝時期,已到了王導的晚年。雖然之前王導固然堅决拒絶元帝要他共升御床的邀請,然而他對後來的成帝却明顯缺乏敬意。《晋書》載:“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嘗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于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38)在成帝完成加冕儀式後朝中大權仍由王導掌握,侍中孔坦深表不滿而冒犯了他,即被貶爲廷尉。還有,王導對于自己親信的不法行爲也都予以袒護。《晋書·庾亮傳》引:“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他對這些人的不法行爲没有繩之以法。這些都是王導個人的政治污點。在《晋書·孔愉傳》中也有材料佐證,“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這個以“守正”著稱的尚書僕射孔愉也是歷經元明成三帝的老臣,當年王導被元帝疏遠的時候,他“陳(王)導忠賢,有佐命之勛,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然而,咸和八年他重表上書主張“宜併官省職,貶食節用”被批准的時候却遭到“王導聞而非之,于都坐謂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可以看出,王導在考慮保護士族的利益態度上是很堅决的。就是通過這類事件的積累,晚年的王導在政治上確被許多人非議,這也是他自言“憒憒”的地方吧。
雖然,王導一生的功過是非很受世人争議,但正如陳寅恪所稱,他對抵抗外辱,民族獨立,文化續延等方面作出的貢獻依舊不可輕易抹殺。東晋以來,司馬氏皇權孱弱,使得士族與皇族之間紛争不斷,以怎樣的方式處理各方矛盾實爲一棘手問題,王導利用“鎮之以静”的玄學政治確實化解了不少争端,堪稱治國之典範。成帝稱他“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晋書·王導傳》),但他個人政治生涯中一些不體面不厚道的事情也爲世人所譏。這個以玄學政治著稱的宰相期待後人對他的理解,因他一生爲國家爲家族從未敢懈怠。孫綽在《丞相王導碑》中評價:“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弘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咏,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己以招岩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鈎,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勛舉。非夫領鑒玄達,百煉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動與理會者哉?”(39)肯定了王導東晋以來領動衆等對玄學義理的繼承與發揚,功不可没。
透過解析王導過江只言三理,我們可以看到東晋政治與文化的一體化,達到高度的自覺的地步。它是中國政治文化遺産的重要部份,即使在今天,也有值得繼承的價值。正因爲此,唐人編修的《晋書·王導傳》心儀晋人之美,遂多贊嘆之語。但是因爲中國社會長期以孔孟之道爲治國之正統,引來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中的大駡。(40)王氏作爲清代史學名家,受清代正統儒學的制約是很明顯的,從而遮蔽了許多歷史事實,評價晋人没有擺脫歷代儒者的偏執。今天,我們應當從尊重歷史事實的立場出發,既無需溢美晋人王導,也無須站在傳統儒學正統的立場上去指責王導的玄學修養,而應當結合當時的歷史情境,加以認真的解讀與評價,正確研究歷史與評價古人。
①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文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49頁。
②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9~61頁。
③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206頁。
④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6頁。
⑤房玄齡等:《晉書·王衍傳》,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236頁。
⑥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7頁。
⑦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0頁。
⑧《世說新語箋疏·方正》,第305頁。
⑨《晉書·王導傳》,1745頁。
⑩《晉書》卷五十八《周處傳附子周勰傳》,第1574頁。
(11)《世說新語箋疏·文學》載:“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嘆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椽,輒翣如生母狗馨。’”(第250~251頁)可見,過江後,王導諸人對於清談興致絲毫未減,依舊通宵達旦。
(12)《金明館叢稿初編》,第54頁。
(13)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2頁。
(14)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90頁。
(15)同上,第112頁。
(16)《世說新語箋疏·賞譽》,第524頁。
(17)《晉書·王衍傳》,第1238頁。
(18)《世說新語箋疏·雅量》,第416~417頁。
(19)同上,《容止》,第721頁。
(20)同上,《企羨》,第742~743頁。
(21)《世說新語箋疏·規箴》,第668頁。
(22)《金明館叢稿初編》,第55頁。
(23)姚曉菲:《兩晉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8頁。
(24)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513頁。
(2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993頁。
(26)同上,第1420頁。
(27)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223頁。
(28)《嵇康集校注》,第145頁。
(029)《晉書·王導傳》,第1752頁。
(30)《中國美學史》,第219頁。
(31)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8頁。
(32)《嵇康集校注》,第221頁。
(33)《王弼集校注》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98頁。
(34)《晉書·王導傳》,第1753頁。
(35)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及其他·言意之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9頁。
(36)《東晉門閥政治》,第340頁。
(37)秦躍宇:《六朝士大夫玄儒兼治研究》,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第301頁。
(38)《晉書·王導傳》,第1751頁。
(39)嚴可均輯:《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第647頁。
(40)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論曰:“《王導傳》一篇凡六千餘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實乃並無一事,徒有門閥顯榮、子孫官秩而已。所謂‘翼戴中興,稱江左管夷吾’,吾不知其所在也?”(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頁)顯然,這一說法罔顧史實,因而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加以辨駁,但陳先生的文章中,對于王導過江後所言“三理”沒有加以具體論述,本文也算是對此的補充申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