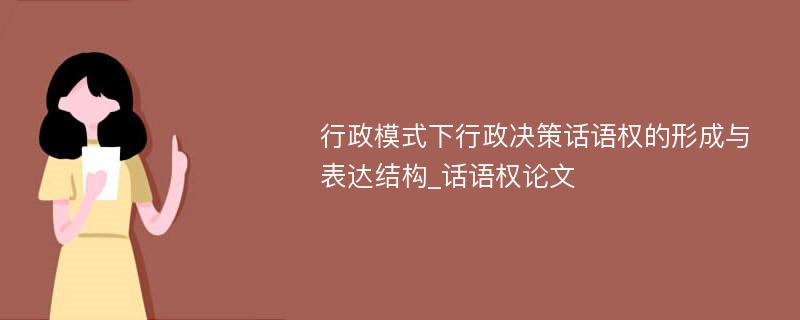
行政模式中的行政决策话语权阐释:形成与表达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论文,话语权论文,模式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3)03-0075-05
福柯指出: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控制,然而它在社会中是一种真实的权力。行政模式的核心是行政决策,从表现方式来说,行政决策权在行政过程中需要通过行政决策话语权来外显,也就是说,每一种行政模式中都包含制定政策的话语权和争端解决的话语权,统称为行政决策话语权。本文从决策话语权的视角,把统治行政模式、管理行政模式和服务行政模式中的行政决策话语权分为“支配型”、“管制型”和“合作型”三种,并试图阐释不同行政模式中的行政决策话语权的形成与表达结构。
一、“支配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形成及其表达结构
农业社会统治行政模式的目的是保持统治权的稳定。无论是以王权或皇权为基础的专制统治,以分封为基础的封建领主统治,还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教权统治,统治权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失去了统治权,统治者将一无所有。为了实现统治目的,统治者除了对军队等暴力组织进行培育和控制以外,另一个方法是对行政决策话语权的合法性进行建构和强化,培育形成一种“支配型”行政决策话语权。
(一)“政治神话”与一元行政决策话语权主体的合法性建构
行政决策话语权是一种真实的行政决策权力。在这种权力关系的形成过程中,话语权主体的合法性建构最为关键,是保持行政模式有效运行的前提。在合法性的建构方式上,统治行政模式普遍选择的方式是“政治神话”。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社会,“政治神话”认为“君权神授”,统治者被认为是神的代理人,统治者的权威是建立在神意之上的,人民对统治者的顺从也就是顺从神的意志。人民的意见无足轻重,甚至不起作用[1](P327)。从行政决策话语权的角度来解读,那就是,统治行政模式中,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借助“政治神话”、“神意”建构取得和控制了行政决策话语权;与此同时,在这一合法性建构过程中,统治者“绝对剥夺”了被统治者的行政决策话语权,成为了行政决策话语权中的一元主体。
统治行政模式中的一元行政决策话语权主体决定其决策方式。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一直被视为是天子,是孤家寡人,拥有原初的、绝对不可动摇的行政决策话语权,皇帝的命令是金言玉律,是圣旨,等同于法律而被统治者因为没有被纳入决策话语主体范畴,只有服从的义务。在同时代的西方也存在类似的行政话语主体结构。比如,在古希腊、罗马,神的话语权是占主导地位的,身为祭司的行政首领对天鸟飞过的痕迹或龟甲裂纹极度依赖,没有了神谕,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在社会大事前便无所适从[2]。到了中世纪,上帝的福音依然不可质疑,无可否认地成为统治者建构行政决策话语权合法性的基础,即使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一情况也没有多大程度的改变。
托克维尔用反讽的语言对法国的民主会议做出这样的评价。他说:“教区的这种民主会议能够充分表达各种心愿,但是它和城市政府一样,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当别人打开它的嘴时,它才能讲话;因为只有在求得总督批准后,并且像人们当时所说的那样,身体力行‘悉从尊便’时,才能召集会议”[3](P90~91)。葛德文指出,“政权本来应该是一种最不可抗拒的必要,它无可争论的是一件使人感到痛苦和受拘束的事。它使别人成了我的行动的公断人和我的命运的最终支配者。”[4](P152)尽管这一观点没有表明统治行政中行政话语决策主体的一元性,但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统治行政模式中,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支配,而这种支配实质上是一种决策话语权支配。
(二)维护一元行政决策话语权合法性的两种隔离力量
统治行政模式中一元行政决策话语权主体确定以后,有效运行这种行政决策模式,保持其合法性,还有赖于环境的力量,那就是话语隔离。话语隔离指由于有效的沟通渠道无法形成,并导致不同话语主体无法沟通或不能有效沟通的话语状态。统治行政模式利用两种话语隔离的力量来维护其行政决策主体中一元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即硬隔离和软隔离。硬隔离又可以称为地域隔离。由于受交通和通讯能力的限制,农业社会的地域边界是一种很难逾越的边界,不同地域的部落、氏族或者王朝很难跨越地域隔断进行交往,统治者借助这种边界的力量,使之发展成为话语隔离的环境,这是话语隔离的天然力量。软隔离是由于语言、习俗和信仰等原因而形成的话语隔离,这种隔离力量是不同地区、民族的语言、习俗的差异所导致的。即使言语隔离化解后,习俗和信仰隔离也一直是话语隔离的门槛。因此,基于不同习俗和信仰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心态成为话语隔离最顽固的力量,也成为维护其一元行政决策话语权主体的基础。
统治行政模式中话语硬隔离和软隔离的力量强大无比。话语硬隔离是一种“隔绝”,话语软隔离是话语权的剥夺。在古罗马,如果城邦成员离开了所在的城邦,则意味着既剥夺了行政话语决策权又剥夺了生存话语权。亚里士多德描述过古代城邦话语隔离所造成的悲惨状态:“如果被放逐,不能不离开乡邦、舍其坛火,则为重大的罪责,仅次于死刑。”[5](P7~8)即使到了今天,由习俗和信仰所引起的价值和文明差异,依然成为行政决策话语权中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代环境下,不同宗教国家的冲突起源与话语隔离有重大联系。
(三)仪式化对“支配型”行政决策话语权合法性的强化
农业社会恰恰是一个仪式化的社会,仪式规范既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又体现在统治过程中。由于仪式具有规范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的功能,统治行政模式自然而然地采用仪式来强化支配型行政决策话语权。在古代中国,“朝政”不但与等级列队、跪拜和维诺等仪式相伴随,“诏书”等法律文件也与形式化的话语相伴随。在西欧封建社会,仪式化在“臣服礼”中得到了明显体现。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两个人对面而立,其中一方愿意为另一方效劳,另一方则愿意或渴望接收他人效劳;前者合掌置于另一人双手中——这便是服从的简单象征。这种服从的意义有时进一步由一种跪拜姿势加以强化。同时,先伸出双手的人讲几句话即表示一个简短的宣言,承认自己是面对着他的整个人的‘人’。然后主仆双方以唇相吻,表示双方的和谐和友谊。表示臣服关系的姿势就是如此。”[6](P250)斯宾诺莎指出,“所有仪式的规则是,人完全不随自由意志而行,一举一动须完全受外界权威的约束,并且他们的行动与思想,不断地表明他们不能自主,而是完全受别人的控制。”[7](P84)在这个礼仪化的过程中,话语权中的支配与被支配角色通过仪式化的过程得到了强化。
统治行政过程中的仪式包含着展现等级支配、约束与服从的规范意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仪式成为统治行政模式中的重要部分,所有堂皇的仪式内含有规范力量的行政决策话语,体现出约束、支配和服从的力量,这些仪式与统治行政体系所要求的社会服从和等级服从相融合,一体性地作用于被统治者,很好地强化了统治行政模式中的行政决策话语权。
(四)“支配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表达结构
通过话语主体、话语隔离和仪式化,统治者的行政决策话语权有了合法性基础,鉴于这一行政决策话语权的基本特性,我们把这种行政决策话语权叫做“支配型”行政决策话语权,它的基本特征是命令与服从。与之相适应,这种行政决策话语权有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即话语权表达结构。统治行政模式中的“支配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表达结构是“发话”与“回话”。这种话语表达结构有三个特征,其一,在行政决策过程中,拥有一元决策话语权的统治者以不可置疑的断语下达命令,支配着整个统治行政体系和统治领域。其二,在这种话语表达结构中,话语的指向是单向的,统治者是发话者,被统治者是回话者。这一决策话语权要求被统治者全部接受统治者的命令。其三,这一决策话语权的作用力是射线型的,发话者是单向的发力点,是命令者,回话者是受力点,只能是服从者。
二、“管制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形成及其表达结构
在社会工业化的过程中,民主和自由慢慢成为了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指针。密尔认为,人的自由,包括人身、意志和社会意义上的公民自由,它们界定了“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性质和限度”[8](P1)。哈耶克指出,“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照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9](P4)随着现代政治体系中民主和自由成为具有社会力量的政治符号后,它所形成的力量也逐步改变并最后摧毁了以命令、支配和服从为基本特征的统治行政模式。在管理行政模式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行政决策话语权——“管制型”行政决策话语权。它的形成与现代政府的政治体制、组织体制和制度特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代议制政治体制对行政决策话语主体的分离
普选制和票决制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的两个基本机制。乔萨托利指出,选举不是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谁来制定政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谁来解决争端[10](P115)。我们认为,恰恰是这种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分离了公民和政府这两个决策主体的话语权,基于这一政治体制发展起来的行政决策话语权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方面,公民在政治上有了平等的选举权、投票权,从而取得了政治话语权,因为民主选举意味着在行政决策话语的主体结构中增加了公民这一主体,行政决策话语中体现了公民权利,所以,管理行政模式中的行政决策话语权主体是二元的,包括公民和政治精英。另一方面,在现代国家的决策话语权中,公民和政府这两个主体是分离的。前者拥有的话语权力是阶段性的,在“一人一票”之后,行政决策权和争议解决权交给了权力机关和票选后的民主精英组成的政府。
在分离的二元主体决策话语体系中,国家对内主权的自大、公共产品的垄断性供给和公共产品的单一性这三个来自国家和政府的因素循环作用,加剧了行政决策话语权主体的分离。其一,国家对内主权的自大。现代国家对内主权的自大表现为政府占据社会管理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处于公共领域的中心,公民和社会处于公共领域的边缘。所以,公共行政很多时候被认为就是政府行政。其二,公共产品的垄断性供给。与国家主权的自大相伴随,政府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既具有认识公共利益的知识,又具有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的能力,自然而然地垄断着公共产品的供给。弗雷德里克森指出,“在我们社会的政治思想中流行这样的一种假设,即只有通过政府的程序才能创造出公共,只有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才能使多数人的意志合而为一”。“我们把公共看成是政府、选举和民选官员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事情。”[11](P22)其三,公共产品的单一性供给。单一性供给是管理行政模式供给公共产品的基本方式,这一供给方式与工业社会标准化的社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是,它是前两个因素连续作用的结果。在一个主权自大、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行政模式中,肯定伴随着公共产品供给的单一性。
(二)管制型行政决策话语权中的组织隔离
官僚组织体系是层级制与部门制相结合、具有牢固边界的组织体系。与统治行政模式中的话语隔离不同,管理行政模式中的话语隔离是通过官僚组织结构来形成的。对行政决策话语权而言,官僚制组织结构中的部门管理和层级服从形成了行政决策话语权的边界。部门制表明了不同行政部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领域和权限;层级制划分了行政决策过程中上下级决策公共事务的边界和争端的解决权限。因此,在横向的领域边界和直线的层级边界形成后,官僚制组织中便存在了错综复杂的行政决策话语权区域和话语权边界,形成了行政决策话语权的组织隔离。
因为这些行政决策话语权边界的存在,导致行政体系行政决策话语权的离散,致使行政决策失去了系统性,从而导致了管理制度“打架”。另外,行政决策话语权边界的存在,还导致了协调的复杂性,所以,在集体行动的协调过程中,除了高层次的行政权力能够对这种隔离性的权力进行协调外,官僚制组织没有设置打破结构性边界的机制。官僚制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话语隔离,既强化了行政体系内上级对下级的管制,也导致了不同部门之间平等的沟通和对话。
(三)管制型行政决策话语权中的制度隔离
在官僚组织的运行过程中,规章、制度、文件等形式化的制度,是官僚体系与公民进行沟通的媒介。韦伯指出,“任何神权政治或任何专制主义的司法都是以实质为取向的,相反,官僚体制的司法则是以形式法为取向的……”[12](P721~723)进一步说来,任何形式化和程序性的制度都有强制性的特征,都会在政府与公民之间产生话语隔离并形成一种管制性关系。威尔逊指出,“能够轻易通过规章来定义的官僚主义行为一般都是那些频繁的、相似的和成型的东西一是那些例行公事的东西”[13](P459~460)。因此,官僚制度是管理行政模式中话语隔离的因素。从而,在管理行政模式中,在政府和公民之间,还有一种话语隔离——我们称之为“制度隔离”。
总之,由于“组织隔离”和“制度隔离”的存在,管理行政模式对内设置了上下级之间的对话障碍,对外拦截了政府和公民之间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对话,形成了一种强制性而僵硬的行政决策话语。卡蓝默认为:“从本质上说,官僚主义更是对于社会的过于简单化的、错误的表现体系。官僚主义是一种既破坏公民自由也破坏公务员自由的方式。官僚主义是拒绝‘进入理解’,对于提出问题予以直接回答的复杂性和后果的回避”[14](P35)。
(四)管制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表达结构及其变化
根据管理行政模式中行政决策话语权内外的管制特征,我们把这种行政决策话语权称为“管制型”行政决策话语权,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表达结构。在古典行政阶段,管理行政模式的行政决策话语权的表达结构是“独自”,在公共行政领域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状态:不管公民如何反应,政府总是自说自话,政府有时让公民参与决策讨论,很大程度是为了辅证政府早已确定好的政策。
管理行政模式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独自”式的话语权表达结构受到了普遍批评,并导致了政府失灵。因此,一些民主行政理论家强调行政人员要“倾听”公民的意见。福克斯和米勒指出,“倾听是话语理论暗含的一种前提责任。不会倾听会造成不良后果。一个不会倾听的公共行政者会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分子,只忠诚于‘行政’。”“倾听就是工作,而且它也表明了一种关切的态度,体现了真实话语的一种愿望。”[15](P151~152)这是对“管制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挑战。但事实上,在管理行政模式中,即使“倾听”成为政府行政决策话语权的一部分,但在官僚制组织中,倾听仅仅是一种单方面的话语状态,纵使有愿意倾听的行政人员,也只是一个单向接收信息的渠道,只是一种信息向上传递的方式。
三、“合作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生成的公共空间
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服务行政模式,特别是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背景。在这一新的治理背景下,公民权的成长与壮大、实质性平等的公共管理关系的形成、新的“共同决策”模式和基于互联网的话语沟通空间的出现,为“合作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生成提供了空间。
第一,“合作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政治生态空间——公民权的成长。一种新的行政决策话语权的形成需要新的政治生态空间,这种新的政治生态空间允许新的行政决策话语权主体的出现。国外学者通过研究美国公民权的发展历史指出,“产生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公民权运动,不但促进了参与公民权运动的组织的各种社会技能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处理公共问题时方式的改变,使之认同了通过对话解决公共问题的途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讨论环保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环保政策”[16](P384~385)。这一政治生态的改变,政府、利益集团和公民等多元利益主体便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争议,意味着公民被赋予了参与解决争议的话语权。这一行政决策话语权主体的改变,为新的行政决策话语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二,“合作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生成的公共管理主体关系空间——合作治理主体实质性平等关系的形成。后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政府无法垄断性地处理公共问题,也无法单一地承担所有的社会责任,合作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促进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需要将管理行政模式中竞争型的社会治理思维转变为合作型的社会治理思维。相应地,服务型政府只能是一个与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合作型政府。在合作行政过程中,服务型政府需要与各种社会组织形成一种实质性平等的公共管理主体关系。这种新型的公共管理主体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是公共管理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实质性平等。这就决定了它们之间能够处于良性的交流与互动状态”[17](P71)。从行政决策话语权的视角看,公共管理伦理的实质性平等关系,意味着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将形成一种平等的行政决策话语权。
第三,“合作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决策模式空间——共同决策模式的形成。共同决策模式的出现是因为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都意识到管理行政模式中以政府为主体的传统决策模式——“决策—宣告—辩护”模式的严重缺陷,希望开创一种共同决策的新模式。这种共同决策模式中的要素包括直接参与、平等基础上的参与、面对面的交流和共享政策制定的能力等;同时,试图在政策制定中为公民创造一个角色,并通过合作性学习的途径,让参与者相互学习、探求价值、定义难题和评估解决问题的潜在方案[18](P757)。可以看出,共同决策模式为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赋予了行政决策话语权,意味着具有实质性平等公共管理主体关系的合作主体,可以平等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来。
第四,“合作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沟通渠道——互联网络平台。互联网打破了地域隔离、组织隔离和制度隔离等话语沟通的障碍,在一个话语狂欢的公共对话平台中,政府无法回避与公民进行直接对话,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受到严重质疑。2001年3月,英国议会发表了《开放渠道:科学和技术中的公共对话》,报告指出:“公共对话的主旋律已经进入了科学、技术、工程和医药领域。”因此,“各种机构在处理与科技相关的问题中进行文化变革是必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扩大公共咨询和对话程序的使用范围,从而使公民积极介入公共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制定之中”[19](P1~3)。
总之,在新的社会治理背景下,公民权的成长、新的公共管理主体关系的形成、新的决策模式的出现和决策沟通渠道的完善,意味“合作型”行政决策话语权的生成有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收稿日期:2012-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