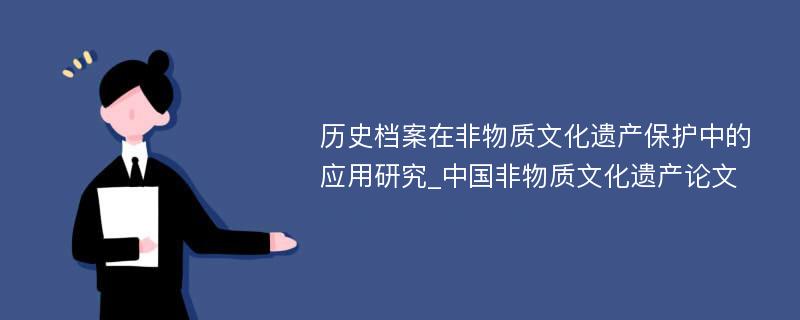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历史档案利用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遗产论文,历史档案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5264(2009)04-0017-04
我国历史档案泛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档案,是历代各级各类权力主体、民间组织及个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类原始记录或相关文献资料的总称。由于历史档案记录和承载了数千年以来我国各民族各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活动信息,因而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历史查考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本文结合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于档案工作支持的现实需要,分析了历史档案利用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历史档案利用的基本原则。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档案关系探析
按照现代档案学关于档案是一种“原生固化信息”的科学认识,历史档案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历史的原生固化信息”,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同属文化遗产范畴,都是社会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并将继续见证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历史。
笔者无意于强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档案的属性上“物与非物”的纷争,但仅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档案的关系而言,认为形成如下共识是必要的。
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历史现象的现实存续,历史档案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二者都具有“历史文化属性”的本质特征。换句话讲,被活态传承下来的那部分社会历史现象我们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固化保存下来的那部分社会历史原始记录我们称之为历史档案。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将二者统称为历史文化遗产。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档案的核心内容都属信息范畴,都需要在更高层面审视“物与非物”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1],通过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相关的器具、实物和手工制品等),展示特定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与精神内核等人类文化信息,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不是物,也不是人,但又离不开人,离不开物”[2],“人”和“物”便成为“非物”物化的直接媒介;虽然档案信息论告诉我们,档案信息“是指来源于档案的能消除人们不确定性的,反映已经发生的各种事物运动状态、方式及其规律的征象或知识……是指依托于载体但又不包括载体的知识内容”[3]。然而档案信息同样不能脱离载体存在,甚至对同一信息内容而言,载体不同,承载的信息也不尽相同(历史档案更是如此)。因为内容和载体是构成档案的两个基本因素,二者相互依存并高度统一。
其三,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档案同属历史文化遗产,其核心内容又都属于信息范畴,那么二者的逻辑关系完全可以在历史文化信息意义上得到高度统一。而共同的历史文化信息属性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档案关系的逻辑起点。
二、历史档案利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意义
从逻辑关系层面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档案之间的联系,目的在于对随后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历史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二是在历史档案(包括研究)工作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发掘与利用。这对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档案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历史档案利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意义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档案中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重要资源。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是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成果、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真实的重要举措,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若干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解决,但笔者认为以遗产工作为主线、以遗产项目为核心、以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的基本思路是应该明确并得到坚持的。由此我们也提出了以项目、历史、工作和传承人为结构板块的“四位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体系”的基本构想[4]。
从结构分工的角度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记录和反映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即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方式与特殊文化内涵。体现为档案由历史向现实的集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流变历程,是从史书、文物及相关文献中提取或挖掘出来的档案史料的有序整合。历史档案资源的利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加拿大前国家档案馆馆长让-皮埃尔·瓦洛所言:“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淘走了多少历史的积淀,犹如那些为淘金者淘去泥沙的河流。档案这种金子就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它也是民主、法制和公共行政的金子。它归根到底是显示各个集体、民族同一性的金子”[5]。
第二,历史档案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直接证明。
档案固有的凭证价值决定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独特和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知识产权)主权纷争的今天,历史档案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便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最有力的证据,因为“档案是契约文件、行动记录和议事记录,是已做或计划要做的事、所体验和表达的思想感情和社会重大争论的可靠证明或根据”[6]。
2005年前后关于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争论,对很多人来讲也许还记忆犹新。在众多国人因为韩国抢得先机而愤愤不平的时候,不少理智的专家学者则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包括历史档案在内的大量文献资料完全应该能够证明中国在“端午节”文化遗产上的产权地位,韩国此举并不会影响中国的“端午申遗”行动。事实上,在我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第三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前,阿塞拜疆、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并塔吉克斯坦早就申报了自己的木卡姆艺术,且同时入选第二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因此,关键在于得拿出足够的证据。历史档案的使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围绕主题进行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可以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到持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能否得到健康发展,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内在的历史积淀,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但归根结底取决于包括特定文化主体(原住居民)在内民众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影响下的积极的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氛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WCCD)在一份报告中,以濒危语言为例说明文化遗产保护应有的态度和核心的依靠力量。报告指出:“应该以一种发展的眼光而不是怀旧的情绪来对待文化遗产……在人类历史上,许多语种都消失了,这方面,靠政府法令是保护不了的,靠民俗学者的学术兴趣也于事无补,它们所能够依赖的,只有说这种语言的人本身”[7]。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表面繁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后,不仅全民社会意识没有提升到想象中的高度,就连文化遗产的固有主体也由于各种原因而存在流失的危险。沙马阿青在《泸沽湖摩梭文化生态旅游区的开发与摩梭文化的保护》调研报告中忧心忡忡地说:“(摩梭)年轻人对于汉族的时装非常感兴趣,纷纷穿上汉人服装,而民族服装只在节日和接待游客时穿,成了‘礼服’和‘工作服’;对本民族的歌舞兴趣不浓,往往只是唱给游客听、跳给游客看,而对流行歌曲却十分感兴趣”[8]。
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在于以人为本的文化持续认同感的培养与传承。因此,通过挖掘档案史料、编纂档案文献、撰写专题史志、公布特色资源信息等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提升公众的遗产认知度和遗产主体的文化自豪感,不仅是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更是加强遗产教育传习、培养和壮大遗产传承群体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包括国家保护中心在内的全国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览、相关读物或专著的出版,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也无不从历史档案文献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历史档案利用的基本原则
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档案之间的紧密联系,且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本质关联,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历史档案信息资源,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档案工作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等,便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努力开展并切实加强历史档案利用工作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效、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为此,必须坚持以下利用原则。
1.历史真实原则
历史真实既是档案的生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历史档案资源利用的历史真实原则,就是要维护历史文化现象的本来面目,不能对历史档案进行断章取义,更不能道听途说或以讹传讹。即在利用历史档案时一定要注意鉴别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真伪,坚持去伪存真,坚守历史本真,维护文化原形。
2.资源安全原则
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既是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档案利用的基本前提。历史教训证明,人为原因导致大量档案流失和损毁,早已成为危害档案安全的头号杀手。历史档案是一种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档案资源,在开发利用历史档案服务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应该同样高度重视对历史档案的保护。因此,保证历史档案实体的安全,维护历史档案体系的完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历史档案利用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以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为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清代上至入关前天命九年(公元1607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中央各部门的满文档案200余万件,辽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各保存有满文和满汉合璧的档案2万余件(卷);藏文历史档案仅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珍藏的就有90个全宗300多万册(份);各地保存下来的东巴经约有4万余册;彝文纸质档案现有5万余(件)册;今存傣文纸质档案8万余(件)册。少数民族文字碑刻有数千余方,摩崖有数百处,印章有数千方[9]。这些历史档案,多姿多彩的形制种类、古朴博大的文化内涵,不仅可以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强大的信息支持,其本身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3.资源效益原则
我国各族人民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包括历史档案在内的各类文化遗产,为中华文化享誉世界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也构筑起强大的精神支柱。历史档案由于承载着社会变迁、文明冲突、价值信仰、族群嬗变等原生历史文化信息,决定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保护与传承、发展诸方面具有无可取代的资源优势地位和广阔的利用前景,也必将成为长期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问题。贯彻资源效益原则,就是要尽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正面效益最大化与负面效应最小化。具体来说,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充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方面要防止因不善保护和过度开发而造成的损毁,不善保护包括不会保护和不当保护,前者如韩国某公司抢注“端午节.cn”后,我国以3万美元进口该中文域名,后者如借创新之名随意篡改非遗,严重损害其原真性;过度开发破害尤甚,不少地方把非遗当“摇钱树”,随意修改民俗和工艺,使之成为招徕游客谋取利益的现实手段[10]。
4.以人为本原则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最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笔者以为,开发利用历史档案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不断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娱乐人民群众身心的同时,不断增长民族才干、创新民族文化、培育民族自豪、凝聚民族力量,从而激发爱国热情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因此,开发利用历史档案服务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说到底,实质就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进步与我国社会的持续和谐。
5.整体生态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历史档案是一个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此,开发利用历史档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着眼于系统结构的整体性,又要着眼于系统环境的平衡性。换言之,就是在开发利用历史档案服务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要妥善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设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第一,合理建设,科学创新”的正确观念,只有做到“保护为纲,纲举目张”,才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目的;二是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保护关系,包括不同级别、不同文化空间、不同传承形式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一视同仁,全面开发,协调发展,整体推进,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体系;三是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环境(文化时空)的协调关系,努力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谐环境。
标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