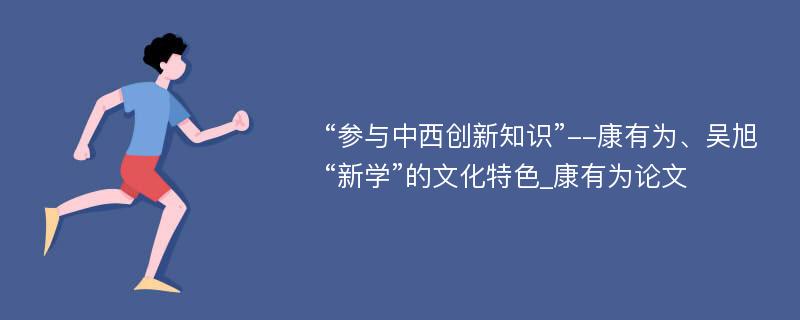
“参采中西创新知”——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康有为论文,特征论文,新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6)06-0059-09
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标志着近代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奋然勃起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新学”,成为那个时代及其以后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主题。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说:“先生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1](P9)由此,“爰有康、梁新说之奋兴焉”[2](P20)因此,深入探讨康之新学形成的学术路径及其文化特征,有助于我们对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时代特征的把握。
一
甲午战争是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谭嗣同说他30年以前所学都是旧学,30年后所学都是新学,而“三十年适在甲午,地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3](P259)梁启超也认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P249)“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无疑,甲午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及其年代,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旧学向近代新学转变的一个历史界标。
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意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直接推动并加深了进步思想家们对于中国近代化道路选择的重新思考。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体同时,是双方学习西方和走向近代化的最初选择。但是,曾经站在同一起点上的中国和日本,经过30年的竞走,在甲午重逢时,已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一胜一败,一强一弱,一个跻身于西方列强之林,一个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其相差又何其巨也!正是甲午战败的事实,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重新检讨中国的近代化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运动过分偏重于引入西方物质、技艺的“制器为先”的选择,开始从“政体”和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近代化道路的选择。
基于对中国变革方向的重新选择,梁启超对于洋务运动作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国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1](P273-274,276)
因而,如果没有政教、学术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徒以洋务琐事虚饰新政,即使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改革与不改革何以异乎?”[1](P273-274,276)至少在康、梁的眼中“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应该承担战败的全部责任。“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1](P275-276)
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认识的逻辑进程,都表明在甲午战争之后,社会进步人士已经开始了超越洋务所限,救亡之策的探讨终于超越了洋务的方案,开始从学术文化的本原上从事旧学的改造和更新,人们救亡图存的眼界从“制洋器”转向了“变政体”,从“采西学”转向了“新学术”。“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1](P45)因而,着力于传统旧学的更新变革遂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首要选择。
作为近代“新学”主要代表的康有为的学术文化的转向也正好发生在这一时代潮流的转折之中。他一方面借助于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功底从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一方面以所能接触到的西学新识改造传统学术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新学’与‘新政’的基本支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划出了文化观念的分界线。一个对西方文化具有了新认识,从而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的新学派,应运而生了。”[4](P187)由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学”,就以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出现,为近代学术文化的弃旧图新和政体革新,寻找到一种学理依据。那么,康有为的“新学派”的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
二
与康有为交往颇多而又学旨不同的朱一新,对于康之“新学”持反对立场。朱认为,学术不应以求新奇为旨归,“夫学术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厌平澹,导之者复不以平澹而以新奇。”[5](P1032)正是适应了“世之才士”“喜新奇”的潮流,康、梁新学一问世即引起“少年新进,从之者众”(《康圣人的故事·追忆康有为》)的社会效应。那么,康、梁新学新在何处?①
导致康有为舍弃旧学的最直接的学术根源是西学,此一问题学界论述已多,此不赘述。现在我们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康有为创立的“新学”体系中,西学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西学的那些内容构成了他新学中的主要内容?
对于西学的认识,康有为显然超越了洋务派局囿于“技艺”的水平,而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洋务派“仅言炮垒、军备、兵舰、船政、译言诸粗节细末,无统筹全局而请言变法者。中国请全变法之疏章,实自先生是书为始(指光绪十四年上书言变法事——作者注)。”(陆乃翔等《南海先生传·追忆康有为》)康有为认为,西人政教风俗,自有其根本,不能简单以“本末体用”而自塞眼界。他基本上是以一种文化平等的态度来权衡中西的。在答复当时讲学于广雅书院的义乌朱一新(独尊宋学的旧学家)说康是所谓“阳尊孔子,阴祖耶稣”的诘难时,康有为十分客观地陈述道:“吾今且以质足下,以为今之西夷与魏、辽、金、元、匈奴、吐蕃同乎?否乎?足下必知其不同也。今之中国与古之中国同乎?异乎?足下必知其地球中六十余国中之一大国,非古者仅有小蛮夷环绕之一大中国也。今以不同于匈奴、吐蕃、辽、金、蒙古之西夷数十国,其地之大,人之多,兵之众,器之奇,格致之精,农商之密,道路邮传之速,卒械之精炼,数十年来,皆已尽变旧法,日益求精,无日不变,而我中国尚谨守千年之旧敝法。”(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在康有为看来,中西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什么文化之不同,而在于“变法与否”。西国之强盛是因为“尽变旧法”,中国之弱衰是“守千年之旧法”。同时,康有为还完全打破了所谓在“伦常礼仪”文化方面,中国远高于西国的观念,特别强调指出:
至于三纲五常,以为中国之大教,足下谓西夷无之矣,然以考之则不然。东西律例,以法为宗。今按法国律例,民律……第三百七十一条云:‘凡一切子女,无论其人何等年岁,须于其父母有恭敬孝顺之心。’三百七十二条云:‘凡一切子女,为其父母所莞属。’……第二百一十三条云:‘凡为妇者,应为其夫者所管属。’……第一百零八条云:‘凡既经出嫁之妇,不得自谓有家居之所,应随其夫之家以为家’。(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
因此,从文化的内核即“伦理道德”“人心风俗”来看,中西本无不同,“岂非庄生所谓‘父子天性也,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凡人道所莫能外’乎!”‘有国有家,莫不同之,亦无中外之殊也。”[15](P1039)原本被认为是中国独有而且引以自傲的“伦理教化”,经康有为“会通”解释后,成为无分中西的人类共有的文化特征,所谓“其立国家,治人民,皆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凡地球内之国,靡能外之”。康有为认为,中西学术文化本无上下高低之分,只有并存相济之功。“方不能有东而无西也,位不能有左而无右也……是二教者终始相乘,有无相生,东西上下,迭相为经也。”(《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时代课题。“师夷长技”和引入西学的洋务运动突破了“夷夏之辨”的文化窠臼,却又不得不在“中体西用”和“中本西末”的思想桎梏中艰难跋涉。康有为却认为中学与西学不仅是互补的、平等的,而且也是相互依存的。因而,西学之圣与中学之圣具有同等地位:“总言之曰:立气之道,曰阴与阳,曰热与重;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国之圣人以义率仁,外国之圣人以仁率义。”(《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这无疑在说,中学与西学特性虽异,但均为圣人之传,是可以相通的。不以‘中国之圣人’创制留传下来的中学为满足,属意汲取‘外国之圣人’创留传下来的西学,会通中西以创建新学之意已经呼之欲出了。”[4](P201)
摒弃了中西文化价值上的偏见后,康有为认为西学“是本质上比中国旧学更为先进的学问”[6](P43),因而“尽释故见而大讲西学”。当然,西学作为构成康之思想体系的重要成分和思想来源,已经涵化在他所有的论著中,但能够代表康有为大讲“西学”的著作,却主要是《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诸天讲》等。
《康子内外篇》是康有为写于1886年的作品,也是他接纳西学后比较完整地代表他融会中西的主要著作。全书15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作为阐述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类著作,西学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康有为解释体系中的新成分。“仁者,热力也;义者,重力也;天下不能出此二者”。(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在宇宙起源的问题上,康有为认为“若积气而成为天,摩励之久,热、重力生矣,光、电生矣,原质变化而成焉,于是生日,日生地,地生物。”(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此书涉及到的西学知识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光、电、声、化的自然科学常识、自然进化理论、人体生物解剖知识、天文地理新说和生物演化学说等。
与《康子内外篇》表达的哲学观念不同,稍后的《实理公法全书》(1891年后)则主要表达了康有为的社会政治学思想,而且更多的体现了西学的特征。
首先,康有为套用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试图突破传统中学解经说古繁琐的论证方式,从简单的“几何公理”出发,借助逻辑推理来重新解释人文社会问题。康有为通过“公理”“公法”的法则认定,“人类存在着固有的‘实理’,并断言只有符合这种‘实理’的‘公法’才是有益于人道之法。”[4](P202)
其次,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是该书主要的立论依据。“总论人类门”中说,“人有自主之权。”“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②据此,他为人类的未来设计了一套符合“实理”的“公法”制度,举凡夫妇、父母子女、师弟、君臣、长幼、朋友、礼仪、刑罚、教事、治事、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均纳入他所设计的“大同”理想社会之中。对此,丁伟志评论说:“康、梁‘新学’之得以标新立异,成一派新学,无论就其关于现实的变法改制的政见而言,还是就其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而言,它都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4](P203)
西学为康有为的学术文化体系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尽管如此,康之新学却不是西学的简单移植。《实理公法全书》虽然从表达形式和立论依据上不具有中学的痕迹,但它与《大同书》一样,在当时是未曾公诸于世的属于对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构想。可以说,在康有为的整个新学体系中,《实理公法全书》并没有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再则,《实理公法全书》所述虽然“大都来自他阅读西书后获的欧洲思想”,但对他的整个思想而言,“儒学和大乘佛学仍为其主要的灵感泉源。”[7](P121)而且,康有为在此“并不是要把西方价值注入中国传统,而是要抛弃一些中国价值于普及价值之外。”[7](P383)他所追求的既不是完全的西方价值,也不是传统的中国价值,而是超越中西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世界化”价值。
全面来看,对于康有为的新学体系而言,西学本身并不构成独立存在的完整体系,而只是在与中学的相互印证和相互解释中体现着自身的意义。《康子内外篇》“学术渊源比较复杂,内篇多从先秦诸子立论入手,又借鉴了明末清初的许多成果。外篇则吸取了老庄、易经、西方进化论、宇宙和地理学的观念,以此构成了他的基本思想理论体系。”(董士伟《康有为评传》)化西为中,以西释中,是康有为对于宇宙、社会、人生新的解释体系中的基本方式,故而在康有为的认识中,西学与中国传统之学,同样构成了他新的中学体系的历史依据或思想资料。一位美国学者说:
盖康氏自幼深爱孔学薰陶,先入为主。……其后旁览西书,虽多掇采,不过资以补充印证其所建造之孔学系统。非果舍己从人,欲逃儒以归于西学。[8](P687)
康有为对于自己创建的思想体系十分自负,把它说成是孔子大道的真正所在,而西学只是弘扬他所发现的“大道”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首先,在其后他完成的5部书中,(《礼运注》、《中庸注》、《孟子微》、《大学注》、《论语注》),代表了他重建儒学所下的努力,“更彰显了康以儒学为基础综罗佛学与西学,而自成一家之言的胸襟。”③在《孟子微》里,康有为将西学中的进化论与春秋三世说结合,形成了他新学体系中的历史进化论,从而也构成他政治变革中的主要理论依据。
其次,对于西方的民主平等观念,也是在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结合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康多次指出“平等”是孟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说“人人可为尧舜,乃孟子特义。令人人自主平等,乃太平大同之几,纳人人于太平世者也。”(《孟子微》:卷一)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道”,而这也正是真正的孔子“大道”即中学的根本所在。所以,康有为说:“独立自由之风,平等自主之义,立宪民主之法,孔子怀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为乱世发也。”(《孟子微》:卷一)
以“民权平等”的西学内容来注解孟子的“民本”,或者用孟子书的“国人”与西方的“市民”相比附,康有为这种在中西古今的思想资源里的牵强附会,虽然不足为训,但却凸显了他试图超越西学和中国旧学另创一种“不中不西”新学的努力。
“继传统引西学”是康有为“新学”建构的主要路径,同时也标示了西学在康之新学体系中的地位。在他的新目录学体系中,我们同样见到如此鲜明的特征。
《日本书目志》代表了康有为目录学方面的“新学”内容,是他新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该书目重在探求新知,共收录图书7780种,基本都是“日本近代所译‘泰西佳书’,‘加以新得’,即反映近代西方和日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成就的书籍”[16],《日本书目志》的著录体例已完全不同于旧学体例,“从著录书名、著者、著作方式,到载体形态都有大的创新”,而这一创新又明显来源于“欧美新的知识体系和图书分类体系”。其中,《图书馆管理法》和《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西学分类,构成了康有为新目录学的主要内容。但是,中学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也是其“作为书目立类和分类的依据”。在《日本书目志》中理学分类的设立,方技、类书等二级类的设立,体现了康氏对传统目录分类的某种继承。所以,“在中国目录学走向近代化的转型期,‘参采中西’是一种转型的必然蜕变过程。”[9]
“参采中西”既说明了康之新学的时代特征,也表明了西学在其新学中的基本地位。
梁启超是康有为新学体系中“一员最有力之大将也。”[10](P103)在戊戌前后旧时代与新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对于“青年思想上,则促起‘新学’之自觉”的学术文化运动,“康、梁实与有转移之力。”[10](P104)梁启超是唯一可与康有为并称的新学巨子。
作为比较,可以看出梁关于新学的文化构成与康大体相同,是“由五部分组成:儒家经典、中国历史、诸子哲学、新儒家道德哲学和西学”。尽管在智力教育方面梁认为西学是关键,但作为关注中国命运的学者,却必须将西学和中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西学只是这种结合意义上的“新学”的组成部分。所以,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梁启超一反常态地不去介绍西学的各种优点和作用,而是发出中学行将消亡的紧急警告。在此,梁的意图十分明确,引入西学不过是拯救中学的必要而有效的手段。“西方一些价值观对修身确实起过作用,并且相当程度地改变了梁的人格理想,但梁决没有完全失去对所有儒家道德价值观的信仰,尤其是那些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11](P112)周传儒曾总括当时中国的学术特点说:正是由于中国旧学齐兴并举的盛况和西方文明大量地传播,“这两种来源不同的知识,交流综合,汇成一代的新学问”。而梁启超“毅然改途,另治新学”的学术特征也与此时代特征一致,是“会通今古,贯串百家”“自成系统,自成一家之言”。[12]
对于康、梁而言,西学在其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固然有程度不同和侧重不同之分,但“参采中西”“会通古今”的基本地位和发展路向却完全一致。这其实也是当时中国所有新学家们共同遵守的学术文化原则。
三
西学构成了康、梁新学中的重要内容,并由此形成其新学之所以为“新”的一个不可忽缺的方面。但是,西学本身并不足以形成对于传承数千年中国“旧学”体系的致命威胁,尤其经过洋务运动的西学引入和甲午战败的时势刺激后,西学已经广为传播,即使是先前竭力反对西学的人们,也转而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这从湘绅王先谦、叶德辉们拼力反对“新学”而并不一味反对西学的立场中,可以得到历史的印证。
康有为的“新学”是对于二千年中国“旧学”的根本否定,而否定的力量并不直接源于西学,而是源于“中学”。对此,康有为自己十分清楚,他说:“仆言今古刘、朱之学相盛衰者,正以循环之运,穷则反本。方今正当今学宜复之时。气则有阴阳,世则有治乱,天道日变,异于旧则谓之新,仆所谓新者如此。”(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异于旧则谓之新”而不是异于“中”才谓之“新”,正是康有为对于自己创立的新学体系的民族性的基本定位。徒有“西学”非但并不构成康之新学的特征,而且也是他明确反对的一种文化偏向,他认为:“缘学者不知西学,则愚暗而不达时变;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所以,康有为对于西学的态度是“以西人之学艺政制,衡以孔子之学”,形成“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可收其用也”的新学模式。在具体的作法上,他坚持“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
当时,站在“旧学”立场上反对康之新学的朱一新,从学术文化的流变和源流上,对于康之“新学”的特征作过概括。他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
(一)诋讦古人,由疑经而疑圣。废《毛诗》、《左传》等古文经学经典,而欲代之以“《鲁》、《韩》之简篇残佚”,“《公》、《榖》之事实不详”之今文经学。如此,则于中国学术文化为害甚大,“若二千余载群焉相安之事忽欲纷更,时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5](P1032-1033)由此,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中学的精神支柱。
(二)康之新学杂糅诸说,任意取舍。“闻见杂博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诸庄;其兼爱无等也,取诸墨;其权实互用也,取诸释;”利于已见而取之,不利已见则弃之。“《尚书》当读者仅有二十八篇,余自《周易》、《仪礼》、《公》、《榖》、《论》、《孟》而外,皆当废弃。‘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势不得不问途于百家诸子”,以成“尊子轻经”之势。[5](P1045)
(三)托于素王改制,“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如此为学,与古人治学大为不同,古人“治经者,当以经治经,不当以己之意见治经。”而康学则“恣其胸臆,穿凿无理”,“适为毁弃‘六经’张本耳。”[5](P1044-1045)
从反对派攻击康之新学的侧重点来看,无论是坚执宋学的朱一新,还是学术门户更为复杂的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等湘绅名流,抑或是学综汉、宋的张之洞,都以持之有故的论证说明了从根本上“变乱”传统“圣学”的康、梁新学(或称之为“邪学”或“康学”)的要害不在西学方面,而恰在“中学”方面。对此,康有为本人也言之凿凿,称中国圣经因“刘歆之伪经,既造伪文,又伪钟鼎、伪简册以实之”。借此,“伪经之学”“实以古文为主”盛行于魏晋而流播于后世,致使孔子大义之学的“今学息灭废绝二千年。”[5](P1021-1024)基于此,康声称自己要“穷则反本”,申明孔子之学的真义所在,而其阐发孔子真义的新学的特征是:“求义理于宋、明之儒,以得其流别;求治乱、兴衰、制度沿革于史学,以得其贯通;兼涉外国政俗教治,讲求时务,以待措施;而一皆本之孔子大义以为断。”[5](P1024)这显然不能仅凭叶德辉一句“貌孔心夷”的诽谤之言,而断定康之新学的本质就是“西学”。
康有为多次陈述过“义理之学”、“史学”及“外国政俗教治”的西学是他新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因此,单凭西学自身并不能形成康之学术文化体系的内核,也无法建构起“新学”的基本框架。近代中国的新学,既是对于中国旧学的否定,同时也是旧学的蜕变和再生。“建构新学必须从固有文化中寻求生长点。……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竭力发掘古学,以期在古学复兴的基础上建构新文化。”[13]
对传承两千年的旧学体系产生根本性否定意义的学术文化力量,源于中学之内。对此,陈其泰作过比较清晰和有力的说明。他认为这种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始于嘉道之际,而其变化的原因则源于清代学术文化内部,“主要是:当考证学如日中天之时,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内部已有分化,后期的著名考证学者中,有的更明显地露出注重探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端倪;考证学派以外的学者,即‘乾嘉别派’,已对考证末流的烦琐学风作尖锐的批判,影响扩大;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公羊变革学说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成为进步学者用来观察国家民族命运和学术风尚的指导思想。以上四项的推动,成强大的‘合力’,终于冲开沉重坚实的旧堤坝,开创出学术的新局面。”[14]正是中学内部的这种否定力量发生发展的历史,恰好与西学的传播引入的历史相结合,共同成就了旧学体系的衰亡和新学体系的成长。康有为自己“也明白,如果不借助朝野一向奉为正统的儒家经典立论,创立‘新学’提倡维新的局面是无法打开的。康有为深以为幸的是,他找到了一种适宜他为自己‘新学’建构的学派、布道的学理,这就是今文经学。”[4](P204)
“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以《公羊》为基本内核的今文学,自古文学被奉为正统之学后,几乎“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唯古是从,重承袭轻创造,正好符合两千年来封建社会政治发展相对平缓的需求。清代占据学术文化正统地位的朴学,在哲学思想上信奉古文经学,“众多朴学家唯古是从,实际上有一种复古的历史观在起作用。”[14]但是,鸦片战争前后,时代剧变,民族命运要求打破现状,革除积弊,认识亘古未有之大变局,要求阐释变易、变革的思想体系就成为社会最迫切的需要。乾嘉年间由庄存与、刘逢禄次第发明出今文公羊学的“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后,经龚自珍、魏源的推动,遂发展为晚清反叛旧学的一股激流。“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在晚清社会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日亟的情势下,这一阐发变易改制的学说,“恰恰反映了这种时代需要,从而导致晚清时期公羊学盛行的新的历史性变化。”[15](P153)今文公羊学是既对正统旧学地位别树一帜,又具有儒家经典合法地位的思想学说,它的出现立即引起厌倦旧学向往新说的青年学子们的积极回应。吴荪轩评论当时的社会反响说:
康时讲学,遂宗《公羊》,大倡其孔子改制之说,每下一义,援引博治,穿贯群籍,几有六经皆我注脚之概。……一班少年,既震其声华,又钦其实学;所以圣人以一监生之资格,居然能领袖群伦,大坐其虎皮而讲学。[16]
要之,康在晚清讲今文经学,倡经世致用之说,树思想界解放之先声,二十年来维新改革之功,终当推为魁首。
因此,戊戌时期,构成康有为“新学”体系主要内容并且引起旧学派群起而攻之的学术文化,并不是主要来源于西学,而是来源于中学之内的今文公羊学。当然,西学的“民权平等说”也是旧学家们攻击的内容,但他们却把它放在今文公羊学的从属地位,如《翼教丛编·序》中说:
康有为人不足道,其学足以惑世。……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17]
今文公羊学的崛起,对旧学体系形成了致命的危胁,从而也引起旧学之士的拼力反对。虚湘父的《万木草堂忆旧》说:“先生……提倡今文真经,而排斥旧文伪经。……盖自郑康成说经,糅杂今古,故经之真伪,久已不能分辨。……此书初出,海内风行,各有翻印,凡五版。……然笃信许郑者,则大肆攻击。”(著书被议《虚湘夫万木草堂忆旧》.民国铅印本)戊戌前后,公羊学的盛行导致了晚清整个学术风气的转移,也造成了旧学衰亡的学术前提。张之洞在1903年所写《学术》诗云:“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前榛满路栽。”在自注中,张表明了他对晚清学风变迁感叹之所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张文襄公诗集》:卷四)
至于反对“新学”的守旧派们,对于公羊学说更是深恶痛绝,如叶德辉称:
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惑之。……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者,亦正蹈斯病。生已盗名,而欲使天下后世共趋于欺罔,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
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其书空言改制,有害于道。(《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卷六)
戊戌时期代表康有为的今文公羊学,同时也代表其“新学”思想的主要著作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问世立即引起了晚清思想界前所未有的震动,如梁启超所评论:
第一,学者所崇奉的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而真经之全部分又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
第二,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创一新殖民地。
第三,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谡“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在康有为所有的论著中,都未曾像《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那样,形成“思想界一大飓风也”的形势,并由此引起整个晚清学术文化界“其火山大喷发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的影响。这一源于中学之内的叛逆思想显然比之于以阐发西学为主的《实理公法全书》要大的多,因为它“忽树一帜”与旧学对抗,“此机一动,前人之所莫敢怀疑者,后人之乃竟起而疑之。……我国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但是,与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康有为早年也是深受旧学即古文经学的影响,“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他31岁前一直尊奉古文经学,并致力于考据之学,22岁时还著《何氏纠谬》,还曾设想编写《礼案》等。这些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就其思想转变的时间而言,从1879年开始,到1884年间,康有为已经厌倦了旧学,转而“渐收西学之书”,并在1885年至1887年间写作了《教学通议》、《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等包含了西学的著作。但直到1890年与今文经学家廖平“羊城之会”后,康才形成了完整的今文公羊学体系,于次年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并开始起草《孔子改制考》。从此,《春秋》公羊学在康有为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占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成为他“新学”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所以,梁启超说他是“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旧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对于康、廖相会及其学术思想之间的纠葛,学术界聚讼甚久,此处不作评论。但这一史实足以说明,“康有为之改宗今文经学是从1890年开始的。在此之前,他的经学思想还是古文经学派。”同时,这一史实还说明,“康氏‘新学’思想形成的过程是,接受西学影响而引起的思想变化在前,接受今文经学的影响而引起的思想变化在后”。[4](P206)显然,康有为创立“新学”体系时先“西学”后“今文学”的历史转化过程,至少可以证明单纯的西学引入,虽然可以扩展人们的视野,却并不足以形成对于传统“旧学”的根本性否定,否定“旧学”的思想武器,只能在本民族传统的学术文化资源中获取。而且,“西方观念的输入,还必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其接合点。”[15](P323)至少康有为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由嘉道年间渐次兴起的今文公羊学,不仅“发皇成为一种有深刻哲学思想体系作指导,有多种著作形成坚实基础的学问”。而且它对于正统“旧学”具有的反叛和挑战的本质特性,“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梁启超《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公羊学专讲“微言大义”的特点不但正好能容纳西方观念,而且它所具有的“变易性、政治性和可比附性,在康有为手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15](P305)正是在接纳西学的条件下,康有为突然折入中学的今文经学,并由此会通中西,“兼摄中外,陶铸涵泳,自成一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一位从折衷中西思想中从事儒学现代化伟业的思想家,也是一位从儒家新解释中努力调融中西思潮的学者。”④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8](P465)今文公羊学是内容复杂异义丛生的一种学说,它之所以在戊戌时期经康有为的阐发引起举世瞩目和学界震动,还在于他赋予传统今文公羊学以新的解释和内涵。这就使得在康有为的今文公羊学超越了同时代其他人的传统今文公羊学而具有了时代的价值。叶德辉就说:“清末有四人同讲公羊,王壬老(运)讲公羊,廖季平(平)讲公羊,康有为讲公羊,我也讲公羊,但我们各有各的公羊,内容绝不一样。”⑤康有为在公羊思想的基本原则即三统、三世和内外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修改,并将西学新识融会其中,从而跳出了今文学家法的狭窄天地,独成一个新的学术体系。
其一,将“改制”作为今文学中通三统的第一要义。通过改制的历史论述重塑孔子形象,认为孔子的伟大并不在于为后人详细规定改制内容,而首先是提出一种改制的思想。后世改制,应理解孔子微言大义所指,并加以发挥。以此为张本,“效法俄日”的改制,也是符合孔子精神的。
其二,把“三世说”与进化论相结合,形成新的历史发展观。传统三世说指有见世、有闻世、有传闻世,经龚自珍的发展成为所谓“治、乱、衰三世相承”的一种历史观。但康有为却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与三世说相融会,认为中国历史和整个人类历史都成为自然进化的一部分,进化的基本轨迹为从野蛮到文明,即从争战到和平、从贫穷到富足、从专制到民主。西方进化学说与三世说的有机结合,使传统三世观念获得新的生机,成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观。
其三,改变了“异内外”的自我中心观。传统今文学强调“异内外”和“夷夏大防”,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观和文化观。康有为在会通中西的文化建设中,认为西方文化是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他虽然坚持弘扬孔教,却并不主张以孔教同化基督教文化,在他看来,今文学异内外所指文化之异已不再具有高下的含义,而只归结为文化种类的不同。[6](P74-76)
通过对传统今文公羊学三统说、三世说和内外观的重新阐释,康有为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这既是一个西学中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传统中学的近代化(由旧学转化为新学)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就标志着康之“新学”体系的基本完成。
今文公羊学为康有为的新学体系提供了独特的表达形式,而且也使他独悟的西学新理落实在中学的根基之上。因而,离开了中学的今文公羊学,康有为的新学体系就不可能形成。“把西学新知附会到《公羊》派今文经学的传统文化观上去,于是康氏‘新学’有了新装。一种中西融合的、形式奇特的‘新学’,才以较为完备的形态应运问世了。”[4](P208)
收稿日期:2006-09-11
注释:
①丁伟志在中西体用之间第191页中谓.“康、梁‘新学’之新,不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突破‘中体西用’框架,援西学改造中学;二、兴起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三、复活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精神,改革治学宗旨,整顿学风流弊。”
②实理公法全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③黄俊杰.从孟子微看康有为对中西思想的调融.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④黄俊杰.从孟子微看康有为对中西思想的调融.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⑤左舜生.游戏召祸的叶德辉.万竹楼随笔.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标签:康有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清代学术概论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学堂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